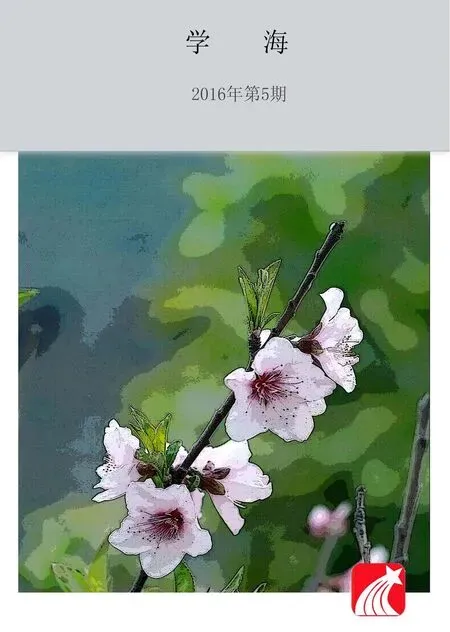帝国、教会与上帝*——但丁的“二元论”及其理论困境
吴功青
帝国、教会与上帝*
——但丁的“二元论”及其理论困境
吴功青
内容提要在《帝制论》中,但丁构建了一个囊括一切人口、土地和民族的普世帝国,并将其权威直接诉诸上帝,赋予帝国和教会同等的地位。但丁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但丁自身思想的限制,这一“二元论”主张不可避免地陷入诸多理论困境。首先,但丁虽然批判了教皇和教会,但他仍然高度认可它们的职权。其次,在但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具有相比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以上两点,为教会对帝国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后,但丁虽然把帝国的权威完全诉诸上帝,但上帝的意志又不可知,帝国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世俗政治即便独立于教会,但它无从建立自身的确定性。只有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浪潮中,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才能一步步实现。
二元论政治自主世俗权力精神权力命运
九世纪以降,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逐渐上升,开始与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分庭抗礼,成为主导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核心因素。在教权论者看来,教会或者同时掌管“两把剑(two swords)”①,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或者虽然只具有精神权力,但由于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②不论哪种情况,国家都受教会支配。教权论者的这一逻辑,在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Unam Sanctam)中达到了顶峰:精神权力不仅造就了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当世俗权力出错时,教会还有权审判它。③对此,王权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路加福音》中的两把剑明确表明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性(dualitas)。因此,精神权力不能干涉世俗权力,教皇也无权控制皇帝,而应摆脱偏见、通力合作。不难看出,王权论者的“二元论”主张,意在谋取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分离,为的是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autonomy)。④从亨利四世一直到红胡子腓特烈、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七世及其拥护者,“二元论”的声音一直在持续地回荡。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⑤,但丁对世俗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故乡佛罗伦萨的失败,还是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流亡,都让他对政治产生了异常痛苦和深刻的感受。然而,但丁在“地上之城”中的这些遭遇,并没有让他像奥古斯丁那样,彻底否弃世俗政治的价值。⑥相反,受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但丁坚持认为:人类的理性仍然有向善的潜能。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有它独立的“善”的目的。因此,“地上之城”尽管不完美,但它毕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具有独立的神圣意义。⑦从这一立论出发,但丁构造了他心中的最佳政制——一个普世的帝国(universale imperium)。在他看来,人类社会(humana civilitas)唯有在一个强力的皇帝的指引下,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普世帝国,不仅符合神意,而且符合自然正当,因此具有和教会同样的合法性。可是,即便如此,但丁仍然必须回答摆在所有“二元论”者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帝国虽然合法,教会也同样合法;那么,帝国究竟如何才能独立于教会,实现真正的政治自主呢?
帝国与教会:两重目的与两种权力
如上,教权论者和王权论者的争论,要害在于如何理解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等级秩序。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权论者能够占据理论上的优势,根本上在于他们通过圣经的解释,确立了精神权力相对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但丁意识到,一旦世俗权力被认为来自于精神权力,皇帝就理所当然地屈服于教皇,国家就理所当然地屈服于教会。要想真正颠覆教权者的这一逻辑,就必须从根本上斩断政治权力的教会起源,直接诉诸于上帝。于是,对于教皇和教会的性质及其权限的理解,便成为但丁论证政治自主性的关键一环。
教权论者之所以笃信教权高于王权,是因为他们认定,上帝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而彼得又将它传给他的继承人。彼得作为上帝的代理人(vicarius),和上帝一样,不仅具有掌管教会事务的权力,而且具有掌管世俗事务的权力。而但丁认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的联合体,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掌管世俗权力。但丁指出:“教会的形式不是别的,正是基督一生的言行”(“Forma autem Ecclesie nichil aliud est quam vita Cristi”,Monarchia, 3:15)。但丁注意到,基督在生前已经当着彼拉多的面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明确放弃了世俗权力。虽然根据《诗篇》的记载“海洋是他造,海洋属于他”(《诗篇》94:5),上帝并非没有统治世界的权能;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教会做了榜样,不再关心世俗政治。既如此,教会就应该言行一致,主动放弃自己并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的、任命世俗君主的权力,回到“基督一生的言行”这一纯粹属灵的形式之中。
归根结底,教皇掌管的精神权力和皇帝掌管的世俗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应当彼此分离。这一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于人类的两重性。但丁认为,“在万物之中,唯有人类处于可朽与不朽之间”(Monarchia,3:16)。前者对应的是人的身体,后者对应的是人的灵魂。因为人的这种两重性,人类的存在就有了两重目的(duplex finis):一个是与身体对应的尘世幸福(beatitudo terrestris),是自然的;一个与灵魂对应的永生幸福(beatitudo coelestis),只有依靠恩典才能成全。在但丁看来,尘世幸福和永生幸福同是人的最终目的(ultimum finem),都值得人去追求。⑧相应地,两重目的必须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尘世的幸福,需要遵从哲学的教导(phylosofica documenta),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道德和理智德性(virtutes morales et intellectuales)来完成;而永生的幸福,则要依据我们的神学德性,即信、望、爱方能实现。不过,由于贪欲,人类变成了脱缰的野马,非经骑手的控制无法走上正途。上帝给人类分派的两个骑手,一个是教皇,另一个是普世帝国的皇帝。前者通过启示(revelata)引导人类走向永生的幸福,后者利用哲学的教导引领人类走向尘世的幸福。但丁的这一思想谱系,可以由吉尔松绘制的图表来说明⑨:
人
可朽性不朽性
尘世的幸福永恒的幸福
自然恩典
哲学教导灵性教导
自然德性神学德性
哲学家的权威启示
皇帝教皇
根据两重目的和两种权力的划分,但丁有力地证实:普世帝国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上帝。上帝是教会权力的来源,也是世俗权力的来源。帝国和教会一样,二者是平行、独立而平等的权威。帝国既无权干涉教会,教会也无权干涉帝国。由此一来,帝国所代表的世俗权力便排除了教会的干扰,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但丁的这一“二元论”逻辑,可拟简图如下:
上帝
教会国家
教皇皇帝
然而,令人相当困惑的是,对于自己的“二元论”主张,但丁似乎有所犹疑。在《帝制论》的末段,但丁总结完自己的观点后,突然语焉不详地说道,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即皇帝的权威究竟直接来自于上帝还是其代理人(教皇)的问题不能从字面上理解(sic stricte recipienda est),以至于认为罗马皇帝从不会服从于教皇。“毕竟,可朽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要听从于不朽的幸福。因此,恺撒之敬重彼得,犹如长子敬重父亲”(Monarchia,3:16)。寥寥数言,一改此前的论断,不再谈论两种权威的平等,转而肯定皇帝对教皇的服从。如果是这样,但丁此前的“二元论”又有何意义呢?
正是由于《帝制论》末节的这一表述,有些学者试图认定:但丁延迟地否定了此前的主张。⑩不过,仅从文本上说,即便但丁肯定了皇帝对教皇的敬重,也不能推导出皇帝在政治上对教皇的服从。因为,就在说完上面这几句话后,但丁在《帝制论》的结尾又强调说,“他(皇帝)只依据上帝统治世界,因为上帝是灵性事务和世俗事务的统治者”(“cui ab Illo solo prefectus est, qui est omnium spiritualium et temporalium gubernator”,Monarchia,3:15)根据这一论述,我们仍然可以推断:皇帝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上帝,不受教皇的约束。也就是说,皇帝对教皇的敬重不构成皇帝在权力上的服从,二者的权威还是平等的。

职权:教皇与教会
就《地狱篇》而言,但丁控诉教会和教皇腐败的诗句屡见不鲜。第一歌中,但丁以母狼的贪婪来比喻教会,为整部《神曲》中教会的腐败形象打下了基调。第十四歌中,维吉尔借助克里特岛的神话告诉但丁,巨人的塑像从头到脚逐渐堕落,仿佛人类的历史逐渐堕落;支撑这位巨人的右脚即教会由陶土做成,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以此隐喻教会的腐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同样,对于教会的领袖教皇,但丁亦极尽讽刺和挖苦。在地狱的外围,那“由于怯懦而放弃大位”的教皇切里斯迪诺五世随同其他卑怯的灵魂一起,跟着一面大旗涌动,赤身裸体被牛虻和黄蜂蛰来蛰去(第三歌);在地狱的第八层第三囊中,教皇尼古拉三世和即将到来的卜尼法斯八世因为买卖圣职,身子倒插在空洞里,脚掌被火焰灼烧(第十九歌)。但丁的这些安排,表达了他对教会和教皇的严厉批判。在但丁心中,二者是引导人类走向永恒幸福的指南针,但由于贪婪和腐败,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初的本质,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变得岌岌可危。这样看来,《神曲》似乎构成了对《帝制论》中“二元论”逻辑的佐证:既然教会因而腐败而遭受责难,既然教皇也不再像教权论那样说的具有无上的权威,甚至因为腐败不得不在地狱中受罚;那么,教会的权威如何能高于国家,教皇的权力又如何能够高于皇帝的权力呢?


如果说,《地狱篇》中对尼古拉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等教皇的安排中隐含了但丁对对教皇职权的批评和限定,那么,就整部《地狱篇》来说,但丁还是给教皇的职权留下大量的空间。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第一例,在灵泊狱中,悬浮着众多没有受洗的婴儿和男女。但丁说,“他们并没有犯罪;如果他们是有功德的,那也不够,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洗礼,而洗礼是你所信奉的宗教之门”(《地狱篇》第四歌)。洗礼作为天主教教会规定的“七大圣事”之一,是一个人是否得救的根本前提。这种因为人没有受洗而被罚入地狱的权力无疑来自于教会,并最终归于教皇。第二例,在第六层地狱中,住着很多异端信徒和伊壁鸠鲁主义信徒。他们因为生前犯下异端之罪,死后被置入发烫的石棺中被火焰烘烤。而异端之为异端,无非在于正统教会的裁判,这一裁判权的拥有者,正是教皇(《地狱篇》第十歌)。第三例,在地狱第八层第九囊,但丁以“分裂教会”为名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和阿里放进地狱,遭受身体分裂之苦,其初衷,乃是为了维护基督教教会的统一(《地狱篇》第二十八歌)。这自然意味着,基督徒要在一个统一的教会下,接受唯一教皇的领导。

皇帝:权能、德性与信仰

作为皇帝,他首先需要拥有权能(potestas,力量)。但丁所构想的普世帝国,是将所有人口、土地和民族都囊括在内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普世帝国的统治者,皇帝的目的是伸张正义,维持和平,因此不得不具备强大的权能。但丁之所以对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的许多君主不满,而唯独对亨利七世情有独钟,根本上是因为在他心中,亨利七世是一个颇有权能的人,这只“不以土地也不以金钱,而以智慧、爱和美德为食”的猎犬,才是“衰微的意大利的救星”(《地狱篇》第一歌)。仅仅有权能当然还不够,理想的皇帝还要有统一世界的强大意志。这样的人,必须贪欲最少、最富正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勇于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
皇帝仅仅有权能和意志还不够,还需要德性。在《帝制论》中,但丁明确要求皇帝具有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virtutes);在《地狱篇》中,但丁用诗歌的形式,将这一体系更为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罪分为不节制、恶意与放纵三种。但丁根据这一划分,将地狱分成九层,其中二到五层分别为邪淫、贪食、贪财和易怒罪;第七层为暴力罪,八至九层为恶意之罪。不难看出,在但丁的体系中,凡是犯下这三种罪的人,即便他具备皇帝所需要的强大权能和意志,也要在地狱中受罚。无论是因为邪淫罪而被狂风吹得忽上忽下的苏丹国王赛蜜拉米斯(《地狱篇》第五歌),还是因为阴谋诡计而在火焰中受苦的奥德修斯(《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他们都没有因为自己的权能而升上天国。特别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即便生前建造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一个最接近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死后也要因为“杀人流血、掠夺臣民财产”的暴力伤害他人身体和财产之罪而在血河中受苦(《地狱篇》第十二歌)。这就说明,仅仅具有权能而不具有德性的人,死后无法进天国。



归根结底,在中世纪时代,“永生的幸福”还是比“尘世的幸福”更为重要,“可朽的幸福在某方面要听从于不朽的幸福”。在《帝制论》中,但丁虽然给出了一个帝国和教会分离的“二元论”体系,但在《神曲》中,但丁却向我们揭示:只有依赖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普世帝国和皇帝的作用,能够帮助人在“地上之城”获得幸福,但它不能帮助一个人进入“上帝之城”。但丁虽然也说,“尘世的幸福”和“永生的幸福”同样重要,都是人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和救赎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还是比“尘世的幸福”更重要,因此精神权力仍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优先性。虽然但丁对于精神权力进行了严厉的限制,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认可,保留了教皇和教会相当大的职权。结果,但丁虽然强调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和平等,但他仍然无法彻底清除精神权力凭借它的优先性,对世俗权力形成的干扰。
帝国、上帝与命运

然而,问题在于,作为实现“尘世的幸福”的普世帝国,它本身是否可能?虽然但丁强调,罗马帝国作为普世帝国的原型,曾经受到神意的保护(《帝制论》第二卷)。但是,新的普世帝国能否实现,何时实现,是否为上帝庇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理论上,普世帝国具有深刻的神学基础,具有和普世教会一样的合法性,但这种神圣性不足以解决普世帝国作为世俗政治在现实中遭遇的困难。普世帝国的未来,最终还是靠人类自己。只有当人类社会有了结为帝国的自由意志,只有当具有皇帝潜能的君主们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运用自由意志积极进取,克服现实的困难,普世帝国方有实现的可能。

但是,自由意志在心灵中的这种作用仅限于人德性上的成全,本身并不能确保世俗政治的成功,更无法确保普世帝国的实现。世俗政治成功与否,并非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决定,而是取决于命运(fortuna)。关于命运,但丁在《地狱篇》中说:
“现在我要让你接受我关于命运女神的看法。智慧超越一切者创造者创造了诸天,并且给它们指派了推动者,使每一部分的光反射到每一相应的部分,把光分配得均匀。同样,他也给世上的荣华指定了一位女总管和领导者,她及时把虚幻的荣华从一个民族转移给另一个民族,从一个家族转移给另一个家族,人的智慧无法加以阻挠;所以一个民族就统治,另一个民族就衰微,都是根据她的判断而定,这种判断就像早里的蛇似的,为人的眼睛所不能见。你们的智慧不能抗拒她:她预见,判断并且如同其他的神执行各自的职务一样,执行她的职务。她的变化无尽无休,必然性迫使她行动迅速;因此,就常常轮到一些人经历命运变化。”(《地狱篇》第七歌)


然而,正如命运女神的变化我们无从前知,上帝的意志我们亦无法前知。受中世纪晚期意志论的影响,但丁相信:上帝的意志是彻底自由的,人类永远无法测度。上帝意志的这种不确定表现在世俗政治上,就是“一个民族就统治,另一个民族就衰微”,“变化无尽无休”并且“为人的眼睛所不见”。这实际上意味着,普世帝国最后由谁统治,能否保持稳固,是一件人类永远无法确定的事情。诚然,人类虽然可以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但它的这种力量远远不足以决定自身,特别是世俗政治的命运。帝国最终能否实现,还在于神意(Providentia),在于上帝不可知的意志。由此,世俗政治即便能从教会的影响中独立出来,但由于它与上帝的这种神学关联,也使得它最终无法获得自身的确定性。
总 结
在《帝制论》中,但丁从人类生活的两重目的出发,清晰地划分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试图将国家从教会中分离出来。在但丁看来,国家和教会一样,其权力都是来自于上帝。因此,国家的世俗权力和教会的精神权力一样,具有独立而平等的权威。但丁的这一“二元论”努力,旨在排除教会对于国家的影响,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但是,我们注意到,但丁在批评作为个人的教皇的同时,仍然高度肯定了教皇的职权,给教会留下诸多的裁判权,从而为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埋下了隐患。
在《神曲》中,但丁基于中世纪的信仰和救赎体系,肯定“永生的幸福”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优先于世俗权力,客观上为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提示我们,世俗政治要想彻底摆脱精神权力的影响,必须从根本上肯定“尘世的幸福”与“永生的幸福”同等的价值,赋予“尘世的幸福”以同样的神圣性(文艺复兴);必须将君主自身的能力与德性分开,消除信仰对世俗君主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必须从根本上斩断教会对于精神权力的垄断,祛除仪式在人救赎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将人是否得救的重心从教会转移到灵魂和上帝的内在关联中来(新教改革)。
最后,但丁将世俗权力直接追溯至上帝的做法,一方面固然限制了精神权力对世俗权力的干扰,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世俗政治完全为上帝的意志所操控,无法获得自身的确定性。但丁的困境启示我们,世俗政治要想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必须从根本上脱离神学政治的逻辑,将“君权神授”下的世俗政治从上帝之光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将政治变成属人的政治(霍布斯),通过人的操作来实现的政治(契约论)。诚然,一个纯粹世俗的政治其自主性是否可能、有何困难,这是现代政治哲学需要共同面对的主题。无论如何,在但丁对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中世纪政治思想家的伟大贡献,看到了他的局限,以及他为现代政治革命开创的诸种可能。
①“两把剑”见于圣经《约翰福音》18:11,《马太福音》26:52;在中世纪政治思想理论中,“两把剑”常常用来比喻两种权力。
②有关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争论的细节可参考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第十四章,“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第510-578页。
③《一圣通谕》说,“确定有两种司法权——灵性的和世俗的。教皇首要地拥有灵性司法权——它由基督授予彼得以及彼得的继承者教皇;皇帝和其他的国王们拥有世俗司法权。然而,教皇也有权对所有‘因罪的原因’而发生的世俗事件进行管辖和审判……因此,世俗司法权也属于教皇,他是基督和彼得的代理人。”
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但丁以及中世纪的王权论者来说,世俗政治的自主性仅仅表现在世俗政治不受教会权力的干扰,而非像现代哲人如马基雅维利那样,要求世俗政治完全脱离上帝的权威,成为完全属人的政治,实现彻底的自主。不过,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分离,完全属人的政治也绝不可能。而且,就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这点来说,也要等现代政治哲学的图景中才能彻底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革命对政治的自主性诉求乃是但丁以及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逻辑的进一步深化。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将但丁的“二元论”主张纳入到中世纪-近代对政治自主性诉求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有关中世纪-近代政治革命种两种权力斗争的历史线索,特别参考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的“前言”部分,三联书店,2012年,第1-13页。
⑤在但丁的诸多研究者,吉尔松最为完整地揭示了但丁的哲学家身份,见Gilson, Dante The Philosopher,Translated by David Moore, London: Sheed & Ward, 1948.
⑥有关奥古斯丁对“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态度,特别参考吴飞《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于西方文明的终结》的导论部分“奥古斯丁与罗马”,三联书店,2013年,第1-31页。
⑦朱振宇:《但丁的“世界帝国”:在自然正义与末世异象之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8日。
⑧正如吉尔松指出的,虽然在《论君主制》(De regimine principum)中,托马斯比起中世纪的其他神学家更多地肯定了人自然目的的正当性。但他仍然认为,自然目的不构成人的最终目的,人在此世的目的只有与死后生活的目的相连才值得被追求。因此,永恒的幸福才是人唯一的最终目的。Gilson, Dante The Philosopher, pp.192-193.
⑨Gilson, Dante The Philosopher, p.197.
⑩见J.Rivirre, Le problème d’Eglise et de l’Etat au temps de Philippe de Bel, Paris, 1926, p.338,Bellarmin为这种做法负责, G. Manacorda在与G.Gentile的论战中也持这一立场。













〔责任编辑:成婧〕
吴功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wugongqing82@gmail.com。北京,100872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文艺复兴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项目号:14XNJ02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