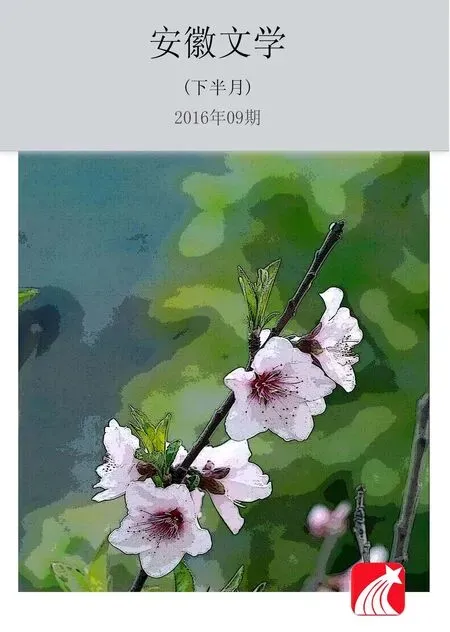论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建构及其成因
——以《离骚》与《渔父》为代表
陈素萍
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论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建构及其成因
——以《离骚》与《渔父》为代表
陈素萍
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诗贵意象”,屈原在创作中借以女性身份出现的“美人”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渔父”构建了一个两性人物意象系统,从而表达其喜怒哀乐、承载其美政理想。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是当时楚地巫文化女性始祖崇拜心理、儒家“忠君”意识和道家趋道思想共同调和的产物。
屈原 两性人物意象系统 美人 渔父 美政
所谓“意象”,是客体与主体、物象与情意相契合的结果。“诗贵意象”,诗人们往往借象达意、借象传情,意象的运用可以使得诗中情感的表达更形象生动、更具体充分。
屈原——中国诗歌领域浪漫传统的开创者,其在创作作品时把客体与主体、景和情融合起来,形成一系列意象,达到“寄情于物”的效果。关于其作品,历来多有争议。现今保留下来的最早完整注本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认为屈原作品有25篇,即《九歌》11篇、《离骚》1篇、《九章》9篇、《天问》1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①笔者认为,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离作者年代最近的古人说法也许更可信。故此文将建立在王逸结论的基础上,主要结合《离骚》与《渔父》两篇作品来展开论述。
一、屈原作品中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建构
屈原作品的情感基调是忧愤,充满着炽烈的爱国情感,蕴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表现了一种坚持人格完美的崇高精神,抒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壮烈悲伤。这种感情基调是通过构建一个两性人物意象系统来表达:以女性身份出现的“美人”意象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渔父”意象。不管是“美人”意象的幽怨、忠贞、美好,还是“渔父”意象的磊落、明智、超脱,都承载着屈原被人误解的悲愤之情、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情、“美政”实现的期盼之情、理想破灭的忧伤之情。在屈原的创作中,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达到浑然一体,凝成了具有鲜明诗人个性和荆楚文化特色的“美人”意象与“渔父”意象。读者凭借其“意象”的引发,可以感受到诗人心灵挣扎的痛苦、生命求索的迷茫、美政实现的期盼。
(一)美好、忠贞、幽怨的“美人”
在屈原作品中,“美人”一词屡次出现。《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抽思》中有“与美人之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思美人》中有“思美人兮,揽涕而竚眙。”《河伯》中有“送美人兮南浦。”《少司命》中有“满堂兮美人”、“望美人兮未来”②。这些“美人”意象,被概括为或指君王,或喻作者,或指贤臣。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曰:“……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臣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③朱熹《楚辞集注》认为:“美人,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④笔者认为,“美人”意象表现的是屈原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对“美政”理想的期盼。
《离骚》,是解读屈原内心情感的一扇窗户。《离骚》中有“求女”的情节,先求宓妃、后求有娀之佚女、再求有虞之二女,但皆以失败而告终。朱熹《楚辞集注》和李陈玉《楚辞笺注》都认为求女即求君。屈原为实现美政理想希望跟楚王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期盼楚王相信他、任用他,但周围有小人的蒙蔽,楚王又糊涂不觉悟,还将自己流放,于是用这样的情节宣泄内心的幽怨,表达自己的期盼。
其实,“美人”也好,“女”也好,早已不是指代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一个特定的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诗歌意象和审美符号。说以“美人”指代“贤君”、“贤臣”,最终也不过是表达诗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屈原本是楚国王族的后代,本打算凭着聪明才智像伊尹、傅说等贤臣一样被明君赏识去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却因当时的楚王听信谗言而被疏远,楚王也因此最终被秦国俘虏,客死他乡,自食恶果。屈原推崇尧舜、汤禹、文王、武王等前贤明君的先王之道,劝导楚王举贤授能,知人善任,认为这样就能开辟出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完成楚国一统天下的霸业,实现“美政”。“美政”的实行,其核心因素是“美人”,明君起主导作用,贤臣是有力保障。屈原以对“美人”的赞美表达对“美政”的期盼,对“明君”的向往,对“贤士”的期待。“美人”是美好的代名词,是“美政”的承载物。
(二)磊落、明智、超脱的“渔父”
在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备受青睐,成为一个具有深厚内蕴的文化符号。“渔父”形象最早出现在《庄子·渔父》中,但真正使“渔父”变成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意象则要归功于屈原的《楚辞·渔父》。
《楚辞·渔父》中有两个形象:坚定执着的屈原、与世推移的“渔父”。很多学者认为此篇章中的主要人物是屈原,渔父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用“与世推移”的思想反衬屈原“激浊扬清”形象的执着高洁,以此来赞扬屈原宁折不弯的伟大志节;或认为渔父的存在是为了点化屈原,劝导屈原不要过分执着以求全身保命,是一位高蹈遁世的隐士高人;或认为“渔父”的存在是为了展现屈原激烈冲突的矛盾内心,是屈原的“分身立言”的另一个声音。
笔者认为,“渔父”的存在不是映衬屈原的反面形象,也不是展现屈原“分身立言”的另一个自我,而是诗人美好理想的一种表达。“渔父”的形象是正面的被歌颂的主要人物。首先,《楚辞·渔父》篇以“渔父”命名,“渔父”在作品中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被侧重塑造的主要人物。因为根据一般的创作规律,如果用人物做文章题目,此人物往往属于被称颂的主要人物或者是文本中被侧重塑造的主要人物。其次,从甲骨文“父”的形状看,像极了一个手持石斧之人,石斧代表着勇敢威猛、力量强大,后来“父”就被引申为值得敬重的人,同“甫”,指“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如田父,渔父。”(《辞海》)。老年男子历经世事沧桑,变得智慧、清醒、隐忍、超脱,不同于打鱼的渔翁、渔夫,故以“渔父”称之。再次,相比较于颜容憔悴的屈原,文中“渔父”的外貌是丑是美虽不得而知,但其言谈表现了渔父的清醒、随意与洒脱。“渔父”引用圣人“与世推移”的态度,对屈原进行劝慰,看似妥协的消极避世之词,实际是用圣人的思想展现“渔父”看透世情、直面困难、珍惜生命、勇敢地有操守地生活的人生态度。当屈原坚持己见时,他也不急不恼,而是莞尔一笑、鼓枻而歌。此笑既非讥笑,也非傻笑,而是看透世事、了悟人生的智者之笑,表现出渔父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豁达磊落的品性。此歌既非悠闲之语,也非嘲笑之声,实乃悲慨哀鸣之音,是历经波折与坎坷后沉淀于心中不可言说的无奈苦痛。
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美政无法实现时,现实的路也许只有两条,或被外部环境压迫,向某些政治淫威投降,改易节行,奴颜婢膝;或愤然抗争,毅然赴死。前者为很多人所不屑,后者方式过于激烈会令生命岌岌可危,难为所有人所师法,甚至也于事无补。现实的状况是如此的艰难与难以改变,于是屈原便会将希望寄托于美好的理想中。隐迹山川之中的“渔父”,远离了昏庸的皇帝、腐朽的朝廷,过得好似闲适、旷达、恬淡、磊落,既可舍弃屈原的刚烈,但也可保留屈原的正直;既可坚守道德原则,也可顺势而行,待机而动。“渔父”其实是对现实状态有清醒认识、对未来人生有准确定位的智者。他懂得,仅有一次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面对黑白颠倒的社会,慷慨赴死,葬身鱼腹,虽然可以表达对君主的赤胆忠贞,但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毁灭。于是在“水清”时“濯缨”、“水浊”时“濯足”,其实这是一种隐忍的无言反抗,是一种聪慧的巧妙战斗,提供的是另一种人生可能。“渔父”的隐匿与智慧抒发着屈原的苦闷,寄托着屈原的希望,也成为后来知识分子心中美的化身,理想表达的出口。
二、屈原建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成因
屈原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同时寄托在代表着美好的美丽、智慧、忠贞的“美人”以及明智、旷达、磊落的“渔父”身上,从而建构了一个承载其忧愤之情和美政理想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反映出屈原对残酷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奸臣小人的满腔愤怒,对明君贤臣的无限期盼,对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的建构是屈原思想中楚地巫文化女性始祖崇拜心理、儒家“忠君”意识和道家“虚己以游世”趋道思想之间矛盾调和的产物。
(一)“美人”意象:楚地巫文化中女性始祖崇拜心理的表现
“美人”可以使我们追溯到母系社会。屈原自称“高阳苗裔”,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高阳即母系时代的神女高唐。于是,神女与美在诗人屈原的无意识里就这样合二而一,“美人”意象隐含有母系氏族女性首领以及女巫的影子,她是最高的无与伦比的美的化身。
据史载,楚乃华夏族后裔,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南迁至荆地。商朝末年,因楚人首领鬻熊灭商有功,其曾孙熊绎被周天子封于荆楚,居丹阳,楚国始建,也常被称为“荆”、“楚”、“荆楚”、“荆蛮”、“楚蛮”等。“楚,叢木,一名荆也。”(《说文解字》)“楚”、“荆”合用就是指满是草木的僻远荒凉之地。
蛮荒之域的楚地,巫风昌盛,君王百姓都虔信不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的楚地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力量渺小微弱。在面对巨大的未知威胁时,便会求助于力大无穷的神袛,希望他们能够赐予力量和勇气,降临福祉,于是由巫师主持的各种各样的祭神祀鬼的巫术仪式就产生了。“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⑤”巫者就是用舞蹈的方式请神降神且可与神相通之女人即美人。
巫者最初为什么应由女性担当呢?因为巫产生于认识水平不高的蒙昧时代。那时正值“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制时期,女性天然地享有最高威望,占据社会中心位置,担任氏族的首领、酋长。首领、酋长需尽全力维系氏族的生存与团结,维护氏族成员的利益。为全族人求神祈福的重大任务自然也由女性首领和酋长去承担。最初只有“女巫”,后来渐渐才有男巫,即“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昭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⑥《国语·楚语下》明确指出巫师要有德行、有智慧、有能力、有学识,只有这样才能与神相交、扮神、迎神、娱神、送神。氏族女首领或女酋长是由民主产生的,一般都是氏族当中深受群众爱戴的能人与圣人,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兼任巫师的最理想人选,即女巫师。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表现的正是一个女巫在龙、凤的引导下执行巫术的场景。由此可见,最初的巫术活动应该主要由女性来主持。
虽然屈原所处的楚国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当时楚国周边的很多地区处在母系制时代。对于威望无比的女性始祖的崇拜之风,对于神通广大的女巫的敬仰之情,自然会影响到巫风盛行的南楚,也会影响到主管祭祀事宜的屈原,使得他不知不觉对女性的美充满了尊敬与爱慕,于是把“美人”当成贤臣明君,当成“美政”的化身,给予强烈的期盼。
(二)“渔父”意象:儒道思想调和的产物
“渔父”意象是儒家“忠君”意识的体现,也是道家全真保性观念的表达。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各派思想既相互融合,又相互斗争,其中尤以儒道两家为甚,但社会思潮中并没有尊儒抑道或尊道抑儒的倾向。创作于此时期的《渔父》是儒道二家奇妙融合的结果。
屈原在《离骚》、《渔父》等篇章中体现出来的忧国爱民、上下求索、舍生取义等精神都较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和执著精神。《渔父》篇尾的《沧浪歌》更是与儒家思想相辉映。在《孟子·离娄上》中写道:“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⑦虽然《沧浪歌》和《孟子》中的思想旨趣不完全一样,但颇有姜子牙隐忍待时的味道,也暗含着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⑧的训诫。
面对社会的黑暗,道家大多不积极人世,但也不能说是消极避世,他们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往往怀瑾握瑜,韬光养晦。屈原笔下的“渔父”就是这样的。寄身青山绿水中的“渔父”并不是完全不问世事,只知嬉笑打闹,陶冶性情,反而往往是天下大事了然于心,天文地理无所不晓。他们对时政有着清醒的认识,能世事洞明,懂得采用变通保存实力,在坚守道德准则的前提下待时而动,完成抱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智者、真正的勇者,“渔父”身份其实是在昏君当道、馋邪得意的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掩饰,一种观察,一种隐忍,一种期待。“渔父”的思想是儒道互补的结果,包含出世与入世两方面的特质,恰好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的行为规则。
“渔父”的存在更是一种理想和期盼。“渔父”是一位智者,世事洞明,任云卷云舒,于静默中保全自己,为的也许是于运动中实现治世抱负。“遁隐林泽,垂钓江滨”只是一种聪明的处世方式,一旦等到政治清明,“水清”之时,也许被“举贤而授能”,他们又可以焕发出无穷的力量,成为帮助君主实现美政的得力助手。历史上确实早有“渔父”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君王的重视,实现价值追求,这个“渔父”即是姜太公吕尚。《吕氏春秋》中记录了有关姜太公渭水直钩垂钓遇文王,后助武王伐纣灭商成就霸业的故事。姜太公的故事,体现了待时而动的儒家之道。“渔父”也成了坐看云卷云舒的隐士代名词,表现出来的冷静、镇定、旷达、磊落,凝结成了不断被人称颂的“渔父”精神。“渔父”这个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代号,而成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曲折表达。一钓竿,一轻舟,一渔父,潇洒、随意、闲适,看似看淡纷繁尘世,其实深藏智慧与抱负,“渔父”的状态其实是在儒与道、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着的中国古代文人们用以慰藉心灵苦痛的临时避难所,是理想重启的休憩地。
三、结语
“美人”的幽怨和美好表达着屈原对“美政”的期盼,对明君贤士的向往;“渔父”的隐匿与智慧抒发着屈原的苦闷,寄托着屈原的希望。屈原在其创作中借以女性身份出现的“美人”意象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渔父”意象来构建一个两性人物意象系统,以此来抒发其仕途失意的苦闷心情,表达其清高而伟大的孤独情感,体现其高洁伟大的美好人格,寄托其呕心沥血的“美政”思想。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是当时楚地巫文化女性始祖崇拜心理、儒家“忠君”意识和道家趋道思想之间矛盾调和的产物。
注释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②楚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③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⑤廖春水.浅说我国古代巫觋及其影响[J].魅力中国,2011(3).
⑥姜英辉.秦汉时期的巫祝研究[D].郑州大学,2009.
⑦孟子[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
⑧论语[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
2012年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湘学专项)“屈原作品中的两性人物意象系统研究”研究成果;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古代潇湘文学的悲剧情感及其审美意义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