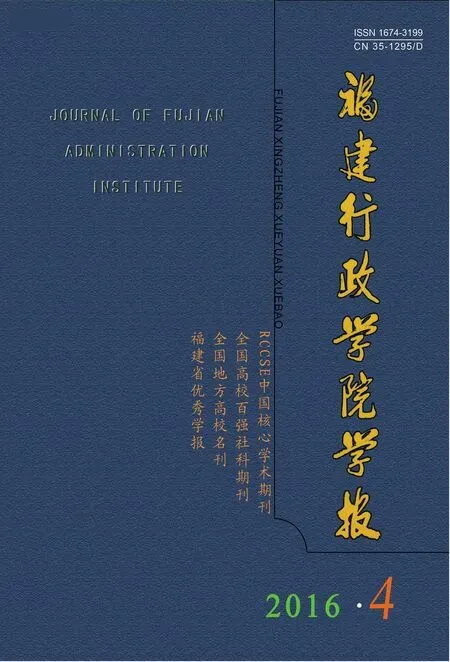“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因应之策
张 韵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因应之策
张韵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女性是生育的主体,然而在生育政策的改革中,对女性职业发展因生育而受到影响的关注微乎其微。实际上,孕产及哺乳期身体与心理状况不佳、产后职业资本减少和职业动机减弱等都会影响女性职业的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给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了生育二孩的机会,但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也空前增加。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全面二孩”政策将会对女性职业的发展产生直接、间接和根本层面的不同影响。应正视生育主体职业发展的权益,在政策上明确男性的育儿责任,改革以企业负担为主的生育保险制度,引进性别评估机制、完善生育政策的评估标准。
关键词:全面二孩;女性;职业发展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生育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家庭的发展而言,普通的家庭有了生育二孩的选择;对社会的发展而言,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挑战得到有效的缓解;对于人口学的发展而言,之前关于放宽生育政策的研究、分析及其相关预测可以得到检验。然而,在这种种影响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将指向我国广大的育龄女性。尽管如此,在与生育政策相关的公共讨论中,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其个人的发展所受到的关注与讨论却微乎其微。事实上,女性经受着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双重压力,而对女性在生育上的理性选择缺乏认识也导致了此前“单独二孩”政策在具体实施中遇冷。[1-2]生育政策的改革不应忽视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个人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我国女性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积极探讨解决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一、生育政策与生育主体
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来实现调节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手段。我国计划生育最初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特殊历史时期,到八九十年代逐步过渡到“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时代。“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1世纪,我国进入人口发展新的转折点,人口结构失衡与人口老龄化成为了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继续实施“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使我国陷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危机。因此,为了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数十年不变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变化与调整,在经历了“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以后,“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也得以启动。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人口数量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将生育这一私人的行为由个人及家庭的选择上升到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也正如此,生育在公共讨论中更多地与社会发展相关问题,如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联系在一起。相反,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发展问题在这种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却被忽视。生育固然是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女性在生理上的特性使其不得不承担生育的责任,然而,在男性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社会中,生育似乎成为一件脱离主体的事件,较少有主流话语从女性的视角来讨论生育与女性个人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生育给女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立足于调整人口,但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不容小觑。就“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社会地位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部分地区的“一孩半”政策反映出了性别偏好的传统,政策中体现出的对女性的歧视不利于推动与促进性别平等,且造成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潜在地改善了女性社会地位。“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通过强制手段使女性摆脱了频繁的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沉重负担,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高经济独立的能力;同时,女性教育水平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也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降低了生育水平。[3]可以说,原先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并不是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为主要目标,但其结果还是将女性从频繁的生育中解放出来,使女性获得了个人发展的时间与机会,我国女性的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近年来,为了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计划生育政策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开始进行改革,直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从此前“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尴尬局面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离预期达到的目标相去甚远。这是因为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而现行的生育政策由于忽视了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所面临的生育与个人发展的冲突,一方面令女性在自身发展与生育二胎间无法兼顾,另一方面则使政策本身收效甚微。
二、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生育是人口发展的动力;对于家庭而言,生育是延续血缘的纽带。然而,对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而言,生育不仅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与复杂的过程,自身的发展还会因为生育而受到影响。女性一次完整的孕产期包括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一般长达22个月。在此期间,女性要承担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譬如孕期由于生理激素作用而产生应激反应影响工作,分娩阶段巨大的生理消耗,以及哺乳阶段所面临的密集型喂养、照顾新生儿的考验。这些实实在在的孕产及哺乳过程消耗了女性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职场女性的工作进度,使女性在职业规划与发展上无法像男性一样连贯、顺利。生育对于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是普遍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点:一是孕产及哺乳期身体与心理状况不佳对女性职业发展的直接影响;二是产后职业资本减少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间接影响;三是自身职业动机减弱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本影响。
(一)身心健康受限对女性职业发展的直接影响
首先,大部分女性在孕期会经历生理上的不适,受逐渐增大的子宫的压迫,容易产生恶心呕吐、尿频尿急、肠胃不适、腰背酸痛、眩晕、下肢肌肉痉挛静脉曲张等症状。同时,孕期生理激素的变化还会对情绪、心理状态带来负面的影响。尤其在孕晚期,女性的躯体功能受限,负面情绪状态明显高于正常水平。[4]再者,生产过程所造成的生理创伤也需要一定的修养恢复时间,对于高龄产妇或身体状况较差的产妇而言,还会导致并发症。最后,新生儿的哺乳期需要母亲密集型的照料,母亲需要在婴儿有需要的时候进行母乳喂养,不分白天和夜晚。密集型的哺乳和看护婴儿不仅消耗了女性的精力,而且也与工作时间相冲突,导致女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工作。可见,生育对于职业女性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耗精力与时间,使得女性无法在工作中集中注意力,无法像往常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女性因为生育而遭到雇主歧视也是常有的事。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也观察到,孕期女性在职场中往往招致雇主较低的职业评价,被认为不够称职、不够独立、缺乏权威并且情绪化,无法胜任理想的经理人。但同样的情况在男性身上则恰恰相反,拥有孩子的父亲在职场中往往能得到较高的评价,也拥有更多的升迁机会。[5]
(二)职业资本减少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间接影响
职业资本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工作技能与知识结构,二是工作机会与工作环境。完成生育的女性想要回到职场,将会面临两个尴尬的处境:第一,由于职场知识结构更新速度太快,自身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职场的发展需要,并且长时间没有接触工作内容,职场技能也有所生疏,无法立即适应职场的节奏;第二,由于长时间离开工作环境,自己的岗位已经被取消或顶替,或者也因此错过培训、升迁等一切与职业发展相关的机会,以及之前积累的人脉资源的流失等。这些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生育过后的女性在职业发展中的机会与可能性,甚至有不少女性因此而在原先本可以游刃有余的职场中被淘汰,不得不另谋发展,由此也造成了大量女性在生育后最终被抛给了非正规化就业市场。然而,非正规就业市场中,女性的权益更加难以得到保障,一方面是社会福利保障的降低或缺失,另一方面是收入的降低。全国妇联主持的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正规就业市场中男性月收入比女性收入高1 684.58元;而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男性月收入比女性高出2 728.06元。[6]可见,产后职业资本减少容易导致女性向下的职业流动。
(三)职业动机减弱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本影响
女性在生育后,由于将大量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抚养、照顾上,工作的心态往往不自觉地发生变化:从前的事业心、进取心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孩子的责任心。虽然生育与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双方都有关,但研究发现,生育对男性和女性职业心态与动机的影响有很大差异。男性在新生儿降临后的一段时间会对事业重心作一定的调整,但这种调整通常是暂时和策略性的。而女性则不同,生育之后,女性往往更倾向于家庭,事业上的成就动机变弱,对事业的追求更加趋于现实,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会服从和让位于家庭。[7]因此,在生育后,女性在潜意识里重新定位自己事业的价值,将抚养孩子的优先等级提至追求事业和理想之前。而且,除了母亲与孩子天然的情感联系外,传统性别文化中对家庭分工的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中的选择。Becker认为,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家庭内部丈夫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专业分工。[8]这一观点由于忽视了家庭分工的公平性而遭到了女性经济学者的广泛批评。实际上,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构造的,传统的习俗与制度制约了人的行为与决策。女性并不是天生擅长家务劳动与抚育孩子,这些都是后天习得的,这意味着家庭分工完全也可以“男主内,女主外”。至少,男性应该和女性共同分担看护孩子的工作,为女性的个人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育龄阶段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给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了生育二孩的机会。然而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其所面临的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也空前增加了。不同特征的女性受到政策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人口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划分的较为科学和有效的方法是队列分析。在生育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较早出生队列的女性曾受到此前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而较晚出生队列的女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将不会再受到此前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其二,较早出生队列的女性在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或已错过最佳育龄期,而较晚出生队列的女性则处于适龄生育阶段;其三,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所在的年龄不同,事业发展阶段不同,政策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也因此不同。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影响是有差异的。为了方便描述,可以通过年龄来表现出生队列的特征,同时考虑到15~49岁的育龄划分,因此将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的女性分为三类:40岁以上的高龄女性;30~40岁的中年女性;3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本文将对这三类女性所受到的“全面二孩”政策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
(一)“全面二孩”政策对高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对于40岁以上女性的影响集中在“直接限制身心健康”的层面。换言之,生育二孩对这部分女性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对其健康的潜在威胁。这是由这一出生队列育龄女性的两个主要特征决定的:
其一,40岁以上的女性曾受此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通常来讲,40岁以上的育龄女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出生队列女性在她们最佳育龄时,恰逢八九十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不少女性在完成一次生育后被采取了强制型的节育措施,譬如置放节育环、节扎输卵管,因此如果选择生育二孩,还需要通过相关手术来修复生育能力。然而,生育政策的改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释放了她们积攒多年的生育意愿,不少女性即使高龄,也依然想要生育二孩,这也为她们的生殖健康增加了风险。
其二,40岁以上的女性将受到高龄孕产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高龄产妇容易产生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因素异常等并发症。同时,胎盘因素、剖宫产、瘢痕子宫和巨大儿的风险也远远高于适龄产妇,情况严重的会导致产后出血,甚至威胁生命。[9-11]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生育能力会下降。不少高龄女性为了生育二孩,不惜用药物调理身体激素水平,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2]可见,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在生育二孩的过程中,其自身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健康的身体是参与工作的基础。而对于40岁以上的高龄女性而言,选择生育二孩将面临着比初次生育时更大的健康风险。这种健康风险导致的健康缺失,严重影响了其工作效率,使其在工作中无法承担与胜任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最终导致其在职场中逐渐被边缘化。
(二)“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年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对于30~40岁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集中在“间接减少职业资本”。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正处于事业发展期,她们面临着照料孩子与工作在时间与精力上难以兼容的冲突。[13-14]生育二孩意味着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时间,选择生育二孩的女性重返职场存在一定的风险。基于我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的生育行为对其就业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曾因生育而中断就业的女性重新就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没有这一经历的女性。[15]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场中的个体主要通过培训和工作经验来积累人力资本,一旦个体离开了工作岗位,其与工作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会中断,同时,已经习得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由于不能及时更新,会在日新月异的职场中被迅速淘汰。[16-17]30~40岁的育龄女性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这一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考虑到生产期和哺乳期的时间较长,离开职场必然会对个人的职业资本积累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伴随“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不少地区推出了延长女性产假的配套政策,实际上这间接延长了职业女性离开职场的时间,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的政策体制对保障女性生育后返回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影响。有实证研究比较了实行不同社会政策体制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情况,结果发现,美国虽然致力于消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18],然而由于生育保险的缺乏,使得女性或者在生育后立即回到职场,或者不得不退出职场。[19]而相比之下,在以“女性友好型”福利国家著称的瑞典,其生育保险制度和高额的育儿补助很好地保障了女性在生育后返回职场的平等就业权益。[20-21]可见,完善的产假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可以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权益。
家庭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希望有朝一日回归职场,发展自己的事业,追寻家庭之外的社会价值,或者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全面二孩”政策下,若缺乏保护女性就业权利的政策与措施,将使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与个人发展间取舍。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放眼未来,“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更多的是尚未生育的年轻育龄女性。对于30岁以下的女性而言,“全面二孩”政策有可能会从“根本上减弱职业动机”。30岁以下的育龄女性年纪较轻,她们中有许多刚从学校毕业尚未开始职业生涯。而“全面二孩”政策或许会让她们面临更高的就业门槛,同时,她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将承受来自社会、家庭方面的生育期待及压力。
首先,“全面二孩”政策在社会心理层面加大了全体社会对于女性生育的期待。由于政策的宣传作用,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被再次强化。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话语体系中,生育不仅是挽救人口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家庭发展的行为,生育即“政治正确”。女性的个人发展也因此被降至次要的位置。
其次,“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长久以来积攒的生育意愿。对于已经结婚但尚未生育的育龄女性而言,家庭成员尤其是长辈通常也会有意或是无意地对其施加生育压力。然而,从我国现阶段家庭分工的情况来看,家庭中承担子女照料及教育主要任务的是妻子,丈夫的参与度往往比妻子低。在这种大的舆论环境下,女性常常难以意识到自身发展的权益,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家庭分工”的名义“禁锢”在家中,放弃了职业发展的机会;男性也以此名义更积极地投身职场,辜负在家庭中作为父亲与丈夫的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对于不愿放弃自身发展机会的女性而言,则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家庭内部的冲突。在生育这一重要的家庭选择上,背离家人的意愿坚持自己的选择往往需要更多的勇气,并且结果通常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同时还背负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最后,“全面二孩”政策间接提高了女性入职的门槛。通常来讲,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同等条件下往往更愿意招收男性员工。这在客观上是由于企业承担了女性的生育保险,同等条件下招收女性员工会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相当于给女性的就业环境雪上加霜,女性在家庭中将要花掉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无疑让用人单位对女性更加避之不及。因此,用人单位虽然在表面上不制定与相关政策相违背的性别歧视条款,但实际上却通过提高女性的入职门槛来降低招收女性员工的可能性。[22]可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女性即便自己愿意放弃生育,也不一定能够在职场上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过高的职业准入门槛使女性一开始就失去了与男性同等的职业发展机会。
总之,“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是广泛的,各年龄阶段的育龄女性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受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于育龄女性中的高龄群体,健康状况是其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对于育龄女性中的中年群体,职业发展的中断是其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对于育龄女性中的青年群体,来自社会及家庭的生育期待和生育压力是其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困扰。实际上,不同年龄阶段的育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按照年龄从高到低,分别体现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不利影响的直接层面、间接层面和根本层面。因此,要改善生育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需要从整体出发来应对问题的重点。
四、基于性别平等立场的政策建议
不考虑生育主体权益的生育政策不仅会对生育主体产生不利影响,其政策本身也将难以得到积极响应并收获预期的成效。譬如,针对此前“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查大多反映出年轻女性对生育的审慎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放弃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没人帮忙带孩子”。实际上,生孩子是女性被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养育孩子不仅仅只是女性的义务,更是家庭与社会共同的义务。现代社会中,女性与男性一样,有着对事业的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已有的配套政策往往只考虑到帮女性争取更加弹性的工作、更宽松的工作时间,这虽然能解决表面上“没人帮忙带孩子”的问题,但却将女性置于职场更不利的位置,最终导致女性与“奶瓶”捆绑得更紧,也为男性逃避家庭责任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因此,当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不应再继续忽视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而应重点关注如下三方面:
(一)政策上明确男性的育儿责任
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家庭分工忽视了家庭内部分工的公平性,夸大了家庭成员的利益一致性,而没有看到其中的冲突。实际上,性别分工是一种社会建构,正是社会习俗、制度与政策法规中种种偏见强化了性别不平等。[23]女性并非天生的家务劳动者,男性也并非无法照料孩子。性别角色实际上是后天习得的,性别分工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习俗、政策法规等人为设置的障碍造成的。在固化与僵硬的性别角色中,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缺乏选择的余地。女性不得不被留在家中,男性也被认为必须在职场上打拼。我国目前的政策背景下,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单方面地增加女性的产假。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后,部分地区在原有的基础上延长了母亲的产假。这一配套政策看似为女性赢得了更多哺乳和生理上恢复的时间,有利于激发女性的生育意愿。然而,这实际上是在强化母亲的育儿主体意识,将母亲更紧密地捆绑在“奶瓶”与“摇篮”的世界里,淡化了父亲的育儿责任”[24],其最终的结果将会导致性别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为了避免这种不良的趋势,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上进行正确与明智的引导,在保证母亲产假的同时,实行全国统一的“父育假”,并且在时间上尽可能与其伴侣的产假达到一致。生育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决定,育儿的责任和权益也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与分享,国家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体现男性在家庭中的父亲角色。“父育假”的政策不仅渗透了男性在家庭中的育儿责任,同时也抵消了企业在雇用女性员工时的“生育成本”,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
(二)改革以企业负担为主的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目前的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依然完全由企业来负担,国家和个人未承担。这一方面加大了企业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今天,企业的趋利本能使得企业为了避免支付女员工的生育保险,而寻找各种理由拒绝雇用女性员工,或者变相与女员工达成不平等的协议,阻止女员工的生育行为。因此,这一本以保障女性为出发点的政策,最后却无法保证女性员工生育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了女性就业的平等权利。[25]为此,应改革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其一,改变生育保障金的筹集模式,将以企业为完全承担方的缴费模式改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的模式。三方共担的模式不仅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女性就业平等,还能够强化国家和社会对于生育的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缴费也使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更广,增加了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女性的平等获益的机会。其二,改变生育保障金的发放模式,以家庭为单位发放生育保障金。如前文所述,生育是家庭的行为,在呼吁父亲承担共同抚育孩子的责任的同时,也应当保证父亲享有同等的权益。按照现有的生育保险制度,如果家庭中母亲没有工作,则无法领取保障金。实际上,父亲是参与了生育保险的,因为其所在的单位缴纳了生育保障金,但他却由于自己的妻子没有工作而无法领到生育保障金。因此,生育保障金应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这不仅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生育保险的权益,也使得男性与女性在企业的用工成本上趋同,从而减少了女性因为生育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
(三)引进性别评估机制,完善生育政策的评估标准
有学者认为,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制定与合法化过程中,女性是生育的主体,然而其立场与利益在政策实施前的评估中几乎被忽视。可见,性别评估机制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盲点。[26]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女性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的目标之一。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性别平等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尤其是在以女性为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生育政策的制定中,应当充分引进性别评估机制,正确认识与发现政策中可能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促进目标群体参与政策的讨论,表达利益相关群体的看法和需求,增加政策的参与度和透明度,最终在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促进了政策的完善和政策预期目标的完成。[27]
五、结语
从总体看,生育政策改革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积极应对了人口结构失衡与老龄化的危机,在家庭层面上释放了积攒多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然而唯独在生育主体的层面上忽略了女性发展将要面临的潜在障碍。女性在承担了生育责任的同时,也应当享有个人发展的权益。生育是家庭行为,照料孩子的义务需要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如此既能为女性的发展留有空间,也为男性融入家庭提供了可能。因此,政府在制定“全面二孩”的相关配套政策时,需要从长远出发,引导男性承担起照料与养育的责任,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提升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后,政府还应当引入性别评估机制,正确认识政策对不同性别群体所可能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在政策层面上促进与保障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
[1] 郑真真.从家庭和妇女的视角看生育和计划生育[J].中国人口科学,2015(2):16-25.
[2] 叶文振.“单独二胎”政策的女性学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12):58-63.
[3] 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P07项目课题组.中国计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研究[J].人口研究,1995(6):32-44.
[4] Otchet F,Carey MS,Adam L.Gener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 Status in Pregnancy and the Puerperium:What is Normal?[J].Obstet Gynecol,1999(94):935-941.
[5] Fuegen K,Biernat M,Haines E,et al.Mothers and Fathers in the Work Place:How Gender and Parental Status Influence Judgments of Job-related Competence[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4(60):737-754.
[6] 金一虹.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6-10.
[7] 国云丹.高知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以上海市21位女性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09(2):26-31.
[8] Becker G.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Economic Journal,1965(75):493-517.
[9] 张雪,刘凯波,刘凤杰,等.北京市“单独二孩”政策对高危妊娠变化的初步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5(3):100-102.
[10] 薛娜茹,杨慧霞.妊娠期糖尿病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相互影响[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2013(5):9-11.
[11] Lind J M, Hennessy A, Mc Lean M.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The Significance of Hypertension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During Pregnancy[J].Curr Opin Cardiol,2014(5):447-453.
[12] 李线玲.新形势下生育保险待遇落实探讨[J].妇女研究论丛,2016(2):14-17.
[13] 郑真真.实现就业与育儿兼顾需多方援手[J].妇女研究论丛,2016(2):5-7.
[14] 黄桂霞.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J].妇女研究论丛,2014(4):27-33.
[15] 宋健,周宇香.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5(4):16-23.
[16] Becker G S.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37-41.
[17] Mincer J,Polachek S.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Earnings of Wome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76-108.
[18] Orloff AS.Should Feminists Aim for Gender Symmetry? Why the Dual-earner/dual-carer Model May not be every Feminist's Utopia.In:Gornick J, Meyers M (eds), Gender Equality, Transforming Family Divisions of Labor[M].New York:Verso,2009:129-60.
[19] Evertsson M, Grunow D, Aisenbrey S.Work Interruptions and Young Women’s Career Prospects in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S[J].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2016(2):291-308.
[20] Saraceno C,Keck W.Can we Identify Intergenerationa Policy Regimes in Europe[J].European Societies, 2010(5):675-96.
[21] Abendroth A K,Maas I,Van der Lippe T.Human Capital and the Gender Gap in Authority in European Countries[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3(2):261-273.
[22] 杨菊华.“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14(3):49-51.
[23] 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6):61-68.
[24] 林建军.从性别和家庭视角看“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14(4):51-52.
[25] 李鑫.我国生育保险制度与妇女就业问题的思辨[J].改革与战略,2011(3):176-179.
[26] 蒋莱.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2):42-46.
[27] 刘伯红.社会性别主流化读本[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89-91.
[责任编辑:林丽芳]
收稿日期:2016-05-25
作者简介:张韵(1989-), 女, 湖北黄石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99(2016)04-0104-09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ll-Round Two-child Policy on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ZHANG Y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Women are the subjects of reproduction. However, in the reform of fertility policy,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impact of the female career development due to fertility. Actually, poo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postpartum career capital reduction and weak career motivation will affect female career development. The all-round two-child policy has brought all the families an opportunity of having two children. Nevertheless, the adverse impact on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has hence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age sequence, the all-round two-child policy will play direct, indirect, or fundamental impact on women in different ages respectively. We should face women’s rights of pursuing a career life, define men’s responsibilities in nursing children in our policy, reform the reproductive insurance which is mainly loaded on enterprises, introduce the gender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perfect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Key words:all-round two-child policy; female; career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