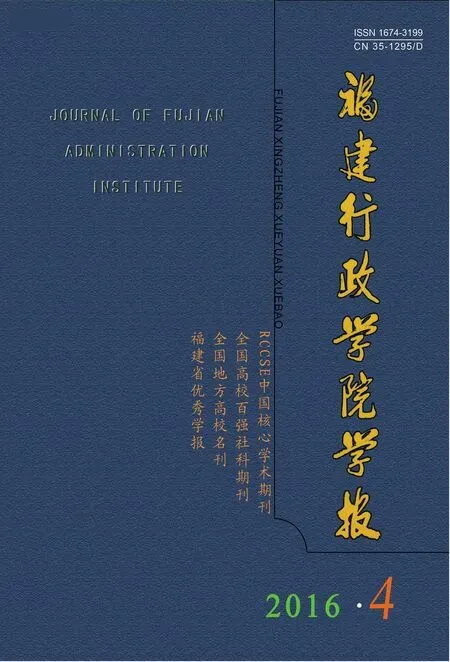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重构
——基于“诉因出现说”和“诉讼类型化”的比较
刘 芳,史寅超
(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2.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福建福州350001)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重构
——基于“诉因出现说”和“诉讼类型化”的比较
刘芳1,史寅超2
(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2.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福建福州350001)
摘要: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承载着保护行政相对人诉权和维护行政秩序的双重价值。最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作为起诉期限起算点,在司法审查中更容易把握,但该标准未充分考虑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时对其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主观认知,而该认知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诉权有重要影响。因此,该标准在维护行政秩序时难免弱化了对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在比较“诉因出现说”关于起诉期限起算点和“行政诉讼类型化”对起诉期限区分的基础上,以“行政行为公布之日”或“申请之日”为客观起算点,借鉴“行政诉讼类型化”对起诉期限的区分设计,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
关键词:起诉期限;诉因;行政诉讼;类型化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较多的话题,该制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行使。基于法院以“超过行政诉讼法定期限”为由而将大量的行政争议拒绝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实,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表示出担忧,纷纷献计献策,试图通过重新解读现行立法中的若干概念来对行政诉讼期限制度进行修正,或者大胆论证,建议将整个行政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取消。*李遵伟从法理和法治两个方面否定了行政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进而提出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观点。参见:李遵伟.论取消行政诉讼时效制度[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11-115.司法实务界亦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在权利救济和行使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着重于对法律具体规定的阐析及具体应用的技术指导。*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贾亚强在《行政诉讼中若干时点问题研究》中具体探讨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时点问题。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确立多年,法律规定亦相对明确和完善,现行立法的改废需要充分的理由,改变长期以来司法界形成的对诉讼时效制度的信任和依赖更非易事,而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规定做技术的分析能对现实中期限的把握有所帮助,但无法从根本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本文聚焦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起算点,以《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此方面的规定为基础,探讨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关于起诉期限起算点的规定
(一)旧法对起诉期限及起算点的规定
旧的《行政诉讼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对行政相对人诉权的行使在三种情况下的时效作了规定:一是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一般情况;二是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但不知道诉权;三是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特殊情况。*参见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司法解释》第41、42条。从这三种情况的具体规定来看,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起算点的确定有两个标准,即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的客观标准和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的主观标准。其中因为《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定,在“知道”的内容上又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标准和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内容标准。如此规定表达了保护行政相对人诉权和维护行政秩序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以行政相对人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充分地考虑到行政相对人因未知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而延误起诉时机的现实,给行政相对人主张适用更长的诉讼期限以法律依据。但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亦引发了一些认定上的问题:“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应在何种程度上被行政相对人了解才构成行政相对人的“知道”。笔者遇见这样一个案例,起诉人陈某等人因不服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2004年6月30日颁布的X房拆许字(2004)第02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下称《拆迁许可证》),于2013年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拆迁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许可证》系2004年6月30日颁发,起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遂裁定不予受理。起诉人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有二:一是本案行政机关以形式的合法掩盖行政审批行为的违法实质,造成上诉人错失起诉的良机;二是本案对《拆迁许可证》的审批行为违法的起诉计算起点应该以“上诉人知道行政行为的违法”开始,因为只有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内容真实地了解之后,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当侵害。二审法院亦认为原审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裁定维持。
本案中,两审法院都认定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而未能在法定期限提起诉讼,故而超过法定期限。但该案在二审立案阶段亦有法官持不同意见,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内容告知上不充分,缺少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要件的论述,使得该行为在基本内容上有缺失,造成行政相对人无法得知与该行政行为相关的关键信息或内容,因此,应该以“行政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而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为此,本案对是否超过诉求期限的争议演变为对具体行政行为应包括哪些基本内容的争议。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应包括哪些内容无疑是对法官裁量权的极大考验,亦会置于法官于法无据的境地。
(二)新法对起诉期限及起算点的规定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在吸收原有《司法解释》对起诉期限规定的基础上,对起诉期限作了较大的改动:一是将一般情况下的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并将司法解释中特殊情况下的起诉期限吸收至法条中,作为一般情况起诉期限的补充。二是将“知道”的内容由原来的“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改变为“知道行政行为作出”*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改变将起诉期限起算点认定的重心放在行政行为“作出”这个点上,同时“应当知道”的补充规定赋予法院更多的主动权,认定是否存在“知道”的事实,避免以当事人主张为主,长期纠缠于是否“知道”的认定。这样的改变纠正了《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及《司法解释》在起诉期限问题上同一问题使用不同用语的情况*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39条及《司法解释》第41、42条中,对起诉期限的起算分别使用了“知道具体行政行为” “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和“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三种说法。在以“知道”为起算点的情况下,更出现了“具体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不同用语。立法上用语的不统一是引发理解歧义的重要原因,应尽量避免。,将起算点的主客观标准统一在“行政行为作出之日”。
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起算点的优势是明显的,这一标准围绕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判断,通常以行政行为的生效为标准,存有争议的往往是对行政行为生效的一些技术界定,如送达的方式及效力问题。因此,笔者将该标准称之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起算点的客观标准。这种标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容易把握,司法实践中的困扰也相对较少,如果仅以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作为所有行政诉讼案件起诉期限的适用依据*《司法解释》第41、42条作为对修改前《行政诉讼法》起诉期限的补充规定,与修改后的起诉期限在起算点问题上存在不一致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第41、42条的规定不宜再作为起诉期限的判断依据,应进一步完善。,能有效避免因“具体行政行为内容”难以认定而造成起算点的争议。但该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会凸显出弊端:
第一,未能关注到现实中行政相对人将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作为其行使诉权的动因。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认为权益受影响即可以作为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的原因,并不需要行政相对人判断行政的合法性,但在现实中,基于对行政秩序的遵从和理性维权的考虑,行政相对人在判断权益是否受影响时通常会结合行政行为合法性这个标准。如此,在对行政机关提供的行政行为作出根据是否充分的判断上,行政相对人也有了相当的主张和需求,“行动者对各种方案的分析和选择,以及对自己方案的调整,都将依赖对必要信息的控制”[1]。毕竟,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知道”不是目的,通过“知道”获取的信息进行判断进而指导行为才是目的。这使得行政相对人是否行使“诉权”是基于行政行为违法这个“诉因”而决定。进一步讲,如果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通过行政机关提供的行为根据来判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及权利受损的事实,此时,法院以行政相对人“躺在权利上睡觉”的理由判其超过起诉期限而不予受理,这样的处理在逻辑上难以成立。“诉因”未出现,“诉权”并未产生;“诉权”未产生,何来“躺在权利上睡觉”。
第二,未能考虑到行政机关恶意瞒报对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在现实中,存在行政机关违背诚信告知原则的情况,比如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生效需要几个行政机关的审批,而几个行政机关之间相互合作,使缺乏某个合法性要件的具体行政行为得以批准,并在公布时,故意隐藏这个信息导致行政相对人无法判断行为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基本上无论怎么及时,都难以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行政相对人就此丧失了对保护其合法权益至关重要的实体权利,违法的行政行为则因此而永远获得“平静利益”*“平静利益”指“潜在被告的心情平静下来, 不用担心被人起诉”。参见:沃德·法恩斯.高手解决法律难题的31 种思维技巧[M].丁芝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2 .,不再担心被纠正。
二、解决之道一:以“诉因”的“出现”作为行政诉讼起算点
对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即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知悉的程度和诉权行使的逻辑关系,以及现实中行政机关恶意隐瞒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已有学者予以关注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充分借鉴日本和美国关于确定时效起算日的基准*日本确定时效起算日基准的基本学说为“法律上的可能性说”和“现实的期待可能性说”,美国确定时效起算日的学说为发现规则与持续违法理论。在该两种基准之下,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日都应当以起诉人是否发现或者知道权利发生的事实的时间或者现实期待起诉人可以行使权利的时间作为基准。参见:肖泽晨.我国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J].清华法学,2013(1):66-69.规定,有学者提出:“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短时效期间的起算日‘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解释为可以期待起诉人提起诉讼的必备原因都具备之日。”进一步解释为,“如果起诉人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部分内容,因而不足以让其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带来损害为由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就不开始计算。”[2]从这一观点来看,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是否全面充分,判断权不在立法,亦不在行政机关,而在于行政相对人,在于行政相对人能否通过该内容产生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诉讼的期待。能产生,则适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条款中3个月的短时效,诉讼期限起算点以知道之日计算;不能产生,则适用“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长时效,诉讼期限起算点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该文撰写于《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故关于期限部分的规定仍延用修改前的规定。
这一解释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捋顺“知道”行政行为作出和诉权行使之间的逻辑关系,亦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监督违法行政行为。但该解释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还会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一)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之争
基于对诉愿程序的控制主体不同,诉愿程序适用的原则截然不同。诉愿程序的开启以至于结束,主控权在诉愿人,称之为当事人主义。操控权在审议机关(法院),则称之为职权主义。*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具体论述,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268-1270.将行政行为内容是否全面的判断权赋予行政相对人,由其决定是否导致“诉因”的出现进而决定起诉期限的起算,法院在其中虽有审查的成分,但基本以行政相对人为核心来决定诉讼期限的走向,体现出强烈的“权利保护”色彩,可以说是当事人主义的集中表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亦有对当事人主义原则的适用,但范围很小,除了原告的起诉、撤诉等少数程序外,基本皆用职权主义。同时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起诉与法院的受理紧密联系,起诉期限作为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之一受到法院严格的审查。虽然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民主国家强调个人权利在诉讼制度中的体现,亦作为一国行政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主要价值之一,但行政诉讼制度“涉及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则之要求,有其客观法制符合性与程序进行之效率、迅速性与经济型及公益等之考量”[3]。因此,我国法院在适用《行政诉讼法》起诉期限规定时,虽然有对行政相对人诉权保护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依照客观法律之规定及行政效率等因素的考量,依职权对起诉期限作出自己的理解,较少受到行政相对人主观认识能力的影响。在此情况下,由行政相对人主观判断“诉因”是否“出现”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较难得到现行司法审查模式和诉讼制度的认同。
(二)良好的诉权保护与无法律依据之争
虽然以“诉因”的“出现”作为行政诉讼期限的起算点能够充分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和实体权利,但法院不得不面临“于法无据”的现实困境。例如,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在上文所举的案例中,被告以法定的方式,按照法律的要求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发布,可以说该案中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内容的告知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可以认定行政相对人已经知道了行政行为。此种情况下,以未能满足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知情的需要而认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内容告知不充分,行政相对人属于“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条款,从而适用20年的诉讼长时效,不论是适用新法还是旧法中的规定,法院都将因无法律依据而受到质疑。
(三)维权与滥诉之争
维权与滥诉,一者出于公正、正义凌然,一者目的不纯、别有用心,两者似乎应该泾渭分明,但现实中以谋他权而提此诉的案例并不缺乏*在笔者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众多征地拆迁案件中,出现行政相对人起诉行政机关征地过程中的所有行政行为的系列案件,行政相对人虽提起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但最终的诉求大多为获取更多的征地及拆迁补偿,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因为对应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的丧失而转寻它径,曲线救国的诉讼策略,造成司法在回应权利保护诉求之时,亦将当事人诉之利益等因素考虑进去,以免将司法沦为当事人以维权之名行滥诉之实的工具。将足够期待诉讼“诉因”的“出现”作为行政诉讼的起算点,对违法行为的追求可能会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原先的行政行为会被后续的行政行为所湮没,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经过重新调整,其与最初的行政行为的关系将愈发微弱。以前文所举案例为例,根据证据材料显示,该案原告在其房屋被拆迁后,按时住进了被告依承诺建设的安置房,此后,原告的投诉均围绕安置房的相关问题而进行,此种情况下原告就最初的拆迁许可行为提起诉讼,直接诉讼利益的缺乏将引发对其诉讼目的的怀疑。
三、解决之道二: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基准的起诉期限
从“诉因”出现的角度解决行政诉讼期限起算点的问题,虽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并且勿需对行政诉讼制度做大的调整,但这样的解读给司法审判实践带来的难题也不小。对此,笔者将目光投向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和司法传统更为接近的德国,研究其相关制度的规定对我国是否有借鉴意义。
以行政诉讼类型化见称的德国,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均建构在对不同类型诉讼的基础之上,与我国以撤销之诉为中心来统一规定适用各种不同类型行政行为的诉讼制度不同,德国撤销之诉虽然地位重要,但在实质裁判条件和诉的适法性、诉的理由具备性等方面,德国行政诉讼法均区分为撤销之诉、义务之诉、停止作为之诉、一般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来分别规定。其中,作为诉的适法性条件之一的起诉期限也因为诉的类型不同而被分别规定。根据规定,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限为行政行为公布之日起1个月内;义务之诉分为两种情况: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否定决定)适用行政行为作出否定决定之日起1个月内,不作为(行政机关不予答复)适用提出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停止作为之诉,无明确的期限规定,除了原告已经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反对地忍受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利影响等特殊情况,诉权权利一般不会因期限的规定而丧失;一般的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均无期限要求,换言之,不必遵守起诉期限规定。
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不适用起诉期限的原因和该类诉讼的标的有关,给付诉讼时行政相对人以依法产生的给付请求权主张行政机关履行给付义务,确认诉讼”旨在澄清各种迥然不同的问题和法律关系”。[4]311“当事人提起这两类诉讼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既不会直接导致既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也不会直接形成新的法律秩序”,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设置目的——维护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并不冲突,因此,“撤销诉讼适用起诉期限顶理成章,而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等适用起诉期限的理由却并不存在”[5]。当然,没有起诉期限限制并不说明原告永远不会丧失诉讼权利,使得被告永远都难以获得“平静利益”,德国在各类诉讼中均对原告诉权的具备有较高的要求,在确认之诉中尤其对各种确认诉讼中原告的确认利益有单独要求,“尽快确认”被作为“时间上的因素”与主观因素(正当利益)一起作为请求法院进行确认法律关系的前提要件。[4]311
可见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对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是与其诉讼类型化制度相匹配或者相统一的。针对不同行政行为的类型,对立法价值做不同的倾斜,适用不同的起诉期限规定,并辅之以原告资格等制度的规定,使得德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呈现出形式多样但适用中却井然有序的局面。虽然从局部看,保障当事人诉权和追求行政秩序稳定的立法价值在不同行为类型上有不同侧重,但从整体来看,基本做到了兼顾。我国《行政诉讼法》尚未建立起诉讼类型化制度,欲借鉴德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将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作出较大调整,但从长远着眼,德国的规定对我国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且我国也具备一定的实现基础,理由如下:
一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的理论和制度设计为主。虽然我国没有建立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制度,但整体上的司法传统和制度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相容性。二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类型化预留了空间。我国《行政诉讼法》虽未直接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化,但根据受案范围与判决内容一部分的规定,可以将诉分类为确认之诉、变更之诉、撤销之诉、履行之诉,虽然这种类型化的分类探讨目前主要在学理界展开,法律规定及司法实务中,在起诉条件、证据规则、法院审理规则等方面仍适用统一的规定,但立法中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及被告的特殊性设定相应的判决形式,可以说是对整个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预留了一定空间。三是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为我国走向行政诉讼类型化提供试验田。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之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进入司法程序,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在作出程序、表现形式、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影响等方面均区别于传统行政行为,法院在司法审理中亦面临着新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从受案范围、起诉条件、被告的确定、证据规则、判决形式等方面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规则已呈现出区别与其他传统行政行为审理规则的特点,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将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的确立积累经验。
四、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重构
综上,出于制度相容性的考虑及从根本上理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关系的长远考虑,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基础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设置,让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所承载的立法价值更为单一化,即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力,维护行政秩序稳定性。巡此思路,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重构作如下建议:
第一,在起诉期限制度的确立模式上以整个行政诉讼类型化为依托,改变现在起诉期限适用于所有诉讼类型“一刀切”的模式。“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各种不同诉讼请求的差别、采用一元化的标准造成的”[6]10不同的诉讼类型设计对应的起诉期限。可以说,在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基础上,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对应于每一种具体的诉讼类型而做单独的规定,使行政诉讼期限制度能够有效应对各种不同诉讼对起诉期限提出的要求,是解决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问题的良方。对于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的确立,学者们提出过多种方案,如薛刚凌教授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可以扩展为两大类、七种具体类型。*其中个人救济诉讼包括纠正违法行为诉讼、当事人诉讼、行政赔偿诉讼及行政合同诉讼四类; 公法秩序诉讼则包括公民监督诉讼、国家监督诉讼及执行诉讼三类。参见:蔡志方. 行政救济法新论[M].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2000:172.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当下行政诉讼类型体系的重构中,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四种类型的划分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7],但笔者对诉讼类型的划分更倾向于司法实务界的学者主张的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这三种基本类型,因为“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当事人能够提出的所有权利请求以及救济的方式”[6]14。笔者亦以此对具体的诉讼期限作出规定。对于撤销之诉,以“行政行为的作出”为期限起算点,考虑到撤销之后对行政秩序的推翻,起诉期限不宜规定过长,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1个月为宜,并不辅之以任何例外的规定。对于确认之诉,因为不会对既有的行政秩序产生影响,故而不作起诉期限方面的限制,但对于可能被滥用的确认之诉,尤其在确认利益的认定方面则将时间因素考虑进去,防止“法院有悖于其本来职能地变成法律问题的咨询或者鉴定部门”[4]318。具体设计上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把时间因素置于原告享有确认利益从而具备诉权的内容之一做以要求。对于给付之诉,具体包括一般的给付之诉、义务之诉和停止作为之诉,其中一般的给付之诉和停止作为之诉均不作起诉期限上的要求,义务之诉分为两种情况,对于行政机关明确以作为形式予以拒绝的,可适用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限,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如行政机关以不作为的形式(不予答复、沉默等),起诉期限可参照撤销之诉的规定,期限予以适当延长,起诉期限以“提出申请之日”起计算。
第二,以更具操作性的客观标准作为起算点。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作为起算点虽然较之旧法更易于判断和把握,但何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在实践中仍不免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建议将该标准改为“行政行为公布之日或提出申请之日”作为行政诉讼起算点,使起算点的计算更为客观,避免了在本该清楚明了的程序技术问题上产生认定的困难。
参考文献:
[1]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14.
[2] 肖泽晨.我国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J].清华法学,2013(1):70.
[3] 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269.
[4] 弗里德赫尔·胡芬.行政诉讼法[M].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 林俊盛.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6):115.
[6] 李广宇,王振宇.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J].法律适用,2011 (5).
[7] 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述评[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 (3):88.
[责任编辑:郑继汤]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简介:刘芳(1979-),女,天津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 史寅超(1974-),男,广东揭阳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员。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99(2016)04-0055-07
Reconstructing Time Bar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Based on Comparing“Cause of Action” with “Class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IU Fang1, SHI Yin-chao2
(1.Department of Law,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Fuzhou 350001, Fujian, China;2.Administrative Tribunal, Higher People’s Court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001, Fujian, China)
Abstract:Time bar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has double valu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to appeal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and maintaining the administrative order. In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the time when the administrative act is done is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secution, which is easier to grasp in judicial review, but the standard ignores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cognition whether his interests are violated, and this cognition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o exercise his rights to appeal. Therefore, it is inevitable to weaken the right prote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der. Based on comparing “Cause of Action”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e should take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t or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use rule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classification on prosecution deadline for referenc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secution deadlin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time bar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ause of action; class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