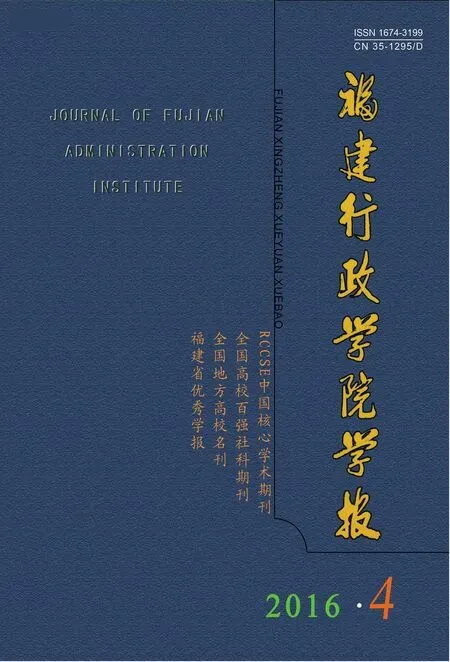行政法学视野中的“吹哨人”制度
詹 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63)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吹哨人”制度
詹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63)
摘要: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正试图引进、探索的“吹哨人”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着眼于“内部人”并通过奖励、保护机制使“内部人”将组织内部潜藏的违法信息向外界传递,打破了政府与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在行政法学视野中,“吹哨人”制度是我国政府加强对市场监管的“技术手段”,也是促成政府与私人合作的“粘合剂”,更是激活公民权利、鼓励公众维护社会道义的“驱动装置”。我国引进“吹哨人”制度,根本上是治理思路的革新,即通过多元、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跃迁。
关键词:“吹哨人”制度;法律定位;行政监管;公私合作
一、一场“重赏之下未必有勇夫”的大讨论
自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公布《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食安办[2011]25号)》以来,全国31个省市纷纷建立有奖举报机制,将该项制度在行政执法领域推向高潮。然而,与立法规范上有奖举报制度“备受青睐”不相匹配的是其在实践运作中“饱受冷眼”,并引发了一场社会各界关于“重赏之下未必有勇夫”的大讨论。综合目前的举报实践来看,要么社会公众因没有掌握“内幕信息”而无法举报,导致举报奖励频频“遇冷”,无人问津;要么部分内部人士在向提供违法信息时是“举报勇士”,案件查实之后,举报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领奖懦夫”。2012年温州市瓯海区就开始实行有奖举报制度但截至2014年,却只发出3单匿名举报奖励,领奖者寥寥无几。2013年1月,辽宁省食品安全办公室首批奖励76名举报有功人员,公告发出后,在法定领奖日期截止后仍有44人未领奖。无论是无人前来举报的“冷”现象抑或是愿意举报但不来领奖的“怪”现象,都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税收征管、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领域大力推行的有奖举报制度确实存在着针对性不够、奖励不多、保护不周等严重的制度漏洞,不符现实之需。为此,许多专家学者、业界人士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安徽、陕西、苏州市、上海闵行区等)都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吹哨人”制度,试图将该制度引入中国,建立中国版的“吹哨人”。*比如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11年谈论雨润公司“瘦肉精事件”时,就提出引入美国的“吹哨人”法案;2013年,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在参与旧的《食品安全法》修订会议时,就曾给食药总局搜集了国外“吹哨人”制度的信息;同济大学法学院孙效敏教授也在进行相关制度研究,试图推动在国内建立类似美国的《吹哨人法案》;2015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欧俊博士就提出构建我国环境领域的“吹哨人”制度,并写成专题论文进行发表;而安徽省、陕西省、江苏省苏州市、上海市闵行区等地方政府都在探索建立“吹哨人”制度,来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参见:佚名.寻找中国版食品安全“吹哨人”[EB/OL].(2014-04-15).http://ent.ifeng.com/HOT/yaowen/detail_2014_04/15/35779919_0.shtml;佚名.安徽率先实行“吹哨人”制度,保护“舌尖上的安全”[EB/OL].(2014-12-16).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12/16/c_1113655016.htm;佚名.“吹哨人”制度应成为社会常态[EB/OL].(2015-11-12).http://news.cqnews.net/html/2015-11/12/content_35748238.htm.
所谓“吹哨人”(Whistleblower)最早源自英国,是指警察在发现有案件发生时,吹响哨子以引起他人的注意。Nader、Petkas和Black-well首次在理论研究中将该词义(Whistleblowing)引申为:“组织成员对组织内部的腐败、浪费、欺诈等非法或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揭发。”[1]与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有奖举报制度不同的是,“吹哨人”制度着眼于“内部人”,即组织内部具有特殊信息优势地位的成员;并围绕“内部人”行为及对其伦理矛盾的关怀和救济进行制度安排,通过高额的奖励制度和严密的保护措施,使“内部人”在发现组织内部隐藏的违法行为时,能够将信息及时向外界传递出来,避免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美国学者Dcvk在一项“举报机构有效性”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从1996年至2004年八年间的216例公司财务欺诈案中,142例(65.7%)是由外部监控人员发现的,绝大多数均为非政府背景,其中公司雇员占18.3%,分析师占16.9%,媒体占15.5%,而政府机构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查发现公司财务违法行为,只占极小部分。[2]由此可见,作为非政府机构检举人的“吹哨人”在发现公司内部违法行为,帮助政府机关完成行政任务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吹哨人”制度是一项立意高远兼具长远智慧的制度设计,值得我们用于对现有举报制度的反思、改良。然而,“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性”。“吹哨人”制度也颇具争议之处,如处理不善,未免会像引入行政听证制度那样产生“橘生淮北”的效果。事实上,在国外,“吹哨人”制度虽然帮助政府在行政执法领域频立“战功”,*比如著名的安然公司舞弊案、“水门”事件以及2012年曝出的“葛兰素史克虚假广告案”等都有“吹哨人”正义的身影。为了纪念无数的“吹哨人”为美国民众公义所做的巨大贡献,美国国会在2013年将每年的7月31日定为“全国吹哨人日”。 参见:刘源.“獐子岛事件”呼唤中国的吹哨人制度[EB/OL].(2014-11-13).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8,20141113445649940.html.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其极具伦理风险,他们将内部举报者称为“鼹鼠”,意为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偷偷攫取他人的秘密和错误并加以披露,如果运用过盛会导致社会“反叛者”丛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忠诚关系撕裂。[3]食药总局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我国“吹哨人”制度立法层面的问题时也坦言:“会比较谨慎,暂时有争议,更多希望地方政府发挥探索作用”[4]。所以,我国要引进“吹哨人”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该项制度在我国法律上的定位。在现代行政权的作用方式由“单一强制”向“多元合作”转变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勃兴于传统强制行政行为式微之势的新型执法方式,“吹哨人”制度必然有其成熟的外在环境和独特的内生机制作为支撑,而正是这些因素为我们在行政法视角下打量“吹哨人”制度提供了丰富而清晰的观察点。因此,笔者将对这些外在环境和内生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多角度地探寻“吹哨人”制度在行政法上的样态,为廓清我国“吹哨人”制度法律构建上的重重迷惘奠定基础。
二、作为行政监管“技术手段”的“吹哨人”制度
在美国,“吹哨人”制度多产生并运用于证券市场、产品制造等专业化明显、市场主体众多的领域。在这些行业中,随着产品日益多样化,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复杂,人们往往从属于某一个或者多个组织,市场参与主体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状态。我们知道,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治的空间,很多违法信息天然地被组织所屏蔽、隐藏而无法向外界传递,致使行政机关对潜藏在组织或行业内部的违法行为常常鞭长莫及、无法掌控,相关监管目标随之落空或社会公众蒙受巨大损失。为了增强行政机关对于这些纷繁复杂、混沌无序的组织的监管能力,美国政府在这些监管领域中建立“吹哨人”制度,充分利用组织成员观察不法行为的优势地位、权利和路径,将组织成员或行业人员纳入到行政监管体系中来。截止到目前,美国在证券市场和产品制造行业就构建了以《欺诈声明法》(《False Claims Act》)、《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等为文本基础,以专门的“吹哨人”办公室和保护机构为组织基础的完善、严密的“吹哨人”制度,大大加强了政府对于这些利益交织、违法行为丛生的领域的监管能力。201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委员会在该年度内共收到举报案件3 238起,平均每天约10件,并帮助委员会追回了超过1亿美金的非法资金。[5]由此可见,在专业化、组织化日益明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仅仅采用单一命令式的强制行政行为已经无法满足复杂环境下的多重监管任务,必须拓宽思路,以务实、权变的姿态来寻求新的应对之道。而具有将“内部人”融入行政监管体系,利用“吹哨人”对企业的制约作用和企业间竞争机制,实现行业行为规范的功能的“吹哨人”制度,可以成为我国政府在转型社会时期破解行政监管难题的“技术手段”。那么这一制度定位的原因何在呢?或者说其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监管“技术手段”,有何“新”意呢?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吹哨人”制度可为我国行政监管引入多元主体,增强政府对市场中不当行为的“溶解力”。长期以来,我国在行政监管领域一直奉行以政府为主导,配合“命令式”强制性行政行为的监管模式。行政机关采用这样的监管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惯性作用下依旧“管控力”强大,权力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够满足一定的监管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不健全,市场主体还只是具有“安全与秩序”下的自由竞争需求,无法主动参与到整个市场监管的过程中来。所以,在特定的时期和背景下,“单一强制”的行政监管方式在维护市场秩序、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市场主体所需求的自治空间越来越大,组织内部匿影藏形的违法行为丛生,政府所面临的监管问题空前复杂化与多样化。这迫使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行政主体不得不分散监管力量,将传统监管模式下有限的“弹药库”分由各个部门“单兵作战”。例如,证券市场由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监管;税收违法行为则由税收部门管理;而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则由农业、质监、工商、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多个部门协同负责。据统计,光是食品检验一项,“目前全国具有食品相关检验能力的技术机构就7 000家,从业总数达15.04万,大部分隶属于卫生、农业、质检、粮食、食品药品监督、环保等部门,而且各部门分头建设、各自设置技术机构”[6]。这样的执法监管力量,不可不谓“强大”。然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政府监管体系运行成本高,执法效率底下,基层力量薄弱。这真实而深刻地告诉我们:继续固守以政府为主导,将市场行为的做出者——市场主体摆在服从者地位的监管模式,只会使我们的执法力量在浩瀚庞杂的社会事务中被消耗殆尽。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强调单一命令式的行政执法模式,是一种相对外部化的“看管式”的监管手段。它只强调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行政机关在制度运行架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将市场个体、行业组织等“私人组织或个人”摆在行政行为的末端接受者、服从方,忽视了私人或组织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得行政主体在面临多重监管任务时常常因为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管制手段而“沮丧不已”,甚至束手无策。与之不同的是,“吹哨人”制度的设计思路则要广得多,给予原先处于行政行为末端服从者的“私人力量”以持续、合理的关注。它立足于行为当事人——组织成员或行业人员,以激励和保护机制来构建“合作互利”的基础,并通过行政双方相互利益的满足来获得相对方的合作性服从。在“内部人”维护社会伦理和自我保护的“自发力”以及政府奖励的外部刺激下,“吹哨人”制度可以填补行政机关部分市场、社会监管领域的“真空”。有学者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吹哨人”制度最适合于政府监管失灵的领域。[7]通过将处在观察不法行为优势地位的内部人员纳入到政府监管机制中来,一是在组织内部违法行为发生时,可使“内部人”在特定情景下及时“倒戈”或利用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使其竞争对手勇于“揭短”,让行政监管机构能够即时掌握违法信息,有效惩治违法行为,形成“吹哨人”对企业的制约机制;二是这种制度设计让违法、违规组织认识到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从而增加组织违法的成本和风险,打消侥幸心理,产生对潜在违法者持续、有效的“震慑力”。唯有这样,行政监管方能打破传统的单一、低效格局,将行政机关监管的触角有效地延伸至组织内部,形成内部信息提供和外部查处惩治的监管合力,大大提高了行政主体对于市场中尤其是组织或者行业内部纷繁复杂的违法行为的“消化”能力,有效加强了对潜在违法者的震慑、警示作用。

三、作为行政主体与社会力量“粘合剂”的“吹哨人”制度
在过去,行政法将社会秩序之维护作为行政权的目的指向,国家机关独享行政权力,整个行政活动的演进过程,包括事前的信息收集、事中的证据调查以及最终的处理决定和执行都由行政主体推进,排除私人的主动参与(不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等当事人的被动参与)。然而,在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逐渐认识到其不再能够固守垄断行政资源的单一格局,放弃事事躬亲的“全能政府”理念,转而致力于寻求私人合作,强调放权于社会,以回应政府的多重行政任务。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负有执行资源分配以及福利保障等任务的行政活动,不再完全由行政机关来单独完成,反而更加强调行政机关的“掌舵者”角色,以免行政主体陷入浩瀚繁杂的具体事务当中。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吹哨人”制度就是政府以合作、务实的姿态来重塑整个行政活动演进过程的制度创新:制度设计者从行政机关当前的事实信息收集能力呈现“后知后觉”疲态*事实上,一直以来行政机关只是处于规范信息的优势地位,而对于事实信息,则更多地掌握在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证人甚至普通公众手中,行政机关并非处于强势、支配地位。参见:孟倩.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13.的窘境出发,在整个行政活动的事前信息收集、事中证据调查等环节,借用私人力量来协助行政机关完成启动调查、信息收集、证据核实等“辅助性”事务,帮助政府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抽身”出来。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行政机关仍处于推动整个行政活动发展的主导地位,但其中的部分过程则由处于特殊地位、具体情境的私人力量来完成,从而将政府的“掌舵者”职能与执行具体社会事务中私人的“划桨者”角色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完成社会治理的目标。从这一过程来看,这种针对行政活动所展开的合作形式——“吹哨人”制度,当属台湾学者詹镇荣教授所归纳的“法律执行民营化”之典型。*这种针对行政活动所展开的合作方式,被台湾学者詹镇荣教授形象地称为“程序民营化”或“法律执行民营化”,即国家非直接投入命令、禁止等强制手段,而系容任私人参与管制行政阶段上之前段程序。参见:詹镇荣.论民营化类型中之“公私协力”[J].月旦法学杂志,2003(11):18.
从以上公私合作的角度出发,可以预见我国在进行“吹哨人”制度的本土化法律构造时,必将公私合作治理的思路纳入该项制度建设的考虑范围。本文就沿着这样的思路,对“吹哨人”制度中所蕴含的合作价值基础和合作载体两个方面试作分析。
第一,对有序市场、社会的追求是“吹哨人”制度中公私合作的价值基础。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人类对于秩序的追求,是人类面临社会分工、协作的风险时,欲将集体生活的发展趋势控制在合理稳定范围之内的心理要求。然而,这种对于秩序追求的愿望,却时常被“偶然的混乱状况”所挫败。[9]国家间的战争、社会暴力行为、企业的违法经营、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等等充斥着整个市场和社会,不断地冲击现有的法律秩序框架,大大扰乱了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科技发达导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的今天,市场有序、社会稳定既是政府一直在追求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行政目标,也是个人通过稳定的社会体系,接入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并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两者对于秩序形式的追求,都毫无疑问地比以往更加强烈、迫切,而且日趋走向“携手共舞”的格局。一方面,越是具有复杂分工、精密结构的社会整体,其结构就愈加脆弱,即使在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秩序框架下,“偶然的混乱状况”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和危害也愈加明显。在这样“危如累卵”的情势下,政府对于秩序的追求,对于社会全局的掌控欲,变得日益膨胀和明显。然而,完全掌控社会的政府,又是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和经济的发展。为了缓解、平衡这样的矛盾,政府不得不借助“吹哨人”这样的制度,来定点、即时掌握“偶然混乱状况”的信息。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举报行为背后隐藏着社会个体无时不在的“审判者”心理,“大多数社会个体在发现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10],处于组织内部的潜在举报人,对违法行为有着更加直观、清晰的观察,相较于一般社会公众,往往具有更强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意愿、冲动。因此,“内部人”选择对组织内部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在危害行为发生时,及时吹响哨声,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正是举报人对于现有秩序价值进行认可的“内心确证”,也是维护秩序体系,避免“偶然的混乱状况”危害扩大的“矫正过程”,同时也符合行政机关对于有序社会结构的预设目标。
第二,内部信息是“吹哨人”制度中政府与私人合作的交易载体。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就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资源。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人总是依赖、从属于某一个或者多个组织来共享信息资源,即“组织人”的产生,以便在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占得“先机”。但组织是一个相对自治、独立的场域,很多违法或不当信息往往被组织体系所屏蔽、潜藏,导致传统行政机关的信息优势地位被打破。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所带来的信息格局呈现出“蹊跷板式”的不对称态势:在翘起的一端,是组织以及组织人对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信息的垄断地位,导致信息“供给端”十分盈余;而在翘板下垂的一端,则是政府处于事实信息获取、收集的弱势地位,使得行政机关对于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强。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占有格局,极易使组织内部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扩大,从而使社会公众蒙受重大损失或行政机关相应的管理目标落空。一旦有了“吹哨人”制度的介入,信息交易的平台便构筑起来,组织内成员可以与行政机关分享、交易所获得的违法行为信息,信息供需的倾斜结构便转向平衡态势。在这样的信息共享、互易过程中,一方面“内部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精神奖励来补足信息提供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并能够为自身提供一种避免卷入违法行为的免责机制;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于危险、危害行为的应急处置能力,大大减少了行政机关落实行政监管目标的成本。可以这么说,信息交易是“吹哨人”制度中政府与私人合作的本质;它将原先对峙的行政机关和私人力量“串联”起来,成为两者同向而行的“纽带”。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通过“吹哨人”制度所架构起来的信息交易制度,应当只是行政机关获取事实信息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替代行政机关对信息收集、调查、验证的过程,行政机关对于交易获得的信息仍旧负有调查核实的义务。
四、作为公众参与、激活权利“驱动装置”的“吹哨人”制度
翻开权利理论和实践的篇章,权利本位论者始终强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追求自由并“迈向权利的时代”。可以说,权利本质上是特定利益的表达,也是自由的体现。按照传统权利理论的理解,国家对于个人权利有根据权利的主张作为或不作为的消极义务,至于个体权利的行使抑或是放弃则完全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与国家无关。然而,为权利呐喊、斗争是我们圣神的职责,正如18世纪英国政治家爱德蒙·柏克所喟叹的那样:“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好人的袖手旁观”。如果权利主体只在个人利益上“争长短”,而放弃行使代表一定社会公益的基本权利或者选择对侵权行为默不作声,那么权利将走向极为危险的境地:要么被国家公权力侵蚀殆尽;要么造成权利主体之间无序的对峙、斗争,最终沦为强权者的“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市场监管、监督政府行为、打击违法犯罪等诸多领域建立并运用“吹哨人”制度,不仅有加强政府监管,避免违法行为给整体社会运行成本带来损失的目的,更有维护社会正义、倡导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初衷。事实上,美国一直将有关奖励和保护举报人的立法称作“吹哨人法案”,正是为了避免“举报人”或“告密者”这样的名词可能传递的负面影响,转而采纳美国民权活动家拉尔夫·纳德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吹哨人”说法——“吹哨人”这个名词在西方国家代表为社会正义挺身而出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为了纪念无数的“吹哨人”为美国的民主公义所作的巨大贡献,推动公民对“吹哨人”制度的支持,2013年美国国会专门出台法律将每年的7月31日定为“全国吹哨人日”。因此,“吹哨人”制度中所蕴含的倡导人人为权利而斗争的权利观和为维护社会正义而挺身的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个处于权利初醒时代的国家而言,显得弥足珍贵。
立足于我国国情来讨论,我国公民的权利实践呈现出两极的运作样态:一端是过度彰显个人权利的利益表达功能。人们笃信权利“标签”的文明与高尚,将权利作为一种“修辞”来为自身追求私利的正当性摇旗呐喊,使得权利主张在私权领域泛滥,导致权利异化。[11]另一端则是极度忽视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对于部分与个人利益关系不直接相连,具有社会公益的权利,权利主体基于“搭便车”的心理,选择对部分权利进行忽视或放弃,造成中国社会公众严重的“权利冷漠症”[12]。这种弥散着自我情结、视社会公益为“瓦上霜”的权利实践模式,是否说明了我们在高喊“迈向权利的时代”的同时,却走进了权利毫无约束的绝对化幻境,而遗忘了为权利呐喊的“永恒责任”?[13]
鉴于我国社会公众“权利冷漠症”的普遍存在,一些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热情、激活个体权利的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吹哨人”制度,作为一支域外政府、社会用以促进社会公义的“中坚力量”,能够给我国政府破解权利实践难题带来怎样的契机呢?笔者将其概括为两点:
第一,“吹哨人”制度能合理、及时激活基本权利。单从举报权来说,我国《宪法》第41条赋予了(虽未明确规定但可推定出来)公民举报权这一基本权利,将其作为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的个体权利不同,举报权这种富含“公益”色调的基本权利,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举报权并非个人利益或自由的直接表达,常常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联。宪法之所以赋予公民举报权,就是为了让公民来监督权力机关合法行使权力,帮助行政机关及时掌握、查处违法行为,优化权利行使有序性结构。所以,举报总是与政府行为“形影相随”,而政府是社会公益的代表,这使得举报权具有“公益性”的天然面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我国社会公众往往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民思想,认为打击违法行为、加强行政监管是“公家”的事,在面对违法行为时,公众往往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自保”倾向,大家纷纷放弃为权利而斗争的义务和责任,争相“搭便车”,不愿为权利而发声。另一方面,举报权的行使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举报人在进行举报时往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成本和风险,尤其是内部人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关系,如果告发导致组织利益受损,告发者不仅要承受组织内部其他成员的负面评价,还有可能遭到组织或行业的排挤、报复,会对其经济收入、职业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在解决这些权利怠于行使的问题时,我们必须从其本质特性出发,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吹哨人”制度的法律构造逻辑起点就是举报权的本质特征,由此延伸出其他制度安排,成为激活基本权利,根治我国社会“权利冷漠症”的切入点。
相较于一般的举报制度,“吹哨人”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组织信息的外部传递,其落脚点在于特殊范围内、具有特殊信息地位的“内部人(Whistleblower)”。在这样的背景下,“内部人”在对组织内不当行为进行揭发时,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组织成员与社会人双重角色共存,在举报行为发生时极容易产生伦理困境。所以,内部人举报所引发的后果是组织成员、组织、社会三个单元之间交错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的权力关系。政府必须通过奖励、保护措施来引导行为人,让举报人在举报前产生举报动机,在举报时提供伦理关怀,在举报后给予持续、有效的保护,全方位给予举报人制度的关怀,权利用起来自然也会十分“上手”了。事实上,国外的“吹哨人”制度在社会管理、公司治理等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以物质奖励的形式来激发揭发者的举报热情——“告发人诉讼”制度“功不可没”。所谓“告发人诉讼(Whistleblower Litigation)”,是指告发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认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政府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一定比例的罚金作为奖赏。[14]这一制度最早在1388年英国的《水污染防治法》(《Water Pollution Act》)中出现,后来美国在1863年制定的《防止欺诈请求法》(《False Claims Acts》)也进行了规定。具体的方式是:告发者可以选择会同司法部代表政府提起民事诉讼,若告发者提供的信息属实且新颖,那么在联邦政府据此追回相关款项的同时,告发者可以获得25%的罚金;如果不选择让司法部一起参加诉讼,告发者甚至可以获得30%的高额酬金。这种特殊的激励措施,一方面能够将揭发者所提供信息的重要性通过比例的形式与最终挽回的损失相挂钩,相较于我国目前的有奖举报制度的奖励形式更为合理,对于举报人的激励程度也更大;另一方面,可以使告发者主动、积极参与到后续行政机关证据的收集、挖掘,法庭作证、质证等过程中来,增加其参与程度,从而激发其行使举报权的勇气和热情,同时也可以弥补告发者面临法律救济时必然面对的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可能损失,比如升迁受限、同事的冷眼相待、被调离原来业务岗位或范围等不利益。[15]可见,在“吹哨人”制度中对于举报者激励方式的制度设计更加符合举报者的具体处境和心理预期,表现出其对基本权利本质特征的关注。这样的制度安排突破了传统行政理论的单一视角的局限,将目光投向相对人一方,注重对相对人行为机理的体察,确是在总结和重新认识传统行政模式后所生出的制度“新芽”;它蕴含并倡导了一种人人应该维护社会道义的公民价值观,展现出改变我国社会公众“权利冷漠症”,促成社会善治的良好契机。
第二,“吹哨人”制度能使公众以“资讯提供”的方式参与整个社会监督,更具针对性、直接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传统一元化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模式开始形成。[16]全能政府的失败破产,社会自治力量的归位,不断促成“政府要减轻管理压力”与“社会欲扩大自治空间”双向需求的统一。因此,公众参与成为政府开展公共改革的主要“阵地”。在参与理论中,公众参与因功能设计取向不同,会产生不同范围、不同效力和不同方式的参与形式。朱新力、唐明良两位学者在论证说明政府引进公众参与具有多层次目的基础上,以公众参与的功能为划分标准,将公众参与归纳为三类:以资讯提供为主要功能的公众参与模式,以权利利益防卫为主要功能的公众参与模式和以判断形成为主要功能取向的公众参与方式。[17]笔者对此种类型化分析甚为赞同,但在此着重论述的是第一种参与模式,其与“吹哨人”制度的联系也最为密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方面信息在借助高科技媒介的传递下,更加容易发送、接收;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格局下,很容易造成部分主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形成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这就导致即使是具有强大组织、执行、监管力量的政府,也会面临信息获取困难、决策缺乏正当性的窘境。我国政府当前广泛采用的举报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等作为资讯提供功能的参与方式,都是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的实践注脚。“吹哨人”制度亦是社会公众以资讯提供的方式参与到政府活动中的重要形式。不同的是,该制度以“内部人”作为为行政主体提供信息决策依据的潜在参与者,比以广泛的社会公众为潜在参与者的举报制度,更具有信息获取的针对性。因为,“内部人”本身就很有可能是信息“垄断”格局下的制造者、享有者、使用者,有获得组织内部信息的权利、路径、机会,对于违法行为的发生、经过、后果往往了如指掌。“吹哨人”制度能通过为潜在举报人提供奖励和保护的形式,驱使“内部人”将所获知的信息传递到行政机关手中,那么公众参与的信息释放功能会进一步扩大,更有利于行政机关采取行动,来应对隐藏在组织内部场域的违法行为。此外,相对于座谈会、听证会等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举报人向行政机关提交举报材料或信息,是直接参与到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中来:接受举报的机关必须对内部人举报申请给予答复,甚至在行政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后,让举报人参与到案件调查、证据收集等过程中来,最后给予举报人以一定的奖励,而贯穿其中的则是行政机关对举报信息的保密,以及为举报人提供持续、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这些参与的种种过程,会使参与人获得比单纯的“圆桌会议”参与形式更加直接的“参与感”,对参与者也更富有吸引力。这种参与的针对性和直接性,使得“吹哨人”制度不仅是促成行政机关理性决策的信息收集装置,亦是驱动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行政机关行为决策的整个活动中来的动力装置。
五、结语
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以来,传统行政制度设计的目标定位已经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转向政府、市场、公民“携手共舞”的多元格局。在变动不居的转型社会所引发的错综复杂、交织无序的社会关系面前,行政机关开始抛弃传统制度的沉珂,不再固守管理社会需“事事躬亲”的观念,以更为积极、务实、权变的姿态,尝试运用富含民主参与色彩的、符合社会分工规律的制度来完成包含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等多层面向的行政任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接纳“吹哨人”制度,并在食品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实践与探索,未来这项制度的争议焦点会逐渐减少,共识之处则会慢慢增多,通过立法构建我国统一的“吹哨人”制度可以期待。当然,一项制度的学习和引进,必须要有合理、切实的目标定位,在充分了解、剖析这一制度的外在环境和内生机制的基础上,再做精致、具体、稳步的推进,否则便是机械的模仿或者生搬硬套,会使“吹哨人”制度这一外来“物种”,难以适应我国法律、文化、经济特有的“土壤”,长成苦涩失甜的“淮北之枳”。因此,站在本国的法律、文化的特殊背景下,来考察“吹哨人”制度究竟为几何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本文就是在深入了解、研究国外“吹哨人”制度的外在环境和内生机制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的观察视野从行政监管、公众参与和公私合作三个角度来打量“吹哨人”制度,为发掘“吹哨人”制度在我国特有国情下的支撑点以及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进行本土化制度构建作一些努力和尝试。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如何看待和打量“吹哨人”制度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吹哨人”制度,归根到底还是治理思路的问题,即通过多元、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跃迁。
参考文献:
[1] Nader,R.Petkas,P.J.Black-well.K.Whistleblowing:The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M].New York:Bantam,1972:103.
[2] Alexader Dvck, Adair Morse A,Luigi Zingles.Who Blows the Whistle on Corporate Fraud?[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0(6):2232-2234.
[3] Miethe.Terance D.Whistleblowing at Work-tough Choices in Exposing Fraud ,Waste ,and Abuse on the Job[M].Westiview Press,Crime & Society,1998:21-25.
[4] 佚名.寻找中国版食品安全“吹哨人”[EB/OL].(2014-04-15).http://ent.ifeng.com/HOT/yaowen/detail_2014_04/15/35779919_0.shtml.
[5] 刘源.“獐子岛事件”呼唤中国的吹哨人制度[EB/OL].(2014-11-13).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8,20141113445649940.html.
[6] 周应恒,王二朋.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一个总体框架[J].改革,2013(4):23.
[7] 佚名.欧美建有“吹哨人”制度,内部人攻破食品问题壁垒[EB/OL].(2014-07-22).http://travel.cntv.cn/2014/07/22/ARTI1405995520240573.shtml.
[8] 盐野宏.行政法总论[M].杨建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6.
[9]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28-236.
[10] 吴燕,罗跃嘉.利他惩罚中的结果评价——ERP研究[J].心理学报,2011(6):661.
[11] 沈寨.当权利成为一种修辞——对当下权利实践问题的反思[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32-135.
[12] 章志远.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之法理基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2):90-91.
[13] 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13-15.
[14] 曹明德,刘明明.论美国告发人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J].河北法学,2010(11):69-71.
[15] 李飞.法律如何面对公益告发?——法理与制度的框架性分析[J].清华法学,2012(1):156-157.
[16] 石佑启.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J].中国法学,2005(2):53-59.
[17] 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基本图谱:“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结构的展开路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28-131.
[责任编辑:郑继汤]
收稿日期:2016-05-11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BFX044)
作者简介:詹强(1991-),男,江西婺源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99(2016)04-0045-10
On Whistle-blower System in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ZHAN Qiang
(School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63,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some local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introduce and explore the Whistle-blower System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onnotations in that system. It focuses on the insiders and makes them transmit the internal hidden illegal in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hrough incentive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Whistle-blower System is not only viewed as a technical method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over the market, a connec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 but also is referred to a driving force of the activation of the civil righ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ublic to maintain social morality. Essenti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histle-blower System means the concept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at is, through multiple and cooperative way to achieve the overall trans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Whistle-blower System; legal orientatio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