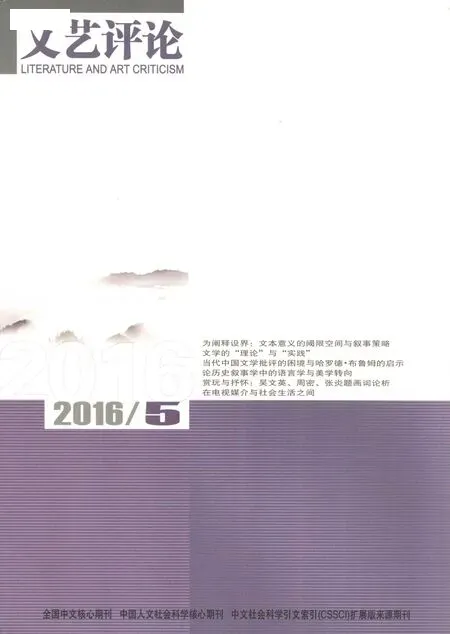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启示
○曾洪伟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启示
○曾洪伟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状况如何?随便翻阅或点击当下一些报刊杂志或网络媒体,如《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中国作家网等,诟病、批评、开方“疗救”当下文学批评的文章可谓层出不穷、俯拾即是,如《文学批评的温度、力度和风度》(刘巍,《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张江、程光炜、方方、邵燕君、高建平,《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重塑批评精神》(张江,《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文学观象:文学呼唤崇高》(张江、高建平、李国平等,《人民日报》2014年8月29日)、《文艺拒绝低俗与铜臭》(南帆,《人民日报》2015年4月10日)、《文学批评理应回归“文学”的批评》(李晓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文学阐释的“强制”与“过度”》(王熙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0日)、《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张江、梁晓声、陈众议、南帆、雷达,《文汇报》2016年1月12日)、《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高玉、谢文兴,“中国作家网”2015年4月29日)等等。这些学者或批评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与层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进行把脉诊断,通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成就当然不容否定,但问题同样不容轻视”①,中国文学批评患上了这样那样的病症,其精、气、神亟需重建与重塑。但在病症的轻重上,批评家们则存在着分歧,有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的“末路说”,有后天缺钙、发育不良的“软骨症说”,有属于疑难杂症的“困境说”,还有需综合诊治的“伪批评说”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病症究竟已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当下批评界有无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与出色榜样?
从综合、整体、宏观的视阈考察,笔者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已名不副实,并陷入了岌岌可危的身份危机、学科专业危机、生存危机之中,必须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否则将不治而亡。这并非危言耸听,蓄意制造文化噱头,以博人眼球:因为当下所谓的“中国文学批评”已名存实亡,既缺乏“中国”立场,又无“文学”之韵和“崇高”之骨,更无“批评”之实。而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立场、批评原则、批评方法、批评个性、批评风格对于缓和、纾解、改善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危机状况,无疑具有很好的学习、参照、借鉴价值与意义。
一、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文化身份、批评主体的迷失与布鲁姆民族与世界、自我与他者对话、互动的文学批评
在当下的中国文艺界,存在着一种批评之怪现状,即批评家罔顾民族文艺作品的本土原发性和民族审美性,简单套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对本土作品进行粗暴切割,“强制阐释”,蛮横裁定,无视外来理论可能存在的文化错位性、水土不服性、排异性以及阐释的局限性,强行将外来评判标准凌驾于本土、民族审美标准之上,或者对后者干脆视而不见,眼中只有西方、异域、他者,而无民族、本土、自我,最终导致民族审美标准在文学话语场中的失声、失语,并被剥夺话语权力。“近年来,文艺批评领域流行一种风尚,那就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一些理论家、批评家总以为只有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先进、高明,中国的文艺作品只有合乎西方标准,才是佳作,否则,无论大众如何欢迎,都是次品。中国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好与不好,本民族的读者、观众说的不算,必须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来评判,人家说好才算好,这种奇怪现象早已为社会各界所诟病。”②例如,路遥《平凡的世界》在出版之初遭遇的“两极阅读”接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谓“两极阅读现象”,即“《平凡的世界》发表后,曾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面是被大众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热棒,一面是专业评论家对《平凡的世界》评价偏低”。导致这种奇异的接受反差的原因何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受到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和先锋文学的话语霸权影响,文学作品有没有现代感和先锋性成为那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由于路遥没有追逐现代派先锋文艺的时尚风潮,“而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坚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扎根大地、根源人民”③,植根传统、彰显民族风格特色,因此,在当时的专业评论家看来,由于其不迎合、不契合当时西方时髦、主流、“前沿的”文艺理论标准,虽然它也受到了中国本土大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但不能被视为优秀作品而进入经典。无疑,这是由于外来批评标准与本土作品之间严重的文化、理论错位和水土不服造成的畸形文学、文化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的。
这种不顾中国文学的本土实际和现状而移除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化根基、丧失文化主体性与个性的文学批评“国际化”(西方化),对本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将带来深层和深远的伤害:从根本上讲,这是借文化引进之名而对自身文化进行的无意识自我文化殖民和戕害,毫无文化对话和文化间性的平等性、复调化原则,亦无文化“拿来主义”在进行文化择取与文化接受时所应该持有的文化审慎、坚持文化主动性与主体性的原则、姿态与心态,这种西方一元独白的、单边的、话语霸权式的文学批评格局与范式(“强制阐释”、粗暴批评)在中国的泛滥,因其极力遮蔽、压抑、消解文化的民族性、主体与自我,所以它并不能真正使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走向繁荣、成熟,不能真正使其走向世界,反而必将导致民族文学(批评)的逐渐枯萎与衰颓。
因此,鉴于当前中国文学批评失语的严重态势,中国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批评的中国性、主体性或者说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当然,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身份与自我身份,并非必然意味着排斥西方批评理论资源与模式,意欲让中国文学批评走上类似以往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一元独大/霸的歧途与老路,而是在继续引进西方/外来批评理论资源的同时,积极建构、强化民族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和主体性,以破除原先文学批评领域西方/他者独霸学界、文坛,“中国”“自我”被遮蔽、被排斥的“西方”独白的畸形批评格局,建构和维护以“我”为主的中/西二元或中/外多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布局,最终建设一种充满活力、富有张力、既具有世界开放性品格同时又凸显中华民族精神、气韵和品质、具有平等对话性和双向互动性的文学批评。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中,恰当地处理了民族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本土与异域、主体与他者的多元对话、良性互动、动态张力中展开文学批评。一方面,在批评理论、工具、标准的选取和使用上,他有对异域文学理论、美学理念、学术观点的吸纳与引进。如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在其核心的文学批评思想中,我们可以窥见康氏的影响:“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④“……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⑤而英国唯美主义者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对布氏的美学思想影响也很深,并由此而促成了他唯美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与塑造:他自称是“一个终身的唯美主义者”,并宣称“审美王国”是“真正诗歌”的唯一泉源。同时,他还接受了佩特的看法,“把浪漫主义定义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strangeness)效果的艺术,并认为这种观点适用于所有的西方经典作品。于是,他把从但丁的《神曲》到贝克特的《终局》这一文学历史进程看作一个从陌生性到陌生性的不断发展过程。他认为,这种陌生性是一种无法习得的审美原创性,只在少数天才作家身上才能产生,而只有莎士比亚等人才能把人情风俗的‘陌生化’推向经典的高度”⑥。另外,布氏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对西方文学史的循环四分法又受到意大利学者维柯的历史循环三阶段(神权、贵族、民主三个阶段)理论和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对西方文学史的四分法(传奇的、喜剧的、悲剧的、讽刺的)文学循环论影响。同时,布鲁姆又有自己基于外来理论的戛戛独造,如体现其理论身份、学术地位、文化声誉的“误读理论”,它是布鲁姆“利用弗洛伊德的著作提出了[的]过去十年中最富有大胆创新精神的文学理论之一”,“布鲁姆所做的实际上乃是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重写文学史”⑦。如今,这一理论(或称“影响的焦虑”理论)被他广泛地应用于(经典)文学批评、宗教批评实践之中(前者如《西方正典》,后者如《美国宗教》)。另外,在面对外来理论与思潮的涌入时,布鲁姆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理论立场,本着“根据所需,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原则,运用自己的眼光,有所吸收,但同时又有所选择,充分体现出其理论择取的自觉性、主体性、主动性以及个性。如他对策源和生成于法、德等国的去审美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批判与拒斥。
另一方面,在文学(经典)批评标准或参照系的选择、建构上,布鲁姆既树立了异域/世界标准,如世界经典的核心莎士比亚,又建构了本土/民族标准,如美国民族经典的核心惠特曼,两者都被应用于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且两者各具特点,具有同等批评地位,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在布鲁姆看来,它们只是适用于不同的批评空间和文化场域而已:莎氏主要用于评判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而惠氏主要用于衡量美国文学。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没有一位西方诗人,包括布朗宁、莱奥帕尔迪或波德莱尔,其影响能够超过惠特曼或狄金森”⑧,“艾略特和福克纳也许最能挑战惠特曼,这是就他们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而言,但是这两人还没有他那几近世界范围的影响和重要性。狄金森和詹姆斯的美学成就可以媲美惠特曼,但他们在普遍性上也无法与他抗衡。美国文学在国外总是以惠特曼为第一位,不论是在西班牙语美洲国家,还是日本、俄国、德国或非洲都是如此”⑨。即由于惠氏的世界性影响,他也被布鲁姆用于作为其它国家(如拉美等国)的文学批评参照系和标尺。而由于其诗歌的独特气质,布氏认为,即使是作为世界经典核心的莎士比亚在某些方面也未必能超过惠特曼。“他(惠特曼——引者注)是我们时代氛围的诗人,无可取代也无法匹敌。英语世界中只有少数几位诗人能超过《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绽放时》:莎士比亚、弥尔顿,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人。甚至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否已经取得了比惠特曼的《紫丁香》更急切的哀情和更阴郁的词藻,这一点我都不能肯定。”⑩这就是说,布氏并不因为莎氏的普遍性和卓越艺术成就而无限拔高或任意神化莎氏,张扬他者世界性,压抑或贬黜主体/自我的民族性。“民族”与“世界”同台演绎,两者共荣共存,互不排斥,在各自适合的批评场域发挥各自的标尺、衡量作用。这体现出布氏意识深层兼收并蓄的宽广世界视野和理论胸怀以及强烈的文化平等意识。
因此,布鲁姆在其批评实践中立足、扎根民族/本土,胸怀国际,放眼世界,努力营造与建构一种多元、平等、包容、对话、富有张力与活力的批评氛围与范式,极力反对外来理论与文化对自身文学、文化的蛮横绑架与强制阐释,充分体现出其充满民族文化自觉性、不迷信、不盲从、不厚此薄彼、具有清醒的文化择取意识、深度的文化辨识力和高度的自信力、主体性突出的文化品格和个人魅力。这无疑是值得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批评界学习与借鉴的。
二、当下中国文艺批评的审美缺位与布鲁姆的唯美批评
当下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批评家将商业标准与艺术标准错置,将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导致文学气息淡化、艺术风向迷失、美学风尚俗化、矮化、丑化、恶化。“时下的文艺批评,面临着艺术标准与商业标准的博弈。一些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不是从艺术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商业的立场出发,哪些作品在市场上受到热捧就追踪哪些作品;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以点击率、收视率、销售量为依据,认为有了好销量就是好作品,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而真正的文艺批评或者说有责任、有担当、专业/美学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应该是“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在大量潮水般涌来的文艺作品中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选出来,推介给人民大众,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⑪即文艺批评应该首先坚持艺术标准第一的原则。
文艺批评审美缺位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文化化),即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部,批评的去审美化现象一枝独秀,并形成一股强制阐释和消费潮流,横扫文坛和学界;西方20世纪先后涌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批评理论与方法(如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符号学、原型批评、叙事学、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与概念术语(如陌生化、互文性、交往理性、身份认同、文学场、性属、族裔、文化霸权、身体、创伤、空间、生态、动物、文化记忆等等)被批评家们广泛应用于中外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之中。由于这些批评理论和方法大都不是从审美和艺术(艺术创作、艺术手段、艺术构成、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等)的剖面切入研究文本,而是从更为广义和宽泛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角度如文化学、心理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生态学等观照文学,文本的艺术性、文学性被遮蔽、被覆盖,而其它非诗性特征则被阐扬和被放大,甚至被过度阐发,这样文学批评就不再是一种艺术探掘和审美批评,而是褪变和转型为一种它学科研究,文学研究者从(审美批评)“专家”演变为(跨学科、超学科、多学科)“杂家”,“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⑫,文学研究不再与审美相关,而文学文本也沦为这些批评理论(有效性)的试验场和验证所,因此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越来越淡薄,批评离文学越来越遥远,文学批评的生态格局严重失衡,而由于审美内核的缺失,文学批评更是面临一场学科合法化生存危机。
“文艺批评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它们不能离开审美的批评。”⑬而哈罗德·布鲁姆是严格坚持审美至上原则的批评家。作为唯美主义者与审美本质主义者,由于深受康德“审美无功利性”和奥斯卡·王尔德、沃尔特·佩特唯美主义思想影响,布鲁姆坚持审美自主性原则,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⑭,“……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⑮。因此,审美成为其文学批评的核心或者说唯一衡量标准,而其它的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因素等则被统统排斥在外。如他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对以“憎恨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热潮和对《哈利·波特》、斯蒂芬·金通俗畅销小说阅读时尚的极力批判与声讨:“……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⑯“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各家图书馆也难逃此劫。我被一再地告诫说,孩子们读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他在读书就行,不管他读的是哈利·波特还是斯蒂芬·金。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因为学着去读《哈利·波特》会使你进而要去读斯蒂芬·金的小说,这也正是后者在评论最新的《哈利·波特》时得意地宣称的。这篇评论发表在反文学的《纽约时报周日书评》上。”⑰在他看来,这些文化活动、文化现象以及文学作品中审美要素的缺席与丢失,或者说非审美因素(如政治、文化、道德因素以及商业因素)在文本批评或文本构成中喧宾夺主,鸠占鹊巢,凌驾于审美因素之上,使文学批评实践和文本生产、文学消费剑走偏锋,误入歧途,迷失方向,并势必使文学和文学批评陷入生存困境与危机。由此,布鲁姆提出了“以艺术抵制理论”(art against theory)的口号,旨在以审美批评反对当代肆虐、横行文坛和学界、呈一边倒的政治批评和文化研究(这里的“理论”并非泛指所有理论,而是特指去审美化的批评理论形态),以此矫正和祛除当代文学批评严重的去审美化极端趋向与偏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布鲁姆作为一个唯美批评家的审美“良知和纯度”。
因此,布鲁姆的艺术/审美至上批评原则,对矫正和重建当下中国文艺批评原则与标准,引导文学批评和文学生产、文学消费走出去审美化(即市场化、商业化、理论化、意识形态化)的迷局与困境,重振文学、审美的士气,重树崭新的时代文学、美学风尚,无疑具有较大的学习借鉴价值与意义。
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崇高的缺失与布鲁姆对崇高的坚决捍卫
在当下的中国,在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日渐增多、日趋严重的现实问题,并在文艺界和文学批评界广泛蔓延,发展成为一种顽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这其中之一就包括崇高、高雅缺失而通俗、庸俗甚至媚俗、恶俗盛行,崇高陷入无人喝彩的尴尬、落寞境地。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当下的文化领域,‘躲避崇高’已非个别现象,反而成了某种时尚,放纵欲望、淡漠理想、娱乐至死的风气日渐乖张。言及崇高,不仅很难引起共鸣,甚至还会遭到嘲笑,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诉求和当下国家经济文化的强劲发展,高歌猛进、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和时代主旋律,以及文学本身的核心价值和主流倾向,都迫切需要和热切呼唤大量具有崇高风格、高雅形态和大气磅礴的作品问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强大又对未来充满梦想的民族。这是一个充满崇高精神的过程,需要产生具有崇高精神的、大气磅礴的作品”,“在今天这样一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文学都是一副面孔、一种风格。但是,倡导审美多元化、风格多元化,并不是要让低俗取代高雅、猥琐消损崇高。文学无论分化出多少种风格,它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引领人、提升人,让人向着宏阔、高尚、博大的精神之地进发。就此而言,崇高又不仅是一种风格概念,它更是一种精神气韵、灵魂色彩。如此意义上说,崇高应该成为所有作家和作品的执着追求”⑱。然而,理应担当起指引文艺创作方向的文艺批评此时却哑然失声,未能积极、主动发挥其引导文艺创作的现实职责与功能,而且由于深受商业利益的蛊惑或诱惑以及后现代消费文化、时尚、风潮的熏染,文艺批评也羞于或耻于论及、更勿论倡扬崇高的文艺风格,文艺创作中崇高隐退、淡化、缺席,低俗、庸俗肆虐横行,中国文艺创作普遍缺乏审美/艺术的纯度和高度,以及人文关怀的深度,从而也降低了中国文艺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声誉度。因此,在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中,仅仅提倡审美维度的文学批评还不够,还必须针对当下中国的文学现实状况,大力提倡和强调崇高指向的、具有崇高风骨的文学(批评)。
而哈罗德·布鲁姆特别关注和强调文学的“崇高”审美品格,并在不同的论著与场合对其(以及相邻概念如“经典”、“天才”等)进行了阐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崇高”成为他文学/美学思想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在其早期的著作《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1989)中,我们可以初见他对于“崇高”(sublime)的论述,而在其后的《布鲁姆文学主题:崇高》(Bloom’s Literary Themes:The Sublime,2010),《影响的解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2011)和《魔鬼知晓:文学伟大与美国崇高》(The Daemon Knows: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2015)以及《西方正典》(1994)、《天才:一百位创造性心灵典范》(2002)等众多著作中,他对于“崇高”或相关概念、话语的阐述与理解越来越翔实,越来越深入,并日益多元化。总体而言,无论从批评理论还是从批评实践来看,布鲁姆都是极力推崇与拥趸崇高形态的文学风格的。
在布鲁姆看来,崇高是一个多维、立体、具有丰富意涵的概念。它既指一类文学(文本),又主导文化文学(文本)、高雅文化文学(文本)、大众文化文学(文本)、民间文化文学(文本)中的高雅文化文学(文本),其具体表现形态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具体范围则是他在《西方正典》中所罗列的、类似宗教圣典性质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从“神权时代”到“贵族时代”、从“民主时代”到“混乱时代”的“唯美”经典文学文本(如乔叟、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等“强力”或“精英”作家的作品)。“本书(指《西方正典》——引者注)对作家的选择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是随意而为。所选作家的理由是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因为一本书可以论述26位作家,却容纳不下400位人物。”⑲同时,它又指一种审美/经典衡量标准:“我们只能说,《创世纪》与《出埃及记》《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奠定了文学的力量或崇高,以后我们就用这种衡量标准去评价但丁和乔叟、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⑳崇高还可指一种文学生产、经典生成或竞争模式(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亦或从读者接受(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审美接受/体验心理(即具有难度的审美感知与体悟)。“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想我真正的主题就是传统所说的崇高,我将——效仿古人朗吉努斯,还有《为诗一辩》中的那个雪莱——把崇高看做是文学竞争的模式,每个人都要努力回答他与过去及现在的竞争对手较量时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优于,等于,还是劣于?朗吉努斯和雪莱还暗示说,文学的崇高就是读者的崇高,也就是说,读者必须能够推迟快感,放弃简单的满足,为的是一种比较迟缓的、难度更大的回报。那种难度是原创性的真正标志,这种原创性必须显得古怪,直到它篡得读者的心理空间,作为一个新的核心确立自身。这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理论,甚至比朗吉努斯还古老,因为它可以追溯到阿里斯托芬在《蛙》中的描述。这是关于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一次比赛,而欧里庇得斯则表现了影响焦虑症重患的所有病症。”㉑另外,崇高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艺术手法(即“塑造人物的无所不包的特性”)。“而布鲁姆认为,崇高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是最为丰富,也是最为多变的。莎翁的崇高主要体现在其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上,如福斯塔夫、哈姆雷特、奥赛罗、伊阿古以及李尔王。正是这些栩栩如生的崇高性人物扩展了我们的意识。阅读这些人物的过程就是理解伟大,即积极与消极的过程,也是在我们自身中分享这种伟大的过程。布氏眼中莎士比亚的崇高性就在于其塑造人物的无所不包的特性,那种融合了积极与消极的特性。从这一角度看,布鲁姆继承浪漫主义有机论对莎士比亚剧作人物、剧本体裁与特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崇高观。”㉒
尽管布鲁姆的崇高概念具有繁复多姿的涵义,但其最明亮的底色与核心内蕴还是对于“庄严”“高尚”“宏大”“深沉”“雄浑”“伟大”“力量”等美学品格与气韵的吁求。而他在后期之所以如此热烈地推崇与膜拜、强调与阐扬崇高风格,为高雅文学奔走呼告,是与他不满此期(后现代社会)迎合大众、消解崇高、去除高雅、崇高失落、大众狂欢、平庸美学盛行的文化现实与潮流密切相关的,即他拟以审美现代性的分化对抗后现代主义的去分化,以崇高抵挡凡俗、庸俗、低俗的侵蚀与扩张,并尝试恢复和重建现代主义的精英美学景观。“布鲁姆重建西方经典的做法与他对美国文学现状的悲观看法有关。他认为当今西方文学已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到处蔓延。出于抗衡时代‘流弊’的愿意,他要以‘审美价值’为核心重建经典的历史,并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根本标志。”㉓而布鲁姆重申与强调崇高的社会现实语境与当前中国崇高缺失的文化现实环境高度类似,他对于崇高美学的坚持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学与文化对于崇高的大声呼吁与热切呼唤正相适应。
因此,研究、学习布鲁姆的崇高观与文学批评对于改变当前中国非理性的文学、文化现实,一定程度地改善和优化失衡的文学生态和畸形的文学批评形态(崇高缺失),增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崇高底色,提升其美学品格/位,无疑具有重要的精神、思想资源价值和理论反思意义。
四、当下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失声与布鲁姆的否定美学
当下中国文艺批评的又一个严重问题,是“批评”的质疑、否定、批判、建设精神与品质已走样、变味,“批评”的本性缺失,徒剩表扬而毫无批评可言,圈子、面子、人情、红包批评、“伪批评”盛行,批评和批评家已然失去身份存在的意义与依据,并由此引发学科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在当下文艺批评场域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声音微弱,批评理念、判断标准混乱,文艺批评本身也面临边缘化趋势和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和当下一些批评家批评精神缺失、批评锋芒消退,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沦为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势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些批评家在不良思潮、低俗趣味、错误思想面前不敢发声,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有的批评家眼里全是面子、圈子和人情,一味跟在创作后面点头应声、庸俗吹捧、拍马奉承,表扬唯恐没能说足说尽,批评则躲躲闪闪,甚至有人操守沦落、格调低下,把文艺批评视为博取学术资本、为人炒作造势的工具”㉔。
“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发展的,还是诊断性的批评。这是一种切断种种利益链,直面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讲真话、说实话的批评。学院中的文学研究者们有优势,应该也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㉕,“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㉖。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批评界,众所周知,布鲁姆是一位个性不羁、傲然独立、不媚俗、不迎合、不从众、不附和、具有鲜明批评风骨和强烈批判意识与精神以及犀利批判锋芒的批评家。他的质疑精神、反叛性格、否定美学已成为确定和辨识其独异批评身份的鲜明标识(因此他是一位对抗型、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其误读理论也被学界戏称为“抬杠诗学”或“对抗/反叛诗学”。而这一批评品格也是导致他新见迭出、建树卓著、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什么东西,我一概反对。”其文学批评的一生可谓是批判、反叛的一生。从最早的T.S.艾略特、新批评到解构主义,再到后期的文化批评(憎恨学派)、通俗文学、电子文学、声像文化乃至宗教文学,布鲁姆一律质疑之、批评之,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诸多在批评界卓有影响的著作,如《西方正典》《美国宗教》等。“我依次反对过T.S.艾略特,新基督徒式的新批评主义及其信徒、保尔·德曼及其同伙的解构主义,反对过当下新左派和老右派对文学经典所谓的不平等和道德可疑性进行的攻击。”㉗
因此,引介、研习布鲁姆及其批评作品,对重塑中国文艺批评精神,重建中国文艺批评生态,净化和优化批评风气,重构良好、良性、复调、富有张力、活力、生命力的批评格局与批评图景,推出优秀、高质、有分量的批评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性与布鲁姆批评的开放性、接地性
上述四点探讨的是中国文学批评本体或者说其内部所存在的问题,而从外在或者说从它与学院外社会、文化大众的关系来看,由于中国文学批评整体缺乏“走出去”(走出象牙塔)的自觉、主动意识,与象牙塔外广泛受众缺少有效的对话、交流、互动、沟通,这对其生存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加重了其危机。
高建平先生在检视、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状况时,明确地指出其“滑进纯理论的象牙塔”、日益与学院外的世界、社会隔绝、疏离、隔膜的趋势与弊端。“过去几十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文章,也许可以大致这样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文艺思想的大转型。旧有的观点被突破,新的思想形成,出现了许多有冲击力的文艺批评文章。到了90年代,学术界检讨80年代的空疏,大兴引文注释之风,文学理论和批评走向学院化,这对纠正时弊的确有一些作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一些学者那里,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讲思想,不讲社会功效,躲进学术的象牙塔,做纯而又纯的‘学问’。这恰恰是学院批评之弊。”㉘学院批评家往往借维护学术纯粹之名号,有意与社会脱节,与群众脱钩;他们以生产“阳春白雪”形态、面向象牙塔内小圈子同行、高高在上的“纯粹”学术产品为荣、为傲、为正宗,而拒绝批评的社会化、大众化,更毋论使其发挥社会功用。
学院批评家长期固守知识精英的价值观、优越感和“做纯粹学问”的理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封闭、保守、僵化的精英意识、思维模式与姿态,再加之在学界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社会化与大众化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并未为大多数人所认识,而且文学批评成果的社会转化(即服务社会)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行,因此,在这些或主观或客观因素的误导下,学院批评家往往与象牙塔外的世界缺乏主动的交流互动,对社会、大众的精神诉求、审美希求以及批评的社会功用漠不关心,文学批评沦为他们在象牙塔内自导自演、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我欣赏/陶醉、不接地气的独角/白戏,最终批评离社会、离大众越来越远,而社会、大众亦逐渐疏离批评:批评与大众之间彼此隔膜,互不关心,文学批评与社会大众似乎成为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这种自我封闭与画地为牢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播范围、受众群体日益萎缩,生存空间日显逼仄,学院批评缺乏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开阔空间、宽广视野以及广泛的受众基础、肥沃的社会土壤、丰富的文化源泉、鲜活的思维气息,中国文学批评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和发育不良症,缺少生机、活力与生命力,再加之中国文学批评自身存有的种种缺陷与问题(如前面所述四点)以及当前其它文化形态(如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图像文化、消费文化)的强力挤压,中国文学批评虽表面繁荣但内里却危机重重。“学院常常有学院的标准,但学院的标准,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于更高更内在的社会标准。”㉙因此,在遵循学院批评自身内在的学理逻辑、规律与规则的基础上,为获得健康的发展和强劲的生命力以及为促进批评的繁荣,学院批评不应闭关自守、闭门造车,而应敞开胸怀、开阔视野,主动走上与社会相结合的道路。
在前期,布鲁姆也是象牙塔内一位资深的学院批评家,其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学者批评,其产品形态也是标准的、传统的学院批评,他也曾反对学者批评溢出象牙塔,与社会勾连融合,而极力维护学院批评的学术“纯粹”性与封闭性;而到了后期,为矫正当代文学精英主义潮流的文化偏至以及其引发的现实危机(文学终结、文学式微),推动经典普及,实施大众美育、心灵救赎,布鲁姆根据时代、社会、受众(普通读者)的精神、心灵、文化、审美需求,改变其批评策略与批评思路,转变其批评身份与批评形态,实现由学者批评向作家学者批评的转换,提倡审美的批评和批评的审美化、大众化以及真正的批评,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使文学批评走出封闭的象牙塔,走入社会,走进大众,注重文学批评的社会效应/益,其批评的开放性、接地性突出:如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社会文化大众编辑了六百余部“切尔西屋”(Chelsea House)文学经典批评丛书,从21世纪开始又专门为青少年学习文学经典编辑了系列文学经典学习指南丛书等等。这些丛书都具有明显的大众普及性质与定位。而其批评(产品)结果也获得了更大的接受、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从而更具生机、活力与生命力:其后期多部批评著作如《J之书》《美国宗教》《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等相继成为全国畅销书与批评经典,此即为明证。
因此,布鲁姆后期开放性、接地性、社会化、大众化性质/形态文学批评的成功转向,说明中国文学批评打破自身的封闭性,改变自身的形象与范式,走出象牙塔,对社会/大众开放,发挥其社会功能,同时获取更大的生存、生长、生命空间和更为广阔的未来无疑都是可能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布鲁姆从学者批评向作家学者批评转型时所运用的批评策略与批评方法,又为如何开放与转型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答案、示范、榜样和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以此而言,布鲁姆批评的开放性对于改变/善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性和生存发展状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习、汲鉴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境遇中凸显出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学习、借鉴、推广其文学批评,可以有效地指导和引导、示范和规范、净化和优化中国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可以一定程度地扭转当下中国文艺界和批评界的不良倾向与走向甚至危机;同时,通过与中国文艺批评遥相呼应和对话,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还可以有力地支持中国文艺批评的理论建构和精神资源建设。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①②⑪㉔张江《重塑批评精神》[N],《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
③张清俐《〈平凡的世界〉研讨会:以读者为中心是文学史批评方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5日。
④⑤⑥⑧⑨⑩⑫⑭⑮⑯⑰⑲㉓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第20页,“译者前言”第2页,第204页,第224页,第225页,第412页,第12页,第20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中文版序言”第3页,“序言与开篇”第1页,“译者前言”第4页。
⑦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4页。
⑬㉕㉘㉙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N],《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⑱张江、高建平、李国平等《文学观象:文学呼唤崇高》[J],《人民日报》,2014年8月29日。
⑳㉑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M],刘佳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第6页。
㉒屈冬《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探讨》[J],《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
㉖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㉗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M].New York: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1994,P.486.译文引自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