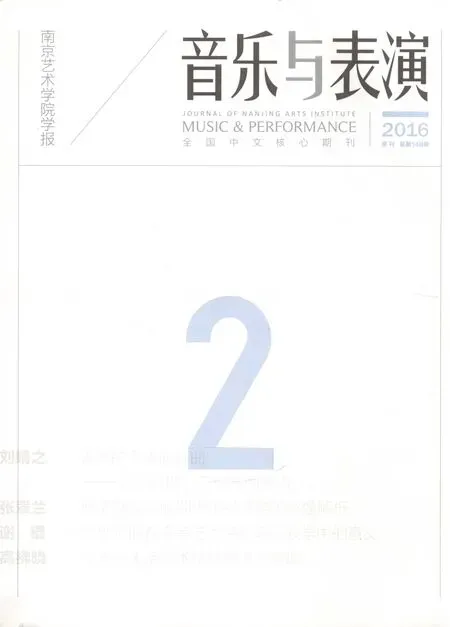论音乐中的喜剧意识── 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机智、幽默和嘲讽表现引入
蔡 麟(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论音乐中的喜剧意识── 从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机智、幽默和嘲讽表现引入
蔡 麟(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喜剧性是重要审美范畴之一,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喜剧音乐表现丰富多样,在西方音乐历史进程中尤为凸显,古典音乐喜剧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和音乐表现范畴存在。本文试从喜剧意识的展现和戏剧运作切入,探讨古典风格音乐喜剧的特质表现及其与启蒙思想之间的契合。
喜剧意识;机智;幽默;嘲讽;维也纳古典乐派
喜剧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质态,即喜剧性,常与悲剧相对,指隶属于美学范畴的审美概念,有别于通常文艺作品中的体裁、门类之说(最常见的莫如戏剧中的喜剧)。不论是作为重要审美形态的喜剧还是作为艺术类别的喜剧,关联密切亦有区别。喜剧性表现特指且涵盖一切存在于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的各类喜剧性审美现象,千姿百态的展呈方式让人领略到喜剧之美的“别出心裁”和“匠心独运”,它们虽与喜剧类作品关系最为密切,却不囿于其中,在众多严肃类型的文艺体裁中 “崭露头角”,极富深意。反之,喜剧体裁作品表象上的逗趣、滑稽总是“笑里藏刀”,真正的意图往往是慧黠地暴露甚至鞭挞那些衰落、虚伪和丑恶的行为及现象,又或是对世间事物摆出理性守望的姿态,以乐观心智获求心灵的坦荡、超脱和升华,彰显严肃的艺术旨趣。
古今中外,众多先哲都对喜剧问题给予关注,许多闪光之见散落在各类文艺理论、哲学美学论述中。但喜剧美学研究尚未形成有机体系,过于笼统,有关喜剧的各类形态特质比较分析匮乏,较之悲剧研究相形见绌。音乐美学对其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音乐史论、音乐分析中对其也是捉襟见肘,不够深入畅快。喜剧审美研究不仅表现为通常的形态分类和常用手法归纳说明,喜剧主体意识的形成、表述和传达,喜剧客体的反应和呈现,喜剧审美接受心理因素的分析等诸多问题都值得研究和商讨。同时,它还历久弥新,甚或发生变异,在不同的时代、文化和思潮影响下,涌现新的喜剧形态范畴或赋予传统喜剧形态以新的意义和概念生成。
鉴于此,笔者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创作主体喜剧审美意识的形成、表现和运作方面,试图以戏剧动因和动作切入,展示音乐中喜剧意识的动态运作过程和效果呈现,并以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创作中的常见喜剧形态范畴引入,试论音乐中的喜剧意识。藉此抛砖引玉,希图喜剧性这个纷繁复杂的重要美学问题在音乐中的表现得到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喜剧意识反思
关于喜剧的本质,历史上诸多美学家、哲学家作过研究,普遍认为,喜剧表现某种矛盾冲突,然而对于喜剧矛盾的特质解读却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而足。
康德认为:“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1],喜剧反映的是期待和结果间的矛盾。柏格森欲把有生气的和机械的嵌在一块[2],将富有生命力、灵活多变和笨拙呆板并置,故生滑稽可笑感。黑格尔辩证地探究了形式巨大和内容空虚间的矛盾,以为喜剧性“是把极端的乖讹荒谬打扮成具有实体性力量的假象,表现出一些根本没有什么真正实在货色的外形和个别现象”[3],因此“喜剧只限于使本来不值得什么的、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归于自毁灭”[4],即以自我否定“收场”。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强调:“滑稽的真正领域,却是人、是人类社会,是人类生活,因为只有在人的身上,那种不安本分的想象才会得到发展,那种不合时宜、不会成功以及笨拙的要求才会得到发展”[5],有力地扩展了滑稽的社会内容和意义。
简言之,因视域不同,对喜剧矛盾的解读也是各有千秋,不论是出于欣赏者的审美心理维度、客体对象自身的探究、主体意识能动性的表现,还是社会、政治、道德因素考量[6],这些观点均有精辟之处,启迪思想,但也不免偏颇,在此提请注意。康德将注意力放置接受者的心理层面,却规避了喜剧本身的主客体,且期待和结果的矛盾并不一定引起发笑,有时反而致悲;尽管西方有“笑论”的学术渊源,但黑格尔鲜明地提出“喜剧性”这一概念,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喜剧之美,可笑性并不等同于喜剧性,更不是喜剧的特质呈现,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以否定性倾向为主的滑稽等喜剧形态,常表现为对可笑人物的模仿、嘲弄,代表西方传统的、源自柏拉图的喜剧 “丑本位”观,强调丑是喜剧的基础、丑自炫为美的滑稽现象[7],但其无法涵盖、替代灵活多样的喜剧大观。
悲剧与喜剧是两种不同质态的审美范畴,二者虽表现形态、手法、审美特点不同,但最终目的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肯定美、否定丑,起到伸张真善美,批判假丑恶的作用。回溯历史,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喜剧观念有了长足进步,有别于之前突出的悲喜对立。启蒙主义时期,随着狄德罗、博马舍和莱辛等人“严肃喜剧”理论的提出,他们更着意于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幽默风趣、勇敢机智的正面喜剧性格,以生气勃勃、自在灵活的善行智举藐视反面力量,巧妙地“化险为夷”。在这股欧洲喜剧改革浪潮的推动之下,悲喜交融的积极意义被发现和肯定。至黑格尔,他的喜剧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辩证性,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悲剧和喜剧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既看到了悲剧与喜剧的根本区别,也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见,美学界对悲剧和喜剧的关联也历经了认识论上的发展:从早期的将二者相互独立关照,到18世纪将二者视为混杂,再到19世纪之后的悲喜剧间的融合与转化。尽管二者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得以重视,但明确它们的个体特质对于喜剧研究仍显至关重要。
悲剧重主客体间零距离、卷入式的感同身受。喜剧的主客体则保持一定审美距离,主体在理性反思中以智慧实现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重理性反思,超越式审视。喜剧矛盾不同于悲剧冲突的悲壮之美,它是温和、无害的,总能 “转危为安”,却类悲剧,常同人类的崇高品行相关联。喜剧比悲剧具有更加独立于题材本身的审美立场,表现手法也更为灵巧自由,价值评判自在其中。喜剧创作主体相对于悲剧创作主体,它更需一种超然、智性、批评和自由想象的审美心境。
二、主要喜剧形态的喜剧意识特质解析
喜剧性作为一种审美质态,本身也是历史的。西方传统喜剧与社会现实及其变化息息相通,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喜剧审美形态也演绎着发展、消退、出新、变化甚或变异的历程。故本文选取维也纳古典乐派中常见的机智、幽默和嘲讽三种主要喜剧形态进行特质分析。尽管为了便于比较说明,将三者区分论述,但事实上,或更普遍情况下,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帮衬、协同合作。如果讽刺是出于对反面现象的否定而嘲笑之,那么善意的幽默和风趣的机智,则以表现内在矛盾或正面事物的卓越才情而令人感受到欢快甚或赞赏的肯定性愉悦。
(一)机智
理性的逻辑性创造,常应用格言式语言,并将其安置到隐蔽处进行“暗箱操作”。机智往往还是故意为之的,因为它常常把存在于两极的事物并置,貌似悖反,使人容易混淆价值判断。有机智必有机心,如能独具慧眼地捕捉喜剧性慧黠,拎出精妙设计的关联,则整个对象便在一种全新的光辉下呈现。这种具有启蒙式(冲破旧知,重获新知)的智性启迪会令人身心倍感愉悦。
海顿的作品33作于1781年,同样包括6首弦乐四重奏,因献给俄国的保罗大公爵而得名“Russian Quartets”,又因这套作品中的小步舞曲乐章由谐谑曲取代,而称作“谐谑曲四重奏”。海顿自称这套弦乐四重奏是以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方式来写作。它和作品20(1772)的创作间隔将近十年,其间海顿在埃斯特哈齐宫廷担任乐长,事务繁忙,主要进行歌剧、交响乐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海顿从事了不少喜歌剧创作,这对他的喜剧音乐写作无疑有很大影响。他为传统严肃的器乐创作注入了机智灵巧的构思、敏捷合理的转换、超然自信的洒脱,这套作品无疑成为海顿喜剧风格的成熟之作,喜剧性音乐作品的最亮点。
Op.33 No.1的第一乐章[8],音乐的虚假调性(D大调)开端有其存在的内在理由和后续逻辑——预示了属调。换言之,音乐伊始,作者便有意将主(b小调)属(D大调)关系“故弄玄虚”,二者相冲撞的两个音符(#A-A)被故意“捆绑”在一起,致使头八小节的调性不够明朗,但同时也暗示了这一乐章中调性等级关联的构成。这种故弄玄虚和模棱两可的效果在头八小节中借助力度的的等级递增得以强化(p、cresc、f),为“悬念”营造气氛,这即是这对不协和半音的真实意图:
谱例1.

直到第10-11小节,随着明确、完整的终止式的出现,主调才“豁然开朗”,主和弦在强力(f)支撑下正式亮相。这一刻的“气宇轩昂”和先前的“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相较,确有些许正襟危坐的姿态。但好景不长,这一架势很快便在两个小提琴声部的半音下行接续中消解,伴随这一消解过程的还有力度的等级递减( f、p、pp )。好不容易得以明了的主调性这么快就被消解的原因是什么?
属调领域的到来!在此,它并没有通常所见的过渡连接。乐曲开篇即通过调性模糊的“设问”给予调性等级构成以交代,故此不需要通常所见的转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清晰有力的说明——同样的旋律以D大调主和弦根音位置的明确姿态呈现,语气坚定,随后辉煌结束。
谱例2.

更富有后续逻辑性的是,再现部处,在真再现之前,匹配了一个貌似更为合理的假再现(50-58小节,A大调),这为真再现开头中的假调性(D大调)伺机而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属主支撑关联。这一切的发生都如此有理有据,真假混杂,却又不同寻常。随后 “捆绑”故伎重演,但不久后伴奏织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悦耳的和弦“慷慨激昂”地否决了此番貌似更为合理的假调性呈现,为b小调主和弦解决的到来“扫清障碍”:
谱例3.

并用卡农式的“sf”对下行的消解因素作强化否定,即肯定主调(呈示部的消解是为了属调的进入),此番进程不像呈示部那么突兀,更显从容和必然。整个过程彰显了喜剧进程的想象自由和比例逻辑。
谱例4.

可见,这个高度发达的音乐心智游戏完全是由音乐语言自身来构建和完成的,这是无可辩驳的纯音乐机智表现:不协和音的真实意图在假调性的后续逻辑与巧智编排中逐渐显现,精简化的“精明运作”配合着快速的喜剧节奏和动作进程,伴奏与旋律间的双关理解游弋于逻辑的智力游戏中。
(二)幽默
幽默的表现范围广泛,虽引人发笑,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发人深思[9],其本身较机智、嘲讽更具包容度,拥有情感质态的复合性。其间有滑稽但不浮夸,有机智但更富人文关怀,有讽刺但不乏友善,一般说来,幽默温厚达观,需要博大的胸怀、豁达的气度和些许自我批评的精神境界,是乐观、理性、人道和自然的结合。它的表现更为奔放、洒脱、超然。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幽默是喜剧的最高级形式,此概念已在当代各种笑论中取得了普遍意义。
莫扎特喜歌剧《费加罗婚礼》中的“认亲六重唱”①第三幕,第18分曲。,据称是其最为满意的一首分曲。这是一首喜剧进程复杂而迅速的六重唱,呈示部的第二群组具有发展性因素,故采用省略发展部的奏鸣曲式。呈示部中的“第一群组”在主调(F大调)上,三个性格各异的主题承载着戏剧进程。首先是马切琳娜欣喜地发现,费加罗就是自己遗失多年的儿子,温暖的民谣式旋律顿时响起,可小提琴却在暗自嘲笑马切琳娜的瞬间转变和母爱泛滥:
谱例5.

随后,唐·库尔乔和伯爵小丑式饶舌性的第二主题跟进,把他们故作姿态、爱管闲事的不安感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最后的主题是个带有感官性膨胀的心醉神迷时刻——这一家三口互拥相认,马切琳娜和巴尔托洛医生先后演唱的增四、减五度音程勾勒出这条旋律的特质,同时,这个不协和音程也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伏笔,最后以半终止结束。
谱例6.

此时,连接部以苏珊娜不知情的闯入开始,她天真地数着钞票,想为费加罗赎身(转入C大调)。“第二群组”伴着矛盾即将爆发的这一刻到来,因此,其本身具有更为激烈的矛盾冲突,带有一定的发展性因素,音乐和动作匹配,四个主题说明了动作进程。一家三口仍陶醉于相逢时刻,不协和音程旋律的重复加剧了矛盾到来的急迫。苏珊娜见状怒不可遏,音乐随即转向属小调(c小调),旋律以二度跟进,七和弦相伴的弦乐心灵震音效果将矛盾推向高潮:
谱例7.

很快,小提琴奏响安抚性旋律,C大调重新回归,但音乐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了结,苏珊娜并没有消气——安抚性旋律中时不时出现那个不协和音响:
谱例8.

因此,第四个动作,可以料想,即是表达苏珊娜更强烈的愤恼——旋律在原有不协和音程基础上,作了加花处理,安抚性的音型虽继续着,但明显是苏珊娜的烦恼情绪占上风。苏珊娜并不像罗西娜那般有自觉自省的超然心态。
呈示部音乐就在这种越来越“闹”的喜剧性进程中结束。再现部是对闹剧的解决,仅再现了“第一群组”中的第一和第二主题。因为第二群组兼具发展性,其间膨胀感的减五度音程已被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它的效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故对于寻求和解的再现部而言,第二群组明显不再合适。
结束部的音响格外纯净,简单的主属和弦,温暖的和声标志着和解的时刻,此处音乐告诉我们:情感质态已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四人沉浸在欢乐中,人际关系安宁和谐。与此同时,莫扎特巧妙地置入了伯爵和唐·库尔乔的小调音响运动,悲喜交织,情感更为复合。
谱例9.

这部歌剧是人物喜剧与计谋喜剧的完美融合,在这个六分钟不到的重唱中,有喜剧节奏氛围、狂欢式“布景”安排、复杂情感交融和启蒙理想的彰显,每个人物都以富有个性的音乐姿态存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真诚友善却充满危机,幽默热情又启迪心智。
(三)嘲讽
在近代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讽刺喜剧迅速发展,且带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政治倾向。喜剧客体往往精神贫瘠,却故弄姿态,成为被揶揄、嘲弄和讥讽的对象。这些对象是人类理性精神所鄙夷的“丑陋”事物,审美主体正是在对它们的鄙弃和否定中,使理性精神上升到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歌剧《女人心》的脚本作者达·蓬特,在剧中将爱情作为反讽和嘲弄的对象,认为情感是毫无意义的存在。但莫扎特的音乐表明其并不全同达·蓬特的观点[10],将嘲讽和感情的顶真并置,不论是变心、装腔作势、故作贞洁还是重寻真爱,即使感情会变,但莫扎特规定情感特质的态度却每每认真,惟其如此,反而构成了对达·蓬特创作本意的“嘲讽”。正因为这部歌剧的审美旨趣暧昧复杂,才引发了褒贬不一的灵活多解。
《难以平息的焦虑》①第一幕,第11分曲。是多拉贝拉在与未婚夫费兰多告别之后演唱的咏叹调,声乐旋律呈典型的正歌剧咏叹调姿态,抒发他对身在军中男友的担忧,但伴奏却以三连音的喋喋不休的饶舌,通篇揶揄她的焦虑之情。
之后,另一位女主角菲奥尔迪利吉的《坚如磐石》②第一幕,第14分曲。依凭夸张的音域表现和花腔的演唱,着意戏仿正歌剧的姿态,表达坚如磐石般的爱情信念。在主旋律高调表白之时,伴奏声部却在下方以模棱两可的姿态质疑她对爱情的忠贞——主和弦的“力挺”(气势满满的柱式和弦与八度附点分解)和“心虚”(tr的心理颤抖和顿音的迅速“遮蔽”)前后并置。
这两首咏叹调通过音乐语汇本体的特性表达反塑了人物形象。喜歌剧音乐语言的隐喻和修辞应该是通俗易懂,不应过分雕琢和装饰。相反,正歌剧主人公往往是王公贵族,主体表现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语言务求高雅、堂皇。因此,这些貌似平凡的和高贵的音乐语言形态间的对峙,反言显正,生动而真切地呈现了嘲讽的效应。
谱例10.

谱例11.

三、启蒙思想与喜剧精神的内在契合:古典式音乐喜剧作为一种表现范畴存在
启蒙思想的核心即理性的批判精神,音乐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发生巨大改变,其中不乏大量的实践和言论,形成蔚为大观的“理性——实践”景象。启蒙理想与喜剧特质具有强烈的内在契合,它们相互支持、映衬,古典式音乐喜剧应运而生,最为直接的明证即喜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同时,喜歌剧的语汇迅速被器乐吸纳再创,各种喜剧手法频频出现,喜剧形态多样。
如果说启蒙理想和运动是音乐喜剧发展进程中的“东风”,那么维也纳古典时期音乐语汇的高度成熟和“自律”便勾勒出“万事俱备”的景象,二者促成维也纳古典乐派成为音乐喜剧表现的黄金期,古典式音乐喜剧作为一种表现范畴存在。不论从种类、质量还是数量上看,此时都呈现了西方音乐历史中喜剧性表现的成熟和高超境况。此后,机智和幽默甚至在音乐中消退,难以再现古典风格中的辉煌,滑稽、反讽、荒诞甚至怪诞虽不时可见,但同古典时期的表现已不可“同日而语”。区别于古典风格自在自为的表述方式,不类巴洛克时期概念式的游戏或猜谜,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运用更多是通过由外向内的置入、“拼贴”得以完成的,不同于源于形式语言自身的游刃有余的“陈述”方式。而且,现代喜剧的情感模式与过去也大相径庭,它打破了悲与喜的情感界限,以悲为喜、以喜当悲,消解了各自的情感特征,使对立面相互转化、彼此同一、互为表里,不再具有明确的褒贬意向。它同18世纪的悲喜混杂不同,虽打破了体裁间的限制,创立了在一剧中同时既表现悲,又表现喜的戏剧形式,然而在其中,悲喜仍然是泾渭分明。而现代喜剧却是绝望的悲转化为荒诞的笑,荒诞的笑表现的却是撕裂的痛和惨烈的悲。这一点充分体现出现代喜剧对传统喜剧审美观念的超越。喜剧性不可能与悲剧性截然相分,有悲剧内涵的喜剧更能反映现代西方人的处境和心理。当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必须回归,但上述关照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感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喜剧更多是得益于古典风格自身的形式语言能量储备和想象性探索。
古典音乐风格是一种戏剧式风格,戏剧即在形式结构中。同巴洛克时期音乐相比,不论在音乐观念还是音乐语法体系本身,二者都呈现一种断裂式跨跃。理性的反思、探索、转化和再造表现在音乐的方方面面,以适应新时期新理念的需求。十八世纪的欧洲习惯了有戏剧作品的生活,戏剧性格已渗透至古典风格创作的方方面面——调性等级体系形成,古典调性等级次序是基于自然泛音的自然张力的等级结构安排,特别强调主属对极,并将这种不协和提高至整体结构层面,从而构成一个个音乐事件,因此调性被赋予戏剧意味和性格,表现意义的范围得到充分扩展;以周期性的乐句感为核心的周期性音乐运动体系的构建,为清晰表述的音乐事件及戏剧动作创造了条件;古典式节奏、拍点、脉动被赋予性格化,甚至力度、休止、装饰音等都被充分赋予戏剧性格;音乐材料和结构的有机聚合(转换、调解),注重挖掘材料潜在的动力性品质,体现音乐陈述的理性逻辑;传统的复调写作,它常给人以严密、紧凑感,有历史的沉淀但缺乏生机,有内涵但难以亲近,对位的古典式再造重新赋予它新的蓬勃生机;古典奏鸣曲原则被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不是一种特定的形式,是一种关乎比例、导向、发展和解决的写作方式,重新诠释,而非装饰处理、再现回归,而非模式化曲体概念。
复杂喜剧的情感质态较为复合,一首巴洛克音乐作品的单一情感进程,虽可将悲剧情愫推向极致,却无法表现灵活多样的喜剧形态。喜剧性矛盾是无害的,正与反、肯定与否定、悲与喜、丑与美,真与伪皆可“和平共处”,甚至相互转化,审美评判自在我心,超然心态理性彰显,这同古典音乐风格重比例、平衡、调解、转换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80..
[2](法)柏格森.笑之研究[M].张闻天,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3](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18.
[4](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84.
[5](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89-90.
[6]朱克玲.悲剧与喜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55-60.
[7]闫广林,徐侗.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53-54.
[8](美)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M].杨燕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0-123.
[9] 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87.
[10] 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歌剧的戏剧[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07-108.
(责任编辑:王晓俊)
J601;J609
A
1008-9667(2016)02-0048-08
2015-10-10
蔡麟(1979—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上海音乐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