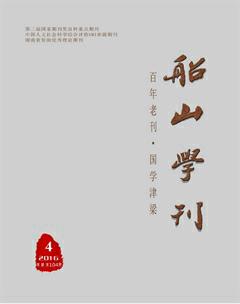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刘可风+解丹琪
摘 要: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极大地改变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基础。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及其统治所带来的传统儒士地位的下降作为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与其它因素一起,共同导致了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并进而对思想领域发生作用:宋代的义理之学由此转向一般并日趋务实;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进一步将其对“实体”的关注转向“达用”;元代的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并为明清实学之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元代;游牧民族;经济伦理;思想;实学
对实学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极,以明清实学思潮为代表,认为实学即实用之学,主张学问须经世致用,与之相对的本体论哲学等形而上问题可谓虚学。广义之极,认为上溯孔子时代,以内圣外王为核心命题的儒学思想均可谓实学。还有相对折衷的观点认为:“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实学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于二者之中的某些内容”。①其中,“实体”是中国实学的哲学基础,侧重于本体论意义,“达用”则侧重于致用。按照这一界定,程朱学派亦可谓实学,只不过相比明清实学,更多地侧重于实体之学。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无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不论采用哪种界定,似乎都不妨碍我们形成如下的认识,即: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思想在从宋到元、直至明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对“实体”的关注一直在逐渐转向“达用”。而元代,正是这一转向的开始。
一、 元代社会的总体特征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元代不论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史所载,元代之前,“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②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直至1271年据《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大元”,并于1279年统一南宋,元代统一全国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却最终得以实现。其版图之大、民族之多,以及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等均史无前例。
元代社会生活之总体特征亦相当鲜明。一方面,蒙古骑兵对中原地区的战争和掠夺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先进的中原文明被相对落后的“野蛮”民族所统治,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发生强烈的冲突和碰撞;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满乱象的社会熔炉中,出于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利益调节的需要,在社会经济从破坏走向复苏、并进而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正酝酿出一种融合之势。这种融合,以各民族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接触和碰撞为基础,是对现实矛盾的反应和反思,也是对各种冲突的力求化解。不论这种融合事实上达到了何种程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以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渗透到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具体而言,地域上,元代对内统一、对外扩张,其版图“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③,实现了长久以来未能实现的“地理之合”;政治上,元代由蒙古族行“汉法”治天下,并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吸纳各色人等,虽难免存在不平等之处,但客观上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促进了“民族之合”。信仰上,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本族多为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对其它各宗教信仰的态度却异常宽容,政策上允许信仰自由,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兼容并包,并呈现出其它王朝难以比拟的“宗教之合”。经济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同传统的农耕民族密切接触并相互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所固有的行为方式,并对我国古代“重本抑末”的思想传统发生影响,形成了元代独特的“农商之合”。社会各阶层之间,元代统治者虽然实施汉法并重用个别儒士,但更为保护蒙古及色目人的社会地位,并格外注重管理权利在各色人等之间的制衡。这一变化使中原传统儒士作为贵族精英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远离官场,或消沉隐居、或迫于生计,涌向曾为他们“不屑”的各个社会阶层,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新的变化和“士民之合”。意识形态上,基于上述社会变革,元代儒者较宋代明显更加务实、并讲求致用,在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元儒始终致力于修正宋末的空疏风气,忌空求实,重视践履。理学内容上以朱陆合流为特征,形式上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表现出一种“思想之合”。这些特征均使得元代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乃至整个思想领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趋向。
二、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
基于如上这些变化,元代的经济伦理关系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精神渗透其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体性关系”,伦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复杂的制度、组织系统和礼俗伦常,体现为现实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其发展是“以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和利益调节的必要性为依托的,是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联系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体现着特有的民族精神”④。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代及其相应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时的伦理关系。曾有学者概括:“与原始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血缘伦理,与奴隶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等级伦理,与封建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宗法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契约伦理,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平等伦理”⑤,换言之,伦理关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实条件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其中,经济伦理关系作为“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伦理意识的支配下, 与其它经济主体、与社会和政府、与环境等形成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关系”⑥,同时关涉经济和伦理两个领域,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画卷,是社会经济关系变迁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endprint
就元代而言,蒙古帝国入主中原,使我国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改变,以社会民众为代表的经济主体与其它经济主体、社会、环境等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亦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从总体上说,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事实上,将元代纳入中原王朝之“正统”,并认定蒙古大汗忽必烈为元世祖皇帝,是以一种包容而宽广的历史观作为基础的:迄今为止,仍有很多学者更愿意用“亡国”或“被殖民”来描述元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原人士的生存状态。确实,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帝国几代统治者征服世界的步伐已遍及整个欧亚大陆,近4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均在其征服和统治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原王朝,只是庞大蒙古帝国所辖广阔领土中的一个区域,仅此而已。这就使得,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原之主的元政府,在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上难免有所偏离:拥有先进文明的中原人士不再是权力和利益的中心,虽然他们极力帮助元廷依“汉法”治国,但中原地区富饶的土地却已然失去控制地暴露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之中。作为战败者,在不平等的新制度下,中原人士无力保全其曾有的荣耀和财富,不幸沦为了蒙古人和色目人之下、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一个阶层。蒙古人的统治,及其对色目人和与之经商的偏爱,使得不少原来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色目商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优待,并进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异域商人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范围日益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日趋频繁。各民族之间所产生的新的冲突和联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和调节的需要,都使得元代的经济伦理关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观元代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经济伦理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在于:这一时期,除了任何时代普遍具有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之外,还有几个更为突出的重要因素明显影响其经济伦理关系。这些因素,即游牧民族的统治和中原儒士社会地位的改变。
客观地说,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元代各经济行为人之间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经济伦理关系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思想领域,促成了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三、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
有元以前,中华民族素以汉族所统治的农耕文化为本,世世代代在广袤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虽不乏“农末俱利”等个别观点,但占据社会主流的,始终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元代蒙古游牧民的入侵和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农耕经济方式与游牧经济方式的冲突、碰撞到融合,却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一状况。
商业精神为游牧民族所固有⑦,这一点,或与其“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有关。
首先,“游牧”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游”,意指迁移、流动。形象地说,游牧民历来“逐水草而居”,过着以迁徙为特征的畜牧生活,其生活半径和流动性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其次,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方式所限,游牧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明显大于农耕民族:其生存状态极易受到夏季干旱、冬季寒流等恶劣气候的影响,有时甚至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⑧。这些困境,一方面决定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产品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也造就了他们所特有的勇气。换言之,游牧经济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迫切希望与农耕经济进行商品交换,但长久以来,中原地区重本抑末的思想传统并不鼓励实现这种交换,故客观上加剧了游牧民族因需求未能满足而进行的战争、入侵和掠夺。
直至元代,游牧民族作为统治者统一了全国,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方式终得以和平共存,并开始以正常的方式进行互市和商品交换。基于这一改变,游牧民族此前执着于战争和掠夺的勇气,才部分转化为从事商业的精神和力量,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原地区固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商业的复苏、发展乃至进步。
具体而言,游牧民族活动半径大、流动性强等特征明显拓宽了人们之间经济伦理关系的视野和范围,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比如,以交通为例,元代较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为积极地广开运河、修筑驿站,并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其中,驿站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及其与经济联系之紧密,均堪称史上之最。如史所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⑨,“溥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驿使往来,如行国中”⑩。区别于专门用于传递文书的急递铺,元代的驿站还担负着运送兵器、钱钞、以及丝、茶等商货的职能。曾有学者整理并指出“元代大站用马多达上千匹,站户超过30万”,而这一相应的数字在唐代是“大驿配马75匹,驿夫25人,小驿配马8匹,驿夫2—3人,驿夫总数约17000人”,明代是“每驿配马30-80匹,驿夫视驿马多少而定”?,元代对驿站的重视可见一斑。又如,元末将领董抟霄用以运送军粮的“百里一日运粮术”更是物流史上的一绝。其“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的陆运之方,可一日实现两万人口粮的百里运输。虽劳民者众,但对每人每次运粮的要求并不算高,只需“负米四斗”“行十步”,且分工合理,注重效率,与现代组织的流水作业法颇为相似,充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对商品及货物流动性的高度重视和相对成熟的操作技术。
不仅如此,游牧民族的对外扩张进一步为我们打开了国门。如前所述,作为中原地区统治者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诸多汗国,客观上打通了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渠道。经济上,元政府更是积极面对外商,欢迎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推行“罢和买,禁重税”的政策,禁止贪官污吏强买勒索,以保护外商权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海外贸易,使泉州港成为当时马可波罗眼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上唯一的最大商港”。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如上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元代商业之活跃和兴盛。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触角亦随之不断扩大并向外延生,内涵也日渐丰富且更加复杂。endprint
四、儒士治生的现实考量
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及其思想之实学转向,亦归因于元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改变。
元代之前,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精英的象征,这一精英既代表学识上的地位,又暗指社会地位。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其说是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道德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其实暗含着公利和私利的问题。一方面,君子作为社会地位较高之人,比小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故相对而言,私利较易满足,甚至可以完全不忧私利。另一方面,君子较小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忧天下之忧”,即更多地以“义”为准则,追求“公利”的实现。故“君子”和“小人”在义利问题上的关注点不同,均系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要求所决定。换言之,以皇帝或士人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不应寻求私利,为的恰恰是让庶民“乐其乐而利其利”。有元以前,大多数时候,知识精英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社会的认可,成为社会地位极高的人;或在其强烈的影响下,使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同时具备知识精英的素质。故“君子”多能集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于一身,始终做到讳言私利,并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传统。宋代,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太祖皇帝削弱武将“杯酒释兵权”,致使传统的“崇武精神”日渐丧失,并由此确立了两宋“重文轻武”的政治基调,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代受到了史上最为优厚的礼遇,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
但是,到了元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蒙古族的入侵和统治,使中原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民众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以元世祖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虽然执行汉法并重用了少数汉人幕僚,但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管理方面,仍多以“求富务实”为目标,普遍重用蒙古或色目商人为朝廷显宦。不仅如此,元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极不平等的四等人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如前所述,蒙古人和色目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诸多特权;居住在北方包括金朝遗民在类的所有人统称汉人,位居三等;南宋遗民因最后才被统一,被称为南人,地位最为低下,而众多才华横溢的江南儒士恰在其中。
这些精英们大多与仕途无缘。他们中间,少数人因为民族气节不愿为元廷效力。多数人则是入仕无门:元代科举的废止斩断了他们走向仕途的通道,即便在1315年科举恢复之后,由于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地位之不平等所决定的考试难易程度和录取名额上的悬殊,仍然使得真正能通过这一方式走向仕途的中原人士少之甚少。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很多以往地位高尚的士人沦为了庶人。一时间,“九儒十丐”竟成为了这些知识精英们的生活写照,他们地位卑微,甚至不如娼妓,只比乞丐好那么一点。社会因此而蒙受损失,但同时,又由于这种新的结构,产生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曾称之为“精英作用的扩散”。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儒士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向很多曾为他们不屑的行业,而这一过程恰好使这些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关注。儒士精英们“被迫”在更为广泛的空间中施展才华,却客观上促进了元代社会各行各业、各经济部门之间更加均衡而全面的发展。
如前所述,倘若对孔子所言“君子”和“小人”作社会地位之理解,元代知识精英们此刻的命运正在从“君子”沦为“小人”。其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之自然而然地更接地气,更加务实,并可以合理地“喻以利”。这些,都为元代经济伦理思想从“实体”向“达用”之转向创造了现实条件。
五、义理之学的经世致用
基于如上社会背景和经济伦理关系之变迁,素来高高在上的义理之学开始逐渐走向平常细事,并日趋务实、以求致用。
元儒郝经(1223—1275年)的“有用之学”和许衡(1209—1282)的“治生论”便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
郝经,出身于名儒世家,战乱中家境没落,多年来“忍穷为学”,“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饱经沧桑,学有所成。其思想保留以宋代理学的总体框架和意旨,但很多方面有较大革新。
首先,郝经格外重“情”,这一点,有别于宋代理学强调“性即理”或“心即理”的朱、陆两派。在他看来,“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情之生也,发于本然之实,而去夫人为之伪”。他承认“有情则有欲”?,对“形而下”的自然人性和欲望予以肯定,认为“情”乃去伪存真的本然之实理,尽“情”乃“下学上达之道,自流徂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学也”?。因此,他批判“后世虚空诞妄之学”为“不情之学”,认为他们“务乎上而不务乎下,务乎伪而不务乎实,谈天说道,见性识心,斩然而绝念,块然而无为而不及情,其所谓性与心者则安在哉”??言语间,“上”“下”争锋,“伪”“实”相对,重“情”及求“实”之心切,可见一斑。
郝经还强调道之简易,认为学问应当“近而易行,明而易见”。“谓夫虚无惚恍而不可稽极者,非道也;谓夫艰深幽阻高远而难行者,非道也;谓夫寂灭空阔而恣为诞妄者,非道也。”?所谓“至易者乾,至简者坤”,在他看来,真正的道“非有太高远以惑世者”,应当是简而易行,“至中而不过,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的。
基于同一思路,他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创见,认为“六经自有史耳”,“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明显撼动了传统观念视六经为千古不变、万世常行之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思想,是郝经的历史观,更是他的经世论。因为,从“史”的意义上去解读“经”,主张“六经自有史耳”,并立倡二者一之,无异于将可能溺于训诂、或泥于高远之经学重新拉回实处,以求“落地”。而这一点,正是当时社会所亟须的:“训诂之学,始于汉而备于唐。议论之学,始于唐而备于宋。”郝经批评“训诂者或至于穿凿,议论者或至于高远”,并要求“学经者不溺于训诂,不流于穿凿,不惑于议论,不泥于高远”?,其现实主义思想可谓一剂清风,对宋末虚妄空寂之学术风气凿有一定的“填实”之效。
以此为基础,郝经的有用之学更是自成风格,并颇具功利主义的意味。“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21)与那些高高在上、只读圣贤书的儒士不同,郝经为学的目的恰是“道济天下”以“经世致用”。这一态度或源于他对现实的追问,即,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的宋代会在蒙古蛮族的侵略下不堪一击?为什么在宋廷垂死之际,仍为国奋战且立下功勋的,不再是那些平日饱受优待且高调论战的士大夫们?如他所言:“理之统体,则谓之道;道之功用,则谓之德;德之充全,则谓之仁。”(22)郝经将“德”界定为“道之功用”,“仁”界定为“德之充全”,换言之,“仁”就是“道之功用”发挥得较好的一种境界。可见,在他看来,“功用”乃评价仁、德与否的标准,无“用”则不可谓之“德”,更不可谓之“仁”。这,便是郝经立志不学无用之学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基础。endprint
为了学以致用、道济天下,郝经拒绝成为隐居出世的“山林之士”或流于训诂的“文章之士”。他“用夏变夷”欣然应征,为“行中国之道”的忽必烈朝建言献策,提出了“务农以足食”“轻赋以实民”“罢冗官以宽民力”“减吏员以哀良民”“总钱谷以济国用”等一系列增加国家财富的思路与方法,与传统儒士们“言利色变”,视一切增加“国用”的行为为“聚敛财富”的狭隘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彰显出其经济伦理思想的“达用”之特征。
同郝经一样,元代理学家许衡的经济伦理思想亦表现出一些现实主义的倾向。
由于世代为农且生逢战乱,年少即学有所成的许衡“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核菜茹,处之泰然”(23),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贫苦生活。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思想也极为朴实、且平易近人。他主张“日用之事”应同“学问”共循一理,认为“君子之道,自其近小处而言,托始于夫妇居室之间”(24),“明明德是学顺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25)。其所谓“当于文理”的视野,较之以往那些传统儒士,有着明显的拓宽。在他看来,传统观念所甚为重视的“三纲五常九法”是“文之大者”,但仅以此为关注点的“文理”或“道义”却缺漏颇多。事实上,理应出于“事物之间”,“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都应属学问关注的对象。因而,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独诗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26)在这里,那些如“柴米油盐”“衣食起居”等诸多为传统观念所不屑的“上不得台面”的日用琐事均被纳入了“文理”和“道”“义”的视野。而这一范围,正是广大百姓经济民生之所系,也是最难免与“利”相关的经济活动领域。在讳不言利的理学盛行之时,许衡大胆地将“道”之关注和“理”之内涵扩充于此,并肯定这些“盐米细事”只要“合宜”,便可谓之为“义”,其进步意义,用现代的学科语言来说,无异于充分尊重经济价值,并置其于应有的伦理关注和规范之中,实现经济与伦理的融合。
基于这一广阔视野,许衡极具创见的“治生论”应运而生:
“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诸葛孔明,身都将相,死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尔。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27)这一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学者”当以“治生”即“谋生计”,为第一要务,因为,如果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对“为学之道”有所妨碍。其二,关于如何“谋生计”,许衡认为当以“务农”即农业生产,为主要手段,但只要“处之不失义理”,从事商业也是可以的。
许衡的这一见解,相对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孔颜之乐”和重本抑末、尚农轻商的观念而言,显得离经叛道、格格不入,并因而饱受非议。然而,客观地看,他开拓性地将谋生与为学、经商与务农相提并论,恰是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以期通过对君子为学的物质条件的必要关注,唤起世人对经济民生问题的更多参与和重视,更好地促进为学之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思想让“高高在上”的儒家理想道德一定程度地接上地气,并在元代这个避虚就实的社会中找到了现实的土壤:事实上,元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和知识分子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早已使得大量儒士生活贫困、境遇窘迫,作为一个阶层,他们再也不能像在宋代那样受到礼遇、并拥有较大的财富和权利。为了养家糊口、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奔忙于“生计”已成为他们无奈却必然的选择,即使迫不得已从事那些为世人所不耻的末业,亦不足以批评。相反,如前所述,在元代,知识分子因不得志而被动涌向各个行业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这些行业前所未有的成长,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处于那一时代的许衡,虽未系统阐明这一趋势,却已然察觉到了这些转变。如此看来,治生论这一崭新认识的提出,便是极其自然的事了,传统儒学亦因祸得福,被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诚然,作为元代北方理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郝经、许衡等如上种种观念只是一些颇具亮点的思想碎片,还比较稚嫩、不够成熟并自成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形成于蒙古人所统治的元代这一特殊时期,抑或与身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对商业交换的固有兴趣和儒士社会地位之卑微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其在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毕竟,它滋生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印证了其时经济活动之日益频繁和丰富,同时亦决定了宋代义理之学经由元代转向一般、日趋务实,并最终走向明清实学之繁荣的发展历程。
【 注 释 】
①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9页。
②③《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
④⑤宋希仁:《论伦理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刘可风:《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反思》,《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说:“对于无定居的游牧民族……往往正好有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做了他们的特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1页。)
⑧\[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时代文华书局2014年版,第13页。
⑨《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兵四·站赤》。
⑩《元史》卷六十三,志第十五,《地理》六。
?参见李云泉:《略论元代驿站的职能》,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列传》第七十五,《董抟霄》。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郝经》。
???郝经:《陵川集》卷十七,《情》。
??郝经:《陵川集》卷十七,《道》。
??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
(21)郝经:《陵川集》卷二十,《志箴》。
(22)郝经:《陵川集》卷十七,《仁》。
(23)《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第四十五,《许衡》。
(24)许衡:《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
(25)(26)许衡:《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27)许衡:《鲁斋遗书》卷十三,《附录》,《国学事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