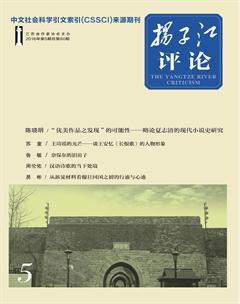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
周伦佑
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处于舆论和社会关注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演变,近三十年来,如果我们从“文凭热”、“文化热”到“经商热”、“网购热”来追溯其演变轨迹,消费文化与欲望化耗散,对中国人的精神消解,对严肃文学造成的致命冲击,把中国诗歌与诗人从社会关注的中心抛向了舞台的边缘。诗人们犹如被主流社会“放逐”的那些边缘群体一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及写作状态都处在了体制外。“底层化”、“边缘化”,已成为描述中国诗人生存状态的两个常见的词语。但是,中国诗人仍然在体制外,在社会底层诗意地生活、写作,中国新诗仍然在艰困中以澄澈的诗性温润着当代人的心灵。
长时间以来,人们常常爱把商业化浪潮冲击下的诗歌与小说、散文乃至文学评论相比较,也爱把诗人与小说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以及学者相比较。在进行人的比较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诗人可爱,诗人有激情;我认识的两位文学月刊女编辑就曾对我说,她们参加过小说家的讨论会,也参加过评论家和学者的学术会议。觉得小说家的讨论会冗长、沉闷;学者们的讨论会比较刻板、枯燥,而且,会上基本是按照行政职务和级别来安排座位、安排发言,很不习惯;还是诗人的讨论会好玩,自由、激情,活力四射,特别有意思。
仅就以2012年10月在漳浦旧镇举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讨论会是纯民间的、自发的,由诗人道辉提议并承担会议的全部费用。道辉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众多诗人的响应。到会的100多位诗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自费去参加的。因为讨论会预定的时间正好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机票都是全价。其中航程最远的大概是诗人董辑,从长春到厦门,往返机票就花了四千多元,而只为了参加一天会(道辉原计划的会期只有一天,后改为两天,但董辑是按一天会期购买往返机票的),四千多元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发星和他的几位朋友。为了参加这次讨论会,他们从各自的出发地相约同行,坐了5天的火车和汽车才赶到漳浦,会议后,又要坐5天的火车和汽车才能回到家。其中的大凉山彝族诗人麦吉作体,除了往返的10天火车硬座行程之外,到了西昌,还要再走两天山路,因为他在大凉山深处的一个山区小学做老师。他自费颠簸劳顿12天千里迢迢去参加诗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漳浦旧镇给到会的诗人们唱一首彝语古歌(讨论会上麦吉作体没有发言)。这种使人热血沸腾的情景,在中国的小说界、散文界、评论界和学术界是不可能见到的。这一切,只源于发星们、麦吉作体们、董辑们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爱完全是纯精神的、非功利的。
对文学的痴迷只有诗人才会如此这般。他们图什么?他们的作品很多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不了,他们自费印的诗集和刊物就是自己阅读,自己交流;他们在自己的民刊上发表的作品和职称不挂钩,和工资不挂钩,和职务升迁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本来意义——诗歌来自生命,又反过来关照生命;诗歌照耀他的生命,温暖他的生命!最后主持者还给参加会议的比较有知名度的评论家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包,我感觉很惭愧,私下退还了,否则,真是无地自容。麦吉作体们自费颠簸劳顿坐10天10夜火车和汽车,还要再走两天山路去参加一次不准备发言的诗歌讨论会。说实话,这种生命行为,散文作家们做不到,小说家们也做不到,學者们更做不到——大多数小说作家、评论家都体制化、享乐化了。
这是人的比较。在将诗歌与小说、散文等作比较时,人们的看法就大不同了。
在谈到“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时,目前在评论界最流行、最通常、也被诗人们自己认同的一个说法是:“当代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我在许多场合(包括一些学术讨论会上)都听到人们在这样说。这种说法初始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就觉得不一定对了。 既然说到“边缘”,首先要确定一个“中心”作为参照系——即以什么为中心?如果是以“权力”为参照的中心,那么,除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产品(体制文学、体制学术等等),所有严肃的写作,不仅是当代诗歌,包括当代的小说、散文、评论——甚至被学者们奉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学术,也都被边缘化了。当然我理解,人们不是以“权力中心”作为参照系来谈论诗歌的边缘化的。还有一个参照是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辉煌。那个年代,诗歌处于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引领着小说、美学、评论乃至整个社会思潮的变革;可以说,诗歌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的诗歌与那个时代相比,已经不再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了,公众的关注度也大大降低了。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论说“诗歌的边缘化”,那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基本成立的。
但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我也可以问一句:如果是以80年代的辉煌作为参照,除了诗歌之外,难道现在的小说、美学、评论的影响力可以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吗?为什么人们只是在谈“诗歌的边缘化”,而没有人谈小说、散文、评论的边缘化呢?这引出了另一个参照系:金钱—商业利益中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现在的出版者、评论者、学者们正是以这把“金钱—商业利益”的尺子作为价值尺度来看待当代诗歌,才得出他们认为的“当代诗歌被边缘化”的结论的。他们之所以不说“当代小说被边缘化了”,是因为他们认为小说还有一小点读者,出版社还愿意出版小说,文学杂志还愿意发表小说,也是因为还有这一小群读者(一二万人,约占十三亿人口的不到十万分之一)还愿意掏钱买小说书;他们之所以不说“当代散文被边缘化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读者即发行量,发行量即金钱—商业利益。这才是他们心目中“当代诗歌被边缘化”的真正的价值参照系。
说到这里我想再问一句:现在一本以刊登小说和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每期的的印数有多少?一本以刊登文学评论的学术期刊的印数有多少?这点,大概这些刊物的编者最清楚。除了个别的印数上万(如《收获》),大多数刊物也就二三千册吧。据笔者了解,很多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每期的印数只有一千册上下。堂堂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二三千册(甚至一千册)印数,难道不表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学术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吗?再从读者接受面的变化来看,随着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和微信的广泛使用,手机阅读已经成为年轻一代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纸质读物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影响迅速式微,销售量下降,读者减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现在,纸质印刷品中还有一点读者的是历史类读物。置身于当下中国的精神氛围中,还有哪一位小说作家、散文作家、学者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也就是说,从现象上看,继诗歌被边缘化之后,小说、散文、学术也依次被边缘化了。
2013年在复旦大学参加的一次学术活动的讨论中,我说到了当代先锋诗歌的一个传统:非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即一般所说的“民间刊物”。我说到这里时,孙绍振先生赞同我的观点,说诗人们自己出版大量印刷精美的民刊,是中国现代诗的一个伟大的传统。2014在同济大学的“当代汉语诗歌讨论会”上,我又继续了这个话题。我说,除了以发行量为标准的商业利润算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据《诗选刊》编辑部统计的数字,在当前,中国非正式出版的诗歌民刊有427种,自己印制交流的个人诗集每年有两千种以上(按每一种最低印1000册计算,大概有二百万册以上)。这样一种诗歌奇观,是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法国、德国或美国都不可能有,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体制外诗歌出版盛况。而且,这种现象是在权力与资本病态结合,诗人个体大多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经历了前政治时期的政治高压以及后政治时期的商业浪潮冲击,中国的现代诗仍然在体制外活力盛大地生存着,发展着——全国的427种体制外诗歌刊物、每年两千种以上(二百万册以上)的自印诗集,仍然不顾各种禁令自发地出版着,投递着,交流阅读着。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一个大奇迹!
支撑“当代诗歌被边缘化”这个观点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个说法也是想当然的,没有统计数字支持的。应该说,诗歌的读者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诗歌作者就是最铁杆的诗歌读者。2012年到福建漳浦参加“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时,我说,在中国,写诗的作者大概有十万人吧?广东诗人杨克说:你太保守了,你根本不了解现在的网络世界,现在的微博、微信对发表、传输的内容有字数限定,这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方式。网络上写“微诗歌”的人很多。杨克在搞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他们广东作协搞了一个“微诗歌”大赛,参加的作者一次有几十万人。他们统计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在线诗歌写作的人,估计有几百万。我开始不相信,后来,开会的有个“微诗歌”协会的副会长,很年轻的女孩,她给我一个数据:说经常在网上、微博上写作诗歌的不下五百万!而据我了解,当前,全国写小说的最多一千多两千人,写评论的也就一两千人,写散文的,网上网下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这样看来,与小说、评论、散文相比,白话新诗的作者和读者还是最多的。仅就“几百万诗歌写作者”这个数字和写小说的“一千多两千人”、写评论的“一两千人”、写散文的“两三千人”这三个数字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相信:当代诗歌仍然是中国新文学最有活力的存在。
如果要我们对艺术与商业的亲密关系做一个排序,排在首位的无疑是绘画,紧接着是电影、音乐、戏剧、小说、散文,诗歌肯定是排在最后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艺术中,诗歌是最不容易被商业化的。也因此,诗歌才能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保持它的纯粹性。拒绝商业化,正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伟大。正是诗歌的这种非商业性和非功利性,为物欲泛滥时代的审美和精神的超越性追求保留了最后一块净土。我们应该加倍地珍惜和爱护它。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钱和商业尺度来衡量它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问一下:中国当代小说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小说刊物吗?回答是没有,一本都没有;中国散文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散文刊物吗?回答也是没有,一本都没有;中国文学评论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评论刊物吗?回答还是没有,一本都没有;中国学术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学术刊物吗?回答依然是没有,一本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不可能有,所以没有。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作这样一个假设:
——如果哪一天国内所有发表小说、散文的文学期刊全部停办了,国家出版社也不再出版小说、散文了,我们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们会怎么办呢?我想,除了改行写广告文案,只有失业;
——如果哪一天所有由国家出钱养着的大学学报(社科版)以及各省的文学评论刊物都停办了,其他文学期刊也不刊登文学评论了,国家出版社也不再出版文学评论和学术著作了,我们的评论家们、学者们会怎么办呢?我想,除了改行,还是只有改行!
但是,当我们将同一个问题抛给当代诗歌,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哪一天国内主要发表诗歌作品的刊物(包括《诗刊》 《星星》等)全部停刊,所有的文学期刊全部取消诗歌版面,所有的国家出版社都不再出版诗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中国的现代诗会消亡吗?回答是:不会,一定不会!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中国的现代诗一定会在体制外的生存空间中继续顽强、茁壮、活力、茂盛地生长、繁荣和发展。
这是因为,近20年来,《诗刊》、《星星》等主要发表詩歌的体制刊物在绝大数诗人眼里早已不存在了(它们早已被体制外诗歌界边缘化了),其他体制文学期刊用于发表诗歌作品的版面也已一再压缩再压缩;国家出版社也很少出版诗集了。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经历了前政治时期的政治高压以及后政治时期的商业浪潮冲击,中国的现代诗仍然在体制外活力盛大地生存着,发展着——全国的427种民间诗歌刊物、每年两千种以上(二百万册以上)的自印诗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样多的诗歌读者,这样多的诗歌作者和诗人,这样多的民间诗歌出版物——这样一种由自生自长,而自足自为,进而自在澄明的诗歌存在,是绝不可能被边缘化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边缘化。
我虽然在上面对汉语诗歌的当下生存状态作出了比较乐观的描述和肯定,但并不等于我没有看见汉语诗歌存在的问题。下面仅就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是所谓的“下海归来派”现象。“下海归来派”又被有的诗人称之为“诗歌还乡团”。这是指一些顺应潮流下海经商先富起来的以前写诗的人,这些年又重新上岸,把诗人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四处活动,八方露脸。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下海经商的前诗人,基本上都涌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个“文化热”、“诗歌热”的社会氛围中,爱好诗歌并选择诗歌写作是很普遍、很时髦的事,就像今天人们热衷于经商一样。后来发生的分化(出国、经商、践踏诗歌、坚持严肃写作),原本就是有前因的。诗人经商致富当然是好事,但我不喜欢成了商人,还要死死扭住“诗人”这个称号不放。即使在几千年官本位的中国权力体制中,政府总理任期满后,都只能称“前总理”,为什么只写了一两年诗,而有了二十多年的商人经历以后,仍要称自己是诗人呢?执政者都在主张废除终身制,在我看来,诗人也应该废除终身制。不写诗了,经商了,就是商人了,即使称诗人也应该加一个“前”字,叫“前诗人”。顺便说一句,这些“前诗人”即使重归诗人行列,也大多带上了商业心态和商业眼光,并且会以商人的方式来包装自己、炒作自己(因为他们有钱,他们相信钱的力量)。这对坚持严肃的诗歌精神是有害的。至于“口水诗”、“下半身”、“废话诗”、“裸诗”之类,不过是商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一种人妖化行为,完全是对诗歌的践踏。评论者不应该把这种种乱象与当代诗歌的先锋实验相混淆。
二是中国诗人的“写作资源”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诗歌风气被几个北方诗人热衷的“翻译体写作”所牵引和毒化。所谓“翻译体写作”,是指那种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以西方人名、地名为诗题,与西方大师的幽灵对话,大量充斥于每一首诗中的外国场景与人物,扭捏作态的刻意断句和转行,不时插入诗中的对话和引语(一定要加引号),拖沓、涣漫的节奏——直至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现当代诗歌标准为圭臬的近似于“翻译诗”的诗歌写作。一次,在和国内一位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英美现代诗翻译家的朋友通电话时,我善意地提醒他:“你翻译的外国诗对你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影子般的参照作用,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意义。”他说,“伦佑,你说得对。但是没有外国诗歌资源怎么写作啊?”我说,“你自己呢?你的生命本身,你的生存体验,你的痛苦虚无,你的所思所感,还有我们置身其中的这片土地的忧患历史,过去与现在,当下境况,你肉体和精神每一天的疼痛!这些都是你的写作资源啊,你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写作资源呢?”这段对话提示了我的写作价值观。和那些强调西方知识资源,主动与西方接轨的近似于翻译诗的“翻译体”写作者不同,我的知识背景、审美趣味和诗学价值观就其根本上来看,是本土的、中国的。我个人在写作中更强调诗人切身的生存体验、个人经验以及置身其中与这块土地共忧患的疼痛感和介入感。在这样的基点上,可以说,我近些年完成的 “后中国三部曲”三首长诗:《变形蛋》 《象形虎》 《伪祖国书》既是“介入当下”的作品,更是“介入中国”的作品。
第三是建立“诗歌标准”问题。这里所说的“诗歌标准”,牵涉到诗与非诗怎么区别?一首好诗和一首坏诗如何鉴定?评价一首诗歌作品是优秀的而另一首诗歌作品是重要的,是根据什么来判定的?这是与诗歌的本质确认生死攸关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里仅举笔者经历的一件事,作为对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2012年,我到郑州参加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活动。在会上,遇到北京《诗刊》社的一位编辑,他也是一位诗人,但他不承认诗歌有标准。晚上有个诗歌朗诵会,由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朗诵会上这位《诗刊》社编辑也朗诵了他的诗。我听这位编辑朗诵后对他说:你朗诵的只是一首诗的素材,还不是一首诗。朗诵会下来,这位编辑找到我,问我:“周老师,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有什么标准吗?”我说,理论上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如果由我来编一本《中国新诗百年百人百首诗选》,假如你入选了,我请你选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首诗,你能选出来吗?他说:当然有啊!然后说出了他认为的自己那首代表作的标题,并念了一些片段给我听。我说:“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的?”他说:“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这首诗好。”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已经找到了共识:这说明诗歌是有标准的,好诗和坏诗也是有标准的。你怎么能说诗歌没有标准呢。
虽然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的批评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标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存在着——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所以,诗歌标准的建立是有根据的,也是能够形成共识的。
第四是诗歌写作的“有效性”问题。2011年12月,我到广东佛山参加“中国先锋诗歌二十年讨论会,”在许多诗人的发言中,我听到最多的是对“写作无效”的感慨,说社会变化太快了,一切都破碎化了,诗歌的表达乃至于词语完全失去了对应物,语言无效了,诗歌无效了,写作已经完全无效了。我在会上说出了相反的声音,我说:所谓的“写作无效”,其实是诗人们逃避现实的结果,是自我取消的结果。我们所说的“词语的对应物”并没有破碎或自动消失,它继续坚硬、庞大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生活中,它每天都在我们眼前胁迫着我们,扼杀着我们,甚至在睡梦里也在践踏我们的睡眠。而我们的诗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作优雅,刻意回避之,不敢用词语去“对应”这个生活的敌人。要说无效,那些逃避现实的写作肯定是无效的。退回到自己那点小小的个人趣味上,守着几个无害的词语和句式把玩,你怎么能获得你期待中的“写作的有效性”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词语完全失去了对应物”,而是中国诗人完全失去了用词语去对应那个“对应物”的良知和勇气。
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有一段话,我根据记忆把它抄录在这里与诗人朋友们共勉:
凡是对词语敏感的地方,语言就还有力量;只要语言还存在禁忌,写作就仍然是有效的。词语的力量不是表现于畅销与流行中,而是存在和彰显于禁忌之中。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诗人,置身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时代的光明与黑暗中,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過词语彰显的力量,参与到现代性变革的伟大进程中。
最后,请允许我以2015年10月5日撰写的《〈钟山〉文学奖书面答谢辞》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
诗歌往往被视作一个民族的精神镜像。当这面镜子被打碎,丧失其完整性时,许多人转身离去,而这时依然会有少数人弯下腰、蹲下身子,从地上捡起破镜的碎片,努力使这面破碎的镜子恢复完整。重建当代诗歌精神及其价值标准,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根据词源学的考察,“象征”原指古代恋人分手时将一块信物从中分成两半,两人各执一块,以便相逢时重合验证。它代表人类对完整生活、圆满幸福的期待。我是握着一件信物——一块破镜的碎片来到这里的,我看到在座的各位评委和各位朋友的手里也都握着一件信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小片破镜的碎片在闪光;我们都是握有信物而期待圆满生活的人。我们手握同一件信物的碎片走到一起,在这里,在这个早晨,我看见那一面破碎的镜子在各位的努力下,突然间呈现出完整的镜面,并以它澄澈万方的光辉照亮了这座大厅,照亮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照亮了中国诗歌的天空!
我由此坚信:只要我们拥有圣洁的精神,只要我们坚持不使自己的灵魂蒙尘染垢,只要我们手中握有的信物——哪怕只是一小块理想的碎片——不丢失,人类便不会失去最后的希望。
(2012年12月5—7日初稿; 2015年12月6日修订完成于成都温江柳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