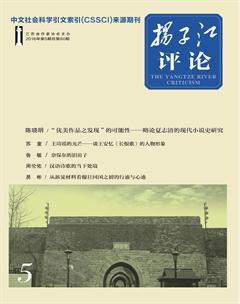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生活中应该有戏剧性的情节”
白草
于从容不迫、舒而不缓的叙事进程中,往往再来一个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性变化,令正在有滋有味地沉浸于情节之中的读者吃一惊吓,似乎是滕肖澜目前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无法无天的爱》(2012年)里上海好青年郭启明说,他就一直以为“生活中应该有戏剧性的情节”,或可视为作家本人的观点。初看起来,滕肖澜的小说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此种近似于模式化的因素,试举几例:《这无法无天的爱》里看上去正经、稳重的农村女孩卢晓红,为了改变生活处境与男友一道绑架儿童;《上海底片》(2013年)里的王曼华,使出种种手段总算办好了出国手续,临行前却被楼上掉下的花瓶砸死了;《小幺事》(2010年)里顾怡宁之父始而陷身火海、终而与两名警察一道莫名其妙出了车祸;《星空下跳舞的女人》(2011年)里的阿婆气度优雅,像往常一样在餐饮店吃奶茶时,被另一个老女人兜头泼了一杯奶茶,原来她的舞伴是该女的丈夫,小说写道,这个插曲“完全是电影里的桥段了”。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2009年)中,陈也的哥哥陈昆研究生刚一毕业,就从飞机上摔下来,死了,剩下全是陈也一人的独角戏——找个漂亮老婆,争一口气,“不能让别人小看”,以此来弥补没考上大学的遗憾。而第二部长篇小说《海上明珠》(2012年,初发表时名《双生花》)的整体结构则完全建立于戏剧性基础上:一次意外车祸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医疗事故——护士抱错了小孩,导致城、乡两个家庭所抚养的孩子原来均非己出;且遭际的不同,又造成了两个年轻女性迥然相异的个性、命运。叙事者说这可是“千年不遇的事”,其戏剧性因素、色彩笼罩了全篇。
试以中篇小说《规则人生》(2012年)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情节进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来真是处处惊心;不过,它再怎样出人意外,总有着一个潜在的“规则”:大鱼终将吃掉小鱼,小的终究玩不过大的。商人老赵机警得像老狐狸,冷酷到六亲不认,以“装死”来逃避债务,从而独吞所有财产,意欲逃往国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殊不知身边的“小三”正是他的克星;而当这个曾为大学校花的“小三”不动声色地把老赵的财产转到自己名下,也在那里庆幸自以为得计时,她的初恋男友的妻子——一个“人淡如菊”、“眉宇间又透着坚毅”的“官二代”,早把身为公安的表弟安排在“小三”的楼上,居高临下,洞察一切,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正如小说中所写,这一切“像电影里的情节”,跌宕起伏,又全在情理之中,因为那个“规则”制约着情节内在逻辑的发展:民难斗得过商,商难斗得过官,自古皆然;也因为那个“规则”的制约,无论情节发展如何令人大感意外,终是合乎情理,无有例外。质言之,那种戏剧化的情节,其实原本就是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也是被拣择、被叙述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是小说的一个主要方面,虽非全部。事实上,滕肖澜的小说在叙事艺术上显出大方、从容的风格,正源自于一种质地的素朴——对人性的细微体察以及出于仁者之心的宽容理解,于形象的呈现中便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琐屑猬冗;尤为突出者,当脆弱的人性于摇摆不定、似欲变异之际,突然间又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人性再度更新并复位。比如《倾国倾城》(2009年)里的庞鹰,这个低调、温和的女孩子,为了男友的业务不惜违背个人意愿,与上司套近乎、拉关系,这种关系被另一个上司所利用,当作一笔交易,显得突然的拍床照情节即为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就是这个低调、温和的女孩子,她最终在人性跌落的瞬间猛地关掉了摄像机开关,没有出卖与己相关的人,更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尊严,小说结尾她因蟹壳卡喉、咳得泪水大颗大颗往下掉落时,作为读者的我们,无论怎样控制自己的阅读情感,亦忍不住感到一阵心疼。再如《快乐王子》(2010年)中的几个受助人张阿婆、瞎女人、赵瘸子等,没有一个人出卖恩人严卉。无论是庞鹰还是张阿婆、瞎女人们,最后时刻皆守住了一个底线,不伤害他人——这是滕肖澜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一个大致特点。尽管《姹紫嫣红开遍》(2007年)里初出校门的余霏霏偷拍了她与剧团团长的床照,以此要挟并当上了多少人眼红的影片女一号,然而这是个次要人物,作家几笔就将她打发掉了。所以滕肖澜的小说,于严酷之中总有一种大温情在。即便是《城里的月光》中陈也被师傅“出卖”了一次,可当叙事镜头对准师傅家中惨淡的生活景象,还有屋内那个一边呵呵笑着一边拍手的傻儿子,一种怜悯的情感悄然氤氲开来,冲淡了出卖行为本身的性质——不过是揭发徒弟给车间主任送礼、自己取而代之做了值班长,绝非取人性命、断人活路的极恶大憝。
关于滕肖澜小说题材及写法方面,目下已形成了一种较为便宜而刻板的说法,即她擅写小市民、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这种说法表面上看颇有些道理,再进一步则经不住推敲。第一,正如郭启明所说,生活中应该有戏剧性的情节;《规则人生》里的“小三”朱玫“是不甘心平淡过一生的”,她经历的一切真的就如电影情节一般,变化多端,又惊又险。这说明滕肖澜小说中的人物多不甘于平淡、平庸的生活,不管是使蛮力,还是玩机心,皆一个劲地奔着人生目的去;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滕肖澜特别擅长于把平常生活写得不平淡,平静之下波澜暗涌,多戏剧性变化即为其中一法,“看似寻常最奇崛”,是一种格外不多见的叙事能力。
也因此,滕肖澜的小说自有一种意味、一种丰富、一种吸引力,不论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一旦读起来很难放下手。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此种意味和吸引力盖源于文本内部隐性的对比结构:绝非简单地对比出善恶、美丑、好坏来,而是通过对比,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人情的变易;唯有通过对比,才会显示出丰富的差异。人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地域的差别、文化的差别、教养的差别。《海上明珠》里毛慧娟的前夫李俊与罗晓培的华人男友,只要一出场,即成为对比:一个喝咖啡,一个吃大蒜;一个是香饽饽,一个是烂草根,总之,“野鸭子比凤凰”,光脚赶不上。《这无法无天的爱》里的郭启明,一个良善得有点软弱、温婉得犹如女性的上海小青年,他的旁邊便站着说话总欠正经、且满心势利的曾伟强;正是这个郭启明,使得卢晓红改变了她心目中上海人的形象——“上海人的名声不好,自私自利,鸡鸡狗狗的”,虽然对于大上海来说,它在一个以“捏脚”为职业的乡下女孩心目中会是个什么样形象,根本上是不足为意的。小说无意描写乡村,寥寥数笔,比如宁愿坐牢也不想回去过“种田种菜”日子,便将一种严酷呈示出来。不说《美丽的日子》(2010年)主人公姚虹如何费尽心机、预备着“成为全上海滩最好的媳妇”,单看一个次级形象、她的同乡杜琴,哪怕卖肾给房东也要留在大城市,上海待不下去,另择地方,反正“不是北京就是广州”,这才是看不见的真实。滕肖澜写城乡对比,不加个人评论,更无私人好恶,只是一种真实的呈现:大上海无可替代,它的优越性就摆在那里,别说乡村,一般的城市在它面前也显得土头土脑。
即以人物对比而言,滕肖澜多数小说中主角对面总有一个次一级角色,两个人总是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前者家庭出身富裕,稳重而又宽容,待人温和,人缘好;后者则多为乡村出身,聪明以至于精明,人缘差,处处上进处处败。以新近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乘风》(2015年,初发表时名为《我欲乘风》)为例,试略作分析。家里钱多得花不完的袁轶,是“天下第一痴情种子”,为了追求大学同学柳婷婷,也考入了非自己专业的机场,他的对立面则是一个外地高考状元温世远,农村出身,为人阴沉,“是个输不起的人”。柳婷婷选择了温世远,而同父异母的妹妹柳晶晶则又是她的对立面,偏喜欢袁轶。温世远的全部资本就是好学上进以及曾有的状元头衔,他在业务上的失误(把客人行李重量的十位数计算为千位数),意味着否定了他的全部价值,因此不惜把错误推到袁轶头上,令其背黑锅,而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是一桩“很无耻、很卑鄙的事”,二者人品高下立见。这是滕肖澜叙事所具有的一种很难确切表述出的品质,它调动起我们的阅读兴趣,顺着情节一波三折地走,又不致让人轻易做出价值判断,喜欢那个时时被当做冤大头的“袁小开”,憎嫌事事要算计一番的温世远;或喜欢城市,讨厌乡村等等。原因在于她的小说中可不时令人感受到一种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品涵养实与财富、家世等等相关,一旦养成则又独立于其上。袁轶的行为表现,连叙事者都忍不住赞叹,其人虽年轻,“但修养不是一般的好”,自己心情不好“还要照顾别人的心情”,受了损毁亦终能淡然处之,实为一种高贵的气质。正相反对的则为温世远,虽大学毕业,仍不脱农民式的思维及行事方式,讲求实惠,爱慕虚荣,必要时一定会损人利己。第11节中,叙事者用了“阶层”词语来比较袁、温二人,没有用过时的“阶级”一词。这不单单是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一个词语的问题,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在当代文学中,所谓乡村、民间、底层尽管本就是被建构起来的词语,却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标志性概念,占足、占尽了道德优势,甚至往往与纯朴、真诚、纯洁、无私等词语互换。在此种陈旧观念的支配下虚构出来的小说人物,今天看来,多显得高调而不近情理。滕肖澜的小说一开始即远离了此种陈旧的结构性套路,自走新路,且自如地呈现出了以往被粉饰的近乎残酷的真实。
《乘风》是一部极好看的小说,其吸引力一如前两部长篇小说《海上明珠》和《城里的月光》。题材也是一个方面,当代小说中专门正面描写民航、描写机场而且写得耐读的,《乘风》大约是第一部。机场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世界,正如小说中写道,“机场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可是小说却以爱情为主线来结构全篇,不只写了年轻人的追爱,也写了“航代”两个高官之间的三角爱,以浓墨重彩的爱恨情仇代替了这个小世界内部远为复杂、外人绝难窥见的人际关系,成了一部民航人的爱情纠葛史,束缚了想象空间,格局略嫌狭小。
滕肖澜的小说还有一个贡献,即刻画了一类新型年轻的“失败者”形象,这类人多为进入城市打拼的农村青年,除了年轻,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资本,因而意味着个人理想没有着落,前路茫然无所措其手足。虽然作家笔下留情,最后安排温世远去香港接受培训,业务上将有大发展,实际上这个人物在某一方面还是失败了,那么起劲地帮他上进的恋人柳婷婷终于离他而去,柳父嫌其为外地农村背景仅为其中一个因素,他请女友吃饭从未超出百元消费的做事风格,亦使女友忍无可忍,以致在大街上撒泼般地发泄不满和不屑。再如庞鹰,也是可着劲儿帮助她的男友,后者却是人品存在问题的青年,不断变换工作,毫无愧色地利用女友,以便达到以其个人资质、能力很难实现的目的,自称“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这无法无天的爱》里的卢晓红,她在实施极端行为(绑架儿童)时对郭启明说过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了:“我老早说过了,你是城里人,不会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也不想做坏事,可不做坏事就只能当一辈子穷光蛋。”“我说错了吗,你就是花,你们几个都是花,谭心是花,郭钰是花,就连曾伟强也是花——不过他是朵喇叭花,比你们稍微贱一点。可我和宋长征是草,长在地上的草,被人踩来踩去的那种。我们跟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确是一段让人颇感惊心动魄的表白:城市已经不了解农村了,没有农村,它照样自足地前行;在一个农村女子心目中,城乡间的差别犹如“两个世界”,城里人是“花”,乡下人则是“草”,花草不相谋,冰火两重天。30多年前,《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被赶出了城市,背着简单的行李,最后“望了一眼罩在蓝色雾霭中的县城”,孤独绝望地走向他从来就不愿意生存的乡下,他认命了,也甘于承认所谓个人道德上的亏欠——谁叫你抛弃乡下女子,喜欢城里时髦女郎。然而,卢晓红们则大为不同,就是被杀掉也不甘认命,不特此也,他们从一开始即抱持不做坏事便当穷光蛋的畸形观念。当代小说中农村青年人物谱系图上,那些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男男女女们,在缺乏公平机制的氛围下,似乎永远于噩梦般的原点踏步不前。
滕消澜小说中与此相关的另一类型形象,看似达到了人生目的,实则仍为存在大缺陷的失败者。这类人物多用心计,频使巧计,步步都要算计一番,《十朵玫瑰》(2006年)里的林芳便是一个颇为显眼的例子,她像“经营一项事业”般策划每一次约会,最终将一个被群芳众艳包围的官二代夺取到手,可是,象征着爱情的那一朵玫瑰,永远不属于自己。在滕肖澜的小说人物群像中,这一类型的人物所在多有,机关算尽,到头只是一场空。以一种宽厚仁者的心态看待并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折腾、算计,看爬上去、滚下来,也是滕肖澜小说叙事魅力的一个因素。
不知是否可以说,滕肖澜小说似乎不仅对戏剧性情节、而且对人生中的巧合,有着某种偏好。戏剧性过头了,若非内在叙事逻辑的一个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裂痕和漏洞。《姹紫嫣红开遍》中的主人公、艺术家项海,一直与网名“柳梦梅”的网友互通衷曲,多么好的一个情节,我们于阅读中禁不住会想象她是对门的罗曼娟,或任何一个内心丰富、情感细腻且遍尝了人世酸甜苦辣的女性,却绝对不能接受“柳梦梅”是同一幢楼上的一个赌徒!这是个致命的漏洞:“柳梦梅”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但绝对不能是一天到晚赌到眼睛发红的赌徒,赌徒于他自己特定世界里或许赌技高明、感觉细敏,一旦离开特定场合,其情感则是粗疏、麻木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体会情感的细精,细腻情感也是长期磨练、训练的结果,一个情感麻木的赌徒怎么可能探触到一个艺术家颇多情致的内心世界?《海上明珠》主人公之一的罗晓培,被护士抱错替换,阴差阳错成了城里人,她的男友——一个新加坡华人,英俊帅气,光彩照人,把一个乡下人李俊比照成了“烂草根”。小说结尾时,这个被毛家当成“香饽饽”的新加坡人不仅情感出轨,又得了胃癌,突然间良心发现,自愿代替罗晓培捐出一只肾,以挽救她的兄长。《海上明珠》是一部让人读起来特别过瘾的长篇,在滕肖澜三部长篇小说里,这一部最为曲折丰富,可是结尾叙事进度总给人感觉像跑步一样,步伐急促,要匆匆收场的样子。这且不说,从常识角度看,一个人得胃癌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发病至确诊,期间必得经历厌食、不适、疼痛诸般苦楚。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头天还在搂着女助理腰肢饮咖啡、喝酸奶的英俊华人,怎么一下子得了癌癥?一个长久患胃病终至于癌变的人,除非服用灵丹妙药,平日间他的气色无论如何很难光彩照人的。——说到情节跑得太快,中篇小说《拈花一剑》(2011年)可谓从始至终一路快跑,没有障碍,没有难度。作家本人在序言中说,这部小说是一个有趣尝试,以纯文学的写法,“来刻画一个天马行空的武侠故事”。说是天马行空,倒也名符其实:官——两个将军,一个王爷,还有王爷的女儿郡主,与盗——天瞳山上一个武艺高强的贼寇,相互间使招用计,打打杀杀,全杀光了,只剩下一个身世卑贱的女仆拾儿来收拾残局,埋尸筑坟。没有不受约束的想象力;表面上看似放纵至极的想象力,实为不守规矩的想象力,无规矩即无艺术。这部小说在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上无甚新鲜之处,值得分析的是它的观念:上层权贵暗斗明争,视人命为草芥;唯有底层才是纯朴、可靠的,便是爱一个人,像拾儿爱了将军杜如轩,也会爱到天荒地老。滕肖澜写当下题材时,成功地避开了当代文学中那种底层即是道德完善标志的陈旧观念,在这部武侠故事的编写上,却又不小心掉入了陷阱。
巧合过头了,除非叙事上巧妙补救,以情理弥缝之,同样也多少会显出破绽来。巧合总是与非常态境遇、条件相伴。中篇小说《又见雷雨》(2014年)可说是此种巧合的集大成,一场车祸,碰撞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富豪肇事者撞死了两名男性后,娶了其中一个的遗孀做妻子,另一女人竟是他抛弃多年的前妻;如果说这样的情节已经有些过火,那后面的故事则更为离奇、不合情理了,前妻之子当众侮辱了富豪之后——其实也是他的亲生儿子,驾车径直撞向电线杆;次子亦为情所困,于雷鸣电闪之际从楼上一跃而下,当场毙命。瞬间失去二子的富豪随后出家当了和尚。与其说这个中篇小说是对名篇《雷雨》不太成功的模仿,还不如说作家似乎有点过于依赖情节的巧合了。对一个有经验的作家而言,叙事进程中略施巧合小技,或以巧合建构全体,原本是在很自信的掌控之中,为何这个文本给人的阅读感受是处处只见巧合,而不见了人情变易呢?观念有时会决定形式、技巧;宿命的观念也被认为会造成命运的遇合、巧合。在滕肖澜的小说中,确乎存在着与某种血脉相关的宿命因素,《海上明珠》中的温筠就大发感慨道,“到底是血浓于水”,被鄉下人养大的亲生女儿跟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无论脾气、性格,皆有着雍容气度;而抱养的、疼爱了二十多年的乡下女孩,看着和气,实则骨子里是冷的,有距离。一种观念,真的会压住想象的空间,直往巧合的主题上奔去,少了叙事的丰腴,显得急促、干硬。用得少点,像《倾国倾城》里的庞鹰,上司崔海原来是十几年前将自己从河里救出的恩人,利用她去陷害另一个同行,这虽是一个小细节,毕竟令人生疑,须知此乃大上海而非巴掌大的小县城,转个拐角就会碰见一个熟人;用得多了,则如《又见雷雨》、《上海底片》,几乎处处是巧合,整个文本少了一种温润之感,显得干巴巴的。王蒙先生说过,没有巧合和偶然,就没有生活,也就没有小说和戏剧;但巧合不可用得太多,尤其不能用得违背生活的逻辑、人物心理及行动的逻辑(《谈创新》)。滕肖澜小说中那些引人直入胜境的戏剧性情节,即是写出了生活、人物等的内在逻辑;反之,则令人感觉巧合未免稍稍多了一点。
巧合总是或多或少依赖偶然性因素。芥川龙之介认为真正像样子的小说,不仅在故事发展上偶然性较小,在人性的描写上偶然性也是比较少的(《批评学》)。巧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强化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细节,也就是把那么一点点事情放大了,大到文本整体结构不足以撑得起、以致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这在中篇《握紧你的手》(2012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小说写了当下社会民怨沸腾的强拆事件,刻画了一个良心发现的人物形象:女老板孙晓美为了尽可能保住饭店不被廉价拆掉,便在网上招募了一个“职业钉子户”,天天“上班”,以对抗拆迁队。她算找对了人,这个名为李谦的男子以前正是折迁队的。他之所以应聘,盖因拆迁时曾造过孽——一个上海知青的女儿好不容易从边疆回到上海,以为真的找到了“家”,实现了父母此生最大愿望,过去大家谈起上海二字感觉这个词语本身就是“闪着光的”,可好景不长,家被拆了,她立刻点燃汽油把自己烧死了。李谦没能救下女子,十几年间一直想着为自己“赎罪”,就等孙晓美这个女人的出现了,在李谦看来,见到网上召募启事,一下子觉得“那个女人仿佛又回来了”。这一巧合绝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它是全篇的一个基本结构,所有的情节发展即为围绕它而展开。可是,此巧合痕迹太露,经不住推敲。第一,上海知青的女儿准备烧杀自己时,她竟然对着认识不久、来往不多且前来谈判条件的拆迁队员李谦吐露心声:“非常非常喜欢——就算你是个坏家伙,我还是喜欢你。这些天有你陪着,我很开心。我会永远怀念这段日子的。”这委实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场面。让受害者感谢施暴者,以爱和温情来稀释、冲淡一种罪恶,是当代文艺中一种最为陈腐、伪善的观念,搞得是非不分、善恶难辨,缺乏一个基本的维护人性的理性标准。这部中篇显然也多少受到了此影响。第二,即便我们相信李谦的赎罪出于真诚,他的做法又让人大加怀疑:赎罪要有一个对象,知青女儿死了,可那一对老知青还在边疆眼巴巴等着消息。非常奇怪的是,十几年时间里,李谦未做出任何寻找受害者父母的行动,哪怕去上门道个歉也没有;相反,此人却一直在苦苦等待着另一个全然不相干的孙晓美出现,最后真的为她而死,以此来给那个可怜的上海姑娘赎罪。这是廉价的作秀、表演,有如害死了甲女,却跑去给活着的乙女上坟烧香,是没道理的。
类似的赎罪描写,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少见,基本上表现出不近情理的特点。试举二例。姚鄂梅长篇小说《西门坡》(2013年)中有一个情节:化名庄老太的曹凤霞,年轻时因为丈夫出轨,于怒火中烧之际,一把火点燃了正在自家屋中苟合的那对男女,从此逃亡在外;到老年时一时间良知醒悟——“老天爷”通知她该到赎罪的时候了,于是主动回到家中,为丈夫和他的情妇当牛做马,服侍其余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不能为自己的男人生出一男半女,愧疚丛生,自感理亏。倘若庄老太即曹凤霞是一个无知少识、为传统观念所束缚的村妇,她烧了一对出轨的男女,再去服侍他们,此种行为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庄老太却是一阅历、见识俱非寻常之人,几十年在外漂泊的经历,见惯了人世冷暖,眼界大开;而且庄老太是“西门坡”即妇女互助社的大管家,此社团组织专门收容遭受家暴或经历悲惨的妇女,一同作工,一同生活,实为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庄老太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自不待言。就是这样一个类似妇女“领袖”的人,却突然之间做出决定,甘愿给那对形体上残废、神情上更为猥琐的男女当仆人。这显然是一种向下的想象力,为了达到莫名其妙的赎罪目的,不惜扭曲人物自身性格逻辑。再如王手中篇小说《斧头剁了自己的柄》(2014年),内中亦有相似的情节描写:一家鞋料店老板为讨回被恶意拖欠的30万元,便指使以前的一个店员将对方绑架,只讨钱、不动手,不料却被警察一枪击毙。男店主看到计划失败,毅然卖掉小店,与妻子离婚,抛弃子女及年迈父母,然后千里迢迢奔赴死者的老家——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给人家当起了儿子,算是为自己赎罪。这里的漏洞更为明显:第一,一个抛弃妻儿老小、可说是六亲不认的人,却急匆匆跑去给人家当儿子,此种赎罪行为怎么可能是真诚的?第二,以常理推测,也过于低估了警察的智商,以为击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青年,便收网结案,未免太天真、简单了。给人当儿子这个情节背后,掩藏着一种不负责任、逃避责任的心态:当不当儿子对店主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儿子,会保住性命,不当儿子,则要当囚犯甚或死囚犯,以命偿命。王手是当代作家中叙事艺术一流的作家,这部小说中出现如此的失误,令人叹惋。
这些显得极端的赎罪行为,绝非作家想当然的编排,却是当下现实的一种折射。每当一件坏事、一桩恶行发生,矢口否认、极力推卸责任已经成了一种本能般的社会反应。文本中强调描写的行为,恰恰是现实中所应有而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这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反”映现实——“映照了生活的反面”(《诗可以怨》)。作家的济世情怀无可厚非,但是心忧现实、关怀社会的理念倘非小说化为内部的细节、形象,而漂浮于情节及性格逻辑之外,过于主观化的情怀反而会起到某种粉饰作用,是要不得的。张承志说过,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冷血动物”(《新诗集自序》),良非虚语。
滕肖澜的小说自有一种魅力,拿起来很难放得下,却又生怕它一下子到了结尾。杨绛先生曾谈到一部法国小说,说读起来让人“直咽口水”(《记我的翻译》)。倘若借用这句话来形容滕肖澜小说给人的阅读感受,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