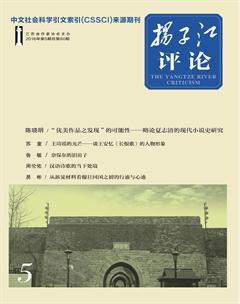当代儿童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王帅乃
自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欧本纳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后,争取性别平等与保护生态环境就被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将父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指出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蕴藏的等级制观念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女性与自然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被客体化为“他者”,成为较“劣”的一类。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由于女性生理特点以及女性长期来履行的养育性社会角色使得女性与“身体”保持了更为亲密的关系,女性被认为与自然更为接近,从而可与自然互为隐喻;其次,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等级制度,认为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中的其他生物都是生态网络中的一点,并无高低之分;再次,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差异,认为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保持多样化状态;最后,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二元对立思维,认为“男/女”与“自然/文明”两种对立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因此解决其中任一难题都会对另一组关系的重构产生启示意义。在中国当代儿童小说创作中,包含生态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大致分为三类,即以班马的《沉船谜书》a为代表的二元对立之思,以彭学军的《你是我的妹》b为代表的对“乡村乌托邦”想象之质疑,以及以韦伶的《幽秘花园》c为代表的对建构女性主体与自由多元世界之追寻。
一
当现代工业文明与消费文化的推进对自然环境造成侵蚀、破坏,特别是当生态危机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虚无化等精神困境初露端倪时,对工业文明产生的焦虑使得人们将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作为人类面对生态问题的早期态度,这种理解是较为符合认知发展规律的。《沉船谜书》就是该类将“女性—农业文明—自然生态”作三位一体思考,将之与男性形象带来的科技文明与生态破坏相对立后进行叙事的代表性文本。
《沉船谜书》讲述的是两千多年前古羌高原王子用三棵神树造了一艘瑰丽精妙的楼船,驶出古三峡而后从容自沉于长江中游的“舒鸠”无人河湾里,两千年后“仿古心理学家”老木舅舅和渔女红妹子用“古人心境”而不是用现代思维破译“沉船之谜”的故事。文本开始交代红妹子及其姑婆荷姑住地时,便有意识地将故事的这个主场景神秘化。小说多次提到这一江段是一个“迷宫”,九曲回肠,被白雾和茂盛的芦苇包围,外界很难得知这里有别样的美景存在,考察队的大船也开不进这里细长狭窄的河道。显然,这是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尚未侵入的原始生态系统。而沉船所在的河湾,则是一个“葫芦形状的大河湾”,它水体清澈、孕育着别处没有的游鱼;红妹子黄昏沉潜入水时,她的感觉是“水下一收了光线就如同完全关闭了的密室一般,成为绝对的黑暗……她还想游下去,却已经不知道手脚的划动和时间了,好像进入无尽的冥冥之中”d;老木进入巨大的沉船时,觉得自己“步入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这场所十分陌生,但又像是昨日曾来过似的,那船舱内的……都在水中静静映照着明暗的光线,幽荡一种遥远却又暗暗亲切的情绪”e。神奇的江段、葫芦状的大河湾,以及这艘千年古船,在小说中都呈现了类母体抑或类子宫的样貌,这里昏暗混沌、逃逸出“时间”概念之外,这个摇荡着的水环境提醒我们想起记忆最深处那给予我们滋养的温暖而混沌的地方。从全文看,这片水域和这艘大船确实是兼具“死亡”与“新生”两种功能意蕴的所在,而“死”与“生”的交替循环与“永生何以可能”也正是《沉船谜书》重点探讨的哲学命题。
这个故事发生在孕育生命和象征更替、流动的“水”的环境中,引导故事发展的关键人物红妹子则是继承了姑婆巫女灵性的少女,她被水文勘测队从西藏带回故乡时父母均已失踪,其姑婆身世更是离奇——她是婴儿时坐着荷缸漂到此地的。这两个女性人物是解开沉船之谜的关键,她们对自然感知的灵性与自由不羁的处世方式为考古队所诟病。考察人员面对停电和大雾这样的突发状况恐惧不已、惶惶不安,将之定性为“有鬼”;另一方面,红妹子和她的鱼鹰也直觉地不信任、不喜欢以纯科技思维、依赖器械进行探测古船的考古人员,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卡洛琳·莫琼特曾指出,在“机械”的世界中,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理性控制正是通过这种机器隐喻而实现的f。在后来的故事中,考察队员把红妹子点着烛火的家说成是女巫的幽灵鬼火,队员阿炳甚至错杀了保护他的鱼鹰“篓子”,这些情节说明,人类已经习惯了对与自己相异的人事先入为主地抱有敌意、习惯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父权话语支配下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在二元对立体系中将男性与理性、文化相联系,女性与感性、自然等概念相联系,进而定义前者相较于后者更高级,从而逐步合理、合法化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被定义为与“科学技术”相对的女性和自然被社会强势话语言说而难有对等的机会去真正言说自我。
从笛卡尔的人本主义到培根的“知识时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理性中心主义总体呈强化趋势,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被客体化、物化的程度逐渐加深,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认为人本主义“挖掉了所有迷信和宗教的根本。但是由此一来,人本主义把人作为一个超自然的主体,又为自己创造了神话。”g在《沉船谜书》中,男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遭遇了颠覆。首先,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掌握现代科技文明却将自己放逐于主流研究界之外坚持“仿古心理学”(声称考古必须要体察古人之心),甚至穿戴仿古、工作时总是关闭现代科技工具的“边缘学者”,正是因为这一特质,他得到了红妹子和鱼鹰“篓子”的信任,也得以成为古船制造者千载之下的知音。其次,文本突出了以红妹子、羌族王子等生态型人格者的高智慧,其中羌族巫师教导王子与树交流感情、学习树的智慧那一段叙述可以说是全文的理念核心:第一,人若与树同呼吸共命运,人的悲喜树都会记得;第二,在树顶观看世界,懂得“大事情都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做成”;第三,生命可以转换成不同形式,人可以和树一样去思考永生的命题。羌族王子以其超越时空的识见,为自己在千年之后安排了极致的“死亡”和“重生”,同时也提醒现代社会的人类注意到那已被破坏的生态。沉船事件从发生到被发现到最后的顺利结束——由于水质被污染导致鱼类种群变化,进而被鱼鹰察觉这一变化,再至红妹子在鱼鹰的带领下发现沉船告知外界,最终是烧船后留予后人的王朝文明秘密——都在这位掌握了人与自然秘密的古人的计划之中。最后,羌族王子之所以能够留给后人这样的秘密,是因为他没有在父权斗争中被“异化”而失去爱的能力,他从始至终都与灵魂之树相伴,这三棵大树几经形态的改变也始终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保护着这位人类智者直到千年以后。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文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的理念——“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h
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沉船谜书》这样的叙事安排一方面展示了感性力量、女性与自然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承认了传统性别结构的定义,强化了性别的本质主义,它没能彻底地突破“女性—感性”体系代表自然、进而代表“正义”的思路,并且固化了“自然—现代文明”必然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倾向的思路选择性地忽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差异,这样不单可能遗忘在对自然造成的伤害中女性可能处于一种共谋的地位,还可能会歪曲自然实体真实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本文的二、三部分还将重点讨论)。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内斯特拉·金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最终目的是“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当作创造一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的有利因素来使用,这种文化政治能够把知识所包含的直觉的、心灵的和理性的不同形式都融会在一起,让科学与‘自然的魔力合而为一;它促使我们改变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并且创造一个自由、生态的未来社会”i。而以《沉船谜书》为代表的如《小绿人》《山鬼之谜》等一类小说,最终均无奈地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维护似乎难以两全,生态型人格的主人公要么远离自然并对世人遮蔽他们所知的秘密,要么选择归隐自然与现代文明割断联系,这等于是表达了对二者共生发展某种程度上的绝望。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类小说尚没有能够实现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最高理想,属于早期观念觉醒阶段的文本。
二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将自然与女性相联系,在相关作品中最常看到的也就是将流动变化的天象水文、大地、生物(尤其是植物)与女性互为隐喻。上文已经分析了在早期具备生态意识的作品中比较常见的处理是将“女性—自然”紧密联系,与另一组隐喻以不能互融的形式出现。这一部分选择考察的文本《你是我的妹》属于乡村题材的小说,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了上述处理,对“女性—自然”这一隐喻既有继承性的叙写,更提出了质疑,这就从某种意义上松动了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模式。
《你是我的妹》是湘西女作家彭学军的代表作,其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跟随下放的母亲来到湘西苗乡桃花寨的“我”与妹妹老扁、阿桃一家以及半疯的阿秀婆的故事。桃花寨名副其实,在初来乍到的人眼里,整个村落仿佛生长在一片安详温馨的粉红中。小说的核心人物与次要人物几乎都是女性,甚至故事的一开始,连“我”的父亲都被作者“放逐”到“另一个地方搞工作组”去了,因而整个文本给读者一种“红粉桃花女儿国”的印象。然而,这并不代表这个“她乡”式的小村能够避免男权话语的侵蚀——阿桃的恋人龙老师明知冲喜是迷信,仍然选择做“孝子”弃困境中的阿桃于不顾而另娶,阿桃的父亲每见妻子生一个女儿就砍一棵结婚时种下的象征爱情的桃树,这些行为背后隐含的是将女性物化的思维:女人是冲喜的物事,是生育的工具。延留着宗法制残余的乡村父权社会企图借女性的躯体延续自我衰朽的生命,而女性个体的意志被无视、掩埋,成为只剩下一具符号化身体的空洞能指。
小说中桃花寨最大的危机是野猪吃人,而作者就曾这样描写过阿桃爸:“阿桃妈生下四桃时,阿桃爸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一张阔嘴扑哧扑哧直喘粗气,像一只走投无路的野猪在堂屋里打转,两只眼睛东瞄西望,寻找着发泄的对象和途径。”j阿桃爸妈的爱情曾是村里的佳话,而如今阿桃爸成天黑着脸,阿桃妈为求得子不停生育,生产时无人作陪,生产后以泪洗面、忧心忡忡,农耕文化下的男权思想甚至将那一刻的阿桃爸“异化”成与“吃人”的野猪无异。然而,阿桃爸连年砍树,剩下的树却越来越繁盛,一年一个女孩接连降生,那最后一棵象征着“妹”的桃树在决定它生死的那一天忽然开得如火如荼如诗如画,这是对以“盼子”为表征、企图扼杀女性生命的父权文化的反讽与抵抗,“暴怒的父亲被震撼了,原本朝向花树握着砍刀的手慢慢垂下,仿佛一个高大强悍的成年男性和他所代表的父权文化在女性的生命场里黯然颓败。”k最后为野猪所害的“妹”被葬于树下,原来的树边居然抽出了小树的嫩芽,作者让女孩与桃树永远融合在一起,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将希望的种子留给读者。
但我们也进一步发现,桃花寨里对女性的不尊重根源在于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耕文明在《沉船谜书》中代表的是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和谐,而在《你是我的妹》中则呈现出小农经济的另一面:正是它带来的贫弱才使“生子”成为改善生活的一种可能,它与生俱来的封闭也使得人们难以在思维上有新的变化突破。面对来自山林的野猪之害,人类显得几无抵抗能力,最后依靠阿秀婆的母性之爱以同归于尽的惨烈方式结束了这场祸事。“妹”凭借桃树繁盛的花事消弭了父亲眼中“绝望的、黑豹般”的野兽性、“吃人”性,最终却难以逃过被野猪吞噬的命运。自然在这里并不是完全与女性一体的象征,真正的自然也正是如此,万物与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份子,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张又矛盾复杂的联系。人性在这里更多的是被挖掘与赞美,因为爱,因为对美与生命的感悟,男性的眼睛也可以被那“瑰丽无比的色彩滋润得平静起来、柔和起来”,即使有主流男权文化的桎梏,阿桃的父亲最终仍选择了“不顺从”于扼杀生命与美的丑陋的意识形态,人性之高贵也正由这代表着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中显露。换句话说,小说《你是我的妹》暗示着人类彼此之间的可沟通余地是更大的,真正应该解决的是农村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文本的这种解决策略符合帕特里克·D·墨菲在《代言另一种自然》里提出的建立一种非等级制的、不拒绝(男性—女性、自然—文明)联系的“差异意识”,建立非“他者”的“另者”观l。可以想见,“对话”在这其中将需扮演重要角色。
《你是我的妹》揭示了男权背后的重要根源,即它与贫穷、封闭往往有着相生关系。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中,生存困境中的人类总是更容易选择将女性作为牺牲品,重男轻女观通过农村社会长期的男权话语机制的运作本身被固化的同时又反过来固化了贫穷。女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承受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枷锁,阿桃在阿秀婆葬礼上忘情的擂鼓与舞蹈不如说是小农社会文化下贫弱之地女性的歌哭;作为“干部女”的“我”和阿桃姐妹情深,可是当“我”要回城时,阿桃却仿佛忽然记起主人公“干部女”的身份与之产生了隔阂,这是阶层差异造成的隔膜——即使是一样拥有女性的躯体,她们各自的苦恼、最强烈的诉求仍然是不一样的,亦即此处在诸多“身份”(Identities)中,阶层身份的重要性超越了性别身份——就像西方女性主义在其发展完善过程逐渐中认识到不同种族、国别、阶级的女性受压迫的状况不同,谁也无法为谁作“完全代言”,文本暗示了主流社会的女性亦需省思自身的生活是否建立在对边缘社会女性的压抑之上。
在《你是我的妹》里,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女性之间最终实现的是彼此间的滋养与共生。城市出身的“我”在目睹阿桃姐妹相依为命的感情后,逐渐转变了对妹妹老扁的自私态度,认识到“是阿桃教会我怎么做姐姐的”,姐妹之情越来越融洽。作为主流社会中的知识女性,原是市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母亲”,下放时主动要求到苗区来,这是女性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的一种变式突围——她尽最大可能地维护了自我的意志,选择此处是因为能够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这一举动将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的编码转换成了女性主体的积极选择。在文本的最初和最末,“母亲”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临走念念不忘的是“阿桃应该离开那儿”。多年后,母亲终于将阿桃的作品带到了国际文化展上,成为令阿桃走出山村的伯乐。“她想写一本少数民族文化风俗、发展历史方面的书。她喜欢和一些走路颤颤巍巍、耳聋眼花的老人打交道,她十分吃力、很有耐心地和他们促膝交谈,并四处收集一些陈砖旧瓦、破碗烂罐,甚至死人骨头,拿不走的就把它们一一画下来。母亲对自己的事业如痴如醉……很多年以后,当两鬓斑白的母亲将一部城砖一般厚重,图文并茂、装帧精良的《少数民族史志》递到我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母亲的伟大。”m让藏匿深山的苗乡女性的智慧与文化为中外所知,这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隐喻。而更深层的意义是,这是一次由女性群体内部自觉发起、完成的超越阶层、民族的融通互助,是女性自我完成的对于女性的书写。
三
生态女性主义要实现其最终目标、冲破传统的男权话语体系,必须使女性走出心灵束缚,重新发现、认知自我,而女性的个体经验各自不同,建构主体性的方式也必然随之不同,韦伶“生态/女性”书写的经典之作《幽秘花园》就充分调用了艺术、童年、自然等概念的文化符号意义,书写了一个关于“救赎”与“希望”的文本。
《幽秘花园》以第一人称、幻想小说的形式讲述一对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夫妇的故事。小说前两章的存在将文本分成两个叙述层次,从现实落笔,自第三章才进入正式的故事,交代了白老头、白婆婆退休教职工的身份。这对夫妇隐居在其他教职工家对面的山坡上,“与世隔离,永不与人往来”,成人们都吓唬自家孩子说这对夫妇是疯子,小孩去对面玩会被用棍子赶走。“疯子”也许是主流社会赋予边缘群体最通用的污名,齐泽克曾将“称谓”所包含的赋权职能定义为“称谓的意识形态维度”,它是一种协定。通常这种协定或者说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称谓”的基石,是父系律法n。与成人管夫妇俩叫“疯子”相对的是,文本让叙述者“我”(韦三妹)在知道两人真正姓氏的情况下仍坚持用“白老头”“白婆婆”称呼他们,体现出一种对“称谓”的特殊敏感;不难发现,这对夫妇的困窘还表现在其住所的特殊性上,“对面小山坡上孤独的一所房子”也让他们处于一种被集体“凝视”的状态中,“这边山坡”和“那边山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读者后来知道老夫妇的家屡次被红卫兵打砸破坏,在小说叙述者“我”所代表的儿童的纯真之眼中,这些没有主体性可言的打砸抢者始终被符号化地指称为的“戴红袖章的家伙”而连“红卫兵”这样的明确称谓都没有;老夫妻的八个孩子很可能是在文革迫害中死去,正是这点给白婆婆带来了难以释怀的伤痛,使她丢弃了过去的记忆,沉溺于园圃;至于白老头最珍贵的画作,也被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毁坏,这暗示着在极权社会中,话语只能是单一的。绘画作为“艺术”的一种“在根本上是异在的……是一种理性的、认知的力量,揭示着一种在现实中被压抑和被排斥的人和自然的维度”o,故而它们极易遭到政治高压社会的扼杀。上述之外,小说中“我”对摆放在白婆婆相片下的小相片中人身份探寻的结果,更是象征着从古装相片女子到胡蝶到白婆婆甚至再到“我”,一代又一代女性如同断翅蝴蝶一般或因权贵所喜或因政治高压或因话语围墙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囚禁”在“花园石墙后面”的囚徒命运。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是一个受到话语监控的场域,其间的主人公如何在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里突围,是文本的中心所在。
白婆婆的“花园”是这片话语禁区里最迷人的所在,这里是她用以忘却忧愁疗治心伤之地,是孕育万千生命、展现女性伟力的地方;但同时它也是囚禁白婆婆心灵的牢笼,令她被丧子之痛缠绵束缚住而困守于此,不肯回忆起完整的自己,不肯重新拾起童年时“去远方”的梦想,女性的主体人格得不到真正生长。因此,花园意象在这里具有双重功能,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妥的。正如上文所强调,单纯突出女性与自然之间本质性联系的方式“不仅支持统治性意识形态,而且还限制生态女性主义者促进社会与文化改变的能力”p。实际上,这里的“花园”可被看作白婆婆内心世界的实体化存在。“我”正是在这里初次感觉到了“花园起舞”的美好,这种经验延续到成年之后,让“我”受益不尽。文本用了大段文字描绘这种舞蹈带来的精神之乐,而白婆婆被政治伤害割裂的记忆和被封闭的内心童年自我,也正是在遇见韦三妹后,在其舞蹈引起的共鸣下方才苏醒。如果以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的观点来看,这正是因为“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忘却过去的苦难和快乐,即可把人生从压抑人的现实原则中提升出来。反之,追忆又激起了征服苦难和追寻永恒快乐的冲动。”q花园通向“外界”(也是通向白婆婆童年自我“瑰瑰”)的那个小洞,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人去移开那块明明只是“画”上去的石头。当韦三妹因为儿童的好奇天性移开石头偷爬出花园遇见瑰瑰并把她带回园内与白婆婆相对时,白婆婆的心结也自然被打开。童年的瑰瑰和如今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约而同地成了三妹的朋友,这本身就说明白婆婆最初的希望从未被真正放弃,也因此女童三妹才能遇见她们、引领她们相遇。在这里,“儿童”作为一种“复演”的原始人类、一种更“贴近原始自然”的文化符号被运用,其承担着特殊的引领意义。
与花园相比,白老头留在门窗上的生态之画——那借助门窗构造和光影作用让人分不清虚实真假的“海洋/沙漠”图,才是作者真正认可的精神归宿,这种承认不论性别为何与自然均可联系的写法也许是克服二元对立论的一种重要方式。“海洋/沙漠”图打通的不仅是空间之隔,还有联系心灵的路径。白婆婆曾不再相信“沙漠与海洋”,将其连同丈夫的绘画创作一并斥为谎言,囚禁自己的同时也囚禁丈夫渴望重新振作的心灵。当然,这是因为“文革”的思想钳制和子亡夫走带来的巨大创痛。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承受着双重压迫,即作为“女人”需要面对的性别压力,和作为“人”需要面对的生存异化。面对压抑和异化,《幽秘花园》提供的“生态解决法”微妙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以自然实体而是白老头画在房屋上的画作为象征,亦即以人类艺术文明的形式表现的“自然”。艺术的作用在于“维护和保护着对立——对分隔了的世界的不幸意识、挫败的可能性、未完成的希望,以及被背弃的承诺”r,以虚构法造人精神的实境。“我”在初见“门窗画”时就震撼于沙漠和海洋这对奇异的生态系统组合,它们将现实的不可能抽象到艺术世界的可能,冲击人们固有的审美想象与思想维度,象征着精神自由的广阔天地和永将追寻的远方。因此,白婆婆总是能够在画上看出丈夫走到哪里,想要去哪儿,而白老头也能在千里之外感受到妻子内心,当她想起从前渴望他回到身边时,便立刻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曾经阻止丈夫作画的白婆婆在重新发现自我后,亲手完成了一幅许多游鱼和男孩女孩们牵手飞翔的“大地艺术”,这也意味着她借艺术完成了对自己的最后治疗、重建了自身主体性,她拾起了曾被抛弃的承诺、最初的远方之梦,韦三妹后来在门窗画上看到夫妇二人跋涉于沙漠海洋的身影也印证了这一点。《幽秘花园》试图证明,生态自然与人类文明通过“艺术”之桥梁是可以相通相联的,这就自然而然地打破了早期刻板的二元论框架下将女性与自然同男性与文明对立起来的理念之围。引入后结构女性主义的思路,利用类似《幽秘花园》中的写作策略,承认并推动女性复杂、变动的主体性的建构,而不是简化女性的身份使之变得单一、静态,这也许是生态女性主义文本创作可以尝试突破的一种方向。
从叙事学角度看,《幽秘花园》的双层叙事结构也说明了作者对故事写作掌控力的自信。在内层故事中,二位老人终于离开小屋去寻觅远方的新世界,小屋被地震带来的凹陷永久保存在水里。经历了多年,政治灾难终于还是结束了,“我”把这个童年故事告诉了孩子们,孩子们意欲寻找小屋。小屋成了跨越两个叙事层面共同存在的实体,屋内的图画永远不能被证实是否存在了,故事也因此多了虚实相生的张力。而不论是内层故事里出走的老人还是外层故事里以前者为“美”的儿童,都是自由平等意志最终在文本中得以实现的载体。《幽秘花园》告诉读者的是,“希望”在永远的“前方”,在自然,在艺术,在允许多元思想的社会和纯净的心灵中。
小 结
性别话语的规训,往往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儿童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少年精神成长的陪伴者,值得文学研究予以特殊的关注。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已有渐醒的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声音,其已隐隐包蕴“去中心化”、解构传统性别话语的意识,这确然是值得欣慰的文学现象。笔者通过对上述包含生态女性主义倾向的典型文本的分析,也发现当前儿童文学领域内的“生态女性主义书写”尚未发展至自觉、成熟的阶段,但这不意味着现有文本没有深度解读与再解读的价值。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意识形态分析理论,将会供给我们新的考察与衡量文本的尺度,而这不论对文学研究抑或是对理论本身的拓展与完善都将有所裨益。
【注释】
a班马:《沉船谜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又名《巫师的沉船》,《沉船谜书》是再版后最新的书名。班马(1951~ ),原名班会文。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者、理论研究者。1976年后历任上海《少年报》编辑、广州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讲师。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合著),长篇小说《六年级大逃亡》,童话集《现代梦幻童话》,散文集《星球的细语》,文论集《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前艺术思想》(国家八五重点图书)等。《星球的细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儿童文学奖,其作品还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优秀论文奖、第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沉船谜书》是其幻想小说代表作之一。
b彭学军:《油纸伞》,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彭学军(1963~ ),女,湖南长沙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主要涉及少女题材,尤擅以湘西为代表的乡村少女题材的写作。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终不断的琴声》、《你是我的妹》,中短篇小说集《油纸伞》、《歌声已离我远去》等十余部。长篇小说《腰门》获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短篇小说《油纸伞》获1995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作品《冰蜡烛》获第2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你是我的妹》是其重要的代表作,曾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小说类大奖、海峡两岸少年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阿桃》。
c韦伶:《幽秘花园》,21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韦伶(1963~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广州市女作家协会副会长,少女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作品均涉及少女题材,反映青春发育期的少女文化。1982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幽秘花园》《寻找的女孩》《月亮花园》《山鬼之谜》《鱼幻·裸鱼》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多部。作品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新作奖大奖、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奖等国内及海外多种奖项,并被译介到日本、美国、泰国等地。长篇小说《幽秘花园》是其代表作之一。
d班马:《沉船谜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e班马:《沉船谜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页。
f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 ic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 Collins US, 1980, 192~193. 转引自苏贤贵:《生态危机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g[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5页。
h南宫梅芳:《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iYnestra K.,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Plant J. ,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21~30. 转引自武田田:《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温馨小品——论〈与狼为伴〉中的两性欲望与自然之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j彭学军:《油纸伞》,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k陈莉:《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l[美]卡拉·安布鲁斯特:《水牛女孩们,你们今晚不出来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越界需吁求》,转引自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编:《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蒋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m彭学军:《油纸伞》,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4页。
n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87~102.
o[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37页。
p[美]卡拉·安布鲁斯特:《水牛女孩们,你们今晚不出来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越界需吁求》,转引自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编:《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蒋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
q[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r[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