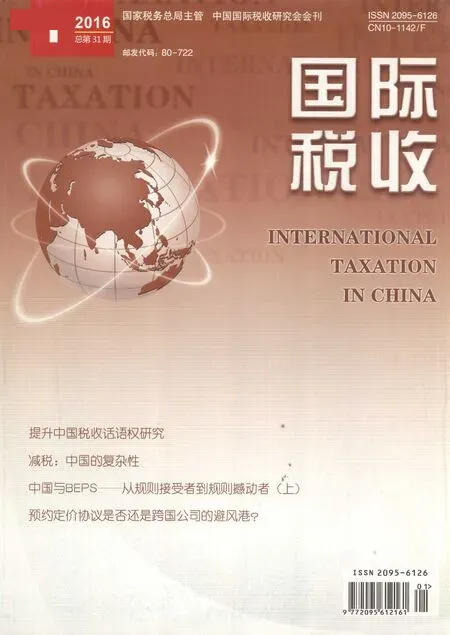减税:中国的复杂性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减税:中国的复杂性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在当前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当论及如何进行这一改革,特别是政府该如何去推动这一改革时,人们开出的基本药方无非两类:简政放权和减税。前者属于改革层面、需要动用改革措施加以实现,后者则往往被归之于政策层面,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中体现出来。鉴于前者的实施不免触动利益格局,亦非短期所能见效,而后者主要限于政策调整,又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产生效应,于是,减税便被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选举措,甚至被当作解决眼下问题的通用疗法。
然而,沉下心来,置身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和税情,便会发现,实际的情形真不似上述的议论那般简单,其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减税自然涉及对中国税负状况的评估。国际通用的税负状况评估指标,就是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在同年GDP中的占比。一旦使用这一指标评估中国的税负状况,首先遇到的一件麻烦事,就是“对口径”——须将“宏观税负”调整改造为“宏观税费负”。
这是因为,目前政府向纳税人所征收的收入,并不都称作税。除了税收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费、基金、罚款,等等。政府所编列的预算,也不仅仅是一般公共预算。除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面对如此多的政府收入形式、如此多的政府预算收入种类,究竟该将哪一块儿或哪几块儿计入宏观税负指标的分子项,历来是有争论的。出于不同的考虑,基于不同的立场,有人倾向于“窄口径”——只将名义上叫做税的政府收入计入宏观税负范围;有人偏好“中口径”——仅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入宏观税负范围;还有人坚持“宽口径”——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计入宏观税负范围。三种不同口径的争论持续了多年,人们对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究竟处于世界哪一档次的认识始终处于混沌状态,中国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广泛认同度的宏观税负统计指标。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新预算法于2015年1月正式实施,有关宏观税负口径问题的争论似乎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不同于老预算法,新预算法明确规定,所有政府收支都需进入预算,政府预算是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构成的统一体。上述四类政府预算收入,在性质上都系政府向纳税人征收的收入,其间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名称或形式,故而,将各种形式、各种称谓的所有政府收入全部计入宏观税负的统计范围,已成顺乎改革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举。
一旦以宽口径的标准评估中国的税负状况,会进一步发现,以2014年为例,名义上称作税的政府收入来源和以其他名称标列的政府收入来源之比,大约为53:47。税收之外的政府收入来源规模如此之大,让其游离于宏观税负的统计范围之外,不仅妨碍中国税负状况的恰当评估,而且更易造成政府宏观决策的失真。为了避免此类事再度发生,或者为了彻底断绝此类事再度发生的逻辑链条,将各种非税的收入来源统称为“费”,从而将“宏观税负”指标调整改造为“宏观税费负”指标,以“宏观税费负”作为评估中国税负状况的适用指标,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2014年的数字计算,将税收收入和各种非税收入,或者,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合并并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全部政府收入规模为225 570亿元,占同年GDP的比重为35.42%。这一数字,相对于工业化国家39%左右的平均税负,在当今世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不仅如此,减税还牵涉到减谁的税以及减什么税的抉择。这是因为,税收是一个统称,它是由不同人缴纳的税和不同性质的税所组成的。在当下的中国,这两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国情和税情特点。
就前者来说,以2014年为例,在总额为119 158亿元的全国税收收入中,来自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公司、私营企业等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超过90%。而来自非企业来源即自然人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不足10%。企业来源收入与自然人居民来源收入之比,大致为90∶10。倘若剔除包含在自然人居民来源收入中的个体经济所缴纳的税收收入份额,则属于纯粹自然人居民来源的收入占比仅为6%左右。企业来源收入与自然人居民来源收入之比,则大致为94∶6。
如此失衡的税收收入来源结构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尽管中国的宏观税费负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中国的企业税费负位次却远高于宏观税费负位次。抛开企业缴纳的税费总要通过各种渠道转嫁出去之类的问题暂且不论,可以说,中国的税费负担基本上是由企业独自挑起的。
就后者而论,仍以2014年为例,在总额为119 158亿元的全国税收收入中,来自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间接税收入的占比达到64.2%。若再加上具有间接税特征的地方其他税种,那么,整个间接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超过70%。而来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收入的占比,仅为26.2%。间接税收入与直接税收入之比,大致为70∶30。可以说,中国税收收入的大头是间接税。
如此失衡的税收收入种类结构启示我们,尽管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费负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但中国税收的绝大部分可以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堂而皇之地嵌入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之中。这部分税收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因其所占份额高,对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影响大,不仅大幅抬高商品和要素价格水平,降低商品和要素价格的竞争力,而且使得价格的升降同税收制度的变化和税负水平的高低捆绑在一起,扭曲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
进一步说,由于间接税与盈亏状况并无直接关联,即便企业陷入亏损,也要照常缴纳间接税,对于亟待探索求生之路、走出困境的亏损企业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一方面是中国的税费负担基本由企业独自挑起,另一方面是中国税收负担的大头在于间接税,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场上静观上述两种力量的各自作用以及交互影响,不难看到,即便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费负并未构成偏高水平,但跳出总量的局限而深入其内部结构,则无论从来源还是种类看,都是严重失衡的。这种失衡的结构格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相关纳税人和不同税类、不同税种之间税费负水平的畸重畸轻。具体说,就是相对于自然人居民,企业税负畸重;相对于直接税,间接税税负畸重。
说到这里,可以对本文的讨论小结如下:
第一,减税,固然表面上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安排范畴,但实际上是一个需从政策安排和改革推进两个层面同时发力的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故而,不仅在宏观经济政策安排层面,而且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层面,不仅从需求一侧,而且从供给一侧,全面系统地谋划好有关减税的各种相关部署,是保证减税落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处的恰当选择。
第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局上,不仅要减税,而且要降费。税费机制在规范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税的规范性远高于费,费所带来的不当干扰远高于税,相对而言,更重要的是降费。故而,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为契机,将始自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税费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将事半而功倍。
第三,在减税降费的旗帜下,有必要对涉及的税费项目或种类排排队,从而明确实施的先后次序。就税费总体而言,相对于减税,降费应优先考虑。就减税而言,相对于减自然人居民缴纳的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应排在前面;相对于减直接税,减间接税属更佳选择。换言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着眼点的减税操作,应当也必须将着力点放在降费、减企业税和减间接税上。
责任编辑:李 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