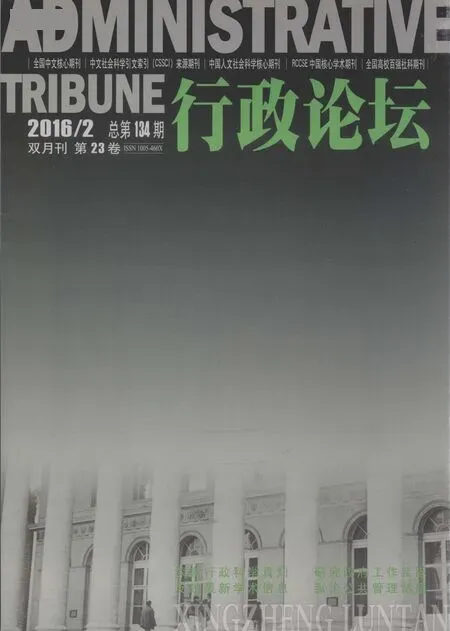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李强彬
◎杨春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李强彬
◎杨春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关于“政策议程如何设定”的已有研究侧重对议程设定影响因素的探讨,忽视了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依据驱动政策议程设定之核心元素的不同,笔者将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分为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在实践中,四种典型途径各有其内在的机理、优势和不足,为避免政策议程设定中的偏差和失误,特别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充分发挥媒介“意见市场”的功能,增强决策者对焦点事件的前瞻意识,以提升政策议程设定的质量。
政策议程;议程设定;典型途径
在政策制定中,关于议程设定的各种优先性排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潜在的政策行动,直接反映着决策者对问题的态度、看法和对解决方案的选择,因而科学、合理地设定政策议程十分重要。但是,实际的政策议程设定活动往往却是盲目和令人失望的,比如本该受到关注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往往无法及时、准确地在政策议程设定的优先性排序中“得其应得”,而无关紧要或“操之过急”的议题却备受重视。出现类似的错位或偏差,不但源于政策议程设定过程本身的隐蔽性,而且在于政策相关者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关注,以致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重新发现问题并审视问题的真实性、重要性和优先性。为此,把握好“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以尽可能避免决策失误和政策失败是十分必要的。
一、相关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自拉斯韦尔明确地界定“政策科学”并将其分为七大阶段以来,“政策何以制定”这一研究议题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作为“政策何以制定”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及其设定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政策过程研究中一个新兴的热点,其重要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1]32。在学术研究中,围绕“问题是如何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形成主体互动论、问题属性论和社会系统论等三种主要的解释途径。
(一)主体互动论认为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过程是问题提出者与其他政策相关者互动以争取支持与认可的过程
代表性的研究如科布和罗斯依据问题提出者将问题置入议程所需互动对象和互动方式的不同而把议程设定分为外部推动、动员和内部推动等三种模式[2]。其中,外部推动的基本过程是:问题经社会团体提出,然后扩散至其他团体以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最后对决策者形成政治压力而将问题置入议事日程。在动员模式中,问题或议案往往不经公众讨论而直接先由当局者提出,再通过宣传或说教的方式谋求公众的支持。内部推动模式则是问题首先被决策层中有影响力的团体提出,而后这些团体直接与决策者沟通,将问题置入议程,从而不需要争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戴伊认为问题的提出、扩散并被提上议程的过程是政策提出者进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与其他政策相关者互动的过程。国内学者王绍光在考察我国的政策议程设定模式时,根据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将中国的政策议程设定模式分为关门、动员、内参、借力、上书和外压等六种模式[3]。
(二)问题属性论把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过程看作问题相关属性和要素的呈现并获得公众尤其是决策者重视的过程
对此,科恩和奥尔森等人认为在组织决策行为中,人们的问题偏好是模糊的、技术手段是不明确的、人员是流动无序的,因而政策相关者仅仅是问题进入议程的一个因素,只有当问题本身的属性、相应的政策方案以及决策者选择的时机等这一系列围绕问题的“要素”达到一定条件后,问题才能被提上议事日程[4]。沿着上述“垃圾桶”模型,金登亦强调问题进入议程的复杂性状况和偶然性因素。根据金登的观点,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过程是问题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由问题所催生的国民情绪和政治压力等“多源流”作用的过程[5]123。此外,在格斯顿看来,问题能否被提上议事日程,有赖于是否形成了触发机制即问题所引发的一个重要事件,事件的范围、强度和触发时机又反映着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等“问题”本身的属性[6]23。
(三)社会系统论把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过程看作社会环境要素积累或转变的过程
对此,豪利特和拉米什做出过精彩的论述:“政治或决策议程就是一个用人们在政治演讲中浓缩、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态度和信念构成的议程”[7],他们尤其重视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中观念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过程,因为他们坚信虽然问题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互动情境,但思想观念却决定着问题提出者行为的强烈程度和决策者对问题的态度。斯通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认为人们提出问题并将其置入政府议程是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她以土著印第安人面临的问题的变化为例来论证此一观点[8]328。国内学者刘伟和黄健荣将社会系统和主体互动两种途径相结合,提出了政策议程设定的“体制—过程模型”,并依此区分了内创型、外创型、动员型和融合型等四种政策议程设定模式,强调要将“问题进入议事日程”置于具体的体制环境中予以分析[9]。
综上所述,关于“政策议程何以设定”的上述研究试图从影响政策议程设定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的角度来揭开政策议程设定这一“黑匣子”,却忽视了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政策议程设定过程的考察需要追问:驱动政策议程设定不断演进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什么,不同要素驱动的政策议程设定途径又有何特点,实践中又如何不断改进不同要素所驱动的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为此,本文通过对政策议程设定本质与现实的观察,尝试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以期促进政策议程设定质量和效能的提升。
二、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从本质上讲,政策议程设定就是政策相关者在正式、权威的政策方案出台之前对被感知到的社会问题及其相关要求、态度和意见进行优先性排序的政策活动,实质上是各种影响力相互角逐的过程。就实际的政策议程设定过程而言,无论将政策议程设定描述为政策相关者之间互动的过程或是问题属性呈现的过程,抑或是社会系统要素聚集的过程,其演进无疑受到议题相关者政治影响力大小的约束。与此同时,决策者也不得不考虑相关者的权利诉求,并且,作为社会问题“放大站”的媒体和事件亦直接驱动着议程设定的演进。基于此,根据政策议程设定驱动力的来源及其属性,本文重点考察驱动政策议程设定的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
(一)权力驱动及其实现
作为特定体制下因资源占有多寡和能力大小不均而形成的一种非对称性影响力关系,权力“不仅存在于显性的决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对政策议程设定的控制中”[10]。可以说,权力这一影响力本身就构成了政策议程设定演进的基石。因为,议程的设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判断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政策相关者围绕资源的竞取而给问题贴上标签并与其他相关者进行互动的一种政治活动,这一政治活动之所以能够运转起来,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权力。通过权力的运用,问题的提出者或相关者才可以影响、修正和塑造其他利益主体的观念与行为,继而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关注、认可与支持。最终,问题能否进入正式的政策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问题支持者所掌握的权力资源的多寡和所具有的影响力的大小。相对来说,那些掌握实际影响力的个人和组织往往更能通过强制、说服或潜在的操控等方式来影响议程的设置,驱动议程设定的演进。
进而,权力驱动的政策议程设定通常有两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一是当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危及权力优势群体的利益时,为减少政治资源的流失或重新分配权力,权力精英往往会运用“不决策”的权力进行议程操控,以遏制、排挤、压制问题提出者的“声音”;或者,对提出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界定,从而阻止特定议题或方案被提上议程。二是当大多数政策相关者未意识到问题或对问题没有形成意见偏好,而权力优势群体需要提出新的议题时,他们可以通过偏好动员或偏好塑造来获得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的认同与支持。
相应的,对于没有资源优势或资源相对缺乏的政策相关者来说,其政策诉求则容易被忽略、被隐藏或“被俘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策议程设定活动中完全无能为力,与权力精英进行讨价还价、争取权威决策者的支持同样能够驱动议程的设定。例如,2005年河北省普通农民王淑荣为了能把镇里征收盖养殖场却被闲置下来的土地要回来,她发现《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与《土地管理法》存在冲突,于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相关情况后最终建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规定[11]。可见,尽管王淑荣个人的影响力和能够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但她通过接近权威决策者并获得其支持,从而促使当地政府修订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有研究将政策议程设定的过程描述为“决策倡议者努力缩短‘权力距’的过程”[12]。
(二)权利驱动及其实现
作为一种自然的正当性要求,权利是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过程得以良性运转的基本要素。无论将权利看作民主政治实践发展的产物,还是将其作为道德规范的自然的产物,权利的观念都要求公民在政策议程设定的过程中能够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在正式的政策方案出台之前表达偏好、反映诉求、影响议程的优先性设置。相应的,政府的决策行为应当维护和增进公众的权益,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在权利驱动的议程设定途径中,权利诉求产生于公民个体没有能力去实现对于自己能够做什么、能获得什么以及将得到什么的某种期待,但是依道德性规范的要求,此一期待是应该得到回应的。进而,一旦当局者认为特定的权利应该得到关注与保障时,权利的观念就推动着特定的问题进入议事日程并表现为具体的政策行动。
抛开“权利神话”,特定的问题要挤入政策议程并居于优先位置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斯通所说,“即便权利有时候是针对个别人或者个别情况的,但是要通过这样的权利来改变制度权力结构和塑造个体行动的惯例是极为困难的”[8]328。因为,个体性的权利呼声总是容易被规模更大的权利诉求联盟的呼声所掩盖而难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也就很难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权利所驱动的政策议程设定演进往往需要通过形成权利联盟来推动特定要求被提上政策议程。与此同时,个体性权利也倾向于通过形成权利诉求联盟来影响政策制定。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权利诉求本身已经重新确认或重新修正了社会的内部规则以及其成员的分类;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利诉求联盟能够动员的资源和形成的政治压力远远大于个体性权利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量的维权抗争事件总是倾向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动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毕竟,当权利诉求联盟形成,联盟内部就会进行分工与规划,并有组织地采取申诉、集会、宣传、游行甚至是暴力抗争等方式向当局者提出要求。迫于权利诉求联盟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当局者往往不得不快速地将特定的诉求纳入议事日程。此时,权利就成为驱动政策议程设定的核心元素。比如在“乌坎事件”中,出于维护村民土地增收权益的考虑,个别村民先后进行多次上访、申诉,却无济于事。然而,通过建立维权联盟①除了原先的宗教理事会和神明理事会在其中发挥了文化动员与物质支持,还成立了“乌坎热血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和“老人联合会”,尤其是“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其中发挥了支持和动员作用。,有组织地进行“9·21”“9·22”“11·21”等集体“大上访”“大游行”甚至“警民冲突”,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高层级政府的高度关切,促使广东省委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赴乌坎解决相关问题。
(三)媒介驱动及其实现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被誉为“第四权力”的媒介在政策议程设定中作为议题“放大站”的功能愈来愈显著,其“领导权威与国家、公司企业、政府所发挥的领导权威相比,可以说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能够决定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日程表”[13]。媒介之所以驱动政策议程设定的演进,基本的缘由在于它不但是信息传播、偏好表达和议题放大的重要工具,而且能主动地对社会偏差和公共议题进行批判性评论,因而媒介“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想什么,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想”[14]。在设定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和评述可以将问题的客体显要性(object prominence)和属性显要性(attribute prominence)传递给公众和政府,从而影响公众和政府对问题的认知,进而引导舆论、塑造民意并推动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促成政策议程设定的发展。
在媒介驱动的议程设定中,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力所指向的问题本身的突出程度即问题的客体显要性。对此,媒介往往可以通过传播、报道的密集度和优先性来影响受众(政府和公众)关于特定议题的感知度。感知度越高,特定议题的突出程度往往也越高。因为在事实上,人们并不能对特定时段内的所有议题予以关注并区分出优先性,通常情况下会受到媒介传播和报道的影响,认为传播靠前、标题醒目、报道次数和篇幅越多的话题就是特定时段内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应当进入政府议事日程。相反,对于媒介没有进行密集和优先性传播的问题,普通公众很可能因为时空与精力的限制而难以感知或者只能为较小范围的公众所感知,难以进入正式的政策议程,尤其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来说。在这一方面,媒介成功地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
问题某方面特性的突出程度则是问题的属性显要性。对此,媒介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公众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也来源于媒介”[15]。比如人们在看新闻时,并不是只看报道了哪些话题,他们会进一步关注媒介信息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具体内容往往伴随着媒介的情绪、情感和具有价值倾向的解读,对于那些对特定话题没有感觉和经验的受众而言,往往更倾向于接受媒体的看法和观点。并且,随着媒介报道次数的增加和解读者权威性的提升,关于特定问题的认识和观念会在其受众那里得到明显的强化。在媒介的放大与引导下,人们对特定问题某方面的属性而不是其他方面属性的关注度往往会显著地受到影响,从而促使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特别关注问题之某些方面的属性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属性。
(四)事件驱动及其实现
作为问题激化、外显与放大的一种重要方式,焦点事件能以紧迫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从而迫使当局者不得不将相关议题纳入议事日程并做出公开的回应。尤其是,焦点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消极状况能够为问题现状的不利者提供向当局发出变革要求的良好时机,并形成变革的政治压力,而只要“当一个事件把一种消极状况催化为要求变化的政治压力时,就会因触发机制的持久性而发生性质改变”[6]23。因而,“某些议题可以因为某种危机,自然灾害或者轰动性事件(如飓风和空难)而被提上政策议程并采取行动”[16]。
焦点事件之所以能快速地驱动政策议程设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聚焦社会注意力、形成社会恐慌、催生政治压力等三种方式来推动政策议程的设定。
1.焦点事件能够很快聚焦社会注意力,尤其是与那些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数据或理性分析才能被发现的问题相比,焦点事件所指向的问题往往是具体而紧迫的,且相对来说,受影响人数越多、范围越广、破坏性越强、持续时间越长的焦点事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事件所反映的问题也更容易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因为“政策议程设定过程本身即是关于在特定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各种问题吸引公共注意力的过程”[17]。
2.焦点事件通常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紧张,而处于紧张中的人们必定会要求当局者采取特定的行动予以回应。因为,除了焦点事件本身所展现的消极状况,它往往也暗示着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这些风险如同“无知之幕”,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不会成为类似事件的受害者,因而不论是事件的当事者还是与之毫无关系的公众都希望当局能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比如2011年的“正宁校车安全事件”就使校车安全管理问题暴露出来,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促成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
3.对于政策现状的不满者来说,焦点事件为他们带来了发起政策动员、要求变革的重要契机,他们往往会“将焦点事件与已经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从而加深并强化对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将焦点事件与潜在威胁相结合,诱发人们对社会潜在、巨大的危险的关注,从而产生政策预警,促进政策变革;将焦点事件与其他类似事件相融合,产生对问题的新的解读和界定”[5]123-124。这样一来,那些曾经被当局者束之高阁的问题就很可能得以明晰而紧迫地呈现在社会公众和政府的面前,迫使当局者调整议事日程。
三、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四种典型途径比较
驱动政策议程设定演进的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在动力基础、动力机制、实现方式、关键主体、民意基础和偏差表现等诸多方面各有其特殊性,见表1。就四种典型途径的动力特性而言,权力途径中那些占据优势资源和拥有更高能力的权力精英往往掌握着关于问题前因后果、紧迫性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话语权,具有显著的精英性和自上而下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能见度较低、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来说,权力精英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权利驱动的途径中,问题产生于公民对权利现状与权利需求之间差距的不满,因而普通公众对问题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他们往往通过诉求表达的规模性向当局阐释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具有显著的公众性和自下而上性。在媒介驱动的途径中,尽管媒介并不能凭空构建一个社会问题,但媒介却能够甄别出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在媒介的放大与引导下,议题的优先性排序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事件驱动的途径中,焦点事件所显化的问题属性将引起社会和当局的关注,进而形成政治压力,以应急和倒逼的方式快速地推动议程设定的演进。

表1 驱动政策议程设定的四种典型途径比较
就四种典型途径中动力的作用方式而言,权力在政策议程设定中的运用不但广泛,而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一方面,权力本身可能潜在地被操纵和塑造;另一方面,权力可能使应当被讨论的议题或方案在“无声中”被确定。与权力相比,权利是一种更具扩散性的政策议程设定驱动力,因为权利主体为将其权利诉求置入当局者的议事日程,需要明确地表述权利诉求并在更大范围内传递以寻找更多的盟友,寻求更多的来自其他政策相关者的认同与支持。相对于权力和权利,媒介途径的动力基础来自对事实的追寻和传播技术的支撑,特别强调舆论和民意的重要性,尤其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更显重要,“它决定人们将要谈论和思考的话题——这种权威在其他国家为暴君、传教士、政党和官僚所保留”[1]34。相对于前三种途径,事件则是一种应急式的政策议程设定驱动途径,具有被动性,因为事件往往是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危害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之后所采取的政策行动是倒逼式的。
就四种典型途径中议程设定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而言,权力驱动途径的关键主体是拥有更强影响力的权力精英,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使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因而潜在的控制与操纵是其典型特征。实践中,尽管权力精英为了减少公众的抱怨会允许那些不威胁到其自身利益的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一旦议题可能触及其特权地位或核心利益时,他们则会通过隐藏问题或重新界定问题等方式阻滞公众议题在议程设定中居于优先性。在权利驱动的途径中,相关者往往会通过公开的竞争与抗争的方式进行互动。对同一议题,因为权利诉求的差异,公众往往会分化为数个不同的权利诉求联盟,为把各自主张的权利诉求置入议程,联盟之间会形成竞争关系,对于当局者则往往会采取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权利诉求。在媒介驱动的途径中,作为交流和沟通的一种平台,媒介主要通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来与政策相关者进行互动,进而影响政策相关者的态度与行为。在事件驱动的途径中,当局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往往会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互动,最大限度地听取公众意见和维护公众利益,对于那些不满于现状的相关者来说,则可能借机责备当局者的政策安排。
就四种典型途径潜在的“危险”而言,在权力驱动途径中,如果权力精英不受约束地通过话语操纵、偏好塑造、“隐蔽议程”和“不决策”的方式而垄断或操纵政策议程的设定,就会导致最终的政策议程被扭曲甚至失控,致使紧急但不被权力精英所认同的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而“如果有太多意义重大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那么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18]。在权利驱动的途径中,如果权利诉求联盟之间以及他们与当局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协商机制,一方面,可能因为陷入“无政府的闲扯”而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权利诉求的广泛性而使得议程设定通道变得拥挤、无序。在媒介驱动的途径中,如果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或由于职业水准较低而未能对社会问题做出公正、合理的描述与评价,则可能误导公众和社会注意力,进而造成政策资源的浪费。例如,2015年7月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僵尸肉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强烈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进行查处,但经长沙和南宁两市海关调查,却证实“僵尸肉事件”完全是媒体演绎出来的[19]。在事件驱动的途径中,虽然焦点事件是显化问题的重要方式,但如果政策议程设定只能通过焦点事件驱动而不具有前瞻性和主动性时,成本将是巨大的,焦点事件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代价。
四、结语与展望
毫无疑问,问题及其相关的意见被提上政策议程的过程会受到问题本身的属性、政策相关者、制度、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政策议程设定本身即优先性竞争的特质出发,需要进一步回答政策议程设定是如何被驱动的。通过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驱动途径的考察,我们发现:驱动政策议程设定演进的力量是多样化的,每一种途径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现实中的政策议程设定也往往是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核心的问题是在议程设定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民主性、责任性、有效性、准确性、前瞻性和及时性得到保障,避免议程设定中的各种偏差,以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在中国语境下,加强和改进我国政策议程设定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防止权力滥用;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保障实质性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媒介发挥“意见市场”的功能,并在媒介传播与正式的决策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衔接关系;增强决策者对焦点事件的危机意识,提高政策议程设定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权力驱动的政策议程设定模式需要对不断增长和发展的公众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做出有效的回应,需要更好地发挥专家、媒介、利益相关群体和公众在政策议程设定演进中的功能和作用。
[1]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10版.彭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COBB R,ROSS J K.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Process[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6,70(1):126-138.
[3]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86-100.
[4]CHOEN M D,MARCH J G,OLSEN J P.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17(1):1-25.
[5]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拉雷·N.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M].朱子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7]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88.
[8]德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M].修订版.顾建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刘伟,黄健荣.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8,(3):30-40.
[10]BACHRACH P,BARATZ M.Two Faces of Power[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2,56(4):947-952.
[11]朱虹.河北普通农民上书地方法规修正[N].人民日报,2005-5-31(10).
[12]鲁先锋.“权力距”视野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2):69-75.
[13]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鞠方案,吴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4.
[14]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4.
[15]PLEIN L C.Agenda Setting,Problem Definition,and Policy Studies[J].Policy Studies Journal,1994,22(4):701-704.
[16]詹姆斯·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M].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9.
[17]WEISSJA.ThePowerof ProblemDefinition:TheCaseofGovernmentPaperwork[J].Policy Science,1989,22(2):97-121.
[18]盖伊·彼得斯.美国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M].顾丽梅,姚建华,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4.
[19]施志军,武红利.海关称未查获过“僵尸肉”——专家表示该词难以确切定义[N].京华时报,2015-7-11(010).
(责任编辑:朱永良)
D630
A
1005-460X(2016)02-0068-05
2015-11-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群体性事件政策议程学发生机制与治理研究”(14CGL038);四川大学青年学术人才项目“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化、科学化公共决策制度的构建”(SKQX20130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项目“维稳模式重构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研究”(SR15A03)
李强彬(1980—),男,四川眉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杨春黎(1990—),男,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