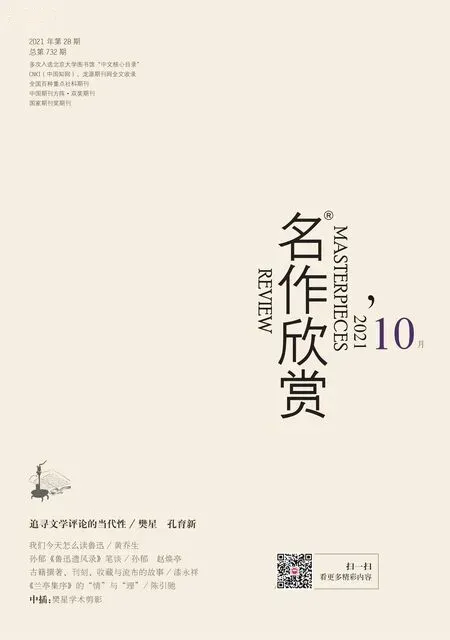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北京 赵稀方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北京 赵稀方
年龄的原因,近年来已经不敢熬夜了,但读《陈骏涛口述历史》那一晚上,我却不忍释卷,一口气读到下半夜。吸引我的,并非故事如何精彩,而是作者的坦诚。
所读过的回忆录,基本上从自己的立场说话,为自己辩护是可以理解的。由晚辈写的缅怀文章,自然更以歌功颂德为主。这本《陈骏涛口述历史》却完全不一样,它给人的印象是对人宽、责己严,对自己甚至苛刻到了严酷的地步。
就历史而言,本书一大看点是陈老师引用了自己的“文革”日记,并且主动暴露出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文革”中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还主持了唐弢先生的批斗会。这很出人意料。众所周知,“文革”是“过来人”的心理阴影,每个人都在竭力为自己撇清,少见如陈老师这样在多年后主动揽责的。
就学术而言,身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陈老师,自我评价并不高。他在总结自己的评论文章时说,自己“学养不足,知识功底不深”:“我的评论文章,除了少数以外,多数都是一般化的,或者说浅层次的。满足于追踪式的评论,缺少挖一口深井的功夫,这是我的最大弱点。”我所见过的成名学者,无论如何谦虚,多自恃自己的学术,所抱怨的是不为世人所理解。像陈老师这样算是功成名就的学者,居然能如此贬低自己的学术,并且作为晚年的定论,心理足够强大。
就个人生活而言,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妻子,二是对孩子,三是对父母。出乎意料的是,陈老师居然在三个层面上都否定了自己。他高度称赞师母的付出,但承认自己不太会关心师母,甚至说自己“自私”。他很爱孩子,但承认不愿意在孩子身上花费时间,“我对孩子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对于父母,他对自己的苛责更深,他说自己是“不
“陈骏涛口述历史”在本刊连载半年,目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无论是刊物选载的内容还是全书,都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陈骏涛先生以对自己亲历的文学史事件的回顾,为线条化、平面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增加了无数丰富生动的细节。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学者对此内容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反馈。本刊将分上、下两期与读者共享,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一文学史事件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对其意义更为充分的认识。 ——编者孝之子”,忏悔父母去世,自己居然都没回去。在伦理道德本位的中国,陈老师敢说自己是“不孝之子”,绝对非同一般。
仅此,已经足让人震动了。这还不够,书中又设置了另外一重修辞,即陈墨的无情评点。这需要提到本书的对话体体例,是对话者又是编者的陈墨一方面与陈老师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文末进行犀利评点,使得陈老师即使想有所隐瞒,都无处遁形。自谦者往往容易说自己不行,但家里人很行。陈老师在回忆家世的时候,说父亲曾经参加过北伐。陈墨通过年代考证,认为他的父亲不太可能参加过北伐,陈老师记忆有误,有误的原因是这一事件是可以被铭记的政治亮点。在另外一个地方,陈老师坦承自己智力不高,陈墨尖锐地指出:陈老师20世纪50年代复旦本科研究生毕业,智力是很高的,缺乏的是“特立独行的活力或勇气”。陈墨是陈老师过去的硕士生,他敢于如此尖锐地批评自己的老师,也是惊世骇俗之举,为吾辈所不及。话又说回来,这种行为肯定是陈老师首肯的,这是很需要胸襟的。
这还没完,致命的一击来自于最后,那就是师母何立人的“访谈录”。一般而言,家属对于传主都是美言有加,增光溢彩,何立人师母对于陈老师的批评却毫不留情。有些事我们原本还觉得陈老师过于谦虚,经何老师一说,发现所言非虚。女儿漫红考大学的时候,何老师希望陈老师能辅导一下她的作文,这是陈老师强项啊!但他不上心,“还说他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就是靠自己”。周末的时候,陈老师总是让何老师把孩子带到外面去,以便自己工作,从未想到——何老师说——她多么希望能够全家一起逛公园。这真有点让陈老师无地自容了,陈老师老来对此也感到后悔,觉得自己把事业看得太重了,对家里付出得太少。
至此,陈老师情何以堪?他如何能够承受这“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觉得,在这里很需要为陈老师说几句公道话。很明显,不是陈老师个人出了问题,而是时代出了问题,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
在政治上,他不过随波逐流罢了。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每个人的主体都是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难以幸免。对于“文革”,每个人都有责任,这现在已经是常识了。陈老师之揽责,并非说明他的罪责,恰恰相反,说明他敢于承担。
在家庭上,陈老师也并不特别。那个时代的父亲,大抵都是这样。我记得自己的父亲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很少管家里的事情。那个时代,家里孩子很多,基本上都是放羊。
最容易让人诟病的“不孝”问题,其实也自有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陈老师竟可以说是最孝顺的子女。陈老师不回老家的原因,是为了省下钱来寄回家。从书中看,陈老师从工作起一直坚持往家里寄钱,到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以至于家里老人都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削减一些。陈老师认为,把路费省下来寄回去,比自己回家应该是对家里有更大的帮助。在经济极度困难,家里出事需要经济支柱的时候,陈老师的做法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吧?
再说学术,陈老师说自己“学养不足,知识功底不深”,这诚然不错,但1949年以后接受教育的那一代知识人,谁不是这样呢?能够奢望他们和中西学问贯通的“五四”那一代学人相比较吗?其实即使到我们这一代学者,情况仍然一样。去台湾客座几次,我的感觉是,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我们的功底都不及对方。原因何在?所受教育不同。
由此看来,陈老师的自我批评,其实只是说明他比较有自省和忏悔意识,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缺乏的。陈墨兄敢于尖锐批评老师,坦诚交流,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师生关系所缺少的。这本书的创新,正在于这种文化层次上的突破。
作 者: 赵稀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