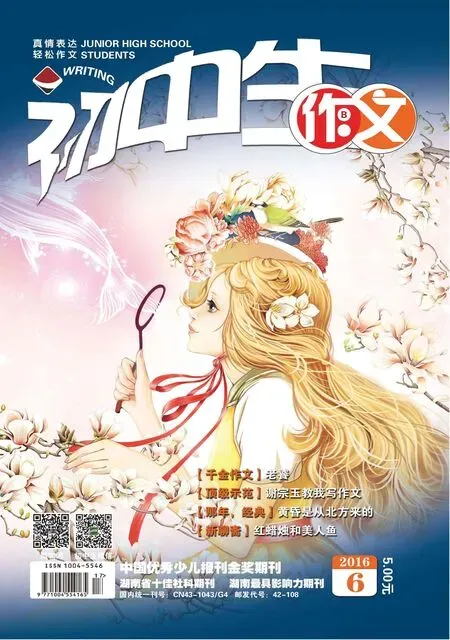黄昏是从北方来的
——季羡林《黄昏》赏析
文/马 以
责任编辑:江 冬
季羡林
黄昏是从北方来的
——季羡林《黄昏》赏析
文/马 以
责任编辑:江 冬

【导言】

季羡林(1911—2009):生于山东清平县(现临清市),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有“国学大师”之誉。代表作有《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天竺心影》《病榻杂记》等文集。
【原文】 黄昏
季羡林
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数,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感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一群群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压在他们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鸦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东方吗?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从西方吗?西方不正亮着红霞吗?从南方吗?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最适宜了。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端,是北冰洋,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吗?
然而,蜕化出来了,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融入淙淙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被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被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跑了来,像——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又充满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流动。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则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们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吗?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不是一切人们,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常常待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愿意这样做,我(自然也还有别人)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做而已。常常在夏天,我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起来,四周的白墙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天空里飞着蝙蝠。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我蜷伏在屋里。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在白天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是黄昏了。我从门缝里望出去: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儿凄凉,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这时,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着它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门外。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黄昏不觉得寂寞吗?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了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它也真的不能久留。一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的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问它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吧。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辽旷的非洲。非洲有耸峭的峻岭,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再想下去,森林里有老虎。老虎?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吧。像不像两盏灯呢?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比人高。草里有狮子,有大蚊子,有大蜘蛛,也该有蝙蝠,比平常的蝙蝠大。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漏了进来。一条条灿烂的金光,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也该有萤火虫吧,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也该有花,但似乎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是什么呢?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在毒气里,不只应该产生“恶之花”吗?这花的香慢慢融入棕红色的空气里,融入绚烂的彩雾里,搅乱成一团,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然而,不久这热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融了。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现在渐渐地更亮了。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在静默里瞅着暗灰的天空才露面的星星。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的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稀疏的冷月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去吗?随了眨着眼的小星爬上天河吗?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屋檐吗?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吗?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风,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吗?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门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赏析】
你写过关于黄昏的文章吗?如果没有,你打算写一篇吗?如果要你来写,你会写黄昏的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写呢?
想一想,其实自己也还从没写过关于黄昏的文章。那么如果现在要我去写,思来想去,觉得最好还是学习季羡林的这种方法。
季老的这篇文章,最令我想去学习的,就是他在写自己对于黄昏的一些独特感觉。在文章的第一段,他就这样写道:“我要问:有几个人感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是啊,黄昏,对我们而言多么熟悉,可也许正因为太过熟悉,我们往往忽略了它。而即使是意识到了这种忽略,也往往毫不在意:黄昏那么多,错过了也还会再来。
因此,如果要我去写黄昏,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感受它,感受它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能给我以什么样的触动。而黄昏给予我的这些印象、感触,无疑将成为我这篇文章的主体。感受黄昏的时候,与时间、地点有关,更与个人的修为、情怀、视角、敏锐度以及情绪等有关。这些主客观因素,将决定我的感受是平常还是独特,是平庸还是精彩。
我们且来看季老的感受是否独特与精彩——它们其实差不多是同一个概念,一个人在文章中的感受,如果独特,就定然精彩;如果精彩,又必然独特。
季老在文中的感受是多元的,但概括起来,大体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觉感受。文中,我们可以找出大量关于黄昏的视觉描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文中,季老总体的视觉感受,就是对黄昏之美的喜爱。他的视角,处处在于对黄昏之美的探寻与发现。但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季老笔下的黄昏,并非我们平常想象中充满绚烂晚霞以及人畜归来等的温馨之美,而是显得苍茫、暗灰、清冷等。季老眼中的黄昏之美是如此一番景象,这便是其感受的独特性。而他这种对于美的独特感受,也将启发我们对于美的全新认知。
二是听觉感受。“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则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们心头”“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在这样的声音描述里,我们依然看到了季老个人的独特体验:如果是你,你会觉得黄昏的声音“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压在人们心头”吗?虽然阒静,却又像悠扬的笛声、亮唳的鹤鸣吗?季老写黄昏的声音,依然是在写黄昏之美——这样的美,他觉得只有“笛声”“鹤鸣”这些美妙的事物才能比拟。
三是心灵感受。虽然说,一篇文章中对于视觉、听觉等的描述,都难免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心灵感受,但也有一些是表现得十分鲜明的,比如说回忆与想象。本文中,季老回忆了自己童年时对于黄昏的种种特别印象与情感。不过更为独特的,是他对于黄昏生发出的种种想象:他说黄昏是从北方来的,又说黄昏去了南方。这样的话多么荒谬,却又是多么特别!可是这样的话真的荒谬吗?虽说黄昏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北方、南方则是地理概念,彼此互不能交叉,但季老在这里,写的就是一种独特的心灵感受,运用了类似于绘画中的写意手法——虽不写实,却能表现其神韵。季老说黄昏是从北方来的,是因为北方的严寒、萧瑟,正契合其心目中黄昏的清冷;而他说黄昏去了南方——遥远的非洲,那儿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老虎、大蚊子、大蜘蛛等,则是因为这契合了他所认为的“黄昏是神秘的”。若理解了这个,我们再来看季老的这种想象,是多么奇妙!
难以赘述。总的来说,季老的这篇《黄昏》,的确是写出了其独特的感受(就连语言表达,也是极具个性的)。而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季老身为“国学大师”,其在文中除了提到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外,再无其他有关黄昏的诗文引用——是这类诗文少见吗?或是他不知道其他的吗?当然都不是。这告诉我们,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在于其中体现了多少“学识”,而在于体现了多少作者的“个性”——而这,主要源于作者对于这个世界以及生活的独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