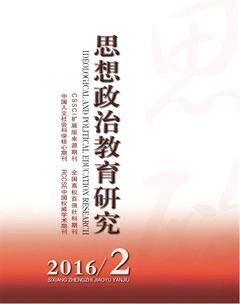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探究
摘 要: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学界提出了包括外部灌输和价值认同与心理建设等路径,但鲜有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探究,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心灵世界里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类自我意识和信仰结合起来,使之转换为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转换为信仰提出的绝对命令,成为社会成员基于其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呼唤和向往而自觉遵循的人生基本价值规范。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自我意识;信仰;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2-0009-05
自中共中央提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探讨它的培育路径一直是学术热点。总体上看,学界所提出的培育路径除强调外部灌输外,也涉及心理建设,但鲜有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心灵世界里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类自我意识和信仰结合起来,使之转换为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转换为信仰提出的绝对命令,成为社会成员基于其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呼唤和向往而自觉遵循的人生基本价值规范。
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把它置入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路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路径,学界提出了宣传教育途径、国民教育途径、重点群体突破途径、领导干部示范路径、思潮引领途径、模式创新途径、制度设计途径和环境优化途径,这些可以概括为外部灌输路径。学界还提出了利益趋动途径,但通过利益驱动使社会成员接受某种价值观念,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和行不通的。有学者指出,只有获得情感上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内化为心理世界的道德自觉和价值支撑,在行动上自觉地遵守与维护[1];宏观上看,只有建立在人民群众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才名副其实,这种心理认同“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表现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普遍接受和由衷支持”[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建设途径是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激发社会成员自身内部的动力[3],激活认同主体的潜在情感,促进社会成员认知、认同、选择并将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判断、道德情感、价值取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社会成员的情感心理层面,从根本上看应该深入到社会成员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是指,把它与中华民族心灵和精神世界里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类自我意识和信仰结合起来,使之转换为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和社会生活中区分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判断标准,成为信仰提出的绝对命令,成为基于中华民族全体社会成员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呼唤和向往而自觉遵循的人生基本价值规范。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心灵世界里的人类自我意识结合起来,使之转换为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
董德刚教授指出,研究人的价值观离不开基本的人性假设。但他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构人性模型的尝试是失败的。首先,他提出的人性模型不是价值哲学和价值观所需要的人类自我意识。董德刚教授认为,人性是自利和利他的统一。[4]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人性模型不是对“我是谁?”或者“人是什么?”的回答,例如西方所说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和文化的动物,再如儒家学说所说的“仁者,人也”,即人是有道德发展潜质的生命体。因此,他所提出的人性模型不是、也不能上升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类自我意识,因而不能成为价值观的形而上前提。第二,董德刚教授的论证也有不足。他引用了西方广泛流传的话展开论证,“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句话的文化含义按照古希腊的看法是,人有灵魂和肉体,作为肉体的人,他具有欲望(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且总是要死的(有限性),这些与其他动物没有区别;但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使人不愿满足于和停留于动物的生存状态,而要追求神的智慧,追求神圣、崇高、纯粹、无限和永恒。从这里我们找不到自利和利他及其统一的任何根据。最后,他由此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能成为作为人生基本价值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不过,董教授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心中没有关于人的基本定位,也就谈不上抛弃那些低级的、庸俗的甚至无耻的、罪恶的动机,胸怀崇高的、神圣的、纯粹的价值追求,更谈不上在社会生活中需要遵循什么基本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了。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建构、选择和确定是价值观研究的理论前提。就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确实需要在理论上为它提供某种人类自我意识,确立社会成员建构个人自我认同和在自我认同基础上确立起自我的人格和尊严的价值原点,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换为人之为人的判断标准,成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判断标准。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人类自我意识方面我们遇到巨大的理论难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中,我们有三个选项:第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这是我们关于人的经典看法。学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论断只是指明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5];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只是在批判的否定的意义上谈的,表现了马克思理论探索的社会批判价值。[6]第二,人是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动物。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7]这种论述虽然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特殊的地位,却被广泛接受,例如在《现代汉语字典》中人就被解释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8]还有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选项,即人是理性的动物。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直接源于恩格斯在宏观概括近代西方哲学时做出的论述,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看到恩格斯的批判而不自觉地延续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主题。这样,在延续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主题和基本框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延续了那里掩藏着的观念: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样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3-1846年间对理性做过持续的和尖锐的批判。因此,即使挖掘出这个选项,它也是没有价值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或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这种观点,还批判了对人做符号化定义的探讨方式。他在探讨“协作”时有云,“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接着在注释中补充说,“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动物。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9]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这里的论述?他抛弃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从来不用本质规定的方式为概念下定义。[10]他从人自身的发展程度和丰富程度的角度研究人。但这样一来,在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类自我意识到底是什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某种人类自我意识?当下在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深处有没有某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人类自我意识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有言行严重错误的人,我们经常听到这样地批评,“你还是人吗?!”“禽兽不如!”如此等等。只要钻牛角尖地问一句,什么是人,人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显然,在这些批评里潜藏着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类自我意识。虽然我们在语言上说人是社会的动物,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但在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里,有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古老而深厚的人类自我意识:“仁也者,人也”。仁的含义非常复杂,大致包含:(1)亲亲,“为仁者,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一》);(2)爱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下》);(3)德、正、直兼有的品质,“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左传·襄公七年》);(4)无私,“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八年》);(5)遵礼,“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6)守志,“杀身以成志,仁也”(《国语·晋语二》);(7)立功,“夫仁者讲功……无功而祀,非仁也”(《国语·鲁语上》);(8)利国、利民、利众,“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仁,所以保民也”(《国语·周语中》)。如果说,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我们能找到中华民族那种大爱奉献的“仁者”形象,从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和夏、商、周的历史中我们能找到以智慧和德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圣者”形象,那么从仁的这些主要含义中我们能够感受我们的祖先逐步觉醒的人类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中,以德为中心,守候生命,追求神圣、崇高、纯粹和永恒构成其核心内容。经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理论阐释,加之孟子的明确定位,再经由汉武帝把儒家学说提升为统治地位,“仁也者,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对“人是什么?”最根本的回答,它深刻塑造中华民族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价值追求,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人格和精神特质。今天,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自觉地把它与中华民族这种古老而深厚的人类自我意识联系起来,使之有效建构全体社会成员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自我人格和尊严,成为社会人格的判断标准,成为基于这种社会人格辨别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判断标准。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仁”所内含的人格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君君臣臣”原本强调礼,在君权下被弱化、替换为倡导依附性人格。但是,“杀身以成志,仁也”(《国语·晋语二》),“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论语·子罕》),“养吾之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以说,儒家学说中的人类自我意识有鲜明的人格独立诉求,正如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subjectivity一样。在中华民族工业化、市场化、法治化的文明转型阶段上,在继承“仁”的同时显然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潮流复现其人格独立的含义和价值诉求。
2.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心灵世界里的信仰结合起来,使之转换为信仰提出的绝对命令
公方彬教授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因子,崇高的精神诉求以净化灵魂走向卓越。[11]叶小文教授更明确地提出,讲“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关注重建信仰、充实精神支柱的问题,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并且反复强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的链条,用信仰唤起心灵的敬畏,通过这种敬畏产生自律和他律,即内心有道德的自我规范,外有社会的公德和法规。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信仰无法得到科学的逻辑证明,却可以通过适当的抽象确立对历史和人民的敬畏而坚守。[12]这里给我们的启发是,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升为信仰提出的绝对命令;否则,就无法把它根植到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转换为社会成员为捍卫信仰而自觉遵循的人生基本价值规范。
什么是信仰?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信仰是承载终极价值的理想化人格及其生活的理想家园。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道教的元始天尊及儒家学说倡导的圣和佛教的佛,这些词汇虽然因为不同宗教和理论学说而不同,所指称的对象却都是承载某些终极价值的理想化人格。正是这种理想化人格使不断自我超越的人不再孤独、漂泊、无助,它所承载的终极价值,例如真、善、美、自由、正义、永恒(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含义不同,重要性的高低序列也不同),使人生有了明确的方向,赋予沉重的肉身以不竭的意义和价值。理想化人格所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家园也是信仰的题中之义,例如基督教的天国,伊斯兰教的天园、道教的十方长乐世界及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和儒家学说的“大同”理想。这些词汇虽然同样因为不同宗教和理论学说而不同,但所指称的对象却都是理想化人格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家园,在那里生活着的人都是克服了现实人所具有的缺陷。正是理想化人格使它们不同于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例如桃花源、乌托邦,等等。
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解有偏差。共产主义至少有三层含义[13]:(1)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表示拒绝描述未来。马克思在1843年明确表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14]恩格斯晚年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也表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目标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5]如何理解他们似乎相互矛盾的表述?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蕴含着他们(2)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的价值原则,表现了马克思理论探索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6](3)自觉解决时代弊病的社会改造运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7]即使是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我们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正是这种偏差使之不能成为信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马克思在这里确实表达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原则,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分工固定化的批判。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个性”[19],这似乎反映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中的理想化人格,它通过社会化高度发展“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20]并且最终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状态:“社会化的个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1]。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它以人类本性为出发点、价值准则和归宿。这样,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纯粹的未来社会,而是现实地能给人的心灵以净化、方向和使命感的理想家园。
但是,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普遍追求是自由吗?或者是别的什么?在中国,一个年轻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就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抚养和教育孩子上,西方伦理学领域自由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悖论在中国不成为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妇孺皆知的名句,人去世了要盖棺定论,对于那些敢于担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给予“浩气长存”“永垂不朽”的碑文。在这些日常行为和语言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先哲追求的最高价值:“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这些都表现了永恒是中华民族心灵深处追求的最高价值,正是这种最高价值显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信仰。孔子、孟子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中从历史上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先贤中抽象出“圣”这样的理想化人格,他们知天而顺应天,得道而守道。他们所实现的“治”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养、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化人格和社会理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与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一道构成中华民族的文明密码,建构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深刻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自觉地把它与中华民族这种深厚的文化信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圣”这种理想化人格提出的人生基本价值规范,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上有信仰的生活,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并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洪流之中,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但必须看到,这种理想化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弃绝了人之作为人不可能没有的七情六欲,把理想性和终极性消解在现实性之中,“那尚有终极关怀意味的‘内圣似乎比‘上帝距离我们更远”,“人们的信仰从此便被实际地‘压扁在‘现实性一维向度之中”[22]。不仅如此,它还塑造了中华民族指向“完美化”的集体价值认知,这种集体价值认知忽视了“道德人”的有效性界限,消解了个体的独立性,也消解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家学说和佛教的自由思想弥补的儒家信仰的缺陷,那是中国传统社会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信仰体系的产物,不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信仰选项。应该看到,孔子、孟子不仅强调人格独立,还强调自由。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这里的“心”是否被时代的社会形势左右而迷失其本真性,这就要求具有“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这种自我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也要有“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行为。
三、结束语
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是应对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渗透,一方面是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义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这两方面都不允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停留在挂在嘴边的言说层面,而应该使它进入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转换为人们内心的价值规范和人生准则,塑造相应的精神品质和人格特征。而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就不能单纯强调教育灌输,不能停留在情感心理层面,更不能以利益驱动,而应该深入具体历史境遇中人们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呼唤,从人不死的价值追求中寻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在学界探讨的启发下,使之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灵认知、内化和生成路径,以期与学界一道探讨和研究。当然,由此也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理论支撑问题,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需要完成的基础理论任务。
参考文献
[1] 李梅敬.“外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与传承路径[J].唯实,2010(1):30.
[2] 李卫宁,粟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构建群众心理认同基础[J].理论前沿,2009(3):31.
[3] 胡凯,夏继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建设思路探析[J].伦理学研究,2009(4):56.
[4] 董德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问题与出路[J].哲学动态,2011(3):25.
[5] 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3.
[6] 侯铁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再理解[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4):92.
[7][17][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40,37.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5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3.
[10] 赵敦华.“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描述定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4(7):1-11,.
[11] 公方彬.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J].文汇报,2006-12-4(1).
[12] 叶小文.略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学习时报,2011-11-7(6).
[13] 邓晓臻.共产主义的文本阐释[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7(1):9.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28-62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22] 荆学民.从高山庙堂到田野乡间:信仰何以根植于民众之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