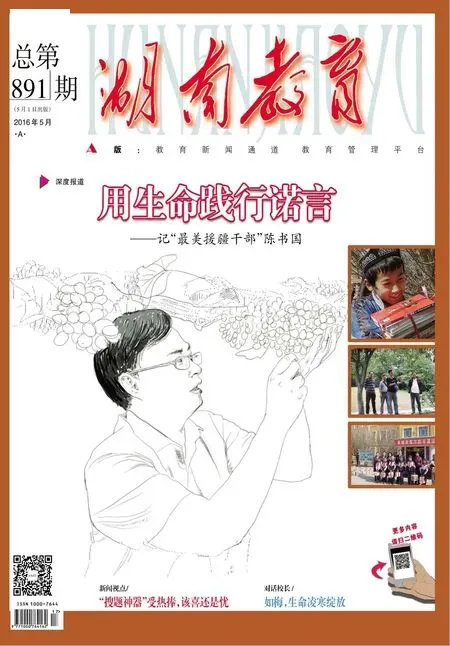石磨里的童年
李海涛
石磨里的童年
李海涛

“端豆腐 ,端豆腐 ,正宗的石磨豆腐……”回到乡下,每逢清早听到这样的叫卖声,我总会快步走出家门买上一两块。不是“端”么,怎成“买”了?其实这“端”“买”之间,折射的正是过去与现时的一种不同价值观。过去买东西,人们总会背个布袋子,提个菜篮子,担副皮箩筐,这些工具都是可以往复使用的,体现的是贫穷岁月里的节俭环保。因为豆腐总是上门来叫卖的,所以从厨房里拿出一只大菜碗盛上一碗底清水,装着豆腐轻脚慢步端回家,既不损坏豆腐,又能保洁保鲜。而现在则不同了,人们买东西,那叫一个轻装简便,都是撂脚摆手去的,尽管国家为了低耗环保,所有商店超市的塑料袋均实行收费了,但三两毛钱谁都不在乎,低耗环保没落实,商家倒又多收了三二文。
提个塑料袋把豆腐买回家,母亲总会一本正经地端详好一会,然后煞有介事评论一番——“这是旺伢子家的豆腐吧,他的豆腐根本不是石磨的,你看这表面还有豆渣”“今天的豆腐是憨矮子的,他的豆腐是石磨的,用的还是高山岭上架来的泉水,这豆腐不厚,但鲜嫩好吃”……实践出真知,母亲虽然七十多岁了,但对豆腐的鉴定结果十有八九是不出错的。但鉴定归鉴定,结果我不会运用,不管是旺伢子憨矮子还是六麻子家的豆腐,只要听到叫卖声,我还是会习惯性地端它一两块,说不清为什么。
那时,我们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台石磨。石磨摆放在公用的正厅里,上面能动的叫磨盘,下面固定的叫磨底。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打一两箱豆腐。打豆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先不说工序繁多,也不讲下石膏水有怎样的技术含量,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小孩子家家不参与也搞不清楚的。而单单在磨豆腐这一道工序上,就让我记忆犹深。
“推磨移磨,累了歇缓”,这推磨真是个力气活,我们那屋的石磨大概有七八十斤重,一个人是推不了多久的,况且像我父亲那样的男劳力是不会来干这活的,他们的气力要用在刀刃上,去干扛树、修河圳那样赚工分的营生。所以磨豆腐的差事总是由妇孺老小来完成。我家磨豆腐,母亲是个主力军,她总是半弯着腰,用左手推着磨盘把,右手拿着瓜勺,不停地从木桶里舀出浸泡好的豆片放进磨口里。我们兄弟几个则按划拳顺序轮番上阵,用一只手握着磨盘把,叠加在母亲的左手上面。刚上阵时,我们都使劲用力,但推不了四五分钟,便开始耍懒了,身子跟着磨盘转,手却不怎么用力,直到母亲推起来特别费力了,我们才在下一位的嗔怪中换班。但母亲总不会怪我们,她会表扬我们肯做事,说肯做事的人将来有出息;会表扬我们讲团结,说家和才能万事兴;同时还会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争取跳出农门,要懂得感恩珍惜上天赐予我们的粮食。有时家里来客了,母亲要做饭,同厅的婶婶伯母们又会自觉跑来帮忙,就如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当起了磨豆腐的主角。
现实的生活比虚拟的社区更加阳光,真实的交流比数字的流动更温暖人心。石磨磨去了青黄不接的困顿,磨来了亲人邻里相互温暖帮衬的纯真。“咯吱咯吱”,那是时代劳动的音符;“白乳流动”,那是人心纯净的写真;“你推我磨”,那是和融家国的影射;“逆时针向前”,那是再苦再难也要永葆进取的最强音。
石磨储存了我的童年记忆,让我体味了节日的喜庆和劳动的喜悲。石磨转呀转,转走了艰辛的岁月和母亲的青丝,转来了生活的富足和我辈的中年不惑。我常想,那时候长大的我们为什么会在起床之后做好一件事——叠被子,洗脚之后做好一件事——洗袜子,吃饭时做好一件事——不挑三拣四、吃饱就好?劳动创造真善美,亲情滋养精气神,石磨赋予的是我童年的记忆和亘古不变的真理。
(作者单位:平江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