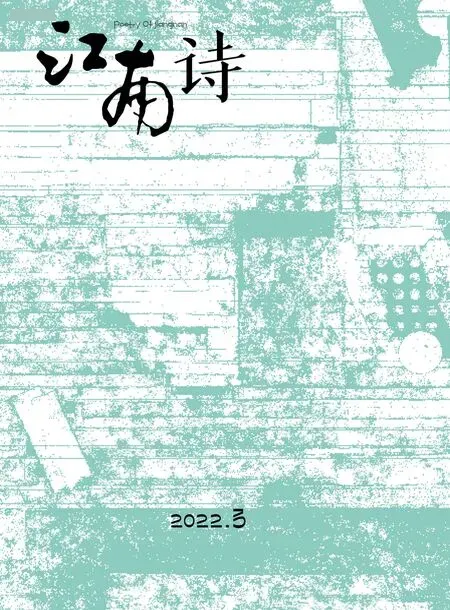创作与评论“双枪并举”的诗人
——著名诗人、评论家晓雪访谈
◎项兆斌 Xiang Zhaobin / 晓雪 Xiao Xue
创作与评论“双枪并举”的诗人
——著名诗人、评论家晓雪访谈
◎项兆斌 Xiang Zhaobin / 晓雪 Xiao Xue
述你此前的诗风系“明丽隽永的风格,即用浅显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意蕴。或曰平淡中出奇,自然中现彩”;《茶花之歌》不仅承传了明丽隽永的诗风,而且更凝练、更深刻、更传神,创新之花尤为鲜艳,(其)最大的贡献,是晓雪《两行诗100首》对新诗的诗体创新。”我读过你的绝大多数诗作,虽然你的人物诗、爱情诗、哲理诗、四海风情诗等极富特色、不乏佳作,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你跨度长达60年的描写家乡大理的一大批抒发乡情的诗作、民间传说题材的叙事诗和创新诗体的“两行诗”,我认为这些诗作见证了你在诗国艰难跋涉且不断自我超越、自我突破的全过程,从而奠定了你作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领头人之一和新诗民族化领头人之一的历史地位。请谈谈你对自己诗歌创作艺术成就的认知。
晓 雪:“领头人”绝不敢当。可能因为我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缘故,许多前辈,同辈和比我年轻的诗友都给过我许多热情帮助和多方鼓励,对我的作品和为人有不少溢美之词。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只能把朋友们的真诚鼓励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写诗几十年,我也写过“赶任务”的急就章,写过简单“配合政治任务”的空泛无力的平庸之作。但在诗歌的民族化方面,我是一直在努力的。我力求把诗写得单纯、朴素、简洁、明丽,寓丰富于单纯之中,寄深沉于平淡之外,用自然简朴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意境和深刻的哲理。不故弄玄虚,不故作深奥。我力求把诗写得既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又有个人的独特风格,努力坚持民族性与当代性相统一。

晓雪
项兆斌:我读过你大学时代写就的成名作《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其飞扬的文采和在诗歌评论敢攀高峰的勇气,奠定了你以后作为评论家的基石。但却有人散布流言,说你五六年靠大学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一举成名,稍后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却又写文章批判艾青。2011年12月19日上午,我与诗人颜石在京出席柯岩遗体告别仪式后,颜石有意约我到艾青家拜访艾青夫人高瑛。到艾青家后,颜石说我是来自云南的“黑马作家”、诗评家,高瑛便谈起你:“你们云南的诗人晓雪,艾青生前和我都喜欢和信任他。”你能简略谈谈你和艾青的关系吗?
晓 雪:艾青是我最崇敬并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我的诗和诗论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写《生活的牧歌》时没有见过他,1957年6月他到昆明接聂鲁达,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交。反右斗争中我确实写了批判他的文章《艾青的昨天和今天》(见《诗刊》1957年12月),是应《诗刊》之约写的。1978年9月6日在北京再见到他时曾提起此事,表示道歉,他笑着说:“你那篇文章在当时是最温和的,要约我写,我也会写。以后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但我1999年为《诗刊》300期纪念写的文章《感激、怀念与反思》中(见2000年6月中国文联出版社《百年烟雨图》)还是写了这么一段:
“记得《诗刊》编辑部的航空挂号约稿信写得热情、诚恳而紧迫,说:‘我们虽然已发了田间、沙鸥等同志的文章,但《生活的牧歌》对艾青评价那么高,影响很大,读者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意思和态度,我们热切地希望你尽快写一篇批判文章,从理论上说清楚艾青为什么犯严重错误,文章字数不限,可以长一些。希望你一定写,我们期待着!’我是11月初收到约稿信的。当时反右斗争已进入高潮,艾青正在北京受批判,我在云南也因写了‘全面吹捧艾青’的《生活的牧歌》而作检讨。《诗刊》当时迫于形势向我约稿是情理之中,我自己则完全可以不写。因为我内心里根本想不通,也无法‘说清楚艾青为什么犯严重错误。’但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22岁的青年,《诗刊》如此信任,编辑部图章旁边还有臧克家主编的签名,也就在很矛盾和痛苦的情况下写了《艾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长文。虽然文章一开头就说:‘艾青在民主革命时期写过不少优秀的诗篇,而且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希望诗人争取有美好的明天’。(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明天’部份约3,000字发表时被删去)但那毕竟是一篇不该写的批判文章,我至今一想起来就感到悔愧、难过和对不起艾青同志。”
1979年以后,我作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持云南省文联、作协工作的负责人,又是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评委之一(艾青是评委会主任),赴京开会的机会很多,除在会上见面外,每次都要到艾青家里去看望他。1995年11 月29日上午,我与周明、王昆等一起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坐在轮椅里对我说:“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是我的话,你理解得很准确,很深。过去没有人注意到,你注意到了。你的书名《生活的牧歌》取得很好,抓住了我的最主要的特点,我一辈子就是唱生活的牧歌。”我说:“艾老过誉了,《生活的牧歌》只是我学生时代学习艾老诗歌的粗浅体会。”可能以为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又伸出大姆指强调说:“一个人一辈子抓准一个问题、看准一个人很不容易,你看准了我,你抓准了问题,我就是唱生活的牧歌,我没有歌颂别的什么东西,我歌颂生活。”因为12月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要召开“晓雪作品研讨会”,他不能亲临出席,便特别写了一封信交给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同志,表示祝贺。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和你结的是诗缘。
“五十年代,你的大学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对我的作品理解很深。我曾为有你这样的读者和研究者而高兴!
“五七年六月,我陪同聂鲁达夫妇去云南,第一次见到你,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反右中,你因我蒙受批判。在21年艰难岁月里,每想起受我株连的朋友和读者,心里就隐隐作痛。当我们再次见面,你已步入中年,我是老人了。我们成了忘年交。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我始终关注着你。只要见到你的文章,必定一读。你的作品和你的为人,被熟悉你的人们所称颂。”(1996年4月号《诗刊》)

韩作荣为晓雪颁奖
新时期我又写了《继续研究艾青》、《诗人的青春——喜读〈艾青近作〉》、《给人民以最好的东西——再谈艾青近作》、《艾青的诗美学》、《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艾青在桂林》、《艾青研究的新开拓——序周宏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等文章。艾青去世后,我写了《哭艾青》等悼念他的三篇散文。为纪念艾青逝世十周年,我写了《我感到你并没有离去》的诗,称他“属于祖国每一个美丽的黎明”,“属于未来每一个开花的季节”。为纪念艾青百年诞辰,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发表。
项兆斌:你是诗人,也是评论家。一般说来,写诗要形象思维,搞评论则主要靠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两种思维是不一样、有矛盾的。请你谈谈你是怎么做到两者兼顾、“双枪并举”的?
晓 雪:早在六十年前,我就在1956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短论:《作家们,关心和参加文艺批评吧!》盼望和提倡作家、艺术家们兼搞评论。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俄国大批评家杜布罗留波夫的文章,称赞“诗与科学的结合”。我认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有区别,但并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处理得好,可以相辅相成。不存在只有逻辑思维而没有形象思维的人,也不存在只有逻辑思维而没有形象思维的人。问题在于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想象更丰富、思考更深刻。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大作家、大诗人,都是既能搞创作、又可以搞理论批评的,他们脑子里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从学生时代就努力賞试既搞创作又搞评论。
退休之前,我一直从事业余写作。由于工作繁忙,有限的业余时间还要坚持读书,可以用来伏案写作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我写诗多半利用出差、开会、下乡劳动锻练、参加各种笔会或出国访问的机会,平常上班的业余时间主要用来读书、搞评论。在动笔之前要读许多作品,因此花的时间和精力比写诗多得多。有人称我为诗歌评论家,也有人称我为文艺评论家。我主要从事诗歌评论,除继续研究艾青外,对藏克家,李广田、光未然、郭小川、贺敬之、田间、李瑛、徐志摩、曾卓、白桦、邵燕祥、纪鹏、晏明,雁翼、吉狄马加、叶延滨、等130多位老中青、海内外、各民族的诗人分别写过专题评论和序跋,还写过许多综合性的诗歌评论文章,如《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中国新诗发展的广阔道路》、《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国诗歌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还写过对李白、杜甫、陆游、苏轼、李清照的诗歌评论和研究毛泽东、陈毅诗词的文章。但同时,我的评论还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民间口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研究和戏剧、电影、电视、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等艺术门类。光是美术方面,我就为十七位画家的作品、画册、画展和各种综合性的画展写过20多篇评论、前言和戏跋。因此,称我为文艺评论家,似乎也说得过去。
当然,结合诗歌创作,我对诗歌理论,诗美学的思考要更多、更新也更深入一些。所以我除了写大量诗评之外、也写了《诗的美学》、《艾青的诗美学》、《徐志摩的诗论》等一批诗歌理论文章,写了由429段语录组成的《诗美断想》。《诗美断想》受到评论家张炯和诗人吉狄马加的特别喜爱和关注。张炯称那400多段“断想”是“字字珠玑 、流光溢彩。”(2008年4月7日《文艺报》)吉狄马加说:“这是诗人的悟性和理论家的哲学思考的最为美妙的交融。他抽象地揭示了诗在社会中的作用,诗的美学价值以及许多瞬间的关于诗的最奇特的感受。读这本书时,我想到了艾青天才的《诗论》,想到了罗马尼亚民族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那些关于诗的最精辟论述。我想,可以这样说,《诗美断想》是晓雪作为生命个体对整体生命意义的探索,是对这个世界的存在与虚无的思考。这样的断想、只可能出自诗人的手,纯碎的理论家们是难以企及的。……我坚信这是一块真金,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总有一天会说:哎,这真是一块金子,为什么以前我没有发现呢。”(2011年8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第134页)。

晓雪与项兆斌 2016 昆明
项兆斌:我读过不少你近年写的评论文章,尤其是批评低俗、庸俗文风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你阳光、透明、公允,无私无畏,敢爱敢恨,“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为做正直的评论家作出了表率。如你发表在2015年第1期《云南文史》的文章:《当代文艺工作的光辉指南——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某作家“老虎屁股摸不得”、“公然在文艺评论界的会上臭骂批评过自己的评论家,甚至大打出手”,还批评了“(在)低劣作品面前不敢发出自己声音”的评论家。请你进一步说明,怎样更好地开展文艺批评工作?
晓 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等等,这些问题在诗歌界也是存在的。但我认为诗歌界“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敢于说真话、讲道理、批评不良倾向的评论家太少。总书记说得好:“文艺批评要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同于批评高度。’”“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搞好“真正的批评”,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很大差距,还要不断努力。
项兆斌:中国新诗诞生了不少杰出的诗人和经典之作,百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新诗形式成败之争从未止息,时至今日否定新诗形式合法性大有人在,且来头不小。如大诗人毛泽东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季羡林《漫谈散文》)对两人的观点,你如何评价?
晓 雪:领袖和大师的话也不一定句句是真理。毛泽东主席不喜欢新诗,乃至根本不读新诗。他说过:“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新诗。”“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是因不喜欢新诗,不读新诗作出的判断,显然有失编颇,过于武断。其实,从1957年毛泽东致臧克家的信来看,他明确宣告“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对新诗还是支持的。季羡林先生同前去拜望他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也谈到“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要求新诗找到一种像古典诗歌的律诗绝句那样五言七言的固定形式,是不可能、没有必要、也不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随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产生白话新诗,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我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就是一部诗歌形式因内容需要而不断变化、发展、丰富的历史,除律、绝之外,还有四言、六言、九言,还有古体,近体、词、曲、小令等多种形式。新诗更不可能统一规范为一种固定的形式或格式。季老的话反映了他对“我们现在的诗歌”强烈不满,我想他的意思也不是要找到一种固定的单一的人人遵循的形式(模式),而是要“我们现在的诗歌”“找到”(创造出)更适合表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生活内容而又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读者喜爱的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是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项兆斌:读了你的散文诗《雪与雕梅》《无味之味》、《情思绵绵》等,感到你写的散文也写得不错。请你谈谈诗与散文的关系。
晓 雪: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散文大家往往也是著名诗人。散文和新诗是最亲密的文学姐妹。诗应当像散文那样,如行出流水般自然、流畅,应当像散文那样不矫揉造作,不涂脂抹粉,不故弄玄虚;而散文也应当像诗那样洗练、简洁、富有诗意。
散文的诗点在一个“散”字,但绝不能“散”得杂乱无章,不知所云,而应当“散”得别开生面,“散”得舒展自如,“散”得生动话泼,“散”得诗意盎然。散文不限题材,不拘长短,不管形式,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但无论哪一种散文,我认为都应当饱含诗意,耐人寻味。没有诗意的散文不是好散文。这大概就是许多散文家都爱诗、懂诗、写诗,而许多诗人往往能写出好散文的缘故吧。
写一首好诗固然不容易,但我觉得散文比诗更难写好。我不是在缺少灵感、缺乏诗情诗意的时候才想起写散文。而恰恰相反,我是在自己有了许多感受感悟,许多生动素材和充沛的激情,觉得无法把它浓缩在诗的形式中,才提起笔来试写散文的。
项兆斌:人生有涯,艺海无涯。最后请你祝愿下一个新诗百年。
晓 雪:新诗有了一百年的历史,比起近三千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来,仍只是短暂的一小段。新诗的诗体建设没有古典诗歌那么成熟完美,新诗的整体成就远不为古典诗歌那么辉煌,百年诗坛的天空当然也不如古代诗坛那么群星灿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迎着时代大潮应运而生的新诗,百年一路走来,尽管有争论,有曲折,有教训,仍然为反映时代风云、歌唱伟大祖国、倾吐人民心声作出了不容否认的贡献。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田间、郭小川、贺敬之、李瑛、余光中到北岛、舒婷、吉狄马加等等,百年来我国各民族的几代诗人都在新诗的创作和诗体的建设中取得各自不同的成就。对百年新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给予总结。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下一个百年,我国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的时代呼唤出现伟大的诗人,需要产生更多又新又美的诗歌。只要我们扎根于伟大时代的生活厚土,继承和发扬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五四新诗的优秀传统,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开拓创新,各民族的几代诗人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过去百年成绩的基础上,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诗歌,创造中国诗歌的新的辉煌。我对新诗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晓雪,原名杨文瀚,白族,1935年生于云南大理喜州。195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论艾青的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现代作家论。著有诗集《祖国的春天》、《苍山洱海》、《爱》、《晓雪爱情诗选》、《绿叶之歌》等28部和《晓雪选集》6卷。部分诗文被译成英、法、意、西班牙、缅甸、泰国等国文字和维吾尔、哈萨克、朝鲜、蒙古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1996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2003年获第五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2010年获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2012年获王中文化奖,2014年获国际诗人笔会授予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14年获纽约东西方艺术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中国艾青研究学术峰会授予的艾青研究突出贡献奖。

访问时间:2016年2月17日
访问地点:云南昆明晓雪居所
项兆斌:晓雪先生,我受《江南诗》诗刊编辑部委托对你进行采访。采访的目的有二,一个是中国是诗的国度,自1917年源于西方的新诗进入中国至今即将百年,对新诗形式如何认识?这是国人最关心的诗国大事。再就是,作为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作为国内外诗坛重大奖项获得者,你六十年来的创作生涯,无论在新诗创作或评论均卓有建树,总结你个人的创作经验,对今时正确地认识中国新诗百年的历程和开拓新诗的未来,不无意义。希望你能接受采访。
晓 雪:我愿意接受采访,谢谢《江南诗》编辑部,也谢谢你。
项兆斌:作为著名诗人的你,少年时最喜欢的却是书法和绘画。你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文中说:“(小学时)书法比赛是全校第一名。”“初中时的业余爱好,主要还不是文学,而是绘画和书法。”我欣赏过你的部分书法和绘画作品,就线条艺术而言,飘逸而不失端庄,瘦削而不失绮丽,极具个人风格。但你在世人心中却是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人们往往忽视了你的书画作品。就艺术门类而言,书画和诗歌其间跨度不小,对你由少儿时代热衷学习书画到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传奇历程,今日年轻读者知之甚少。请你据你的上述经历谈谈相关体会,对青少年励志不无益处。
晓 雪:我认为文史哲相通,诗书画相联。不论你将来做什么工作,不论是搞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一个人从小练练书法,画点画,培养一点对书画的兴趣,对于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触发灵感都是大有好处的。
项兆斌:关于你的新诗创作,艾青、臧克家、张光年、王蒙、李瑛、张志明、谢冕、张同吾、吉获马加、杨匡汉、叶橹等名家早有好评。我为你的新著《茶花之歌》所作序言《中国风的新诗——晓雪诗美探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