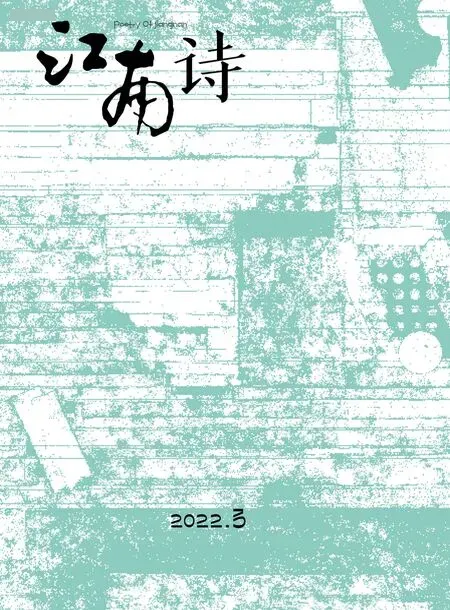探究与执迷
——叶辉读札
◎何言宏 He Yanhong
探究与执迷
——叶辉读札
◎何言宏 He Yanhong
当我将叶辉的诗作以微信的方式转发给一位朋友阅读后,这位对叶辉并不很了解的朋友说:“感觉上,叶辉应该是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我很钦佩朋友的精准,并且为其在代群的意义上来理解叶辉而感到惊讶。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叶辉的诗作,是不是带有明显的标记,体现着1960出生的诗人们所易常有的精神气息,以及他们每每独有的诗歌风格和基本主题?对此问题,我并不很清楚。在对叶辉的阅读中,我只是觉得——隐约地觉得,我在精神上,出现了一种“回退”的的感觉:一方面,我能经由叶辉的诗作从纷繁忙乱的外部世界和世俗生活“回退”到“自我”,在“自我”的一隅深自玩味,找回自我,体味着自我;另一方面,在时间的维度上,我又仿佛“回退”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重新接续起自己以往的“自我”——那被多年来的奔忙与俗务弃置和忘却于时间深渊中的“自我”——个体自我的精神事务,也得以重续。叶辉唤醒了我生命深处的那被吞没、那被严厉的时间所急速弃却的从来没有完成的自我。这是叶辉的诗作让我迷恋、让我长久玩味的很重要的原因。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这在诗歌制度、诗歌文化、诗歌精神和诗人们所热衷探讨和表达的基本主题、诗学风尚等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但是叶辉,他似乎一仍其旧地延续着1980年代的诗歌主题,远离风尚,执迷于对自我、对个体主体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探究,这样的坚持,使我生出很多敬意,也有很多相契与会心。叶辉有一首叫做《山谷中》的诗作,写的是:“山谷中,一位画家正与四周的景色搏斗/他让火舌头吞掉远处的荆棘/让智慧堆成一座房子/他画下一块石头/像大地眼中的砂粒/他哭泣流下一滴眼泪/他感到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徘徊”,这位画家,分明充满着浪漫、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然而他的宿命,他的无以摆脱的真实处境,却是在人类这一永恒的涕泣之谷流泪与徘徊。与其对照,诗中所写的另一个男人——“在他左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为家人采摘食物的男人/他从篮子里挑选蘑菇/将有毒的扔掉”——倒是一个安妥于日常生活的“常人”。叶辉书写了画家眼中的这位“常人”,写“他画下这个男人/在蘑菇中,植物的叶子/遮住他的裸体”,他似乎接受和赞赏“这个男人”对自然的亲近,他甚至径直就将“这个男人”处理成了“自然”,他把他画成了“裸体”。不同于画家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搏斗”(“一位画家正与四周的景色搏斗/他让火舌头吞掉远处的荆棘”),“这个男人”与自然之间,无疑是融合的,虽然在这样的融合中,他也保持着人的理性与自觉(“他从篮子里挑选蘑菇/将有毒的扔掉”),他其实有着非常健全的自然意识。但是在同时,画家在画下“这个男人”的同时,“他还在边上画下他的画架/说:一把天梯”。这是画家不无武断甚至是一厢情愿的主观处理,自然遭到了“这个男人”虽则温和但却明确的“指谬”——“不错,它的确像把天梯/男人说:只是它的顶端/好像已经被锯掉了”。我们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沉沦或流放于山谷之中,何曾能有得救的可能?《山谷中》的两个主题,两个人物,他们和它们之间的对照与差异产生了“戏剧”,一种小小的诗的戏剧性,这样的戏剧,又结束于不无揶揄与反讽的结尾,较为丰富也较复杂地揭示了叶辉对人、对存在和对个体自我的深刻理解。在叶辉的作品中,《山谷中》有一定的原型意义,它很突出地喻示着叶辉诗歌抒情主体的双重面相与内在冲突。
叶辉诗中的主体,在此世、在现实中、在生活里,却又不属于此,出离于此。正如他在一首题为《新闻》的诗中所说的,他是“一个平凡生活的爱好者/一个喜欢真实蜂蜜的人”,他专注、沉迷于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场景、经验与细节,特别是伦理与亲情的深厚与绵久,叶辉的诗作每多书写。但是在另一方面,叶辉诗中的主体,又很孤寂与落寞,他常在阴影中,在局外与暗处(如《月亮》:“房子的阴影中/站着一个人,猫坐在门洞深处”、《在寺院》:“庙宇,古老的阴影下/坐着一个默不作声的僧侣”),冷静、超然地观察、咀嚼、打量甚至是窥视着这个世界,在融入的同时又抽离出自身。比如在《慢跑》中,慢跑着“跟在女儿的童车后面”的“我”沉浸在温暖美好的儿女亲情中,一方面他在尾随着女儿,“要在后面/看着她,爬上了小坡”,像“幼小的树木,缠上了过冬的草绳”地呵护着她;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落得太后”、“离得太远”和女儿的最终“奔向远处”,势必使自己在最后和在本质上“独自一人/在空荡、灰青的马路上”。“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必须直面的真正命运。《慢跑》的主题,在后来的《叙事》中又一次得到了诠释——一个有着五个女儿的父亲,随着女儿们的“不断离开”,“仿佛五盏照着他的灯被移开/他暗了下来”,只能独自面对存在的黑暗。个体的“孤独”、“独自”,是叶辉诗歌着力表现的重要内容。另外像《征兆》里所写的“到了夜晚,灵魂/就变得不安/它在我们熟睡的身体里/吹着尖利的号子//要么,就在嘴巴里/狠狠地磨牙”、《态度》里所写的“湖面上一个人收他痛苦的空网”和“白发苍苍的人正温习课本”等等,都是形形色色的孤独个体的诸多情状。在而不属于,在而超离,时刻领会到个体自我的存在与“独自”,这是叶辉个体意识的重要特点。
但是叶辉对个体的探究,并不太倾向于向内挖掘,像很多现代主义诗歌那样过多地表现精神的混乱、绝望与分裂,他所更多揭示的,还是个体间的关联与“对应”。叶辉用“对应”这样的字眼来概括个体之间超越时空和超越生死的神秘关联。在一首题为《飞鸟》的诗中,叶辉这样写道:“我的生活,离不开其他人//有些人,我不知道姓名/还有些已经死去//他们都在摇曳的树叶后面看我……”;而在《关于人的常识》中,他所指出的这种“对应”与关联,甚至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他认为在我们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间,实际上都有着关联。他说:“每一个人/总有一条想与他亲近的狗/几个讨厌他的日子/和一根总想绊住他的芒刺//每个人总有另一个/想成为他的人,总有一间使他/快活的房子/以及一只盒子,做着盛放他的美梦”。他的很多诗作,都是在写关联。还是在如上所说的《关于人的常识》中,他写到“人行道上的那个广告牌前/站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儿子/他站在父亲以前站立的地方”,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人行道上站立于一处,成了死去的父亲与其儿子之间共同的关联。叶辉的诗歌,如《老式电话》、《遗传》、《信》、《角度》与《划船》等都写过血亲伦理间的深切关联。《老式电话》从一个打错的电话追忆和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划船》则从“捡起东西”这样一个日常举动联想到父亲,从而产生“划到不断到来的记忆里”的渴望;而在《角度》中,诗人像在《关于人的常识》一样,这样写了一个“人行道上”的女孩——“人行道上的一个外地女孩/她正在等人,但好像并不期盼/任何东西”,她的“胸前有一只闪光的/金色盒子、小巧的机关、里面放有一张/她祖母的照片//这张照片,以每天一张的速度/从她原本美丽的脸上/复印出来”,这个女孩,她对祖母的纪念和对祖母相貌的“复印”,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她们建立在血亲伦理和血亲情感基础上的关联。
在《面孔》、《对应》、《考试》、《活页》、《我在公园里讲述的故事》、《果树发芽、开花的季节》、《延续》、《重访小城》和《邻居》等很多作品中,叶辉书写了个体生命与血亲伦理之外的其他个体的精神关联。这些关联,经常发生在人的精神深处,典型的如《面孔》:
夜晚我看到一张脸
在窗玻璃上,在户外未完成的建筑上
被台灯照亮
仿佛废墟上出现的圣容。在我身后,书架排列在
远处的村落中。一阵黑暗里的犬吠
或者上一场暴雨在地上
留下了持久的光亮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高过群山之上
云团飞舞,急速奔涌
有如多少年来飞逝而去的灵魂
——《面孔》中的抒情主体不仅能在“窗玻璃”和“户外未完成的建筑上”看到“圣容”,更是在“一切”的背后和群山之上看到了“多少年来飞逝而去的灵魂”,正是这些“圣容”和这些往昔的“灵魂”,洞彻着黑暗,照亮了夜晚,使我们的生存能见出光。在叶辉的诗作中,时常置身于阴影或暗处的抒情主体,在经常目睹和见证灰雾或黑暗的同时,却也时常发现有光,而那些“灵魂”,那些形形色色的往昔的“灵魂”,便是时常闪烁和照亮我们生命的光源。叶辉是一位相信有灵魂的诗人,“灵魂”是叶辉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的词语。诸如“傍晚,我在公园里给人讲故事/我讲述灵魂怎样不用/双脚行走/而人的身体是他们的全部”(《我在公园里讲述的故事》)、“人失去一种爱情、就会梦到一个抽屉/失去一片灵魂/就会捡到一把钥匙”(《信》)、“一排麻雀站立在屋檐上/像一个个等待超度的灵魂”(《在寺院》)等诗句,充分体现出“灵魂”不仅是叶辉诗作所频繁出现并且为他所娴熟运用的词语,更是他最核心的关切。正是因为有灵魂,万物有灵魂,叶辉的世界才不致于局促,不致于使他的自我陷入彻底的孤独。
叶辉居江南小城,在石臼湖边自建有著名的阵雨别墅,诗风内敛、暗沉,于精俭、净洁的文字之中,自省、仰望、想象与远眺,细究与体察有灵的万物,诗的主体因此得深邃,也得因为有丰富的关联而变得开阔。在叶辉很多人都熟知的《小镇的考古学家》、《在糖果店》、《树木摇曳的姿态》、《远眺》和《陌生的小镇》等作品中,这样的表现非常突出。《小镇的考古学家》写的是一位“恋尸癖”对骸骨的迷恋,通过一具女尸的“灵魂复活”,令人惊悚地挖掘和表现了自我和人性深处极端病态的方面,精神上与潘维的《苏小小墓前》颇为相似;而《在糖果店》中,诗人则通过想象把我的世界扩展到远方——
有一回我在糖果店的柜台上
写下一行诗,但是
我不是在写糖果店
也不是写那个称枰的妇人
在陌生的地方,展开
全部生活的戏剧,告别 、相聚
一个泪水和信件的国度
我躺在想象的暖流中
不想成为我看到的每个人
如同一座小山上长着
本该长在荒凉庭院里的杂草
在糖果店,在甜蜜庸常的实际生活——实际如“那个称枰的妇人”所意味着的确凿无误的生活中,我却在“想着其他的事情”,想像着“一匹马或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展开/全部生活的戏剧”,那是一个有“告别”、有“相聚”,由“泪水”和“信件”组成的国度。在此世,在生活中,在而不属于,叶辉的《在糖果店》,又一次表现了其抒情主体的如此情状。像《在山谷中》一样,叶辉的《在糖果店》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在糖果店”的自我,另一个是出神地超离现实、想想象着远方的自我。只是《在山谷中》,叶辉将两个自我分别化身为“画家”和那个“为家人采摘食物的男人”,而《在糖果店》,这两个男人则合为一体,在精神、情感和诗风上要相对亲切。不管是温和亲切,还是玄妙与神秘,叶辉的诗作都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迷于自我,在对自我向内探询的同时,更多地以关联与想象、以万物有灵的诗心与眼光,使得他的抒情主体扎实且开阔。——也是一种方法,我们不妨就用叶辉的诗来唤醒自我,找回自我。
记 录
我想着其他的事情:一匹马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