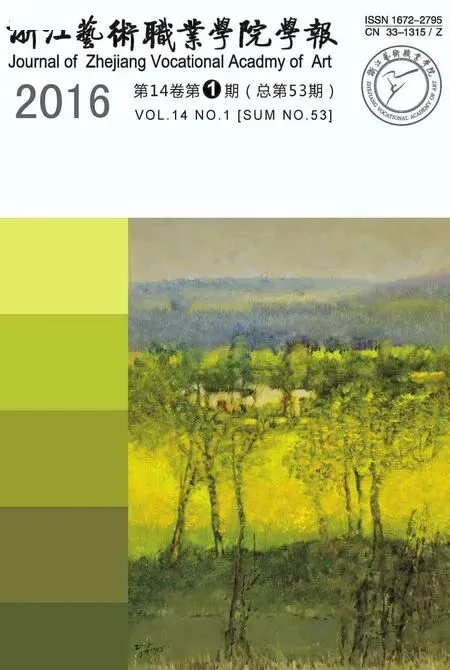论“越女红”的审美特征及其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
宋 眉
论“越女红”的审美特征及其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
宋 眉
摘要:“越女红”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既是对越地文化的呈现,也是对女性社会存在与造物实践的反映。因此,唯有从客观文化语境和主体文化实践两个维度来考察,才能对之进行全面的阐释,对其审美特征作出准确的把握,而这种特征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价值同样值得探究。
关键词:“越女红”;审美特征;地域审美文化;女性智慧
∗本文系浙江省文化厅2014-2015年度文化科研项目《基于“越文化”特色的当代浙江女红设计创新研究》成果。(立项文号:浙文产[2015]12号)
“女红”原指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丝棉纺织、刺绣、缝纫等手工艺,其物质载体为衣、帽、鞋、饰物等生活用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不仅以器物功能满足主体的实用需求,还以其丰富的审美实践凸显出对主体审美情感的满足,因此成为一种审美文化的产物。作为在特定审美生态环境中生长的文化有机体,“越女红”不仅体现了个体、群体在越地社会生态中的历史实践,体现出个体、群体生动、真实的社会存在,呈现出个体与集体的融合、个性自由与社会认同的融合,可堪社会历史与女性存在的文化缩影;从地域审美文化的角度看,“越女红”更是对越地文化的书写——从女性造物角度的独特书写。
从目前的女红研究来看,尚无对“越女红”的专门研究,或是从某一地方工艺美术类别进行具体研究,或是以两浙文化、江南文化为视角进行笼统的描述,相对忽视其与吴地女红之间的差异,不利于对“越女红”地域特色与审美特征的考察,以及对我国女红文化脉系的梳理、对其文化艺术价值的全面发掘;而目前对隶属越地的女红文化的探讨,也多局限于门类工艺美术,同样缺乏基于地域文化特色的探索,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方法上看,无论对“越女红”审美特征的剖析,还是对其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机制的探讨,都需要以其文化特征为根本,对这一审美文化的生成、演进作出全面客观的把握,才能真正促使其活化与再生。从审美文化的生成要素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客观文化语境(包括地域原初文化精神及其发展历史)与主体的文化实践两个层面。事实上,两个层面是无法分割开来的,但为了使论证更为清晰,本文暂且从这两个层面分别来具体探讨“越女红”的审美特征。
一、客观审美文化语境与“越女红”审美特征的形成
1.越文化的原创精神与文化内核
以地域文化加以划分,“越女红”主要是指生长于以宁绍平原为主体、以温丽台瓯越文化为辅助的女红文化。从越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代三国时,越文化在儒学浸润下,融入了重德操、讲信义等儒家价值观念;而在南迁士族的影响下,进一步强化其自然适性之精神,最终形成了以充满诗性的江南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样式。当然,从整体环境上看,浙江文化的总体特色也对越地文化有着深刻的渗透作用,如蕴含于“事功”观念和“耕读文化”方式中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结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融),蕴涵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之中的移民文化特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等,皆反映出其关注民生、以人为本、求真务实、轻视说教、关注细节和勇于创新等优良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作为越文化自身演进的机制,也促成了其工艺美术文化范式与发展规律的形成。
追根溯源,从越文化的源流和发展历程来看,两汉三国时期的轻悍尚武、刚烈豪侠之气塑造了劲烈的民风,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略具原始性的质朴、生猛的气质却长期存留下来,积淀于越地文化传统的演进之中”[1]。但这种“积淀”如何在越文化的演进中得以延绵,目前学界却尚无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一文化积淀正是以越文化原创精神中的本真、质朴、注重感性等文化基因为内核的,而这种内核在越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中,成为糅合二者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越文化之所以在儒学传统和江南士族文化的浸染之下并未失去自身的主体性,除了地域生产力发展等客观因素外,地域原创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它通过诗性精神与本真之美、经世致用思想与日常之美之间的糅合,为工艺美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也形成了创造者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关系,而这些在“越女红”之中得以集中体现。也正是基于此,至明清时期,在以杭嘉湖平原为主体的吴文化女红主导江南女红主流审美文化的历史情境下,“越女红”仍然能够以自身的特色呈现出别样的魅力。
2.诗性精神与本真之美
如上所述,江南士族文化被视为对越文化的一种重要补充与改造。在当代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研究中,诗性精神成为一个关键词,并总是与文人精英艺术的柔美飘逸、精细坚韧和唯美主义等审美特征相表里,与北方文化的浑厚、强健以及重质轻文等审美特征形成对照。但实质上,诗性精神的合理性更在于其与近现代中国大众渴望心灵自由、追求精神解放和个体自由的理想相契合,这也在明清以来的越文化艺术中有所体现,再加上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于是在江南诗性文化和中国社会人文思潮的浸染下,越文化也形成了相近的审美文化品质,这对浙江地域审美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逐渐凸显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审美思想,同时也更为自觉地探索和表达个体生命价值,例如明清以来的越地工艺美术,较传统更为注重情感表达,更注重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自觉探讨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适性的审美文化精神并非仅仅源自南迁士族精英文化的影响,而是与注重本真呈现的越文化原创精神相契合。对于越地工艺美术而言,它们在地域文化与诗性文化的融汇中,依然保存着自身的审美特征,并借助诗性精神为自身提供了更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更具艺术性的表达空间。
此外,由于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越地女性特殊的社会角色,使得“越女红”以平民文化为主导,民间乡野女红极为发达,因而相较于以宫廷女红和文人书斋女红为主体的“吴女红”,“越女红”虽然少了些精致与文雅之美,但更呈现出自然、生动、质朴、活泼的审美趋向,同时也少了些许文人艺术无法摆脱的形式观念桎梏与“雅”的趣味束缚。例如温州瓯绣因地方交通所限,与外界交流甚少,较少受到其他地域的同类艺术或西方艺术的影响,因此不同于苏绣等通过融入外来艺术(如中西方绘画艺术)而改变原有审美特征、更趋精致文雅,瓯绣则保持了其拙朴、天真的生活气息[2],可谓对越文化的原生态呈现。当然,越地也存在着宫廷、文人书斋女红,而它们对越地民间乡野女红是否存在影响等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总之,无论从越地文化传统还是民间女红的审美观念来看,“越女红”的地域文化属性都是十分明确的,若与“吴女红”相比较,以宫廷和文人书斋女红为主体的“吴女红”多见繁丽、骄奢、浮华、文秀,更多一些精巧和柔美;“越女红”则多见尚务、淳朴之俭质,更多一些清淑与阳刚。当然,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对其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意义。
3.经世致用与日常之美、艺术创新
如果说江南诗性文化从审美上提升了“越女红”的文化价值,那么“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浙江社会主流文化思想则是始终贯穿在其中的根本文化价值观念。与“吴女红”的重“工”尚“艺”有所差别,“越女红”的平民性与本真性特质使之鲜明体现出贴近平民生活与日常审美体验的趋向。这种趋向不仅体现在以实用功能为主、装饰性为辅上,还在“日常之美”这一审美特质上呈现出来。事实上,“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深深渗透在审美文化之中,对审美观念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促成“越女红”对“日常之美”的呈现。例如,以祈福、纳吉与伦理教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越女红”,并不似宫廷女红那样在图案纹饰的选择上有较多的规范,以及对图案纹样作过多的符号化处理,而是更凸显创造性和丰富性,更敢于从日常生活中获取题材、形象,更趋于审美情感的直接表达,在器物与图案造型上也更不拘一格,注重对实物的意象塑造与生动概括,形象夸张质朴,色彩搭配也同样大胆随性,凸显出越地民众的热情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这种直接源自本真的越地文化和质朴的民间文化的审美范式,自然也不同于文人书斋女红对道禅文化内涵与清雅蕴藉的刻意追求,后者使女红远离实用功能而成为艺术品。
在“经世致用”与“日常之美”审美观念的塑造下,“越女红”始终守持实用与审美之间的平衡,并以生活为造化之源,不断突破成规,勇于创新,创造出丰富的艺术样式。此外,“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还蕴含着灵动而开拓的浙江水文化特色,加上越商文化的发达,为“越女红”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例如宁波金银彩绣在不同用途的绣品上,使用的配色亦有差别:用于喜庆祀神的金银彩绣多使用大红、橘黄等鲜亮、喜庆、欢快的暖色调,并配以绿色、紫色等对比色形成高纯度的强烈视觉效果,与民间节庆文化和审美观念相契合;而用于观赏的金银彩绣则多采用黑色、灰色、石青、赭黄、灰绿等冷色调,显得端庄雅致,符合文人审美理念。此外,宁波金银彩绣在20世纪60、70年代还独创“仿古秀”(图1),以极富民族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内蕴的敦煌藻井形式、官服补子图案以及灰暗色系呈现出浓郁的古意,深受海外客商的追捧。[3]诚如沈寿所言“色有定也,色之用无定”[4],可见这用色的“无法之法”便在于对器物文化功能的发掘、对审美需求的重视、对客观审美规律的遵循与对艺术创造活力的展现。

图1 宁波金银彩绣
二、女性主体与“越女红”审美特征的定格
1.“越女红”之于江南审美文化的建构价值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江南元叙事”的心理结构,它以摆脱、超越现实功利的诗性审美为根本内涵,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江南情怀”,或曰“诗意江南”的诗性审美形态。[5]此外,也有学者将江南审美文化的特征定格为对诗性品格的呈现与不断纯化,诸如主客体的和谐统一、明丽的物象表现、细腻的情感表达、自由的个性抒发等艺术特点,认为这些特点体现了对“教化”、“载道”等政治伦理规范的超越以及与道禅哲学美学思想的结合。[6]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品质借由文人艺术观念的影响,的确在吴越工艺美术中得到了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元叙事”话语,并不能完整地与吴越审美文化结构对接,同时也遮蔽了地域特征以及同样作为江南文化主体的女性审美文化特征,而这些正是“越女红”对江南审美文化的构建价值所在。
事实上,对于身处政治、道德伦理束缚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女性来说,江南文化赋予她们的并非高深的哲学思想与超越的艺术精神,而是在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社会角色的陶炼中形成的精细坚韧、自然适性;而女性赋予江南审美文化的亦不是哲学与美学意义上的“性灵”或“宁静致远”,而是其独具的生存智慧、审美情感与儒道思想的融汇。“越女红”一方面展现出对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遵循,另一面也呈现出对个体自由的期盼以及女性的看护、和解、智慧、行善等深层人格与心灵境界,因而其创造的作品显现出深厚广博的文化价值,某些作品尽管也呈现出类似文人审美趋向的、柔美飘逸和浪漫、唯美主义的审美气质,但全然无刻意造作之气,在文化内涵和精神上指向的是女性独有的生态际遇与生存智慧。此外,地域审美文化也在“越女红”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如余姚绣花鞋(图2)以当地四季花卉为主要图案,其所用的红绿黄三色线(俗称“余姚三彩花线”)也极具地方特色。与此同时,“越女红”也不乏对越地民间图腾、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的符号化呈现,这些都使得对女红文化的认知需要突破“江南”或“吴越”文化格局,真正立足地域文化来加以观照。

图2 余姚绣花鞋
2.对女性社会生态的全面呈现
在越地,女红不仅是对家用的满足,还是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宁海前童的族谱中就记载着不少靠女人纺织而使一个经济贫困的家庭扭转生机的事例。如前面所述,“越女红”的创造过程主要体现为广大民间女性的日用造物活动,因此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而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越女红”的审美特点的最终面貌。一方面,它最为广泛地借助“器物”实现了百姓日用功能,并在这种实用功能之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女性主体对生活的日常经验与审美感悟,例如在题材上的多样化(除了惯用的如意、麒麟、百鸟、梅兰竹菊、福禄寿等题材外,还纳入了蝴蝶、虫鱼、瓜果乃至典故人物等更具现实生活气息的各类题材)、造型的丰富性(在整体形制与图案上对现实生活物象的生动塑造)、色彩上对自然物象的模仿(如“枣红”、“天蓝”、“蛋青”、“葱白”、“鱼肚白”)等,呈现出“越女红”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的巨大创造力。也正因为如此,“越女红”对江南审美文化的建构是极富生活特色的,也是文人艺术或书斋女红等所无法替代的。
另一面,正如宁波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要问我家中妻,只要看我身上衣”,女性的社会存在价值通过勤劳、贤惠等美德得以呈现。越地女子自幼在娘家闺房里开始学习女红,女红技艺与审美范式在母女婆媳、心手之间代代相传,精细的女红不仅在四乡八村受到传颂,更在方寸之间展现着女性的蕙质兰心。因此,女红展现的不仅是在男权社会和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约制下的中国女性伦理道德观念,或是对女性主体性格、人格特质的由外而内的形塑,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角色意识和生命情感的积极表达,是对女性审美文化的独特表征。
3.对女性智慧与生命意志的积极表达
审美文化是对审美主体文化实践规律的完整呈现,因而女性主体特有的审美定势自然是构成女红审美特点的要素之一。首先,“越女红”体现出女性与自然环境之间深沉而紧密的情感关联,表现为对客观物象自在生命的体悟,并能够将主体生命与之融合,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渴望。以装饰性的瓯绣为例(图3),创造者通过对自然花木、鸟兽标本等长期的观摩,展现出极为写实的艺术风貌。他们在对实物进行直接摹写的基础上,注重明暗空间变化、色相明度对比等,以便在增强纹样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其色彩不仅追求真实性,而且能够表达出创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之情。[7]在艺术手法上,“越女红”既注重真实刻画,也注重艺术性的夸张表现,在构图上则表现为自然与动物、人物形象的穿插、交织以及自由开放式的组合布局,以内在的“散文式”叙事呈现出女性审美文化的诗性品质,而在色彩上除了生活化以外,也注重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如实用性的瓯绣惯于用鲜艳的色彩)。这种体验方式与艺术话语呈现出深刻的女性生命观,而在表象上则与道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如前面所述,“越女红”在意识形态表达上相对自由,在内容上映射着极为丰富的生活现实,这就决定了其表意模式——在内容上更能反映生命本真,在表达方式上更为直接(当然,这种直接是相对于其他艺术形态而言的,从整体上看,女红的表意模式仍旧是含蓄、隐晦的)。例如,平民女性多以象征手法来表达自身对美满婚姻甚至理想配偶的期望,而这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与生活愿景都隐藏在绣品形象之中,如图4肚兜上表现的民间英雄人物,除了呈现儒家忠义观念之外,也在某种程度上曲折地传达了女性对男性的审美态度。

图3 温州鸥瓯绣作品

图4 肚兜
三、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下,“越女红”作为一个积淀着丰厚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有机生命体,已经借助我省文化产业和设计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借助非遗平台获得了有效的保护,但是“越女红”的真正活化仍有待深入发掘其意象符号体系和审美特征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强大的生命力,使之真正融入当代审美文化语境,而非仅仅依靠对女红表层形式符号的简单复制或是对女红生产过程的原生态保护。
1.对地域审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当下“越女红”多借助服饰设计产业与旅游、博物馆等文化产业获得传承和发展,但对于如何充分体现越地文化特色仍缺乏系统的探讨,大量的女红产品在功能上仍处于对某些品类的简单化重复,在艺术形式上仍处于对某些符号的简单挪用和拼接,缺乏文化层面的深入拓展,不利于当代女红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向文化产品的良性转化。一方面,“越女红”需要充分挖掘越地民间丰富的审美文化资源,在器物功能、造型、材质、图案纹饰等方面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在题材、主题选择上要凸显并整合越地服饰文化、民间宗教信仰以及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等民间艺术资源的优势;另一面,要深入挖掘越文化内蕴,并对这种内蕴作出富有时代精神的阐释,这不仅体现在对女红符号的提炼上,还体现在对越文化“实事实功、经世致用”主流文化思想以及“越女红”注重日常之美的特色的传承与发展上,这些都成为确定女红设计主题的文化之根,也是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拓展的保障。
自觉关注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是越文化的积极价值,也是越地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例如,越地夹缬被面中的纹饰,在建国之初便突破了传统单纯的吉祥祈福题材,自觉表现工农兵学商等主题内容,将梅花、菊花与稻穗、飞机等题材进行融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8]而这种现象在“越女红”中也应存在,只是目前尚待考证。与此同时,基于“实事实功、经世致用”文化思想的影响,越地工艺美术都能在功能、造型、色彩、材质、工艺上不断探索实践,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不断开创符合当代大众物质生活需求与审美需求的新样式,这同样是“越女红”需要承继和发展的文脉。此外,“越女红”注重日常之美的特色在当代大众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也具有广阔的传承与发展空间。简言之,从传统工艺美术到文化产品的合理转变依赖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地域审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绝不仅仅是对某种文化符号的简单挪用或拼接,而是涉及到手工制作与机器生产、设计观念与传统文化、自由创作与市场销售等多元相关要素之间的融合,有待于设计师、手工艺人、相关领域学者、经营者们乃至地方政府的共同探索。
2.对女性文化与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从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多是从设计学或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女红这一传统工艺美术在当下的艺术创新与产业化策略,相较于这种注重实效的研究模式来说,从社会学、人类文化研究等角度来对之进行宏观观照和微观调研的探究尚不多见,而从女性这一创作和使用主体的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事实上,这种研究对女红而言极为重要。长期以来,在中国以男性为中心、以封建道德伦理制度为女性文化思想核心的语境下,女性及其创造之物的重要价值往往被遮蔽或误读;而在现当代社会的单一性、标准化的整体发展模式下,各个重要社会文化(包括设计艺术、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男性中心影响、话语霸权仍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使得无论从揭示女性文化之本来面目、或是建构各种领域中的女性话语来说,对女性文化的关注都是必要而迫切的,而诸如女红这类生动的女性造物实践更是珍贵的社会文本。
对于女红的手工细作,研究者们多关注其对当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作用以及对物质消费中的精神缺失的弥合作用,事实上其中蕴含的对身体的关注,本身就形成了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化身心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反抗(也是对男性中心、理性思维的反抗),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融汇;女红的审美体验模式与意象符号建构方式,同样深刻而鲜明地标识着女性智慧——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细腻的情感、强烈的感性色彩、对自然的关注、对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细微之处的敏锐感知等,而这种女性文化及智慧在当代人类文明以及审美文化语境下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生命力。在当代工业技术以程序、规范和标准来消解个体的智慧与情感时,这种文化与智慧也正契合了手工技艺所蕴含的人的生理性、社会性价值以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手工艺之文脉,因此更为鲜明地揭示出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文化语境下,手工艺表面上开始与具体的生活疏离,甚至成为一种自我表达或娱乐消费的途径,但实质上实践着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更为自由、本真的书写,也更有利于女性审美意识的发掘,倘若女红文化能够以此为契机,与创意文化、时尚文化、休闲文化等进行更好的融合,便能够成为建构我省地域文化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陈伯海.越地文化三问[G]/ /费君清.中国传统文化与越地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62.
[2]许衍军等.瓯绣工艺特色及其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J].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2):4.
[3]陆丽君.宁波金银彩绣的特色与传承[J].纺织学报,2010(1):102-107.
[4]沈寿.雪宦绣谱图说[M].张謇整理,王逸君译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27.
[5]刘士林.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J].江苏大学学报,2005(1):2-3.
[6]黄健.“两浙”文化的诗性品格及现代价值[J].文化艺术研究,2008(7):38.
[7]周瑾.温州瓯绣及民间装饰语言的应用[J].美术大观,2014(7):67.
[8]郑巨欣.浙江传统印染手工艺调研[J].文艺研究,2002 (1):115.
(责任编辑:黄向苗)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Female Needle Craft in Yue Culture”and Its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ONG Mei
Abstract:As a special cultural carrier,“female needle craft in Yue culture”is not only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Yue culture,but also the reflection of female social existance and creation practice. Therefore,onl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namely the objective cultural context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main body to study it,can we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and make an accurate grasp of i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What's more,the valu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is worth exploring.
Key words:“female needle craft in Yue culture”;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regional aesthetic culture;female wisdom
中图分类号:J523. 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宋眉(1978— ),女,湖北沙市人,浙江科技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杭州310023)
——以传统文化与拼布艺术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