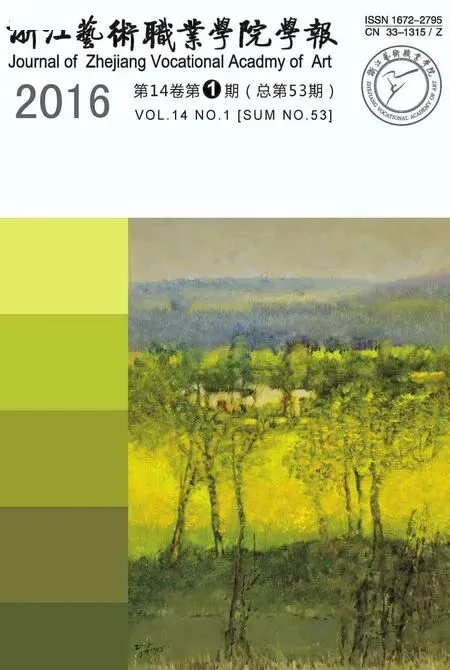舞蹈岩画:人与神的身体对话
沈学英
舞蹈岩画:人与神的身体对话
沈学英
摘要:舞蹈岩画是一种特殊的“原始语言”,是中国北方古代社会萨满文化的产物。有鉴于此,以萨满教信仰作为解释参照,并运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来对舞蹈岩画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将有助于回答舞蹈岩画的作者、舞蹈岩画的人体动态特征以及舞蹈活动所内涵的思想观念等问题。
关键词:萨满教;舞蹈;舞蹈岩画
“关于萨满教的解释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至今,在对于萨满教的理解上仍旧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几种截然对立的看法。”①本文是以时间性视角来认识萨满教的,即依据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零碎信息——如带有宗教意图的舞蹈岩画来对萨满教信仰和行为进行研究。目前,有关萨满教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萨满教是不是宗教;第二,萨满教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还是一种心理、生理疾病现象;第三,萨满教信仰是世界性还是地区性的文化现象;第四,萨满教信仰属于个人技术还是文化系统。参见孟慧英:《论原始信仰与萨满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26页。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超自然信念是不科学、无根据的,是原始的前批判思维的产物。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把原始人与现代精神病患者做类比,认为宗教是“整个人类的普遍的神经症”。但是,如果人类本性中具有创造宗教的本能,那么“原始宗教”就既存在于原始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英国宗教学者麦奎利(John Macguarre)认为,宗教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与神的交际和感通。据此它对宗教下了这样的定义:“宗教是存在本身(神或上帝)对人的触及,以及人对这种触及的反应。”[1]著名宗教学者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教授通过古代宗教研究,提出古代社会的人具有尽可能地与神圣紧密联系的倾向,所以很容易理解他们渴望与神圣力量渗透,并希望神圣力量参与现实。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思想贯穿着这样的信念:神灵和魔鬼就像语言中的词汇一样,主要受到了各个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历史学说的直接影响。[2]因此,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从本质上讲,萨满教同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并无二致。②萨满教是否是宗教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萨满教是巫术,不是宗教。而萨满教研究者中把萨满教作为人类最古老宗教的不乏其人。如波格拉兹(V. G. Bogoraz)提出万物有灵伦是萨满教的一种哲学以及它的神学。俄国萨满教研究者希洛戈洛夫(S. M. Shirokogoroff,汉名史禄国)认为,万物有灵论为萨满教创立了环境,也为萨满教的特殊社会地位提供了基础。福尔斯特(Furst)也认为,萨满教表达了一种生活的哲学:“人类,像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依赖自然和精灵的善意,它们激励并控制环境。”参见[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6页。同时,作为“通神”的一种古老宗教形态,舞蹈与萨满祭礼相伴始终。舞蹈再现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神与人、神话与世俗世界融汇一体的文化景观。因此,本论文将中国北方舞蹈岩画①“中国岩画的分布体系为北方岩画、西南岩画和东南岩画。其中北方岩画主要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新疆的阿尔泰山岩画、天山岩画、昆仑山岩画,甘肃的黑山岩画,宁夏的贺兰山岩画等等。”王晓琨、张文静著:《阴山岩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北方岩画内容极为丰富,时间跨度久远,最古老的岩画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其后有东胡族系、匈奴时期、突厥时期的,也有党项、蒙古族岩画。置于中国北方的广阔萨满文化区域之内,以舞蹈岩画的内容与形态为依据,把中国北方古代先民的历史、环境、文化系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一、舞蹈岩画的作者
岩画指古代人类绘画或刻制于洞窟石壁或露天岩石上的图像和符号。岩画英文称Rock Art②Rock Art(岩石艺术)暗含了一种典型的价值判断,即从概念上把岩石图像从其原初的环境和精神语境中抽出,将其看作一件纯艺术品,而不是把它视为当时复杂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和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已经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汉语“岩画”一词似乎也暗含了一种它是“画”(艺术)的判断。参见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汉文译作“岩石艺术”,它是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载体。[3]岩画中的“每一个图形都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创造。”[4]舞蹈岩画为何人所作?安德瑞斯·隆美尔(Andreas Lommel)在《萨满教: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古代岩画艺术是由萨满创作,是萨满昏迷经验的幻想记录,即“内视幻觉”的产物③“内视幻觉”:一种对内心视像的模仿,例如把某种动物形象投射于某块岩石,这块未经加工过的岩石上就似是而非的浮现出某种动物的形象。西方一些考古学家,如克罗特斯(Clottes)、列维斯-威廉姆斯(Lewis-Williams)、安德瑞斯·隆美尔(Andreas Lommel),认为人类具有进入变化的意识状态或“昏迷”状态的内在天赋,并由此将萨满文化作为古代岩画文化解释的依据。。列维斯-威廉姆斯(Lewis-Williams)结合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志材料,探索了散人(San)地区的岩画和萨满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也发现,岩画的创造者经常是萨满。④列维斯-威廉姆斯认为,萨满不仅在昏迷中用颤抖的双手作画,而且也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作画。岩画表面成为了精神力量的保存物和获得力量的入口,社群成员们不仅通过把自己的手放到绘画的幻象上来分享这些幻象,而且还非常小心的复绘某些特殊幻象,以便保留或增加它们的力量。参见孟慧英:《论原始信仰与萨满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另外,岩画专家盖山林提出:“无论从制作人面像岩画这一行为本身考虑,还是人面像的性质及其制作目的看,都是为了敬祭神灵娱神仙。因此,从事这方面的事情,乃是巫师之职司,可谓非巫莫属。”[5]这就是说,萨满磨刻岩画,将其作为通灵的符咒是萨满主要职司之一。“萨满这个名词好像离中国历史文明距离很远似的,其实它在全世界是相当普遍的。中国古代的萨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们还不清楚,但至少在仰韶时代我们已有巫师的具体迹象了”[6]。甘肃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彩陶盆上有“鱼形装饰”的人头花纹(图一,1),“是一种所谓X光式的图像,这种图像自旧石器时代便在旧世界出现,后来一直伸展到新大陆。用这种方式所画的人和动物常表现出他们的骨骼甚至内脏,好像是用X光照出来似的,是一种典型的与萨满巫师有关的艺术传统。”⑤关于X光式萨满艺术,参见Joseph Campbell,The Way of the Animal Powers(London:Summerfield Press,1983),132页。这种所谓近似于“X光透视”风格的巫师岩画,无疑再现了一种萨满信仰,即人能从他身体的某些致命部分带回它的生命。于此类似,内蒙古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图一,2)、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巫师岩画(图一,3)、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巫师岩画⑥乌兰察布岩画发现于1972年,主要分布在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草原上,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及其与乌拉特中旗交界处,以表现畜牧的图像为主。岩刻的制作,采用平面敲凿的方法,犹如剪影画。根据目前的研究,创作年代的上线可推算到新石器时代,下限到近代蒙古人,上下经历了数千年。参见陈兆复:《古代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图一,4)等都发现了这种奇特的人物形象:人物以全身正面形象面对着观众,有的头上有饰物,双臂悉曲举向上(或向下),五指分开,两腿作最大限度叉开,脚尖朝外,五个脚趾分开。这些巫师岩画开启了中国北方古代萨满拜祭神灵的源头闸门,又能帮助我们据以推测或想象当年萨满的活动情况。
这类萨满巫师岩画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岩画中的人物有意娇柔作态,故作玄虚,以显示其有超人的本领,似有通天地、鬼神的非凡能力。她所具有的法力,似可将神的旨意传达于人,又能将人的要求上达于神,是具有沟通神人、天地关系的特殊人物。”[5]于是,著名宗教学者米尔恰·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①米尔恰·埃里亚德是美籍罗马尼亚裔人,1907年3月9日生于布加勒斯特。1961年创办国际性杂志《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萨满研究领域的代表著作《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技术》(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于1953年、1957年和1960年分别被译为意大利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1964年英文版出版。提出,萨满教是一种基于人类原始本能的意识变化状态,即入迷②“入迷”技术通常被作为宗教的起源或者作为萨满教的本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从超人视角研究萨满的精神实践和神秘的“入迷”技术。一些精神寻求者也希望通过复制萨满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潜力。1962年美国加州埃萨林治疗法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in California)建立,这是最早的人类自我实现或人类潜能运动中心。萨满教与戏剧疗法、瑜伽和其他亚洲精神技术被列为体验课程。该研究所的资助人马斯洛(Maslow),把萨满的意识变化状态(alterd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的探索当做超人心理学的主要课题。(ecstasy),而形成的宗教现象。这为解释舞蹈岩画提供了重要参照。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幅岩画(图一,5),左上方是一舞者,双手高举,系尾饰,右下方有一匹马。此岩画中,马是狩猎对象,并为变形显示,既可以视作一种萨满“幻想”的记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狩猎成功的愿望表达。舞者系尾饰,也是一种保证狩猎成功不可缺少的祭礼仪式。这说明巫师想在系尾饰的形式中通过“交感巫术”的媒介给狩猎活动带来成功。而这种原始信仰一旦成为仪式,萨满就把这种信仰凝固化,使之成为世代相继的惯例并记录于岩画之上。沿着这个思路推测,阴山岩画③1927年底,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脚下发现了岩刻。阴山岩画敲凿在露天的石壁、山崖或磐石上。岩画的题材广泛而庞杂,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形态、科学技术、审美观念和世界观。阴山地区岩画最集中的地方是乌拉特中旗西南一带,其次是磴口县西北的阿贵庙一带。参见陈兆复:《古代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图二,6)中右上方的两个舞者线条简练、形象传神,既可以理解为萨满在召唤猎物并向神灵虔诚地祈求;也可以理解为“萨满想通过这种岩画把狩猎动物置于巫术的影响下,从而使狩猎者易于去控制、处理和捕获它们。”[7]615再如另外一幅阴山“召唤猎物”的舞蹈仪式图(图一,7),三个人当中站在人腿上作舞的,显然是一个女人,她在群舞中的独特地位,显示了她在这一仪式中的主导地位,可以推断是萨满形象。
诚然,舞蹈岩画中的图像自身不呈现意义,我们需要一个认识它们的参照和解释系统。但是,对舞蹈岩画的解释并非易事。由于舞蹈岩画的材料十分有限,而舞蹈又是人类的肢体语言,籍人的感官而生效,两者难以跨越。因此,辅以古籍文献的互相印证就非常必要了。古籍文献所载的巫者活动,可分为“事鬼神”、医疗及救灾活动三个方面[8]。首先,巫者能“事鬼神”。如《国语·楚语下》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然则巫觋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可见巫是司神之官,是智圣聪明之人,具有用歌舞通神降神之本领。《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④“巫风”指巫以歌舞事神。参见《四部精要·子部》,《墨子》卷八《非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页。《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经》中亦云:“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糈用五种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具),合巫祝二人舞,婴一璧。”这些文献都体现了歌舞事神为巫覡之风俗。其次,“巫(萨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治病。从这里有人就把它和巫医等而视之。”[7]342因为,在科技未兴的远古时期,伤病是人类最常面对的痛苦和威胁之一,致病原因也常被理解为鬼神作祟。作为有着驱神役鬼之异能的人物,巫覡自然就成为人们虔心求助的对象,于是而有巫覡行医之事,而有“巫医”并连之称谓。⑤《周易》、甲骨卜辞中有巫治疗疾病的明确记录。参见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第三,巫者的救灾活动体现在祈雨巫仪之中。如《诗经·小雅》记载云:“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⑥《十三经注疏》,《毛诗·小雅》,卷十四之一(甫田)。民族学家利文斯在他的《在南非的传道和调查研究》中引述了一个生活在南非的巴奎勒人(Bakuena)萨满的造雨过程:“在一个造雨仪式中,造雨者(萨满)将一种有茎状植物的根研成粉末,然后把一部分粉末用水调和灌入一只羊的口中,五分钟后羊痉挛而死,其余粉末加以燃烧产生出巨大烟雾直升空中,他们相信这些烟雾能带来一天或两天的雨。”
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巫风略如上述。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巫,史称“胡巫”,其性质和职司与中原的巫无殊,他们也是作为沟通“天人之际”的使者而出现在世间的。[9]胡巫入于中原,列于国典,自西汉开始。《史记·封禅书》记述,汉初“天下已定”,“长安置诸祠祝官、女巫”,确定了新的祠祀制度。在列述分别任用“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之后,又说道:“九天巫,祠九天”。对于所谓“九天巫”,《三辅故事》云:“胡巫事九天于神明台”。因此,“胡巫”即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10]胡巫会利用药物治病,①据《汉书·苏武传》记述,苏武在匈奴引刀自杀后,卫律驰往胡巫之处,胡巫凿一地穴,下置温火,将苏武置于其上,用脚踩其后背,使之出血。于是,已断了气的苏武,半日后便苏醒了过来。由此可知,胡巫会急救和治疗刀伤的外科手术。而且在社会上非常活跃,如《汉书·西域传》记载:“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②胡巫所用之“诅”或祝诅就是巫所用的咒语,这种法术在匈奴很流行。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另外,突厥③据《旧唐书·张仁愿传》记载:“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回纥④回纥人也信巫师,凡举国军事大事,皆请巫师参与其政。、乌桓⑤晋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中曾略述了北方古族乌桓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的事。、契丹⑥魏征主编的《隋书》民族异域传中,记载了契丹人举行风葬的仪式。等民族都对巫师迷信甚深。
我国古籍文献中屡屡提及的巫、胡巫都是后世所称的萨满。萨满在氏族群体中的特殊地位,是由他“通神”的才能得以确立的。于是,萨满代表了技术的垄断专属和神灵赋予的超然权威性。也就是说,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国王”通常也是祭司,人们都熟悉这种神职与王权的结合。在那些年代里,笼罩在国王身上的神性绝非是空洞的言词,而是一种发自坚定信仰的表达。⑦“国王”:泛指早期社会的一切行政首领。参见[英]J. G.弗雷泽著,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3页。
二、舞蹈岩画的人体动态特征
一面岩画虽然形式简单稚朴,却无不负载着一种沉重丰厚的文化。列维-布留尔也曾反复强调,生活在现今的我们企图在理解原始思维方式时,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⑧“原始人周围的实在本身就是神秘的,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每个存在物、每件东西,每种自然现象,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在它们身上见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都是原始人所不予注意的或者视为无关紧要的。然而在它们身上原始人却见到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页。但是,虽然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所重构和复原的文化情境与那个一去不返的真实情境不可能重合得天衣无缝乃至可以合二为一。但是,只有弄懂这些刻、画、塑的画面在使用它们的人们心目中是什么,才能谈得上它们在我们的眼中是什么。
纵观中国北方舞蹈岩画中的人体动态,可以发现其最典型、最基本的舞蹈姿势(图二,1):曲肘举手、曲肘下垂、双手平伸或扶膝;双腿叉开作蹲式;足尖朝外;系尾饰。其中,举手蹲腿的动作贯穿舞蹈的始终而具有典型的意义。另外,对称造型的使用非常广泛,人物上举的双手和屈蹲的两腿,都呈直角状,形成“”⑨,似乎蕴藏着一种深沉内在的力度美。如果以今天的舞蹈创作标准来衡量,舞蹈岩画中的舞蹈形态确是极其简单的。但是,这种带有程式化特点的“祈祷人像”寓意着某种崇拜的信仰,有着深刻的内涵。也就是说,舞蹈岩画所体现出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巫覡法术维持的人类生活的第一阶段中,巫、舞不分,甚至还有准科学活动,它们统一在一个仪式中。”⑩弗雷泽认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经历了由巫术、宗教到科学的三个发展阶段。人类最初是用巫术去控制神秘的自然界,然而,这只是纯粹的幻象;于是人类又求助神的恩惠,巫术思想逐渐为宗教思想所替代;当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付自然时,科学思想又取代了宗教思想。参见[英]詹·乔·弗雷泽著:《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8页。在此前提之下,舞蹈无疑属于象征、信仰和神圣事物的范围,即通过特定形式的身体语言,使人类需求和神灵的意志得以顺利的交流,这种观念无疑带有鲜明的交感色彩,体现着一种古老的信仰形态。
首先,舞蹈岩画中的人体动态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先民用舞“事无形”的价值取向。“巫”、“無”与“舞”三个字的溯源可帮助我们理解岩画中的舞蹈形态。“巫”,《说文解字·巫部》:“巫,祝也。女能事舞形,以舞降神者也①“段玉裁注以为‘祝'乃‘覡'之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十六引《说文》作‘能事无形,以舞将神也',无‘女'与‘者'字。”参见沈立岩:《巫歌·祝由·筮辞:早期语言观念的一个考察》,《励耕学刊》(文学卷),2010年(2)。。象人两褎舞形。與工同意。”②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也就是说,“巫”是以“舞”事“無形”(神灵)者;而“舞”,是“巫”籍以事“無形”的手段。在这里,“巫”是主体,“無”是对象,而“舞”是与对象的手段,巫、無、舞,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因而,这三个字,不仅发一个音,原本也是一个形,即“象人两褎舞形”——[11]。这个两腿微向旁叉开、双手略向侧抬起且手中持物的人体动态,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舞蹈岩画中系尾饰的舞者形象。“象人两褎舞形”中,“褎”是古“袖”字,但这个“袖”并不是如今人所理解的衣服上的遮蔽膀臂的部分及其延伸,而是如其字所示的以“手”(爪)抓“穗”(禾)之象。[12]其实,“两袖舞”的动态表现,实质上是对手舞道具的强调。只是与中原耕稼文化所孕育的“双手执穗而舞”不同,中国北方岩画中的舞者是“操尾而舞”。如图二,2,此岩画中,由四个舞者连尾而舞,他们手挽着手,同时又都用另一侧手挽着他们长长的尾巴。这些尾饰有粗细、长短之分,一般系于两腿间,由臀部垂直朝下,但也有的在臀后。[5]更加有趣的是,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类型古墓葬出土的彩陶盆(图二,3),内壁绘有五人连臂踏歌的图案,皆系尾饰,周壁有三组,共十五个舞者。其形象与见于阴山岩画的集体舞者十分相似。③另据考古发现,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彩陶上的舞者,甘肃马家窑文化半山型彩陶上的人物纹样,青海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舞者形象,也都有尾饰。可见,见于阴山舞蹈岩画中的尾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古代系尾的风习,远远不只阴山及其以北以南地区,它在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就曾在世界各地各个氏族、部落广泛流行过。如果与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狩猎、游牧的生活世界为背景的话,其仪式目的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群体在当前或未来的狩猎中安全或狩猎成功。
其二,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关于宇宙的结构模式颇具特色。“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也就是萨满式世界观的特征。”[6]宇宙三界自成系统,又彼此相通。其中,“山”是一个通天地的工具。埃里亚德(M. Eliade)对此有个术语,叫做“地柱”(axis mundi),就是说这个柱子能从地下通到天上,萨满通过这个柱子,可以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如图二,4④此岩画乌兰察布推喇嘛庙之北稍偏东月15公里的哈达图,面积高0. 66、宽0. 21米。岩画左下方是一女舞者,圆球似的头,没有表现颈部,两只乳房又圆又大,两腿上翘,系尾饰,足尖朝上。这个女舞者的右边,有颠倒对称的两对人,可能表示性交。,此岩画中的舞者,形象古拙,是用石器磨制而成的。这里的舞蹈岩画连同其它方面内容的岩画,悉刻于草原上一座孤立的黑石山名叫哈达图的地方,从南面山脚下直至山顶,其前面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河,河的北面山南面有一块平地,是当年举行山川祭的圣地。为了让山川之神永远能看到人们对其祭典,遂把媚神、娱神舞蹈刻于石壁。所以,通常情况下舞蹈岩画一般被视作圣地,是宗教活动的中心⑤新疆境内发现的151处岩画点,多是沿着阿尔泰山系、天山山系和昆仑山系的山间或山前牧场分布,而且大都处于山势险峻的沟、谷、川内,或在茫茫戈壁的边缘。参见蒋学熙:《新疆岩画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3)、(4)。。舞蹈岩画和特定环境所共同构成的气氛,体现了一种大空间观念,既满足了先民们自身在情感上和形式上的需求,也更好地体现了岩画本身实用上的功能。⑥许多洞穴揭示出,有岩画或塑雕作品存在的地方几乎都是人的足迹难以接近的地方,目的不是让人参观,而是拒绝参观。例如孔特·贝贡在《图·特·奥德伯特洞穴的粘土塑像》一文中指出,要到达图·特·奥德伯特洞穴其道路十分艰难曲折,先要通过一条已经塌陷了的小河,再要借助于梯子爬进一条走廊,最后才能到达当年舞蹈者留下足迹的地方和看见那对用粘土做成的野牛泥塑。其他的洞穴也有相似的情况。参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其三,虔诚、专注的心态是祭祀活动所强调的重要规范之一。正如弗雷泽所说:
交感巫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严整有序和前后一致。巫师从不怀疑同样的起因总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也不怀疑在完成正常的巫术仪式并伴之以适当的法术之后必将获得预想的效果……他只有严格遵从其巫术的规则或他所相信的那些‘自然规律’,才得以显示其神通。[13]
从阴山舞蹈岩画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祈祷的习惯。如图二,5,磴口县格尔敖包沟沟边一座山上,有一幅拜日图,一个人形,双臂上举过头,双手合十,头上有一圆圈,应是此人所敬拜的太阳。这种祈祷动作所包含的神圣和虔诚可谓跃然于画面之上,不难想象,现实中以图像为操作对象的祈祷行为又是暗含了多少可敬畏的情感因素。再如图二,6,是一个头戴头饰的舞者形象,舞者前后各有一类人头形,当是神灵的图像,是舞者崇拜的神灵。虽然从表面上看,神灵的图像似乎并不代表某种具体的对象,而实际上却同某种象征含义相联系,有着魔法的意义。岩画的作者可能是想藉此得到控制某种可怕的力量或神秘的现象,来增加个人和集团的财富。
综上所述,舞蹈岩画是中国北方古代萨满教文化的产物。舞蹈岩画的人体动态特征一般取决于萨满的“入迷”状态、凿刻的环境、对神灵虔诚和专注的心态等诸多因素。从这个观点来看,舞蹈确是一种独特的“原始语言”,它是以沟通神人的萨满为使者,保持人神之间精神联系(媚神)的主要形式。亦即是说,舞蹈与神灵结合为一体,神灵是内容,舞蹈是形式,神灵借助舞蹈而存在,舞蹈因神灵而获得意义[14]。
三、舞蹈岩画的结构分析
罗兰·巴特将符号看做是一个由“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构成的表意系统,“因为一切意指都包含一个‘表达面'(E)和一个‘内容面' (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ERC'。”这样一个意指系统(ERC)可以包括进另一个意指系统中,也即是一个意指系统全体成为另一个意指的表达面。①“表达面”和“内容面”这两个概念是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发展而来的:“表达面”相当“能指”,“内容面”相当于“所指”。罗兰·巴特进一步提出,“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并非是任意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基于此,罗兰·巴特将“能指”称为“表达面”(E),将“所指”称为“内容面”(C),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行为和过程称为“意指关系”(R)。参见[法]罗兰·巴特著,李幼蒸等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9页。这两个意指系统就会有二级关系。如果按照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舞蹈岩画就是一个包含着双层意指结构的符号体系。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萨满教仪式的核心元素,舞蹈岩画中的每一个姿势和动作无一不是与“神”的形象直接相关。在这里,以舞蹈形态对神灵的意指构成了舞蹈岩画整体结构体系的表层结构。而“舞蹈呈现之神”这一表意结构又可以进入一层新的意指关系,即舞蹈岩画表意结构的深层结构。由此可以推论出,舞蹈岩画的结构是以舞蹈形态及其内容表达神的“增值”行为,以神的“增值”行为表达中国北方古代先民以“增值”为核心的生存方式的二级表意系统。(表一)

表一 舞蹈岩画结构示意图
如图所示,舞蹈岩画表现了神的“增值”行为,而神的“增值”行为又是先民“增值生产方式”的象征和表达。亦即是说,舞蹈岩画结构的本质是他们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方式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清晰的体察舞蹈岩画中的两种面向——它所具有的神圣的宗教品格和世俗的功利倾向,即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对应和适应。在原始世界里,人类的生产主要包括生活资料(例如食物)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②“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缔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并且两者互相关联、互相同一。
首先,“狩猎巫术”是舞蹈岩画所具有的实用功利价值之一,也是为了获取食物和保证狩猎成功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原始人看来,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种巫术的情境(magical context)之中,这种关系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交感巫术①其实,中国北方古代舞蹈岩画可以作为交感巫术的应用事例来解释。虽然弗雷泽对巫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但是我们认为,在萨满教的世界中,神化了的动植物,是北方先民对生物世界认识的曲折反映。尽管这种认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也远非科学意义上的生物学。但归根结底,人类观察动植物,为的是熟悉其性能,认识其对人类的利弊,并据此趋利避害。有关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参见[英]J. G.弗雷泽著,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金枝》(上册),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sympathetic magic)。据此,中国北方舞蹈岩画就为“逐水草而居”、依靠狩猎来争取生存的中国北方古代先民所具有的“狩猎巫术”提供了旁证②中国北方舞蹈岩画中最主要的动物形象一般是牛、羊、马等大型草食动物而较少出现危险动物、鸟类动物和食肉动物,这也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一个重要旁证。。如图三,1,磴口县格和尚德沟畔那幅舞蹈岩画,两个执弓搭箭的骑者,看来要外出行猎或出征,马前有两个人站着,双臂上举,作祈祷状。这可能是萨满为了狩猎丰收,而在祈求神灵的保佑。也可能是,狩猎成功后,在向神灵答谢。于此类似,如图三,2,是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巴音宝力格一幅祈祷图画,右上方有两个人形双臂平伸,至肘部折而朝上,两腿叉开,似作祈祷仪式,左下方有一北山羊,双角后伸,身躯肥硕,四腿直立。从感应巫术方面来说,这是一幅自足图像③以构成生殖要素的自足与否可将岩画分为两类,分别称之为“自足型图像”和“非自足型图像”。自足型图像中包含了至少一个阳性和阴性元素,是可以自行生殖的;非自足图像是由单一性别构成的,其自身不能生殖。参见牛克诚:《生殖巫术与生殖崇拜——阴山岩画解读》,《文艺研究》,1991年(3)。,画面上的人与动物在通过动物模仿来传递一种生殖“力”;这幅图像中的“祈祷者”正是现实中祈祷动作的一个形象记录。再如图三,3,所示,狩猎动物和一些神灵形象难解难分地混杂在一起,这些狩猎神的符号既是狩猎动物的主宰,又是狩猎动物的保护者,它们既容许猎人们获得一定的猎物,同时又严禁他们滥捕滥杀。其中,狩猎神虽然以神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狩猎文化中人以神的名义构想出来的一种调节生态平衡的手段。[7]573
其次,饮食与生殖在远古文化中往往是结伴而行的。如阴山岩画中的仿生育舞者(图三,4),双臂平伸,双膝蜷曲高高地突出了臀部,尤其是下肢显然是模仿青蛙的后肢。以求通过巫术的相似律④弗雷泽将巫术的思想原则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称之为“相似律”,后者称作为“接触律”或“触染律”。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率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参见[英]J. G.弗雷泽著,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金枝》(上册),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the law of similarity)而使蛙的多产顺延到人的身上。再如内蒙古乌兰察布舞蹈岩画中的“双人舞图”(图三,5),男女两性的身体细节和外貌特征被大大省略了,但是,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则被突出出来,男性的性器是“写实”的,女性的乳房和性器则以“抽象的”小圆点表示出来。这幅岩画唯有能够体现生殖“力”蕴藏的地方以重笔进行了勾勒,很惹人注目,而身体其他的部位细节却完全被忽略了。与其说这是一种图像简化的需要,毋宁说是岩画制作者对生殖“力”之所在的强调和重视。另外在中国北方岩画的生殖图像中,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交媾、人畜交媾、男女交媾以及裸露生殖器官的画面,这些画面以十分显著的地位表现着动物增殖和人自身增值的思想。因此,人类自身的繁殖是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5]而北方岩画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生动形象的反映了这一丰产巫术的观念。
综上所述,宗教从发生起就联系到人类的存在和人类的需求。我们要在萨满教的需要中发现它存在的理由,它的活力、它的存在方式与文化能力。意味深长的是,众多萨满教神灵,是通过祭礼中的舞蹈——“通神”的具体形态,再现于圣坛的。舞蹈无疑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这里却归功于神的传授。由此,舞蹈成为了人神交流的必要工具,是神灵在场的现实表达,再现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神与人、神话与世俗世界融汇一体的文化景观。亦即是说,“它是氏族、部落的精神文化代表——萨满召请神灵以战胜邪魔、病灾的直接的通神之地,是关系到整个民族、部落当前的行止、休咎、祸福,以及将来绵延、兴盛的神圣祭坛。”[16]

图二 舞蹈岩画形态图

图三 “丰产巫术”舞蹈岩画图
参考文献:
[1]W. E.佩顿.阐释神圣:多视角的宗教研究[M].许泽民,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57-58.
[2]埃里克·J夏普著.比较宗教学史[M].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31.
[3]盖山林.内蒙古岩画考察纪实[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阿纳帝.世界岩画——原始的语言[M].陈兆复,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2-7.
[5]盖山林.贺兰山巫师岩画初探[J].宁夏社会科学,1992 (3).
[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5.
[7]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8]赵容俊.文献资料中的“巫”的考察[J].中国历史文物,2005(1).
[9]盖山林.巫·胡巫·阴山岩画作者[J].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
[10]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J].民族研究,1997(5).
[11]庞朴.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26.
[12]于平.舞蹈形态学[M].北京:北京舞蹈学院出版社,1998:17.
[13]J. G.费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6.
[14]孙慧佳.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舞蹈结构与功能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137.
[15]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91.
[16]王宏刚,荆文礼,于国华.萨满教舞蹈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李 宁)
Dance Rock:Body Dialogue between the Humanity and God
SHEN Xueying
Abstract:As a special kind of“original language”,dance rock is a product of Shaman culture of ancient Chinese northern society. For this reason,it will help to know the creators of dance rock,human dynamic features of dance rock and ideology embraced in dance activities by taking Shamanism belief as the reference,and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emiotic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dance rock.
Key words:Shamanism;dance;dance rock
中图分类号:J709. 2 K879. 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1-03
作者简介:沈学英(1979—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舞蹈教学与文化研究。(天津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