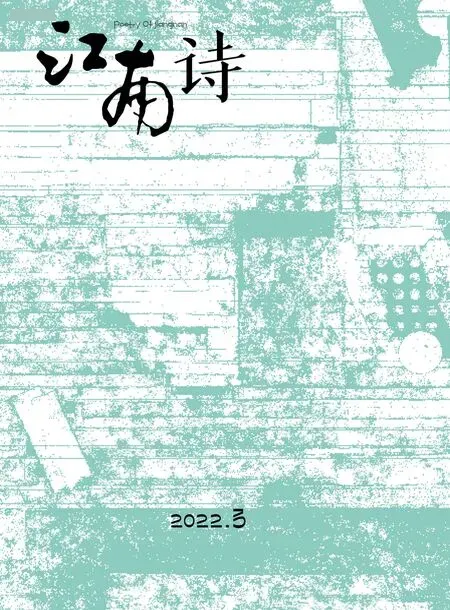在跨界之中散怀抱
◎汗漫 Han Man / 冷焰 Leng Yan
在跨界之中散怀抱
◎汗漫 Han Man / 冷焰 Leng Yan
一支笔,一根自救的浮木
在异乡、在纸上,复原故乡
冷 焰 :我们先谈谈地域的跨界吧。我记得,我们认识是1985年春,在邓州,我们组织了一个《星岛》诗社,当时你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时你经常来我家玩,第一蹭饭,呵呵,第二谈诗,惠特曼、桑戈尔等等。后来,我去郑州一家报社,你去了南阳一所高校。再后来,2000年吧,你去了上海,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谈谈地理上的这一跨越,从中原故乡到南方上海,从小城市到大都市,对你写作和生活的影响。
汗 漫:我们彼此见证对方的青春,哈哈。1984年,大学毕业在邓州工作,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这座城市里,我的写作和职业生涯开始起步,形态、表情都很有诗人气质哈哈,长头发,寡言,在县委大院是一个另类的人,不合时宜,很迷茫。1989年到南阳一家高校,认识了妻子,生子,诗歌写作初有收获,在九十年代诗坛有了动静,2000年参加了诗刊社的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算是一个标志。到上海,是2000年秋,当时妻子在上海读硕士研究生。我经过面试、笔试和考察,也来到目前所在的这家中央企业工作,从办公室文秘做起,到目前的管理岗位,一路走来,似乎从一个“诗歌的人”变成了一个“散文的人”——显著标志是,头发剪短了,烟戒了。
移居上海,标志我进入了中年,生理、心理都发生了变化。比如,渐渐适应南方人热爱的米饭和糖,渐渐听懂鸟叫一样的沪语和苏州评弹,渐渐在南方地理、人文两个层面的游历中完整了对古老中国的认知。但我也渐渐认识到自己的孤单——回到河南,河南已经把我当成上海人;在上海,上海把我当成一个外地人,或者叫做“新上海人”——这是上海发明的一个称呼,北京、西安好像都没有发明一个“新北京人”“新西安人”的说法。这是上海的狡黠,对那些闯进这座城市的异乡人,既接纳又微微保持一点距离、一丝优越感。但在上海,我也享受到一种小城市里所没有的自由度和人际关系上的疏离、宽松,这有利于写作。我慢慢喜欢上这座城市,并因此对河南、对南阳怀有一种背叛感和愧意。
这些年的写作缓解了孤寂,并获得精神同类的回应。通过写作,澄清个人生活中浑浊的部分,使内心得以安定。苏东坡说得好:“吾心安处是故乡。”
冷 焰 :你这些年的写作,不论散文还是诗歌,尽管题材已经转换为你当下的个人生活,侧重于南方经验的传达,但我仍然能够看到你的中原背景。或许拉开与故乡的距离,反而更有助于辨认自我?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有利于生成出表达的复杂性和冲击力?
汗 漫:是的。我觉得,在剧变中的当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只能暗藏于个人的身体和记忆。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是“故乡”,与童年、少年时代的风物、情感,已经完全脱节、悖离。你回到故乡,人们“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们都成了客人。所以,一个人最后的乡土,就是自己的骨头和血肉。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与故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是有益的,像看一幅油画,太近了只能看见色彩颗粒。在异乡,一个人才能完整地拥有故乡,在纸上复原、重构一个故乡。所以,移居或旅行,就是跨来跨去,对一个人内心的丰富与整合都有意义——这可能也是我为自己背离故乡所寻找的托词。惭愧。
三十多年的写作史,我已经远离了最初“成名成家”的浮躁欲望、“进入文学史”的野心、雄心,而感恩于写作所带给我的福祉:我能够用自己的笔作为一座还乡的栈桥,而不至于无所归依。
我喜欢两个关于诗歌的定义:米沃什说,诗是见证;希内说,诗是纠正。可以说,写作就是见证生活、纠正内心。我们这些能够写作的人,与一般人相比是幸福的——写作在帮助我们辨认自我、重构生活。语言给予我的已经够多了,而我回报语言的却那么少。很惭愧。
散文是写作者的个人史,是散怀抱
冷 焰 :我注意到你移居上海后,散文的写作量大了,而诗歌也还在持续地写,这两种文体之间跨来跨去的“动力学原理”是什么?你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确定为“诗人”还是“散文家”?
汗 漫:我用诗歌语言的标准对待自己的散文写作,力求精准、独到,所以写得不快、不多。这些年来,散文写作的量稍稍多于诗歌,可能因为散文是一种自传性的文体、中年文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生活的延展,很多个人经验无法在诗歌中保存下来——诗歌是一种减法性、蒸馏性的写作,会过滤掉许多芜杂的情节、细节;而散文需要这些情节、细节中的芜杂,以便还原生活的本相。布罗茨基在谈到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时也说:一旦遇到三个人以上相处的问题,诗歌就不方便处理,只好借助于散文(大意如此)。
我喜欢布罗茨基。他把散文当成一首长篇叙事诗来写,所以他的散文依旧充满了诗歌的准确性、自由度和感染力。《文明的孩子》、《小于一》、《理智与悲伤》,他这三部散文集,从九十年代开始到2015年之间陆续翻译为汉语并出版,成为我的散文写作标高。要谢谢布罗茨基,也要谢谢他的翻译者黄灿然、刘文飞。正是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叶芝、博尔赫斯等等诗人身份的散文家——还有本雅明和罗兰·巴特,他们本质上也是诗人——持续以汉语的面孔来到我们面前,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文体有了“革命的资源和动力”——这是异域诗人对汉语的贡献,也是中国诗人纷纷在散文中“揭竿而起”的背景和后盾。
可以说,这些年来,好散文大都出自诗人手中,比如周涛、邹静之、于坚、沈苇、陈东东、黑陶、雷平阳、庞培等等。他们也在越界、跨界,姿势很漂亮,动静很大。但他们本质上依旧是诗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祛除种种的遮蔽,建立全新的表达。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实验,能够为恢复汉语的活力做出一点贡献,不论诗歌还是散文。至于我是诗人还是散文家,或者叫做“诗人散文家”,我并不在意呵呵。
冷 焰 :你刚才提到了作家本雅明和罗兰·巴特,这也是我所喜欢的两个思想者。在你关于上海的散文,例如在《人民文学》发表、两度获得年度“人民文学奖”的《一枚钉子在宁夏路上奔跑》、《妇科病区,或一种艺术》和《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等作品中,我也看到了本雅明们的诗性和思辨力,为我认识你的生活、认识上海,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谈谈你的散文观以及上海对于你散文的意义。
汗 漫:散文就是写作者的个人史。怎么样写作不是问题,怎么样生活是一个问题——这像一个散文观吗?哈哈。的确,散文与其他文体相比,更加真实地反照出写作者的处境和心境,无法虚构或假设。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可供作者隐藏自我的树林太小——这是俄罗斯诗人吉皮乌斯一段话的大意。
我所在的这家科研机构,含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研发中心和上市公司,已有近六十年历史,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中央工业研究院,解放后一直隶属于国家部委直接管理,有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五十年代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历史积淀深,恩怨是非多——我办公室所在的、英国人建设的一座近百年历史的保护建筑的地下室内,文革期间,第一任院长在这里含冤自尽。在这家已经转制为中央企业的单位里工作,个人命运与周围的人、事、物、情,都必然发生各种摩擦、纠葛。你所提到的那三篇散文,之所以影响比较大,都是因为真实地呈现了我的个人情感、上海生活——我没有把自己藏在一片树林里。
冷 焰 :我能够感受到你在这些散文表达中袒露自我、审视内心的勇气,感受到你生活中的阴影和疼痛。上海,居不易。在一个单位中得以生存而又坚守内心的原则,更不易。我能理解,你是在用写作为生活消毒、免疫。
汗 漫:谢谢你的理解。我喜欢蔡文姬的父亲、东汉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在《书论》中说的一句话:“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散怀抱”,三个字,真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重负和隐疾,需要我们以各种形式来散怀抱,喝酒,唱歌,旅行,等等。写作也是散怀抱。散文更要散,散怀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正是蔡邕,在书法中首创了“飞白”手法——飞动的白,如天风吹海,让大海散怀抱。
但写作不是个人日记。所有从“我”开始的写作,都应该拥有抵达“我们”的能力,从具象凌空而起抵达抽象,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有表达价值,有克服时间、空间而得以流传的可能性。凡杰出的个人经验表达,都必然能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气象云图。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这样,本雅明的《柏林童年》是这样,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也是这样。
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写作、修改中的散文文本。我中年以后的生活、命运与上海有关,散文写作也必然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但我的上海,与土生土长于这座城市里的本土作家的上海,肯定不同。所以我的写作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它必须诚实、从心、独到,而非陈陈相因、无病呻吟、言不及义。
一首诗岂能放弃抒情的责任和能力
冷 焰 :你的职业生涯和文字生涯之间、上海与内心世界之间,有一种紧张但不脱节的关系,双向彼此滋养和输氧,这也需要一种能力。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诗人圣琼·佩斯,美国一家保险公司经理、诗人史蒂文斯,都是在职业之外业余写作。对你而言,业余写作,可能有利于制止一种游离于现实生活的悬浮状态出现,保持与现实的摩擦关系,对写作的及物性、张力都是有益的吧?
汗 漫:你说的对,业余写作是一种有诚意的写作。写作与下棋、打牌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下棋、打牌也是一种精神劳动,是与内心同在的一种方式。我没有写作的优越感。在单位里就是一个经营管理人员,写公文、开会、说闲话、出差。用本名养活笔名,反过来,笔名也在暗暗盯着本名,使自己不至于在现实中变形得丑陋不堪,持守一个人的基本道义立场。单位里知道我笔名的人不多。个别知道我在写作的同事问我笔名含义,我说就是狼狈、尴尬、羞愧的意思,大汗淋漓、汗流满面嘛,大家就一同哈哈大笑。
“汗漫”这个笔名,你知道,还是我在邓州工作时期取的,来自清朝李渔的《凉州》一诗的启发:“似此才称汗漫游,今人忽到古凉州。笛中几句关山曲,四季吹来总是秋。”“汗漫”,开阔、浩大、自由之意——我觉得,这就应该是诗歌的境界,散怀抱。写作,就是汗漫游。我以“汗漫”笔名,也以“汗漫”为人生观。
冷 焰 :我注意到2000年以后、也就是你移居上海以后,诗歌也有很大变化,从最初的意象繁复的抒情性写作,到现在的意象与细节、书面语与口语、形而下的现实体验与形而上的沉思——一种综合性或者说整合性的写作,似乎开始一种转型。这与你进入中年、进入上海以及不断深入的散文写作,也就是说,与你的种种跨界,有关吗?
汗 漫:可能与散文写作实验有关,叙述性、戏剧性、口语化的因素,开始逐步进入我的诗歌。我希望自己拥有综合性、整合性的写作能力。
你知道,在九十年代中国诗坛,我被戴上两顶帽子:一是乡土诗人,二是意象诗人。这与我一个时期内以乡土为背景的诗歌作品比较多、意象创造比较用力用心有关系。这两顶帽子,是评论者为概括的方便而制作的。我不想戴,因为一个诗人的大脑应该具有抗寒能力,不需要借助任何帽子来取暖或标志自己哈哈。只要有“诗人”这一个称谓就足够了。现在,诗坛上的各种帽子满天飞,多余,而且可疑。我提醒自己:必须开阔、切肤入心、诚实独到地写作,跨越题材、手法的藩篱和舆论的喧哗。
冷 焰 :这些年,诗歌界的种种主义之争渐渐消失,诗人们回到文本、潜心写作,是件好事。你则始终处于各种是非、纷争、圈子之外,沉静写作,作品保持了一种抒情品质和人文情怀,很难得。
汗 漫:九十年代,各种探索、流派、命名,众声喧哗,开门立户。但不论怎样写,零度抒情、客观性写作也好,口语、叙述性写作也好,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也好,都必须有一个“我”在场——有“我”在,岂能与“情感”无关?连法庭上的控辩与陈词都有“愤怒”、“仇恨”在场,一首诗岂能放弃抒情的责任与能力?但我反对并警惕于一切虚伪、泛滥、夸饰、陈俗的情感表达。
《诗经》所决定的抒情传统,源远流长,贯通于汉语诗人的血液和呼吸,不管承认与否、察觉与否。诗歌的先锋意识就是求变求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诗歌的抒情本质,没有变。
等待准确的词出现在某个位置上
冷 焰 :你最近迷上了街拍?看你总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晃荡,照片的角度挺别致,让我想起一批诗人摄影家,比如王寅、于坚等等。记得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说:拿起照相机,我就像雷达张开了器官。
汗 漫:拿起手机我也有雷达开始工作的感觉。我是2015年春开始迷上了手机拍摄,手机像素不高,但许多瞬间捕获的画面,让我惊喜——就像神来之笔啊。现在,周末无事,我会沿着上海一些街道边走边拍。在拍照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桑塔格、本雅明、巴特、波德里亚关于摄影的种种观点的理解。的确,摄影就是一种自画像,被拍摄的对象、画面,无不暴露出拍摄者的心境和处境——也像散文写作,藏不住自我。
街拍,使我的观察方式有了变化。以往大而化之、熟视无睹的事物,在用手机镜头逼近的过程中,会有新发现。摄影教会我观察细节、调整视角,也教会我耐心等待。我曾经在福州路一个弄堂里站了二十分钟,直到一个抱着鲜花的姑娘掠过弄堂口,按下镜头——无限的欢喜!等待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空白的位置上,就像年轻时代约会,等待恋人出现在街头拐角的那个位置上,无限欢喜。也像写作,等待一个准确的词出现在诗歌的某个位置上,从而产生力量。也像数学作业——大学数学专业的训练,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必须找到唯一、准确的答案,但这依赖于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在因果之间建立有根据的联系——在平面几何中,只能依靠想象力而增加辅助线,才能破解一道难题。
冷 焰 :文学、数学、摄影学,万象归一。手机摄影对你的习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汗 漫:手机拍摄对我的写作有启发、有推动。不久前,我在汾阳路上晃荡了半天,拍下了一个刺青店、一棵街头的绿树、街头花园里的普希金铜像。回家,扔下手机,写出一首诗。摄影,大约也是一种写作,特别像诗歌的写作——都是通过营造画面和意味来感染阅读者。与森山大道、王寅等人的摄影相比,我是乱拍,但有自己的感受蕴含其中,也是好的。街拍,使我发现了“另一个我”的存在,很有意思。
以“简朴和陌生”为座右铭
冷 焰 :希望你的诗、散文和照片都越来越好,像你的笔名“汗漫”一样,开阔、自由、独到。最后,谈谈你的写作、出书计划,哈哈,想知道你准备怎么再跨越一步、两步。
汗 漫:惭愧,写作这么多年,只出版了三本书:诗集《片段的春天》,1993年;散文集《漫游的灯盏》,2003年;诗集《水之书》,2009年。
2003年以来写的散文,算了算,大约有60万字吧,可以出四本散文随笔集,初定名为《南方云集》、《一个人的词语实验室》、《纸盆地》、《春瓮秋瓶》。我也不着急出版,总觉得这些文字还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避免遗憾。
2014年以来诗歌写得多了,100多首了,还需要打磨,之后再出一本诗集。
冷 焰 :用里尔克的话说,“是时候了”,我们都好好地为自己的内心而生活、写作吧。期待读到你更多、更新的跨界之作——跨入新境界。
汗 漫:谢谢你陪我谈了这么多,让我有机会对自己的写作和生活进行一次回眸。跨界无止境,我们都在跨——现在,咱们都准备开始跨入晚年了。墨西哥诗人帕斯谈到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诗歌时说,“他为两种相反的至高境界服务:简朴和陌生”——简朴和陌生,似乎也可以作为晚年生活和写作的左右铭,与你共勉。
江南诗评
主持人语:
很难用“江南性”来概述叶辉的诗风,其1990年代以来的写作,量少质优,卓尔不群,构成了对“数量化生产”的反讽,同时因“远离风尚”的某种“退避”,而将自我的世界扩展到远方。他的诗,具有纯粹的、洞彻的、通灵的、凝神静气的品质和力量。何言宏说叶辉的诗“沉迷日常”又“超然观察”,写作成为“个体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探究”,这是一个敏锐而内行的发现。“我们不妨就用叶辉的诗来唤醒自我,找回自我。”这是诗评家作为显在的读者为潜在的读者说出的一句肺腑之言。(沈苇)
冷 焰 :应《江南诗》诗刊之约,很高兴与你这位老朋友做一个访谈,主题是“跨界”。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思,非常切合你:在教育背景上,你大学读的是数学专业,工作后与数学毫无关系;在地理空间上,你从故乡中原移居上海16年了;在个人身份上,你的职业是一家中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业余写作成绩也不小;在文体上,你因为诗歌写作而获得《诗刊》“新世纪(2000年—2009年)十佳青年诗人奖”,因为散文而两度获得“人民文学奖”,从而佐证了你的诗人、散文家这样一种双重身份。近来又在微信中看你迷上了街拍,呵呵,“手机摄影家”大概又成为你的新追求?所以,你是一个跨界的人、多侧面的人,我们又是多年老友,应该对“跨界”这一话题有话可谈。
汗 漫:关于跨界这一主题,我想了想,自己大学毕业这些年来,的确是一个跨来跨去的人,无论是地域、职业、写作文体,还是精神处境,一直在跨界、临界——界,就是鸿沟、障碍、冲突、疑难。可以说,与职业作家相比,或与那些距离文坛比较近的从业者相比,我是一个在俗世中沉浮的人,写作、或者说一支笔,就是一根自救的浮木。我的面目可能不那么纯粹、雅致,但在世俗生活中反抗庸俗,难度可能更大一些吧,这也许有利于在文字中表现出相应的难度和张力。
捷克小说家克里玛说:语言和生活经验不能相脱节,你很难在一种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去表达严酷的现实。他青年时代当过救护员、邮差、勘测员等职业来谋生,坚持写作,并在文字中形成一个嶙峋、冷峻的东欧观察者的形象。我感觉,这些年自己的写作如果有一些收获的话,它们恰恰生成于我与文坛保持距离、与人间烟火痛切相关的个人生活,不完美但真实、粗粝。我喜欢陶渊明“心远地自偏”这句话——选择一个“偏僻的位置”,有助于一个人的内心走得幽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