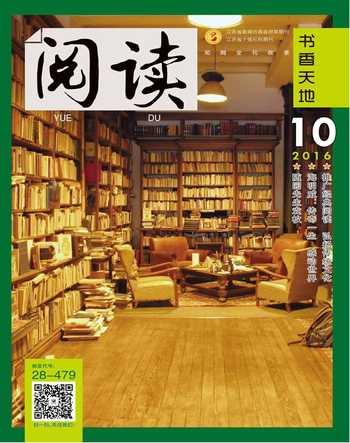追风筝的人(节选)
卡勒德·胡塞尼(1965-),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后随父亲迁往美国。著有小说《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唱》。胡塞尼“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激动展示给世人”。2006年,因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乳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说出第一个字。
我说的是“爸爸”。
他说的是“阿米尔”。我的名字。
也许我在那儿站了不到一分钟,但时至今日,那依旧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而一秒与一秒之间,似乎隔着永恒。
我们的冬天总是那样匆匆来了又走,伤疤提醒我们怀念那个最令人喜爱的季节。
“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袖,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綠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提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26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来照片上。
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在消逝的天光中。
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这个谎言。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里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他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我想要继续生活,想要遗忘,想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后一次模糊的瞥见哈桑,他瘫坐在后座,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融化的白银。
“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我会把他撕成碎片。”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
雅尔达(回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们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透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生活会继续的。
好像他在打理房间,等待某人归来。
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更伤人。
时间有时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尔布,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至成孤儿。”
“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过客。”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仰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里。
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
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她对我说的话。”
“她说:‘我很害怕。”
“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
“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
“我不想再遗忘了。”
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
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索拉博,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正在死去。现在只剩你和我了。只剩你和我。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
他的喉结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追风筝的人》,李继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