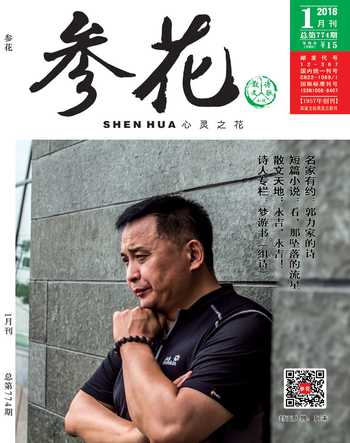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势论初探
摘要: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关键词:势 意境 审美特征
一、语言、结构与意象
势是中国美学体系中一个理论范畴,它具有内在的逻辑布局与外在的结构动态相一致的美学特征。内在的逻辑布局主要是对于意象的安排经营。因为结构布局的表现诉诸于语言文字,语言被接受者把握借助的主要是意象,尤其对于中国艺术来说。势在语言层面的经营,最终转化为意象的表现。形式是任何一门艺术存在的物质表现,与主体心理结合,符号表现为意象的运行,这是文学艺术更深层的存在方式。
语言是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语言存在的目的就是解释无穷无尽的意,但是语言无法尽意,然而又必须用语言传达意,这就使先贤后哲们陷入了一种困境。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要数先秦时期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到了庄子,认识得更深刻:“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易传》提出“言不尽意”的观点,“不尽”是不能完全表现、穷尽之意,另一方面来说还有不必要完全表达的意思。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再后来的陆机、刘解、苏轼等许多杰出的评论家都对此有自己深刻的认识。虽然探索的途径不同、方式不同,而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突破语言的遮蔽,使事物完全澄明于人的面前。禅与文学正好代表了努力的两个方向:禅苦恼于语言的遮蔽,干脆物极必反,“至言去言”“不立文字”“不落言签”;而文学则是扩大语言的张力,寻找各种中介来最大可能的尽意。
《文心雕龙·神思》云:“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辞令(语言)”能够揭示物的存在状态,使“物无隐貌”。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对作家来说,如果完全忘言得意,就毫无创作可谈。只有在创作中,调动达意之言的各种文术去表现意,虽然不能完全尽意,但必须以语言的有限,去表现物的无限、意的无限。这样对鉴赏者来说,才能超越作品语言的有限,去领悟无限,去体认自然之道。同时刘勰在《神思》篇中又说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对语言的显现功能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语言是相对的。陆机《文赋》所讲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也揭示了语言在表达上的无力状态。那么语言如何揭示虚灵超越的神、意呢?就文学创作中的心物交融的物的层面讲,无论是物色感召于心在前,还是以心取境居始,最终物要成为心中之物,客体物象变成心灵意象,构思方得以完成。而心(枢机)孕育意象时不仅离不开语言(辞令)的功用,而且最后心中意象表现为具体作品,也是由语言致用的,即所谓“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刘勰认为心物交融的过程,正是以语言作为其交融的思维形式的。这种思维形式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的东西,因为语言实质上也是作为心物交融过程的具体内容而存在的。不只创作者需要借助意象来表现无尽的意,接受者把握创作者的情感脉流和意向以及文本自身显现出来的审美内涵同样需要这一中介。势的不可见性,语论文学之势的遮蔽性,势的接受层面的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势的时空表现
中国文化追求人生的哲理深度,艺术同样追求超越于具体的形式层面的不可言说的意蕴。势的体现需要借助于形式和意象的作用,势对形式和意象的审美深度还具有开拓的作用,即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形式和意象进行突破。时间和空间在文学中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心理的存在,起关键作用的是意,人的精神意志。王夫之对势做的界定是“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势在开拓意的时空广度和宽度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使意象随着主体精神的自由发散而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进入与宇宙同在的无限时空,体现那体和生命的本质的道。
个作为宇宙的本三、结语
文学艺术的空间是一种想象化的空间,在原始时代,基于对自然科学认识的贫乏,人们对于空间的意识是极其神秘化的。由此引导出他们的艺术创作是在心象空间无限进行的,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对意象的探求。势就是对这种虚拟的空间存在的艺术效果进行最大可能开拓的一种美学思想。正是由于语言的虚化和想象性的特征,文学艺术突破了绘画、书法等视觉艺术的三维物象空间,在时间的融入中,走向心律、心象、心理、意念等主观意识发挥下的多维空间建立。时间在空间和心理的共同影响下变得变幻莫测,没有单纯的时间,时间被空间化或者被心理化,成为神秘的体验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涂光社.因动成势[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2] 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薛洋,女,长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