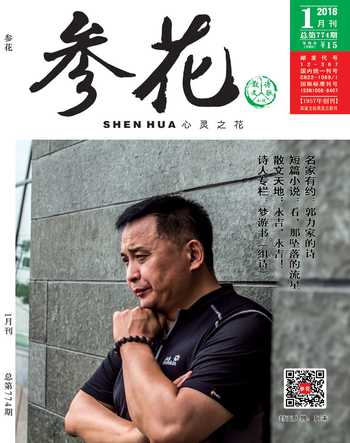华贞芝散文三章
华贞芝
母亲的心
小时候,一直觉得母亲不喜欢我。
有了弟弟后,母亲就把我扔给小姨照看。弟弟生得健康好看,嘴巴特会讨大人喜欢,我则孱弱且寡言。母亲出生守旧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弟弟无缘由地哭闹也会惹来母亲对我不满的斥责,饭桌上好吃的也随着母亲的筷子落进弟弟的碗里嘴里。更让人难过的是母亲要去走亲戚串门的时候:弟弟将那胖胖的小手递给母亲攥着,一路嬉笑一路蹒跚。随他们一起去的还有那只大芦花鸡,我喂了它好多蚂蚱才长大的。我牵着老黑静静退在大门里目送他们在朝阳晨露中渐行渐远,想象着不久后亲戚家的热闹,料峭的春风裹挟着沙子吹得我眼睛生疼。
母亲回来了,给我带回了当时颇受女孩子喜欢的纱巾,我也不止一次想象过将它扎到马尾上的粲然,但还是骄傲地忍住了,甚至装作没有正眼看一回。母亲默默把它收在了我的小抽屉里。那团粉嫩终究经不起岁月的摩挲,终于在寂寞的光阴中褪却了颜色。
初冬时节,亲戚回访了。来的是表姨,网兜里拎了四个罐头瓶,里面是泡得发胀的樱桃,在酒里翻滚着。老黑不知道是什么,直往她身上扑。“给,大丫头!”胖胖的表姨把网兜往我怀里一堆,一股热浪也随之扑面而来。她又伸胳膊又甩手的,“可累死我了!今年冬天你就不用遭罪喽!”她看我抱着吃力又接了过去,“你妈呦,不知道从哪儿淘弄的偏方,非说这东西泡酒能治冻疮。大春天就跑到我家,不准我们家崽儿(孩子)夏天吃樱桃。这不,泡好了,赶紧就送来了。喏,这是你妈让我给你织的毛袜子……”表姨一路唠叨着进了门,如同一个大火球。
有了樱桃酒和毛袜子,那年冬天我终于摆脱了冻疮的纠缠,内心是有点感激母亲的,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她之间已经横亘着一条河,与生俱来的执拗和孤傲让我不愿往她那边涉过一步。我们就这样站在两岸,彼此看着,客气着。也许她是向我这岸走过,只不过我这边太冷了,凝滞了她的脚步。
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待嫁是那个年代农村女孩儿的宿命,而读书独立却是我年少狂热的梦想。临近毕业的日子,我的内心真的一半是炽热的火焰一半是冰冷的海水。沮丧和彷徨相伴,渴望与恐惧交织。希望是那么丰腴,而现实却是那么骨感。在百般的折磨后,我觉得去和既定的命运抗争是多么不智的事。
可事实却是那么出人意料。
“丫头爱念书,就让她念去吧。”面对邻里的不解,母亲淡然回答。完全没有我想象中一个妇人在面对重大抉择时应有的纠结。要知道,这样的决定意味着她从此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少了收入,多了艰辛。
可能我天生就贪婪,没有选择中专却走进了高中。三年后,面对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已经无可选择,唯有成全。不知何时,白发已悄然爬满她的双鬓。但我分明看到了她眼神里的喜慰,也看到了忧愁——弟弟也已离高考不远。
“去吧,念下来就不用像我一样受累了。”车站上,母亲把行李递给我。触手可及的是母亲那双粗糙风干但不失温热的手。那上面有如很多小钩子刮疼了我,那种久违了的温热一下子让我眼里涌满泪水。
毕业后,我遵从了自己当初的意愿,选择了远行。作为报答,我把薪水的大部分都汇给了她,她没有客气,理所当然地接受。
在自己的天空飞翔了两年,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距离怎么可以用空间丈量?距离又哪里是亲情的对手?天地虽宽,哪里及得上母亲的怀抱更让人安然?于是,并不优雅地转身,才发现母亲早已在另一岸等了好久。
买完房子我已经是囊空如洗,装修只能搁浅。但独立逞强的我从没向亲人张嘴。母亲是在那个温暖的午后来到的,在我单位门口塞给我一包东西,小声说:“这是我帮你攒的钱,知道你不会拿(管理)钱,买房装修能应急。”说完就推我回去上班,她则急急地走了。怀抱那一袋沉甸甸的钞票,心下不禁一阵惘然,站在那里愣了好久,原来母亲一直把我给她的钱好好放在那里,不曾好好享受我的回报。
母亲自小生在姊妹众多的家里,11岁就失去了娘亲,贫穷与苦难伴随了她的童年。照顾一家人的伙食,照看比她小六岁的妹妹,迫使母亲和文化绝缘。所幸的是我和弟弟是她辛苦人生的收获,最令她引以为豪的是我们姐弟都读了书,有了自己的事业。
寂静深夜里,前尘往事纷至沓来。走过了幼稚与偏执,而今我也做了母亲,再回首那些旧日时光,就如同在一条温暖的河流里漫溯,才发现自己是这个世上最愚蠢的人,才懂得一个母亲的心原来是那么高也那么低,高得遥远,低至卑微。
河殇
走出农门是当年我勤奋读书的动力,然而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把我和城市融在一起。每当假日来临,我都要迫不及待地收拾行囊,回到家乡,夜里听着山风和门前的流水声我会睡得格外踏实。儿时,我就是这样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入睡的。
那时小河很宽,大约四五米吧。河水很深,两岸长满密密匝匝的柳毛子。在水深的地方,柳树浸入水中的部分会长出细细长长的白须子,在水中招摇,像极了老人的白胡子。那是柳树的须根。
那一丛丛的柳树是小鱼的窝。我们叫这种小鱼 “柳根子”,也有叫“白漂子”的。柳根子比其他的鱼要活泼得多,喜欢在水面游动,大概是它的鳔比较发达的缘故吧。圆滚滚的身子有小拇指粗长。
阳光出来的时候,它们就从窝里涌出来,一群一群的。我们在罐头瓶里装上一些掰碎的玉米面饼子,再用皮筋在瓶口缠上一块塑料薄膜,塑料中心掏一个小洞,刚好够一只鱼钻过去。然后,把罐头瓶放进柳毛丛里。人迅速离开,站在不远处静静候着。
那些“柳根子”看见玻璃罐里焦黄的食物就迅速围拢来,把瓶口挤得水泄不通。不一会儿,瓶子里就挤挤挨挨黑压压的一片了。一时间,黄色的玉米饼子碎粒被鱼扑通得上下翻飞。
这是起鱼的最佳时机,动作要快。于是,浪花四溅中那些精明的鱼始悟上当,待要冲出囹圄却发现为时已晚。
如果想要抓到大一点的鱼,就要到深水处,这得高高挽起裤管才行。那些穿着短裤的伙伴就把裤脚使劲往上提,直到露出两个白白的小屁股蛋为止。
太深的地方我不敢去,因为那样的地方常有水蛇和七星子出没。七星子长得极像蛇,两眼后各长有七个腮孔,看上去深不可测。犹令我害怕的是那家伙长有吸盘,会吸血还食肉。一旦被它叮上,就完了。
胆大的男孩子捕到七星子会迅速跑向岸边扔在沙滩上。那倒霉的家伙一落进滚热的沙子就万分难过地扭动身子,很快就会骨碌一身泥沙。我们就会互相招呼着奔过去,有扔石头的,有扔沙子的,还有用柳条使劲抽打的。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使劲打,打死它!”直到人累鱼死方休。
有那野蛮的男孩子还会把它的头用石头砸掉,架起一堆火来烤七星子,然后逞能般的分而食之。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对这种鱼为什么会同仇敌忾,可能就因为它长得吓人吧。
瞎嘎子就比较讨人喜欢了:大大的脑袋,胖胖的身子。在夏日的午后喜欢从石头底下跑出来晒太阳,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可能真是眼神不济。所以我们都喜欢用手去捉,伙伴们也暗暗较量谁捉鱼的功夫厉害。有时碰上幸运,还会翻到瞎嘎子下的卵。它们喜欢把卵产在石头上,足足有一小碗,和鸡蛋打在一起,放点酱蒸出来是绝好的美味。
那时候雨水真是勤,尤其是雨季。往往一夜间小河就变成了狂啸的海洋。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 的气势。常常会看到一垛柴火或者一只小猪从上游飘摇着下来,转瞬就消失了。每当这时妇女们都会变颜变色地搂紧孩子,指着被大浪卷走的小猪告诫小孩不能下水。
秋天,高粱晒米的时候,小河就瘦了下来,水里沉了很多枯叶。蛤蟆也从山上下来了——它们要到水里产卵。在河边随便翻开石头就容易看到带籽的蛤蟆、蝲蛄还有花背的泥鳅。
午后,河水比较暖和。邻家三个大点的孩子会拿上铁锹、破塑料到小河分汊的地方“憋坝”。我和弟弟就跟在他们后面帮忙。老虎儿搬石头砌坝身,我和粉霞堵塑料,大青用锹端来沙子。弟弟牵着老黑站在岸边等着捡鱼。
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河水逼近另一个河汊。但是河底好像有无数泉眼,所以每次都不能完全把河水赶跑。水越来越少,鱼也越来越慌。它们先是跑出来噼里扑通乱撞一气,然后逆流而上拼着命地去赶水,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悠哉游哉。这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的鱼篓里就沉甸甸的了。
那时候,我常想,如果哪一天小河彻底干了会是啥样?是不是就可以尽情抓鱼了?当我把这个问题拿去问老虎儿爷爷的时候,一向和蔼的老人把脸一沉:别胡说!我撅着嘴巴把要给他的蝲蛄又拎回家了。
记忆里,如此涸泽而渔仅有两三年光景。后来家家户户都纷纷把旱田改成水田。小河里隔不远就砌起一道高高的石坝,将水憋进各家的水田里。这时候,如果再憋坝捉鱼会挨骂的。
好像突然地小河就变窄了。端午插秧时节,老亲故邻却为了水红着眼锹镐相向。小河在这些恶狠狠的咒骂声中越发没了力气。
当大表哥他们从城里的农校学到了人参栽培技术后,纷纷回乡拿起了镰刀镐头,一片片大树顷刻间匍匐脚下。
从山下远望去,大片大片的人参帘子蔚为壮观。人参下山后,旧人参地种出来的玉米、土豆格外的大。几年工夫,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却成了一只掉光了毛、满身花斑癣的老狗。
人参农药中有一种叫“敌杀死”的,可以毒死河里的蝲蛄。用石灰可以呛死鱼。大青和老虎儿哥俩常常从家里偷出几袋石灰往河里一倒。灰白色的气泡淌到哪里,哪里就有死鱼。青蛙和七星子仰面朝天,翻着白肚皮,铺了一河。
人们陆陆续续拿着笊篱、鱼篓奔向小河,彼此兴奋地招呼着,像赶集一样热闹。老虎儿神气地说,这多过瘾,一盆一盆的。老虎儿爷爷却叹口气:作孽呀!
近处的山上可砍的柴少了,河边的柳树也渐渐被人们割了毛柴。雨季来临,小河裹着大石挟着泥沙冲开石坝滚过稻田,一路咆哮着像一头疯狂的野兽。
洪水过后,小河又病恹恹的了。两岸稀拉拉的柳毛子上缠着些破衣服在风中摇摆。一场河水涨过,河里又有鱼儿游动了,只是再也没有以往那么厚实了。蝲蛄却一个都没有了。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七星子,还依然那么吓人。
前几年,有很多人家陆续又把水田改回了旱田。因为水供不上,白天晚上都得有专人看水,为水打仗的事还是不断。我们小时候憋坝捉鱼的那个河汊不知从哪天起也不淌水了,只有略凹的河床白花花地躺在太阳下,像条被掏空了内脏的咸鱼干。小时候的幻想终成现实,只是没有我想象的欢愉。
近几年,上边不让砍伐树木了,开始鼓励种树。那些旧人参地里栽上了红松、樟子松、刺槐,连河边也插上了柳条。狂风呼啸中,这些小苗死死地扒住脚下的泥土,幼弱的身子不胜寒威。
清明到了,我得以回家看望父母。站在小河边,望着河边稀疏的柳毛子,眼前不由浮现孩提时抓鱼的情景。
“妈妈,你不是说有鱼吗?鱼呢?”儿子摇晃着胳膊把我问醒。
“哦,它们可能上哪儿去玩了,忘了时间。”
“它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它们不会迷路吧?”儿子有些担心。
“柳毛子长起来的时候,可能就差不多了。”我安慰着他,也安慰自己。
是啊,何日小河才能再胖起来,让红红的柳毛子再妖娆地起舞?但愿那时候小鱼还认得它们的家。
杀年猪
自记忆起,一进腊月门,就陆续有“吱——吱——”的声音响彻云霄。在山村寂静的清晨,那声音长长的,脆脆的。一声声灌进我们的耳朵,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哦,谁家又杀猪了!
总是要等邻里的年猪杀得差不多了,父亲才向母亲宣布准备杀猪的决定。脸上是少有的严肃,语气里却是刻意的平静,令人难以捉摸。我和弟弟内心早已乐开了花,但谁也不敢大喊大叫,怕大人会说肚子里装不住香油的话。
杀猪前一天要“空肠子”,就是不给猪喂食只喂水。喂了一年猪的母亲好像特别不习惯,不时去猪圈望望。看着猪摇着尾巴向她讨吃的,母亲的眼神就有几分不舍。然后回转身盘算着明天的菜。豆芽早就生好了,还有酸菜该拿出来浸上了,再把屋檐下的红辣椒拿回来洗好晾干。父亲一挨黑就开始出东家进西家地邀请邻里来吃猪肉。我和弟弟也喜欢这个活,偷偷跟在父亲后面,浩浩荡荡的。
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烧上两大锅水。我们也早已兴奋得睡不着了,趴在被窝里睁着晶亮的眼睛等待天明。
太阳从山梁那边露出头时,邻里的叔叔大伯相邀着陆续走拢来,带进来一身寒气,抖落一脚雪。每人跟前一碗茶,你一言我一语地估猜猪圈中那家伙的分量。
总是要抽完一袋烟的工夫,才听到大蟹子在门外连咳带擤鼻涕的声音,山响一样。由于姓解,头顶光秃秃的又红又亮,很像煮熟的蟹子盖,四肢又长大,就混了这样的名字。他猪杀得好,不呛血、肠子摘得干净还麻利。所以一把杀猪刀用了那么多年,越磨越光。
“大蟹子,你不就会杀个猪吗?牛哄个啥?来这么晚,害我们等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又好久没挨女人骂了?”一个大叔上去作势要摸大蟹子的头顶。大蟹子一弯腰闪身躲了开去,“快抓猪吧,我先不和你一般见识,待会儿杀完猪,看我咋收拾你!”
于是大家捻灭烟蒂,扛着大磅秤向猪圈走去。屋里的女人们有烧火的,切酸菜的,淘米的。从弥漫的热气中,不时爆出快乐的笑声,可能又说到了大蟹子在谁家挨收拾的事又或者是在谋划今天的节目。
很快的,猪圈里就传来了“吱——吱——”的叫声。大家七手八脚就把那头猪摁倒在地,将四个蹄儿用绳子捆在了一起,像个大包袱一样被倒挂在了磅秤的钩子上。两个汉子憋足了力气摇摇晃晃将杠子扛了起来,旁边的人迅速挪动秤砣,眼神快的人喊出“360” ,很快就被另一个人极为霸道地否定了:“380好不好,什么眼神?380!”两个抬杠子的好像也特别满意这个数字,一下子泄了力,不约而同往旁边一跳,将杠子闪在一边。
“这猪真不小!”“比老刘家的肥!”听着大家的议论,父亲只是微笑着,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是极高兴的。但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地表现出来。真是的!
当大盆里的血越来越多时,猪的叫声也越来越弱。有人给大蟹子点上一支烟送到他嘴里,大蟹子两手全是血,歪叼着烟眯着一只眼,始终没说一句话。那秃秃的脑门上沁出了密密的汗珠,在晨曦中亮亮的。
然后是拎热水,煺猪毛。煺光了毛的猪被几个人抬到屋子里早已准备好的破桌子上,仰面朝天。四个人分别扶着猪蹄,使猪身保持平衡。
大蟹子换了支烟,把杀猪刀从猪的心口处向下一扎,然后右手握刀柄、左手摁刀背用力向着猪尾的方向将猪身划开。两边扶着猪蹄的四个人也分别朝四个方向用力掰去。只听“嘎巴,嘎巴”的声音,惊心动魄,谓之开膛。
随着霍霍的声音响处,一摊白花花、软囊囊的东西“哗”地向周围淌去。我们赶紧缩脖子,捂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股热腾腾、腥哄哄的气味一下子钻进鼻孔,并迅速弥漫开去。大人们却似全然没有闻到,纷纷凑上前去说这猪喂得真肥,膘厚实。不停地在围裙上揩着手。
这样的评说是对母亲一年辛苦的最好褒奖,她笑吟吟地站在那里,脸色被热气熏得微红。她偷偷望向父亲,却碰上了父亲“冷峻”的目光,于是赶紧低下头来去找活计了。
一条猪腿卸成几块再加上一块腰条一起扔进酸菜锅里。其余的都按照母亲的吩咐分成大小块儿挂到了仓房里,好肉要送邻里的人情,其余的留待过年。
大蟹子拎着猪大肠向雪地里走去。他把翻过来的猪肠子扔到雪里,然后两脚上去一顿踩碾揉搓。“大蟹子,用不用洗?”门口的人向他喊去。“那能不洗吗?不过,别洗得没味了!”他应道。于是,不久就会闻到一阵呛人的辣椒炒肥肠的味道冲鼻而来,那味道怪极了!
我们小孩子用一根铁扦子把沙肝穿上,在上面划上一道道小口,边在火上烤边往上撒盐。随着沙肝上“滋啦滋啦”滴油,我们的小舌头也“吧嗒吧嗒”滴口水。有时候分不均匀,还会打起来。为了止住小孩子的哭闹,婶婶大娘就会上去把大孩子揪住,从“大鱼”嘴里拽出沙肝,撕下一块塞进“小虾米”的嘴里,边塞边骂上一句解恨的话。那时候大家一定都希望一头猪能长十条沙肝。
那边,男人们已经坐了两桌,女人的桌子也在另一间屋子摆下。男人们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谁也不服谁。屋里弥漫着散装老白干和旱烟叶子的味道。吃了肥肠的大蟹子好像被辣椒刺激了,张罗得最欢,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一会儿工夫就大了舌头,在那边开始唱起黄段子,里面的女人都换成了邻里媳妇的名字。
这下子更捅了马蜂窝,那间屋里的女人早已等得不耐烦,这时候一窝蜂地涌了过来。桌上的男人们马上配合着让开场子。只见大蟹子边叫喊边用两只手在头上胡乱地划拉着,最后只好徒劳地护住头顶发红的地方。可是哪里能护得住啊,不一会儿,他的脖子里就被灌进了凉水,裤子也瞬间成了两边开衩的旗袍。
我和弟弟被大人逼着胡乱吃了口饭,就到屋外雪地上搓猪尿脬了。我们模仿大蟹子的样子使劲用脚碾搓,那个囊就越来越薄,也越来越大。然后再用碱水洗。最后,那个囊就被吹成了一个大大的泡泡,在阳光下晶亮晶亮的。我们央求爸爸用水彩在上面画上梅花,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气球。
屋里的笑声一浪掀过一浪,几乎把夕阳赶到了西天角。
不知从哪一个冬天起,再也听不到这种笑浪了。也偶尔会在冬日的晨曦中听到杀猪的声音,但人声却极寥落。更多的人家是把猪卖给屯子里一家外来的屠户,虽然比不得自家杀了卖肉上算,但这样更冷净。大蟹子也老了,杀猪刀早已挂了起来。
最近几年,人们的生活好了起来,一年四季都有肉吃。但人们似乎都不愿忘记冬天杀猪的情趣。所以一近冬天,刚落雪,就天天有杀猪的声音再次响彻云霄。三五个人说笑着把买来的猪运到屠户家里,拿上二十元钱,半小时的工夫,就可以往家端血扛肉了,干净利索。
东家把至亲好友请了满屋子,有那子女出息的,轿车从院子里一直摆到街上。猪血猪肉照例要有,那是农村的地道。但人们更注意的是哪家的海鲜样数多,散白酒和旱烟是早已上不了台面了。
院子里,小孩子们追逐着真正的气球,五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没有谁再为抢不到沙肝哭鼻子的事了。大蟹子偶尔还会被谁家请去喝酒,知道老黄历的人依然开他的玩笑,问他吃不吃炒肥肠了。他都会讪讪地说:“牙都掉光了,哪里嚼得动?”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动手不仗义吧,也许他真是老了。
其实,我们又何尝没有老呢?我们的身体老了,我们的思维老了,我们的价值也老了。
可是,我分明感觉猪肉的味道远不如从前那么香浓了。而儿时杀年猪的情形却常常摇曳在梦里,那沙肝的味道也时常萦绕在齿边,挥之不去。
(责任编辑 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