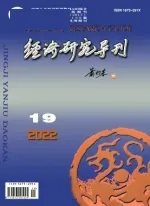珠海淇澳岛旅游资源调查与开发
孟凡祺
摘 要:根据在珠海市淇澳岛的田野调查,对淇澳岛上新老“八景”及其他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并实地拍照、分类,详解旅游资源的变化和原因。从旅游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淇澳岛的旅游资源,并以近期“申遗”成功的日本端岛的案例为导向,为淇澳岛的旅游开发提出建议。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文化资本;旅游资源;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148-05
2015年7月至8月,笔者在广东省珠海市香山区淇澳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田野调查。其间对淇澳岛这个由于“港珠澳大桥”的计划而进入人们视野的小岛的兴衰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笔者选取的主题是淇澳岛的旅游资源调查和开发。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找到了淇澳诗人自己书写的“淇澳八景”诗,进而从新老“八景”的现状、变化和背后的故事入手,走遍了淇澳岛的每一个山头、每一处海滩,对“八景”和其他旅游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系统地整理和分类出淇澳岛的旅游资源,并试图从日本端岛的开发模式中得到对淇澳岛旅游发展的启发。
一、文化资本与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与联系
根据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论,文化资本的“大多数特征可以从事实中推断出来,即文化资本在其基本的状态中是与身体相联系的,并预先设定了某种实体性、具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某种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1]。即说明文化资本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而成的,而且是附着在社会各种具体的形态中,如教育、遗产、书籍、工具、图片等等。文化资本的获取并没有像其他资本一般有社会阶层或者群体的限制,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取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随着民族记忆、历史认同同步形成,烙印在个人和群体的性格和记忆中,并且具有继承性。在旅游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诸如山水、碑刻、文化遗产、考古遗址、纪念馆等等,在其物质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在这一点上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与具体化的资本一样,都是从属于相同的传递法则的。”[1]将淇澳岛的沙滩、山林、故居、纪念馆、宗祠等物化为文化资本,或许更容易理解淇澳本地人对于景致遭到破坏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于自身历史和宗教的自豪感。因此在调查中,笔者时刻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作为首要的原则,观察这些资本是否被传承,如何被传承,以及拥有它们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现代旅游存在着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旅游的研究,人类学界已经有许多学者做出了自己的成就,但大多数的旅游研究中,都集中在对于旅游目的地“社会外部的、可视的、物化的、政策的、行政的、操作的等方面,鲜见对东道主地方社会的内部动力,包括地方文化系统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旅游的承受力,小族群社会结构在旅游冲击下受摧残的程度预估,地方民众在心理上接受游客的态度等方面的研究”[2]。法国学者纳什(Nash,1977)在《前工业社会中的旅行》一文中将现代旅游称之为“帝国主义行为”。人类学对于旅游的研究,“是为了描述旅游在不同情况下的客观表现,包括通过比较的方法解释旅游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除此之外,它还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尽可能了解旅游作为社会行为的表现特征,尽最大可能地去理解和分析人类在旅游情境中的行为”[3]。无论在哪一领域的人类学研究,归根结底,人类学家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群体的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除了采用传统的田野方法如同访谈、观察等外,人类学家还需要对一个族群的物质形态,包括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工具、民居、器物、服饰等都应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认识,进而通过这些自然与物质的存在和变化去描述和记录某一民族、族群、社区的文化形貌,在此基础上去寻找特定人群的精神活动,包括认知、信仰、精神、心理等活动[2]。这一观点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认识和传递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旅游资源是一种文化资本,体现在其社会化和客观化的物象中,可以被感知、传递。
旅游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在史密斯(Smith,2001)看来,有四个“H”:旅游景区(Habitat)、历史(History)、遗产(Heritage)和工艺品(Handcrafts)。这四个关键词可以对旅游的各个方面产生作用和影响,比如旅游资源与实际承受能力的关系;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使得东道主社会发生的变化;因为旅游活动产生的潜在的文化冲突等等。这四个“H”的确是旅游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时刻铭记的四大要素。
二、淇澳岛旅游资源介绍
淇澳岛,因下大雨时,岛屿有很多湾,宋名“奇独澳”,清末改“奇”为“淇”,并去“独”字,而成“淇澳”。淇澳岛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海域,地理位置为北纬22°25,东经113°38,距大陆约1公里,岸线长24公里,陆域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
淇澳岛的旅游资源在本地诗人钟大元、钟大安笔下形成了“淇澳八景”,后来因为大桥建设、时间变迁、树木砍伐、海滩破坏等原因,大多景点已经不复存在或者破坏严重。前人淇澳村老人协会会长钟金平先生,是一位热爱家乡的诗词爱好者,他带领喜爱诗词的老人们将“淇澳八景”重新整理,形成了“淇澳新八景”,这新八景都是近年来才认定,全部有据可查。这“新八景”和“老八景”除去重合的部分,一共有十五处,分别是:淇澳老八景:赤岭观日、婆湾晚舟、松涧流泉、峡州烟雨、金星波涛、蟹珠夜月、鹿岭观霞、鸡山返照;淇澳新八景:赤岭观旭、沙丘溯古、牛湾纱影、扪角蚝园、白石烽烟、红林雾霭、金星晚望、岗树新风。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挑选几处有代表性的景致,以体现淇澳岛从风景秀美的南海小岛到如今满目疮痍的废墟的变化过程。
(一)赤岭
赤岭分别出现于新老八景中,是唯一重叠的部分。这个景致是在和平公园山顶看日出。半山腰还有淇澳最大的宗族钟氏的祖坟,但也被荒废,仅仅清明祭祖的时候会有钟氏代表前往祭拜。整个公园是作为影视基地开发的,据村民说因为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多剧组选在这里拍电影。但笔者先后前往和平公园三次,并没有看到任何剧组在这里工作。
整个公园以水泥路为主,环山公路是中新公司收购地皮之后建设的,人们都认为是地产商为了获取政府许可而随意修建的,作为公司保值和增值的手段而已,因此也就在公路和影视基地稍微修建好之后,停止了对和平公园的进一步开发,这就造成了现在大部分地皮荒废、管理人员和力度不够的情况。
(二)婆湾
婆湾是淇澳的老八景之一:婆湾晚舟。婆湾是钟大元、钟大安等诗人歌颂最多的景点,“玉水明沙岸一湾,钓家渔艇聚其间。晴波雨浪奇堪醉,雾嶂烟发秀可餐。宿鸟噪林催棹去,乱鸦啼树挂帆还。星星灯火明如画,水调渔歌响一滩。”说明在大桥建设之前婆湾沙滩资源丰富,是渔民的主要码头和聚集地。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沙滩,原因是在大桥修建时建筑工人将沙子用作建筑材料,很多中山、珠海人也前来运沙,有的是给建设大桥用,但更多的是向外地运输,低廉的成本和松散的管理让这些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大规模地偷沙,使得现在淇澳绝大多数海滩已经没有沙滩。
(三)牛婆湾
牛婆湾位于岛的东北部,是大澳海湾中的一个小海湾。整个大澳都没有人烟,是曾经伶仃洋大桥计划上桥的地方,连桥墩都建好了,然而由于整个伶仃洋大桥计划搁浅而彻底荒芜。据老乡介绍,当年在这里连开工仪式都准备好了,曾花费十几万搭建舞台,这里还因伶仃洋大桥计划而短暂畸形繁荣过,连发廊、饭店等都开张了,很多公司买下了地,却因为大桥改道而放弃投资,只是圈了起来,也没有人看管,于是也就成了现在荒凉的样子。可以说,这里是随着伶仃洋大桥沉浮最典型的地方,也代表了整个淇澳岛的沉浮。
这里有绵长的海岸线、一望无际的草甸和丛林茂密的苍山。但是在这些景致中,最为显眼的是遍地的工业垃圾,海滩上堆满了从其他地方飘来的拖鞋和泡沫塑料,数量之多令人惊异。整个大澳的路况非常差,土和石子铺的路令人几乎难以前进。
(四)沙丘遗址、后沙湾遗址
沙丘遗址位于淇澳岛东北部沿海,近婆湾。后沙湾遗址位于大澳山上,有古道可以到达。在珠海,只要有淡水流过的沙滩几乎都是史前遗址,即沙丘遗址。后沙湾遗址有新石器时代两期文化堆积层,第一期文化层出土的彩陶圈足盘和刻划白陶豆,都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用热释光对彩陶进行测年,其年代距今4818年(误差加或减482年,1989年测定)。后沙湾遗址是最早有人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物证。从此,“珠海历史五千年”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结论。
两处遗址保护得并不好,沙丘遗址已经是烂泥滩,连牌子都难以找到;后沙湾遗址的碑立在一片荆棘中,很难靠近,也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珠海市政府和文物局立的遗址碑已经被淹没在荒草中,倘若不仔细观察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和大澳的后沙湾遗址情况相似,当地人说当年的开掘是野蛮式的,似乎仅仅是为了增添遗址的数量而开掘,根本没有保护性措施,开掘结束之后也迅速撤离,没有对现场进行任何程度上的修复,就连树立几块宣传牌向游客介绍一下遗址的情况和出土文物都没有,可以说根本没有从保护旅游资源方面考量。”
三、日本端岛的旅游开发
在旅游研究中,日本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域,因为无论从自然资源还是人文历史,日本并不能算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国度。然而,作为全世界游客,尤其是近几年“大举攻占”的旅游热门目的地,日本在自己的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上做得非常出色。日本的国内旅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在进行乡村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时,非常重视在原有的一些遗址上进行开发(‘复原和‘修整),尽可能保留其传统的、‘旧式的、古董的、原貌的民俗景点或博物馆,使之成为‘乡土式的综合博物馆。”[4]其实,不仅是乡村旅游开发采用这样的模式,日本本土旅游相比于“新建开发”显然更加倾向于采取“保存修复”的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旅游吸引力。
吸引力的构建和标志物密不可分。例如,日本端岛的标志物就是如同军舰的岛屿形状和岛上荒废的众多的楼房建筑等。再简单一点,端岛的标志就是灰色。笔者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名为《1972青春军舰岛》的摄影集,是日本摄影师大桥弘重回军舰岛——端岛进行对自己儿时记忆的重拾之旅,照片都是灰黑色的楼房、走廊、住宅、学校等等,倒不是摄影师故意采用黑白照片的方式,是因为端岛的的确确就是一片灰黑的废墟。人们想到端岛,就会想到这些水泥废墟,就如同想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会想到翠玉白菜一样,这就是标志物在旅游吸引力塑造中的作用。
去端岛观光的游客需要统一上船,在岛上的游览也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由专门的导游带领解说,不可以自己随意行动或者拍照。一旦有人跨过政府树立的标志牌界限以外,就会被拘捕长达30天之久。端岛实际上是一个“露天博物馆”或者“生态博物馆”,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遗产群,承载着历史和时间的记忆。对端岛的开发倒不如说是对端岛的重新发现,并没有加入任何现代人的痕迹,仅仅是在端岛规划出了一条观光路线,修筑了栈道和护栏。大部分岛上的区域是严禁人们进入的。对外展示的,不是经过精心修饰的景观,而是原原本本的废墟,即使它看上去可怖又巨大。前文提到的标志物的宣介功能,也被端岛开发利用得非常好。风靡全球的《007》系列电影中的《大破天幕危机》就曾在端岛取景。作为反派头目的基地,那或许是端岛第一次进入世界人的视野,也被一些旅游杂志列为“全球最可怕的九个无人岛”之一,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岛屿曾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在1960年比东京的人口密度高出了9倍多,也拥有着全日本第一幢水泥大楼。
维基百科上有一个摘自日本《军舰岛实测调查资料集追补版》第566页的关于端岛人口变化的表格显示,1960年时端岛的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超过其承受能力,于是人们加快建设高楼住宅以将过多的人口塞进房子里,也就造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端岛上密密麻麻的建筑废墟,每一幢楼都可以看出非常结实,也体现了当时端岛上的日本居民的高收入和高技术。当时在端岛工作的矿工,薪资是50万日元为底线,比日本本岛上的同类职业收入高出许多。岛上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从学校到市场、从游戏室到西餐厅,都呈现了一幅因煤炭而欣欣向荣的经济景象。可是,仅仅在十五年后,往日繁华一时、熙熙攘攘的端岛就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鬼城”,不禁令人深思世界经济能源的转向对普通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端岛在2015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通过了审核,作为明治时期工业发展遗迹登录为世界遗产,成为了“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钢铁、造船和煤矿”的一部分。19世纪在端岛发现煤矿资源。日本政府支持的三菱矿业(现三菱材料)接手经营煤炭产业后,便强迫所征用的朝鲜人当矿奴,让他们在海底700米处的煤矿里劳作,受尽残酷的虐待和劳动折磨,因此这里被称为“地狱岛”“监狱岛”。日本在将端岛纳入为明治日本工业遗产的一部分时,遭到了韩国的强烈反对,更有当年被强征到岛上开掘煤炭的韩国劳工们的泣血抵抗。然而无论如何,端岛还是成功“申遗”,并利用联合国遗产这样一个名号大肆宣传自己的旅游业,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人类遗产”和“象征资本“都可以放入博物馆的广泛定义中,作为展示人类历史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令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标志符号。日本将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和推动旅游发展联系在一起,成功申遗。端岛重新开放旅游后,前来游玩的旅客并不多,而且大多是日本本国游客。而在2015年世界遗产大会结束,端岛“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便呈现出爆炸性增长,长崎到端岛的定时船运已经不足以容纳大量前来游玩的旅客。由此可见,“申遗”和旅游业发展的紧密联系。
作为端岛建筑群的标志物,30号建筑是整个游览路线的核心。建造于1916年的日本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30号建筑七层楼曾经震惊了日本本土。这样的标志物也是端岛吸引游客的核心要素。旅游景观和旅游标志物是旅游象征结构的展示方式。彭兆荣教授将旅游象征分析为一个具有跳跃化的关联效应,即“景观→标志物→景观”的转换[2]。端岛的30号栋,从“物”的角度看,仅仅是一幢荒废破旧的水泥建筑。然而,当它成为端岛的标志物,换言之是日本明治时期煤炭工业催生的城市繁荣的标志性景观后,它就成了一个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物,人们也不再会从“难看的破旧楼房”的角度去理解它了,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端岛的象征”。同理,端岛也成为“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的象征”。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中的个人通过资本的投入和积累可以获得“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又可以与社会地位相联系并取得与权利关系的转换,它们都在进行着“争夺空间”的事情[1]。麦克内尔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与旅游人类学的结合。他认为旅游中的“象征资本”,即附加在标志物上的价值是非个人可以得到的,“象征资本是一个充满了地方和认同价值的标示物,它包含了地方和人们所赋予的著名价值,但却无法用于买卖和交易。”[5]因此,旅游标志物的主要作用就是代表整个景观并且进行宣传工作,手段可能有印刷小册子、拍摄宣传片、制作纪念品等不同的方式,以达到宣传整个旅游目的地的目的。30号栋、端岛小学等标志性景物,就被日本观光局当作标志物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利用。在端岛的观光路线上,导游会向游客介绍面前的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建造的,并会拿出历史照片和现在对比,在几个标志物前还会推荐游客拍照,介绍到这里是“必须要拍照的标志点”。这样的旅游宣传非常符合如今游客希望向别人展示“到此一游”的心态,上岛的游客一定会在这几个标志点拍照,进而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给更多的人,无形中就等于帮助端岛进行了宣传工作,也是观光局非常乐意看到的“双赢”局面。
日本端岛的旅游开发可以说只进行了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已经可以体现出旅游人类学中几个核心观点和概念,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单纯从开发手段的借鉴意义,相比较塞班岛、巴厘岛这些风景优美、海滨旅游资源丰富的海岛,端岛对于淇澳岛的启示意义更大。淇澳岛的旅游开发,不需要符合人们心中关于“海岛旅游”的刻板印象,只要把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曲折发展的路径展示出来,就足够有特色了。
四、关于珠海淇澳岛旅游开发的几点建议
(一)做好旅游定位,抛弃传统“海岛旅游”的观念
淇澳岛并非如同一般旅游海岛一样,有沙滩、椰林、海浪、度假村等“海岛因素”。相反,它的海岸嶙峋、垃圾遍布、海水浑浊,也没有高大上的度假村和高端酒店。那么,索性就放弃这个“海岛梦”,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淇澳岛,一个有自己伤痛和“丑陋”的淇澳岛。
很多海岛有海滩有椰林,但也许只有淇澳岛有伤痛和无奈。这个因为港珠澳大桥而兴起的小岛,在最高潮的地方被狠狠地抛下了云端,剩下了一片愁云惨淡。从前因为大桥计划准备动工的土地、准备开业的店铺、准备装修的住宅,随着计划的搁浅戛然而止。走在淇澳的烂尾楼群里,笔者竟然有一种在端岛上的错愕感,只不过,这些房子从未住进过人,而端岛则是曾经的居民因为政策原因全部撤走。这两者竟然有如此相近的地方。总之,淇澳岛的旅游开发,走传统海岛旅游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光是治理海水污染、清理海岸垃圾、搬运沙子覆盖海滩就根本不可能。相反,如同端岛一般走“记忆旅游”“开放博物馆”的道路则更加可行。
(二)确定旅游标志物
淇澳岛旅游标志物可以是“港珠澳大桥”这个虚拟的概念,根据这个并未成形的计划延伸出的民居、道路、海滩、自然景观和村民生活等方面的变化。也可以是传统的宗教旅游,在淇澳有一句话特别流行,那就是“不怕淇澳人,就怕淇澳神”。一座小小的岛上竟有17座庙宇,更不用说路边随处可见的社坛和碑了。在这里,几乎每个居民都有信仰,宗教信仰已经深深根植进他们的人生和族群记忆中,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再到离开人世,都有相应的宗教信仰在背后指导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方式。岛上居民的信仰可以被归纳成为三级信仰,他们并不是信仰单一宗教的,而是有各种各样的神灵,根据自己的需求向不同的神灵祈求。淇澳岛的天后宫和观音阁,据说非常灵验,很多外地人每月逢初一和十五都会到这里来拜神祈求保佑。无论是采用哪种标志物,它对于整个岛屿的旅游开发都起到最核心的凝聚作用。当旅游标志物和目的地形成一个整体之后,它对于游客的吸引力就有了“神圣的仪式性”作用了。这里并非指宗教一般的吸引力,而是“在旅游活动中游客被某种黑色会价值和道德力量所引导,在现代传媒宣传的作用下,在游客的情感中产生一种对某些景点的特殊的吸引”[2]。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旅游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树立旅游标识物,因为它是游客“必须要去”某个目的地最大的吸引力来源。“为了实现这一吸引力,游客会不自觉地遵循着旅游的结构程序一步步地往下走,最终完成旅游行为。”[2]
(三)对于标志物要进行保护
淇澳岛有很多文化遗产,有考古发现的遗迹、有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宗教庙堂等遗产,去做所谓的“申遗”工作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如今“申遗热潮”中那些因为拥有“遗产”头衔地方在旅游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淇澳岛本地的遗产,在开发、宣传之余,更应注重保护。因为当旅游事业迅速发展,游客骤然增多的时候,人类本身很可能因此成为破坏遗产的罪魁祸首。为了接待更多的游客,扩大旅游范围,会出现一些破坏性的建设,可能会对旅游标志物造成严重的影响。以淇澳岛的文昌宫为例,倘若他日游客增多,势必要将庙里天花板上众多的环香取下来,以免香灰掉落烫伤游客。但这样一来,文昌宫可能会失去了往日的氛围,变成了观光之地。所以,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之间,仍旧存在不少冲突之处,似乎并没有办法永远达到东道主和游客之间“双赢”的状态,而这也是珠海市政府今后应该考虑的。
参考文献:
[1] 包明亚.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33.
[2]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193.
[3] [美]丹尼逊·纳什(Nash Dennison).旅游人类学[M].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84.
[4] 段从军.法国和日本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的启示[J].民俗研究,2002,(4).
[5] MacCannell,D. Empty Ground. London: Routledge,1992:161.
[责任编辑 李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