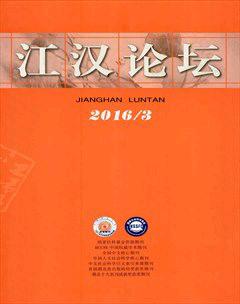权力、国家与现代民主批判
林钊
摘要:马克思和尼采都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有激烈批评,却又把对方视为资产阶级的同道,需要比较两者政治哲学的异同来阐明他们批判理论的差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斗争理解为权力和国家的本质,把民主国家看作人性的异化和有待超越的虚幻共同体。他们的分歧在于,马克思要求国家消亡和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尼采则要求恢复等级和精英统治。在尼采指责社会主义否定生命的同时,马克思则证明超人只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形象。
关键词:马克思;尼采;国家;现代民主;政治哲学;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39-05
马克思和尼采不仅是同代人,也是他们共处时代的最尖锐的敌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民主政治。不管这个时代是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的”,还是被尼采称作“末人的”或“群畜的”,它都被认为是有限的、消极的、虚伪的和必须被超越的。两位哲人的时代控诉成为20世纪社会批判重要的思想资源,但他们思想之间未被厘清的紧张也导致现代批判理论始终呈现某种难以消解的暧昧:既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和压迫,又希望克服它的平庸和颓靡。西方批判理论的衰微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和尼釆的政治哲学作深入的比较审思。只有厘清马克思和尼釆在政治哲学上的异同,包括对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超越的理解,才能明白他们为何对现代政治有诸多相近又相悖的论断。
一、权力和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来自于彼此平等的共同体成员的自愿让渡,因而可以保证对公共权力的服从乃是对自身意志的服从。洛克就曾说:“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马克思和尼采都对这种政治权力归属所有人并服务所有人的神话不屑一顾,他们都认可权力是秩序的体现及维护者,只有差异才能产生权力,也就是说,必须把权力理解为支配一服从的辩证关系。权力不是洛克或卢梭以为的来自平等自由人自然权利的自愿让渡,相反,它是不平等的人际交往的产物。马克思和尼采的分歧只是在于,权力究竟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权力是社会化、去自然化的结果。在最初的原始氏族状态,个人利益并没有从公共利益中解放出来,因而氏族内并不存在对立也不需要强制手段,人们在充满危险和匮乏的环境中也可以以自主而平等的方式共存。但劳动分工和剩余产品交换催生出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人与人之间出现分裂乃至对抗,为了私有财产不被其他人抢掠,拥有私产的人们需要更大的权力的保护,国家随之产生,它以共同体的名义保护并控制交换,国家、政治、权力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经济交换中诞生的,是生产力提高和自发组织的原始共同体破裂后的产物。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政治权力或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异化性质,它是对个人利益的脱离,也是对自发性的人类交往即社会的脱离乃至抑制。马克思强调,经济上的阶级对抗关系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压迫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就如同阶级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一样,支配性的政治权力也是人造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表明,它们并不拥有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青年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完成”,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的学习成果都表明,人类可以期待一种后权力的生活,那是对前权力的人类自然状态的更高层次的复归,巴黎公社便是非政治生活的一次实验。
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像马克思所考察的那样和谐友善,相反充斥着剧烈的冲突——整个自然都是以竞争为原则的,没有理由认为还没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人就可以伊甸园一般平静。尼采说:“我使用了‘国家这个字眼,我的意思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一群黄头发的强盗,一个征服者和主人之种族,他们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并且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不加顾忌地把魔爪伸向那些在数量上或许占有优势,然而却没有组织形态、四处漫游的人民。‘国家就是这样在地球上兴起的。”国家产生于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它天然就为支配而生,而非自由主义所坚称的保护。国家成员的权利确实是交换的结果,但并非平等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交换,而是主人与奴隶间心理感受的交换。按照尼采的心理学解释,在最原始的状态中,强大的、在战斗中获胜的人们会以残酷的、动物般的野蛮对待失败者,而失败者以服从换取免除惩罚。只要我们看得真切,义务一权利的准确翻译是牺牲一享受、服从一支配。权力是生命的本真意义,也是人类达成群体生活的根据。如果我们肯定生命的生长、求强、壮大、蓬勃,其实也就在肯定压迫、伤害、强暴、剥夺这些被看作“非法”、“不义”、“邪恶”的力量。就算如马克思和人类学家所考察的那样,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和谐平等的氏族,但那段历史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权力,没有对卓越、统治、征服的追求,也就没有创造。换言之,在尼采的视野里,权力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它在历史出现的时刻就有,并将一直存在。国家或政治权力,不是避免奴役、寻求安全的出路,相反正是等级秩序的体现。如果权力因其统治本性而被视作野蛮的话,那人类的文明史同时就是野蛮史。
通过比较可知,马克思和尼采都坚信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并没有所谓自然法所规定的“正义”内置于国家之中——那只是某种唯心主义的神话。相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分才是国家的“本性”,两者的斗争贯穿了国家的历史。在马克思那里,斗争的主体包括奴隶主一奴隶、贵族一农奴、资产者一现代工人,这些阶级斗争的内容的改变决定着保护这些斗争中获利阶级的那种国家形式随之改变。在尼采那里,国家形式的变化根据于人类服从心理的转变:“君主政体,体现了对超群之人、元首、救星、半神的信仰。贵族政体,体现了少数精英对高等人的信仰。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尽管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两位思想家都认可,国家是对抗的产物,是一架具有支配功能的机器。
二、民主与人权
虽然马克思和尼采都建立起了一套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模型,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民主时代——而非历史,所以他们才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批评者”和“诊疗者”。民主是现代人已然面对的命运。促成民主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平等主义和利己主义,它们构成了自由民主制的前提——“天赋人权”的基本内涵。宗教改革实现了前者,它使人因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要求世俗世界的平等;工业繁荣强化了后者,它鼓舞人追逐物欲并以此为正当。马克思和尼采都敏锐地发现,“人权”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掩盖了构成权利实质的社会内涵。法国大革命和自由主义用政治解放的方式把民主的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并由此拉开了政治现代化的序幕。可对于政治解放,他们的评价就算不是消极的,也远谈不上乐观。如果说国家是人类本性的扭曲,那么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这种扭曲达到了顶点。
尽管马克思坚持启蒙以来的历史进步主义,但他指出人类进步实质上比人们想象的要有限得多。这种进步与其说是人们取得彼此“承认”程度的提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矫饰性的增加,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仅仅是因为被欺骗才以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保护。由于契约成为现代人交换和交往的基本方式,要想揭开政治中被伪饰了的权力支配本质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分工和交换的繁荣为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它们是调节人们交换矛盾的力量,但这些调节机构的存在本身就预设了人们的交往并不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国家起源于社会交往,却以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僭越于社会之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而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总是由拥有特殊利益而非普遍利益的统治阶级接纳并掌握国家机器,以之作为反对其他阶级和其他特殊利益的武器。现代民主制的建立和由之带来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经历了1789年大革命和拿破仑革命的法国便是例子:“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
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的“公意”原则被资产阶级自身的利己主义所击碎。大革命解放了利己主义的个人,使得受到契约保护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成为人际交往的根本方式,但是大革命无法战胜利己主义,只能把现代人留在“公民”与“私人”两重身份割裂的罅缝中。“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这个根本性断裂决定了政治解放无法凝聚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而只能是人类获得整体解放的一个前奏。政治解放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把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交换的秘密堂而皇之地呈现出来,但是它没有就此改变交换的不公平的性质,反而用自由契约的形式把支配和剥夺的实质遮掩住了:农民通过“自由”交换变成无产阶级,工人通过“自由”交换固定在贫困线上。马克思指出,民主政治所保护的人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实际上沦为自私的个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它所导致的结果是,看起来政治上独立的个人(工人),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一进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其实就处在了被奴役的地位上:“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恩格斯说得更明白:“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众所周知,尼采极端敌视民主,乍看之下,他与马克思有诸多类似的结论,比如:民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宗教改革与民主革命一脉相承:政治解放意味着真实人性的异化;资产阶级在生产着平庸的人类等。不过,他论证的立场和思路却与马克思大相径庭,甚至正好相左。尼采反对历史进步论,在他的视野里,历史的演化恰恰昭示着人类的退化。国家起源于强大民族对弱等民族的征服,最初的国家保持着对自然性的差异、等级、竞争的肯定,但这些“真理”渐渐被遗忘。从苏格拉底到基督教再到启蒙运动,一套虚无主义的“道德谱系”愈发坚固,从君主制到民主制,国家的本性愈发消散。尼采说:“对国家的蔑视、国家的衰落、国家的死亡、私人(我避免说个人)的发动,是民主国家概念的结果”,“现代民主是国家衰落的历史形式”。
民主革命是宗教革命的延续,都是平民(herd,或群畜)渴望获得自我统治的努力,当路德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师”时,便为平民摆脱高贵者的引领打开了方便之门。基督教道德中潜藏的奴隶对主人、病人对健壮者、弱者对强者、平庸者对卓越者的怨恨、嫉妒、诅咒都在民主政治的平等“人权”中得到发酵,即抹杀人类天然的高低贵贱之分,让不平等者平等起来,让高尚者服从低贱者的价值。“道德今天在欧洲是群体动物的道德,……我们甚至在政治的和社会的机构中找到这种道德的一个日益可见的表达:民主运动保留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在同一场合,尼采说:“欧洲的民主化在最确切的意义上准备生产一种适合奴隶制的类型的人。”
和马克思一样,尼采也要解构民主政治的平等幻象。马克思批评的是在公民平等表象后面隐藏并一直被强化的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压迫,而尼采则痛惜平等背后奉行的是平庸大众对高贵精英的统治。因为强者总在追求卓越、超拔、与众不同,只有弱小者才渴望平等和相同,所以“对一个人是正当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不可能是完全是正当的,为一切人所要求的一种道德,恰恰损害了更高等的人”。平等主义试图用一个普遍的标准将天然存在差异的人们囊括起来,而这个标准其实来自大众的设定,结果必然是对高贵和伟大的排斥,是全体人类的低矮化。尼采这样质疑道:“当‘权利的平等可以十分容易地转变成错误的平等时,转变成共同战斗反对一切少有的东西、异己的东西、特许的东西、更高级的人、更高级的灵魂、更高级的义务、更高级的责任、创造性的全权和主人时,……伟大是可能的吗?”
马克思和尼采都明白,平权——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是一场欺骗。对马克思而言,资本家实行贸易自由的权力就是剥夺工人追求富裕的权利;对尼采而言,大众实现自主的权利就是剥夺高贵者统治庸人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政治解放解放了利己主义的个人,但利己主义没有促成“真正的人”,相反是对人性的破坏。马克思从社会性来定义人性,正如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一再表明的,利己主义所设定的原子式个人其实在消解和割裂人的社会性存在。尼采把张扬和支配看作“生命”的本质,当平民要求“利己主义”的人权时,那只是低贱的“末人”在表达其对舒适、享受和自我保存欲望的追求,于是高贵被排挤,平庸受弘扬,弱小者违抗服从的义务,高等人遗忘统治的责任,生命或曰“真正的人”正在死亡。尼采这样总结:“民主是人的衰败的,即被贬低的形式”。
三、民主的超越
马克思和尼采都把资产阶级民主看作人性的异化,但他们的分歧远大于共识,他们给出的扬弃异化的途径完全相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把对方看作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一个人所支持的其实就是另一个人所反对的。
马克思对民主政制的不满在于资产阶级的允诺和它的兑现极不相符,“应然”的人权和“实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之间的断裂触目惊心。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政治解放太有限了,它无力改变反而肯定人在市民社会层面上的疏离、分隔和对立,直白地说,就是它客观上保障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权。马克思要求一种更彻底、更完全的人类解放:“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人类解放既是民主制的完成,也是对民主政制的超越,这个奇怪的逻辑只有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中才能得到理解。共产主义作为那个超越民主的更高的阶段,在其中,因为私有制的废除,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得到统一,阶级以及阶级间的压迫和对抗都消失,作为政治异化的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将因为人们实现自我管理而失去存在意义,人类将自自然状态结束后再一次拥有自治性、肯定性的社会存在。巴黎公社便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失败的胜利”:“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
巴黎公社寄托了马克思对超越民主国家的期待:工人的革命、“庶民的胜利”、现实的民主,而尼采却认为民主精神本身就是谬误,它代表的不是人性的繁荣而是腐朽。如果说马克思把社会性,也即权力废除、阶级消失、人类团结视作人的解放的标志的话,那尼采倒觉得自由就是远离社会、确立秩序、恢复统治。学者勒夫总结得好:“马克思作为激进民主派,把自由民主制看成从原始共产主义通向自由社会的一种手段,尼采作为激进的贵族主义者,认为自由社会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明白尼采的贵族主义立场,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基督教、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视作“同流合污”的虚无主义表现,因为这些彼此敌对的主义都共同宣扬平等原则,都在试图抹杀追求卓越和统治的生命真相。社会主义者比以往各种平权运动更为激进的民主倾向恰恰反映了弱者对生命的恐惧,而把张扬和支配视作坏的、需要被否定的因素。当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民主运动都主张让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时,当马克思把未来许诺给无产阶级时,尼采则哀叹这是人在“社会主义的笨人和浅薄者”的理想中蜕化堕落:“人蜕化堕落和贬低为完全的群体动物(或者像他们所说的,成为‘自由社会的人),人动物化为具有相同权利和要求的侏儒般的动物。”工人革命只是基督徒奴隶起义的再一次翻版,尼釆期待着“把强制带人伟大的政治”。
尼采把破除民主症状的希望寄托于“超人”。不管关于超人有多少让人头晕目眩的隐喻,它必然包括独一无二和自我创造,它是对平等主义导致的人之庸俗化、扁平化、低矮化的抵抗。只有保持不平等,才能保持差异,保证人的自我提升。在尼采的语言里,“个人=压迫”。基于这个根本立场,尼采对任何平等化、集体化、社会化都保持警惕,所以他指责社会主义是“专制主义绝妙的小兄弟”,“力求真正消灭个人”,将个人视为“不合理的奢侈”,并试图将其“改善为一种合目的的集体机构”。当马克思呼吁消灭压迫,建立自由社会,让个人重新回到社会的保护和肯定之中的时候,尼采却说消灭压迫就是建构虚假的彼岸世界,社会在压抑个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国家的神圣化、最大化。一言以蔽之,尼采把马克思视作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谋。
马克思从两方面回击尼采,并成功证明不是他,而是他的强大对手才是资产阶级的同道。其一,工人阶级并非贱民、群氓、庸人的集合,在摆脱了剥削后他们会在自由人联合的共同体中获得丰满的人性。当尼采嘲笑工人是一群麻木工作、贪求物欲、复仇意识强烈的奴隶时,马克思则指出正是因为交换原则成为社会的唯一支配原则,以至于人(活的劳动)竟然可以和无生命的物作等价交换,人才被贬损和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除了机器般的劳动他们几乎丧失一切个性。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平台上,马克思看到,个人之个性是在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中培养的。在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后,无产阶级亦将超出所有权这一利己主义观念的“狭隘眼界”,并在不受强制分工破坏的自由劳动中享受创造的愉悦,成为全面发展、个性丰满的劳动者。而且,即使在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马克思所寄望的工人也非尼采以为的“群畜”,他们勇敢、无私、团结、自觉,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尼采赋予超人的那些禀性,而“末人”的头衔只会属于那些唯唯诺诺、鼠目寸光的小资产阶级。很难想象,如果无产阶级不是超人般的,如何能够承担起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使命?
其二,将支配—征服—占有的模式设定为生命的真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生活在观念中的投射,超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形象。马克思和尼采都以斗争来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但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只是一个必然被跨越的历史阶段,他倡导阶级斗争乃是为了消灭它,尼采却把斗争—压迫看成社会结合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异。如列斐伏尔所说:“不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让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使马基雅维利成为马克思的先驱),将政治或者国家看作一个永恒的、超时间的本质。”从马克思的立场看,权力意志渗透着资产阶级的贪婪、狡诈和无耻。尼采把权力当作永恒真理,把倚强凌弱视作正义,把多数人的受剥削视作应当,这其实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不谋而合。尼采强调的创造、超越、改变的超人精神从来不属于受不公平的社会条件压抑的苦难大众。“个人=压迫”的公式,无非是自由主义用利己主义来阐释人性的翻版,仍然在建立一种先验的、永恒的人之形象。就此而论,权力意志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旧框架,超人也终究会是孤独的、克里斯玛型的英雄。尼采和他所讨厌的资产阶级一样,只在个人那里寻找进步和自由的力量,把社会/群体看作敌对于他、有待征服的对象,他们都忘记了,正是那些受鄙夷的大众和他们的交往,才是历史运动的动力。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