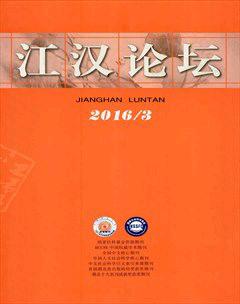经济学解释与预见的出路
杨渝玲
摘要:在制度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环境或者情境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这两个研究方向上是把情境作为内生变量来看待,并辅以实验数据运算、处理和分析,以此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依据。大数据时代在缓解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的同时,把核心焦点又进一步彰显出来。情境是无法回避的,是人类的认知应有之维,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情境因素成为一个显著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而被重点加以关注和考量;对于规律的研究也因为情境的改变而出现多种可能性,以多种可能性组成可能世界为依托,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趋势或趋向,现实条件具足以后,就会是可能性走向现实性。
关键词:人数据:经济学方法论;情境策略: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05-06
信息化早已成为现代科技的重要特征之一,随之而来的网络化、数据化铺天盖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分析数据已成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在科研中运用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方法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问题已经成为必要工具。如果说古希腊数学神秘主义代表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的理念,主要还是在宗教层面上,以虔诚之心供奉数字,把数提升到“万物”的高度上的话,那么今天,数据成为全社会的基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万物”的基本尺度,这对包括所有学科在内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呈现出与以往研究质的区别,出现了“人文计算”,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挖掘等,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一、经济学方法论论争的历史回顾
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的著作《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用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经济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开创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科学哲学传统,指出经济学科学性的核心在于检验问题,即经济学理论的功能是用于解释还是预言?于是,一大批的科学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此进行探讨。
最早把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中来的是哈奇森,他曾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1938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经济学要被认可为科学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可经验地检验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组成经济学的命题至少应该能够在人际间进行经验检验。由此,哈奇森分析了经济命题,以确定经济命题在经济学中的逻辑地位。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命题都可以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大类,其中综合命题又可以分为应用理论的综合命题和归纳概括命题。在应用理论的综合命题中,预测是从经验地确认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以此为基础,哈奇森认为经济理论需要经验检验,包括观察的检验。哈奇森的这些观点曾受到马克卢普的质疑,马克卢普从当时的科学哲学背景出发对哈奇森的观点予以反驳,他认为可检验性是从理论整体出发的,其中可以包含着不可检验命题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理论整个体系经过检验,那么它所包含的各个命题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间接检验。但是哈奇森和马克卢普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作了这样一个假设:从自然科学中得到的方法论标准能够被应用于社会科学之中。对他们两人来说,经济学方法论家的使命是借助于从当今哲学中获得的洞察力,把逻辑分析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分析之中,尽管在马克卢普捍卫经济学正统观点之处,哈奇森却得出了批评性的结论,但是两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关于经济学的可检验性观点令经济学家们注目。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方法论分析必然会涉及使用形式逻辑来对科学命题及其检验方法进行评价。1953年,弗里德曼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在于,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设,它们可以对尚未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提出确定而有意义(即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对于这些假设的检验也包括对这些假设的价值做出检验,这是弗里德曼与哈奇森和萨缪尔森的观点的不同之处。在布劳格看来,19世纪对经济理论的假设或假定已经澄清并基本上达成一致的观点是,在检验的最后环节是通过理论对他们计划要解释的现象的影响来判断这个理论的,也就是要求对经济理论的预言进行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绕开关于证伪主义概念本身的争论而另辟蹊径的汉兹的观点,他注重对出现的证伪主义研究持续热潮的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解析。他解答了以下问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什么会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如此之大?这是前所未有的,况且波普尔的哲学研究中涉及到经济学的内容也仅有几部分而已。汉兹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标准”,即证实原则只能为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提供极少的指导;而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即证伪原则比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实践上更加行之有效。因此,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人们提供了真正的“方法论”。但是汉兹认为,波普尔的进步理论在经济学中却是不恰当的。因为波普尔所要求的理论进步表现为独立可检验,必须存在超量内容及“预言”新事实。但事实上,经济学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解释和预言。解释和预言不是对称的,比如,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最为成功的,是它在为微观经济学现象提供可接受的解释方面的能力;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最成功的,则是它在预测总体经济变量行为方面的能力。所以,汉兹认为对称命题——主张解释和预测仅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在经济学中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存在着多个理论同时解释同一现象所带来的困惑。经济学进步中“什么是进步的?”和“什么将是进步的?”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没有了严格检验与似真性之间的联系,方法也就在寻求科学的现实目标上只有有限的价值。”
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波普尔的标准对于经济学来说过于苛刻,而经济学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宽泛的规则。汉兹认为这些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因此,证伪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方法论是不合适的,如果仍是执著地坚持这样做的话,经济学将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汉兹并不因此而否认事实对于理论的选择及经验检验的重要性,放弃证伪主义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从经验中学习。
二、经济学检验的情境解决方案:制度与实验
在以上论争的进程中,问题导向和情境分析的诉求渐渐显露出来,于是经济学家们不再纠缠于证实与证伪,而是致力于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改善经济学理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这一过程的寻觅中,随着实践问题的不断出现和逐步解决,从理论上来看,科学理论本身内在的逻辑也随之展现,制度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就是典型例证。
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传统,使制度经济学再度兴起,但是自身观点又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体系,因而遭遇了与旧制度经济学相似的命运。真正帮助制度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工作是由科斯和诺思等人来完成的。
尽管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名称都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核心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过程”和“演进”,试图解释经济制度持续渐变的过程:而科斯的核心概念是“最优化”,力图证明制度安排的最优结构的状态。科斯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欢迎,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主流经济学的修正与融合上取得了胜利。科斯在观念上的创新性研究,从基本概念、分析框架、方法论到对问题情境的关注,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诺思认为制度包含着稳定和变化的双重含义。其一是制度总是保持其相对稳定性,至于制度为什么保持相对稳定,新制度学派认为主要是因为构成制度的非正式规则或曰习惯法(不成文法)变化缓慢。诺思认为,尽管构成制度的正式规则经常在变,但由于“支配原理”(快变量受慢变量支配)的作用,制度因非正式规则变化缓慢也维持其稳定。另一重含义是变化,制度一方面保持相对稳定,但又总是在缓慢地变化着,由此诺思引入“路径依赖”的概念。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也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尽管实验方法从一开始应用到经济学中就饱受诟病,但是,也许是受到实验心理学的影响,因为二者都同样是面对人的心理的研究,都涉及到对人类偏好的测度,因而,实验心理学的确立对经济学引进实验方法无疑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实验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甚至改变实验得以进行的各种假定前提。”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设计一些场景和规则来看实验者的决策与反应从而做出一些判断,是对情境的设计和分析的过程。
在制度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环境或者情境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这两个研究方向上是把情境作为内生变量来看待,并辅以实验数据运算、处理和分析,以此作为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的重要依据。其实,经济学的这一制度的分析和实验方法的使用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尤其是与科学发展是同步的。下面我们就借助对数的演变的追溯,以及所投射出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研究与人的研究的一致性,以此说明科学与人文相统一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如此看来,我们借助于大数据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也就有了历史与逻辑的依据。
三、数的嬗变:关于自然界和人的研究相统一的逻辑演进
最早对数及数字的系统认识,并且把对数的认识提高到一定的高度的是著名的数学神秘主义的代表毕达哥拉斯,他的“万物皆数”的理念,主要是在宗教的层面上对数的高度重视和认知,即虔诚之心供奉数字。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米利都学派的祖师泰勒斯将希腊哲学引向“重智”,将希腊心灵引向理性思维和自然界。泰勒斯把对知识的重视提升到神奇、倾慕和景仰的地步,“把对自然界的认识从狭隘的技术、工艺规律提升到文化层面,使它成为代表基本价值的追求由是鼓励、激励其他聪明才智跟随他的踪迹,建立希腊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传统。”尽管这不能单纯地归因于泰勒斯的功劳,而应该与希腊神话的结构、特征、机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泰勒斯独到的眼光,
泰勒斯的学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数学和天文学的探究,以及在研究“原质”时讨论宇宙起源与生化过程的猜想,由此激发了思辩研究,还有后来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等的研究,尤其是后者的“流变说”犀利地摧毁了希腊哲人以往的对事物的表面肤浅的认识,由此激发了爱利亚学派“存有”(Being)哲学,并且直接影响柏拉图走向“理念”(Idea),即对恒久不变的世界的探索。从恩培多克勒开始,自然哲学不再仅仅用数学和猜测来完成,而是进入具体的推理和观测阶段,这成为天文学的重要基础。此时,“数”的含义也从毕达哥拉斯的纯
“数”字的含义,扩展到数或者数字的比喻意义之下的作为事实证据的数据。
无论是雅典学园或亚历山大学宫,科学与人文是始终并存,彼此浸润,互相激励,从未分开过。在《对话录》中哲学、宗教、神话和科学探索浑然一体,成为文、理交融的典范,罗马时代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自然之本质》六卷长歌,尽管在学宫时代,科学逐渐从哲学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是从当时的学术环境来看,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科学家、哲学家仍然在一起研讨论辩,“文”“理”同样构成西方文化整体的要素,缺一不可。通过《蒂迈欧篇》以及柏拉图其他篇章所宣扬的思想,科学、宗教、哲学三者乃得以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成为西方文化学术传统的主流。在罗马时代,希腊科学经历了四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更加坚强而有韧性,能够经历得起风霜而继续生存。
希腊强大的科学传统的植入,是与毕达哥拉斯对“万物皆数”的理念的极端推广有直接的关系。为近代科学传统拉开了序幕。“……毕派所首先发现,而柏拉图所发扬光大的宗教和科学之结合,亦即永生追求与宇宙奥秘探索的相通。这一结合为原始的希腊宗教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比前远为高超奥妙的境界,同时也为数理天文的探究产生了绝大动力。”“永生追求”的人生目标与“宇宙奥秘探索”的相通,恰恰就是宗教与科学的相通,人生追求与科学研究相一致。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推动下,科学与哲学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在文化土壤中科学与人文是本质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在17—18世纪发生了一场人类智识的革命,被认为是继文艺复兴之后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其范围几乎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使得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一过程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此时期为启蒙时代。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这一时期:“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