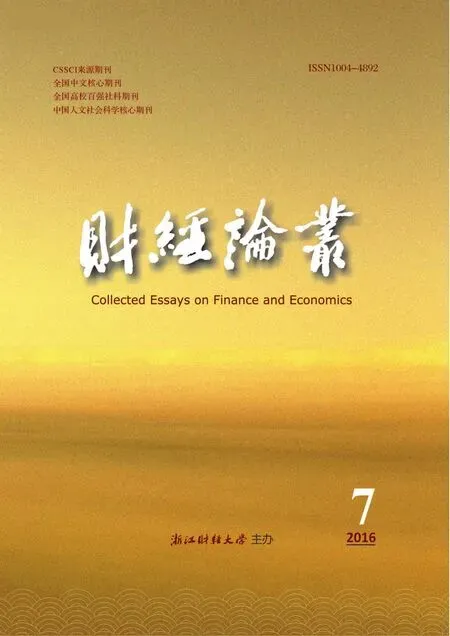出租车数量管制、经营模式与专车规制
商 晨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出租车数量管制、经营模式与专车规制
商 晨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专车受到非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出租车需要接受政府监管而专车不用。本文从出租车数量管制入手,通过构建包含管制数量、监管成本、代理层级的委托代理模型对出租车行业改革和专车发展进行分析,认为监管技术、监管成本、出租车数量都会影响出租车经营模式,政府对专车行业应当从提高专车司机投机成本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两方面来进行规制。
数量管制;经营模式;专车规制
一、引 言
最早的专车公司Uber 2010 年诞生于美国旧金山,2014年年初进入中国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专车公司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搅动了沉寂已久的出租车市场,使出租车市场改革重新受到关注。但专车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和大多数专家民众都认为,专车使乘客拥有便捷优质的出行选择,打破了出租车市场的垄断,不应急于否定[1];但地方的行业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都认为专车是黑车,应当坚决取缔,媒体上也经常出现专车车辆被查扣甚至公司被查封的消息。不同群体对专车的态度反差如此大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新事物,人们对专车的属性还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要想对目前“野蛮生长”的专车制定必要的行业规范,既要尊重市场的客观需求,也要避免不合理的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前提是要对专车的客观属性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专车与出租车是“近亲”,对出租车行业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专车的深入了解。本文将从解释出租车行业数量管制的原因入手,建立一个多层级委托-代理模型,通过比较静态方法分析最优的出租车管制数量的决定因素,对出租车行业经营模式的变化规律进行探究,并且讨论政府对专车规制所应该着眼的方面。
二、出租车数量管制和经营模式的理论分析
出租车虽然比公交车、地铁等典型的公共交通方式具有更强的竞争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强、负外部性、交易成本结构特殊等市场失灵问题,完全依赖市场调节会带来社会福利和市场效率的损失,所以必需由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管制[2][3]。在世界大多数城市,出租车运营都要经过政府的授权,受到严格的管制。
政府对出租车管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质量管制。各地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在三种手段的选择和组合上存在较大差别。在质量管制方面,由于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间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政府对出租车的服务进行质量管制是必需的,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地方政府不对出租车的运营质量进行必要的控制;对于价格管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分歧:有一部分研究认为可以放开出租车价格管制[4][5]。实践中也有一些城市尝试放开价格管制,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几年出现的打车软件加价叫车其实也是一种价格管制的变相放开,但这也给一些不熟悉移动互联终端的群体带来更大的不便。总体来看,价格管制仍然是大多数地方政府所选择的政策。
出租车管制中争议最大的是数量管制。数量管制减少了行业供给,增加了打车难度,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很多大城市的打车难问题非常严重,公众对此意见很大,要求政府放开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呼声一直很强烈。但在理论研究中对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态度却存在较大分歧:大多数意见认为数量管制造成了垄断,降低了社会福利,所以应当取消数量管制[6][7][8][4][9][10]。但Schroeter(1983)、Gaunt(1996)、Yang et al.(2005)等一些研究认为放松数量管制不会使福利增加,甚至弊大于利,出租车数量管制是合理的[11][12][13]。Moore和Balaker(2006)[14]通过对之前的28篇研究出租车市场管制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其中有19篇支持放开管制,2篇认为结果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还有7篇认为放开管制弊大于利。从实践看,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城市曾经放开出租车数量管制,但随后均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如司机工作时间增加,收入减少,司机为此私自涨价、挑客、绕道等问题日益严重,所以这些城市又重新开始实行出租车数量管制[15][2][16]。来自理论和实践的证据都表明,单纯强调数量管制弊端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应当对出租车数量管制背后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1.对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解释
(1)政府俘获理论
政府俘获理论首先由1971年被斯蒂格勒提出,后由匹兹曼等人发展完善。该理论认为政府管制部门是经济人,政府管制的权力可以产生租金,特定利益集团可以对管制部门进行寻租,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双方共同分享管制带来的垄断利润。Barrett(2003)基于政府俘获理论,解释了爱尔兰政府在1978-2000年间冻结出租车牌照发放,但2001年利益集团的努力没有奏效,政府取消了出租车牌照的冻结[17]*爱尔兰于2009年又重新恢复了对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张树全(2009)同样基于政府俘获理论,认为国内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机构庞大,需要依靠收费来养人。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管理的成本低而收益高,所以地方政府倾向于加强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18]。卢正刚 等(2007)进一步认为,在西方健全的法律体制下政府俘获的现象比较少,但在法制有待健全的转轨国家,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的可能性则比较大,合肥市的政府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间存在明显的利益链条,管理部门具有明显的管制俘获的特征[19]。
政府俘获理论的确可以对管制部门执着于数量管制进行部分解释,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难以对管制解除后又重新恢复的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爱尔兰2000年取消数量管制,2002年出租车数量增长到2000年的3倍,牌照价格由8万爱尔兰磅下降到5千爱尔兰磅[17]。出租车行业没有高额利润,不会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就不会被利益集团俘获来进行管制,但爱尔兰政府却在2009年重新冻结了出租车牌照的发放,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也出现过。其次,很多实施数量管制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没有从管制中分享垄断利润。2004年以前国内很多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的出租车牌照投放方式为审批制,只要申请人的相关经济能力比如车辆数量、运营资金、办公场地等通过审查,既可无偿获得经营权[20]。并且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台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政策”。
(2)出租车经营具有外部性
出租车经营具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造成的社会边际成本超过运价。按照经济学理论,社会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才能实现社会净福利最大,所以政府需要对出租车的数量进行限制,来确保市场出现有效率的结果[7][10][13]。
政府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可能有缓解交通拥堵和控制污染的考虑,但应当不是主要原因。以上海为例,1996年上海率先在国内严格控制出租车数量,但上海决定是否投放新的出租车牌照的依据并非交通拥堵指标,而是出租车满载率。当满载率持续高于70%时,政府才增加出租车的数量[21]。出租车满载率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政府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缓解交通和环境的压力。
(3)数量管制可以简化政府对司机的监督
Cairns 和Liston-Heyes(1996)认为,在高度分散的出租车市场上,政府在监管司机提供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及设备的良好维护方面的行为时,存在很强的信息不对称,司机在提供服务时很容易出现“缩水”(shrink)的投机行为,在大城市中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如果出租车市场是自由进入的,出租车服务的价格仅仅和司机的机会成本相等,司机就有比较强的投机动机。但是如果服务的价格能超过机会成本,司机有投机行为时,暂停他运营的权利可以使他承担损失,政府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可以使出租车运价超过机会成本,从而可以起到对司机的约束作用,简化政府监督[15]。
这种观点既可以从理论上解释政府坚持数量管制的原因,在逻辑上与政府将满载率作为数量调整的依据也是一致的,但认为数量管制会使价格超过机会成本是不正确的。政府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后,出租车服务价格会提高,但相应地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会提高。寻租的结果最终会使租金完全耗散,即运营价格等于机会成本,牌照拥有者的利润等于零。
基于Klein和Leffler(1981)提出了可自我执行契约的理论[22]。本文认为,政府通过对出租车数量的管制可以使拥有牌照的企业或个人获得更高的经营收入,发生投机行为后政府如果收回特许经营权或者限制对其投放新的经营权,较高的运营收入就成为司机投机的机会成本。出租车数量控制越严格,运营的收入越高,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数量管制就成为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有效管理,保障公共利益目标的手段之一。
在国内一些城市的出租车管理政策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逻辑。2006年4月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意见》规定,出租车公司竞标出租车特许经营权需要以规范经营、安全运营、服务质量为主要竞标条件,公司和政府要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如果不能达到服务承诺,有可能被收回特许经营指标。上海的出租车公司的服务质量和诚信的数据,直接决定出租车公司的发展。上海的出租车牌照不招标,每一轮更新都是以公司服务质量投诉量来决定本轮更新比例[23],成都的政策和上海相似[24]。由此思路出发,我们还可以解释其他的出租车管制措施,比如伦敦的出租车没有数量管制,但服务秩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Cairns 和Liston-Heyes(1996)[15]的观点对此难以进行解释,但从司机投机成本的角度就不难理解。在伦敦要取得出租车运营资格需要参加非常严格的执照考试,考试的准备时间至少要一年[6]。出租车司机如果欺骗乘客,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吊销执照[21]。司机之前为考试花费的大量时间就会成为沉没成本,司机自然会约束自己的投机动机。所以伦敦虽然没有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但这种手段和数量管制本质上一样,区别仅在于伦敦司机投机的机会成本是前期投入的大量时间,而数量管制下司机投机的机会成本是未来可以获得的高额收入。
2.出租车经营模式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除事后处罚机制以外,管理机构对出租车进行一定的事前监管也是必要的,这是通过不同的出租车经营模式来实现的。下文将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对几种出租车经营模式进行归纳,由于资料所限,讨论仅限于国内的经营模式。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在一种契约关系下,一个人或更多人聘用另一人代表他们履行某些服务,他们间就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5]。出租车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关系到公共利益,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效用函数,所以政府与出租车司机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代理人的司机,行动目标是自身收益最大化,而非委托人(政府)的收益最大化,而且出租车行业具有比较强的个体劳动属性,司机具有很强的信息优势,这也是政府应当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监管的原因。
在具体的委托代理形式上,政府可以选择单层的代理关系或者多层的代理关系。如果出租车数量比较少,政府将出租车运营权交给司机,直接对出租车的运营进行监管,就属于单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但一些大城市出租车数量比较多,政府直接监管存在很大困难,往往把部分监管责任委托给出租车公司,形成政府与公司和公司与司机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这时,政府作为最终的委托人并非不承担对司机的监管责任,而是与公司分摊监管责任。一个例证是,无论国内那种出租车经营模式中,乘客如果对出租车服务不满意,可以拨打出租车公司的投诉电话,也可以直接向政府的运管部门进行投诉。
不同经营模式的区别在于,政府和公司间监管责任的分摊比例是不同的。国内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个体经营制(温州模式)、挂靠经营制(天津模式)、承包经营制(北京模式)、企业经营制(上海模式)。我国85%以上的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与北京模式基本相同[26]。个体经营制中,政府和司机间是单层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将出租车运营权交给个人,并且直接对司机进行监管,所以政府的监管责任比例是1。其余三种经营模式中,政府都将部分监管责任委托给出租车公司。
挂靠制中出租车公司基本无偿从政府获得特许经营权,然后将车辆加价转卖给个人,特许经营权也随之转给个人,但司机的运营需要挂靠公司,由公司负责代缴税费、培训、年检等,个人向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挂靠制比个体经营在组织方式上前进了一步,有专人传递信息、组织学习、代办日常事务、督促安全生产[27]。但总体来看挂靠制中公司承担的监管责任非常有限,主要的监管责任还是由政府承担。
在承包制中,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由出租车公司所有*北京承包经营的出租车原为个人出资购买,但1996年以后政府要求公司回购车辆,现承包经营出租车的所有者为公司。,个人与公司间是承包关系,个人通过份子钱的形式向公司付费使用出租车经营权。公司虽然可能无偿获得经营牌照,但要向政府承诺监管义务,如果公司达不到规范、安全和服务质量等承诺,将被取消特许经营权。所以相对于挂靠制,公司对司机的监管更加严格。
在企业制中,出租车经营牌照和车辆也为公司所有。但与承包制不同的是,司机与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双方是劳动雇佣关系,驾驶员按照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营运,收入按任务定额和服务质量等各项指标考核后确定。出租车的维修、保养、投诉处理等都由公司统一办理,司机只需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提供服务,公司对违反公司有关管理制度的驾驶员照章处罚直至解聘。相比其他经营模式,公司制对司机的约束更多,奖励和处罚制度更健全[27][23]。
三、模型设定与比较静态分析
作为理性人,政府通过出租车的数量控制和经营模式选择的目标,是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
max(U-C)
(1)


(2)
上文已分析,政府对出租车司机实施监管需要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由此会产生代理成本C。具体来说代理成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首先,尽管政府可能将部分监管责任委托给出租车公司,但仍然需要对出租车司机的运营承担一定的监管职责,会给政府带来监管成本C1;其次,由于出租车运营中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约束可能的投机,政府需要通过出租车数量管制来提高投机的机会成本,但数量控制会造成出租车市场出现短缺,民众在高峰期打车等候时间增加,会对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政策产生不满,由此给政府带来成本C2;再次,由于出租车运营有比较强的个体劳动性质,委托人和代理人间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司机仍然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甚至出租车公司也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和司机合谋损害政府的利益,由此给政府带来成本C3,则有:
C=C1+C2+C3
(3)
1.政府所承担的出租车监管成本与监管的出租车规模成正比,而同样的出租车规模,多层代理中政府监管成本就比单层代理中要少,而且同样的代理层级下政府所承担的监管责任比例越小,监管成本也越小。此外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有效监管的单位成本的变化,政府的监管成本还和对每辆出租车进行有效监管所需的单位成本有关,考虑以上几方面因素,则有:
(4)
其中,k为政府选择的代理层级,k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在现有的出租车经营模式中,k等于1或者2,但在第四部分会讨论k进一步增加的情况。。n1为政府进行数量控制的出租车数量,n1≥0。α为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在每一级代理中,所承担的监管责任比例,α∈(0,1]。t为对每辆出租车进行有效监管所需要的单位成本,t∈(0,+∞)。假设随着委托代理关系层级的增加,政府监管成本C1呈指数下降。
监管成本随政府责任比例增加而增加,随代理层级增加而减小,但始终为正,随出租车数量增加而增加,并且边际成本也上升,对单位出租车进行有效监管所需的成本增加,政府监管成本也会增加,并且单位监管成本越高,政府越倾向于通过提高出租车违约成本的方式约束司机,政府直接监管成本上升的速度要慢于单位监管成本上升的速度,函数具有以下特征:
2.假设出租车市场出清时,公众打车比较容易,对出租车行业满意度较高,政府效用能达到所期望水平。数量管制所带来的成本与出租车短缺程度正相关,则有: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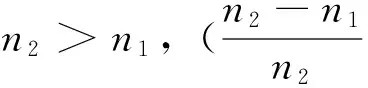
3.政府与司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成本主要由司机运营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所导致,道德风险行为与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正相关。出租车数量越多,双方信息越不对称,且司机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越小,司机越有可能选择投机;政府与司机间代理层级越多,信息之传递过程中“失真”的可能性越大,政府与出租车司机间信息越不对称,代理成本越高。此外,需要对司机进行有效监管的成本越高,司机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越困难,道德风险行为会越多,代理成本越高,并且上升速度会快于单位监管成本上升的速度。则有:
(6)
将(2)-(6)式代入(1)式,所得政府净收益函数对n1求一阶偏导数,并使结果等于0,可得最优的出租车管制数量为
(7)



同理,将政府净收益函数对k求偏导,并使结果等于0,可得最优的k*满足以下关系:
(8)
(8)式中k*对t求一阶导数,可得
(9)
(9)式分母大于0,所以(9)式符号由分子部分的符号决定。由α的取值可知(-lgα)>0,所以分子部分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将(9)式分子等于0的α值记作α′,则有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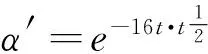

由以上分析可得:


四、模型结论的分析与讨论
专车提供的服务与出租车基本相同,专车行业的运营效率也会影响到政府的效用函数,所以政府和专车行业间事实上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前文的模型也可以用于分析专车。
1.监管技术创新导致规模扩张
由命题(Ⅰ)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出租车进行监管的单位成本下降,城市出租车的最优数量规模应该增加。
以上海出租车发展为例,在1996年以前上海没有对出租车市场实施严格的数量管制,1992-1995年出租车数量由1.2万辆增加到3.8万辆(2013年数量也不过4.9万辆)。但监管技术却没有跟上规模扩张的步伐,由于国产的计价器质量比较差,司机普遍不愿意用计价器而是和乘客议价,乱收费、拒载等问题非常普遍。时任市长朱镕基亲自命令从国外进口几千台计价器,还统一从国营上海仪电厂生产计价器,强制要求出租车使用,否则“抓住两次就吊销营运证”,计价器的使用使乱收费、拒载等问题逐渐被压制住[21]。显然,监管技术创新使监管成本降低,这为出租车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
技术创新导致监管成本降低同样是专车获得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专车进入中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发展的速度非常惊人,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大众出租车公司成立于1988年,目前拥有9000余辆出租车*数据来自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官网。,而2014年7月才出现的“一号专车”,在各大城市提供的车辆就已经超过1万辆*数据来自快智集团1号专车官网。。专车规模的快速扩张并没有导致企业对运营质量失控,相反,专车司机的运营要接受严格的监督。以滴滴专车为例,企业要求司机统一着装、全程标准化商务礼仪服务,上下车主动开关车门、提行李,车内备有免费充电器、饮品、干湿纸巾、雨伞、儿童老人专属靠垫等出行必备用品。公司对司机会进行定期的安全培训,还规定了多条违规项目,如果司机迟到、没有使用标准话语、没有配备饮用水、因任何原因要求乘客取消订单等,都会受到相应处罚,轻则被警告,重则解除合作。专车平台能够对数量庞大的专车司机进行严格监管的基础就是已经比较普及的GPS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
2.出租车数量增长与出租车经营模式变革
由命题(Ⅱ)可知,出租车最优数量与政府在监管责任中的比例成反比,如果政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将更多的责任委托给出租车公司,那么最优的出租车数量就能够增加。
设个体制、挂靠制、承包制、企业制中政府的监管责任分别为α1、α2、α3、α4,由2.2分析可知α1=1,αi<1(i=2,3,4),且α1>α2>α3>α4。
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出租车数量的增长,出租车的数量也需要增加,此时,政府监管责任比例较高的个体经营和挂靠经营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政府应当选择监管责任比例更低的经营模式来适应这种变化。温州是个体经营的典型,温州市区3770辆出租车中,个体经营的占88%。在2010年浙江省的出租车服务质量评比中,温州名列倒数第二,有消费者因为出租车服务质量向温州运管部门投诉时,得到的回复是10天后才处理。2013年12月由温州市政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租车行业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温州出租车即将由个体经营模式主导,逐步转变为由公司主导的经营模式,鼓励出租车企业回购个人出租汽车。其原因用运管局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的话说,就是“政府部门要管理这么多出租车确实有困难……温州模式这样一路走来,纯粹的个体经营很散很乱”[28][29][30]。类似的问题在实行挂靠经营为主的天津也有,“此种(天津)经营模式体现的管理难点是,尽管出租车辆挂靠在不同公司,但由于实行的是个体经营,管理部门直接面对的是众多经营个体,管理模式较松散,管理困难大,难以到位”[31]。
以承包制的代表城市北京和企业制的代表城市上海作比较,两地常住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北京出租车数量为6.6万辆比上海4.9万辆更多,但上海的出租车口碑相对要好很多,车辆干净整洁,拒载与绕路等问题不常发生,而且在上海打车并不那么困难[21]。
3.监管成本、责任比例与代理层级
随着技术、制度和乘客维权意识的提高,对每辆出租车进行必要监管的单位成本会逐渐降低。举例来说,在传统出租车服务中,乘客通过将司机所选择的路线与手机导航软件推荐的路线进行对比,即使对城市道路不熟悉,也可以容易地判断出司机是否绕路;运管部门要求出租车运营时必须放置司机服务监督卡并且使用计价器,服务监督卡和计价器打印的发票上都有司机和车辆的信息以及投诉的方式,这给乘客维权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总体来看,对出租车进行监管的单位成本在逐渐降低。
由命题(Ⅲ)可知,在单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最优代理层级应当与出租车单位监管成本反方向变化,随着监管成本的下降,最优的代理层级应该增加。
温州的个体经营模式就是单层的委托代理关系,温州已经确定经营模式的改革方向是企业制,实际就是在政府和司机之间增加出租车公司这一级代理关系。这个结论与3.2的结论是一致的。
同样由命题(Ⅲ)可知,双层委托代理中政府的责任比例较高时,最优代理层级也应与出租车单位监管成本反方向变化。挂靠制中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监管责任,但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挂靠制中发展出新的代理层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对政府来说,代理层级增加和政府责任比例降低本质上相同,都是将更多监管任务让别的机构承担。但增加代理层级显然要比在现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调整责任比例更复杂,所以现实中的经营模式改革都选择降低政府责任比例而不是增加代理层级。
由命题(Ⅳ)可知,当政府监管责任比例较低时,代理层级与监管成本应当同方向变化,随着监管成本的下降,代理的层级应当减少,如果监管成本上升,代理的层级应当增加。
目前国内出租车经营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企业经营制,这种模式相对于其他几种模式,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目前还没有观察到企业经营制发生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但我们不妨假设,如果为了应对来自于专车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出租车也开始采用基于“互联网+”的监管技术,监管者仿照专车平台进行运作。此时单位监管成本出现大幅降低,保留出租车公司这一代理层级将不再有明显的必要,政府完全可以成立一个规模不大的监管机构,直接对出租车运营进行监管。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看,既然轻资产的专车平台可以做到对大量的专车进行有效的监管,政府部门做同样的事情也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所以命题(Ⅳ)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
五、政策建议
政府对出租车的监管也可以采用各种比较成熟的新技术来降低监管成本,将能够使有效监管的出租车数量大幅增加,政府就可放松对出租车的数量管制,使市民能享受到更便捷的出租车服务。
专车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事物,专车到目前的发展是游离于政府监管以外的,但专车与政府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接受必要的监管。套用我们的模型来分析,目前专车运营中,政府的责任比例α基本为0,但这个比例应该适当提高。由命题(Ⅱ)可知,α提高时,最优的行业规模数量应该降低。目前专车行业的扩张似乎没有边界,只要有一辆车一台智能手机,接入了专车平台就可以上路接单。这样无序的状况应该有所改变,未来专车在政府的规制下,行业的规模应该得到控制,车辆和司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以参与运营。
目前政府给专车的运营划出一条红线:严格禁止私家车接入专车平台运营,专车车辆必须来自租车公司,司机必须由劳务公司派遣。必须由劳务公司派遣司机其实就是增加一个代理层级,由政府与专车平台、专车平台与司机两个代理层级变为政府与专车平台、专车平台与劳务公司、劳务公司与司机三层代理关系。目前专车的委托代理关系中α值接近于0,如果出现单位监管成本上升的情况,代理的层级应当增加。但这种情况现实中恐怕不会出现,目前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普及,在没有新的革命性的监管技术出现之前,监管成本会大体保持稳定,并且随着技术和制度的边际创新而逐渐降低,不会出现单位监管成本上升的情况。所以在专车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增加劳务公司这一新的代理层级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新产权理论出发,这种制度安排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司机驾驶租车公司的车辆,司机有车辆使用权,但车辆使用的残值不归他,他没有足够激励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车辆,车况反而会比较差。
从专车服务在国内一年多来的发展情况看,政府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管,但专车公司对司机的管理提高了乘客的体验,专车服务在大众中享有比较好的口碑。但这恐怕不会是长期均衡的结果,专车作为新事物需要提高知名度、拓展市场,所以会尽心尽力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给乘客发各种补贴、红包,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当企业已经打开市场,有稳定的盈利时,也能主动保证比较高的服务质量,并且进行大幅度的让利。所以政府对专车运营的质量和价格进行必要的规范,从长远看是必须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政府对专车的监管应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司机投机的机会成本,使司机作为经济人主动克制自己投机的动机,而对司机是否隶属于公司不必进行规定。伦敦有超过一半的的出租车是个体司机,但并不妨碍伦敦出租车的服务质量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高昂的投机成本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对司机的驾驶技术和车辆的车况应当设置比较严格的条件,可以对专车司机一年当中的违章次数和需要承担责任的事故次数做出规定,如果超出就取消专车运营的资格。在专车进行车辆检验时也可以设置更高的标准,并且提高车检的频率,这些措施就可以保证车辆有比较理想的车况。
[1]王伟健. 网招“专车”前路如何[N]. 人民日报,2015-1-08,015.
[2]王智斌. 国内外出租车经营管理模式研究——以数量管制和经营者准入资格为核心[J]. 金陵法律评论,2014,(1):217-229.
[3]袁长伟,吴群琪. 国际出租车管制模式与改革启示[J]. 经济体制改革,2013,(6):151-155.
[4]Williams,DJ.Theeconomicreason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AComment[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80,(14):105-112.
[5]Seibert.Taxideregulationandtransactioncosts[J].EconomicAffairs,2006,(6):71-73 .
[6]Beesley,M.E.Regulationoftaxis[J].TheEconomicJournal,1973,(83):150-172.
[7]Shreiber,C.Theeconomicreasons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75,(9):268-279.
[8]Coffman,R.B.Theeconomicreasonsforpriceandentryregulationoftaxicab[J].JournalofTransportEconomicsandPolicy,1977,(11): 288-304.
[9]Toner,J.P.ThewelfareeffectsoftaxicabregulationinEnglishtowns[J].EconomicAnalysis&Policy,2010,(40):299-312.
[10]Cetin,T.,Eryigit,K.Y.EstimationtheeffectsofentryregulationintheIstanbultaxicabmarket[J].TransportResearchPartA,2011,(45):476-484.
[11]Schroeter,JohnR.Amodeloftaxiserviceunderfarestructureandfleetsizeregulation[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83,(14): 81-96.
[12]Gaunt,C.Theimpactoftaxideregulationonsmallurbanareas:SomeNewZealandavidence[J].TransportPolicy,1996,(2):257-262.
[13]Yang,H.,Ye,M.,Tang,W.H.,Wong,S.C.Regulatingtaxiservicesinthepresenceofcongestionexternality[J].TransportationResearch,2005,(39): 17-40.
[14]Moore,A.T.,Balaker,T.Doeconomicsreachaconclusionontaxicabderegulation?[J]EconJournalWatch,2006,(3):109-131.
[15]Cairns,R.D.,Liston-Heyes,C.Competitionandregulationinthetaxiindustry[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6,(59): 1-15.
[16]徐康明,苏奎. 出租车改革当借鉴国际经验[N]. 南方日报,2015-05-14,GC02.
[17]Barrett,S.D.Regulatorycapture,propertyrightsandtaxideregulation,acasestudy[J].EconomicAffairs,2003,23(4):34-40 .
[18]张树全. 政府管制动机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影响[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146-150.
[19]卢正钢,赵定涛,杨敏. 合肥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效应及其成因解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07,(3):57-62,124.
[20]黄凤鸣. 出租车行业特许经营权研究[D].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1]陈中小路,陈伯英. 上海出租车的管制逻辑 “最不坏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N]. 南方周末,2013-06-06.
[22]Klein.,B.,leffler,K.B.Theroleofmarketforceinassuringcontractualperformance[J].TheJournalofPliticalEconomy,1981,(89): 615-641.
[23]李阳阳. 四张药方,治好上海五万的士[N]. 钱江晚报,2013-1-30,A8.
[24]徐雁行. 成都市员工制出租车企业驾驶员管理研究——基于心理契约视角[D]. 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2.
[25]Jensen,M.C.,Meckling,M.H.Theoryof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76,(4):305-360.
[26]柴宝亭. 我国出租车经营模式分析[J]. 汽车与安全,2013,(8):48-53.
[27]凌显峰. 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分析及其适应性评价[D]. 吉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8]甘凌峰. 温州出租车官司集中爆发[N]. 都市快报, 2011-5-17,A21.
[29]刘星.温州改革出租车个体经营模式[N]. 中国青年报,2014-1-03,07.
[30]欧阳潇、陈越、叶卉. 探秘温州出租车乱象 拨打投诉热线称10天后才处理[N]. 温州晚报,2014-8-29.
[31]苏晓梅. 拒载不拒载 谁说了算?[N]. 天津日报,2013-8-14,009.
(责任编辑:风 云)
Quantity Control and Business Model of Taxicab ,Regulation of Tailored Taxi
SHANG 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censure of tailored taxi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axi i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while tailored taxi is no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orm of taxi and development of tailored ta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antity control of taxi. Through the analysis with a principal-agent model which includes quantity control, supervision cost and supervision levels, we find that the supervision technology, the supervision cost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taxi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taxi business model.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drivers’ speculative behavior and raise threshold to supervise tailored taxi.
quantity control;business model;regulation of tailored taxi
2015-1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BJL001)
商晨(1977-),男,山西太原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F294.3
A
1004-4892(2016)07-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