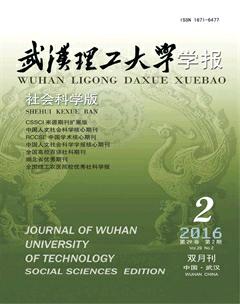刘师培文学起源观考论
黄春黎
摘要:刘师培以“古学出于史官”为核心,系统地构建了他所认为的学术是出于官守的理论主张,对其文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加上学术发展的趋势,刘师培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上古社会的实际,认为后世学术出于史官,从而系统解决了孔子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刘师培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起源的问题,认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文学与六艺、诸子乃是同源而异派,他的这一看法对于提高文学的地位以及认识文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刘师培;古学;史官;文学起源;巫祝
中图分類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20
晚清民国之际,各种西学思想渐次传入中国,时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而传统学术既受到西学的冲击,同时又受到西学影响,中学与西学的融合、会通也在不断发展。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他们都是出身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学术底子,但又吸收西学,借以纵论时政。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在这一时期是杂糅在一起的。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着力解决中国学术起源的问题,并因此写作了大量文章,认为学术出于“官守”,即相关部门官位的职守,虽是继承前人之说,但却推陈出新,创获极多。在此思潮影响之下,加上他兼有文人的身份,因此对文学的起源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其中尤以《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影响最大。客观来说,刘师培的文学起源观是其中国学术起源相关论述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揭示刘师培文学起源观的价值。
一、刘师培“官守论”与晚清学术思潮
众所周知,清代学术的发展以朴学最为大宗,然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极具经世价值的今文经学复又兴起,尤其是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与康有为的政治观念一致的是,康在学术上也极其推崇孔子的地位。他认为儒学为孔子所创,“儒为孔子所创教名”[1]107;认为“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1]96,甚至认为纬书也是孔子所作,“六纬,孔子穷极天人之书”[1]96,“孔子作纬,刘歆作谶以乱之,后人攻谶并及纬,大谬”[1]105;至于诸子出于孔子,如“老子之清虚柔退出于孔子,墨子兼爱亦出孔子”[1]97,“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之学只改得半部《春秋》”[1]93,“庄子乃孔子后学而兼老学者也”[1]94,总之,六艺、诸子均出自孔子。客观而言,康有为论学,有其政治目的,于中国当时政治有益,但在学术认知上未免太过主观。因此,他的学说在当时就遭到诸多学人的反对。有见于此,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通过撰文对康有为之学说加以反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仍然在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并倡立孔教,实际上康有为“特利用孔教,求自为当时之教主而已”[2]4567,他晚年的主张更趋近于专制、颟顸,必然遭到革命派的抨击。章太炎于1906年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诸子学略说》一文,主张“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3],继承前人之说,但又有新的发展。相对而言,刘师培的相关著作在数量上则更多,也更为系统。
刘师培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大学者,他的研究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学习西学而勇于开新的一面。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刘师培尤其热衷于探讨中国学术之起源问题,他能利用中国古文献,又结合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立论深邃,见解独到。刘师培《甲辰自述诗》之五十三自注曰:“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4],因此他的论述能够密切结合西学,从而推陈出新。刘师培的相关论述主要见于《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期)、《古学起源论》之《论古学出于宗教》(《国粹学报》第8期)、《古学出于官守论》(《国粹学报》第14、15期)、《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7期)等文章中,与此相关者尚有《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国粹学报》第13期)、《舞法起于祀神考》(《国粹学报》第29期)等文章。刘师培的核心观点是:一切学术出于史官。由此出发,旁及巫、祝之官及祭祀、宗教活动。刘师培诸多有关文学起源的观点,实亦包含其中,而专论文学者则是《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1910年)一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事实上,厘清中国学术起源的问题,方能解决孔子与六经、六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为方便论述,我们将刘师培的一系列主张统称为“官守论”,涉及具体问题则单称。
二、刘师培“官守论”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刘师培在学术上是与康、梁等人针锋相对的。刘师培撰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孔学真论》等文章,尤其是《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一文,是在蔡元培《孔子生日纪念会演说词》基础上写就的。《演说词》开篇即言,之所以纪念孔子,“不过以孔子为吾中国民族大有学问、大有道德者”,“非如流俗以此为迷信宗教之仪式也”[2]4567,刘师培在《书后》中也指出:“孔学传于中国,二千余年,而误者多称为宗教。倡‘保教者,南海康氏之说也;……鄙人平昔宗旨,力主孔子非宗教家之说”[2]4564,因此刘师培始终是反对孔子宗教教主地位的,并直接指向康有为。刘师培既是革命人物,但他又是一位学者,因此即使是政治的斗争,他也善于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而核心在于学术起源、诸子起源、孔子地位等诸多问题。这一时期的学术问题,往往涉及政治问题,尤其在国粹思潮兴起之后,国粹与革命结合,相应的学术探讨更趋于向深度发展。客观而言,这一时期,学术推动革命,而革命也在推进学术。
刘师培的相关论述以《古学出于史官论》一文最为核心,也最为详尽,而其他文章或早于此或晚于此,亦有涉及。我们以《古学出于史官论》为主要依据,可以窥见刘师培的主要观点。
首先,刘师培认为学术出于史官。
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且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学出于史,有明征矣。……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4487-4488
刘师培在方法上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他在文章开头指出,“西儒斯宾塞有言:‘各教起源,皆出于祖先教”[2]4486,所谓祖先教就是祖先崇拜,外在表现为对祖先进行祭祀、纪念,因此刘师培文中注明:“观斯氏《社会学原理》,谓崇信祖宗之风气,初民皆然。又法人所著《支那文明论》云:‘崇拜死者,乃支那家族之主要也。而其特色,則崇拜祖先是也”[2]4486,在当时,因祖先崇拜产生法、书、礼,记录者则为史官,实际上史官成为当时执掌文事的最为重要的官员,因此刘师培认为“学出于史”,有其合理之处。
其次,六艺、九流、术数、方技均出于史。
天人之学,史实司之。司天之史,一司祭祀,即古人“巫史”、“祝史”并称者也,墨家之学本之;一司历数,即古人“史卜”并称者也,阴阳家、术数家本之。司人之史,亦析二派。一掌技艺。兵、农、医药、乐律,艺凭于实;阴阳、五行、卜筮,是为掌技艺之史。一掌道术。明道德者谓之“师”,子书之祖也,儒、道、名、法之学本之,所谓推理之史也;司典籍者谓之“儒”,经、史之祖也,六艺、小学本之,所谓志事之史也,是谓掌道术之史。由是而观,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2]4492-4493
刘师培认为,根据史官执掌的演化分离出各家学术,与《汉书·艺文志》相对应的是,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皆出自史官。
我们发现,刘师培主张学术出于史官,其最为重要的目的乃在破除后人对孔子的迷信,因此他对学术起源的重心,也是要处理好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进而理清儒学的地位。刘师培十分肯定孔子的学术贡献,他在《孔学真论》中认为,“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2]4573,师、儒本有区别,但孔学则兼两者之长。然而“不有史官,则孔子虽有订六艺之心,亦何从而得其籍哉?”[2]4489刘师培认为孔子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承者,但不是后世今文家所言的开创者,尤其所谓孔子作六经的言论,则是刘师培所极力反对的。
六经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述,汉魏以后,以刘勰的《文心雕龙》最成体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5]我们深信六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刘师培作为精于中古文学的学者,对此认识极深,他提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的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是出于客观认识孔子、六经地位的需要,也是个人学术研究的拓展。
刘师培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传统史官论系统化,并直接与时局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重要武器。他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中指出,学术操于史官有两种弊端,即“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有官学而无私学”[2]4496-4497,而“周末之时,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由今观之,殆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耳。一曰反抗下民无学也。……二曰反抗私门无学也”[2]4502,由史官流为诸子之学,实则是反对学术专制而出现的,因此刘师培所认为的史官论,其目的更在指出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端,至于康有为的诸种学说更在其反对之列。因此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实际上也涵括了将文学从六经中解放出来的意图,希望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意义
刘师培在《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指出:
《说文》“祠”字下云:“多文词也。”盖“祠”从“司”声,兼从“文词”之“词”得义。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盖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执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祭祀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2]3959
巫祝皆为祠祭之官,因祭祀所需而擅长文词,所谓文章流别当溯源于清庙之守即缘于此。客观而言,文学艺术的起源确与祭祀、宗教有关。
在早期文献中,巫祝、巫史、祝史、史巫连称极为常见,也说明巫、祝、史在职能上有重合之处。研究表明,巫史在早期社会中的职能非常一致,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一文中认为史较于巫则更理性[6]。如从巫、史二字得义之始来看,巫重于行为,以舞蹈而降神,而史重于记录,则擅长使用文字。如果说中国早期最有知识的人群经历了从巫到史的演变,是有合理之处的。刘师培在《古学出于官守论》中认为:“上古之时,学术之权操于祭司之手,以巫官为最崇”[2]4504,《论古学出于宗教》又谓:“古代司教之职,复有祝、宗、巫、史四官。……古代史官,为一切学问所从出,司历数而兼司祭祀”[2]4478-4479。实际上,巫史是早期最为重要的知识人群,那么说文学出于巫祝之官,与古学出于史官,有其一致之处。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此文只是刘师培所有论著中的一篇小文,但在精神上与其相关的“官守论”文章一致。我们注意到,《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六艺为圣人之作,故不着重考究其起源的问题。至于诸子,一并溯源至于王官,诸子学即王官之学,因此位列六艺之后。《诗赋略》近似后世集部,为纯文学的归类,共分五部而赋居其四,就渊源而论,关于赋,“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7]1756,可见赋与《诗》的关系联系很紧,而关于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7]1756,未追溯其源,但以其能“观风俗,知薄厚”而著录。简言之,歌诗、辞赋为《诗》之流裔,且有相应的政教功能,故列于诸子之后。刘师培认为六艺、九流、术数、方技皆出于史官,那么作《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目的显然是要将文学溯源于官守,改变文学从属于经学的地位,提高了文学的品格。
其次,树立起了广义的文学观,但又十分强调修辞的功用。古人对“文”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刘师培《文说·耀采篇》谓:“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2]2071-2072,上古之“文”逐渐归于纯文学之谓,则是对文字技巧、声色的追求,但对三代两汉之文而言,此时的文学只是一种“杂文学”的状态,因此刘师培所言文学出于巫祝之官,亦就广义的文学而言。之所以认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在于“盖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在刘师培看来擅于词章者可谓早期的文学家,他们所作文字的价值在于实用,刘氏在《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复又言之:“草昧之初,天事、人事,相为表里,故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事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2]1540,显然,文之兴起,一在事神,一在事人,其目的是契合于“用”,而非谓纯文艺的追求,这是上古之事实,因此文学只能溯源于一种杂文学的状态。然而刘师培又强调“文辞特工”,表明他对文辞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因此,他在《文说·耀采篇》中指出:“盖文之为体,各自成家。言必齐谐,事归镂绘,以妃青媲白之词,助博辩纵横之用”,“故史尚浮夸之体,声拟轻重之和,实为文章之正鹄,岂拟小技于雕虫?”[2]2074此从孔子“文胜质则史”一语变化出来,因此可见作者对文采的强调,文词之“多”与“工”需统一。
第三,社会学的视野有助于对早期文学发展史有着更为客观的认识。文学起源之外,关于文学初级阶段的发展问题,刘师培亦有符合社会学认知的判断。《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中指出:“周末得文章正传者,仅墨家、纵横家二家而已。何则?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工于祈祷;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则工于辞令”[2]1540,又谓“要而论之,墨家之文尚质,纵横家之文尚华;墨家之文以理为主,纵横家之文以词为主。故春秋、战国之文,凡以明道阐理为主者,皆文之近于墨家者也;以论事骋辞为主者,皆文之近于纵横者也。若阴阳、儒、道、名、法,其学术咸出史官,与墨家同归殊途,虽文体各自成家,然悉奉史官为矩矱。后世文章之士,亦取法各殊,然溯文体之起源,则皆墨家、纵横家之派别也”[2]1546-1547,刘师培认为文学亦出于史官,而墨家之文尚质,纵横家之文尚华,实际上我们也发现,春秋战国以后之文,辞藻日益受到重视,纵横恣肆之文,自战国至西汉前期,绵延不衰,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已进入到诸侯争霸之时,外交活动愈加平凡,辩论之风随之风起,故纵横之文地位超过墨家之文。因此刘师培认为“词赋诗歌,亦出于行人之官,厥证甚多”[2]1546,注重修辞文体均与纵横之文相关,对于文学的质文之变有着较为清晰的考察。
客观而言,刘师培所论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原貌,尚有不太周密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亦有其合理之处,对于上古文学的研究极有启发。刘师培以学术出于史官为核心观点,涉及诸子学、文学等各学科,結合西方社会学的知识,正可补备上古传世文献较少的状况,因此他的论述,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M]. 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
[2]仪征刘申叔遗书[M]. 万仕国,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14.
[3]邓 实,黄 节.国粹学报:(第5册)[M].扬州:广陵书社,2006:2161.
[4]刘申叔遗书补遗[M]. 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388.
[5]刘 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6]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3.
[7]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