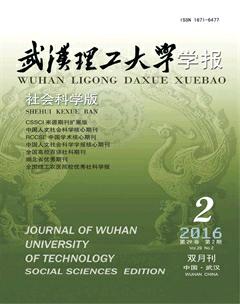中西伦理学“道德理性”及其现代挑战
俞懿娴
摘要:什么是指导人分辨善恶、采取善行、避免恶行的原理?人当如何生活行事,始能过着美善人生?善良的个人应如何结为社群组织,建立社会规范与原理,以生活在理想社会里?这些原是中西伦理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为了回答这些课题,传统中西伦理学均提出“道德”和“理性”的观念。在西方,自古希腊哲学起,“道德理性”即被视为“美善灵魂”的特质与人的特殊功能,而正义和谐则是这美善灵魂的状态。在中国,先秦显学中的儒道墨三家,无不以“尊道贵德”为其基本哲学信念,相关学说中富含“道德”和“理性”的观念。其中儒家传承《尚书》“德治”的思想,认为“德”既是个人质量与行谊,又是社群道德与政治智慧,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古典伦理思想在西方到了17世纪科学兴起之后,渐次受到动摇。随着科技推动着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现代文明的发达,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虚无主义的风潮弥漫,传统的“道德”和“理性”观念一面受到挑战质疑,一面似已不合时宜。综观中西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二者思想在先秦和古希腊时期最为接近,同样强调“道德”和“理性”具有客观永恒之价值与标准。迨西方文明发展进入现代,其传统伦理思想即受到批判和质疑。因此,不仅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和西化的过程中传统伦理思想式微,西方文明本身的伦理生态也遭到严重破坏。
关键词:中西伦理学;道德理性;比较哲学
中图分类号:B82;B82-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01
一、中西古典伦理学中的“道德理性”
什么是指导人分辨善恶、采取善行(good conduct)、避免恶行的原理?人当如何生活行事,始能过着幸福、美善的人生(good life)?善良的个人应如何结为社群组织、建立社会规范与原理,以生活在幸福理想的社会里?这些课题,不仅是中西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也直接关乎毎个人身而为人的价值、理想、意义、目的,以及身而为人所当采取的行动。
为了回答上述课题,中西伦理学均曾提出“道德理性”①的观念。在西方,古希腊文化早有“德”(arête, virtue/excellence)和“善”(agathos, good)的概念,荷马史诗里提到:“要成为善人,必须在战时及和平的时候勇敢、多才艺,且表现成功卓越。”不过荷马理想中的善人,必是贵族,“善”非贩夫走卒可以具备。又“善”(形容词)的名词“德”即人特殊社会功能的表现,如国王善于指挥阵仗,武士善于作战。同时“德”也是个人的道德质量,且必然涵盖“正义”(dikaiosune, justice)的品质[1]。到了后荷马时期,“德”成为遵守律法习俗(law-abiding)的善行,主要指正义——一个人能遵守社会的共约习俗或律法,坚持社群认定的伦常之善,即是有德。这“德”的观念正是日后辩士学派(the Sophists)所袭用的概念。同时“德”还发展出一通俗的用法,作为“关系辞”(a relative term),而非“通名”(a general term),意为擅长(good at)于某事。擅长于某事,即具备对于某事的专门知识、经验和技巧,因此“德”取得了“知”的意义。“德”可为技艺(techne, art),也可为知识(episteme, knowledge),苏格拉底因而据以提出“德即知”(Virtue is knowledge)的主张。结合“德”的功能义和人性,苏格拉底提出“人类功能”(ergon, human function)概念。根据柏拉图(Plato)的语录,苏格拉底对于“德”有以下解说[2]:
其一,“德”是整体的、高尚的精神质量(spiritual qualities),包括勇敢、节制、虔敬、正义、智慧等等均属之。德是整体的,有德必有勇有智。
其二,“德”是人类之善,是人类的功能发挥至卓越的表现(excellence)。所有其它的善,外在的善和物质的善,必须受到人类之善(德)的管理和运用,才能真正有利于人。
其三,“德”是人类的智慧(anthropine Sophia, human wisdom),来自神圣恩赐。“德”是对自己无知的自觉,对于苦乐正确的计算,对于善恶的分辨,以及对于基本道德原理的直观洞见。
又根据Hans-Georg Gadamer的分析,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谓的“德”,事实上包含了一“多利安式的知行合一”(an Doric harmony of word [logos] and deed [ergon])。如在《查米地斯篇》(Charmides)中,苏格拉底说拉契斯(Laches)仅在行为(ergon, deed)上是勇敢(andreia, courage)的,却对于什么是勇敢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因此没有做到“知行合一”。[3]而这“知”(logos),即理性。为了追求这“知行合一”之德,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不断寻求节制、勇敢、虔敬、正义、友谊各种德目,乃至于“德”本身的普遍定义。而柏拉图的“理型论”(doctrine of ideas)也正是基于此而发展出来的。
苏氏将“理性”与“德”结合,影响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都坚信“理性”是人灵魂最高的功能和本质。唯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功能,人才能过着美善幸福的生活。在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说里,理性灵魂(logistikon, rational soul)有如驾着一匹良马和一匹驽马的御者;良马是非理性的精神(thymoeidoes, spirited soul),驽马则是非理性的嗜欲(epithymetkon, appetitive soul)。如《费卓斯篇》(Phaedrus)中的苏格拉底说:
此时良马尚知分寸,不敢立即奔向其主人所崇敬之对象〔此指“美之理型”〕,静待主人之指示。那劣马不仅不听主人的口令与鞭策,并且咆哮奔跃,企图接近其主人所敬爱之对象。其结果徒陷主人与良马于困扰……良马乐于服从,劣马则不愿,因之飞车窒碍不前。良马内愧,其灵魂不安,不觉汗流浃背。劣马卒倒在地,略感伤痛,亟图恢复其桀骜风度,大发脾气,针对御者及良马咆哮愤怒,殆若一恶性重大、包藏祸心之叛徒。……御者曾再次鞭策两马前进,终于同意两马暂息片刻。歇息后,两马似乎忘其所以,御者不得不再予鞭策。经一番挣扎拉扯,再行出发。于更接近御者所敬爱之客体,劣马故作泼态,俯首、耸身、蹻尾、紧咬口中嚼口,不肯前进致敬。御者愤怒之余,拉扯缰靳,但因用力过猛,使此劣马口腔中牙龈鲜血喷溅,用力逼使劣马曲膝下跪。劣马于痛苦中沮丧之至。而御者不肯宽待,如此者一而再、再而三,劣马终于屈服,放弃其任情胡闹。良马始终悚栗不安,使御者既爱且怜。(Phaedrus, 253d, 254b-e)。…假如灵魂中高贵的部份(或者说是“灵魂之心”)控制其它部份、而为其主人,且此项成就表现一位爱智者的生活秩序之中,则他的世间生活必然幸福美满。因为灵魂中卑劣的成份被征服了,而其善良的部分便获得充分的解放,所以他能自作主宰,身心安泰。 (Phaedrus, 256b) [4-5]。
柏拉图在此生动地描写理性灵魂如何驾驭控制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进而肯定唯有非理性的灵魂服从理性,以理性为主人,人才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立场大致相同。他也将灵魂分为三部分:最低阶层的植物灵魂(vegetative soul),其主要功能为自养(self-nutrition),生长(growth),再生(reproduction)等;中间阶层的动物灵魂,是嗜欲与感觉的灵魂(appetitive and sensitive soul),其主要功能则为欲求、感觉、运动等;最高阶层则为理智灵魂(intellective soul),其最主要功能则为思维、推理、计量(calculation)。这三类灵魂,植物魂是所有灵魂所共有,动物魂是动物与理智魂所共有,而唯有理智魂是人所独有。(De Anima, Book Ⅱ) [6]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三分说,显然是出于一生物学家的立场观察所得,未如柏拉图的灵魂论那样原是根据古希腊社会的阶级分工而来。②不过亚里士多德仍受柏拉图理性、非理性灵魂二分说的影响,将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归属于非理性,而理智灵魂则属理性。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非独为人所拥有者,因此若要问人类灵魂的独特功能,则唯有诉诸理智灵魂。他在《尼高迈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中分析道,而若想使人类灵魂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臻尽善尽美之境,求得人类至高的善(human good)与快乐,享有高贵神圣的幸福人生,则首需将灵魂中非理性的部份置于其理性部份的管辖之下。③人只有在以理性为主、非理性为仆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有德之人。能服从理性原理的灵魂,便能使其作为人的功能发挥至最完善的地步。其杰出表现可分为两类:一是理智的,一是道德的。哲学智慧(philosophical wisdom)、理解力与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皆是理智的杰出表现(intellectual virtue/excellence),而节制大方等品格则是道德的杰出表现(moral virtue/excellence)[7]。
不过,不同于柏拉图认为经过辨证思想层层反剥、灵魂的转向④以及理性的观照,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理型”;亚氏则反对超越现行世界的理型存在。他虽肯定理性或者理智作用(nous, intellect)足以把握事物的“本质”(essence)与普遍的“共相”(universals),不过这仍先须透过感官经验提供事物的影像(mental images),再从中抽取可理解的部分,始能取得。但这无碍于理性作为灵魂之中最为神圣的部份,其从事纯粹思辨(speculation)与默观(contemplation)的活动,最能摆脱世俗的利害与自身以外的目的,使人最为幸福、自足。这便是亚氏所谓的理论活动(theoria)。此外,另有两类型的灵魂活动:创作智慧(poiesis)以及实践行动(praxis)。创作智能(productive wisdom)或称艺能,以制造自身以外的某些事物为目的,实践智慧则是以善为目的的行动。“制造”(ergon/producing or making)不同于“行动”(praxis/acting or doing)。虽然二者同样能造成事物的改变,但是前者在改变活动以外之事物,而后者则在造成行动自身的改变。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能衡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恰当的行止、什么是善巧方便(expediency),同时能通盘考虑引导人过着美好人生的原理。实践智慧是计量性的,它不同于科学知识,也不是演证知识,因为它处理的对象不是普遍必然的原理,而是最终极殊别的事实。实践智能可说是人根据善恶价值所作正确合当推理的行动。它和意见一样,处理变化的、殊别的事物,不过只有它具有推理作用,并以“智巧”(cleverness)为官能。智巧是一种知道如何把事情办到办成的能力,作为实践智慧的官能时的善智巧是以高贵事物为对象,至于恶人有恶智巧则以邪恶事物为物件[8]。
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是根据人类的善而行动的一种理性能力,而“道德人格”(character)正是因之而成立的。不过这理性灵魂必须结合非理性的部份,以形成“人格状态”(the states of character),而人的行动也是由这部份的灵魂所发动的。非理性的植物魂与动物魂均不能产生行动。因为行动是人蓄意的作为,而植物魂与动物魂皆是自然与被动的。而非理性灵魂中唯有情欲(passions)能依趋乐避苦的原则产生行动。因此与道德行动可能有关的非理性结构必是下列三者之一:
其一,情绪(emotions):嗜欲(appetite),愤怒、恐惧、自信、嫉妒、享乐、爱、恨、渴望、同情、怜悯,以及其它各种伴随着苦乐的情感(feelings);其二,产生上述各种情绪的官能,例如肝是愤怒的官能;其三,这些情绪产生的状态(states),即个人情绪在各种情境中的强弱状况。例如,过激或不足的愤怒皆不合适,只有适当的愤怒才适于个人的感觉。亚里士多德分析道,这三者中前二者皆无法产生道德,甚至连恶行也不能产生。因为“情绪”与“情绪的官能”和“有意的选择”无关,吾人无法决定个人是否要愤怒或恐惧,也不当为了有这些情绪而受责难,这些皆出于天生自然的本能。三者当中唯有情绪的状态可以选择控制,因而与人的善恶行为有关。行动的善恶或说道德品格,就在于实践智慧能运用衡量(deliberations),选择适当的情绪状态,使之无过与不及,合于中庸之道,以人类的善为目的从事活动。在此衡量选择固然重要,不过德性上的中庸状态更是人自发行善的基础。实践智慧能指导非理性部份中的人格状态,借着衡量,选择中庸之道,养成良好习惯,以形成美好的道德人格[8]。
上述所说,便是支配西方古典伦理学的主流理论。在中世纪,“理性”成为上帝依照自身的形象造人所留下的“烙记”。在近世哲学,“科学理性”(scientific reason)、“计算理性”(calculating reason)以及“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乃至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取代了传统“本质理性”(natural reason)与“神圣理性”(divine reason)的地位,因之“理性”的古典意义也就日趋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