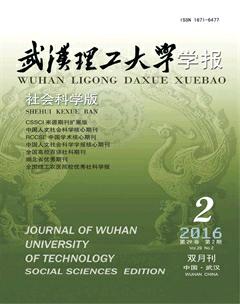艺术理论抑或政治哲学?
杨杰
摘要:学者多认为《声无哀乐论》是一篇艺术理论文献或者音乐美学文献,事实上它是一篇哲学文献。嵇康认为声音只有音阶节奏是否平和的体性,而没有哀乐的属性;哀乐是人的情感属性,平和的音乐只是宣导人本有的哀乐之情。他进一步认为音乐本身也没有德行、功用等“象”。他认为音乐是有教化作用的,首先要实行无为之政的良善政治,使得人心平和,产生平和之乐,二者相互涵养天下才会大治。与儒家以礼乐为主的乐教观不同,嵇康的乐教思想是以人心平和,从而实际上是以无为政治为首要目的的。因此嵇康的音乐理论最终指向的是乐教何以可能的政治哲学问题,《声论》是一篇政治哲学文献。
关键词:声无哀乐;和声无象;无为之治
中图分类号:B23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02
人们一般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下简称《声论》)视为艺术理论文献或者音乐美学文献,认为同《乐记》相比,《声论》深入音乐之体性,探讨音声自身的规律,并表现了审美的艺术性。比如叶朗认为,嵇康“认为音乐(艺术)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其积极意义是“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形象的认识的深化”[1]。李曙明更是提出“音心对映论”的说法,认为嵇康的音乐理论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自律论”、“他律论”的“和律论”[2]。可见无论是音乐学研究者还是美学研究者,大都是就音乐本身或者审美来讲的,而没有认识到嵇康写作《声论》一文的真实目的。
事实上,嵇康并不对音乐艺术或音乐理论本身感兴趣,或者说他并不认为音乐与政治无关。《声论》的写作很多地方是直接针对代表儒家乐教观的阮籍《乐论》而发的。比如《乐论》说“满堂而饮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3]72,认为酒宴上人们闻乐而泣是由于音乐自身不快乐的原因;嵇康则指出“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是由于人们在听音乐之前内心已有了哀乐之别,音乐自身并没有快乐与否的区别。也因此,《乐论》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发问,《声论》则以之作结,二人可谓殊途同归,都回到音乐的教化作用上面,这才是嵇康作《声论》的根本原因。而《声论》的开始,秦客以儒家“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的乐教观发问,引出东野主人“声无哀乐”的主要观点;其间经过六个回合的问难与答辩,结尾回到音乐“移风易俗”的主题,进一步佐证了《声论》的写作目的是乐教而非乐理。
一、关于“声无哀乐”问题
《声论》的开始,秦客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政治的好坏,而音声则对政治好坏作出相应的反映(“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因此悲哀忧思、安详快乐的感情表现于乐器也就是音乐之中(“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秦客引用的前论“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源于《乐记·乐本》,其原文是:“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4]1077。
“声音之道”与政治的相通之处在于,声音通过自身的哀乐表现,体现了政治的治乱好坏。秦客的引用是符合《乐记》的说法的。在儒家那里,声音之所以一定要有哀乐的属性,是因为一方面音乐秉受天地之情和人之性情而来,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以及“乐由天作”[4]1075,1090,因而自身被赋予了哀乐情感;另一方面只有具有了情感属性,音乐的教化作用才能得以可能。
东野主人也认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说法,但他的理解与秦客不同。秦客认为,这句话说明了音乐是有哀乐情感的;东野主人则指出,风俗民情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状况,国史通过审查政教得失、民风盛衰,用“吟咏情性”的方式来讽喻国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说法源于《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4]15,这是就诗教来讲的,嵇康显然知道所谓的“亡国之音”是就诗教乐教合一而言的,并不是指音声如何。
嵇康是明确区分“音声”与“乐”的。据笔者统计,在《声论》里,“声”字出现125次,“音”出现76次(包括二字连出的情况),“音声”出现9次,“声音”出现28次,音“岳”的“乐”字出现16次。“音”、“声”或二者连言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客观的声音或者人声以及人使用乐器发出的声音即纯音乐,嵇康认为,不但自然界中的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哀乐的,人通过鼻口或者借助器乐发出的声音也是客观的无哀乐的。而“乐”(音“岳”)则主要是指先王制作所传下的“至乐”,是在儒家诗乐教化中的乐;这是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嵇康将其中的“音乐”特别是器乐所表现的纯音乐拈出来,作为其重新探讨乐教的重点,试图通过对纯音乐的新的理解来解决以往乐教未能成功的问题。
秦客主张的“声有哀乐”,完全是从儒家的理路出发的。“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形于声音”[3]432-433,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声音是有情感的人发出来的,因而被赋予了情感的性质。
东野主人的辩难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从名实角度看,喜怒哀乐爱憎惭惧是人的属性,是用来描述人的情感的,与声音无关;描述声音的只能是自身音律是否和谐,而与哀乐没有关系,二者各有名实,不可混淆。
其二,哀乐是人在听音乐之前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已形成于内心的情感,在听到形式和谐的音乐时显露出来而已。因此音乐触发人本有的哀乐之情,而不能说音乐自身有哀乐的属性。
其三,形式和谐的音乐由于自身音调大小的不同,对人的情绪影响有的猛烈有的恬静,人的形体便有或躁动或安静的反应。躁静与哀乐不同,前者是音乐引起的人的体态反应,后者是情感表现,因此不能说哀乐是音乐引起的。
其四,假如音乐有哀乐的情感倾向,那么它引发的人的情感表现应与自身一致,即只表现出与音乐的哀乐属性一致的一种情感,怎么能同时感动不同性情的人、引发不同的情感呢?
其五,音乐秉受天地之情与个人性情,自身只有和谐的性质,其音调、音律、音阶、音色都有其不随人类、时代而变化的“常体”,因此它才能够感发众人,其对人的感染没有固定的方向;人心则事先已有一定的情感方向,应和着音乐的感染而表露出来。二者各有轨道,虽有关系,但不能将哀乐这种情感属性赋予音乐的身上。
嵇康对“声无哀乐”观点的论证,一方面是从“名实之辩”或者说“主客二分”的角度考虑的,另一方面是从分析乐理、音乐现象、情感自身的性质等角度考虑的。这使得嵇康对音乐的分析在深度上远远超过《乐记》,后者更关注“教化”的层面而对“乐理”本身没有多少探讨。不过讨论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只是第一步,嵇康不得不面临儒家典籍记载中音乐的道德、政教功用等问题,从而他进入了音乐的“象”的问题。
二、关于“和声无象”问题
由“声无哀乐”过渡到“和声无象”是很自然的,儒家乐教传统中乐对人情感的影响只是一种中介,其目的还是使道德规则借助乐的力量内化为心灵的一部分,使之成为外在的自然行为。因此儒家是主张“乐以象德”的,乐象征着德行,是儒家比德观念在音乐上的表现,这在《声论》中秦客所举的各种“前言往记”中多有见到。
不过历来人们对“和声无象”的理解多有不同。蔡仲德说“‘象在此是‘表现之意,‘无象与‘有主相对而言,意谓平和而不表现什么感情,故下文说人已有哀心在内,听了不表现什么感情的‘和声也会流露出悲哀的感情。”[5]戴琏璋认为,“所谓和声无象,是说和谐的声音无所模拟,无所反映。”[6]二人的诠释只是说出了《声论》中“象”字的一部分含义。张玉安认为,汉魏时期的音声之象受象数影响而有三层含义,即“征象、象征;表象、表现;气象、象感”,嵇康没有讨论“和声无象”的内涵而是将之当作一个自明的前提,《声论》是“在音乐领域扫除象数的一种努力,和荀粲、王弼在易学方面扫除象数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7]刘莉则认为张玉安的理解过于狭隘,“嵇康提出“和声无象”的观点主要是为了批判儒家功利主义的乐象观,并非汉魏流行的象数观念”。她从《声论》对“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和“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的批判出发,认为“和声无象”批判的是“儒家人为附会在音乐上的盛衰吉凶之象、功德之象和主体心象,目的是剥离附会在音乐上的谶纬迷信、道德教化和主体情感内容”[8]。
笔者认同刘莉对“象”的外延的界定,但是对于其内涵,则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和声无象”是直接针对《乐记》的。《乐记·乐象篇》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正义》解释“声者,乐之象”曰“乐本无体,由声而见,是声为乐之形象也” [4]1113)。音乐本身只有通过声音才能表达自己,声音作为乐的外在形象,也传达着乐自身所包含的历史性内容,这就是秦客所说的“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但是《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后乐器从之”[4]1111-1112,就是说在诗、舞、乐一体的乐教传统中,三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诗,是以言辞说其志向;歌,是以有韵律的节奏应和诗词;舞,是以舞蹈动作振动仪容以表达心志。诗、歌、舞三者本于人的内心而与乐器生发的节奏韵律相应,就形成了整体性的乐。因此“乐以象德”的功能未必就是“声音”产生的:“昔伯牙理琴,而钟子知其所至;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3]433。这三个记载,秦客认为是伯牙、隶人、鲁人将心志赋予乐器产生的声音或者自己的哭声之上,听者从而得知他们的心志。但是,主人认为秦客承认声音变化无常且有哀乐的观点,与后文秦客观点的推论“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是矛盾的,因而不能成立。主人随后指出如果“仲尼识微”、“季子听声”和“师襄奏《操》”的记载成立,则文王之功德、风俗之盛衰也当流传到后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记载也是不成立的。主人由此指出,类似的记载只是“俗儒妄记”,神化先人迷惑后世而已。对于秦客的进一步质疑,主人详细剖析了“葛卢闻牛鸣”、“师旷吹律”、“羊舌母听闻儿啼”三个“前言往记”,指出这些记载有的只是偶然有的是后人添油加醋有意为之的。
但是主人是认同“《咸池》、《六茎》、《大章》、《韶》、《夏》”这些“先王之至乐”“动天地、感鬼神”的功效的,对于季子、仲尼的记载,他又问道“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就是说他反对的是把这些功德之象赋予音声之上,而对整体性的乐是否有“象德”的问题,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并且对于秦客提出的各种“前言往记”,主人反对的只是俗儒认为音声蕴涵、传达功德之象的做法,而对“先王之至乐”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并没有反对。因此,嵇康讲“和声无象”而不是讲“乐无象”,将纯音乐从整体性的乐中抽离出来,为的是以便更好地理解音声自身的特性,从而更好地阐发其解决音乐的教化功能的问题。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琴赋》中,嵇康对琴声所作的艺术想象,与“和声无象”的“象”含义不同。前者是演奏者或者欣赏者在演奏或者欣赏音乐时产生的艺术联想,在琴声中达到人乐合一的境界,并没有给音声增加任何内容,而只是对音声之美的一种艺术描述;后者则是赋予音乐以功德、情感的属性,甚至将这种附加的属性作为音乐的本质。因此,《琴赋》中的“艺术之象”与《声论》中的“和声无象”并不矛盾,钱锺书先生所谓“《琴赋》初非析理之篇,固尚巧构形似(visual images),未脱窠臼,如‘状若崇山,又象流波等。《声无哀乐论》则扫除净尽矣”[9],当是其未深思熟虑之论见。
三、关于“乐教之本”问题
《声论》的主体内容是通过对音声与情感关系的分析探讨音声之本性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篇音乐美学或者音乐理论文献;而其第八问难却突然讨论礼乐,其观点与儒家的礼乐一体的乐教观似乎也很相类,似乎脱离了主旨。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声论》的主题是讲“音声之理”的,“作为一篇美学论文,这就够了。讲‘礼乐之情是画蛇添足”,甚至认为第八个回应讲“礼和乐的配合”,与其反对“名教”“礼法”的观念不符,因此“这也是他(嵇康)的思想中的一个内部矛盾。”[10]事实上,将嵇康思想僵化地看作反对“名教”“礼法”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其思想的“矛盾”是无从谈起的。综合嵇康的人生轨迹,一个试图逃离政治而不得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对音乐理论或音乐美学本身感兴趣。事实情况是他自身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素养,以及当时音乐逐渐从政治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发展的现实,促使其更深刻地思考儒家乐教观中最重要的部分——纯音乐——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从而使政治与音乐的关系能够得到重新梳理,这样二者才能都合理健康的发展。因此由“音声”到“乐教”,成为嵇康思考的合理路径。也因此,从根本上说,嵇康探讨的是政治哲学问题,《声论》是一篇政治哲学文献。
在嵇康看来,儒家乐教理论中强调音乐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以之作为音乐的根本性质和治国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态度,既对音乐的发展不利,又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一方面,儒家强调音乐对人心和社会的教化作用,不仅否定了“音声之体”,而且其僵化的、无创新性的音乐越来越形成一种压抑人性、强迫人心的仪式性力量,成为一种伪饰的、异化的外在力量,从而成为人性的束缚。因此,儒家的乐论是从人心出发而最终却违背人心的,而其保守的音乐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发抵不过“新声”的冲击,音乐在它那里走向了死胡同。另一方面,在“人心-伦理-政治”的序列中,由人心的性情之和推及到社会家国的天下大和,并不是一种必然的、自然而然的、无矛盾的联系。儒家认为音乐能实现这种自然的“施化”,使得统治者不在根本上思考为政之道而在音乐上下功夫,追求歌功颂德式的表面繁荣。这在嵇康看来,统治者还是没有抓住政治的根本,而是将“声音”与“政治”做了一个错误的链接。因此,在嵇康看来,儒家乐论以政治功用为音乐的根本、以音乐为政治功用的手段,既没有理清音乐的问题,也没有明白政治的根本。几百年来,儒者纠缠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上,都没有使音乐对政治产生实质上的正面作用。而其解决之道,必然是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一个新的解读。这就是他提出的“心为乐体”的乐教观点。
第八问难中,嵇康在论述“古之王者”时的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之后说:“然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3]422。“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有读“乐”为“快乐”之“乐”的[7]80,有认为这说明在“乐-心”一体音乐欣赏中心的感受作用是主要的,即一个音乐只有经历过欣赏才完成了自身[2]。但是,既然此段是在讲乐的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这句话就不该只是讲乐理或者音乐审美,而应该是讲乐教的。
秦客认为,乐之所以能移风易俗,就在于其能引起人的哀乐情感,东野主人否定了音声有哀乐情感的属性,也否定了音声能引起人的哀乐情感,那么如何解释“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说法呢?主人并没有否定乐的这一社会功能,而是对之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一般人常说的“移风易俗”,是在世道衰弊之后才想起的,实际上已经晚了。在实行简易之教、无为之政的时代,上静下顺、天人通泰、百姓安逸、自求多福,人们自然而然地依循正道、怀忠抱义,而不追求其原因。因此人们内心平和,也就发出平和的声音,以舞蹈、歌词、乐器装饰之,让它引导、迎合、培养人的自然性情,使人心与“道”会通而达到和谐的境界。由此随着乐的传播,万国万民都受其感化,从而整个天下百姓都达到了和谐的地步。因此所谓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指在世道还未衰弊之前,人心本就是平和的,平和之乐能涵养这种平和之心,进而感化天下万民之心。所以说在乐的教化作用中,“心”是最主要的,而保持人心平和的方法,就是采取无为的治国之道,这就是“无声之乐”。这个“无声之乐”被赋予了道家的内涵。在儒家那里,统治者要采取有为的德政,正如《礼记》所记载的“‘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4]1394,统治者要勤政爱民才能治理好国家,这种“德政”为“无声之乐”。但在主人那里,所谓的“无声之乐”是要无为之治,显然嵇康接受的是道家的“无为之治”式的“无声之乐”的。
不过,嵇康又明显部分地接受了“礼乐合一”的儒家乐教观。嵇康认为人的性情喜欢和谐的音乐,为使之不过于放纵淫逸,圣人便制礼作乐加以引导。君臣百姓自幼至长都加以学习固守,教化的作用也就完成了,这就是“先王用乐之意”。这段嵇康没有明说,实际上是指“古之王者”之后的衰弊时代。在这个时代,嵇康承认了在礼乐的共同作用下教化的可能性。并且嵇康又强调,在衰弊无道之世,需要平和的心与平和的乐相互配合,涵养人的情性,从而形成良好的世风民俗。但是音乐并不能纠治邪淫之心,因此更为根本的,还是要实行合适的政治,使人心平和,这才是音乐教化的根本意义。
另外,嵇康反对“至妙”的“郑声”与“流俗浅近”的世俗小曲,只是从功利主义考虑的。因为二者并不能与平和的人心发生正面的契合,因此应当舍弃。但是他指出,无论“郑声”还是“小曲”,其自身只有“善恶”即韵律音阶平和与否的区别,而没有淫正之别。淫正同哀乐一样是属于人心的,对其的纠治只能是由平和之政引发平和之心,而不能寄托于音乐。
四、结 语
在嵇康那里,作为乐教体系重要组成元素的音声自身没有哀乐,只有和谐的体性,因此只能引发、宣导人本有的哀乐之情。为了使乐教得以可能,只能是使人的情感与音乐契合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使人心平和是首要的,音声的善恶平和与否是次要的。所以只有良善的政治结构与治国之道,使人心平和,进而平和之心与平和之乐相互涵养,才能使这种和谐的社会结构推广到整个天下万民,从而实现“移易风俗”的目的,这种良善的政治就是嵇康所向往的道家式的无为之治。因此虽然《声论》的主体部分都在探讨音声的本体、论证音声与情感乃至政治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其探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音乐对人心、政治的教化作用,因而嵇康的音乐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声论》根本上是一篇政治哲学文献。
[参考文献]
[1]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8-199.
[2]李曙明.音心对映论:《乐记》"和律论"音乐美学初探[M]//韩锺恩,李槐子.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520.
[6]戴琏璋.玄学中的音乐思想[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7(10):76.
[7]张玉安.嵇康"和声无象"说解析:兼谈汉魏时期所流行的乐象观[J].学习与探索,2005(4):165-169.
[8]刘 莉.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105-114.
[9]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三联书店,2008:1723.
[1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9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398-399.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