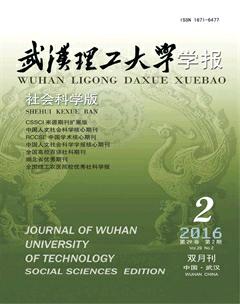天命与政权:先秦天命观演进的逻辑路径
李培健

摘要:在人类早期社会,天命观是维系政权的重要理论工具,它可为政权提供超验性依据和宗教性阐释。不同时期,天命观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先秦时期,天命观演进的逻辑路径依次是:殷周宗教天命观、春秋自然天道观和战国五德终始说。在殷商时期认为天命不易,到了西周时认识到天命有常,并总结出“天命有德”的理念;到了春秋时期,又发展出自然天道观,认为天象是连接天命与政事的中介,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太过具体细致;到了战国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它既强调德,又具规律性和普遍性,可谓是对之前天命观的一次大总结。
关键词:先秦;天命观;宗教天命观;自然天道观;五德终始说
中图分类号:K22;B22; D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03
天命思想起源于上古社会的原始宗教信仰,当时原始人无法理解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如风雨雷电等,往往把它们归咎为某种神灵的役使,认为人和自然背后有某一神灵(天帝)在支配,还将其作为统治者行使政权的超验性依据和宗教性阐释[1]。由于原始人长期以来并无完善的文字记载系统,所以“一种观念或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至到见诸文字、写成定本,是有时间上的距离的”[2]68,因此天命观被用文字正式记录下来已是殷周时候了。《尚书》中有不少关于天命的记载,像“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天用剿绝其命”等言语。尽管统治者都保持着天命信仰,不过,随着具体政治形势的变迁和认识社会和自然水平的提高,天命观的内涵也有相应的变化,其演进的逻辑路径依次是:殷周宗教天命观、春秋自然天道观和战国五德终始说。
一、殷周宗教天命观
殷代至上神称为帝,其权威所及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天时,它可以令雨、令风等;二是王,即上帝能降福祸于王;三是我,它能保我田、保我吏;四是邑,殷人认为上帝能入于城邑宫室,带来灾祸困穷,因此他们凡是有所兴建,必先贞卜以向帝询问诺否。另外上帝的命令既有善意的,如令雨、降食、佑王等,又有恶意的,如令风、降祸、降旱等①,总之上帝是人间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君主通过祭祀其帝庭的臣工(风、雨、日、月等)和先王来祈求上帝的意志。由于祭祀大权由商王垄断,所以在殷商统治者看来,只要不懈怠祭祀,君权即永享(天命不移)。如据《尚书·西伯戡黎》载,西伯攻灭黎国后,祖伊惊恐便向商纣王报告,说“天既讫我殷命……天弃我,不有康食”。而商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见纣王是相信自己受命于天、政权永固的,西伯能奈我何?
殷周易代后天命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不仅表现在二代至上神名称的改变,“西周时代开始有了‘天的观念,代替了殷人的上帝”[3];更为重要的是,二代在信仰内容上显著不同,而这也正是二代天命观的本质差异。周初统治者以“小邦周”灭亡“大邑商”,面对新兴政权的如何维护有很强的忧患意识。《逸周书·度邑》载,武王灭商后,“具明不寝”。周公旦问起原因,武王说:“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来所定天保,何寝能欲?”武王担心商亡的灾难会落到周身上,却苦于无安定之策,如何能踏实休息呢?这种浓重的忧患意识就促使周初统治者不得不深入思考天命与治权的关系。商亡的现实使周初统治者认识到上天赐予人间君王的统治权不是永久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即“命不于常”[4]。既然天命无常,是否意味着天命是无法把握认知的呢?这也不是,天命也有其原则,即天命有常,而这个“常”即是德。他们认为殷亡不是上天有意为之,而是自己失德所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4]。进而便总结出“天命有德”[4]的政治理念,有德即能获天命和保天命,“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4]。由此可知,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上天赐予人间君王的统治权是有限制的,不具有时间上的无限性,即天命无常;但上天并非随意行事,它也有其原则和规制,即视人间君王有无德,德的要求主要是保民、慎刑等,所以天命又是有常的,是可以被把握的。因此,与商代相比,西周时期,尽管仍保持着宗教天命观的信仰,但更有新的意蕴:时间性与原则性的统一、神圣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殷商之际天命观的这次转变,对后世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认为,西周天命观中蕴涵着的人文、伦理色彩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如何从宗教学、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周时代的‘天命观的变化,是理解早期中国文化演生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文化上许多重要嬗变都是以宗教为转轴的。美籍华裔历史学者陈启云先生指出,早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超越性突破”之前的殷周易代之际,中国古代文明的宗教元义即经历了一次近乎“超越性的突破”,这是中国早期社会宗教文化传统的一次大转轴。[2]49在人类思想史上,“元义”(Archetypal Meaning)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引子,可能产生“再发性意义”,甚至是“重发性意义”[2]67。殷周天命观的这次转变,对后世思想的发展有两点重大影响:第一怎样才能保持天命?第二天命有常的历史规律是什么?借用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发性、重发性观点可得出:天命不移源自对天命的信仰,这是原发性第一义;而对天命不移的怀疑则是对传统天命信仰重新认识后的原发性第二义。之后从哲理上深入思考的如何维持保有天命是对原发性第一义的继承,此为重发性第一义;而思考天命转移的具体规则或天命之定数是为重发性第二义。兹列图示1如下:
后世对天命观念的思考,大致就沿着重发性两种元义进行的。周代“天命有德”的政治思想回答的正是如何维持天命的问题(重发性第一义);而春秋时的自然天道观和战国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更关心的则是天命的具体规则、定数(重发性第二义)。
在周初统治者眼中,天命和治权的媒介是人君的德,即君主有德便能获得天命,无德或失德便丧失天命,这与殷商天命观相比突出了人君的主观性。在商人的观念中,先王可以直接到达神界,生王对先王举行祭祀仪式,让其宾于帝以保佑自己,因此神的世界和祖先的世界是直接打通的,但生人的世界和祖先的世界、生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则靠巫觋的仪式来传达消息[5]。这说明上帝拥有对人间的绝对权威,人君完全听命于上帝,只能通过具体的仪式上的祭祀和贞卜来获得上帝的旨意,所以天命与治权联系的桥梁是祭祀,这就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即只要商王独占祭祀大权就可以获得上帝所赐予的人间统治大权,因此当西伯攻灭黎国,纣王却置若罔闻、不以为患,反而自信地说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礼记·表记》上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到了西周,人君成为天子,与神的世界以德来联系,而德是可以被君主自主掌控的,是种自为的行为。但这也存在一个逻辑推论:人君明德而治,则上天降治权焉;人君弃德而行,则上天废治权焉。所以当西周中后期,统治出现危机后,民众便开始怀疑甚至谩骂上天,这其实也是对周王统治权正当性的怀疑,这就造成了西周“天命有德”天命观的动摇。于是到春秋时,一种新的论证上天、人君和治权关系的天命观便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