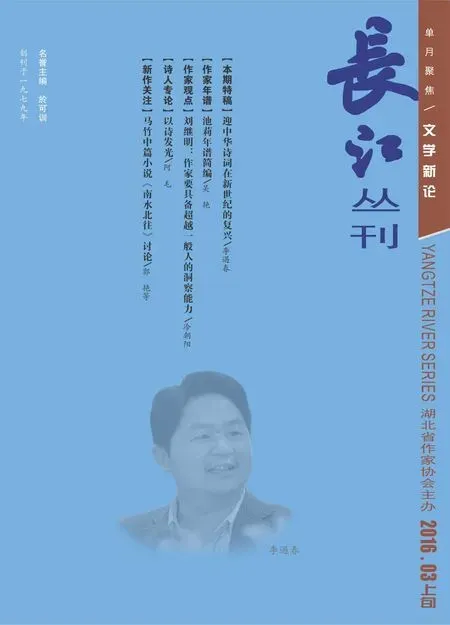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
■吴棃荣
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
■吴棃荣
纵观格非近三十年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格非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初期作品因“有意味的形式”而晦涩难懂,近十年作品则因对“传统”有所回应而可读性大增,但是,其创作前期与后期都引来了一番批评的热潮。本文试图对格非小说文本进行纵向分析,来探讨其小说创作前期——先锋文学潮流期间的创作与创作后期——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在意象上的流变问题。全文分为两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探讨前后两个时期的人物意象与物性意象在意象使用或意象内涵上的转变,分析人物意象由“扁型人物”到“圆型人物”,物性意象由“内涵简单”到“内涵复杂”,“音乐”意象由“边缘”到“旗帜”的变化。第二章则论述格非小说意象以上转变的成因,探讨人物意象与物性意象发生变化背后的格非审美观念变化因素,考察“音乐”意象份量增加背后的个人爱好及消费时代里作家有意识地进行艺术探索的原因。
何谓“意象”?在文学研究中,它的概念与内涵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词典《辞海》对“意象”有如下的解释:(1)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性表象。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2)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这种介定指出“意象”是源于现实生活、包含作者的内在思想、能激起人的想象力的物象,讲求情景交融。而西方的文艺理论中,意象更偏重主观对客观的直觉感受。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指出:意象是想象催生的形象,是理性观念最完美的感性形象。20世纪初的诗歌流派意象派,学习中国古诗,沉浸于凝练的意象营造,认为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情的复活体。象征主义诗歌派代表人物艾略特还提出了“客观对应物”的概念,认为诗人的情感与情绪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寻找主观情绪相契合的“客观对应物”,用实物来表达。由此可知,中西方的“意象”概念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其一,意象表现一种可感的具体形象。其二,意象是作者内在情思的体现,包含了创作者所要传达的理性内容。结合这些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意象:“意象”之“意”可理解为“意念”,“象”指“物象”,而“意象”即是创作者赋予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客观、具体的形象。“意象”是诗的细胞,营造意象是创造诗歌艺术的核心,然而,意象在小说中也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如英国批评家辛·刘易斯所说:“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意象来达到不同程度的效果。”一般而言,小说意象是环境、人物、情节的构成成分,“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蕴藏着丰富文化密码之矿藏。”意象在小说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因此,意象已成了研究小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元素。
从1986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至今,格非的小说创作已历时近三十年。格非始终积极地对小说的艺术与内涵进行探索,其小说也颇具研究价值。目前,学者们对格非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综合来看,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迷宫”叙事手法、“存在”主题、时间叙事、欲望的言说、历史观的书写、乌托邦构想叙述及创作转型上,而“意象”研究有所不足。格非在其理论著作《小说叙事研究》中曾言:“作家可以通过创造新的‘意象’找到词语之间新的组合关系,或者构筑起新的‘隐喻系统’来激活读者的想象力”,可知格非颇重视小说中意象的营造。诚然,当阅读格非的小说,触目所及的字里行间总是有许多意象在闪现。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意象分为三种:神话意象、物性意象、人物意象。按照这种划分标准,格非的小说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人物意象”与“物性意象”。格非小说中,杏、棋、父亲、母亲、疯子、知识分子等人物意象,雨、雪、阳光、月亮、桥、天井、田野、河流、竹林、树木、花、鸟、镜子、琴、日记、书信、梦境等物性意象俯拾即是。而其中,物性意象又可以再细分为:水意象(如河流、雨)、乡村意象(如梅雨、树木、小河)、城市意象(如街道、诊所、校园)、天气意象(如细雨、雪、霜、阳光、月亮)、植物意象(如桃树、杏树)等等,有的划分相互之间有所交叉。所有这些意象鲜活而富有灵性,具有特殊的内涵与功能,为格非小说增添了咀嚼不尽的文学韵味,也为我们从意象着手研究格非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在格非小说意象上,其研究状况是:专门研究格非某个意象或意象群的论文颇少,对格非小说意象的阐释一般散见于一些学术论文中。迄今为止,格非小说被研究过的意象主要有梅雨、河流、水意象,桃花、树林、植物意象,天井意象,花家舍,乡村意象、城市意象、梦意象及父亲意象、母亲意象、知识分子、疯子、秀美等女性意象,绝大多数的论文章节皆是对这些意象的精神内蕴作详细解读,也还有极少数的文章论及其意象运用的变化。如熊延柳的《从模糊到具象——论格非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考察了格非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没有自我生命意识的指代性“符号”转向有独立性格、有自觉的生命意识和有女性精神特质的“有血有肉的人”,女性形象明晰化且富有立体感、真实感。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的意象研究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展开论述。

格非
就格非的整体创作状况而言,格非早期的小说因致力于以形式和叙事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探索,被划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潮流中。而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先锋小说作家的写作呈现分化的状态,大多数的先锋色彩减弱,后继作品也不再被当作有先锋特征的潮流来进行描述”,格非的创作也不例外。易晖在《世纪末的精神画像》中指出:九十年代初,格非曾搁笔一段时间,《傻瓜的诗篇》是他重开笔的第一个中篇。而格非继1995年发表《欲望的旗帜》后更是一度在喧哗的文坛沉寂,2004年才以《人面桃花》的长篇力作重新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难发现,格非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文学选择,并在探索中有自己的坚守。格非近期创作相对于早期创作而言,意象设置上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并不断发见新的“意象”。而因他有一段小说创作的蛰伏时期,故本文拟将格非的小说分为两个阶段,以发表处女作到《傻瓜的诗篇》之前为创作前期和以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为后期,从动态的角度来探讨格非在前、后两个创作时期小说意象的发展、变化问题。
一、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
“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刻意营造的元素,一般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固定的用法,然而就创作实践的整体观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趋向性与规律性的东西。格非的小说意象即是如此。
(一)人物意象:由“扁型人物”转向“圆型人物”
“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描写人物是小说的显著特点,而着重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扁型人物”与“圆型人物”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扁型人物是指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和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形式简化,个性简单;圆型人物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多义多变,性格思想较为复杂。一般来说,小说中这两种人物形象是缺一不可的。
就格非的小说而言,其前期的小说中大多是模糊朦胧、单一稳定的扁型人物,后期则具体清晰且多变多义的圆型人物占优势。格非前期作品《追忆乌攸先生》里的乌攸先生和杏、《迷舟》里的萧与杏子、《褐色鸟群》里的“我”和“穿粟树色靴子”的女人、《背景》里自杀的母亲、《青黄》中的张姓男人与小青、《大年》里的玫等等,都属于“扁型人物”。这些人物大多停留在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没有线性的人生发展轨迹,不见丰沛的情感活动方式,也几乎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具体的原型。正如余华所说:“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如果除去它们对主题或氛围的提示作用,只从文本层面来考虑,把它们直接用字母符号等来标志也并无多大不妥。与此不同的是,在“江南三步曲”、《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过是垃圾》、《隐身衣》等后期作品中,格非塑造了秀米、谭功达、姚佩佩、庞家玉、谭端午、胡惟丏、李家杰、苏眉、崔师傅这样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圆型人物形象,他们具体生动,他们有着丰富而完整的个性心理、人生轨迹或命运,而且格非往往抓住环境的变化,在环境的变换中书写个人的成长或变异,使人物形象愈加复杂化、立体化。
由以上的简析可知,格非在前期创作中“人物”与其它物象一样,只是一个叙事符号,一种道具,而后期则让“人物”回归文本,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这体现出格非塑造小说人物的观念与方法上的转变。而结合前面的阐述,不难发现,格非前期与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大致由“扁平”到“圆型”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人物背景与人物性格上。
格非前期小说中,“空缺”叙事手法使用频繁,或表现在核心意蕴的不存在,如《青黄》中追索“青黄”一词的来源以无果而终;或表现在重要的情节缺省,如《迷舟》里主人公萧去愉关究竟为何,去通风报信,还是只是单纯地会见情人,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情节来指示。与此相类似,笔者认为格非的这种“空缺”也显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即:人物背景不足,主要是人物相关信息、人物生活史的欠缺与断裂。在前期阶段,《迷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之死。主人公萧不是死于混乱的战场上,不是死于道人掐算的“酒盅”,不是死于发誓要杀他的情敌之手,而是死于看望情人的举动被怀疑为通敌叛逆,本有机会出逃却被母亲关门阻截的偶然性、荒诞性因素。于读者而言,除了对萧的命运的感慨,很难总结出他的外表、言行举止的特征以及思想、性格,格非在此似乎只是以萧传达出命运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的生命谓叹。《褐色鸟群》里“穿粟树色靴子的女人”在文中闪闪烁烁,很多年前“穿粟树色靴子的女人”在城里的企鹅饭店前捡靴钉,十年后“穿粟树色靴子的女人”在乡间山坡上和丈夫发生矛盾,而丈夫死后与“我”在一起,成婚当天却突然死去。至于十年前、后的“穿粟树色靴子的女人”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文中并没有说明,在此,格非传达的是真相的不可知性。再如《背景》主要指向因果循环,以“我”与同父异母的女孩瓦偷情为核心问题,多种叙事场景不断转换、跳跃,父亲、母亲、“我”、弟弟、瓦在各个片断式的场景中重复出现,令人摸不着头脑。这类作品,大多都是中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的断面集中地刻画人物,而加之作者一系列迷宫叙事手法的运用,令读者在阅读之后,头脑中很可能只残存一个极模糊的影子,而很难总结出人物的具体的长相、个性、言行举止特征,甚至有时还分不清孰真孰假。所有这些人物都以模糊的面目出现,正是源于格非只借用人物的抽象符号意义去营造小说形式,没有着过多的笔墨描绘人物的清晰具体的生活历程及与之相应的生活环境的结果。而格非后期创作的小说以长篇居多,人物信息则“空白具体化”,人物生活史得以恢复。格非系统地描绘人物,往往刻画出人物的外表与内心,出身与经历,注重交待人物的社会关系与生存环境,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体、更立体地跃然于纸上。《人面桃花》是民国初年少女秀米的革命成长史小说。格非采用了横、纵向的对比手法,将秀米写得令人过目难忘。秀米从年少到年长、从外表到心理活动,从在普济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到花家舍遭遇不幸,再到回普济从事革命事业,及她从单纯柔弱的少女到可堪大任的革命者等等,在小说中步步紧扣,娓娓道来。而即使是不为少女时期的秀米所知的世界,如张季元神秘的革命活动、张季元与母亲的莫名关系及对秀米的暧昧态度等,小说中也借由张季元的一本布满革命与情欲的日记来补充。如此一来,秀米的方方面面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其鲜明的20世纪初的革命者形象存活于读者的头脑中。再如《山河入梦》书写谭功达的政治事业与爱情,作品中有着清晰的人物命运走向,从县长到被罢职,到随便与一个女人成亲,最后因包庇姚佩佩的行踪而死,追逐桃花源的线性生命过程的呈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这两部作品,格非以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命运轨迹书写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通过主要人物表达对历史、对社会现实、对人类命运等的理性思考。人物成了格非表现小说主题思想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像前期中只是主题的牺牲品。

《相遇》
性格、思想是人物的核心。“我们看一部小说主要看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揭示,这也就是构成小说的魅力和教育意义的因素。”在小说中,创作者们往往可以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段来对人物形象作深入细致的刻画。而格非后期的作品较之前期,采用了各种各样人物塑造的方法细致入微地“写人”,从而使人物个性更鲜明、更复杂,且富有变化。
格非前期作品中,《追忆乌攸先生》里的杏、《迷舟》里的杏子着墨颇少,她们没有鲜明的个性表现,都是失语的弱势性格,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男主人公的命运,客观上导致了男主人公的死亡悲剧。杏谐“性”,作者只是把她们设置为“性”的符号,用以揭示欲望对命运形成牵制的人生真相。而《青黄》的张姓男人始终满脸忧愁,其阴郁的性格一成不变。小说中,张姓男人的故事散落于每一个叙述者的回忆中,各种片断式的回忆相互矛盾。其故事内容大致是:张姓男人带女儿来到麦村,娶了一个叫二翠的女人,后来死去。然而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来麦村,是怎样娶到二翠的等等,在小说中一团迷雾,这些谜语和张性男人的阴郁性格相得益彰,造就形象的神秘莫测、如影似幻,为格非获得“神秘主义”的小说格调。前期创作时期,格非笔下的人物往往缺乏正面描写,在小说中只是作者表情达意的工具,缺少鲜明的性格情感。而后期则更注重人物的真实性与复杂性的刻画,以复杂多变的人物揭示世界人心的复杂性或生活的世俗性。如谭功达的痴呆,姚佩佩的活泼、天然,庞家玉的“实利”,谭端午的“无用”,胡惟丏的孤傲,李家杰的流氓等等,在作品中描绘得入木三分。《春尽江南》的女主人公李秀蓉与庞家玉是同一个人,但不同的命名,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前者理想化,满怀幻想地为艺术献身于诗人谭端午,对与她发生性关系的谭端午说出“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这般天真烂漫、情真意切的誓言;后者则趋于功利性,自学获得律师资格证,开律师事务所,为高薪工作而自鸣得意;她亲自督促儿子的学习,一旦考试失利就几近歇斯底里地谩骂,还为让儿子上学习环境好的班级,不惜金钱甚至甘愿奉献身体;而在世俗力量的漩涡中,她清醒地意识到:“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总的来说,李秀蓉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情少女,而庞家玉则是自觉投入时代潮流的女强人,她们是各自时代环境的产物。格非用名字的改变寓示形象的转变,对比性地描述人物内涵的前后变化,并以这种动态变化的人物昭示时代的改变对人物的影响,可见格非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独运。《不过是垃圾》里的苏眉、曹尚全也是这样在时代浪潮中异化的人物。苏眉前期是被李家杰疯狂追捧、小心维护的纯洁少女,后来变成李家杰亲口说的为钱卖身的“婊子”;曹尚全在学生时代作诗,有浪漫、自由的诗人气质,而到了90年代后跟随李家杰下海,唯轻浮浪荡的暴发户李家杰马首是瞻,一变为圆滑世故。这些作品,格非不仅仅建构人物的生活史轨迹,还往往抓住人物的生存环境,在环境的变换中书写个人的成长或变异,从而挖掘到了人物愈加复杂化、立体化的层面。
(二)物性意象:由“内涵简单”走向“内涵复杂”
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曾对诗歌意象作出深刻的论述,指出“意象”是“理性观念”得以传达的最完美的感性形象,具高度概括性的特征,能以有限的形象、有限的想象表达出无穷的理性内容,引发人的思索,让人体会到超越自然限制的自由。在此,康德道出了意象传达精神内蕴的功能。而格非注重小说意象意蕴的深入挖掘,单个文本中物性意象的内涵在前后两期中存在一定的变化。
格非前期小说中,物性意象的内涵相对比较单一。如格非通常使用“雨”、“枪”、“喜鹊”指示“死亡”;用“树丛”、“杏”、“杏树”隐含“性欲”;用“火”制造“不祥的阴影”;用“马”引出“战争”;用“候鸟”代表“时间”,用“狗叫”暗示“危险”等等。其中,“雨”和“火”意象是作者颇费心力的意象。“雨”在格非小说中随处可见,可作为解读格非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前期小说中,“雨”的出现之处颇多:
“天上开始下起了小雨,围观的人有些不耐烦了。康康在一名法官的示意下朝乌攸先生瞄准......当小脚女人满身是泥赶到枪毙现场,乌攸先生已经被埋掉了,她看到地上的血水几根像猪鬓一样的头发。雨还在下着......”(《追忆乌攸生生》)
“当送葬的队列在村头的树林时里闪现出来的时候,彤云密布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和雨水顷刻之间将天地搅得一片凄迷。”《迷舟》
“警卫员握着手枪走近了他。天已经突然亮了。黎明的暗红的光消失之后,天空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小雨。而对那管深不可测的枪口,萧眼前闪现的种种往事散落在河面上的花瓣一样流动、消失了。”(《迷舟》)
“尸体入殓的时候,呼啸了一夜的大风突然停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子里静寂无声,女人伏在棺材的边沿,久久地望着她男人的尸体。”(《褐色鸟群》)
“中午的时候,人们匆匆忙忙将那个姓张的人安葬了。那天下着黄梅时节断断续续的小雨,我记得雨水把漆黑的棺材浇得锃亮。”(《青黄》)
“平板车就停在那儿。被雨水浇烂的泥地上到处都撒满了褪了色的纸折的花朵。隔着屋檐垂落的雨帘,我看见几个穿着蓝布制服的烧尸工人正在廊下打着纸牌。四周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像是从出砖后的窑洞里散发出来的,雨幕遮盖了红红的砖墙旁密密的树林的影子......”(《背景》)
“一九六七年春天,赵瑶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刑场。”(《风琴》)
......
下“雨”本是一种客现的自然现象,然格非将其频繁地引入小说中,并在每次有“死亡”发生之时运用,可见“雨”是渗入他的主观情思的物象。格非在2000年上北京之前都是在南方生活,南方多雨,而雨往往给人纤细、柔婉的印象,易于产生潮湿、阴郁的氛围,诱发回忆与想象,这就令格非自然而然地以“雨”这一南方多见的物象作为抒发幽思的寄托。上述的篇目中,格非都以“雨”意象传达人物死亡时的悲凉、伤感情绪,“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格非“死亡”叙事的象征。
除“雨”之外,格非早期小说的“火”意象也有着特定的指示意义。《大年》中写道:“昨天夜里,厨子在出炉膛灰的时候。不慎引着了麦秸,厨房里大火蔓延起来,烧坏了两张桌子和一些水桶。这件事并没有酿成大的灾祸,但是它的不祥的阴影却一直跟随着他。”文中的年前厨房失“火”在丁伯高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被视为“不祥之兆”,这为随后丁伯高被杀、家庭破败的悲剧作了一个寓言式的铺垫。长篇小说《敌人》书写赵家大院的崩溃历程,文中开篇就写到一场大火。“西北方的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仿佛落日时的情景。”赵家继一场大火后就笼罩在寻找敌人的阴影中,接二连三地遭遇像谜一样的恐怖事件与死亡,小说中家长赵少忠甚至还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部小说正如古罗马著名的天主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所说:“我心就是我的仇敌。”小说中,大火已然消失成一种记忆,但赵家大院的人们及当地的村民却长期受到这场大火的困扰,可见,不是大火造成了毁灭,而是人们由大火引起的恐惧心理派生出敌人,使人们在寻找敌人的过程中一个个地走向悲惨的命运;而赵少忠弑子举动使恐惧消失,使这个家族摆脱掉“敌人”的魔爪,回归到平静的生活则表明,这个赵少忠一直在寻找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这样,我们不难理解小说传达出的这样一个主题观念:“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内心中那些阴暗的品性。”(评论家谢有顺语)这两部作品中,“火”物象的出现是一种晦气,造成了“不祥的阴影”,与小说的哲思主题紧密相联。“火”的意义虽单一,却异常深刻,读之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与前期作品相比,格非后期作品中物性意象的意义则大多是层出不穷的。《人面桃花》里的“桃花”是一个古典意象,意蕴颇丰。结合标题“人面桃花”可知,小说中的“桃花”有“美女”之意,象征着秀米的倾城之貌。陆侃、张季元、秀美都为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劳心劳力,“桃花”就与“桃花源”的人生理想契合。“桃花”绚烂、艳丽,最终却难逃飘零的悲惨宿命,象征着悲情,这正合于秀米多舛的人生际遇和“桃源梦”的破灭。《山河入梦》之“梦”,既代表了谭功达壮志雄心的梦想,也寓示着他最终有梦难圆、如南柯一梦般的“一场空”的悲剧。此外,还有“金蝉”和“花家舍”意象值得一提。它们不仅本身涵义丰富,而且在动态变化中展现出更深层次的寓意。“蝉”是我国古诗中的“高洁”意象,“金蝉”作为《人面桃花》中计划实现“大同”的头领之间的重要信物,在此代表的是革命事业的纯洁与高尚。它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三次,其一是张季元离开普济时送给秀米,暗示秀米将加入革命;第二次于桃源小岛,韩六送给秀米,后来这枚金蝉随小东西入葬,代表爱母的纯洁之心和革命事业的失败;第三次则是秀米回普济寂然度日时,灾年里用金蝉换不来粮食,这是对革命事业的彻底否定。格非在这样三次环境的变化中,以“金蝉”为线索,千里伏脉地寓示了秀米革命事业由兴起到湮灭的完整过程,文中的“金蝉”意象可谓绝妙之至。再者,花家舍是“江南三步曲”系列中一个内核式意象,它的名称一成不变,内质却在各个时代的洪流中大有迥异。在《人面桃花》中,它是王澄观倾尽毕生的桃源小岛;《山河入梦》里,它是郭从年的共产主义新村;而到《春尽江南》则成了富有现代商业气息的“富贵温柔乡”。花家舍存在着被构建与消解的两重性,桃源小岛在环境上具备世外桃源的特征,却是利用强盗、土匪建成,到处是江湖血腥之气;共产主义新村有着理想的物质生活条件,仍充满无孔不入的特务性的秘密监督,把人规格化、模式化,而现代商业性的花家舍则从外观到内质都完全没有了理想的色彩。格非不仅以这样横纵向对照的方法展现出花家舍的多样性、复杂性,还以花家舍的变迁寓示着时代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花家舍在前两部作品中是乡村形态,代表主人公的“社会理想”,后一部则变身为现代化的城镇,转向“社会现实”。格非就是在这种动态的意象展示中传达出“文化反思”的主题: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传统文化的因子已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植于每一个国人的心灵深处。而乡村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发源地,格非笔下的花家舍由乡村变成城镇,象征着西方文明入侵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

《边缘》
以上的分析表明,格非笔下的物性意象在精神内涵上发生了改变,意象的象征意义趋向多样化。格非前期倾向于择取一个具体的意象,使它在各个文本中反复出现,传达某一种特定的抽象意义。后期则要么选择本身就意义丰富的意象,如上文中内涵多样的传统文化意象“桃花”和字义多重的“梦”;要么自主赋予意象多重精神内涵,从而在多重的内涵中形成更复杂的“张力”。“张力”的诗学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美国现代批评家艾伦·退特的《论诗的张力》,“我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而罗伯特潘沃伦进一步指出张力“存在于具体与抽象之间;存在于即使是最朴素的比喻中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于美与丑之间;存在于各概念之间。格非小说中的意象皆是具象与抽象意义的结合,为小说增添了文学张力。而后期创作中,物性意象意义的多层面、多向度性,使整个文本空间内的冲突多样化、丰富化,积聚了大量的诗性张力,让意象在多样化意义的相互交织中强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内涵。如上文中的“花家舍”与“金蝉”意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以小见大地勾勒出了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有限的形象蕴含着无限的意味。
(三)音乐:由“边缘”到“旗帜”
美国评论家勒内·韦勒克曾指出:“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统再生出意义。”可见,音乐与小说艺术门类是相通的。而小说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如果从音乐、从其他艺术中汲取养料,便能萌发出新的生命之花。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把小说与音乐相比较不是没有益处的。”格非作为小说家,对音乐有着独到的见解与阐释,并且渗入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音乐是人性最基本的表达,有着优美的旋律、动感的节奏,能带给人各种各样的听觉感受与心理情感体验,对音乐的体味与欣赏往往因人而异。而格非对音乐的会意更像是一种机缘。“我总是凭借音乐来回忆一些往昔形象的片断,有些事情我原先以为没有经历过,可是某一种特定的旋律又会将我带到它的边缘。”音乐能令格非沉浸于回忆中,继而令回忆起来的事物或情景为格非提供写作素材。比如:《背景》就是格非听肖邦的《即性幻想曲》后回忆起许多年前的往事而写成的。而在创作前期,格非的《风琴》中反复出现类似这样的句子:“在老式风琴沉闷芜杂的乐声中,赵瑶完全忘记了时间。”“风琴的声音依然在延续......所有的一切,战争、恐惧、屠杀和愤怒,都在琴声中变得遥远了。”在战争的年代里,音乐是赵瑶精神的避风港,可以令他暂时地忘记时间、忘记伤痛。由此可知,在创作前期,格非就已着重音乐艺术感染力的刻画,格非作为创作者及其创造出来的人物都在音乐中得到一个自足的空间,从音乐中获益,格非是借以创作,赵瑶则用来逃避现实。总的来说,格非的小说在前期对“音乐”这一物象有所涉及,后期作品中“音乐”意象更是频繁出现,有的小说甚至通篇与“音乐”相关,且音乐在文本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后期作品中,格非的《戒指花》、《人面桃花》、《春尽江南》、《隐身衣》等皆有音乐的描写。《戒指花》中一首悲歌贯穿全文,奠定小说忧伤的情感基调。而最后以童歌结尾,唱出一个失去双亲的小男孩的心酸,并以小男孩主动唱歌给丁小曼听的纯真美好反讽新闻报业明知是假也要报导的虚假与实利主义;《人面桃花》里“瓦釜之声”能预知吉凶未来。小说第一章,写秀米第一次听到时,“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飘在空中,最后竟落在了一个荒坟上”。再一次叩击时,“那声音让她觉得伤心。那声音令她仿佛置身于一处寂寞的禅寺之中......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消逝,像水退沙岸,又像是香尽成灰。”秀米从美妙的瓦釜之声里感受到一种悲伤的情感,在此,格非巧妙地以音乐之声来暗示秀米被抢入土匪窝后的不幸遭遇与命运。而《春尽江南》中,音乐成了治疗疾病的处方,出现“音乐疗法”,用精神的艺术去治疗身体的病痛。小说中写到谭端午尝试用音乐治疗妻子庞家玉的强迫症与抑郁症,庞家玉“在音乐声中,她仿佛坐在一个深宅大院中。阴暗的房中燃着的一支香,烟迹袅袅上升,杳杳与梦。屋外却是一片灿烂的金黄,俨然就是花家舍岛的那片晚春的油菜花地。”美妙的音乐使庞家玉暂时忘却了俗世的纷扰,进入到安宁、纯净的境地,从而缓和了内心的冲突,也促使她后来由功利主义转向对爱、美与生命自由的关注。格非在一次关于《隐身衣》的访谈中曾表示,他在《春尽江南》中有所节制地写音乐,仅写到音乐疗法,原本要用的音乐材料因怕把握不当都搁置一旁。而到了《隐身衣》,则用上了那些材料。诚然,《隐身衣》里,格非将“音乐”的融入发挥到了极致。小说把音乐设置成这部小说的一个核心元素,用音乐来图解世事。以主人公城市手艺人崔师傅为中心,其顾客是知识分子和有钱的老板,他们俗气浅薄,把高档的音乐设备当装饰,顾客之一黑社会人员丁采臣居然被逼而坠楼身亡;其亲人如妻子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出轨,提出离婚,姐姐则在其行业衰落、无处栖身时,全然不顾亲情地逼他搬家,令崔师傅只好卖掉珍藏多年的音响来换得一个新的住处;其朋友颂平之,有一个地下音乐室,在其中放着或高雅或低俗的音乐,与各色人物进行黑暗的浊名污利交易。格非以崔师傅这个音乐器材经营者的音乐品位及其行业的没落,书写各种社会现实,折射出了消费空间对人文精神和信仰的挤兑。同为音乐发烧友的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说:“这位老兄听了这么多年的音乐,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写和听,终得以在这部小说里交汇,形成玄机和奥义的层叠。”诚然,这部小说以音乐把世事诠释得淋漓尽致,音乐与文学交流、融合,可谓是格非在小说中融入其它艺术门类的一次成功勘探。
格非在后期的创作中,对音乐的表现不只止于小说人物对音乐的欣赏,音乐对人物精神的作用,而是灵活地将音乐用在小说的各个方面,或用来奠定小说基调,或借以暗示人物命运,或当作人物精神出问题后的治疗之法,最深入、最有特色的则是用作图解世事,达到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格非小说中“音乐”这一意象从量上来说,描绘音乐的作品增多;在质上,格非对音乐的表现更多样、更深刻。格非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有《边缘》与《欲望的旗帜》这两部长篇小说,前者透视人的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后者高举“欲望”的旗帜,小说标题与内容相统一。而音乐意象从量和质的角度发生了由简入繁、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故在此,笔者将格非小说“音乐”意象的流变概括为:由“边缘”到“旗帜”。
二、格非小说意象流变探因
以上笔者从意象内质、意象使用情况上对格非小说前后期的人物意象、物性意象流变作了一番解读,就意象内质来说,格非小说的人物意象由“扁型意象”变为“圆型意象”,物性意象的内涵由简单趋向复杂;而意象的使用上,音乐意象分量加重,甚至一度成为核心式意象。以下笔者将探究其意象内质与使用形势流变的原因,以此来考察格非在小说中的意象设置情况。
(一)审美观念变化
格非曾在新世纪的一次访谈中说:“我认为应该重视中国的小说叙事传统,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体验。如果说是校正,首先是个人校正,需要校正的是我个人在30岁前看不起中国文学特别是传统小说的错误。”格非谦虚的言词道出了其在不同人生阶段审美观念的不同,而这种审美态度的不同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他前期小说在文学风格上无一例外都具有先锋文学的“典型特征”,犹如一座座神秘的迷宫,一般只有学识较深的少数学者才能读懂。而新世纪以来,格非创作了“江南三步曲”、《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重视人物刻画、关注叙述故事、凸显思想内容的可读性作品。格非的这种改变并不是为了迎合读者,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消费文化的环境中重新审视了先锋叙事,重新发见了“传统文学”。格非小说中的意象内质的变化,与他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关。

《欲望的旗帜》
先锋文学最初是以反叛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可概括为“形式革命”,这种写作存在着明鲜的局限性,从而使先锋文学难以为继。其局限主要有:过于偏重形式,忽视或难以发见深层次的“精神内蕴”;破除原有的写作模式的同时,建立起了一套破碎的更为明显的模式,走向了另一种模式化,可谓走向了“形式的疲惫”。一部作品由形式与内容两部分有机组成,无视艺术技巧而只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固然不可取,但一点也不表现生活的本质也不能算是优秀的作品。先锋文学的形式极端化行为,恰恰牺牲了使小说更有永久生命力的根本性的东西,更有价值的深层次精神内蕴,其内在的文本动力缺失,而到了90年代市场化的环境中,更是在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难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愉悦。格非早期创作的发展也不例外,以致使他曾在先锋文学退潮时曾搁笔过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在文坛沉寂了近十年。面对创作遇到的问题,格非与先锋文学的其他作家一样都采取了创作转型的方式,格非坦言:“我自己的写作一度受西方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影响较大,随着写作的深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寻找汉语叙事的可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诚然,传统小说因其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线索以及丰富的思想内容等而具有可读性,享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在时代的浪潮中其文学魅力也毫不褪色。格非就在先锋文学的消退中对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学进行了全新而深入的审视,从否定、颠覆传统小说转变为对小说“传统”有所肯定、有所倚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渊远流长,它亦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基础。英国著名的批评家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指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在此,艾略特揭示出了作家与“传统”的关联,那就是: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与传统构成某种关系,作者不断地从前人那里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叙事资源丰富多彩,不难发现,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对古典小说不同文类的重新择取与书写从未间断:鲁迅《故事新编》的神话题材,沈从文学习唐传奇,汪曾祺之于明代的小品,张爱玲与张恨水之于章回体都体现出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的吸收与借鉴。而当代的格非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在后期创作理念上认为“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回应”,“现在我觉得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要获得新生的话,只能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因为人物与故事才是小说的血肉,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就有着非常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及臻于完美的结构。”格非从先锋文学的退场中意识到了传统文学的优越性之所在,认识到表现小说人物与思想意蕴的佳技,那就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有所回应,对传统小说中体现了小说本质的东西予以重视,比如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富有故事性,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思想蕴涵等等方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后期的作品中的人物意象变得丰满具体、真实可感,物性意象注重多重内涵的表达了。
(二)个人爱好及艺术探索
格非后期创作中的音乐比重变化与其个人爱好及消费背景下的艺术探索有关。“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周围有很多同好,或者说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很久以前,我对于听古典音乐的这个群体就开始了思考。”格非如是说。格非精通音乐,不只是在曲目上精通,还跟真正了解音乐硬件原理的人有很多交往,在这两方面都是行家,这就为他在小说中引入音乐元素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当然,其融音乐于小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来源于格非对小说艺术积极专研的精神。格非一直用实际的创作实践对小说艺术进行创造与革新,他从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创作早期就对小说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他的早期小说,《迷舟》(1986)、《大年》(1988)、《风琴》(1989)、《敌人》(1990)、《唿哨》(1991)被评论家们当作新历史小说来研究,《陷阱》(1987)、《褐色鸟群》(1988)、《没人看见早生长》(1988)、《背景》(1989)则被认为带有现代派的印记。而到了新世纪,格非认为对小说艺术的重视与创新势在必行。格非曾在理论专著《小说叙事研究》中道:“小说艺术的发展在电影、电视的挑战面前似乎日益感到捉襟见肘,很多人在年代久远的过去所预言的‘小说的死亡’,在现在看来,如果未必是一种现实,它至少也不是杞人忧天。”的确,1989年以前,中国文学领域吹奏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旋律,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社会背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原则的驱动下,社会趋利奔钱,家庭、学校至整个社会都卷入恶性竞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追求自身价值,且以等量的看得见的物质来衡量。这个物质霸权的“大时代”背景里,文化格局扭曲,正如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写道的“海子死了”,寓示着文学的边缘化。2014年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阅读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52.8%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者比较少。这些数据表明生活压力大、追求效益的时代,我国国民的书本阅读日益匮乏。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格非自然对小说的发展满怀忧戚。他在后期把音乐大量地掺入小说,寻求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结合,也正是源于他在市场氛围中对小说艺术的忧虑与孜孜不倦的探索。
结 语
格非小说意象的转变,是格非小说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先锋文学整体走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文学的反叛,进而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与理论,格非早期创作的价值不是在于产生文学经典,而更多地体现在“先锋”的写作姿态与对小说形式的勘探上,意象只是其小说的一个“形式”表现,一个符号式的工具。而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则是格非以现实关怀着眼当下实利主义的时代风向,以知识分子式的智性思考回归传统,呈现“有现实意义”的小说叙事方式和思想主题,为我们带来先锋文学转向后新的思索,意象则变为一种具体明晰、意蕴深厚、关注现实的存在。
格非在小说叙事上的意象运用转变,来源于其强烈的自省意识和积极专研的精神,来源于他在时代变换中对先锋文学和传统文学、对小说艺术表现的思考,然而,格非在新世纪的时代环境中的所有转变都是建立在对纯文学的坚守的基础上,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言:“商业熏染在当今社会中一些名作家开始有了变化,迁就市场,但格非用他的作品证明了商业熏染中他仍在坚守着自己。”另外,创作家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与作家早期的创作泾渭分明,我们往往能从作家近期的作品中体味到作家从前的风貌,格非的创作转变亦是如此。格非小说走出前期小说“空缺”与“重复”的迷宫的时候,我们仍可以在后期小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隐身衣》等“写实”系列里常见人物经历的省略之神秘,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里的有着暧昧笑容的胡惟丏、《隐身衣》里毁了容的女子,此处,读者还是可以看见小说家煞费苦心设置的谜语。再者,对于格非后期小说中乡村意象的描绘,人物名称使用上带有古典意象的痕迹等等,我们还是能从中领略到格非对乡村意象和古典意象一如既往的偏好。所以格非在意象上的流变是一种在变化中坚守,在坚守中勘探的流变。
当今多元的文学样式中,格非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格非对文学发展的思考、对文学创作的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格非是“学院”型作家,自称为“业余作家”,他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来进行自由创作,格非也还比较年轻,我们有理由相信,格非将创造出更多的作品来阐述他对世界的关怀,来应对小说艺术面临的严峻挑战。新的时代格局对汉语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格非的写作还有哪些可能性,这是作家努力的方向,也是笔者在研究其小说过程中始终停留在脑海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