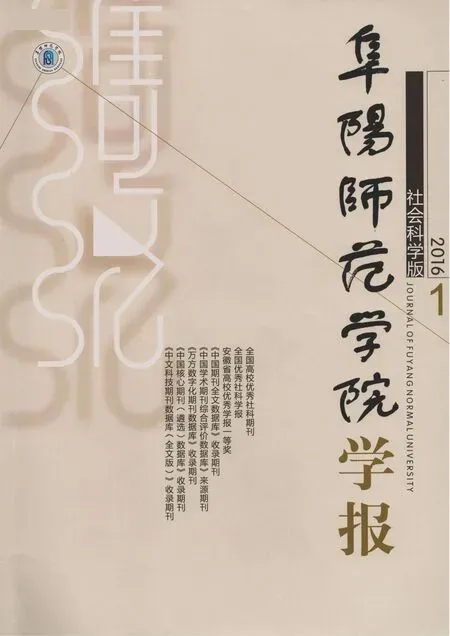论魏晋士风嬗变的历史、时代动因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论魏晋士风嬗变的历史、时代动因
刘运好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士风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术变迁的历史投影。魏晋是士风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从政治文化说,魏晋承袭汉代而来。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直接影响时代的学术变迁,而时代的学术变迁直接影响一代学术风气和士人价值选择,因此在观念上又深刻影响了一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立身行事的基本作风,从而成为影响一代士风形成、变化的主要时代动因。然而,发端于汉末的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魏晋士人思想、观念、行为所表现出的基本特点,而主体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错综交织、儒家思想与玄释思想的错综交织,又使得魏晋士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显得异常复杂而曲折。
关键词:魏晋士风;主体意识;意识形态;学术变迁
士风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术变迁的历史投影。与汉唐相比,魏晋是士风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从政治文化说,魏晋承袭汉代而来。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直接影响时代的学术变迁,时代的学术变迁直接影响一代学术风气和士人价值选择,因此在观念上又深刻影响一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立身行事的基本作风,从而成为影响一代士风形成、变化的主要时代动因。然而,魏晋士风的历史呈现似乎又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发端于汉末的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魏晋士人思想、观念、行为所表现出的基本特点,而主体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错综交织、儒家思想与玄释思想的错综交织,又使得魏晋士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显得异常复杂而曲折。士林主体意识的变化曲线,也是魏晋士风的变化曲线。
一、汉末清流:延续与抉择
魏晋士风的变化发端于汉末。关于汉末士风,罗宗强先生以“士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士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士人生活情趣、生活风貌的变化”分析之[1]1,32;蓝旭又从“婞直之风”“自适任情”“名节与礼法的松动”概括之[2]。就对历史描述而言,这些阐释无可非议,但似乎都没有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其实,汉末士风以清流集团为代表。清流集团裁量执政与荣华丘壑的两个极端,恰恰包涵着对恢复名教秩序的政治热情和“汉官威仪”的政治遥想。在骨子里,前者是对两汉儒术精神的延续,后者是对先秦儒学精神的延续。而“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的群体意识觉醒,则是在儒道精神的双重砥砺下所形成的带有特定时代的士风特点。对两汉儒学、儒术并重的传统有延续,也有抉择。
“独尊儒术”是武帝以后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而儒术既包括儒家之学,也包括儒家之术。然而,政治秩序稳定,则学有所成,术有所用;政治窳败,即使学有所成,术亦无所用。术有所用,士子情有所向,志有所归;术无所用,则情失归依,志亦散漫。由怀禄事君,安于依附皇权,到裁量执政,力图“澄清天下”,是汉代士风嬗变的基本轨迹。范晔对这一士风的嬗变作了明确阐释,《后汉书·党锢列传》曰:“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3]2184-2185也就是说,自武帝至桓灵之际,士风凡三变:
第一,崇尚儒术,经世致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儒学藉经学化运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独尊儒术”成为官僚选拔的制度依据,于是士子习儒,学而优则仕成为个人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这就从观念形态与人生践履上影响了士人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追求。一方面“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动了整个社会崇儒读经风气的形成,促进了儒学的发展,遂使传业者渐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甚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4]3620-3621;另一方面“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人们又特别注重儒家之术的应用,人守六艺,家抱章句,其目的是为了通经致仕。在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中,培育了士大夫强烈的皇权依附意识。虽经过王莽篡政的短暂变化,但是东汉光武中兴,汉德重开,仍然秉承以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拉紧了士大夫的皇权依附意识。所以,尊崇儒术,怀禄事君,具有强烈的皇权依附意识,是两汉士风的基本特点。汉末裁量执政,甚至污秽朝廷,实际上是对此前两汉士风的强烈反弹。
第二,荣华丘壑,注重名节。因为君主荒淫,政治窳败,国柄操纵在宦官手中,“士子羞与为伍”,于是部分士人则选择疏离政治,归隐丘壑。两汉隐逸之风,始于王莽篡政。王莽篡政,使原本怀禄事君的士子耻于高官厚禄,在精神上归依失所,于是安贫守道,以归隐丘壑为荣,从强大的皇权吸引力中自觉游离出来,如“王莽居摄篡弑之际”,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汉书·桓谭传》);崔篆之兄善于投机,为王莽宠信,母博通经学,亦受王莽礼遇,而崔篆认为家门之耻,遂隐居不仕。这一士风的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部分士子游离于王莽政权之外,并非消解了皇权依附意识,而骨子里恰恰包涵着对“汉官威仪”的遥想,心理深层也恰恰是陷于依附刘汉皇权而不可自拔。重名节,是恪守忠于汉王朝的名节。二是这种士风的转变深刻影响了汉末士风的形成。如桓帝时,魏桓不愿“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而隐身不出;徐穉虽受“安车玄纁,备礼征之”的礼遇,亦不应征;姜肱、黄宪、申屠蟠、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征为博士,皆不至等。东汉尚名节之风始于此时。尚名节是士林群体自觉的一种标志。然而,其中亦渗透深厚的对现实政治的绝望情绪,如徐穉所以屡征不仕,是因为“大树将颠,非一绳所为”,而不愿过着“栖栖不遑宁处”的生活。汉室衰微,既无法力挽狂澜,也只能避世逃义。
第三,裁量执政,激浊扬清。逮及东汉和帝之后,幼主即位,太后临朝;特别是安帝虽享国日长,然权归邓氏,“始失根统,归成陵敝”,而且“计金授官”,使王朝呈现出“惟家之索”[3]243的衰瑟局面。历顺帝而至桓帝,先是外戚梁冀跋扈专权,梁冀被杀后,又权归宦官。此后于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使国家职能部分丧失,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空前破坏,皇帝成为窃国者操弄权柄的玩偶,这不仅堵塞了恪守儒术以求仕宦通达的读书人进身之阶,也掏空了西汉以来所培育的士大夫集团的皇权依附意识。于是士林阶层,积极用世者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奋起抗争,裁量执政,激扬政治。士大夫借权行道,太学生波荡从之,在野名士又声援响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清议朝政的风气。历两汉而建立起的士大夫的皇权依附意识,却因为“主荒政缪”的现实而被打破了。士大夫失去了政治上的精神皈依,也打碎了既有的政治理想;饱学经艺以求仕进的太学生以及藉声名以求荐举的在野名士也都失去了进身之阶,使怀禄事君成为了一种空想,于是才出现“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婞直之风。
汉末士风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由“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发展到后来的“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才逐步形成了企图以儒术纲纪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以太学生、在野名士为两翼的清流集团。而“澄清天下”则是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政治理想,如太傅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司隶校尉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5]1、6等等。这一阶层裁量执政,是为了重构儒家名教“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匡复两汉既定的政治秩序。虽然党祸酷烈,然此风尤炽。党人李膺、范滂即因党锢之祸而成为人格名节的楷模。这种名节人格也成为清议品题。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公卿皆畏,莫不侧席。”[6]432太学生同声高论,加之“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清议风起,一方面公卿畏惮,酿成党祸;另一方面互相题拂,激扬名声,则又使士人更是以名节相高。游离于现实的皇权而崇尚名节,也标志着士人人格意识的自觉,表现出汉末士风的新变。
然而,汉末士风之变,形式上虽趋新,骨子里却守旧。第一,“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甚至污秽朝廷,政治取向是在于“澄清天下”,恢复两汉既定的政治秩序,重铸辉煌的汉官威仪,而非有意打碎既定的政治秩序。第二,荣华丘壑,任情自适,表面上疏离了皇权政治,但是这种疏离是对现有皇权政治的疏离,而不是对整个刘汉皇权的疏离,是汉室衰微、大权旁落之后,部分士人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后的心理失落,是对现实政治窳败的失望甚或绝望所造成的。这恰恰符合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人生践履原则。中国的隐士从来就不能算是真“隐”,许由之类的真正隐士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心造幻影,所谓的“隐”多半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之流,“隐”的背面正是源于对政治的“诗意激情”——虽自适而并非任情!第三,重“保身怀方”“去就之节”,固然包涵着士林主体人格的意识觉醒,表现出与两汉盛世时士林世俗人格的差异性,但是所怀之“方”仍然是以儒术或曰经术为核心,所守之“节”也是不事二主的忠臣之节,还是属于思想上的“保皇党”之类。也就是说,汉末士风在新变中仍然保持与两汉士风的历史连贯性。本质上也只是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化积淀于士人心理而表现出的流风余沫而已。而且清流集团是以儒学思想为本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也体现了两汉一以贯之的以学为体、以术为用的经学传统。直至曹魏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士风才真正发生了部分转向。
二、汉魏之际:扬弃与超越
建安(196-220)虽是汉献帝刘协年号,但大权已落于曹操之手,标志着曹魏集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士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由皇权依附走向集团依附,再由集团依附复归于皇权依附;学术上,由重儒术走向重儒学,再复归于儒学、儒术并重;行为上,由通脱简易走向遵循名教,再由遵循名教走向放达任诞。既表现出对汉末士风的扬弃与超越,也表现出后一历史阶段对前一历史阶段的扬弃与超越。
在政治上,曹魏士风的转向始于董卓乱政。董卓乱政的最直接后果是:在皇权权威上,打碎了“汉官威仪”,导致了皇室流播,百官沦落;在权力职能上,打碎了皇权的集权专制,出现政出多门;在权力分配上,地方军阀藉讨董卓之机迅速崛起,拥兵自重,打破了中央对地方力量的制衡。至此汉室已名存实亡,使一向恪守皇权依附的士大夫在精神上“不知所归”;而天下板荡,生灵涂炭,又使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渴望救百姓于倒悬,于是崇拜戡乱救世的军事精英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孔融《六言诗》“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正是这一心理的典型反映。在连年征伐吞并其他军事集团的过程中,以社会精英为首的军事集团逐渐发展为具有国家性质的政治集团,并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一方面这些政治集团为了逐鹿中原,更加拼命地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人才也择主而依,希望建立事功,于是那些在精神上崇拜军事精英的士林群体,逐步地向崛起的政治集团靠拢,士大夫原有的皇权依附意识也逐步向集团依附意识位移。士子依恃军事集团,或以庇身远祸,如袁焕、管宁;或可缘夤仕进,如邺下文人。在这种背景下,甚至出现了士大夫官僚阶层宁为魏臣而不为汉官的现象。如《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自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7]268夏侯惇所言之臣,则指魏王的私臣,宁为魏臣,不为汉官,则说明至少在政治集团内部已经完全消解了曾有的皇权依附意识。当初,曹操被封为魏公,荀彧上书明确反对,而后来曹丕篡汉自立,却成为政治集团内部一致的政治导向,显然与士大夫政治心理的转向密切相关。但是,政治集团一旦升格为国家机器时,重新建构士林对新皇权的依附意识,则又成为新上位的君主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曹丕即位后,立即崇儒尊经,试图以建构儒学国家意识化的手段全面恢复汉代一元政治文化,士风也由集团依附而复归于皇权依附。直至正始后,魏室衰微,曹爽、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的形成,士风才又发生了偏转。
学术上,曹魏士风的转向始于曹操的用人制度。时世动乱,正是用人之秋,于是曹操下令,“唯才是举,名扬仄陋”。然而所言之才,不是饱学六艺、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者,而是治国用兵之才。本来,曹操在破袁绍、平荆州的过程中,已经网罗了大批人才,但还惟恐野有遗贤,远人不附,于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连续三次下令求贤。即便盗嫂受金、背信弃义之徒,只要有定天下、成王业之才,均网罗博赅,为我所用。所以郭嘉“不治行检”,因能“使孤(曹操)成大业”(《三国志·郭嘉传》)而受到曹操器重。曹丕《又与吴质书》所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虽意在赞扬徐干彬彬有箕山之志,但当时“鲜能以名节自立”的士风亦于此可见一斑。曹操虽以申、商、韩、白之术为导向,但那只是拯救乱世的一种战时方略,本质上并未悖离儒家思想。儒法杂糅的思想倾向,重术存学的人才观念,使曹操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兼济之士。所以建安文士,一方面较东汉文士更注重现实,关心民瘼;另一方面又不像东汉文士那样砥砺名节。露才扬己,积极用世,是当时士风的主体色调。隐逸山林,埋首书斋,虽或有之,更多的却是待时而起。如阮瑀在建安中“曹洪欲使掌书记”不就,但是“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7]600。隐居仅仅是等待时机,择主而依,并非真正的高蹈避世。虽有祢衡击鼓骂曹,矫世佯狂,实在是因为怀抱用世之才却不为世所用,而导致心理倾斜的结果。其《鹦鹉赋》借鹦鹉自况,浸透怀才不遇的悲凉,即为明证。文士对自我才能的自信,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是这个时代士林的基本风貌。“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祖德书》),则是上层文士的普遍心态。而军旅之暇,又“妙思五经,逍遥百氏”,也造就了邺下文学、学术的繁荣。黄初以后,曹丕兴学校,崇儒学,整理经籍,进一步推进了经学繁荣,在由儒术向儒学的转变过程中,士风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留心事功而转向留心学术。所以曹魏后期,文学创作由建安彬彬之盛而逐渐走向衰落,学术则十分繁荣。正始学术的繁荣实际上与曹魏士风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
行为上,曹魏士风的转向源生于汉末名士的潇洒风度。汉末名士行随其性,纵意所如,反而透出一种特有的风神气度,如郭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后汉书·郭太传》);符融清谈,“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后汉书·符融传》)等等,皆是不拘形迹,潇洒适性,这种士风直接影响了曹魏士人。建安文人绝少矫饰,通脱简澹,任性率真,纵情自适。即使身为贵胄亦复如此,如曹操与人谈论,或调侃,或正言,一任性情,史书谓之“轻易”(通脱);曹丕“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酌桂酒,脍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大墙上蒿行》),任情自适、通脱放达成为基本行为特点。特别是曹植,接待宾客时,不仅纵论古今,品弹艺文,而且在论谈之中,或澡讫傅粉,科头拍舞,跳丸击剑;或著衣帻,整仪容;或命厨宰,酒炙交至,故邯郸淳一见曹植,即“叹植之材,谓之天人”[7]603。其行为完全不拘礼节,毫不矫饰,纯任自然。这一切必然影响一代士风。可以说,整个邺下文人集团大多以潇洒风流为美。思想活跃,行为通脱,已开正始风气之先。然而,随着新皇权的建立,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逐步恢复,文人亦由通脱简易而转向遵循名教,曹植是其代表。黄初以后,曹植所上奏表,一方面“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为“醉酒悖慢”而追悔莫及;另一方面又陈词慷慨,“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表达杀身成仁的意愿。所上诗歌亦充满对君主的肉麻的吹捧。曹植后期规规于儒,以循臣自居,与前期任纵发扬,随性自适,简直判若两人。直至正始以降,时势迁变,士风才由遵循名教而转向任诞放达。
虽然建安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态度与党人精神一脉相承,孔融、王粲、徐干等出身于汉代世家大族,曹操、孔融等早期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是汉末名士政治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切使曹魏士风与汉末士风具有历史的关联性;但是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由衰微到重建,由重刑名到崇儒术再到援道入儒的思想发展过程,又使曹魏士风在政治、学术、行为上表现出与汉末士风的不同点,尤其是新生代士人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扬弃与超越始终伴随着汉魏士风递嬗的历史过程。
三、魏晋易代:解构与重构
由于曹魏试图重建儒学国家意识化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所以曹丕去世后,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迅即走向衰微,从太和浮华到正始玄谈,虽然立足点并没有偏离儒学,但是在学理上却解构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主体的神圣性;司马氏集团以血腥的手段篡夺魏鼎,又从政治上解构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体的神圣性。于是,司马氏在建立西晋王朝后立即推行文化复古运动,崇经尚儒,重构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儒学的解构与重构,造成了魏晋易代之际的士风始终面临着儒学与玄学艰难的抉择。
正始时期,司马氏集团表面上敦崇儒学而暗地里玩弄权术,使士风又一次发生了偏转。这一时期,历史虽然短暂,士林的分化、士风的变化却相当突出。正始前期,曹爽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争权日趋炽烈,士林大多缘夤权贵,泥身世俗。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术有学者,如傅嘏、裴徽、王肃、钟会等,学有所成,且通于谋术,故事功亦著;第二类是有学无术者,如夏侯玄、何晏、王弼等,学有建树,而疏于谋术,故事功无成。士风之变,一因学理的演进,一因时势的变化。从时势变化上说,高平陵事变后,依附曹爽的文士几乎全被杀戮。面对政局险恶,竹林七贤游于竹林,恣意酣饮,实质是佯狂避世,远祸全身。这类文士,并非完全消解了建安文人的宏远抱负而昏兀颓放。如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所以当时文士出言玄远,惟恐罹谤遇祸。嵇康本是魏室姻亲,为中散大夫。曾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可见还是留心世事的。然魏鼎倾覆,无力回天,惟以逃世而守节,故大将军司马师欲征辟为官,康避之河东。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亦答书拒绝。身处季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有“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7]605。这类文士以“学”为高,以弃世为入世;其“术”不在经世致用,而在批判时世。就儒学而言,正始名士在建构玄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恰恰解构了儒学精神。何晏、王弼以古文经学为根底,援老入儒,创立玄学,造成了“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文心雕龙·论说》)的学术格局。竹林名士则在任诞放达的行为上和援庄入儒的理论上,解构了儒学精神。阮、嵇以儒学为底色,援庄入儒。特别是嵇康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从理论和行为的双向上解构了儒学精神。正始士风与学风互相激荡,造成玄风大炽,以“自然”为大纛,追求超越世俗的任诞放达,不仅与汉末名士的潇洒风神不同,与汉魏之际的通脱简易也有区别。
正始玄风在形式上解构了儒学伦理的秩序,而司马氏集团依靠权谋机诈,弑君篡立,又从本质上掏空了儒学伦理的内核。所以西晋立基之初,一方面敦崇儒学,试图以名教匡救世风,重构一元政治文化以及文士的政治信仰;另一方面又贯通儒学与儒术,选择身怀“道术”之士,充实、更新官吏队伍,为新王朝统一天下服务。虽然西晋的政治文化、吏治制度的建设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对士风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西晋初期,士林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原司马氏党羽,自觉追随新王朝左右,如何曾、王沈、裴秀、贾充、郑冲等。这类人多为西晋开国元勋,表面敦崇儒学,而内操阴柔之术。如何曾以孝道为幌子抨击阮籍居丧无礼,也博得“立德高峻,执心忠亮,博物洽闻,明识玄达”(《晋书·何曾传》)的美誉。但是,也正是他谋废魏主,劝晋王登基,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第二类是由竹林名士分化而来,如王戎、山涛、向秀等,随着西晋王朝建立、政体一元化的完成,他们也不得不追随新王朝,以获进身之阶。如山涛早年为避祸逃身,投传而去,高平陵事变后,政局明朗,他又以宣穆皇后中表亲的身份投靠了司马氏,后来位至三公。这类人大多以超越的姿态明哲保身,以务实的态度选择人生去就,外尚老庄而内崇儒学。第三类或因学而得名,藉名士或官吏的荐举而入仕,如张华因作《鹪鸟赋》而见知于阮籍,由是声名始著。“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晋书·张华传》);或因进入太学藉试经而得官,如刘卞“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晋书·刘卞传》)。这类人守身儒业,以“忠为令德,学乃国华”而见称于世。此外,还有以术立功,因学立名者,如杜预、束皙、刘寔等;亦有超越世俗,专心于学者,如刘兆、氾毓、皇甫谧等。但是,纵观西晋前期,以务实的态度对待现实政治、人生选择是士风的基本特点,士人的人格也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因此贯通儒学与儒术则是其学风的主流,晋初思想家并未脱离具体的治国方略而进入纯粹的理论探讨,显然也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西晋后期,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儒学伦理思想体系的崩离已难以挽回,思想界也无力回天,于是晋初已经沉寂的玄学又开始泛滥,但也有部分名士仍然孜孜于重构儒学的思想体系。是时士林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儒生名士集于一身,如裴頠、郭象。裴頠早期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是一个典型儒生,其《崇有论》虽取玄学的思辨方式,却论述儒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构儒学思想体系的努力。然元康后却以清谈名士著称于世,竟至“時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晋书·裴頠传》)。郭象不仅因《庄子注》“时人以为王弼之亚”,而且善于清谈,赢得太尉王衍“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的赞叹。然裴頠思想以儒学为本,郭象思想以庄学为宗,二者又有本质区别。但郭象又著《论语体略》《论语隐》等经学著作,也并没有忘怀于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第二类是清谈名士,如王衍、乐广、庾敳、卫玠、王澄、阮瞻、毕卓、胡毋辅之等。庄子相对主义哲学是其清谈核心,如《世说新语·文学》曰:“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刘孝标注曰:“夫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一息不留,忽焉生灭。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驰车之轮,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可见乐广是以象征的举动、简约的言词,阐述至与去、生与灭、动与静的相对主义哲学。然而,儒道兼综又是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如玄学名士阮修“好老易,能言理”,却又认为儒玄并无根本区别;乐广以为“名教中自有乐地”,王衍常“自比子贡”,显然都带有浓郁的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元康文士基本上是以世俗的情怀对待功名,以超越的态度对待人生。经学或儒学之学、术,也淹没在玄学义理的探讨中。
简言之,魏晋易代之际,源生于太和时期浮华之风的正始玄学,虽援道家思想以入儒学,形成了与儒学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然正始玄学的哲学根底是建立在古文经学之上;竹林玄学的“越名任心”的自然观也只是反对司马氏伪饰名教的利器,骨子里仍然是名教的维护者;司马氏集团虽然行为上打碎了儒学的政治伦理秩序,在理论上却还是以儒家名教作为虎皮上的大旗,解构儒学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学。入晋之后,前期致力于儒学的国家意识化的建构,后期即使是清谈名士也并没有完全消解儒家政治伦理秩序的意义,所以解构与重构并存,一直是魏晋易代前后的士风与学风的基本特点。
四、两晋之际:冲突与兼融
惠帝即位后,社会迅速进入动荡时期,先遭内乱,后罹外患,终于导致西晋覆亡。东晋偏安江左,虽获小安,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势,内忧外患,犹如中朝。东晋士风也几乎完全延续了中朝士风的余习,唯是又接受了佛学的浸润而已。一方面清谈玄理弥漫朝野,以消弭南渡士族与本土士族的文化和利益上的隐性冲突;另一方面名士名僧交往日益密切,谈玄说佛,也使佛教与本土文化由冲突而走向融合[8]。以融合儒玄、儒释的清谈,消解现实的心理焦灼;以游弋山水,点缀雅致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精神的超越,是这一时期士风的基本特点。
东晋玄风大炽,直接源自永嘉学风和士风。永嘉名士虽处乱世,而玄谈不绝。著名有卫玠、谢鲲等。卫玠既风姿俊爽,又善清谈,在永嘉名士中颇负盛名。《卫玠别传》载:“玠少有名理,善通老庄,琅玡王平子……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5]447王平子名澄,宰相王衍之弟,也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名士,听卫玠谈理,至会意精微处,竟绝倒于坐,可见其清谈警动人心的魅力。又《世说新语·赏喻》载:“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以“正始之音”评价卫玠,其清谈义理的深刻也可见一斑。谢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晋书·谢鲲传》)。谢鲲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且不慕仕途,不拘礼法。初入仕途即遭贬辱,别人为之叹恨,而鲲清歌鼓琴,不屑一顾。挑逗邻家美女,女投梭折其两齿,竟泰然处之,曰“犹不废我啸歌”,是典型的风流才子。卫玠于永嘉六年(312)渡江,同年死去;谢鲲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皆是南渡的清谈名士。
东晋玄风大炽,亦有深刻的时代原因。东晋偏安江左,此时北方已陷入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北方士族大量渡江南迁,将中朝的玄学文化与清谈风尚带到了江南。而南渡士族偏安江左,面对山河破碎,两都毁弃,而产生了深重的身世飘零与文化飘零的双重感伤,于是崇尚虚无的玄学,成为士族摆脱心理困境、寻求安身立命的一剂良药。另一方面,南北士族不免有利益与文化上的冲突,执政者往往通过玄言清谈的方式,协调士族内部关系,促进南北文化融合,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所以,东晋玄言清谈领袖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导和谢安。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晋书·王导传》)。青年时期处于玄风盛行的中朝,时风习然,故善清谈。渡江之后,身登宰辅而褒赏清谈,成为清谈领袖。《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其实王导倡清谈并非如一般名士,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而是别有政治意图。他任丞相,“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以清静无为的治政方式,调和士族内部的关系,维持江左偏安局面。所以,王导提倡清谈,固然与其崇尚老庄思想有关,但也成为其治政的一种手段。“新亭对泣”的故事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继王导执政的谢安,也是著名清谈家。少年即以清谈出名。《世说新语·赏誉》曰:“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王濛、王修父子均为东晋清谈名士。王濛竟赞赏谢安清谈不倦,词锋逼人,可见其清谈水平之高。其未出仕时,寓居会稽,弋游山水,所交游的王羲之、支遁、许询等均为东晋名士。四十出仕,指挥过著名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苻坚,使江左转危为安。他也曾试图收复北方,因国势衰弱而未能如愿。故其执政亦主张清简,“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他崇尚清谈,与谢安有同样的政治意图。《世说新语·言语》曰:“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谢安已经清楚认识到,国事衰瑟,无力用兵北方。在治政上,以“秦任商鞅,二世而亡”为鉴,只能推行无为而治,致力调和士族内部矛盾,使“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才能维持残山剩水的半壁江山,非不为而不能有所为。
因为王、谢是江东世族,又是东晋政权赖以支撑的重要政治力量,所以王、谢褒赏清谈,上影响帝王,下影响公卿士族。东晋开国之君,元、明二帝崇玄礼佛,“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5]323。其后的简文帝未为帝时即为清谈领袖,《续晋阳秋》曰:许询“能言理,简文皇帝、刘真长说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膝赏对,夜以系日”[5]491。于是朝野上下,无不以清谈为尚。当时清谈名士的身份,有大臣而兼名士,如殷浩、刘惔、王濛;有文人而兼名士,如王羲之、孙绰、许询;有高僧而兼名士,如支遁。东晋清谈,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名士为清谈之便,常筑室群居,而所居之地则为佳丽山水。“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老庄超然冲虚的人生境界,成为文人的一种群体性实践行为。而且“以玄对山水”,更进一步促进了文人对山水之美的发现。第二,名士清谈,除了主客对语的形式以外,更多是以群贤聚会的形式。《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群贤聚会,“言咏写怀”,不仅探究玄理,也包括真切的人生体悟。《楚辞·渔父》是一篇情理并茂的文学作品,支遁通释其意旨竟然是“叙致精丽”,必然已超越清谈玄理,也包含自我体悟的文学性审美。可以说,兰亭雅集是东晋清谈的直接延伸。
东晋清谈虽仍然发挥“三玄”义理,但是对玄学义理的取舍则与中朝宗归不同。第一,言《易》理,取王弼之说,特别注意哲学本体的开掘。如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曰:“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5]238八卦只是变化之影迹,天下只是寄“一”之表象。“影迹”“见形”皆以“一”为本体。所论亦如王弼,已经升华到本体哲学的高度。第二,谈《庄子》,发挥向秀、郭象之说,而自铸新说。据《世说新语·文学》所载,刘惔答殷浩问善人少、恶人多的问题,就以“泻水著地”为喻,发挥郭象“独化”思想。诸名士钻研玩味《逍遥游》的理趣,也以郭、向为参照对象。《世说新语·文学》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支遁援佛理以阐释《逍遥》,而且后来“遂用支理”,这就完成了玄释的融合。第三,崇老庄,而仍以孔子为圣人。《孙放别传》记载:“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5]110孙放之答,庾亮称赞有加,足见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之高,表现出鲜明的儒玄融合倾向。调和儒道,在东晋一直不乏其人。
最后说明的是,第一,东晋国家教育衰落,选官唯重门阀,这直接堵塞了寒门庶族以学、术以求仕进的道路,反而刺激了寒门庶族以“学”立身扬名的纯粹的人生追求;这也导致了高门世族不再以追求学、术旌扬家风,而是在清谈玄释中追求人生的雅致。因此,东晋一朝,国家经学衰落,而民间经学鼎盛;高门世族经学衰落,而寒门庶族经学鼎盛。第二,东晋虽玄风大炽,然而抨击玄风、恪守儒者,也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南渡文士如陈頵、范宣、范宁,也有江南本土文士如熊远、戴逵、戴藐、虞喜等。第三,东晋大多数文士超越放达,兼综儒道。东晋的两大文人集团:以支遁为核心的会稽文人集团,以慧远为核心的庐山文人集团,都聚集了大批名士。这类名士“虽然已经渗入了崇尚虚寂的人生旨趣,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但是,玄风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显然还是玄学思潮的产物”[1]307。所以东晋名士与元康名士并无本质差异,大部分是在行为上泥身世俗,在精神上超越世俗。直至陶渊明,真正超越了“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以纯粹自然的人生选择,将玄学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概括言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一直成为纲纪国家职能、政治伦理、国家吏制的主要思想支点,魏晋亦然,因此也成为决定士林的群体意识、价值取向、学术嬗变的深层历史与时代动因。士风的变化正是以上诸多的历史与时代合力所造成的,时代的安宁与动荡、文化生态的自身发展规律也影响士风的变化。士林观念形态的变化又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诗学思想。也就是说,影响诗学的途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以上三个方面特别是士风的嬗变,毫无疑问是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方面,而儒学的经学化则是其核心。
参考文献:
[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蓝旭.汉末士风述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3).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袁宏,等.两汉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刘运好.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J].孔子研究,2015(3).
□淮河文化论坛 主持人:吴海涛教授
Historical and Era Motiv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U Yun-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Anhui)
Abstract:Academic atmosphere is the historical shadow of the ideology and academic changes in one era.Wei and Jin Dynasties are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drastic change in the academic atmosphere.In political culture,Wei and Jin Dynasties follow Han dynasty.The national ideolog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on academic changes of the times.Academic changes of the times also have an immediate impact on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scholars’ selection on value in one era.So,in perception,academic changes of the time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the life attitudes,personality spirits,and the basic style of their behaviors.And these have been the main motiv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However,the awakening of scholars’ subject consciousness,originated at the last reign of Han Dynasty,is the essential feature,which are reflected in scholars’ ideas,perceptions,and behavio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With the mixture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group attached consciousness,the Confucianism and Metaphysics,the awakening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scholar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ppeared extremely complicated and tortuous.
Key words:academic atmosphere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deology; academic changes
作者简介:刘运好(1955- ),男,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08BZW032)。
收稿日期:2015-11-06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1.001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1-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