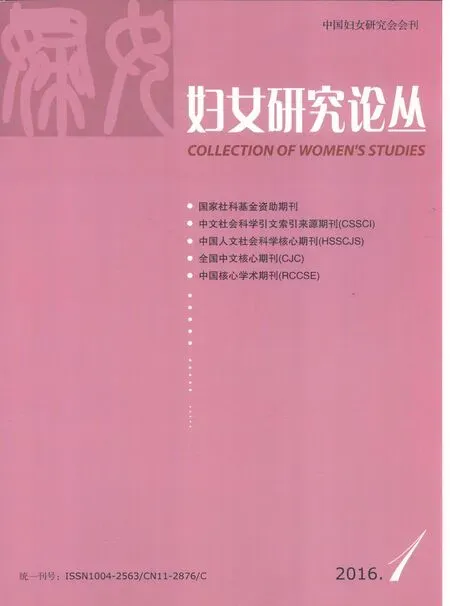何殷震的“女界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何殷震的“女界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何殷震;女界革命;女权;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清末中国女权主义思潮发轫阶段,除了自由主义女权还有一支无政府主义女权思潮。何殷震的“女界革命”的构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财婚制度的批评,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构想了一条以“男女革命”为核心的追求人类彻底平等的社会革命道路,即“女界革命”的道路。何殷霞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女界革命”的构想,既与晚清的自由主义女权又与无政府主义内部的男权两边展开对话,对于两者既有吸纳又有批判与超越,这种双重特性使何殷震的“女界革命”论述在晚清直至今天的女权论述中独树一帜。
如果把历史镜头回放到近代女权主义思潮源起阶段,除了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女权这一脉络,还有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思潮。对这一思潮,只有少量研究者进行研究,大众知晓度甚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女权有其付之实践的政治经济框架——民族/民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失去了实践的土壤,只能作为一种思潮封存在图书馆,也逐渐被女权行动者所遗忘,未成为女权思考和行动的思想资源。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全球制造的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批判的声音和社会运动日渐增多。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重温和再思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对于我们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构想女权运动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何殷震①何殷震,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但经常作为中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的妻子和轶事的主角进入公众视线。“殷”是母姓,震把母姓放置在父姓“何”之后,父母双姓,以示对父系制度的反抗及对男女平等的践行。为尊重何震这一思想,本文使用“何殷震”。(原名何震,1886-?)“女界革命”的构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财婚制度的批评,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构想了一条以“男女革命”为核心的追求人类彻底平等的社会革命道路,即“女界革命”的道路。何殷震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女界革命”的构想,既与晚清的自由主义女权又与无政府主义内部的男权两边展开对话,对于两者既有吸纳又有批判与超越,这种双重特性使何殷震的“女界革命”论述在晚清直至今天的女权论述中独树一帜。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对于一切权力制度和统治关系的拒绝,也让何殷震拒绝近代刚输入中国的西方文明论②文明既指状态又指过程,是与野蛮(savagery)与蒙昧(barbarism)相对立的社会秩序。文明论把人类历史理解成从蒙昧、野蛮进化到半文明、文明开化的线性历史进程。伴随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文明论被用来衡量全球版图上不同地区或人群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程度。时间序列转化成空间等级,于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人群就有了优劣高低之分。根据文明论的标准,古典中国在全球文明阶序中只处于“半文明”的地位,欧美的文明社会是中国社会进化的目标和榜样。文明论是一种统合性标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揽子标准。性别标准——妇女地位(确切地说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是文明论内在的一个标准。根据文明的性别标准,中国旧式女子的缠足、无才是德、幽闭妇女等女俗曾经都是西方判断中国是“非文明”的主要证据,也刺激中国的改革派把改造妇女、促进女权作为进化中国的手段。简化地说,在晚清,文明的政治标准是民族-民权国家,文明的经济标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工业化机械化的大生产体制),文明的社会标准是自由个体有序组成组织化的社会。文明的性别标准是女性为男性的“同伴”,但未挑战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秩序,妻子的权利仍是合并在丈夫的权利之中。提供的女权方案——即,在民族/民权的国家制度和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下追求男女平权和女性自主权。后者被何殷震斥为“伪文明”“伪自由”“伪平等”。刘禾、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高彦颐(Dorothy Ko)三位学者通过对何殷震思想的研究,认为相比于接受西方文明论框架、倡导女权以求进化中国的男性而言,何殷震的女权主义斗争不从属于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议程;相反,它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起点和终点,这场革命的目标是要废除国家和私有财产,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废除一切形式的社会等级制[1]。另一方面,“女界革命”的思想是在无政府主义理论范式内衍生出来的妇女解放思想,但何殷震对于男女绝对平等目标的追求,以及其提出的“男子为女子之大敌”“女子复仇”之类的激进口号,让中国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在革命道路的设想中,她把男女平等/女子解放的重要性提升到展开这场社会革命的起点和关键,“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成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2]③震述:《女子解放问题》,载《天义》第七卷“社说”栏,1907年9月15日。又载第八、九、十卷合冊“社说”栏,1907年10月30日,标题作《妇人解放问题》,署“震述”,《目录》作“论述”栏,标题作《女子解放问题》,署名同。的革命次序,以及让“女界革命”贯穿于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的理念,已然不同于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构想,鲜明的女权主义特性拉开了她与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男子的思想距离,也使何殷震的思想具有了原创性[1]。
一百年前,何殷震所处的是一个废旧立新的时代,面临着打破儒家旧秩序和创建新社会的历史任务。维新派知识分子准备全面拥抱西式现代性,特别是民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女权”是这个现代性方案中的组成部分。何殷震两面开战,一方面参与到“破”儒家秩序的工作中,另一方面对维新派所“立”之西方现代性方案持拒绝态度,也与自己所隶属的无政府阵营内的男权存在思想上的距离。一百年后,国家、资本已经全面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何殷震的批判和思考也许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思考女权运动的定位、女权运动的方向(包括短期和长期目标)、女权运动的策略。对于仍然纠结于女权运动是否应该保持独立性,以及如何处理女权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的我们来说,可能都会有所启发。
一、“女界革命”对“女权革命”的超越:共识和别途
(一)何殷震并非全然反对女权
“女权”,是何殷震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时尚新名词,是维“新”的人士所乐用的词汇,代表先进和文明,甚至有论者提出20世纪是女权革命的时代。那么,何殷震为什么在“女权”“女权革命”之外,另创“女界革命”一词呢?
何殷震并非不使用“女权”一词。何殷震在《女子宣布书》中称:“男女革命,即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並行。成则伸世界惟一之女权,败则同归於尽,永不受制於男。”[3](PP1-7)在《女子解放问题》中也使用过“女权”一词,批评当时社会里的“女权”多为男子出于私利而倡导,称女权应由女子通过自己的抗争来获取。“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特以女子之职务,当由女子之自担,不当出于男子之强迫;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2]可见,女权仍是何殷震追求的目标。在《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中称“吾辈之所主张者,扩张女权也,恶男子以强权加之女子也。夫女子为男子强权所加,固为可闵;若夫己为女子,不能抵抗男权,而徒以横暴之强权加於服属己身之女子,则其惨毒之罪,尤属可诛”[4]。这段文字清楚显示,何殷震也是在与“男权”相对的角度使用“女权”。
1907年6月10日的《天义》报的“时评”栏,有一篇文章《悲哉男权之专制》,评论英国女子为争参政权,群聚入议院被警察拘捕的事件,该评论支持女子参政权的理由与晚清自由主义女权的论述无异,“天之生人既同,则天赋之权亦同”[5]。并激烈批评这些“得权”(从君主中争来民权)之后的男子压制女子参政权,是“女贼”[5]。“女贼”一词是模仿“民贼”一词而造,意指这些男子当初与君主争权时,指责君主是篡夺民权的“民贼”,那么,这些压制女权的男子,就是篡夺女权的“女贼”。文章标题中也赫然以“男权之专制”标识。这篇评论署名“志达”,但行文用语与何殷震的用法和语气都非常相似,比如这篇文章中批评男子不给女子参政权是“特男子纯全之利己心耳!籍女子已得议政权,然此次压抑之仇决不可忘”[5]。何殷震思想的研究先驱夏晓虹教授也认为,“志达”有可能是何殷震的笔名[6]④《天义》第13、14卷合册所载《女子教育问题》(“社说”栏,1907年12月30日,第1-8页),署名“志达”,目录标题中署名“震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社说”栏,1907年12月30日,第9-22页),正文中署名“震述”,目录页署名“志达”。由此可见,“志达”与“震述”是互相替换。夏晓虹老师提出这份证据,指出这两篇文章的目录页与正文中作者署名“存在相互易位,此后亦未有更正说明,可见二者本可置换”。笔者在此详细展示易位的方式,以作证据。。这一具体事例也说明何殷震无政府主义立场并没有让她放弃在现实生活中争女权,反男权。而且“女权”一词的所指与晚清主流话语中的“女权”无异。“权”,既有权利,又有权力之意。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一切强权的关注,使何殷震之“女权”的内涵,更侧重于权力,而不仅仅是权利。在权力层面,何殷震既反对男子对女子之强权,也反对女子对女子的强权。这是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超越同时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之处。自由主义女权把摆脱男子干预的希望寄托于明达的精英女子对于愚陋下层女子的教导,一统的女性身份掩盖了妇女内部的阶级差异和权力关系。
(二)“女界革命”是超越“女权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主张
在何殷震的理论构图中,“女界革命”和“女权革命”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女界革命”包括“女权革命”,但高于“女权革命”。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给女子指出两个革命办法,一种是“对女界之办法”,一个是“对世界之办法”[7]。前者的方法是“以暴力强制男子”和“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后者是“以暴力破坏社会”和“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7]。可见,“女界革命”包括两个层次的革命:微观层面的男女间革命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革命。那么,微观层次的女权革命与宏观层次的其他社会革命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何殷震把破男女阶级的女权革命作为一切社会革命的发动机关,“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2]。因为根据何殷震的观察与判断,现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种族制度不仅是等级制度,而且是排斥女子、男子专有之制度,都是男子压迫女子的制度:“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2]何殷震依据自己对现存世界的判断,把“破男女阶级”(即男女等级)作为破解现存世界的爆破点。
其次,在革命道路设想中,一方面女界革命不只是微观层次上的男女间革命,也是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的起点,且要贯穿诸革命的全过程,以达“尽废人治”的目标;另一方面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也是妇女解放的手段和保证,因为只有“尽覆人治”,才能确保男性不再利用种族、政治、经济等制度来压制女子。何殷震没有把“女界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唯一目标,提倡“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3][8],她充分认识到“女子私有制度”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她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甚至提到“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9]。说明她一方面坚持男女间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并没有把男女间革命完全独立于其他社会革命,特别是经济革命。“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言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9]另外,何殷震明确地提出其提倡女界革命的原因就是为了对现有革命学说盲视“男女阶级”的情况进行纠偏,“顾今之论者,所言之革命,仅以经济革命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8]。对于何殷震而言,“女界革命”不仅与“经济革命”有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男女革命”也是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等诸革命并行的革命。“女界革命”是进行诸革命时不可缺少的手段,而其他诸革命也是“女界革命”最终实现的保证。刘禾等研究者认为“男女有别”在何殷震的理论框架中是一个更根本更形而上的分析概念[1]。正因为何殷震把“男女有别”理解为贯彻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组织中最基本的物质的和形而上的权力机制”[1],内在于儒家社会的学术、礼俗、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基本制度,所以,她才可用“破男女阶级”作为方法,来撬动儒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种社会制度,其他革命才能“顺次而施行”[8]。在何殷震的理论图景中,女界革命内嵌在其他诸革命中,而非独立于其他革命之外,与其他诸革命的关系也非排斥性和对抗性关系。某种意义上,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是包含在“女界革命”内的革命。正如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为该会所立宗旨:“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⑤《女子复权会简章》,《天义》第一号,第41页,引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此处所引用的宗旨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所收录的《女子复权会简章》之宗旨在文字和意义上有明显差异。后者所录宗旨为:“竭尽对妇女界之天职,力挽数千年重男轻女之颓风”。据文后资料来源显示,这份“简章”转译自《世界妇人》第13号(1907年7月1日),转引自《明治社会主义史料集》别册1)。本文采信北京大学图书馆版本。“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比“竭尽对妇女界之天职”更符合何殷震“女界革命”的思想逻辑,也符合《女子复权会简章》中所包含的整体思想。“简章”第二条“办法”列有两种办法:“对女界的办法”和“对世界的办法”,可见何殷震对女子复权会所要求女子不仅是“竭尽对妇女界之天职”,而是要求女子“确尽对于世界之天职”。《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为女界所列出的革命手段也包括两部分:对待女界的办法和对待世界的办法。在何殷震的革命道路设想中,“女界革命”是把“女界”作为革命的主体,参与到所有社会革命中,确实尽到对于世界的责任,“尽覆人治”,才能确保男性不再依附强势体制来压制女子。
第三,反抗男权,争女权,并不是为了追求女子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权力,而是希望男子再无压迫女人(包括弱势男子)的权利/权势。“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2]“退与女平”,也是何殷震的“女界革命”思想有别于晚清自由主义女权在现代社会既存体制下“争与男平”(权利与义务都与男子等同)的理念。即使在《女子复仇论》这一充满挑衅的篇名下,何殷震开篇明义,当今世界一切压迫机制都由男子掌控和垄断,所以男子是女子之大敌,但“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11](P20)。女权之目的并不是成为男权的复制品,女权只是通往“至公”社会的手段,何殷震是在手段意义上支持女权、践行女权。这才是她在《女子解放问题》中所称“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2]之真正涵义。
第四,从历史阶段上讲,“女权革命”是现实世界中的男女革命,“女界革命”是通往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桥梁。“女权革命”既是这个漫长道路中的必经历史阶段,也是“女界革命”的一种手段。何殷震提倡成立“女子复权会”,是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推行女权,实现彻底的男女平等。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容易理解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稍显怪异和激进的具体平权手段:“不得服从男子驱使”、未嫁之女“不得降身为妾”、“不得以数女事一男”、“不得以初昏之女为男子之继室”[7](P212)。从这层意义上讲,倡导“女子复权会”的何殷震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希望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所开出的平权药方,就是针对她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夫可多妻,妻不可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丧则一斩一期,宾祭则此先彼后。既有号均平者,内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遗母姓。”[8](PP818-819)针对“用父姓而遗母姓”,她身体力行地把母姓加在父姓之后,用“何殷”复姓。何殷震在《女子宣布书》中列举了女界要争取的七项权利,除了《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的婚制问题、姓氏问题,更是提出了男女教养问题及废娼问题。何殷震要求父母在养育孩子时要男女并重,给予男女相同的教养、相同的学术,成人后男女自然能担一切相同的职务,“无论社会间若何之事,均以女子参政其间”[8](PP818-819)。何殷震认为“凡所谓男性、女性⑥笔者注:此处引文中的“男性”和“女性”应理解成“男子特性”和“女子特性”。笔者注。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3]。何殷震提出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据其之上的社会对策,理论境界已超出了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晚清自由主义女权的主要诉求在参政权上,偶然提及职业。相较之,何殷震的女权诉求更具有“社会性”,更切入性别关系的改造:婚姻关系、教育与教养、一切社会职务的参与、生育。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特别是男性女权论者,主要是以“国民之母”为号召,强化女子生育和母教对于强国之价值。何殷震看到女子生育之苦,以及女子生育和养育的照料责任对于女子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设想未来社会,所生子女进入“公设婴育所”[3]或老幼共用的“栖息所”,实行儿童公育。“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而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而“女子无养稚子之劳,所尽职务,自可与男相等。职务既平,则重男轻女之说,无自而生”⑦何殷震丈夫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中提出“栖息所”的设想,设想初生小孩及年逾五十的老者都入栖息所。老者照料养育稚子。何殷震在刘师培文后写了一段“震附记”,对栖息所大赞扬。此处引文附在《人类均力说》文后的“震附记”,《天义》第三卷,1907年7月10日。。何殷震认为造成重男轻女的原因是女子所尽的社会职责不及男子。实行照料责任的社会化,既能解除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更深远的作用还在于为男女平等提供制度性保障,有助于改变两性关系。何殷震把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所以,她心目中的女权革命——女界革命的实质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不是以女性为改造对象的女权运动。何殷震称“吾所倡者,非仅女界革命,乃社会革命也;特以女界革命,为社会革命之一端”[3]。晚清维新男士发动女权之最初动因,是针对女性的改造运动,而自由主义女性论者的话语策略也往往是通过自我归责来论证女权的正当性。何殷震的社会革命,远不止于在既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下寻求有利于女子的社会政策,而是更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造。由此可见,何殷震并不反对“女权”,而是把“女权”视为现实世界中反抗“男权”的手段,但“女权”不是“女界革命”的终极目标。
(三)何殷震对男权的批评更激进和彻底
自由主义范畴内的男性女权论者,如马君武、梁启超等人,以“女权革命”置换“男女革命”⑧夏晓虹教授把何殷震的“男女革命”的思想源头指向马君武所译之斯宾塞和约翰·弥勒的女权论述(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第83辑,2006年)。笔者认为即便何殷震“男女革命”一词的使用受到了马君武译作的启发,但两者只是字面的相同,在内容上存在本质差异。马君武译文中的“男女革命”一词的具体内涵是规避男女间革命的“女权”。,把女权纳入国族主义的框架之中,消解男女之间潜在的斗争和紧张,女权不仅无害于男性,而且有益于男性的国家[12]。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女性论者,尽管一直努力把男性消隐的性别维度和性别裂缝彰显出来,但温婉自责的表述方式,并未直接把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虽对有利于男子之女权保持着警惕,但也没有把斗争之矛头直接指向男性,极力避免激化男女间革命,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框架下,女子自求解放或是合群互助。这类自由主义女权更能博得同时代男性的支持和同情,与男性结成暂时的同盟。
何殷震对于男权制和男子自私的批评比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论者更为深刻和尖锐,除了“以暴力强制男子”之类刺耳的言语外,她把斗争之矛头直指男性和男系。她以“何殷震”之名发表文章,挑战儒家传统中最核心的男系世系制度。何殷震把批判男权之剑同时指向新旧两个方向:一个是儒家学术下的传统男子,一个是持文明论解放女子的新派男子。何殷震认为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男子私女子为已有”,男人利用女子而已。对于儒家经典的批判,不同于晚清主流女权论述归责于无责任主体的儒学和礼俗,何殷震批儒家学术的目的是剑指男性和男权制,指出“男子以学自私”,“倡此说之人,即自便其私之人”[11](P21)。对于儒家学术,何殷震早于新文化运动十年就喊出了“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11](P20)。何殷震的先锋性不在于时间,也不在于激进性。时间上,对于儒家学术的批评,西方传教士早于何殷震。何殷震的先锋性在于她坚定的女权主义立场和批判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男女青年推翻父权文化上的弑父运动,而何殷震却是从推翻男权的角度批评儒家学术。何殷震从“男女阶级”这一视角,批评“女从男,男率女”的儒家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礼俗与法律——贞操杀人、连坐之法——使女子无辜受戮。从维新派到五四知识分子,这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一直借“妇女”作为自己言说政治和对新社会欲望的场所,却一直回避和拖延着两性间关系的重构——男女间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章锡琛等妇女主义者开始推进新性道德讨论,试图为新社会的两性秩序提供新的伦理道德基础,但他们所试图构建的新性别秩序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秩序。这是后话了。
对于推崇西方文明、“解放”妇女的现代男子,她批评这些男子同样是出于男子私心,是出于男子之名利而不是为了利于女子而发动女权。何殷震指出了男子发动女权运动的三个原因:第一,男子博“文明”之名。中国男子崇拜强权,视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所以,仿行其制,让自己的妻女放足入学,以获中外人士赞自己为“文明人”,这美誉不仅事关个人也关系到家庭荣誉。所以,崇拜欧美文明的人士推行女权,无非是利用女子成就自己的文明美名。第二,有利“男子之私”。让女子学习实用之学、一技之长,男子可以“抒一已之困”,名曰使女子独立,实则是男子获利。第三,有利男子之家。中国男子向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把治家教子之事责之于女子。何殷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女学首重家政,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文明女子,让女子用文明的方法治家教子,但“家”仍是男子之家,“子”仍为男子之子,所以,男子是为求己身安逸而解放女子。“今日之解放女人,出于男子之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2]。何殷震一语道破了晚清维新男子所倡女权的男性中心。
(四)何殷震批评西方文明论框架下的女权是“伪自由”“伪平等”
何殷震认为西方在两性关系方面胜于中国的地方在于:(1)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2)实行一夫一妻之制;(3)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但是,何殷震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解放、肉体上的解放,而不是精神上的解放。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彻底解放的标准出发,指出解放应该是“不受缚束”。而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利,二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缚于权/利指男女双方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对方财产(利)和权势门第(权)。缚于道德法律,指很多婚姻不过为宗教、法律、伪道德所牵制,名为一夫一妻,实多有私通奸情。另外,欧美虽然男女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但服官议政女子很少见,参军从警更与女子无关。西方的男女平等也不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何殷震要唤醒“震于欧美之文明”、以欧美女子解放为目标的亚洲女子⑨《女子解放问题》首载《天义》第七卷“社说”栏,1907年9月15日。又载第八、九、十卷合册“社说”栏,1907年10月30日,标题作《妇人解放问题》,在《目录》里的标题仍作《女子解放问题》。[2](PP962-963)。
何殷震除了揭开欧美男女平等表象下的虚伪和不足,还希望为中国妇女指出女子解放的真正道路:必须掌握改造社会之权。但改造社会所需之权,既不是马君武等男性推崇的公权[12],作为国民与国民之母,服务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论者所追求的妇女参政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中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把“参政看作保障女子权利的最有功效的方法”,甚至把女子参政视为一揽子解决教育平等权、财产平等权等其他女权的“唯一方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13]。即使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女权思想源头的约翰·弥勒(John Miller)也只是把参政权作为职业权的一种,并未上升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枢纽位置。对于参政权之重视,是近代文明论大图景下女权与国族纠结之后的历史产物。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的视域出发,反对女权运动只重视“女子职业独立”和“男女参政权之平等”[2]。何殷震从阶级压迫和妇女内部差异性出发,批评自由主义女权的不彻底性。从女性内部的差异出发,职业独立只是解放了个别“女子”,而不是所有的“妇女”。何殷震用“女子”和“妇女”两个词汇来区分妇女内部的两个群体。“女子”隐约指的是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独立的个体女性;“妇女”——出嫁为妇,在家为女——是芸芸众生的普通妇女的集合名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通过职业来寻求女子的解放,只可能是极少数中上流家庭中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的特权。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女性经济不独立与依附于男子的关系,但解决方案是女子寻求家外职业以“自养”,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于女性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何殷震看到“职业独立者,即以职业供役于人之异名耳”[2],没有摆脱被人奴役的命运。何殷震戳破了那个时代刚刚萌出的中产阶级女性以职业求独立的梦想。中等人家把女儿送进学堂,以为“学一点普通学”“一点儿手工”,以为“有一个行业可做”,婚后也“不至于靠男人过活”,但仍摆脱不了“靠人吃饭”、随时被人解雇的命运。她把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称之为“劳力买卖之奴婢制度”。工资劳动者无非是“仰资本家之鼻息”,且为资本“生财之具”;视女子为物,“既屈其身,兼竭其力”。她批评文明论者向中国引入的“富强之学,皆迫人于苦之学”。另外,在私有制度下,富有者利用女子之贫,不仅逼迫贫女入工场,控制女性的身体,剥削其劳力;又常以女子对工资之依赖逼其满足自己之肉欲,使工女处于“半娼半妾”之地位[10]。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业自由,并不能给女子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何殷震认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实行公产制的社会中。而趋向这个社会的方式只能是“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9]。
对于参政权,何殷震认为无非是让少数参政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后果就是不独男女间不平等,女界之中亦生出不平等之阶级。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女性女权论者如陈撷芬,虽也看到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即,少数“明达女子”与绝大多数“愚媪蠢婢”[14]的区别,但仍从精英女性的立场出发,以精英女性教育普罗妇女大众的方式来寻求妇女内部的一致性,以此来对抗男性对妇女的干预,建立起相对于男子的性别独立。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权为了从男性主导的国家主义框架中挣脱出来,彰显性别维度、强调性别身份、建构性别认同(如合群结社),统一的性别身份有意无意消弭和掩盖了妇女内部的差异。何殷震从下层女性的视角,看到了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妇女的潜在压迫性。认为男子压迫女子为不公,女子压迫女子同样是不公。“故吾辈之旨,不惟排斥男子对于女子所施加之强权,并反抗女子对于女子所施之强权。”[4]“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斯为人人平等。”[2]何殷震从反抗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视域出发,认为权力所在之地必是压制所生之地。所以“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原”,苟非行根本改革,使人人平等,宁舍选举权而勿争,慎勿助少数女子争获参政权。何殷震所称的“根本改革”,即是无政府主义理论视域内的政治上的“废政府”和经济上的“共产”。“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11]
由此可见,何殷震是女权主义者,但她超越了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权主义。她之所以在“女权”概念之外,创造性使用“女界革命”,表达的是对于“妇女解放”的理解。“解放”是相对于“压迫体制”而言,在无政府主义视域内,何殷震的目标是破除一切压迫体制。如果说从字面意义上,“女权”是相对“男权”而言的,是追求在既存体制下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与权力,那么,“女界革命”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和摆脱一切强权压制。
二、“男女革命”对“无政府主义”的矫正: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
何殷震“女界革命”的思想无疑深受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在无政府主义的框架之内。何殷震对现实世界中女子的关切以及彻底的男女革命的立场,使何殷震的“女界革命”不同于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男子对于男女平等的设想,具有鲜明的女权特色。也可以说,何殷震用女权主义矫正了无政府主义的男性中心的偏差。
(一)“女界革命”在无政府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次序不同
作为反抗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视域自然是纳入了男女平等的诉求,但是,男性无政府主义者与何殷震对于“女界革命”在革命中的地位和次序的理解是不同的。何殷震把破“男女阶级”视为开启一切革命的起点,贯穿诸革命过程,作为革命的终点。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男同事,似乎对于何殷震的“男女革命”的提法有所保留。张继,与何殷震丈夫刘师培一起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1月从日本流亡欧洲。他在1908年4月写给东京同人的信中要求把《天义》报办成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机关报,提出“需将‘女子复仇’诸语,稍加改变,当以‘自由恋爱’为最确当。且西方革命党舍英国外,亦鲜有男女之界者,惟以社会革命为主而已”[15]。张继明显对何殷震“女子复仇”之类的激进口号颇为不爽,希望把妇女解放议题收纳进“社会革命”,这与何殷震对女界革命的定位大相径庭了。何殷震不希望把“女界革命”限定在女子本身,而是把女子问题定位为社会问题,以“女界革命”作为改造世界之法。张继想以社会革命收编男女革命,取消男女革命的必要性,似乎伴随社会革命的实现,男女平等自然就实现了。现实世界中的男女间革命并不需要像何殷震所坚持的:向男子夺权、向男子复仇,而只需实行自由恋爱(性自由)。
另外,张继建议把《天义》报改造成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对于《天义》报首先是作为“女子复仇会”的机关报面世这段历史似乎毫不在意。对此,刘慧英严厉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派别中的男性是“不自觉地承袭男权中心的传统”,并篡夺了《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机关刊物的地位,削减了何殷震在《天义》报中的话语权,把《天义》报改造成男性主导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刊物[16]。不管是出于无政府主义内部的性别斗争,还是易于激动的何殷震“知难而退和热情消减”的性格因素使然,甚或是幼年的严格闺训促使何殷震选择夫“倡”妇随[17],何殷震的声音在《天义》报后期逐渐隐没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天义》报的宗旨也发生了微妙的语序变化。《天义》报每期的扉页上都印刊物的简章。其中第一至七卷的第一条“宗旨及命名”:“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8]从第八⑩第八期的时间在1907年10月。、九、十卷合册起,宗旨发生了改变:“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18](P122)后者尽管没有放弃男女平等的追求,并加了“绝对”两字。但两者的表述明显存在重大差别,不仅在于语序上的变化,而且是内容上的变化。前者的表述侧重于革命之手段,后者的表述侧重于乌托邦社会的内容。首先,前者对乌托邦社会的表述是“人类之平等”。按照何殷震对于人类平等的激进想象,在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里,只有人类,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3]。而后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中,男/女分类仍是存在的。其次,后者侧重于革命的乌托邦目标,淡化具体之革命手段,只是笼统地谈“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从而淹没或者说消解了“女界革命”之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与张继的思路实则是吻合的,与何殷震创办“女子复仇会”,提倡和彰显“女界革命”之主张却是背离的。
(二)“男女革命”的内容和手段之不同:恋爱自由vs女子复仇
由留法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新世纪》,与《天义》报(留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同时期创刊,也发表过一些谈论“男女革命”和“女界革命”的文章。男性论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自然也是认为“男女之不平等,实公理所最不能容者”[19]。且认为破男女间强权要比破君民、贫者富者间的强权更困难。因为后者,强权与弱者“互有盛衰、互有胜负,故其冲突较易,故革命之果实早熟”,而“男女之强权弱力,乃自然生成,强者永强,弱者永弱,故至今他处革命已大进步,而男女之不平等仍黑暗如故也”[20]。这一论点,似乎与何殷震认为“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的观点相似。但对于如何解决男女不平等的方法,男性的方式相比于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和《女子宣布书》中所列举的具体行为规范,要空洞得多、务虚得多。这位署名“真”11刘慧英认为在《新世纪》上署名“真”的作者是李石曾,参见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的作者认为,一切不平等都起因于强权,包括物力之强权和迷信之强权。破强权自破迷信始。迷信为保强权,迷信破,强权不能独存。迷信,即伪道德也。所以,“男女革命,以破坏伪道德为第一要图”[20]。似乎与何殷震在其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对于儒家学术之剖析声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真”对所谓的迷信,只是统笼地称之为对妇女思想的禁锢,所以,他为中国妇女推荐了可供学习的两位法国的女性典范,一个是法国女科学家礼马(Marie Sklodowska),一位是被无政府党人推崇的法国革命党人药师未易路(Louise Michel)12《天义》报亦刊登Louise Michel的生平与画像,中文名译为“露依斯米索尔”,生平载《天义》报第2号,1907年6月25日。画像刊于《天义》第八、九、十合刊“图画”栏,1907年10月。,证明女子“无不应为,无不能为”[19]。似乎女子的解放需要的是女子自己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做敢为就可以了。无政府主义男子与自由主义维新男士,在理解女子受压迫的问题上似乎很相似,都归结到女子本身以及女子之愚昧,除了等待先进男子之思想启蒙,妇女解放之路就是召唤女性的主体性,对革命过程及新创制的制度中潜在的男性优势似乎毫不察觉,也不在意。
除了思想之解放之外,在具体的行动手段上,无政府主义的男子主张以“毁家”和“自由恋爱”作为追求男女平等的方式。张继在巴黎来信中,提出以“自由恋爱”作为男女革命的手段,取代何震的“女子复权”的方式,这一观点并非张继个人独有,似乎是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男性的主流看法。“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止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家者,实万恶之原也……。去强权必自毁家始”[21];“故今日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始……言及男女革命,……拔本塞源之计……毁家是已”;“自家破,……而后男子无所凭藉,以欺凌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必自废家始矣”[22]。对于无政府主义男性而言,造成对女性压迫的是家庭制度,而不是家庭中的男人。所以,废除家庭制度就能解除对妇女的压迫。他们也激进地批评针对女子的贞操观和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指责“一女不二夫”是伪道德[20],倡导男女双方对等的性自由。“设男子别有所爱,则可娶妾嫖娼,女子则不能,其不公之至,人人得而见之。设男子得御他女,则女子亦应御他男,始合于公理也”[20];“就科学而言之,男女之相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就社会言之,女非他人之属物。可从其所欲而择交,可常可暂。就论理言之。若夫得杀妻,则妻亦得杀夫。若妇不得杀夫,则夫亦不得杀妻。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此平等也。此科学也”[23]。
这种性自由和对等看似非常公平、激进和彻底,相比而言,何殷震在恋爱自由(性关系)和婚姻制度上却保守得多。何殷震激烈批评这种表面上的对等,实质是便于个人的私欲:“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不知女界欲求平等,非徒用抵制之策已也,必以暴力强制男子,使彼不得不与己平。且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举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况女子多夫,莫若娼妓。今倡多夫之说者,名为抵制男子,实则便其私欲,以蹈娼妓之所为,此则女界之贼也。”[3]可见,何殷震所追求的“平等”完全不同于无政府主义男子的平等。相比于男性的毁家和性自由,何殷震设想的是婚姻内严格的男女对等,甚至在结婚条件上,苛刻到以初婚男配初婚女、再婚男配再婚女。不惜通过“以暴力强制男子”和惩治不服从这些规则的女子,保证婚姻内的男女绝对平等。
关于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的男性提出的性交自由(男女杂交[22]),何殷震批评这种“自由平等”的实质是“纵欲肆情”,实则是把“解放”狭义化了:“然中国近日之女子,亦有醉心自由平等,不受礼法约束者。就表面观之,其解放似由於主动。不知彼等之女子,外托自由平等之名,阴为纵欲肆情之计。盖仅知‘解放’之狭意,妄谓能实行纵淫,即系实行解放。”[2]妇女要求真正的解放,应该去寻求掌握改造社会之权。何殷震反对纵欲,但并不反对自由恋爱,“果出于自由恋爱,犹猶可言也”[9]。她追求的是真正的纯粹的男女之爱,认为“爱情发于天性,乃出于自然者也。……若处经济革命之后,则结合均生于感情,乃世界最高尚、最纯洁之婚姻也”[9]。从纯粹的情爱标准出发,她激烈反对财婚,她把基于金钱的结合视之为“卖淫”,称之为“伪爱”。认为因金钱而结合的婚姻,实质是“辱身以求利”[2]。可见,何殷震对于女性尊严的重视。对于不是出于爱情,即使排除了金钱所诱的性交,似乎她也并不完全赞成,“情不自禁,不择人而淫者;有为男子所诱而堕其术中者”[2]。在自由恋爱的问题上,何殷震与无政府主义男性的区别就在于“性爱”与“性交”的距离:精神上的“情”与“爱”。何殷震追求的是发乎情的身心合一的“性爱”,男性则重生理欲求的“性交”。正因为出于对情爱的追求,何殷震强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和婚姻内的严格性忠诚,因为婚姻中的性忠诚是对情爱的承诺。何殷震不反对离婚,但是未离婚之前,“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否则,就违背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3]。
如何理解何殷震的保守和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男性的激进呢?是因为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不够坚定和彻底?刘慧英把何殷震与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的男性在性与婚姻家庭上的态度差别,看成何殷震作为“天然的女权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对冠予何殷震以“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25]的头衔持保留态度。对于何殷震论述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彻底的男女革命的立场,刘慧英宁可称其为“天然的女权主义”[16][18](P106)。暂时撇开是否需要以“毁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尺13何殷震无疑已经改变了婚姻与家庭的意义和功能。在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制下,婚姻不再是保障和传递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家庭也不再承担生儿育女的功能。婚姻是情爱的承诺,家庭是纯粹的情感单位。,刘慧英准确地指出何殷震与无政府主义男性的差别,是何殷震“更多地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女性处境和立场上说话”,而男性则“更多地从无政府信念或原则出发”。在晚清这种历史条件下,毁家和性自由是“为男子自己及时行乐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和自由”[18](PP105-106)。正因为何殷震关切的是真实世界里女子的生活,构想在一个已是男权制的现实世界里追求女权、贯彻彻底的男女平等,所以,她才会提出看似激进和怪异的男女平等的行为标准,才会提出“向男子复仇”和“女子复权”——夺回女子的平等权利。并以“女界革命”为手段,通往人类平等的无一切强权的乌托邦世界。而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男子以“自由恋爱”作为革命的手段、以性自由作为男女革命的内容,取代何殷震“女子复仇”(女子复权)的女权手段,实质上,既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压迫和两性对抗,也取消了“女界革命”的必要性,把妇女解放看成社会革命的附带物,似乎男女平等伴随着其他革命的成功会自然到来。
何殷震用彻底的男女间革命矫正无政府主义的男性中心,但“女界革命”的理论构想仍是无政府主义框架内的妇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何殷震的“女界革命”理论是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或许应称之为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女权流派之所以在前面冠之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限定词,是因为它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各为其基本理论框架/理论范式,构想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原因以及妇女解放的可能途径。
三、“女界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之间的渊源
从“男女阶级”的视角出发,何殷震认为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都是“女子私有制度”,女子受男子压迫,上古时代是因为体力,中古以降受制于金钱,而这都是因为财产私有制[9],所以,她特别强调女界革命与经济革命的关系。这一点也透露出何殷震的“女界革命”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之间的思想渊源。众所周知,晚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文世界的早期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是其中一个主要管道。学界会提到《天义》报在早期传播中的作用,特别是《天义》报最早译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共产党宣言》的片断,但对这段史实的叙述,一般是笼统地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一部分,没有注意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妇女解放理论为什么占据着这么显要的位置?为什么是《天义》报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其他刊物,有意识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内容?自然也忽略了《天义》报首先是作为《女子复权会》机关报这一女权主义报纸的特性。
何殷震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中论证了“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的必要性。该文主要讨论了财产、婚姻与女子受压制之间的关系。在何殷震看来,古往今来的婚姻制度都是财婚制度,中古以降女子受制于金钱。金钱不仅“不惟使婚姻失自由之乐也,且将陷女子于卑贱”[9]。欧美各国看似风俗与中国稍有不同(已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女子可继承财产或从事职业,也有贫家男子委身富家女,但自何殷震看来,这样的婚姻本质无异,都是因金钱而结合的,实质都是“卖淫”,只是现今的时代是“男女互相卖淫之时代”而已。当然,何殷震并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男女个人的贪欲,而把罪责归于私有制的经济制度。把婚姻视为“卖淫”,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婚姻的经典论述。确实如此。《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文后有一附录,摘译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批驳共产党人主张共妻制的那部分,讽刺资产阶级婚姻才是事实上的公妻制。在译文后有一段作者案语:案,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引节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公娼、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故附译其说,以备参考14《附录: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一节》,《天义》第十三、十四卷合册“社说”栏,1907年12月30日,署名“震述”。《目录》标题“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署名“志达”。。
“附录”发表之后不久,《天义》报又发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中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部分的摘译[26](PP137-140),这可能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入中文世界最早的中文译本。译文略去了原文中冗长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演变历史,只在译文前用寥寥数字的编者语概括之:“推论家庭之起源,援引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26](PP137-140)译文的前后有两段编者语,前一段部分除了介绍该书的书名、作者和主题外,点明了译者关注焦点:“其中复有论财婚一节,约谓:今之结婚,均由金钱。”[26](PP137-140)译文后的编者语,再次强调文明新式婚姻的财婚性质以及破财婚之法:
以上所言,均因氏所论财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於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编者识[26](PP137-140)。
从摘译内容之选择和编者按语,清晰地呈现了何殷震想借用的思想资源以及批判的目标——当今世界作为文明标准的新式(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摘译恩格斯《起源》的同一期《天义》报,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序》[27](PP1-3)和第一章全文[28](PP3-21)。刘禾等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节译本[1]。《天义》报的前一期已刊登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并为下一期刊登《宣言》全文作了预告。作为广告语的案语中称“《共产党宣言》发展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29](PP19-26)。译《宣言》之目的是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入门书。刘叔培15《共产党宣言序》,题下无署名,但正文题目有“申叔识”,作者应为刘师培。在《共产党宣言序》中简要介绍了马恩的主要著述后,也点明了《宣言》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区别,批评前者因存在国家组织而会逐渐发展成“集产主义”。但对《宣言》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仍深表认同,“欧洲社会变迁……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27]。同一期刊物,同为无政府主义阵营同志,对于同一种思想资源《共产党宣言》的撷取中,何殷震与男性同事(甚至自己的丈夫)关注焦点的差异显示出明显的个人偏好。在《天义》译介《共产党宣言》之前,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朱执信早已在《民报》(第2号、第3号,1906年1月和4月)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第3号上改为《列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革命活动,重点介绍的也是阶级斗争学说,并译介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十条措施[30](PP14-16)。而且,何殷震和朱执信所摘译的两部分都来自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选译内容的不同再次彰显出两人聚焦的社会问题及变革社会之手段的性别化差异。
何殷震在讨论经济体制时,特别关注婚姻制度,这与她关注现实妇女生活密不可分。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未充分发育。除了极少量女工和家庭女佣之外,职业女性非常少见。绝大多数女性的压迫来自男权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压迫也体现在婚姻家庭中,所以,婚姻家庭自然是何殷震极力抨击和破解的对象。何殷震对于儒家家庭秩序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她的著名长文《女子复仇论》中,而她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资源是应用于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批评,主要是对作为解决方案——也是自由主义女权所向往的文明的现代婚姻制度的批判,是她要戳破的现代“文明”梦之一。她在《女子当知共产主义》[10]中,戳破的是职业解放与经济独立的另一现代“文明”梦,解构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女子通过职业寻求经济独立的幻象。女性无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实现解放的批评,似乎与马克思的妇女解放理论是相通的,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对于未来社会经济体制的设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所以,从何殷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自然不会采纳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为现代妇女开出的经济药方,在国家组织支持下的公有制基础上广泛参与现代大生产体制。所以,何殷震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思想资源的汲取是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的。
何殷震“女界革命”理论因其无政府主义的基底,伴随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似乎被逐渐遗忘了,但从女权思想史的角度,它从没有离开,而以另一种方式在历史中存在。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这一脉络来看,何殷震的《天义》报及其“女界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也算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先声。
[1]刘禾,瑞贝卡·卡尔,高彦颐.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5).
[2]震述.女子解放问题[A].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3]何殷震.女子宣布书[N].天义(第一卷),1907-06-10.
[4]震述.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N].天义(第十五卷),1908年正月十五.
[5]志达.悲哉男权之专制[N].天义(第一号“时评”栏),1907-06-10.
[6]夏晓虹编.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何殷震.女子复权会章程[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8]天义报启[N].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9]震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N].天义(第十三、十四合册),1907-12-30.
[10]震述.论女子当初共产主义[N].天义(第八至十合册),1907-10-30.
[11]震述.女子复仇论[A].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2]宋少鹏.马君武翻译中的转化与遮蔽[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5).
[13]女子参政协进会宣言[J].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9号.
[14]陈撷芬.独立篇[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5]张继君由巴黎来函[N].衡报,第4号,“来函”栏,1908-05-28.
[16]刘慧英.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的变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17]夏晓虹.何震无政府主义的“女界革命”论[J].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83辑.
[18]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9]真.女界革命[N].新世纪,1907,(5).
[20]真.男女之革命[N].新世纪,1907,(7).
[21]鞠普.毁家谭[N].新世纪(第49号),1908-05-30.
[22]汉一.毁家论[N].天义(第四卷)“来稿”栏,1907-07-25.
[23]真.三纲革命[N].新世纪(第十一号),1907-08-31.
[24]鞠普.男女杂交说[N].新世纪(第42号),1908-04-11.
[25]沙培德,马小泉,张家钟译.何殷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英文版Peter Zarrow.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in China[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8,17(4).
[26]志达.女子问题研究:第一篇因格尔斯学说,天义[第十六至十九册合刊(春季增刊)“编纂”栏],1908年3月.
[27]共产党宣言序[A].天义[第十六至十九四册合刊(春季增刊)“译书”栏][M].1908年3月.
[28]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民鸣译.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N].天义[第十六至十九四册合刊(春季增刊)“译书”栏],1908年3月.
[29]因格尔斯,民鸣译.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N].天义(第十五卷“学理”栏),1908-01-15.
[3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含章
He Yinzhen's "Women's Revolution": Anarch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SONG Shao-peng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CPC,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He Yinzhen;women's revolution(Nujie Geming);women's rights(Nvquan);anarchism;marxist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In late Qing Dynasty when China's feminism started to rise,apart from liberal feminism,there was an ideological trend in anarcho-feminism.The author will analyze in this article how He Yinzhen's perspective of"Women's Revolution"(Nujie Geming)was influenced by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it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ystem of marriage and pursued a path of men and women's revolution based social revolution toward total equal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narchism.This was He's vision of a path of "women's revolution."This vision engaged in dialogue with the then liberal feminism and the stream of male centred anarchism,and was able to absorb,reject and go beyond 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in late Qing.As a result,He's vision is till today a unique perspective in Chinese feminism.
D442.9文献标识:A
1004-2563(2016)01-0071-13
宋少鹏(1971-),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妇女运动史、女权思想史、女权主义政治理论。
本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基地自设项目)“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理论和实践”(项目编号:2013030009)、北京市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项目编号:413215004600)的研究成果。另外,刘慧英教授与笔者无私分享《天义》报的材料,特别致敬和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