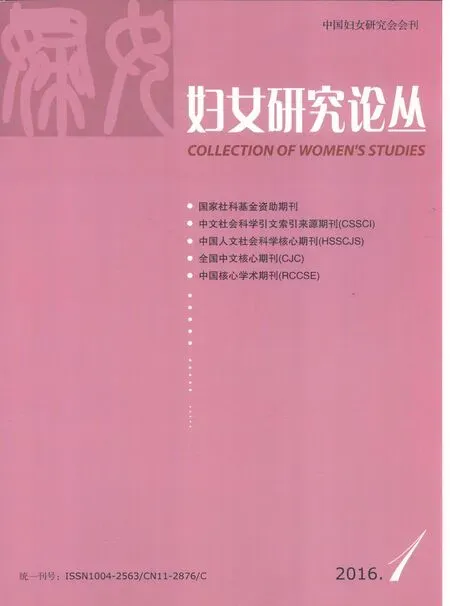英语教育在民国新女性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的研究
刘媛媛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英语教育在民国新女性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的研究
刘媛媛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英语教育;女性认同;金陵女子大学;个案研究;主体建构
高等教育是中外女性身份转变的关键因素,而语言教育长期以来又被视作塑造公民身份的重要工具,那么,于民国时期起步的学校英语教育在中国“新女性”的诞生中起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首先回顾其英语教育的理念和特色,再从新职业女性的促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新主体性的建构三方面,探讨英语教育在金女大群体认同转变中的作用。为求全面展示英语教育的影响,文章还解析了英语学习对她们造成的“感情伤害”,并阐发了金女大的英语教育模式对中国当前女性语言教育的启示。
民国新女性群体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女性的角色开始由“男性的附属品”转为“独立的社会人”。何玲华将新女性定义为“经历新教育的淘洗,以鲜明的主体自觉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知识女性”[1](PP2-3);美国华裔学者王政在其著作《启蒙时期的中国女性》中,认为新女性是“接受教育,并以其新获得的自主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2](P14)。二者都强调教育为女性带来的主体性及社会身份的转变。
无疑,高等教育是中外女性身份转变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为女性发展赋权、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对女性高等教育的研究推动了学界对教育在建构、表征和转变女性认同中所起作用的认识。然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语言教育鲜有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其与女性身份转变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在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语言教育一直被视作塑造公民身份的重要工具。罗素指出:“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中,各方都在……关注语言教育是如何组织和评估的,因为任何权力机构的继续存在都需要培养一批有特殊人格的新生力量。”[3](P2)
民国时期是中国语言文化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西、传统与现代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语言教育在思想传播、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是互相伴随而来的”[4](P1)。如此,一所教育机构所采用的教学语言、教育理念、教材选择、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会对学生的身份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历史资料显示,民国新女性不仅是中国首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是首批接受系统语言教育的女性,而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国语和英语。从语言教育的角度来探讨新女性认同,目前仅见两例,且都是针对以国语教育著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高师)的研究:张莉以冯沅君为例,分析了女高师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如何将一个来自乡下的普通青年塑造成一位新女性作家[5];何玲华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揭示了女高师的国语教育与“新女性”独具的精神风貌之间的关系[1]。同样是女子高等教育的佼佼者,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以优秀的英语教育卓立于扬子江畔,然而,学界关于该校独具特色的英语教育的讨论,大都局限于“培养学生丰满的智慧和能力”[6]“人才培养模式特色”[7]“培养全面发展的女性人才”[8]等话题。目前,尚未见将英语教育与新女性认同联系起来的专门研究。本文依托民国时期语言文化的大发展、大变化时代背景,以金女大师生关于英语学习的叙事文本(包括回忆录、传记、访谈、书信)为主要资料,以学校相关的历史档案为辅助资料,首先探讨了金女大的英语教育特色;再从新职业女性的促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新主体地位的建构三个方面,探讨英语教育如何帮助金女大女性群体实现认同转变;随后解析了英语学习为金女大人带来的“感情伤害”;最后探讨了金女大对当前中国女性语言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金陵女子大学——一所实施英语教育的女子大学
金女大实施英语教育,对于中国女性身份的转变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从教育内容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接受系统正规的英语语言培训。金女大非常重视英语在其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校长德本康夫人认为,“英语拥有所有古典和当代语言在我们(西方)教育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9]。在金女大,英语的重要性犹如英美女校课程体系中的拉丁语(古典语言)和法语(当代语言),被认为是了解古典哲学,进行人文博雅教育和科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而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金女大和华南女子大学创立之前,中国女性从未获得系统学习外语的权利。之前的传教士认为,对中国女性而言,英语学习不仅毫无用处,还会对“女学生在家庭中的良好作用起极坏的影响”[10](PP179-180),以至于使她们“沦为西方商人的情妇”[11](P20)。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之一,张之洞在1904年还认为“少年女子……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至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12](P573)。从观念层面讲,在中国艰难曲折的现代化之途中,英语教育给了中国女性看世界的新视界、新眼光。金女大非常重视英语在丰富中国女性思想和视野中的作用:“英语是通向外部世界,让中国人接触其他理念的唯一的通道。……要同世界保持联系,她们(中国女性)需要英语。”[9]此外,掌握英语给了女生摆脱男权束缚的机会和工具,对曾经被“囚之、愚之、抑之”的女性有极重要的意义,使她们可以绕过当时男性启蒙主义者的翻译和阐释,甚至渗入男权思想的解释,进而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
正如一位金女大学生所言,“金陵的趋势偏重于英文,这是无可讳言的”[13](P4)。在金女大,英语的学习被看作实现其教育理念的一种手段。校长德本康夫人在阐述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目标时明白地说:对她而言,高等教育就是要为那些已接纳女性的领域培养女性领导人。“我们不是在教育普通民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女界领袖。”[9]她认为,良好的英语水平是一位女性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将西方的理念介绍到中国,这些理念是丰富中国女性生活所需要的。可见,金女大的教育理想是按照西方式的标准,同时又立足中国实际,培养出一批中国新女性,她们要能扎根民众,传播西式理念,进而帮助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当时,被称为“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的北京女高师也只是“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宗旨”[14]。
在这样一种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早期的金女大将英语水平作为评判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之一,也是观测一个学生有没有发展前途的一项重要指标。创办初期,金女大曾立有这样的规定:二年级下学期,学校统一举行英语概括考试,以检验学生的英文水平,及格者允许升入三年级;不及格者需补读一年,再考仍不及格,则作自动退学处理[15](P14)。另外,金女大非常关注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学生的性格塑造和人格发展为教育的第一要义①如金女大在其1916年发行的关于学校状况的小册中指出,教师们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为学生的进步感到欣慰,因为学生们不再因不适应新事物而迷失;她们已经获得应付每日的学习任务的能力,而且逐步了解自我,认识到良好的领悟力和判断力是宝贵的人生财富(A Day's Work,Ginling College 1915,Box 7 Publications,Folder 1 Brochures.Smith College Archives)。另外,德本康夫人也多次提到,在金女大,教师们了解女生的需求及渴望,并愿意竭尽全力使这些需求和渴望得到实现(Mrs.Thurston,L and Miss Chester,M.R.Ginling College,1956:5,15;Mrs Lawrence Thurston,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Ginling College Magazine(English Version),1929:5,Box9 Publications.Smith College Archives.)。。教师们积极了解学生所需,并努力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课程、改进教学。自校长到每位教师,金女大教师群体对摸索一套适合中国女性的教学法饱含兴趣和热情,而金女大之所以能在英语教育方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不俗的成绩,与传教士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一位名为 Enda F.Wood的教师这样描述金女大1924-1925年英文系主任康凤楼女士(Miss Carncross)的教学法:她花费数小时为学生纠正句式结构、语法和听写中的错误,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任何教师来说,都是极为枯燥和乏味的,而她却做得津津有味。她总是和学生面对面,一起探讨错误产生的原因。Enda F.Wood认为,这是一种基督徒的工作精神,康凤楼的教学法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她对学生极有耐心和怜悯心,只有非常了解中国女性的人,才会掌握与中国女性交往的要诀。一个学生也许只为一个时态问题而来,这也许是一个只要十分钟便可解决的问题,康凤楼女士却愿意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耐心倾听这位女生在学习中的种种失望或雄心,并确保在离开时,让这位女生获得新的勇气,去迎接未来的学习和生活[16](PP11-12)。
除了关注学生的人格发展,重视口语是金女大英语教育的另一特点。1915年、1920年和1925年的英语课程设置均有与口语训练相关的课目,低年级时练习口头作文、报告和讨论,进入高年级则要学习辩论和公共演讲。如1915年课程表里的“修辞与写作”课,以“学习辩论及公共演讲的原则为主旨”[17]。而且,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出现在1920年和1925年的“当代杂志选读”课不愧为一项妙思,将时事与口语练习结合,让学生报告、讨论其所读所思,不仅能够激发她们的讨论热情,更开阔了她们的视野,引导她们关注社会生活。
此外,校长德本康夫人对中国传统依靠背诵的教学法的缺点非常警惕,指出:这种以背诵为主的方法使得学生“没有机会发展理性思考的能力”[18]。她和她的同事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并藉此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种对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不仅表现在对辩论、讨论等学习方法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写作训练上。1915年课程表中的“修辞及主题写作”一课,“重点训练学生用正确、地道的英语表达自我”[17];1925年的必修课“作文和文学”,主要是为了“锻炼清晰思考及正确表达的习惯,操练语法结构、习语及词汇”[19]。
金女大还存在着其他灵活的学习形式,鼓励学生在使用中学习英语。1918年,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创立了“英语社”和“中国文学社”。英语社是学生们练习英语会话、阅读和背诵的场所,通过戏剧表演、台词背诵和诗朗诵等形式来扩充词汇,锻炼口语表达能力;而中国文学社则除了锻炼清晰优雅地讲话,更注重翻译的练习[20](PP32-33)。1923年,为了提高学生公众演讲的能力,英文教授游英女士将英语社和中国文学研究社合为一处,组成了“文艺会”。文艺会的目的有二:一为发展个性,一为锻炼演讲之能力[21](PP57-59)。另外,学校还成立了校刊,目的是为学生创造机会,让她们自由抒发情感,进而锻炼清晰思考的能力[22](P32)。
在一代代传教士教师的努力下,金女大的英语教学日趋完善并富有特色。它的教学法被学生评价为“灵活、严谨的”,学生们认为自己良好的英语水平和客观、逻辑地分析事理的态度与金女大的训练手段是“分不开的”[23](PP199-201,PP387-389)。金女大的毕业生以高超的英语水平、突出的业务能力和独特的精神风貌而享誉国内外。
二、在英语教育中成长为新女性
无论家庭支持与否,一代代来自不同城市和家庭的女孩子们,都会选择到金女大接受高等教育以发展自我,寻求独立。第一届学生徐亦蓁在回忆录中说:“上帝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这(金女大)就是我的答案,……我必须离开家。”[24]入学之前的她们,都有着数年的英语学习经历,但对何为理想的女性,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她们对就读这所以英语为管理和授课语言的学校,抱着懵懂的期望和些许的担忧。她们期望掌握英语,获取高等学位,或工作或出国,进而自立于世间;同时又担忧自己的英语能力不足以应付学校的课程。可以说,就读金女大对她们来说是机会与挑战同在,让她们拥有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事实也证明,金女大的英语教育给予了她们不曾想象的未来:通过英语阅读,她们的眼界从家庭延伸至国际,女性楷模于是突破了国界,从而激发了她们对新身份的渴望;英语的学习又为她们提供了符号和文化资本,使她们最终得以冲破中国传统性别规范的窠臼,从家庭的小女孩成长为富有远见、具有担当、充满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的时代新女性,有些毕业生甚至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女性的卓然风采。
(一)英语学习促生新的职业女性
基于对民国时期教育和妇女报纸、杂志的分析,英国历史学家Bailey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初期中国的女性教育,只不过是“给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披上现代知识的外衣,以养成勤劳、富有技巧、高效的家庭主妇——目的就是维持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以及民族的繁荣”[25](P120)。联想到男性精英倡导女性教育的缘由:“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无学始。”[26](PP37-44)于是,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良妻贤母”便成为女子教育的目标②对良母贤妻的这一定义,正是梁启超提出的。。这种良妻贤母的教育观导致女校课程以教育和家政类为主,而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下,女性能够选择的职业似乎注定会如此:要么做好贤妻良母,要么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相比之下,金女大的毕业生们却以不同的姿态“入世”:她们中间有教师,有教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也有科学家、翻译家,还有人成为政治家、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甚至机构管理者。这些新职业女性的诞生,与英语的掌握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又与其时的世界语言局势是分不开的。
历经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扩张及其语言同化政策和殖民地政策的推行,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军事、经济上的崛起,英语的全球使用大大普及,在世界语言格局中取得中心地位。于是,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在世界各地急剧增长,英语教学成为一个有着巨大市场的产业。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举国积弱的局面,以英语为媒介的西学被有识之士视为救国的良药,英语则被认为是通往西方世界、研习西学的工具。在当时,很多科学类课程根本不存在中文教科书及参考资料,即使能找到教科书的译本,书中的观点也至少落后于时代十年,而且,这些书对术语的翻译往往让人摸不清头脑[8]。有鉴于此,金女大的教师们认为,英语能力的提高是学生谋求发展的必需,只有掌握了学科术语的英文表达,她们才有可能在一门学科的领域中继续深造[27](P14)。此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但是寻找一份体面工作的必需技能,更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正如当时上海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中所描绘的:“偶将音语学西洋,首戴千金意气扬。”[28(P87)如此情景下,掌握了英语,便拥有了更多的职业和发展选择,与接受国语教育的女性不同,金女大的女性因为可以留学接受更高的教育,有望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尽管仍然受到性别身份的极大限制,但开启了一种可能:金女大毕业生通过英语学习,成长为一批新的职业女性群体,成为中国曲折自强进程中一道夺目的风景。英语能力的提高为学生谋求发展提供了助推器,使她们能够继续深造,成为各种领域包括科学领域的佼佼者。
科学领域:金女大成功培养了一批蜚声海外、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女性科学家,而这些女性科学家,几乎都有着留学海外、以英语为学习和工作语言的经历。无论所学专业为何,金女大的教科书都尽量采用美国原版且坚持英语授课。四年的基础培训下来,学生对于使用英语来解析概念、探讨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甚至论文都已掌握,可以说,金女大的英语教育,已然包含了今天各大学普遍开设的“学术英语”的教学内容,为她们留学海外夯实了语言和专业知识基础。英语成为她们进军科学的工具,帮助她们跨越了语言、文化甚至性别的障碍,使其傲然成长为一代新的职业女性。以中国引进CT和MR技术的第一人、中国医学摄像学的带头人、1935年入学金女大的李果珍为例。从金女大毕业后,她于1948-195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进修,1998年和2001年先后被北美放射学会(RSNA)和欧洲放射学会(ECR)授予“荣誉会员”称号。这两个领域到目前仍然以欧美男性人士为主导,她是RSNA三位中国专家中的一位,ECR唯一的中国专家,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挣得了世界级的荣誉。而她的成功经验便是:“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学习。学好一门外语尤其重要。”[27](P126)
翻译领域:虽然金女大并没有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但翻译练习一直是该校英语学习的传统,成立于1918年、极其注重翻译练习的“中国文学社”便是一个证明。另外,为了鼓励学生练习翻译,学校还将学生们的译课作业编撰成册出版,《世界妇女的先导》就是这样的一部“译著”。值得注意的是,金女大的翻译练习,不仅求“达意”,更求“优雅”,这从“中国文学社”的宗旨可以看到。虽然金女大的毕业生很少被冠以翻译家的头衔,但她们却因翻译工作而赢得社会声望。第一届毕业生徐亦蓁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在1919年夏天为来南京讲座的杜威担任翻译,她的翻译被认为是“优雅”的,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4]。徐秀芝在1939年,为中国银行出版的“中外经济拔萃”翻译了一年文稿,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英国大使馆新闻处翻译反纳粹宣传稿,在中文报刊上发表[29](P46)。1935年入学的刘开荣虽系中文系出身,但英语基础亦佳,她对国内流行的《神曲》译本不甚满意,便决定重译,在译出《地狱篇》后因为“文革”而被迫搁笔[29](P75)。
政治领域:从金女大的课程设置来讲,女性政治家似乎并不在教育目标之内。然而,德本康夫人欲培养“女界领袖”的教育理想,和要求学生们担负“丰富中国女性生活”的责任,又带有浓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意味。此外,金女大英语教育中对学生能力发展的要求,如“发展理性思考的能力”“锻炼口语表达能力”,以及“锻炼清晰优雅地讲话的能力”,亦是成为一名政治家的必需素质。这样的教育方式无意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第一届毕业生徐亦蓁。徐亦蓁毕业后先是担任金女大校友会主席,1928年学校重组时,又被推举为校董;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难民营衣物工作组负责人,随后逐渐走上了国际舞台;1942 到1943年,她在美国36所高校巡回演讲,为战争中的中国教育事业募集资金;1946年,她担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凭借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举止,徐亦蓁逐渐成长为中国新女性的国际代表,在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工作期间,她的口头和书面英语表现,以及她待人接物时的优雅得体,令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感到惊奇。美方代表直接以“中国”称呼她,认为中国虽然政治力量弱小,但中国女性却极有教养[24]。徐亦蓁在回忆录中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女性从男人身后走出来,以共和国国民的身份为本民族做出贡献,争得荣耀。她无疑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
传播中国文化领域:一直以来,由于中国国力长期落后于西方强国,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多以“介绍西方先进理念、知识”为目标,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将中国介绍给世界”也是英语学习者的责任。值得欣慰的是,在1922-1923年金女大学生的英语作业里,这种朴素的思想已有体现。一位女生写道:“人们没有彼此的理解就不会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要写信给你们的原因,希望你们能了解我的国家。”③原文为英文,译文参考金一虹:《女性叙事与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4-35页。[30]毕业后,众多的金女大学子获得了出国进修或交流的机会,在别国居住期间,她们成为中国文明忠实的“布道者”。1924级的谢文秋,是第一个使中式菜谱受到美国人喜爱的烹饪学老师,她通过电视向全美和全欧洲的人们教授中式烹调,著名的《纽约时报》餐饮作家 Craig Claiborne认为,“大概没有一个人——至少在纽约历史上——像Grace Chu女士这样尽心尽力地让美国公众了解其本国的饮食文化”[29](P39)。另一位中国文明的传播者是剑桥大学终身院士鲁桂珍教授,她最为国人所熟知的事迹便是激起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文字及古典医学的兴趣,协助这位剑桥学者完成了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套丛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开始发行,向世人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用鲁桂珍的话说,李约瑟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她自己是支撑这座桥梁的桥拱[31]。
此外,无论学生们在金女大所学专业为何,无论毕业后人生之路是否平坦,做一名英语教师或兼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既是她们晚年的兴趣,也是她们维持生计的终身技能。
(二)在英语的帮助下突破男性话语围墙,提升女性地位
女性主义学者Weedon,C.指出,就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言,话语权的获得是女性应该被赋予的最基本的权力之一[32]。而美国学者Cameron,D.的研究发现,由于与主流性别话语相悖,大部分的女性主义话语要么遭到忽视,要么被边缘化[33]。在男权社会中,话语权的丧失成为女性提升身份的重大障碍。在中国“强种保国”为目的的女性教育下,女性权利实际上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而非其目的,因此,女性话语权的获得就显得更为艰难。
受到法国社会哲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研究话语权的女性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通过语言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34]。这是因为,语言是有等级性的,权力阶层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文化资本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起着标志作用,而符号资本则是机构认可和合法化的权威和身份符号[35]。一旦女性通过语言学习获得了语言所附带的资本,她就有可能打破性别限制,获得社会话语权。
在当时那个急于被现代文明世界接受的中国,英语的资本价值明显高于汉语,而国语则又高于方言。这种不同语言间的层级性,是金女大学子对中西权力关系最直接的体验之一。如徐亦蓁在回忆录中曾提道:“我们的家庭,特别是我的丈夫家,几乎是全盘西化的,……(我们认为)英语比国语及国学要重要得多,因为(在许多机构中)中式学者的工资总是最少的。……我们向往和赞美美国的一切。”[24]我们还曾访谈过一个叫段淑真的老校友,她的家庭曾在家族竞争中处于下风,但是因为进了洋学堂,在药房工作的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就超过了其他做私塾教师亲戚一年的收入。
然而,在教会女校实施系统英语教育之前,作为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象征的英语仅为极少数男性精英掌握,国语亦为父权控制下的中国主流社会所推崇。金女大女性通过学习英语获得了与男性专权相抗衡的语言资本,借助这种语言工具,她们终于能够在父权的主流话语围堵中打出一个缺口,为女性同胞谋得话语权,进而将女性的活动范围推向了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的空间不仅限于国内,还延伸到了国际舞台。金女大培养出的杰出女政治家徐亦蓁,就是为女性谋求话语权,提高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代表之一。
徐亦蓁毕业后不久即尊母命成家,且由于丈夫和母亲的反对,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协助丈夫管理医院,成了丈夫“身后的影子”④这是徐亦蓁描述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时使用的比喻。。她曾叹息说:“我从来就不想结婚。我非常遗憾自己有家累,有一个时时牵拌自己的丈夫。”[24]1928年,金女大重组,吴贻芳博士当选校长,徐亦蓁为校董。作为校董,徐亦蓁需要在各界名流包括蒋介石、宋美龄,以及作为医界名人的丈夫等人面前主持就职典礼,发表演讲,她抓住这样的一个公开演讲的机会,通过话语权的展示将自己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
就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就职演说,促使丈夫意识到我在金女大的位置和地位。他听到我的中英文演讲。我用英语向离职校长道别,......,并用国语发表演讲,阐述了托事部对她(吴贻芳)治下的金女大的希望。我的丈夫因此送给我一辆别克车配一个私人司机,供我从事公共事业之用[24]。
在这里我们看到,徐亦蓁选择使用的语言的顺序与其层级性之间的关系:她首先利用英语,表明了自己在隶属于高级别文明国家美国的金女大的中心地位,这样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参加就职典礼的部分男性;然后,她再利用标准国语将自我置于与中国男性精英同等的地位,因为在那个时候,标准国语刚开始推行,“连宋美龄也苦恼于自己带有浓重上海腔的国语”[24]。她巧妙地通过语言的层级性向丈夫,也向参会的所有男性发出了女性的声音,成功地把自己从“丈夫身后的影子”中解放出来,为自己赢得了参加公共事业的空间。徐亦蓁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金女大学子的自信,激发了她们想要谋得话语权、参与公共事务的决心:“直至今天,1928届的全体金女大学生还记得当天的盛况以及我的形象,她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她一样啊。’”[24]
在这次成功之后,徐亦蓁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增强,她更加注重女性话语权的获得。在担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初期,她希望搜集一些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信息,然而相关部门告知她:没有任何资料。她发现,那些驻外的男性官员完全不在意中国女性的社会活动,对他们而言,女性就是根本不曾存在的生物,作为中国女性的代表,她的任务仅是“出席”而已。然而,她拒绝做一个“哑铃”(dumb-bell),她想要代表中国女性参与辩论,向世人展示中国教育和社会活动领域里杰出的职业女性形象。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她借来打字机,根据自己对中国女性的了解,彻夜斟酌自己的英文稿,练习用英文做政治演讲,并邀请美国友人矫正自己的英语书面语和口语,最终及时提交资料,使中国女性在联合国与法国、丹麦、印度、俄罗斯等国比肩。
事实上,利用掌握英语的优势承担起社会责任,为中国女性在国际上谋求话语权,徐亦蓁并非孤例,这更像是金女大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传统。张肖松在回忆录中提到,1930年她接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在出行前又接到太平洋妇女会中国分会的通知,学校安排她同另两位同学一起去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年会。在大会上,张肖松代表中国女性发表演讲,列举了金女大毕业生在医学、护理、社会工作等领域的贡献,明确地将她的同学们称为“女界领袖”,指出中国女性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36]。
如果中国女性没有掌握英语这门联合国工作语言和世界通用语,如果金女大人没有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主动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为中国女性谋求话语权,向世人介绍中国女性的事迹,彰显中国女性的风姿,很难想象,中国女性还要被父权和西方政治强权围堵至何时,中国女性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又将是何种局面。
(三)在英语学习中建构新的主体性
在获得学习英语的权利上,中国女性走得比接受高等教育还要艰辛,究其原因,主要是男性对女大学生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不安。除了担心“女权主义”发达的西方文化的侵入将使旧有的伦理秩序彻底崩毁,还有男人对女性直接与世界对话的不安与不快。在此之前,女性与外界相通的每一道门都是由男性把守着,而如今,一旦获得了学习英语的权利,女性自己就开启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在英语读、写、译的学习中,以及女传教士教师们的言传身教中,中国女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逐渐被唤醒。女性主义学者Weedon使用主体性(subjectivity)这一概念来描述语言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她将主体性定义为“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考与情感,是她对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32](P32)。应该说正是金女大的英语教育,激发了金女大学生对新的主体性的思考。
1.读、译训练激发的朴素女权主义思想
金女大英语课程设置显示,学生的英语阅读以文学作品为主,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名著是阅读的主要内容。在英文阅读的训练中,她们开始不经男性的译介而接触并思考女权主义思想,如《简·爱》《理智与情感》等作品所反映出的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朴素的女权主义思想伴随着阅读在她们心中扎根、强化,再经由她们的笔端,借着翻译作品流出。
校长德本康夫人见证并记录了金女大学子在女权意识的引导下建构主体性的过程。1915年第一批学生入学时,女孩子们的表现让德本康夫人认为,由于家庭教育背景的关系,这些女孩子缺乏独立的人格[37]。然而,到1916年,她已坚信,在提升中国女性地位这件事情上,这些女生会比任何外国人做得都好[38]。在文学阅读的基础上,第一届学生将反映女权主义的人物传记翻译出来,她们的作品被集结成册,取名《世界妇女的先导》,由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版。这本册子的内容包括:平民女子教育的创办者耐恒·马利亚(Mary,Lyon);红十字救护队的先锋南丁格兰·佛劳纶斯(Florence,Nightingale);俄国革命的祖母客斯琳(Catherine Breshkovsky);非洲人民的曙光司立逊·马利娅(Mary,Slesser);女子选举权的先进夏恩诺(Anna,Howard Shaw);女青年会的先导杜贵斯(Grace H.Dodge);贫民的救主安藤·加茵(Jane,Addams);日本妇女节制会的领袖哈哲女士(Kaji Yajima)。一共8篇文章,介绍了外国杰出女子的事迹,鼓励中国女性发挥潜能,开拓事业。
20世纪20年代后,金女大的英语课程中增设了“当代杂志选读”,而20年代正值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斗争的焦点是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一夫多妻,并强调男女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可以想见,这样的思潮必然在当时的杂志中有所体现,亦为金女大学生接触并消化。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潮对金女大强化理科教育,培养出一代代女性科学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能发挥了引导性的作用。
2.在自传写作中想象并重新定位自我
中国的文学创作形式中,鲜有自传书写的历史传统,这一点于女性更甚。中国女性从属、隐形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男性主权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几乎到20世纪中国女性都没有想过或根本没有勇气从事自传性写作[39]。然而,自传体文学却成为金女大英语学习的对象,1920年的英语课程设置中,对“文学”一课的说明是:“阅读内容包括一份自传和散文若干篇,基于阅读内容着重训练习语、词汇和口头作文,另外布置课外阅读内容。”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民国女性冲破历史陈规、文化习俗及社会权力关系的羁绊,是女性赋予自我价值、建构主体性的行为。而语言教学研究者则认为,“通过语言来表述意义、整合知识及经历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40]。这种类似回忆录的书写形式有助于学生整合知识,寻找自我并发展独立人格,对女性主体性的形成有着特殊意义。
根据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档案,1922到1923年,一位名叫Dorothy Lindquist的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命题作文时,将写作题目定为《我的自传》(My Autobiography),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内,按照副标题“十岁前”“十岁到二十岁”“我的金陵生活”,分三次回顾并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是对“文学”课上学习的自传文本的一种模仿性写作。这些微型自传的内容,反映出这些女大学生们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双重想象,以及如何通过这种想象重新定位自我[41](P21)。在自传中,有学生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我有了更大的目标:我要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我仍然有许多东西要学”;还有学生表达了对独立自我的向往,“独立已成了我一生的誓言”;更有学生强调,自己虽身为女性,但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力量的一部分,“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女孩,多么希望在自己步入社会的那一刻,能赶走这种恶魔体系啊!”⑤关于自传书写的更多内容参考金一虹:《女性叙事与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学生对自我主体性的思考,对未来生活的设计,以及对自身在中国社会中将处于何种位置的规划和想象。这样的思考,代表着中国女性从混沌的、由男性主宰的生命轨迹中清醒过来,对生活、对自我都有了诉求,而这些朴素的、哪怕尚在想象中的诉求,对于她们未来的成长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自传写作不仅是金女大学生寻找自我、建构自我主体的行为,亦是她们总结自我、声明主体性的行为。在金女大自传教学传统的影响下,许多毕业生,如刘恩兰、徐亦蓁、张肖松等都在中年或退休时留下了自传文本,且多为英文。这些自传文本向世人展示了她们如何在中西、男女权力关系中协商突围,最终成就自我。而她们倾向于使用英语书写,一方面体现了金女大偏重英语教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语为她们表达自我提供了便利。当女性自传还难以为中国社会主流接受之时,利用英语表达自我便成为一种无声的抗争和突围。
3.学习英语,肩负民族责任,建构能为主流社会接受的主体地位
美国学者Zurndorfer,H.J.通过对民国时期教育辩论、期刊文章和个人自述的研究发现,“众多的女性学生和毕业生难以融入男性主权的以爱国为中心目标的主流社会”[42](P474)。这意味着,接受教育的女性较难在父权控制的主流社会建构主体地位,而对金女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困境尤甚。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充满剧烈的语言文化冲突,特别是在国家主权面临威胁之时,女性的言语行为更是成为她们民族认同的标签,而民族认同则又被主流社会视为女性身份的重要方面。于是,学习英语的金女大学生在建构为社会认可的主体地位方面面临着更多挑战:由于专注于英语学习,金女大的学生经常“被人非难和窃笑”[13](P4),被称为“西人文化侵略的帮手”[43](P8),这样,建构共和国国民的身份就成为她们对抗质疑、赢得社会认可的破冰之举,她们利用民族主义话语,将英语学习建构成一种民族主义行为,进而建构起一种能为主流社会接受的主体地位。
在金女大学生的书信、演讲、回忆录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民族主义”。肩负民族责任,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是金女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共同目标。徐亦蓁在回忆录中表明,自己8岁就萌生了学习英语、探究中西关系的念头,这主要是因为父亲的嘱咐:“要学习英语以及这些国家(西方列强)的历史,了解它们的用心,它们没有善意,……目的是填饱自己”[24]。有不少学生将求学金女大等同于爱国,如一位学生写到,“她(老师)对我说,‘小姐,如果你不去修大学课程,你就是不爱国。’这话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1](P21)徐亦蓁也有类似的话语,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抱负阐释为民族责任的履行:“在我那个时候,即1915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有些抱负的,都希望首先进教会学校,然后再赴美深造……我们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回国重建我们的社会。”[24]张肖松则突出强调了金女大对她的民族责任感的影响,她不止一次地提到,能够入学金女大,是极少数女性才能享有的机会,因此要对那些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同胞负责;金女大的教育,除了让她获得“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重视合作”,也让她“欣赏责任”,“在这里,......我看到祖国的需求,也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的祖国”[44]。
可见,金女大人对英语学习的回忆,是在探寻自我的同时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英语学习成为她们履行民族责任的行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她们鲜明的主体特征。
三、成长之惑:英语教育带来的“感情伤害”
新女性的成长,伴随着阵痛和彷徨,需要承担“丰富的痛苦”[45](P219)。中西、新旧思潮的冲突与矛盾,将她们推至语言文化和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在金女大人的叙事中,拥抱西方现代化的愿望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相交织,这种矛盾伴随着英语学习的全过程。她们向往通过英语学习迈向一个高级文明的新世界,却又曾抗拒过英语,对英语的抗拒不仅发生在一些女大学生的幼年,还发生在她们求学金女大的时光。可以说,在赋权她们挑战男性主权、建构自我的同时,英语学习也为她们带来了“感情伤害”⑥这是一个女学生在自述中对英语学习感受的描述,“我遇到了很多伤害我感情的事情……因为我糟糕的英语”。,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和困惑。这种感情伤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英语学习本身的困难,二是英语学习导致的认同困境。
金女大高标准的英语要求,希望为中国培养女界领袖的理念,虽然对学生学习英语有极大的鞭策和激励作用,却也给学生带来了诸多压力和困惑。德本康夫人在1918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金女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导致了该校“在前几年一直被两个不同方向的意见所困扰。支持我们的一个差会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因为英文水平太低而被人们批评,连大学的资格也受到挑战”[46]。对于金女大第一届学生来说,英语课程是“极为困难”的,课程的学习是“最令人沮丧的事情”[20](PP6-7)。在第一堂英国文学课上,大部分人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英文都没听懂[20](P6)。她们曾经凌晨3点悄然起床,连续工作5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一份作业,却在上课时失望地发现,仍无法让老师满意[20](PP6-7)。而校长德本康夫人则认为,她们缺乏独立的人格,不是为求知而来,只是由于家长的安排才来就读金女大[37]。在最初的一年里,学生人数骤减,由入学时的8名降为5名,其中一位还是后来的插班生⑦金女大初创时,校园简陋,师资薄弱,教学设备匮乏,这些也是学生弃学的原因之一。。为了达到学校对英语水平的要求,第一届学生每晚7点到10点坚持自习,“埋首书本”是对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总结[20](P21)。这样的生活对她们来说,无疑是苦闷的。英语学习打击了她们的自信心,成为她们入学之初最大的烦恼,以至于影响到她们接受教育的信念。
实际上,英语学习的困难是一代代金女大人必须面对的成长的烦恼。鲁桂珍也在微型自传里写到,学校的课程对她来说都太难了,一年级的两门英语课程,她的成绩一门为D,一门为F,是所有课程中最低的[47]。以至于她一度觉得异常疲惫,甚至有了退学的打算:“我想,如果按照朋友的建议,多学一年再回大学一定会好上很多。”[48]她虽然终于坚持下来,但是对痛苦的学习也有不少抱怨,认为繁重的功课使得学生们纯粹为了学分或考试而学习,忽视了个人精神层面的需求。
如果说困难重重的英语学习曾经打击了金女大学生的自信心,挤占了她们投入精神生活的时间,那么,由英语学习导致的认同困境,则带来了深深的“感情伤害”。国家极弱,外敌入侵,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国人对英语这种一方面象征着高级别文明,另一方面又代表着西方强权的语言怀有深深的敌意。鲁桂珍写到,幼年时期的她对英语持异常敌视的态度:“讨厌外语,为什么我一个中国的女孩子要学英语?”她称那些学英语的女孩子“卖国贼、大傻瓜”[48]。虽然最终在老师的开导下,她意识到学习英语,掌握西方科技是兴国的必然手段,但她以及所有的金女大学生都无法逃离英语学习带来的认同困境:她们的共和国民身份,以及对祖国、民族的可能贡献,一直都被同胞,特别是男性质疑。这种质疑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时期尤甚,在1924年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时期达到顶峰。一位署名曾潇的学生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痛苦地描述自己受到的批评:
友人喟然长叹曰:不谓子等俨然大学生,……舍本求末,弃近而骛远耶。我为子等愧,我为国家人才前途痛苦也。……(子等大学生)能执钢笔,作英文论,洋洋洒洒,流利畅快。试与论中国文,顿露枯窘之色。数年后,纵能造诣幽深,试问我中国何贵有此无数昧于国情,纯粹欧美化、机械式之读书匠矣。子等他日入世,为人母为人师,尽其所知,诏导后人,数十年而后,中国现状如何,有不忍书言者矣。[49](P21)
由于过于专注英语学习,她被友人指责为不仅于国家复兴无益,反而有害,更不能肩负起教育学生、子女的责任。这样的批评让她以及身边的不少女生开始担心个人价值,并对金女大的语言教育理念产生怀疑,要求学校采取措施,提高中文教育的水平。此外,龙襄文和黄燕华曾抵制金陵自立校之日就设立的英语概括考,在学生自治会上,龙襄文还要求吴贻芳用中文发言和主持,可见英语教育带来的感情伤害之深[29](P495)。
令人欣慰的是,金女大以人性、严谨的教学模式,引导着学生逐渐走出成长的烦恼,民族主义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化解了情感上的伤害;同时,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坚定着她们的学习信念。虽然背负着质疑与指责,金女大人从未放弃建校之日的语言教育理念,经过严格的英语训练,一代代金女大人走出校门,或踏入社会,或扬鞭海外,创造了女性事业上的一个个奇迹。
四、结语
19世纪以降,英语的国际化传播冲击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观念和文化。西学东渐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生活方式甚至宗教信仰;随着英语裹挟而来的,还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性别观。1918年,留美归国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将新女性这一称谓介绍到中国。彼时,人们把对现代化的追求诉之于中国女性新身份的建构上,女性高等教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象征之一。高等教育赋予了中国女性打破传统性别束缚的机会和权力,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教育赋权依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这是因为,教育机构本身就承载着生产和复制阶层和文化的功能[50]。由美国女传教士建立的金女大,承载着美国受教育女性对性别平等的理想,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冲击和解构。当金女大选择使用英语为媒介来为中国培养新式公民时,她已然挑战了中国男性的权威,因为当时的男性精英们正在通过国语教育来培养“助手”,而非“领袖”。英语的学习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犹如为女性高等教育插上了一对翅膀,带领她们以更高的境界和更广阔的眼界,去摆脱男性主权的社会结构的束缚,去大胆地想象未来,以建构起新的自我。英语赋权犹如一把利剑,中国女性仗剑而行,在被男权围起的坚固墙垒上打开一个缺口,为自身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和更大的人生舞台。
与在国立女校接受国语教育的民国女大学生相比,接受英语教育的金女大学生拥有更多样的职业选择和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当然,其主体性的建构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虽然在异域语言中接受教育,她们依然具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并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是她们做贡献的方式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相悖,语言以及地理上的障碍也使她们的事迹不为当时的国人熟知。金女大群体对于新女性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她们正是金女大为中国社会变革做出的贡献:通过培养一批批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新女性,并传播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金女大影响了中国一个时代的女性。可以说,相对于女高师“培养白话文女教师”这一保守的革新,金女大不仅把握了女性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且把对这种重要性的期望推到了极致。金女大女性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对中国新女性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需要得到全面的评判。
当前,中国女性对英语学习的热情有增无减,概观英语课堂,总是以女性学生居多。而在语言教育领域,“女性主义英语课堂”正在兴起为一门新的研究课题,研究者们发现,对于亚、非地区的女性而言,英语学习是一种解放自我、赋权自我的手段[51](P308)。2000年,美国著名语言教学研究者Lantolf在《一个世纪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我们总以为自己比前人掌握更多知识,然而,细致的考察显示,我们对历史所知甚少,曲解颇多。那些被我们视为新颖的或革命性的研究成果,其实一再见于历史,或者,至少以某种形式存在过。”[52](P471)金女大建校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此时回顾这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英语教育理念、教学特色、课程设置及其在中国女性身份转变中曾经发挥的作用,对当今中国女性的语言教育和妇女发展事业有着深刻的启示。
[1]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Wang,Z..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M].Berkley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3]Rouse,J..The Politics of Composition[J].College English,1979,(1).
[4]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
[5]张莉.阅读与写作:塑造新女性的方式——以冯沅君创作为例[J].中国文学研究,2008,(1).
[6]钱焕琦.精英是怎样炼成的?——金陵女子大学人才培养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6).
[7]王红岩.金陵女子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特色评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6).
[8]胡艺华.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特色初探[J].高校教育管理,2009,(2).
[9]Matilda Thurston.Personal Report of Mrs.Lawrence Thurston[Z].Burke Library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MCT,Box10,10.5.,August 1915.
[10]Robert,D.L..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M].Macon,Georgia: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96.
[11]Lutz,J.G..Mission Dilemmas:Bride Price,Minor Marriage,Concubinage,Infanticide,and Education of Women[M].New Haven: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2002.
[12]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3]幽清.对于金陵之希望[J].金女大校刊,1925,(1).
[14]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览[Z].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18.
[15]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Z].南京:江苏省金女大校友联谊会,1983.
[16]Enda F.Wood.For Love's Strength Standeth in Love's Sacrifice[J].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5,1(4).
[17]Ginling College Records[Z].Smith College Archives,Box7 Publications,folder 3 Bulletins,1915.
[18]Matilda Thurston to Calder Family[Z].Burke Library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11 April 1907,MCT,Box1,1.17.
[19]Ginling College Records[Z].Smith College Archives,Box7 Publications,folder 3 Bulletins,1925.
[20]Liu,etc..The Pioneer[Z].YDL:UB-CHEA,RG11,Box151,Folder 2946,1919.
[21]蒋琳英.本校文艺会之历史记略[Z].金陵女子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
[22]Mao Shwen-yv.Two Years in the Life ofthe Ginling Magazine[J].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6,2(2).
[23]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G].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24]New,Y.T.Zee.Typescript ms.:Biographical Material[Z].YDL:CRP-MPP Group 8,Box145,Folders 3-4.
[25]Bailey,P.J.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Abingdon:Routledge,2007.
[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地1册)[G].北京:中华书局,1994.
[27]Mrs.Thurston,L.and Miss Chester,M.R..Ginling College[M].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6.
[28]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G].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29]金女大校友会编.金陵女儿(第三集)[G].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0]Handwritten Essays by Chinese Women Students at Ginling College(1922-1923)[Z].YDL:CRP-MPP,RG11,Box231 Dorothy Lindquist,Folders 1-13.
[31]曹聪.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约瑟[N].中华读书报,2008-10-09.
[32]Weedon,C..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2nd Edition)[M].London:Blackwell,1997.
[33]Cameron,D..Language,Gender,and Sexuality:Current Issues and New Directions[J].Applied Linguistics,2005,(4).
[34]Eckert,P..Gender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A].In Coats,J.(ed.).Language and Gender:A Reader[C].Oxford and Malden:Blackwell,1998.
[35]Bourdieu,P..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36]Djang Siao-sung.The Place of Educated Women in China[Z].YDL:UB-CHEA,Box136,Folder 2738,Correspondence,1930-1939.
[37]Matilda Thurston to Calder Family[Z].Burke Library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15 November 1915,MCT,Box2,2.3.
[38]Presbyterian Report——Ginling Mission(1916)[Z].YDL:UB-CHEA,RG11,Series IV,Box155,Folder 2966.
[39]Wang,L.Z..Personal Matters: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0]Swain,M..Languaging,Agencyand Collaboration in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A].In H.Byrnes(ed.).Advanced Language Learning:The Contributions of Halliday and Vygotsky[C].London:Continuum,2006.
[41]金一虹.女性叙事与记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42]Zurndorfer,H.T..Gender,Higher Education,and the“New Women”:The Experience of Female Graduates in Republic China[A].In M.Leutner and N.Spakowski(Eds.).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 Period 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Munster:Lit Verlag,2005.
[43]施云英.本校十周纪念与我的感想[J].金女大校刊,1925,(1).
[44]Djang Siao-sung.My Experience as a Student in a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Z].YDL:UB-CHEA,Box136,Folder 2738,Correspondence,1930-1939.
[45]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46]Annual Report(1918)[Z].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UB-CHEA,Box154,Folder 2961.
[47]Student lists and statistics B-K1918-1931[Z].YDL:UB-CHEA,Box129,Folder 2652.
[48]Lu Gwei-djen.My Autobiography[Z].YDL:CRP-MPP RG8,Box321,Folder 8,Handwritten Essays by Chinese Women Students at Ginling College,1922-1923.
[49]曾潇.记友人言[J].金陵女子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文版),1925.
[50]Bourdieu,P.and Passeron,J.S..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M].Beverly Hills:Sage,1977.
[51]刘媛媛.从认同到性别——语言教学研究的新动向[J].现代外语,2012,(3).
[52]Lantolf,J.P..Introduction tothe Special Issue:A Century of Language Teachingand Research: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Ahead[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0,84(4).
责任编辑:绘山
The Significance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Women" Identity in the Nationalist Period: A Case Study of Gin Ling College
LIU Yuan-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Shandong Province,China)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women's identity;Ginling College;case study;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has been a key factor in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identity in China and the world.Language educa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tool for shaping citizens'identity.A question this paper raises is:what role di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Nationalist Period play in the rise of"New Women"in China?To address this question,the paper uses Ginling College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role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Ginling students'identity.It review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t Ginling College,and discusses changes in women's identity based on three aspects:the growth of new professional women,the rise of women's social status,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new women."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English education on women at the time,the paper will also ponder on the question of how English study created"emotional wounds"among women students and suggest possible lessons one can draw from the Jinling English education model to enlighten today's language education among women in China.
G649.29文献标识:A
1004-2563(2016)01-0053-12
刘媛媛(1981-),女,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思想史、性别与语言学习。
*由衷感谢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对本文选题和写作思路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