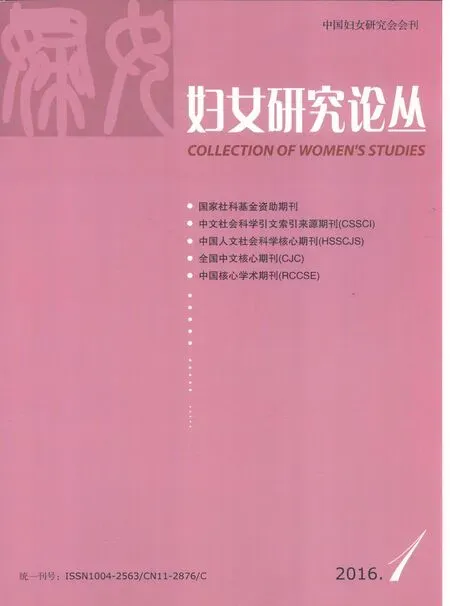“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
——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
杭苏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观念解放”还是“情感解放”?*
——民初湖南新女性“离家”的实践困境
杭苏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妇女解放;观念解放;情感解放;恋慕;情感转化
文章通过分析湖南新女性个体的“离家”过程,探讨在妇女解放过程中“情感解放”与“观念解放”之间的差异,以及“情感”对于个体的解放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家内的自然情感常常阻碍一些观念已经解放的女性离家,获得个体的真正解放,另一方面,对于离家女性来说,虽然她们能够暂时克服这种情感对她们人身的限制,但是出走到社会的她们仍然对家怀有某种既怨又恋的“怨慕”情结,这无疑使个体陷入“解放”的情感困境之中。文末,进一步探讨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情感“转化”之可能,以及“情感解放”的限度问题。
一直以来,有关妇女解放的研究大多关注妇女解放理论和群体性的妇女运动,较为忽视女性的个体解放实践。已有研究有的从类型学的角度将解放划分为社会解放、个性解放和阶级解放[1](P118),有的探讨主体的理性自觉[2](P7),还有的从群体的角度讨论女性的解放实践[3]。但是,由于缺乏对女性个案的考察,我们对“妇女解放”的了解只停留在抽象的学理辨析和粗线条的历史脉络上,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因而,对“个体解放实践”的考察将更清晰地反映“解放进程”中的困境,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妇女解放理论”提供可能。
对于民初女性解放来说,最重要的一步是“离家”。能否成功逃离家庭,特别是脱离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往是女性能否走出传统习俗社会,走向大城市的关键。“反家制”一直是民国思想界最主要的思潮[4](P2),但是,与思想、舆论中对“家”和“家族”的猛烈抨击不同,这些不断尝试着从家庭里逃离的女性,虽然在观念上接受了对家的批判,但在情感上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之情结,而这不可避免地使其陷入“解放的困境”。
一、“离家”的意义:三种解放的扭结点
“离家”这一事件到底对女性意味着什么?通过研究民初湖南新女性的各种回忆文章、书信和相关材料,我们将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我们所研究的民初湖南新女性主要指湖南各县和村镇中的新式知识女性,她们一般出身于当地望族、官绅家或者殷实人家,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给她们提供读书的机会。并且,她们在高小毕业后,大多数读过省内的官立师范。这一方面反映了她们的家庭在女子读书问题上较开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县镇,甚至是乡村中的女性,家长并不愿意在女儿读书上花费过多,只选择学费、食宿费全免的官立学校。辛亥革命后,在谭延闿的开明政权下,湖南新建了六所女子师范学校,数量堪称全国之首[5](P133),其中,长沙、桃源、衡阳的省立第一、二、三女师为官立师范,分别招收各乡镇的高小毕业女子,成为这些女性最重要的新式社会空间。
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决定离家时,她们往往有着现实的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抗婚。“抗婚”的出现不仅因为新女性受到了“自由婚姻”思想的鼓动,更包含了新女性对个人前途的担忧,摆脱社会束缚的愿望,甚至还带有某种模糊的反对阶级差异的思想,这些因素都扭结在“离家”这一个体实践中。
1918年,24岁的黄彰(后来的女作家白薇)从长沙第一女师出逃时,她一方面是因为不愿被父亲逼迫着重回婆家,婆婆的虐待、离婚的无门,使她在传统社会中已经没有适宜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对新知识与新世界的向往。口袋里只有六元钱的她,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坐上了前往日本求学①黄彰一直想升学,但当时的国内大学尚未开放女禁。唯有留学是一条可行的路。的客船,这不可不谓一个过于大胆却又充满勇气的决定。黄彰原籍湖南资兴的秀流村,是长女。父亲曾留日,办过小学、参加过革命军、开过矿,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黄彰于1914年正月逃离生活了四年的婆家,获得父亲的同情后,进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是,婆家后来扬言,如果黄彰不回婆家,就将对她唯一的弟弟进行报复。这一威胁迫使父亲不得不将自己生了六个女儿后才得来的儿子放在首位,为了避免“无后”,他坚持要求黄彰毕业后重回婆家。所以,对于黄彰来说,在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之后,她必须找到一条自我发展之路[6](PP39-80)[7](P171)[8](PP175-179)。这一特点在其时的很多湖南离家女性身上都能得到印证:1920年长沙李欣淑拒婚出走后参加了北京的工读团体;1922年蒋玮(女作家,后改名为丁玲)拒婚离家后参加中共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1926年谢鸣冈(女作家,后改名为谢冰莹)和族甥谢翔霄拒婚离家后当兵;黄彰的五妹黄九如(女教师和女作家,后改名为黄碧遥)婚后离家,带着儿子留学日本,都反映了新女性追求个体解放和发展的愿望。
不过,新女性的“离家”并不只是为了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或者如一些研究[9](P47)所说是为了追求个体解放,其实,在她们看来,这一行为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效果。如同另一位湖南新女性周铁忠在从军受拒后所说:“这次我们来当兵,是下了牺牲的决心才来的,我们脱离了家庭来投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群众和痛苦的自己。”[10](P90)同时,在客观效果上,这些离家者也起到了推动变革的作用。长沙李欣淑离家到北京实行工读后,长沙的报纸称赞她为“比赵女士(赵五贞,为抗婚自杀)所发生的影响要重要些,要远大些,要切实些……能够实行奋斗生活”[11](P8),从而鼓舞了一般女性更加积极地奋斗与进取。
此外,这些女性的离家还潜藏着模糊的阶级意识。1922年正月,蒋玮在离家之前,在常德县《民国日报》上批判自己的三舅是“剥削幼婴”的“豪绅”,是“嘴上讲仁义道德”的“社会害虫”[12](PP296-299)。三舅也是蒋玮未来的准公公,在蒋玮父亲去世后,一直颇照顾蒋玮母女,曾留日,后在常德县劝学所和育婴堂任职,是当地士绅。当蒋玮指责三舅是“豪绅”时,她显然受到了五四报刊的影响,“豪绅”即土豪劣绅,是当时新出现的名词,是革命的对象。在蒋玮看来,三舅私德败坏、安于享乐,却又虚伪地讲究礼教,正和报纸上所说的“豪绅”类似,于是,在和这个豪绅家庭解除婚约之后,蒋玮得以离家去上海寻求自己未来的道路。
从这些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离家”这一事件实际上扭结了个体解放、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三者。通过“离家”,新女性不仅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之中,并且,她还模糊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革新一分子的力量,乃至自己的阶级属性。而这几乎开启了新女性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有的追求。因而,理解“离家”,特别是其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潜在困境,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解放的困境:个体的情感羁绊
(一)“放弃离家”的情感考量
在研究民初湖南新女性的离家过程时,我们发现很多因素影响了女性能否顺利地离家。比如,是否具有他者的支持;家内权威是否过于严厉;个体是否具有顽强的意志,等等。不过,在对黄彰三姐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其他因素相似时,个体的情感羁绊程度往往会影响到个体能否顺利地离家。
如上文所述,1918年夏天,黄彰从长沙第一女师毕业后逃到日本。其时,她的四妹黄九思和五妹黄九如也一起毕业,同样面临着被父亲逼迫成婚的处境。四妹黄九思曾为此哭过好几次,她读高小时,曾和未婚夫同班,后者功课远不及她[13](P19),因而她并不愿意嫁给对方。但是,当黄彰去鼓励她一起逃跑时,她却十分犹豫,虽然不满意父母包办的婚姻,可是她也不赞同逃走,黄彰曾回忆她的原话:“那……那么做,爹娘都要急死去!”[14](P42)正如五妹黄九如在为四姐的悼文中所写的“(她)以为此种违背礼教的举动,将使父母伤心,将使故乡培植女孩的事中辍”,故没有和黄彰一起出逃。事后,她“屡次被迫出嫁,每次都急成病来”,最后一次病得“危在旦夕,还是把她抬去了……怕她嫁去就会死”[15](P88)。
和黄九思一样,五妹黄九如也因害怕逃婚引起父母担心,一开始选择了放弃离家而答应了婚约。不过,和黄九思最后永久地呆在夫家不同,黄九如在生下一子后仍旧无法适应这种生活,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家,带着孩子去日本留学。由此可见,在对父母的情感和自我的未来发展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张力,很多放弃离家者,往往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或是社会革命和自我发展的意识没有形成,而是她们无法割舍自己和家庭的感情。当黄彰被父亲骂为“父子革命、家庭革命”而不认这个女儿,当谢鸣冈的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大骂“昔则为鸟中之凤,今则变为食母之枭”[16](P193)时,离家女性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决绝并不是每一个女性所能承受的。
(二)“怨慕”:离家者的情感困境
不过,离家者虽然克服了家内情感对她们的羁绊,但是当她们以决裂的方式离开家时,她们仍对父母和“家”怀有某种难以释怀的情愫,这往往使她们陷入“怨慕”的情感困境之中。1944年,已经成为名作家白薇的黄彰,回忆当年父亲去长沙女师督促自己回家的情形。当许久未见的父亲出现在学校时,黄彰内心十分复杂:
父亲,生我的上天,我的恩师,病中的神医,兼仙人似的护士,那爱我也将要杀我的父亲呵!……我一看到他来,稚爱的童心热血来潮时,真想跳进他的怀里,像幼儿勾着母亲的颈亲吻,也勾着他亲一亲。但想到他这次来的意义,尤其对我的严重性,真是不寒而栗……他是处我死刑的法官,断我生命的死神
和黄彰的其他文字一样,在这情感几乎满溢到夸张,充满“纠结盘绕的修辞”[15](P90)的述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黄彰对父亲的矛盾情感:既感激、爱戴,又恐惧和愤怒。当她最终选择逃离,决定冲破父亲这位“死神”的管控时,她的内心充满了不舍与依恋:
当我鞠躬向父亲礼别②父亲此时并不知道黄彰已下定决心逃跑。时,心碎了!心里想“别了,父亲!不知哪年哪日,或许七年八载再见吧,也许永远不能再见了。”……依依之情想靠近他些,愿时间延长些,让我多看他几眼。……望着车子走过的长街、列店,落泪了[6](P49)。
这种对父亲既反抗又难舍的情感,更表现在黄彰在日本时给父亲写的一封两万多字的长信,她一方面指责父亲不该给家中弟妹包办婚姻,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这种批判的方式使父亲理解自己选择逃离的苦衷,希望父女能够和解。
和黄彰类似,谢鸣冈在离家的同时,也怀着对父母的忏悔。谢鸣冈的父亲是新化县县立中学校长,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深受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可谓半新半旧。与之相比,谢鸣冈的母亲则更趋保守,在礼教方面极端固执和专断。她在无法说服谢鸣冈出嫁后禁闭了谢鸣冈。谢鸣冈逃离了三次都未果,最后在嫁人后又逃跑,才得以离家。对这样一位母亲,谢鸣冈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矛盾。透过母亲的严词厉声,以及母亲为自己婚事的操劳,她既感到一种“爱非其道”的痛苦,又不禁为这“非其道之爱”动容。她曾通过母亲的口吻写下了母亲为自己准备嫁妆的辛苦,虽然,她是多么地痛恨这一婚约。
你看,娘是多么为你操心呵,为了漆这些木器……刮风的天,生怕灰尘落在金纸上,常常睡到半晚爬起来用油纸盖上,白天又怕孩子们去弄脏了,或者麻雀飞来撒屎在上面,一天至少都要看几十遍;天天都要去监工……[10](P140)
并且,当她离家四年后第一次回家时,她被母亲的眼泪和爱意完全感动了。母亲一开始不理她,甚至骂她。到了晚上,却偷偷走到女儿床前留下了眼泪。
很想一骨碌地爬了起来跪在母亲床前,求她宽恕我的罪过。四年来,我给她的痛苦太多了,仅仅只为了自由和幸福,就使母亲整夜为我失眠,为我的没有音讯而求神问卦……母亲给予我的热爱(这爱是藏在她心坎深处的最高无上之爱,伟大的天性之母爱),使我感动只想流泪[10](PP224-225)。
对父母的这种复杂情感,在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中也有过叙述。孟子曾称被父母和异母弟弟嫌恶,甚至要被杀死的舜向上天哭诉是“怨慕”[16](P302)。“慕”字的意思是“小儿随父母啼呼”③《礼记·檀弓》记载孔子称赞一位孝子送葬“足以为法”,原因之一就是“其往也如慕”。《礼记·正义》又对此进一步阐发:“谓父母在前,婴儿在后,恐不及之,故在后啼呼而随之。”,在婴儿追随父母啼呼这一颇具本能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中自然性、先天性的因素。但是,“慕”这一概念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不仅仅指涉婴儿对于父母的情感,儒家经典还使用它表达成年人对父母的情感。比如孔子称赞孝子送葬“如慕”,《礼记》频频使用“思慕”一词表达孝子对亡父母的情感。“怨慕”这一概念背后虽然带有肯定舜为孝行的道德评判,但是,它也恰切地展现了在不融洽的亲子关系中,子女最真实的情感状态,既“怨”,又隐含着恋慕,两者之间不仅互相交织,而且互相对张,使个体处于内在情绪的紧张和冲突之中。
在以往的妇女解放话语中,“离家”往往是新女性打破传统家制束缚,获得个体解放的关键一步,但是,“怨慕”之情的存在使我们不禁反思,处于“怨慕”之情的“离家者”真的获得了解放吗?她们在何种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不完全”的解放?这为我们重新理解“解放”这一概念有何帮助?
三、反思“情感解放”的可能性
(一)观念解放与情感解放的差异
在传统妇女解放研究看来,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观念的改变,一直被视为解放过程的关键点。观念和意识的改变,能够促使个体成为“新人”,从而推动他们追求自我和社会的解放[17](PP57-62)。对于个体来说,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新女性来说,观念的改变并不是难事。长期的学校教育与知识获取使他们习惯于用观念思考问题,并且,观念的改变十分迅速、抽象,并不过多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新女性的解放过程中,观念解放往往很容易实现。但是,观念解放并不能最终地实现个体的解放,这其中,还需要具体的实践过程。此时,“情感解放”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与观念解放的抽象性、迅速性不同,在解放过程中,情感的变化显得既缓慢又难以彻底转变。对于新女性来说,她们在“离家”中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她们无法接受新的观念和想法,而是即便她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但由于家内情感的羁绊,她们仍旧难以逾越情感的边界选择离家;或者,就算她们能够暂时地不顾情感羁绊离家出走,而对家的情感常常使这些追求解放的女性处于“怨慕”的冲突性情绪中。那么,为什么情感会成为“解放”的困境呢?它与观念解放到底存在何种本质性差别。
首先,情感具有自然性。民国思想界对于“家制”的批判可谓异常猛烈,很多新女性的离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家为束缚个体自由”的观念影响,但与此相比,在面对现实的离家时,她们仍感到情感上的难舍以及分离的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都缘于父母—子女之情的自然性。一直以来,父母与子女之爱都被看作个体之间最自然的情感。不论是西方古典思想中,亚里士多德将家庭看作培养友爱(philia)的自然机制,批评柏拉图的城邦只会培养一个个自私自爱的个体[18](P3),还是中国传统儒家以“孝”这一“自然亲爱父母之心”[19](P1)为中心,缘“亲亲”“尊尊”之义推展出整套社会伦理,都有着类似的判断。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很多研究都将子女对父母的这种亲近与依恋,视为类似于动物本能的反应。可见,当妇女解放需要打破家之束缚,将女性解放为独立个体时,这种父母—子女之情常常因其本能性和固有性,而使女性难以割舍。
其次,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家内情感更因为父母与子女的长期共同生活而愈发坚固,从而形成社会性的依恋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此时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互动形成了共同体内部的情感。和通过学校教育等方式获得的观念革新不同,家内情感是建立在家内成员的长期互动之中的,它难以达成迅速的改变。所以,虽然一些离家女性已经不再和父母共同生活,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女性都生活在家庭这一共同体之中,而没有别的社会位置和共同体,所以她们仍会由于之前的家内互动而产生情感上的依恋。
(二)家内情感的“转化”
民国时期离家女性对父母的“怨”“慕”之情往往互相冲突,使其对“家”有着复杂的情感。她们虽然离开了家庭,但这种复杂的情感却困扰着她们,使其在情感上绝不能称为已到达“解放”的程度。这种困境的产生,是民国时期反抗“家制”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新女性只能通过“离家”才能开启个体解放的第一步,所以她们不可避免地和家庭决裂;但也正是这种决裂,使她们对家的情感无所寄托。对于她们来说,家内秩序已经无法重建,要想缓解情感上的困境,只能通过参与新式共同体的方式,使个体的感情从家内转入社会,而这将对一直以来都以家庭为本位的女性构成挑战。
在儒家经典中,面对父母和兄弟的仇视、家内关系的恶化,圣人舜选择了忍耐和“向上天哭诉”的方式来缓解[20](PP90-91),这不仅是儒家思想对于“孝道”的追求,也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中最适宜的方式。在一个以“家”为伦理根基和政治根基的社会中,大多数传统女性只能选择忍耐的方式来面对家内危机,因为如果她们选择抛弃家庭,她们并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是,伴随着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这种家内情感的“转化”不仅有了情势的需要,更有了实现的条件。对于新女性来说,除了固守家庭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并且,这些可能性的获得仍是缘于离家:离家虽然加速了她们与父母关系的恶化,但是,离家同样打开了其他情感关系和依恋关系的通道,同学、老师、战友和志同道合者都成了新感情形成的基础。
在黄彰的逃离过程中,她的一群同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二十多位同学一起帮忙,用长梯翻墙出校,却被校方抓个正着。不得已,众人又在一个废旧的厕所坑处挖洞,使其得从一小门出校,并且,这些同学再一次凑了三十多元作路费。参见白薇:《跳关记》,出自《女作家自传选集》,桂林:耕耘出版社,1943年。,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黄彰仍对众同学帮助她逃离学校的经历激动不已,称他们为“一群战士”。最后,同学的母亲陈夫人帮她买了去日本的船票,这位夫人也是位新女性,和丈夫决裂后,“携带一群女儿,流离在外……靠在女学校帮忙”。黄彰对这位夫人非常感激和亲热,甚至将其和自己的母亲做了对比:“心灵上,比我母亲和我,有的地方更接近些。”[6](P86)正是这些离家过程中所遇到的新式关系潜藏着新的情感。对于这些新女性来说,在离家后的人生中,她们追求过爱情,参加过群体活动,有些加入了党派,有些则沉迷于物质与消费,经历似乎大不相同,但在这种种经历背后,无不潜藏着她们试图重建一种类似于家庭之自然情感的社会关系(包括恋人、群体、党派、物质化自我等)的努力,希望从中找到离家之后的最终归宿。
正是通过这些新式的共同体,个体找寻到了一种新的归属感。并且,也正是通过这些新共同体中的个体间情感,新女性试图缓解对父母之家的“怨慕”之情,将对家的依恋和恋慕转化到共同体内部。这是民国家制批判后新女性选择的社会变革之路,在她们投身到新的社会组织和群体时,她们希望通过“情感解放”的方式进入一种新的共同体情感中。当蒋玮和几个桃源女子师范同学一起从湖南到达上海后,他们在平民女校的生活是劳累而又紧张的,但是在情感上却是异常激动:她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钱放在一起用,实行“共产”,并且都废了姓,互相称名。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她们感受到互相间的平等和友爱,而这,是以往的家庭生活所没有的。
(三)情感解放的“限度”
但是,民国新女性所采取的这种“情感转化”方式,真能以新式共同体的情感完全代替家内情感吗?对于投身社会革命的新女性来说,共同体的情感或许能够暂时缓解她们因“怨慕”之情而产生的困扰,但是,她们因此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不需要家庭的“社会人”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新女性在社会团体和革命中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况。不过,在此,我们可以先对“情感解放”的限度做一辨析。
民国社会转型所开启的离家浪潮,将传统社会中隶属于家庭和家族的个体纳入了“社会”之中。对于离家女性来说,她们获得了一些新的社会身份,比如“国民”“革命者”和“职业人”等,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不过,这些新生活的获得是以家庭决裂为代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需要通过新共同体内的情感关系来弥补家庭关系破裂所带来的情感缺失。这一过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将依附于家庭的情感“解放”为可以自由地和其他共同体相结合的情感,从而使个体能在更多的共同体中实现情感的自足和独立,并最终实现个体的完全解放。但是,我们发现吊诡的是,在这一所谓的情感“解放”过程中,情感总是在不同的共同体中寻找归宿而不得:当新女性试图用新式共同体的情感来代替和缓解家内情感矛盾时,这虽然使个体从家庭中获得了某种解放,但是共同体仍会演变为类似家庭的束缚,而最终促使新女性摆脱这一共同体,寻找另一种她们认为更适合安顿内心情感的共同体。因而,民国新女性的情感经历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不断寻求情感解放的过程,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不断进入情感、摆脱情感、再进入情感的往复过程。
四、小结
在以往的妇女解放研究中,我们很少讨论个体解放的可能。“离家”这一事件无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窥见在个体解放过程中所遇到的观念和情感间的张力。由于家内情感的自然性、本能性,而且这种情感是家内成员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它对于新女性能否决然地走出家庭,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内情感不仅使一些观念上接受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女性仍旧难以毅然离家,更使得很多离家女性在走出家门后,生活在“怨慕”父母的情感困境之中。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妇女解放”并不只是一场观念推动行动的单维度运动,更包含着个体如何处理情感,以及如何重建现代性情感的问题。
传统中国的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她们所有的情感关系都是围绕着家庭展开的,家也成为她们最重要的依靠和依恋对象。对于这些民初的离家女性来说,当她们与父母断绝关系后,实际上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孤儿。理论上她们当然也可能以这种“孤独者”的身份生存,但实际上,面对“怨慕”背后父女、母女之间自然情感的无处寄托,以及女性个体对于依恋感、情感乃至安全感的心理需求,她们只能在时代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中寻求新的情感,去填补,或者只是缓解因自然情感无法现实化而产生的无意义感和虚无感。
民国之后“日日新”的社会变化,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感受到的是自我与社会变革的无限可能。当这些新女性投入社会革命和新式爱情时,她们往往会感受到比家庭情感更具有激情的情感,而这非常有可能促使她们将情感之重建奠基于此。而真正的问题可能是,这种重建的社会性感情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已经破裂的家庭情感?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新女性在新式社会空间中重建了一些新的情感关系,比如与同学、老师之间的情感,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友情,乃至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试图以此来填补家内情感缺失后的虚无。但是,这种“转化”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最终完成?或者说,这种重建的社会性情感是否能够完全代替自然性情感?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都关乎女性能否在情感上完成真正的“解放”,以及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怨慕”情感能否得到相应的缓解。
[1]尹旦萍.女性解放是什么——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含义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欧阳和霞.妇女解放进程中女性主体的理性自觉[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4).
[3]姚霏.近代中国女子剪发运动初探(1903-1927)——以“身体”为视角的分析[J].史林,2009,(2).
[4]易家钺,罗敦伟.中国家庭问题[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
[5]从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白薇.跳关记[A].女作家自传选集[C].桂林:耕耘出版社,1943.
[7]白薇.悲剧生涯[M].上海:生活书店,1936.
[8]白薇.我的生长与发落[J].文学月报,1932,(1).
[9]汪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的几个层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10]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11]香淑.李欣淑女士出走后所发生的影响[N].(长沙)大公报,1920-02-28.
[12]丁玲.丁玲全集(卷10)[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3]碧遥.悼四姊九思[J].女声,1948,(10).
[14]谢翔霄.我与谢冰莹[A].湖南文史资料选集(24辑)[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5]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6]孟子.孟子·万章上[A].四书章句集注[C].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4).
[18]孙帅.爱与团契——奥古斯丁思想世界中的伦理秩序[A].吴飞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角下[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19]黄得时注译.孝经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20]张祥龙.舜孝的艰难与时间性[A].吴飞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角下[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玉静
"Liberation of the Mind" or "Liberation of Emotions"?:Difficulties Women in Hunan Faced When They First "Left Ho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NG Su-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women's liberation;liberation of the mind;liberation of emotions;love and affection;changes in emo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individual cases with women in Hunan who first"left home"in pursuit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differences that this departure had created with respect to its effects between"liberation of the mind"and"liberation of emotions,"as well as how emotions had influenced the path of individual pursuit of liberation.On the one hand,emotional ties at home often prevented women who had acquired liberated minds to leave home in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ce.On the other hand,for those women who had left home by overcoming the restriction of such emotional ties on them,they would feel both resentful toward and a longing for their home.This undoubtedly had been an emotional dilemma for those women who pursued"liberation".In conclusion,the paper suggests possibilities for those women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by pursuing changes in emotions and recognizing limitations to"liberation of emotions."
D442.9文献标识:A
1004-2563(2016)01-0065-07
杭苏红(1988-),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女性学、历史社会学。
本文获得北京大学才斋奖学金资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