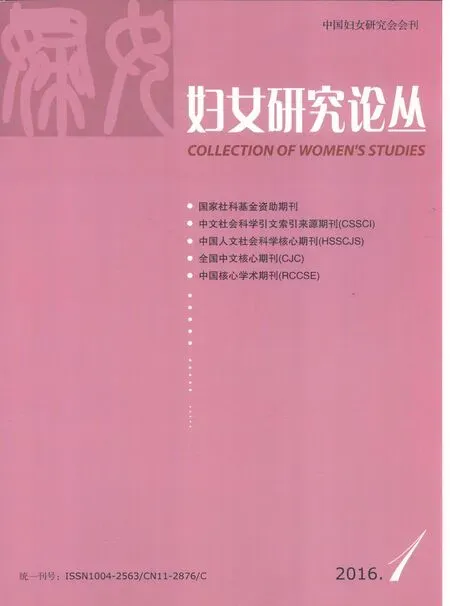视线向东:接纳东欧女性主义*
汪琦著 陈密译 闵冬潮校
(1.南丹麦大学设计与交流系 欧登塞 丹麦;2.3.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200444)
视线向东:接纳东欧女性主义*
汪琦1著陈密2译闵冬潮3校
(1.南丹麦大学设计与交流系 欧登塞 丹麦;2.3.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海200444)
女性主义;东欧女性主义;第二世界;社会性别;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女性主义
文章介绍了东欧女性主义并探讨在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东欧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文章首先对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特别是性别关系和性别话语的变化做一个概述;其次简要描述东欧如何与西方女性主义相遇,以及后者对该地区女性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再次,从四个方面勾画东欧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此阐明东欧女性主义的立场及其如何对西方女性主义霸权构成了强大的挑战;最后,简略探讨东欧女性主义如何能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超出当下的启发借鉴价值。
引言
本文将介绍东欧女性主义,并探讨在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东欧女性主义如何能成为一种新的启发性的资源。将视线转向东欧,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东欧女性主义在经过“一个失败主义和自我怀疑的时期”之后,以“多元化、多维度的在地性和全球性的政治对话场域”出现[1](P385),并以此构成对西方女性主义霸权的强大挑战。这意味着,在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后,一个新对手在全球视野的女性主义力量群中宣告了自身的到来,而这也将极大地改变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力量平衡的格局。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已沦为充满争议的政治标签,其内涵、立场、社会政治关联一直饱受质疑、挑战、裁切、重塑。时至今日,虽然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但多种不同的“女性主义”共存已被接受为常识。东欧女性主义的崛起,不但增强了在西方之外的地理政治地域上宣称女性主义性别知识的信心,而且更为全球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东欧女性主义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其为“跨国女性主义首先是作为‘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女性间的对话’抑或西方与非西方的对话框架”带来了第三种范畴。东欧女性主义开启了第三条路径,同时也要求“第二世界作为全球斗争场所”获得承认[1](P387)。作为第二世界,东欧身处各种后社会主义政治环境之中,东欧女性主义的到来也将引发我们对其他一些社会范畴(如“历史时期”[2](P815))之间的相关性的注意,而不仅仅是以现存的那些地理学方式的、地理政治方式的、种族方式的女性主义分类(例如白人和黑人)来进行全球女性主义的思考分析。在此意义上,“历史时期”作为一个范畴,更能使我们反思导致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变的各种深层的历史条件/环境,并反思这些条件/环境如何塑造了东欧国家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3](P729)。
再次,关注东欧女性主义的意义还在于,中国女性和东欧女性在其面对的众多危机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除了地理上的距离,中国与东欧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特征也极为相似: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并经历着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此阶段,无论中国还是东欧,性别关系的巨大转变都已成显著之势,伴随着规范的性别概念的重组,以及对转型经济中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这种转变已为社会所感知。更为相似的是,中国和东欧都对西方开放并随之“进口”了西方女性主义,例如“社会性别”概念、非政府组织活动、妇女/性别研究以及各色女性主义研究框架等。当今,东欧女性主义已经明确表达了其对西方女性主义普遍适用性日益增长的怀疑,而这正呼应了中国女性主义对当下国内女性主义论争的相似的担忧。基于这些原因,深入了解东欧女性主义,看看从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宝贵的借鉴与启示,或许将是件不乏意义的工作。
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些语词的用法。总体而言,“东欧”一词指的是欧洲的次级区域,包括俄罗斯、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克罗地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等国家①见http://www.ask.com/geography/countries-make-up-eastern-europe-f220b8cc461d2e4d。。有时用CEE(中东欧)一词常用来指称更为次级的区域,它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摩尔多瓦等国组成②见http://www.weastra.com/cee-countries/。。标题中的东欧女性主义指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有的国家多,有的国家少)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流派。除“东欧女性主义”一词之外,另有两个不同的词汇也常可互换的用来指称,即“第二世界”和“后国家社会主义”[1]。换句话说,东欧女性主义也可称为(理解为)“第二世界女性主义”和/或“后国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一的差异在于,第三个词更强调该地区女性主义的历史条件,而前二者则更多地传达出一种显著的地域和地理层面上的内涵。
虽然很难给东欧女性主义指定一个确切的诞生日期,但研究者普遍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为东欧女性主义的成长准备了土壤。然而,要描述东欧女性主义代表的是什么,却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不但材料的选择/收集是个巨大的挑战,还要面临可能误读的风险。因此,在方法和目标这两点上,本文都将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为东欧女性主义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尽可能地保持客观。这些资料包括作者近来阅读所及的书籍章节和学术文章。毫无疑问,与这个主题上的大量知识相比,本文选择的范围远非无所不包,并且也很难说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本文毋宁采用的是一种“马赛克”方法,拾取各处的方块,拼接出图案。也正因此,本文对东欧女性主义的描述并非终极真理而只是管中窥豹。本文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对第二世界女性主义的内涵提供一个全景描述,而只想勾画出东欧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议题,希望这些能对跨国女性主义讨论和反思提供一些原料。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东欧的后社会主义转型轨迹,特别是性别关系和性别话语的改变,并略述东欧几个主要国家的变化与差异;第二部分简述东欧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的相遇以及后者对该地区女性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概述东欧女性主义的主要立场以及其如何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假设;最后的结尾部分略微探讨在中国国内的妇女、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的论争中,东欧女性主义对我们能有哪些方面的启发性。
一、社会性别在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后社会主义语境
东欧女性主义源于东欧地区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同时是对它的一种批判性反应。毋庸置疑,“东欧”包含了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差异显著的众多国家。不仅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验不同,而且各自的成功程度也不一样。以经济为例,所有东欧国家“相较西方国家,拥有更高水平的公有制和经济控制力”,但只有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可与已知的经合组织国家相比的市场经济”[4](P286)。有研究认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似乎是现有的进行战略协作国家的例子,而俄罗斯、爱沙尼亚和亚美尼亚则是以自由经济面貌出现的典范”[4](P286)。政治上,像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是第一波加入欧盟的部分后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以稳定的民主国家姿态积极参与欧盟,这一点将其与其他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区隔开来”[5](P866)。
东欧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无论在其转向社会主义或者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社会性别都处于中心地位。用佩吉·沃森(Peggy Watson)的话说,“性别关系与变革的过程有着本质的关联”,“事实上,性别问题呈现在这一系列变革的每一个细胞组织中”[6](P471)。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a Verdery)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调和身体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建构,同时也是“使身体具有社会性的一套符号系统”[7](P92)。她随后借用康奈尔(R.W.Connell)的“性别体制”概念来描述社会性别在东欧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变革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性别体制“由劳动的性别分工、权力的性别结构以及情感投注的结构组成”[7](P92)。将这一术语用在东欧,那么曾在这里出现过的,实际上就成了对性别关系和性别角色,亦即性别体制的运作和改造的重新配置。在社会主义时期,很多东欧国家都建成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不但下定决心要通过打击、转变传统性别结构和角色来变革社会,而且也“对性别平等青睐有加”[7](P92),它们通过推进政策来“促进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7](P92),同时还做出了各个层面上的政治决策。在东欧的语境中,社会主义的性别体制包含如下特征:妇女作为全职的劳动力、家庭结构和“男女的家庭角色”有一定程度的改变[7](P92)以及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的参与或领导。
在向民主和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都抛弃了早先宣告的性别平等,倒退至各自的前社会主义时代的性别秩序。无论这些国家内部环境变迁如何不同,有“持续和明显的经验迹象”表明整个东欧都在性别平等方面有所倒退[6](P471)。之前的社会主义性别体制被颠覆,这直接导致了妇女政治代表性的降低、妇女失业率上升以及向传统价值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回归。用维德里的话说就是,妇女的“再传统化”(retraditionalization)[7](P100)。对女性而言,这些负面结果既是因下述的变化趋势而起,同时又是这些变化趋势的一个结果。在东欧,尽管不同的国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变化趋势已广为人知。
首先的一个变化趋势是维德里所谓的“去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大转变旨在推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或对它的歌颂。这种政治把女性“他者化”,并“将‘他者化’的女性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7](P100)。由于女性在社会主义时代所获得的权利和社会解放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倡导下进行的,当今的去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就自然而然地把妇女和妇女解放与共产党绑在了一起。而正是因为“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切既已声名扫地……,妇女解放自然也无法幸免于难”[8](P132)。
第二个变化趋势是“在公共与私人之间重新划上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1](P389)[6]。在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家/家庭重新又变得至关重要[6](P481),妇女日益“被等同于家庭”[6](P478)。在此过程中,教会,特别是波兰天主教会,扮演了一个渗透性的角色,他们在不断强化的“要点是,女人的合适位置是待在家里,而不是成为劳动力”[8](P132)。这一点教会是通过“废除流产权、重新引入民族主义符号……以及散播关于妇女正确性行为和个人品行的限制性观念”[8](P132)来实现的。对沃森来说,“传统规定的性别身份”的恢复,“是怀念‘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人们对东欧巨变的期待中常常有明显的表露”[6](PP472-473)。
与第二个方面紧密相联系的第三个趋势是性别本质主义的抬头。一方面,东欧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崛起“在本质上要求建构一个‘男人的世界’,并且在公共领域中拓展男性主义”[6](P472)。于是,女性就在政党政治中被消除了,而且许多东欧的国家议会“更是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男人的天下”[6](P473)。另一方面,通俗的本质主义读物也在宣传性别之间的“自然差异”,把操持家务说成是唯一适合女性本质功能的角色。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因鼓励女性积极进入社会而备受指责,因为这导致她们丧失了本质和女人味。比如在匈牙利,大众读物强力渲染男人对女人男性化的错愕不安。它们讥讽社会主义是“母系社会”,并渴望恢复父权,让女人依赖她们的丈夫[7](P100)。有如沃森所正确指出的,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发展打上了“女人被驯化、出卖以及女性身份污名化”的印记[6](P472)。
第四个变化趋势是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政治保守主义的激增[9][10][11]。维德里认为,后社会主义东欧最显而易见的,是“不断增长的明显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反对女权和鼓励生育”[7](P100)。流产问题或许最能说明为什么东欧的民族主义同时要反女权,因为流产关系到民族复兴,“民族有如胎儿,若被判处死刑,就无法复兴”。换句话说,如果女人拒绝孕育“胎儿公民”,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无法恢复往日的活力和兴旺。如维德里所指出,一个民族国家要从社会主义的过去得到复苏,“就需要一个新的父权制,它通过一个全新的、为国家观念服务的民主政治来加以建立”[7](P101)。女性主义包含了自由流产的理念和实践,自然就被视作民族的反叛和新兴民族国家的敌人。
总之,这四个变化趋势构成了一场“保守主义革命”,它横扫东欧,在根本上改变了后社会主义东欧社会的性别关系。虽然男人和女人都在这场经济和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新的权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分配“是以严格的性别化的方式发生的,并在根本上是由男性特权所决定的”[6](P473)。民族和男人尊严的恢复,其“代价不仅是女性自愿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新的政治领域之外,而且在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份的污名化”[6](P485)。如沃森所说,这一点生动地向我们提示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前的一个说法,那就是“现代性……制造差异、排斥和边缘化”[12](P6)[6](P485)。
二、西方女性主义的到来:设计出的女性主义与文化女性主义
在柏林墙倒塌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毁之后,东欧进入了转型阶段,开始向西方开放。西方的影响在后社会主义东欧无所不在,这被戴维斯·斯塔克(Davis Stark)形象地称为“设计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by-design)[13]。“设计的资本主义”一词描述的正是迅速涌入的“渗入前东方阵营”的西方资本和顾问援助[3](P729)。正如克里斯汀·高德塞(Kristen Ghodsee)所形容的,一支支酷似军队的顾问专家队伍进入资本城市,从零开始建造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地基。他们“建议当地政府如何创建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相信,一个国家一旦建立了合适的制度,“在这些新制度的治理下,个体行为就会得到规范”,如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能够经由设计得以创造出来[3](P729)。
在西方“设计”东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西方女性主义也大举进入前东方阵营。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妇女组织也赶上转型早期的这波援助大潮,开始给东欧的受助者输送援助资金、女性知识/理论和组织模式③关于东欧制度化和性别主流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参见Zimmermann,Susa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高德塞称之为“设计的女性主义”(feminism-by-design)[3]。这样一来,“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概念,便被引介进来,而“性别话语也作为所谓的‘民主转型’(或‘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在过去二十年里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出现,这一点被理解为是融入欧盟的一个重要的要求”[14](P1)。与此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Asymmetric Politics and the Regional-transnational Configuration[A].In Symposium of Gender,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 Gender Symposium[M].Budapest,Hungary: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2007.同时,“每个国家都受到鼓励去建设某种‘国家机制’来处理妇女议题”[3](P731),而且其他“西方女性主义机构——妇女支持团体、社会性别专家小组、受虐妇女庇护所、强暴危机热线、妇女资源中心等等——在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出来”[3](P731)。很多这些非政府组织(NGO)“或是由大型多边、双边捐助者直接资助,或是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欧盟的波兰和匈牙利分包下的西方妇女组织的支持”[3](P731)。很多学者已开始用“NGO化”一词来形容东方阵营中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快速发展[5]。
总之,后社会主义东欧女性所接触到的并仍然努力试图消化的西方女性主义,在形式上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它有一个社会性别上的理论躯壳(转型期东欧的大量女性知识都是在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下进行的)和极为众多的妇女组织和NGO,这些组织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又被认为是发展民主和解决妇女所面临问题的必要条件。尽管在东欧转型的早期阶段,女性主义的理论化和组织化都因西方女性主义的帮助而有所提升,但嗣后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仍然遭到有增无减的质疑、批判和抵制。例如,社会性别概念的批评者就提出“文化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以此解码深藏在“社会性别”中的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文化女性主义指的是,“一些特定的话语和实践,其目的是推广男女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的理念”……“这些两性之间的差异超越了阶级、种族、年龄和族群,可以把所有妇女团结成姐妹”。……文化女性主义“想要寻找缓和父权制罪行的办法,而从不去追问父权制赖以生长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高德塞进一步指出,文化女性主义“作为应对妇女问题的一种方式”,“与西方大型多边、双边援助机构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一拍即合”[3](P728)。对“社会性别”的这种批判性反思既是东欧女性主义走出西方女性主义笼罩的必要步骤,也是其有能力走出这一步的生动体现。
三、东欧女性主义
东欧女性主义——也可称为第二世界女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的霸权及其假想中的普遍适用性。它们宣告了自身在女性主义知识生产中所应有的地理政治的、历史的位置;它们坚持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塑造女性生活以及与女性理解/反思自身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呼吁谨慎对待社会主义传统,以便能够重新挖掘和重估国家女性主义的遗产,从而发挥今日女性和女性主义政治的优势。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叙述东欧女性主义的主要原则。
首先,东欧女性主义拒绝西方女性主义的霸权,这种拒绝的精神动力主要源自后殖民主义理论[15][16]。例如,在中东欧女性主义学者当中,有着对“全球学术政治经济中……权力关系……以及这些权力关系如何在妇女和性别研究学科中运作”的一致性关切[2](P809)。他们“高度关注不平等关系中的如下一些特征:理论模型建立在西方现实之上;英语是学术研究和会议中的支配语言;与西方学者相比,中东欧学者的研究资金更少;在西方,更多的机构资助意味着中东欧学者占据的是客席地位,即使会议是在中东欧地区举办”[2](P810)。此外,“最有声望的刊物只以英文出版,且更为偏好遵循英美论证传统及引用西方学术的研究”[2](P810)④这一点的更多相关内容,参见Busheikin,Laura.Is Sisterhood Really Global?Western Feminismin Eastern Europe[A].in Tanya Renne ed..Ana's Land:Sisterhood in Eastern Europe[M].Boulder:Westview,1997.。由于这些状况的持续存在,中东欧女性主义学者感觉到自己“被殖民”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被降格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搬运工”的位置,而不是新知识的独立行为主体[2](P810)⑤关于这点,参见Blagojević,Marina.Creators,Transmitters and Users:Women's Scientific Excellence at the Semi-Periphery Europe,in European Commission Gender and Excellence in the Making[M].Brussels:European Commiss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2004.。
东欧女性主义同样批评假想中的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的二元对立,提倡以替代方式思考跨国女性主义。就中东欧女性主义学者而言,最僵化的地理政治分歧,如西方/东方、北方/南方引发了跨国女性主义对话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是“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被当作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2](P810),这使得根植于西方某些特殊历史文化情境的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概念被升高到了具有普适性“真理”的地位。如此一来,后社会主义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性别问题理论化的工作就不幸地是“在固有的北美和西欧女性主义遗产的笼罩之中”进行的[2](P811),而且,“当中东欧社会的社会现实偏离已有的理论时,西方学者往往将这些社会视作欠发达的,而不是去质疑理论的适用性”[2](P812)。此外,“绝大多数论及性别与经济转型的西方学者都倾向于对新兴的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妇女地位前景抱以灰暗的想象”[3](P730),并且,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东欧女性是第二等级的公民,是保守的”[17](P243)[2](P812)。在经常是偏颇和带有误导性的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当中,中东欧女性常常被呈现为缺乏启蒙和进取性的“他者”,而作为真正的争取自身权益的当地的女权运动,其丰富细节和活力也往往不被注意或被忽视。
在反抗西方女性主义霸权的同时,中东欧女性主义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后殖民视角的中心点”也感到不安,因为“第二世界在反帝国主义话语中仍然大量缺席”[1](P400)。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第一次为许多中东欧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进入全球女性主义论坛的机会。然而,通过参与,他们却得到了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他们发现:“南方—北方的范式早已确定”,而要进入那个空间是极其困难的[1](P400)。虽然联合国大会“成了一个发展跨国对话的平台,既讨论地方政治的复杂意义,也将美国围绕性别和种族的交集所进行的辩论与代表全球南方的妇女斗争联结在一块,它也创造了一种以‘第三世界妇女’代替‘有色妇女’的模式”[1](PP401-402),而这一模式却不包括东欧妇女。正如马格达莱纳·格拉波斯卡(Magdalena Grabowska)所指出的,东欧女性主义者在世界妇女大会中所体验到的困难,在于其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中,“无法或拒绝去构想其地域认同”[1](P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合国妇女文件中,中东欧女性主义者被划到了是来自“无地区”妇女的范畴,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在第三世界的妇女斗争中去给自己定位”[1](P9)。
第二,东欧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及其普适性提出异议。1989年以来,社会性别及以其为基础的妇女研究,从西方“进口”到后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社会性别概念被广为接受,并作为新的方法用于分析转型之下的妇女问题,而且许多中东欧国家也将妇女研究体制化了。但近年来对社会性别及其方法的批评不断增多,这标志着东欧女性主义者正在大胆抛开引入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寻找他们自己的身份。已有研究指出,许多中东欧国家女性实际上并不拒绝用社会性别及性别分析方法。很多人“将文化女性主义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然出现看作是一种舶来的、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3](P733)。许多中东欧女性觉得用社会性别,即与男性相反的性别,来看待自身显得有些怪异,因为她们为了发展,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与男人并肩作战。因此,“不认可她们(转型中)的情况与男人有何不同”,故而“拒绝将她们的问题与男人的问题割裂开来”[3](P736,7P35)。此外,很多人相信,从1989年以前至今,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是“资本主义延续其剥削的过程的共谋者”[3](P736,P735)。
东欧女性主义有诸多理由质疑社会性别与西方女性主义的普适性。其中之一是,中东欧女性的生活经验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dan)所说的作为家庭主妇的“空虚和非在”大相径庭。如柯内莉亚·斯拉沃娃(Kornellia Slavova)所指出,1989年之前的中东欧女性“置身于一个宣告妇女已被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渴望出来工作”。工作并非如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所呼吁的,是一个需要去争取的权利。因此,由于西方和中东欧的政治文化差异,对贝蒂·弗里丹和西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对中东欧女性来说却无关紧要[18](P248)[2](P814)。
此外,东欧女性主义还尤其指责盲目采用“社会性别”和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行为。让其感到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概念未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考察”就被接受了,而且社会性别“成了一个标志着认识时间差的空洞符号”[19](P480)[14](P10)。有人甚至批评“社会性别”和西方女性主义不但“无法充分解释社会现象”,而且可能“联手制造原先不曾有过的社会分裂”[2](P813)。例如沃森就认为,“仅仅将焦点放在后共产主义的社会性别观念上,把男人置于一端,女人置于另一端,是为转型背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撑,而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男性主义的产物”[20](P46)。对苏珊·齐默尔曼(Susan Zimmermann)来说,虽然“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的体制化可看作是一个发展批判性的女性主义思考的机会”,然而它的作用只是在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再添上作为单一性别平等的性别话语,却没有任何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政治批判”[21]。
在东欧女性主义看来,“社会性别”概念的主要问题在于:(1)性别叙事常常把中东欧国家的女性当作“一个同质性的群体,拥有相同的国家女性主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转型经验”[1](P386),但实际上却是相反,女性和性别关系中存在着显著的国家和次级区域的变化和差异[5](P868)。因此,东欧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东欧的环境中,“政治团结不能以共同的‘女性气质’为基础和前提”[22](P106)[3](P735),他们也表示,必须跳出西方女性主义框架,重建本土的女性主义谱系,比如波兰的女性主义[1](P392)。(2)“社会性别”和西方女性主义忽略了用“其他一些像阶级这样的重要的社会范畴去分析东欧社会,由此把这些社会中限制民主的真正社会因素神秘化了”[2](P813)。社会性别概念作为本质性的差异范畴,与下述事实相矛盾,即“对妇女来说,她们在1989年之前的社会阶级地位,相对于仅仅是单一的社会性别而言,是关系到她们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是否成功的一个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3](P736),另外,社会性别概念也“没能认识到后社会主义情境的复杂性,以及理解社会中新出现的阶级差异的重要性,这些仍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公正理想有着紧密的联系”[3](P748)。马尔加·米兰(Márgara Millán)于是建议东欧女性主义应该在不同的语境中反思“社会性别”的意义以及社会性别的“可翻译性”[14](P13)。
第三,东欧女性主义反对那种将国家社会主义或是看成理所当然的,或是当作在发展西方式自由身份过程中的一个不利因素的观点[1](P396)。他们主张彻底重估国家社会主义遗产,并且坚称,国家女性主义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理解,因此应予以更为慎重的考察。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性别革命是不完全的……,比如对平等的制度承诺极为有限,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法规也流于表面等等[1](P397),但东欧女性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对女性主义影响依然要复杂得多”[1](P397)。比如有的人认为,“在个人层面上,国家女性主义时代对妇女生活有着极其复杂的影响,它提供了自我教育的机会,并且推动了各种妇女活动团体的建立”[1](P398)。其他人则认为,妇女“不仅仅是受害者,她们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平等政策的创造者和执行者”。以工人阶级妇女为例,她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性的自主权”和“去规划她们自己的兴趣和想法的机会”[1](P398)。
在波兰,很多女性主义者开始抛弃自由主义。他们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源于西方社会具体的地理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地域的特征,这就与波兰妇女的生活经验没什么关系”[1](P396,P392)。他们转而重新评价和理解来自社会主义的、本土的女性主义的遗产,强调要去“重建波兰女性主义的本土谱系”[1](P392)。例如,在重新评价团结工会的作用时,波兰女性主义者指出,“在他们的经验中,团结工会在联结女性主义与政治的过程中,起到了虽然不总是很明显但很关键的作用”[1](P393)。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假设,即认为“西方是东欧女性主义唯一的逻辑参照点”[1](P392),因为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本土遗产对波兰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1](P392)。有如波兰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女性主义不应该是从西方、美国进口的物品,“这里就一直存在着我们自己的东西——妇女解放思想的传统”[1](P392)。“在本土的不平等叙事中让女性主义重新扎根的想法”[1](P393)激发了中东欧女性主义者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宣告了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自己的女性主义版本以及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不是以“差异和地域分离”为前提,而是“通过‘共同呈现’、相互作用、相互交叉的理解和实践……”来实现[23](P7)[1](P825)。
第四,东欧女性主义以批判的眼光检视非政府组织女性主义(NGO女性主义)以及非政府组织化的后果。在向民主和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东欧国家“在更为本土的层面上产生出女性主义团体”[5](P868)。据估计,“波兰和东德有二百个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匈牙利和捷克也有近一百个这样的团体”[24][25]。该地区的大多数妇女NGO“都双管齐下,既提供服务,又从事宣传工作”,但是也一直有“相对小一些的指导组织工作,来促进妇女参与正式的政治,还有更少的一部分是争取在正式政治中把女性主义妇女或女性主义目标吸纳进去”[5](P870,P871)。卡佳·甘瑟(Katja Guenther)说,中东欧国家的女性主义动员“核心在于建立女性主义团体”,这个女性主义团体“与两种不同的资源有关”。一种“是当地创建的团体,由相关女性创办,她们团结在一块,围绕一个影响她们或共同体的问题去进行动员”,一种“是外部创建的组织,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发展起来,其工作日程由可能不属于当地任何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决策者制定”[5](P871)。
东欧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矛头是针对经常为本土NGO提供基金的INGO的。甘瑟说,INGO基金“对本土NGO来说是好坏参半”。虽然外来基金无疑地在财政上对本土NGO有所助益,但许多本土NGO的组织者“有时觉得被推到某个特定的方向上,以此来满足捐助者的要求”[5](P872)。一些INGO强行推行“他们对东、中欧女性的议事日程和想法,而少有顾及当地本土的事物和问题”[5](P872)[26]。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Mac Mahon)的批评指向INGO的基金模式。他们通常提供短期的项目基金,在麦克马洪看来,这在“很多方面都有问题”。首先,这种基金模式“对女性主义组织及其雇员造成了一种财源上的不安全感”。这就会“增加工作场所的压力,有时还会加剧女性主义组织之间以及雇员之间的竞争,使组织和个人的工作变成争取持续资助的手段”[26]。第二,“项目基金不可避免地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有局限”。这使得受助项目“通常只关注有利于一小部分受益者的短期结果”,因而不可能“致力于大型社会问题或促进长期的社会变革”。
很多中东欧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用“NGO化”一词来描述该地区NGO的急剧增加。他们也用“NGO女性主义”一词来描绘部分女性主义团体,它们得到INGO的基金,通常都“聚焦于一小部分面对妇女的问题,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实用性解答”[5](P874)[27]。他们于是质疑这些效果以及NGO女性主义的至上地位,认为“当他们如此明确地依赖于这些本身亟须被改造的结构时,还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功?”[27](P113)[5](P874)对甘瑟来说,有太多的理由来怀疑NGO女性主义。(1)NGO女性主义“通过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层化使女性主义变得中立,失去了棱角”;(2)NGO化“阻碍那些反抗统治性的性别关系的女性主义亚文化的成长和维持”;(3)NGO化“压制女性主义者表达和发声的能力”;(4)NGO女性主义“并未去质疑现存的公民社会、国家、经济的结构,而正是这些结构使性别及各种不平等永久化了”[5](P874)。
亚历山德拉·赫里凯克(Alexandra Hrycak)在研究乌克兰的NGO时,特别批判性地审视了那些她称之为“基金会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作用,以及她们如何以中间协商者的身份调和“国外援助和本土组织之间的碰撞”[28]。赫里凯克认为,“基金会女性主义者”通常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地女性,具备流利的英语表达能力。外国捐助者认为她们是妇女赋权方面的专家,她们被聘为美国项目的工作人员或者顾问,去促进基层的妇女运动[28](P84,P72)。她们中的很多人经过美国基金会的培训,成为性别专家,为乌克兰基层妇女组织提供最基本的、规范的维护和帮助[28](P84)。这些基金会女性主义者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的经验、教育和社会地位使她们能够娴熟地掌握并运用”外国捐助者对“乌克兰妇女的问题”的分析,但她们当中却鲜有人“与非正规的、基层社区女性联合会有过任何合作关系”[28](P84)。她们“对妇女的观点与其西方同行一样”,就是说,她们接受了外国捐助者的看法,认为“当地传统是女性困境的根源”,对于转型期妇女的选择,“传统是一种障碍”[28](P85)。因此,基金会女性主义者“常常对那些鼓舞既有的本土妇女运动的原因和事情缺乏同情与了解”,她们也“对本土的母性主义者不感兴趣”[28](P86)。相反,她们往往将乌克兰的母权主义者的优势看作是这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落后状况”的证据[28](P86)。她们“通常对那些激励本土妇女运动的原因和不满持敌视态度”,而且她们更愿意与那些“同样认可传统是压迫性的,是后苏联时代女性困境的根源”的人共事[28](P86,P85)。
同时,赫里凯克也明确指出外国基金会推动下的NGO化的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妇女组织中基金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大多数本土NGO没有基金”,而由基金会女性主义者管理的精英NGO却“吸引了相当多的拨款”,因而也就有能力“支付给工作人员相当可观的工资”[28](P88)。并且因为精英NGO和精英基金会女性主义者“成功地争取到更多的基金”,他们实际上“从当地公民团体抽走了很多资源及业务骨干,这些公民团体在‘来自底层’的公众生活中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8](P86)。另一个问题是“外国援助助长了‘混合型’组织的形成”[28](PP97-98)。由于那些面向外国精英和基金会工作者所使用的语言的组织[28](P98)更受欢迎,许多妇女组织为了迎合捐助者的要求,便采用了各种组织和沟通策略,结果是把其组织办得不伦不类,既不是严格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是严格的非盈利性的组织。有些“本土混合型组织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延伸”,而“另一些则是只在文件中存在的本土女性主义组织”[28](P98)。总之,“外国基金的做法促进了混合型组织的发展,这与公民项目设计者计划在后苏联国家发展公民社会组织的初衷相去甚远”[28](P98)。
讨论:中国与东欧
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东欧那样经历一场彻底的保守主义“革命”。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权力,一个是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不受教会的影响。然而,说到社会性别和性别关系,中国与东欧就有很多的共同点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妇女的一系列后果,并且,像东欧的去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一样,中国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以往社会主义时期妇女政策的嘲弄,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性别秩序和性别关系的重塑。在中国,遭到拒绝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此期间取得的妇女解放上的显著进步。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有一股力量在呼吁女性去重新发现她们的本质,要求女性从社会公共角色中退出,回到家庭和厨房,做个全职主妇。
在现阶段,中国与东欧更为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女性主义在理论和组织上的发展轨迹。和东欧一样,西方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女性主义思考和女权运动施加了极大影响。在中国前所未闻的“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中国后便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妇女研究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体制化;“文化女性主义”蓬勃兴起;外国捐助者/INGO在中国的NGO和女性主义团体中随处可见。在这惊人的情境相似性中,也许是到了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方,寻找新的灵感资源的时候了。我们也许应该去批判性地检讨西方女性主义与我们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追问这么多年以来,除了照搬应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外,我们在女性主义理论建设上究竟有何建树?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认真思考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及其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本土资源的潜力;或者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拥抱东欧女性主义并与其联起手来,共同反对西方女性主义的霸权?有如杨杰(Jie,Yang)所说,“中国女性主义者也许会发现,向其他社会主义同行学习是会有益于我们的”[29](P345)。
[1]Grabowska,Magdalena.Bringingthe Second World In:Conservative Revolution(s),Socialist Legacies,and Transnational Silences in the Trajectories of Polish Feminism[J].Signs,2012,37(2).
[2]Cerwonka,Allaine.Travelling Feminist Thought:Difference and Transcultu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J].Signs,2008,33(4).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528852,accessed 03-06-2015.
[3]Ghodsee,Kristen.Feminism-by-Design:Emerging Capitalism,Cultural Feminism,and Women'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Postsocialist Eastern Europe[J].Signs,2004,29(3).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380631,accessed 03-06-2015.
[4]Drahokoupil,Jan..After Transition:Varieties of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2008,7(2).
[5]Guenther,Katja M..The Possibilities and Pitfalls of NGO Feminism:Insights from Postsocialist Eastern Europe[J].Signs,2011,36(4).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658504,accessed 03-06-2015.
[6]Watson,Peggy.Eastern Europe's Silent Revolution:Gender[J].Sociology,1993,27(3).DOI:10.1177/0038038593027003008,downloaded 01-05-2014.
[7]Verdery,Katherina.From Parent-State to Family Patriarchs:Gender and Nation in Contemporary Eastern Europe[A].in Verdery,Katherina.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8]Lippe,Tanjia van der and Fodor,Eva.Changes in Gender Inequality in Six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J].Acta Sociologica,1998,41 (131).Dol: 10.1177/000 169939804 100203.
[9]Selecl,Renata.Nationalism,Anti-Semitism,and Anti-Feminismin Eastern Europe[J].New German Critique,1993,1(1).http://www.jstor.org/stable/488441,accessed 03-06-2015.
[10]Bracewell,Wendy.Women,Motherhood,and Contemporary Serbian Nationalism[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96,19 (1-2).doi:10.1016/0277-5395(95)00061-5.
[11]Roman,Denise.Gendering Eastern Europe: Pre-Feminism,Prejudice,and East-West Dialogues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1,24(1).
[12]Giddens,Anthony.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
[13]Stark,David.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Central Europe[J].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1994,6(6).
[14]Millán,Márgara.The Travelling of "Gender" and Its Accompanying Baggage: Thoughts on the Translation of Feminism(s),the Globalization of Discourses,and Representational Divides[J].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DOI: 10.1177/1350506814565632,2015.
[15]Said,E..Orientalism[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9.
[16]Mohanty,Chandra Talpade.“Under Western Eyes”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J].Signs,2003,28 (2).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342914 Accessed: 30/06/2015 05:21.
[17]Havelkova,Hana.Abstract Citizenship? Women and Power in the Czech Republic[J].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1996,3(2-3).
[18]Slavova,Kornellia.Looking at Western Feminisms through the Double Lens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Third World[A].in Jasmina Liikc,Joanna Regulska and Darja Zavirsek ed..Women and Citizenship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Aldershot: Ashgate,2006.
[19]Kašic,Biljana.Feminist Cross-Mainstreaming within "East-West" Mapping: A Postsocialist Perspective[J].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04,11(4).
[20]Watson,Peggy.Gend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m[A].in Gabriele Jähnert,Jana Gohrisch,Daphne Hahn,Hildegard Maria Nickel,Iris Peinl,and Katrine Schäfgen ed..Gender in Transi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Proceedings[M].Berlin: Trafo Verlag,2001.
[21]Zimmermann,Susan.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symmetric Politics and the Regional-Transnational Configuration[A].In: Symposium of Gender,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Gender Symposium[M].Budapest,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2007.
[22]Gal,Susan and Kilgman,Gail.The Politics of Gender after Socialism: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Essay[M].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3]Pratt,Mary Louise.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London: Routledge,1992.
[24]Šiklová,Jirina.Feminismand the Roots of Apathy in the Czech Republic[J].Social Research,1997,64(2).
[25]Fuszara,Malgorzata.Feminism,the New Millennium,and Ourselves: A Polish View[J].Signs,2000,25(4).
[26]Mac Mahon,Patrice C..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Women's NGOS in Poland and Hungary[A].in Sarah E.Mendelson and John K.Glenn ed..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A Critical Look at Building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and Eurasia[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27]Lang S..The NGOization of Feminism[A].In Scott J.W.,Kaplan C.and Keates D.(eds).Transitions,Environments,Translations: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M].New York: Routledge,1997.
[28]Hrycak,Alexandra.Foundation Feminismand the Articulation of Hybrid Feminisms in Post-Socialist Ukraine[J].Easter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2006,20(1).DOI: 10.1177/0888325405284249.
[29]Yang Jie.Nennu and Shunu: Gender,Body Politics,and the Beauty Economy in China[J].Signs,2011,36(2).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655913,accessed 31/07/2015.
责任编辑:含章
Looking Eastward: Accepting 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
WANG Qi1Trans.CHEN Mi2Proof.MIN Dong-chao3
(1.Department of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Odense,Denmark;2.3.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feminism;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the Second World;gender;post-state-socialism;cultural feminism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s and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or them to become a new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feminist theorizing and organizing in China.It begins with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particularly the changes in gender relations and gender discourses.While it reviews briefly how Eastern Europe encountered Western feminism and what influences that the West has had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in the region,the article also outlines the tenets of 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s in four aspects and illustrates what they stand for and how they constitute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feminism.Finally,the article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Eastern European feminisms can become more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than it is perceived now.
C913.68文献标识:A
1004-2563(2016)01-0097-09
1.汪琦(1956-),女,南丹麦大学设计与交流系中国与中国文化研究副教授。研究方向:性别与政治、女性主义政治。2.陈密(1979-),男,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别文化研究。3.闵冬潮(1953-),女,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方向:理论旅行与文化翻译、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等。
本文的发表及翻译得到欧盟第七框架项目玛丽·居里国际学者奖金的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a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 within the Seventh European Community Frame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roject title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The Travels of Gender Theoryand Practice to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编号:91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