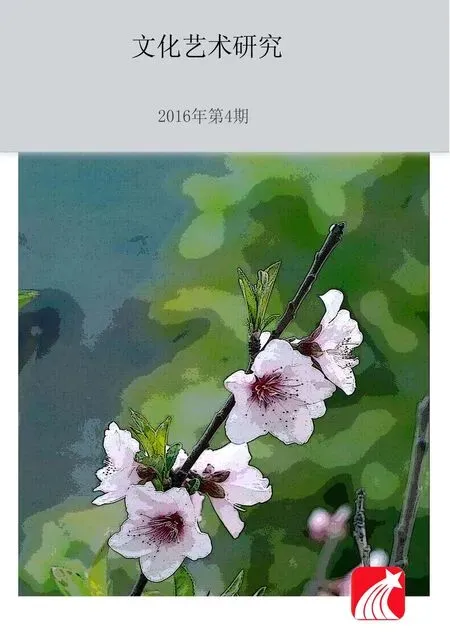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无”的呈现:《哈姆莱特》与认知科学①
[美] Amy Cook文 余雅萍编译 何辉斌 校
(1.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戏剧艺术系;2、3.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无”的呈现:《哈姆莱特》与认知科学①
[美] Amy Cook1文 余雅萍2编译 何辉斌3校
(1.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戏剧艺术系;2、3.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本文由《哈姆莱特》文本中的“无”,引出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混合理论。吉尔斯·福柯尼耶和马克·特纳的概念混合理论,补充并解决了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提出了在心理空间对各种信息进行混合,解构了“无”的传统概念,再现了从“物”到“无”的思维认知过程,对自愿终止怀疑这一传统的戏剧理论发起了挑战,消除了戏剧中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当“无”站上舞台时,“有”和“无”的界线从此变得模糊。
《哈姆莱特》; 无;认知科学;概念混合理论
哈姆莱特:你有无认为我在转着下流的念头?
奥菲利娅:无!殿下。
哈姆莱特:睡在姑娘大腿的中间,想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奥菲利娅:你说什么,殿下?
哈姆莱特:无!
(《哈姆莱特》3.2.115-119)*译文参考《莎士比亚悲剧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原文涉及的《哈姆莱特》文本均出自Shakespeare, William. Hamlet. Ed. Harold Jenkins.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1982。
在《哈姆莱特》中,没有什么比“无”更震撼人心的了。开场守夜军官勃那多(Barnardo)看到的是“无”;奥菲利娅两腿中间的是“无”;是“无”让扮演国王的伶人为赫卡柏(Hecuba)黯然涕下;是“无”构建了先王的角色。在《哈姆莱特》中,“无”出现了三十次之多。文本中“无”的出现恰恰提醒我们它所代表的缺席。认知语言学对“无”这个传统而稳定的定义发起了挑战,展示了“物”到“无”的转变。在舞台表演中,《哈姆莱特》更是进一步将“无”展示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特定的“无”总能找到对应的“物”。对“无”的呈现不仅解决了认知语言学领域的一场重大争论,还唤起我们对自愿终止怀疑这一传统假设的关注。
我们的思维方式
在2001年发行的一期《实体》(Substance)杂志中,就文学可能存在的进化适应的方式,艾伦·斯波尔斯基(Ellen Spolsky)与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蕾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双方展开了一场对话。双方都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且都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然而使用的理论却差之千里。托比和科斯米德斯使用的是源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大脑计算模型。[1]而斯波尔斯基则赞同认知科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e Rosch)和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的观点,认为人脑是具身(embodied)的。[2]两种范式,一是将大脑看作电脑,输入的内容在人脑中进行一系列算法处理;另一个则将大脑看成是和环境互相形塑的有机体。这两种观念之间的转换已经在很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场争论尘埃落定之前,人文科学研究中应用认知科学的某些理论都有必要注明采用的是何种范式。在此,我们不一一详述这场争论的细节,笔者想使用认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帮助解释《哈姆莱特》中频繁出现的“无”。或许应用各种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自然选择,适者能更好地诠释对我们人类至关重要的审美的、情感的、认知的体验。认知语言学和情感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思考戏剧提供了能量,显现了以往隐形未知的体验。
在《肉身中的哲学:具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一书中,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理性的结构源于我们具身体验(embodiment)的细节。把语言和认知看成对这个世界的具身体验,后果之一便是否认了思维和语言试图捕捉和代表的先验真理。例如基本隐喻“多为上”,它来源于我们将液体倒入容器的体验;我们对容器的基本隐喻建构了我们对空间的理解,它也来源于我们对身体内部外部构造的体验。[3]有人为这个较弱的具身范式作辩护——莱考夫或许也会这么认为,抽象的概念是基于体验的域的表现,绝非直接的身体体验——这个范式解释了为何不使用隐喻,我们就没法谈论时间、生命等抽象概念。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TheMetaphorsWeLiveBy)一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我们的某些思维是包含在隐喻中,并由隐喻定义的。如:“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隐喻,就系统地蕴含着更多的隐喻(如“时间是有价值的商品”等)。[4]于是我们和时间的关系就交由时间的思维关联系统来定义了。这就是为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间可以被用于“花”或者“浪费”,时间被看作是一种活动所具备的东西,而不可能同时为另外的活动所具备。隐喻只能从源域(金钱)到目标域(时间)之间映射信息,因此它在显现抽象概念一些元素的同时,也隐藏了其他元素。
然而隐喻理论有它的不足之处。譬如在《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DangerousThings)一书中,莱考夫用社会学术语“非真实性陈述”(social lie)作为例子来探索“谎言”的类型。[5]74“非真实性陈述”这个概念表明我们是按照等级给谎言进行归类的(有些是故意欺骗,有些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口,还有一些则是为了维护某个社会合约而说)。莱考夫承认,他不知道“非真实性陈述”这个术语为何会有如此含义,因为修饰词“社会的”(social)不能完全解释这个词组的意义。概念混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简称CBT)很清楚地阐述了莱考夫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没法解释的内容。概念隐喻理论把意义隐喻化,通过源域来理解目标域,信息往往是从一个域(源)映射到另一个域(目标)。但在《我们的思维方式》(TheWayWeThink)一书中,吉尔斯·福柯尼耶(Gilles Fauconnier)和马克·特纳(Mark Turner)却认为,很多事物没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他们用福柯尼耶的心理空间理论设想信息的混合(blend)。[6]混合由两个或多个输入空间投射到一个混合空间进行意义的建构,因此混合意义包含的信息和结构来自两个及以上的空间。“非真实性陈述”这个概念的意义取决于投射的是有关撒谎的信息还是有关于社会礼仪规范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理解“谎言”并非是通过将信息从“社会的”映射到我们对于“谎言”的理解,而是两者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混合,两者都对我们最终的理解做出贡献。这个理论的先进之处在于它对隐喻思维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把语言中的这些混合进行拆分继而揭示出隐藏的空间和假设。
混合空间就像是准备好了道具、人物以及剧本的舞台,等待着演员的即兴表演。双域混合结合来自不同输入空间的结构信息以构建新的意义。在《文学的心灵》(LiteraryMind)这部著作中,马克·特纳结合各种文学故事(从耶稣为拯救人类的原罪而受难的故事到《逃家小兔》之类的儿童故事)探讨混合这一概念。[7]在每个故事中,混合空间里的信息在各个输入空间中并不存在,它是混合的结果。如在耶稣为救赎人类而受难这个故事中,无罪的耶稣的输入空间和有罪的人类的输入空间相互混合的结果是耶稣的死是为人类赎罪。他的死是戏剧性的,意义非凡的,又极具象征意义的,因为我们并非是字面地或是隐喻地理解这个故事,而是把它作为混合的结果。混合又决定了基督徒们理解十字架、受难、死亡和罪的方式。混合理论揭开了渗透在语言中的各种无意识假设的神秘面纱。如若把“无”看成是一种混合,我们便会质疑它的出处进而思考它的缺席从何处来。
作为心智建构的“无”
在思维的孕育下诞生的“无”是这样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物质证据,因此我们必须建构它。概念混合理论解构了“无”的传统概念,于是“无”便成了多重心理空间的混合,并带有一种新生的构造,能引起一系列的思维活动,把一些原本存在的某物混合成“无”。福柯尼耶和特纳认为混合是对思维间隙的衔接,它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功能;它证实我们将信息从两个及以上的心理空间映射到混合空间构建混合,并且能把“无”当作某物:
在混合中,这个新的元素可被看作普通的物,语言的常规流程——指认事物也可正常进行。以“消失的椅子”为例,消失的椅子是混合中的物。外面看来,便是“无”,但它却可以被人指着,也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它继承了其物理特征,是“实际”输入的思维间隙,在实际输入空间的相应位置根本就没有椅子。所以我们认为像“没人”“没事”“没运”这些普通的名词短语都无一例外地从某一空间中挑取某物。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语法结构中看到这样的表达如“没人看到他”,“我没钱”,“没脑子是你的问题”,“我从没想过有人能理解我”,“他完全是一副不容胡闹的态度”等 。[6]241
一旦我们构建了一个“无”的混合空间,它就能呈现出某物的特征。就像“消失的椅子”具备“椅子”的很多特征,这就是它的层创结构。“无”把缺席选择性地从特定物质的位置进行投射。在探讨“零”的例子时,福柯尼耶和特纳指出了“零”的创造性。起初“零”只是缺失数字的补位数,渐渐地,它成了独立数字,并且和其他数字一样具备了数学功能。[6]244这个“零”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开场中的气势和“无”一样强劲。“一个小小的圆圈儿,凑在数字的末尾就可以变成一百万。那么我们就凭这点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庞大的想象力吧。”*译文参考《莎士比亚历史剧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亨利五世》序,15—17)“零”在某些地方或许只是个符号,但假使六个“零”齐刷刷地跟在“一”后面就成了百万。
《哈姆莱特》中的“无”
剧中伶人的表演开始前,哈姆莱特与国王克劳狄斯及哈姆莱特与奥菲利娅之间的对话,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无”。克劳狄斯问哈姆莱特“最近过得可好”,哈姆莱特玩起了惯用的文字游戏,他回答说自己吃的是“无”,“我整天吃的是空气,肚子让甜言蜜语塞满了;这可不是你们填鸭子的办法”(《哈姆莱特》3.2.93)。克劳狄斯听后说:“你的回答对于我来说就是‘无’,哈姆莱特,这些话不是我的意思。”(《哈姆莱特》3.2.95)哈姆莱特的话冲着他而去,却好像没有击中目标。克劳狄斯没有抓住本意。克劳狄斯宣称哈姆莱特的回答是“无”,因为回答与他无关。哈姆莱特的混合本领更高,坚称话一经说出,就没有所有权,“不,也不是我的意思”*译文参考《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著,裘克安注释。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41页: A man’s words are his own no longer than he keeps them unspoken。(《哈姆莱特》3.2.97)。哈姆莱特把形状和意义恢复到了“无”,将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那儿脱离出来,正如那把指涉缺席的“消失的椅子”一样。
同样地,奥菲利娅躲开了哈姆莱特关于“下流想法”的问题,机智地回答道:“无!殿下。”(《哈姆莱特》3.2.116)呼应了克劳狄斯方才对任性王子的反诘。哈姆莱特再一次巧妙地把“无”变成了“物”,觉得奥菲利娅没有想到的“下流想法”便是“睡在姑娘大腿中间”。在他巧妙的词汇中,“无”突然成了生殖空间,而奥菲利娅所说的“无”肯定是从阳物物化的心理空间来理解的。比起哈姆莱特,奥菲利娅那个部位确实缺席。但在哈姆莱特的语言中,两者的阳物在心理层面却都变得清晰可见。
在舞台上,奥菲利娅的“无”又将如何呈现?哈姆莱特的语言硬生生地把好奇观众的目光吸引到奥菲利娅的两腿中间看她有无。奥菲利娅借着演员的身体表现人物,然而褪去演出服后,舞台上就是个扮演奥菲利娅的演员。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由男生扮演奥菲利娅的传统方法更是增添了一层混合:扮演奥菲利娅的男演员两腿之间并非“无”。那一页文字唤起了读者对人物生殖器的关注;而搬到舞台上,则唤起了观众对演员生殖器的关注。一群扮成女生的男孩,明明“有”却假扮成“无”,这是那个时代反表演艺术的主要特征。[8]莎士比亚打破了奥菲利娅性别的幻觉,因为如果他/她亦男亦女,这样的表演似乎更具魅力。莎士比亚的“无”揭秘了一个被指定为是无物空间里的一个到场物或存在。这个在缺席中的到场是《哈姆莱特》“无”的层创结构。舞台上的语言表演经由在理解过程中产生和混合的空间网络不断改变着它的动态意义。
戏剧中虚拟和现实的混合
尽管目前在文学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着将科学方法用于诠释文学作品,但是在戏剧表演这一块,用认知科学挑战我们对戏剧表演的理解,此类研究目前尚少。[9]站在舞台上的那个吟诵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人,他同时是一个演员,是一个角色,又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解读他?我们会为哈姆莱特的死而难过落泪,为何不会因此而跳到舞台上?戏剧性混合引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认知错觉。舞台上的每一事物都是混合的结果:部分表征,部分代表事物其本身。当莎士比亚写下“是谁在那儿?”这句话时,它是虚构的。当演员在台上念这句话时,它部分虚构,但又有部分确实是真实场景中的真实人物问的一个真实的问题。他既不完全虚构,也不完全真实,这种是是而非、是非而是的状态成就了他非凡的魅力。柯勒律治(Coleridge)曾提出“自愿终止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用以解释不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所拥有的能唤起真实情感的强大力量。戏剧理论、表演分析以及各种戏剧评论都倚着该隐喻讨论戏剧的现象学。终止怀疑已成为戏剧理论的叙事主导。然而,若是从当下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或是情感研究来看,这个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终止怀疑
伯特·史戴兹(Bert States)在《小房间中的大谋划》(GreatReckoningsinLittleRooms)一书中,认为“戏剧的表现基础在于它的双重假装”:戏剧假装我们观众不存在(第四堵墙习俗,即the fourth wall convention),而我们观众假装这个戏的内容真实存在(自愿终止怀疑,即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10]206这种构想认为戏剧就是无中生有,它是“无”的层创结构。终止怀疑的同时把怀疑当作了在场,这种感觉在我们欣赏戏剧时一直陪伴左右。该逻辑就像为了欣赏小说我们必须把不真实的知识趋于真实化。这让我们对舞台上的表演有所感觉,而不会因为舞台上的演出而有所反应。当我们被成功的叙事感动得忘乎所以时,终止怀疑仍不失为一种典型的特征。
我们理解小说特别是戏剧时,终止怀疑称得上是十分核心的概念,但令人诧异的是它很少受人质疑。多数产生质疑的学者都基于一个假设:思维和感觉是不同的机制。看小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状态,要经常打断正常的功能性心理,如此才能体验真理的价值。托比和科斯米德斯以此来区分小说和非小说:“小说无意让读者把它当真——虽然文字描述的无异于世上的真实事件。”[11]12然而斯波尔斯基指出,很大一部分读者却误把小说场景当作现实:
我们不仅可以想到李尔王和他的女儿们,而且还可以想到一个年轻人想要喝啤酒时面临的挣扎(根据他的其中一个文化故事)。在另一个故事里,他还要开车把约会对象安全地送回家。假设存在一个进化机制,告诉读者第一个故事是当地的文化小说,而第二个故事是现实中发生的事。[…] 事实是人们确实经常容易混淆两者(虚构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具有强感染力的故事以及诠释者们的影响。[12]187
托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终止怀疑表示我们在小说的阅读和接受过程中,会采用一种同类归纳法。如此,我们的认知输入才不会将虚构事件和事实混为一谈。斯波尔斯基则认为,故事中的信息点将通过不同方式投射到不同情境中——虚构的信息往往被投射到非虚构的场景中——这就导致一个现象:我们即使知道《李尔王》是虚构的,但我们总能从中发现人类的真理。在文章中,斯波尔斯基没有明确做出论断,但基于我们对终止怀疑这一概念的理解,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混合理论挑战了我们对终止怀疑的认识,为我们全新解读《哈姆莱特》中的“无”提供了参考。
目前对终止怀疑这一概念有两种理论上的质疑。其一是伊娃·沙佩尔(Eva Schaper)把终止怀疑的定义复杂化。其二是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将神经科学研究用于解释此现象。不过两者都没能强大到对终止怀疑的假设形成挑战。沙佩尔考察了终止怀疑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认为假使没有前者,“我们受到自认为不存在或未发生过的事的感染时,总会困惑不已”[13]31。她没法忽视我们对虚构世界产生的情感经历,但是对假设感到十分不解。我们做出反应的对象是虚幻的,我们做出反应的方式也是虚幻的,“终止怀疑存在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要产生真正的感动和共鸣的前提是我们对情感的客体充满信任”[13]34。她进而拆分了终止怀疑这个概念,认为信任比终止更具细微的差别。尽管如此,她没有质疑整个假设:为了感受某事,我们必须相信,导致情感产生的刺激物事实上是存在的。
为了感受霍拉旭(Horatio)在听到哈姆莱特对死亡的请求时做出的反应,我们没必要相信他真的把哈姆莱特缩小后放到自己的心里去。我们也没必要相信哈姆莱特或霍拉旭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的好友对我们说她“遇到了死胡同”时,我们没必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她的人生就是一条路或时间被置于空间之中来理解她关心的问题——她没法更进一步或者她的人生快走到尽头了。如果为了情感上更好地去理解一句话,而不做字面诠释,那么为何当我们听到舞台上的台词时,我们又要坚持终止怀疑的策略?为何我们对自己相信的事物态度如此坚定?
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借他早期惯用的心理分析结合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来解释终止怀疑。他认为,当我们在剧院看剧或是阅读时,我们往往不再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计划等等。此时我们已切断了我们的情感和大脑前额皮层之间的联系。我们还能体会情感,但是情感不再和大脑前额皮层进行真实性确认和计划制订。计划一般是在大脑前额皮层中完成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物体的未来和过去进行想象,在当下看来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只要我们在读书或者看剧看电影时不挪动位置,我们就不会去测试我们正在感知的事物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自愿终止怀疑。一旦我们打算挪动,我们就打破了魔咒”[14]4。他明确地继承发展了终止怀疑的说法,并且认为我们想象假设和反事实时,它也一样通用。认为一种状态是一个魔咒(自愿终止怀疑)就是低估这种状态的力量和普遍性。
霍兰德总结说:“我们可以对不真实的虚拟物产生真实的情感因为我们有两套不同的大脑系统在运作。”[14]6这种说法我认为依旧坚持了错误的真实和非真实的情感情境两分法。如果认为正常的引发情感的情境是经现实检验的话,那么这个“现实”对情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有人因为男朋友没有给她打电话而哭泣,这正如那个扮演国王的伶人对着“无”哭泣一般。没有电话就意味着“无”。在虚构世界里,对于背叛或者缺乏兴趣这样的错误判断也是不经现实检验的。我们使用虚构的碎片信息构建能激发我们情感的非虚构的情境,这种做法不会减少或改变我们经历的情感。
在具身认知中,这种二分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具身认知科学家认为人脑在不断地构成叙事以诠释环境。在具身认知和计算认知的争论之外,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S.Ramachandran)提出了一种反常的大脑状态。他指出这种状态表明大脑在未受损的状态下是如何揭示“真理”的。拉马钱德兰举了疾病失认证的例子。在这些案例中,病人都不相信自己受过伤——他们往往是因中风引起身体麻痹或者受到其他影响右脑功能的大脑损伤。这些病人捏造离奇的故事来解释他们身体麻痹的原因或者干脆直接拒绝解释。他们会说他们在用麻痹的手举托盘,虽然医生看到他们的手根本没有动。他们也会拒绝移动手臂,原因并非因为他们的手麻痹得不能动弹,而是他们有权利选择不做。拉马钱德兰认为理解这种症状的关键在于左右半脑存在差异。他说左半脑负责创建一个“‘信任系统’,一个用来理解证据的信任系统”[15]134,右半脑收集潜在矛盾的信息并且定期修正以配合最新收集的数据。他说如果右脑受损,左脑不再需要修正故事因为右脑再也辨识不了矛盾的数据。拉马钱德兰的半脑“魔鬼代言人”故事或许是引人思考的,然而他对疾病失认证病人的研究表明我们只有对感觉真实的事物才会产生情感这个想法没能解释虚构的故事对我们日常的影响(“我胖”或“克迪利亚肯定不爱我了”)或是半脑受损对我们异常的影响。
拉马钱德兰的理论解释了大脑严重受损的案例,福柯尼耶和特纳的“生活在混合中”理论则解释了每天都发生的在发音和理解上的认知语言飞跃。像霍兰德一样,“生活在混合中”也解释了我们在剧院时大脑容易失去控制这个现象。但和霍兰德不同的是,福柯尼耶和特纳谈到“生活在混合中”,思维和感觉是必不可少的。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教授提出的“操纵虚构(operating fiction,处理和理解某个特定的情境)”类似,福柯尼耶和特纳没有将过程和虚构以及信任联系在一起。虽然使用虚构作为控制对象假定了一套虚构须用到的事实术语。但是“生活在混合中”这个理论避开了这个假设,因为它依赖于建构用于理解话语的临时矩阵的整个概念过程。真理的程度与是否具有混合的有用性或者情感的冲击力是无关的。
福柯尼耶和特纳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柏林曾研究过的一个严重抑郁症案例。患者买彩票——仅仅是为了“好玩儿”,而不是希望中彩票——所以当他们没有中彩票时,感觉严重抑郁。症状类似于那些失去了家或者爱人的人,这个案例说明买了彩票之后希望中彩票的人一直生活在已经中了彩票的幻觉中。当现实打破了幻觉时,这种幻觉带给他们的一切也都随之消失了:“患者对赢彩票没有幻想,并且他们也清楚地表示了这一想法,然而幻想的世界似乎对他们真实世界的心理现实产生了深远影响。”[6]231一个女观众看完《理查三世》后,递给理查三世的表演者伯比奇(Burbage)一张字条,问他是否能以理查的名义去找她。明显,她是希望继续生活在理查·伯比奇和驼背的理查三世的混合中。[16]10在婚礼上争抢新娘花束的女孩子们把花束和丈夫混合了。她们以为抢到了花束就是抢到了丈夫。混合的界限因人而异。在正常情况下,伴娘抢到花束会很激动,然而要是仅仅因为抢到花束就以准新娘的身份开始向亲友发送婚礼邀请函,这就令人担心了。福柯尼耶和特纳的“生活在混合中”不仅限于虚构的故事,而且也适用于更广的——语言、概念、情感体验,这些都被划归到了“终止怀疑”名下,很具有误导性和限制性。
赫卡柏(Hecuba)对他意味着什么?
哈姆莱特:这个伶人不过在一本虚构的故事、一场激昂的幻梦之中,却能够使他的灵魂化在他的意象里。在它的影响之下,他的整个的脸色变成惨白,他的眼中洋溢着眼泪,他的神情流露着仓皇,他的声音是这么呜咽凄凉,他的全部动作都表现得和他的意象一致,这不是极不可思议的吗?而且一点也不为了什么!为了赫卡柏!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译文参考《莎士比亚悲剧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哈姆莱特》2.2.545—554)
伶人在为赫卡柏哭泣流泪,而自认“满怀情感的”哈姆莱特却无动于衷。这表明情感和虚构存在一种有趣的关联。哈姆莱特认为他的处境更能激起现实的情感(他甚至认为能激起行动),然而他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号啕大哭,这让他出奇地愤怒。哈姆莱特为自己的愚钝而愤怒,莎士比亚采用额外的音节和断句的形式,呈现出哈姆莱特“威风凛凛”的决心和“哼不出一句话来”之间的矛盾:
谁骂我恶人?谁敲破我脑壳?
谁拔去我的胡子,把它吹在我的脸上?
谁扭我的鼻子?谁当面指斥我胡说?
谁对我做这种事?
嘿!
Who calls me villain, breaks my pate across,
Pluck off my beard and blows it in my face,
Tweak me by the nose, gives me the lie I ‘th’ throat
As deep as to the lungs—who does me this?
Ha!(Hamlet2.2.567—571)
前三行始于抑扬格,止于扬抑格。将强调第二个音节的抑扬格韵律转为强调第一个音节的扬抑格韵律。第三行继续打断抑扬格的韵律,把额外非重读的音节塞入行中,对第一、第三及第四韵脚作了处理。当然,“嘿”也可放在下一行,或是给演员进入“嘿”之前九个音节中一个小小的停顿,或是创建一个以“嘿”作为开端的抑扬格,且用弱音节“是”结尾。无论是哪种处理方式,演员的情感都在此刻爆发。哈姆莱特的独白揭示了他内心的情感。他发现自己被演员们充满激情的表演感动了。本来打算“无动于衷”,然而现在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决定借用虚构的戏剧让国王感到内疚。情感只有在关于情感的表演中才能最好地诠释出来。
情感的表演和情感并不是一回事。女人看到死去的丈夫时的反应给演国王的伶人表演抒发情感提供了参考。他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现象来表达情感——哭泣,面色苍白等——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像他表现的那么伤心。同样,莎士比亚在剧本中描述着哈姆莱特的情感,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着哈姆莱特的情感,观众并不知道表演哈姆莱特的演员是否感受到了他传递给观众的那些情感。
艾利·柯尼基(Elly Konijn)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她发现演员们在台上体验的情感是由演出场所的“情境——意义——结构引起的,而不是由人物的情感引发的”[17]65。譬如在台上,演员们的情感是跟在观众面前的表演相关联的(挑战、紧张、专注、不安等),跟人物想要传递的情感或者演员要表演的情感无关。无论演员们是否用体验派的表演方法或模仿手法,最终都没有关系。演员们体验到的情感和他们手头的演出任务有关,跟人物的经历无关:“然而在表演中,对表演的真实场景的要求——在观众面前——会让演员没法完全投入到人物—情感中去。”[17]78演员和人物的不一样的感觉,都融于舞台情绪最终的表达。终止怀疑诠释的戏剧情感目标是指观众通过观看演员的演出获得和人物角色一样情感状态的能力。为了理解这个,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我们对情感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是悲剧的要素,所有的悲剧叙事都必须包含能引起怜悯和恐惧的事件,以此让观众体验感情净化。有关净化的学术争论较多,然而很少有戏剧理论家质疑“怜悯和恐惧”的定义。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即使是神经科学家也更钟情于理性的问题多于情感的研究。以往情感被当作人脑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它处于较低的神经层中。[18]39大脑的边缘系统处于大脑深处,往往单独行动。我们人类的前脑用来理解数学,而爬虫类的脑部恐怕就没这个功能。
在《笛卡儿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Descartes’Error:Emotion,ReasonandtheHumanBrain)一书中,达马西奥(Damasio)给情感做了以下的定义:“情感是在大脑系统的控制下,神经细胞终端的诱导下,无数身体器官变化的集合,主要是对特定事件相关思维作出的身体反应。”[19]139感官输入的信息直接传至丘脑,后者负责把潜在报警信息转轨至带有身体报警机制的扁桃体。情感刺激直接从丘脑传至扁桃体(准备身体反应)及感觉皮层(评估信息)。感觉皮层评估完信息,即把抑制的或亢奋的信息传至下丘脑,由它负责发送和接受信息至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些信息包含改变身体状态的神经递质和荷尔蒙,身体会产生以下反应:手心出汗,口干舌燥,心跳加速,面色红润或苍白,胃部收缩以及肌肉的松弛和紧绷。这些身体反应的出现是出于对我们的保护。比如:如果一个人想要逃离,他的心跳自然会加速。
然而心跳加速也有可能是恐慌、愤怒或是恋爱导致的。达马西奥认为,在恐慌和恋爱时,身体总的化学变化有细微差别,但是主要差别在于大脑皮质对身体状态的评估,他称之为“感觉”,是身体中和影像、回忆以及刺激知识并置的情感经历。一种身体反应不仅仅表达一种感觉。若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感觉,必须将他的身体变化和其他信息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某人心跳加速和胃部收缩被认为是恋爱的表现,是因为桌上的烛光和约会对象瞪大眼睛看他/她的结果。而同样的身体反应在其他时候,则被认为是食物中毒。人的情感可以被旁人感知,然而感觉是内在私人的,是由情感的身体反应引起的心理状态。
人们不必要有体验才会有相应的情感。观众看到台上俄狄浦斯滴血的双眼,或是听到舞台后痛苦的呐喊,同样能体会到恐惧。这种刺激和需要身体反应的情感非常相像,因此扁桃体也能接收到信息。演员的表演同样能触发观众的情感。我们的扁桃体部分用于评估演员表情,部分捕捉声调变化,体验他人的恐惧。[20]85旁观者对他人情感的感知足以激发他自身的情感。有个研究曾经让被试者看别人厌恶的表情。当被观察者做出极度厌恶的表情时,被试者脑部处理厌恶情绪的神经元也活跃起来。[21]大量数据证明人类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看到别人情感的表达,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达马西奥称之为“似身体回路”,他认为看到爱的人遭受痛苦会引发类似的生理反应,好似自己在经历这种痛苦一般。身体回路是经由身体流通信息的系统,用于改变人在特定环境下的身体状态,如恐惧、顿悟等。身体状态的认知表征能识别外部变化,即使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好似亲身经历一般。达马西奥认为这样便于模仿。它让我们体验和情感刺激物不一样的经历,譬如回忆。我们回忆的内容往往是和真实事件及人物不完全一致的,而是增加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的。[19]100然而对过去事件的回忆模仿足以唤起我们对那段事件或那个人物的情感。
戏剧依赖人脑重新构建与某些事件相关的情感。戏剧中,演员在台上模仿动作以激发情感。看到妈妈的照片,就能激发和妈妈相关的情感。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一样,我们的回忆是对原始事件或情感刺激的模仿,进而引发真实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认为舞台上悲剧引起的恐惧和怜悯是模仿的,观众对“真实”事件产生恐惧和怜悯也是通过模仿实现的。如果每一种感觉都是人为了解释生理反应而构建的心理故事,那么我们想到赫卡柏时内心的感觉和想到妈妈时内心的感觉没什么差别。两者都是对表征的反应。
科学家对人类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戏剧能激发观众模仿舞台情节,以产生相应情感。达马西奥的研究是基于对有各种大脑异常的病人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扫描,而正常人脑的脑电图(EEG)和脑磁图(MEG)则显示人脑中存在一个镜像神经元系统,能对他人的特定动作产生反应。
里佐拉蒂(Rizzolatti)和克莱杰罗(Craighero)证实在看他人表演动作或是摆一个毫无意义的姿势时,人的运动前区皮质会被激活。[22]其他研究也表明当被试者看到的动作是他所预期的,如伸手拿电话话筒,他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就会被激活。上述研究显示人类不仅拥有和猴子类似的镜像神经元系统,[23]并且比后者的更为高级,这在我们模仿他人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科学家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人脑中存在一个方便我们学习、产生同情、连接他人的系统。我们为何被戏剧或是别人虚构(或真实)的故事感动?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传统观念必须考虑并接受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并非是“无”
王后:你这番话是对谁说的?
哈姆莱特:您看见的不会是“无”吧?
王后:无!要是有人在那边,我不会看不见的。*译文参考《莎士比亚悲剧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3.4.131—133)
哈姆莱特问王后是否看见了什么。王后确认说她看了的是“无”。他俩达成了一致:哈姆莱特指着“无”,王后看见“无”。王后坚持说她能看见的东西就是“无”,这让“无”成了某人的一部分,正中了哈姆莱特的意。当然,在舞台上,哈姆莱特话语间指向的是由演员扮演的鬼魂——或许最初是由莎士比亚亲自扮演的——虽然嘴上说着“无”,然而观众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无”就在舞台上,幽灵般地缺席或在场,凭借它巨大的力量,激发人的激情和血腥想象。混合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充斥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心理空间网络。它让我们透过混合构建的“表层”意义理解真正的内涵。对认知科学的应用必须意识到具身化的演员的力量,因为它改变了语言的含意。作为一个剧中人物,奥菲利娅两腿间肯定是空无一物,然而在舞台上她却拥有特别的某物。
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终止怀疑等传统理论发起了挑战,消除了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当“无”站上舞台时,“有”和“无”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把我们的虚构理论建立在事实和虚构,某物和无物的区别界线之上,其实是字面和隐喻,思维和感觉二分法的具体化,目前科学研究尚未做出证实。很多“9.11”事件的目击者在描述该事件时都说“就像一场电影一样”。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只有跟虚构世界作比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说明为了相信我们必须终止怀疑。然而这恰恰说明这个术语的无用性,因为为了相信,相信本身是没用的。假如人脑能对他人的预期动作作出反应,我们的情感能被没有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激发,那么看到哈姆莱特对伶人为赫卡柏哭泣的反应映射了我们对哈姆莱特坚持说自己看到了“无”的鬼魂的反应。感觉就像它在那里,所以它肯定在那里。《哈姆莱特》中的鬼魂还有奥菲利娅两腿中的某物是否真实存在?一切全在观众的脑海里。戏剧教会我们感知“无”,透过“无”看到“物”。
[1] Tooby, John and Leda Cosmides. Dialogue: 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 Respond to Ellen Spolsky[J]. SubStance, 2001, 30(1&2 ): 199-200.
[2] Spolsky, Ellen. Dialogue: Ellen Spolsky Responds to 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J]. SubStance, 2001, 30(1&2 ): 201-202.
[3]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1999.
[4]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7]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The Origins of Thought and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Barish, Jonas. 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9] McConachie, Bruce A. Doing Things with Image Schemas: The Cognitive Turn in Theatre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Experience for Historians[J]. Theatre Journal, 2001,53(4):569-594.
[10] States, Bert O. Great Reckonings in Little Room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ate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1] Tooby, John and Leda Cosmides. Does Beauty Build Adapted Minds? 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Aesthetics, Fiction, and the Arts[J]. SubStance, 2001, 94/95: 6-27.
[12] Spolsky, Ellen. Why and How to Take the Fruit and Leave the Chaff[J]. SubStance, 2001, 94/95: 177-197.
[13] Schaper, Eva. Fiction and the Suspension of Disbelief[J].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78, 18(1): 31-44.
[14] Holland, Norman. 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A Neuro-Psychoanalytic ViewPsyArt: A Hyperlink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Arts[EB/OL]. (2002-09-19) [2005-02-04]. http://www.clas.ufl.edu/ipsa/journal/2003_holland06.shtml.
[15] Ramachandran, V.S. and Sandra Blakeslee. Phantoms in the Brain: Prob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Human Mind[M]. New York: Quill, 1998.
[16] Sorlien, Robert Parker. The Diary of John Manninghan of the Middle Temple, 1602-1603[M].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76.
[17] Konijn, Elly. The Actor’s Emotions Reconsidered: A Psychological Task-Based Perspective[J]. Acting (Re)Considered: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Second Edition. Ed. Phillip B. Zarrilli. London: Routledge, 2002: 62-81.
[18] Damasio, Antonio R.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M]. New York: Harcourt, 1999.
[19] Damasio, Antonio R.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M]. New York: Avon, 1994.
[20] Carter, Rita. Mapping the Mind[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1] Phillips, M.L. et al. A specific neural substrate for perceiv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disgust[J]. Letter to Nature, 1997, 389(6550): 495-497.
[22] Rizzolatti, Giacomo and Craighero, Laila. The Mirror-Neuron System[J].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004, 27: 69-92.
[23] Rizzolatti, G., Fogassi, L., & Gallese, V.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imitation of action[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 2001:661-670.
Staging Nothing:Hamletand Cognitive Science
written by Amy Cook (USA), translated by YU Ya-ping, proofread by HE Hui-bin
The essay use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powerful “nothing” inHamlet. What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fails to account for, Gilles Fauconnier and Mark Turner’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CBT) explicates clearly by using mental space theory to envision informational blends, d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othing” and present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from “object” to “nothing”. It challenges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and clears distinctions between truth and fiction. When nothing takes the stage, the lines get blurred.
Hamlet; nothing; cognitive scienc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2016-11-19
Amy Cook,印第安纳大学戏剧艺术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戏剧理论、艺术与表演研究。
译者简介:余雅萍(1983— ),女,浙江绍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和文学认知批评研究;何辉斌(1968— ),男,江西广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学认知批评研究。
1674-3180(2016)04-0155-10
J80-05
A
① 本文译自Amy Cook“Staging Nothing:Hamletand Cognitive Science.”Substance35 (2006): 8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