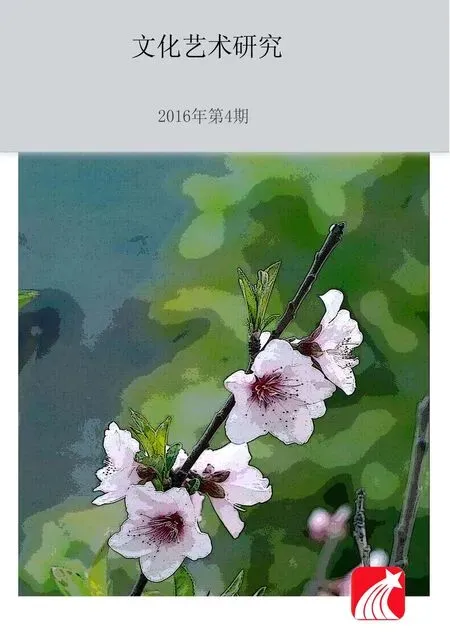电影媒介与电影边界*
——兼论VR影视的非电影性
周 正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合肥 230011)
电影媒介与电影边界*
——兼论VR影视的非电影性
周 正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合肥 230011)
媒介是艺术划分的内在依据,电影艺术概念的界定同样依赖于其媒介。新的电影媒介不断发展,改变着电影的内涵和外延,但是VR(虚拟现实)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与影视的结合,使电影的创作方式和观影体验发生了质的变化,已超出了传统电影的范畴。本文将比较电影与VR影视的区别,以探索电影媒介与电影边界的关系。
电影媒介;电影边界;VR媒介技术
对于“电影是什么或者电影的本体是什么”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大家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随着社会变革与媒介的发展,电影的边界不断扩展,以至形成了一个“泛电影”趋势,并且这种扩展沿着至少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数码化的电影向包括网络、手机等在内的多样化媒体扩散;二是接纳原来并不属于电影的视频艺术、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等类型。[1]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媒介,媒介的发展推动了电影的转型与升级,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电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影+”(如网络电影、3D电影),它们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电影的呈现效果,拓展了其传播平台,电影的本质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范畴,以“运动的声画影像”为媒介实现叙事表意。电影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从胶片到数字化、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2D到3D,每一次变化都丰富了电影的呈现方式和表现手段,不断加深其内涵,也扩大了其外延,但始终存在一个边界,来确定它们是电影,否则艺术的分类都变得模糊了。媒介是艺术划分的内在依据,[2]也是电影的边界。那么电影究竟处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才能被称为“电影”?这就要从电影发展史和传统的电影理论里寻找答案,电影美学本体论、蒙太奇本体论和摄影影像本体论都是在电影发展不同阶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本文认为,任何艺术门类的确认务必遵循其历史发展规律,虽然新的技术和艺术手段层出不穷,但必须有一个确切的范围,否则其概念就会发生质的转移或变化,因此电影艺术的确立也要建立在传统的研究基础之上。不管新的媒介技术如何发展,但总存在一个临界点,以保证电影之所以为电影。最近几年虚拟现实技术(VR)被炒得火热,它的出现与应用使得影像的制作步入一个新的领域,但通过VR技术制作的作品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范围,变成了另外一种艺术。本文将运用传统电影理论对电影与VR影视之间的边界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虚拟现实技术与影视制作
“虚拟现实(VR)”技术并不是近年才有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各种VR产品不断涌现,其普及率也逐渐提高。2014年3月,Facebook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致力于虚拟头盔等设备开发与推广的Oculus公司,马克·扎克伯格断言虚拟现实是继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平台,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交方式。2016年被业界称为“VR元年”,虚拟现实技术开始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影视制作。虚拟现实,又称灵境技术,指用计算机技术产生“虚拟”的世界,让体验者能够无限制自由化地观看,以获得体验的沉浸感。[3]其主要特征为多感知性、沉浸性、临场感、交互性和仿真性。因此,以VR作为电影的呈现技术将会孕育出更多的可能性与想象空间。于是,业界都在尝试深入探索,而学界也把此作为新的研究热点。然而目前的各种产品五花八门,影视、游戏、展示等种种应用混合在一起, VR影视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艺术层面上看,VR电影都显得独具“革命性”,甚至可以说是早产了,因为现在还看不出其作为电影的存在性。早在2014年,好莱坞传奇导演卡梅隆就尝试用VR技术拍摄画面,但当时他认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甚至“好无聊”。即便是技术相对成熟的今年,他依然对拍摄VR电影没兴趣。卡梅隆认为VR和AR都是“有趣的创作工具”,但把它们运用于电影中则“为时尚早”。按照他的解释,在VR环境中拍摄无法移动镜头,拍出来的影片也无法进行后期剪辑,用VR做出来的最多是一个旁白影片,不能称之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VR电影不能称为电影。http://mt.sohu.com/20160729/n461693438.shtml.[4]
二、VR影视超出电影边界的原因
1.呈现多于表现
VR影视的呈现效果终究逃离二维的藩篱,真正达到一种沉浸式的境界,显得更加真实,这恰恰切中了电影纪实的特性,符合巴赞“将被摄影物与世界同一”的看法。然而,巴赞的“景深镜头”和“长镜头”美学理论是被艺术化的,其本身存在着人为的调度和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内部蒙太奇”。而VR的方式是360度全景式的展现,没有了“第四堵墙”,所有的场景都曝光在观众面前。这种与现实的“逼近”恰是对以“距离”论为前提的传统艺术的背离,[5]因此可以说VR影视会让观众缺乏想象的空间,使得审美的张力难以实现。《电影作为艺术》一书的作者鲁道夫·爱因汉姆认为,电影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去除早期电影技术的落后性,他论断的依据为格式塔心理学,还是很有道理的。如果电影太贴近自然,其艺术性就很难存在,所以务必要给观众留下一些“空白”让他们自己去补充。传统电影美学本体论的基础也与此较为一致。从技术层面分析,电影的画面呈现是建立在1秒钟24帧基础之上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省略的过程,快一点或慢一点都不符合观众的观影心理,而剪辑本身更是一个不断挖空的过程,从而在满足画面呈现的同时,也能完成表现的需要。对于电影而言,VR技术对画面完整的呈现倒不是一件完美的事情,反而会影响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因此,VR影视从技术呈现方面来说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已经超出了传统电影的范畴,很难符合电影作为艺术的表现需要。
如果仅仅通过媒介进行光影的呈现,电影还不能被划归为艺术,其表现的方式和手段更重要。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被称作电影,因为它们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现实,毫无艺术可言。是梅里爱把戏剧的手法引入电影,从而让电影有了叙事表意的功能。后来,格里菲斯创造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手段,再经过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电影大师的不断实验与探索,完整的电影艺术基础——蒙太奇理论逐渐形成。蒙太奇是关于镜头剪辑、组接的一种方式方法,也是指导电影剪辑的理论基础,进而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没有蒙太奇就没有现代电影,因此,有的电影理论家甚至把蒙太奇看作是电影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蒙太奇是电影的本体,是框定电影概念的基础。诞生一百二十年来,电影基本按照蒙太奇的思路进行拍摄、剪辑,更多的是遵循观众的观影习惯。不管新媒介如何发展,要么增强电影画面的呈现效果,要么拓展其传播的平台,但不管在电影院还是在电视、网络上,电影都终究没有超越蒙太奇艺术方式的范畴。然而,VR技术时代到来之后,蒙太奇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电影都有一定的焦点和框架,以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但VR电影不需要剪辑,它是360度全景式的展演,没有中断和空白,类似于舞台剧,需要观众自己去定位兴趣点,没有被关注的地方仍然在上演。
2.焦点选择和表现手段的消失
电影创作有一定的选择性,需经过一系列的取舍,尤其是影像的拍摄与剪辑。这就涉及电影的焦点,即主要表现什么、传达什么。众所周知,电影的基本单位是镜头,而物理意义上的镜头具有一定的视角和范围,其本身的焦距和光轴会让拍摄出来的镜头具有一定的景别、景深、高度、方向、画面构图以及推拉摇移。这些手段可以使画面更具有集中性、艺术性和美观性,并且变化无穷,能够更好地叙事表意,甚至让电影形成一定的风格。但由于VR影视的拍摄同时运用多镜头,致使其全景画面失去了景别、景深等,推拉摇移也变得十分困难。因为VR影视拍摄必须固定一个中心点,进行360度全景式、无死角拍摄,因此周围任何与拍摄无关的东西都要被清除,否则就会造成穿帮,这使得镜头调度和场面调度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如此一来,就无法按照电影的艺术手法来叙事表意。景别、景深等是电影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如果这些都不存在,那么电影还能称之为电影吗?VR影视是不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说,VR影视已经触碰到了电影的临界点。
3.时间与空间的变化
电影是一种时空艺术。电影的时间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经过剪辑之后可以延长、缩短,甚至停滞,其实现方式是由镜头组成的线性影像流。而在VR电影的全景化展演中,时间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无法像在电影中那样进行线性流动,时间的长短快慢都由观看者掌握。如此一来,时间的表现方式就变得较为单一,与电影作为时间性艺术的形式不相对应。故此,在这一点上,VR电影对于时间的艺术化表现就欠缺很多,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范围。
空间也是电影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除了电影本身的空间再现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大部分的电影空间是剪辑出来的,属于构成空间,根据不同场景的连接,其影视空间可以拓展或缩小。而在VR影视中,空间是完整呈现的,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和仿真性,所以观众对空间的把握几乎等同现实世界的知觉方式,空间范围的选择也完全靠观众自身主动控制,很难激发“填漏补缺”的空间想象力。因此,VR电影空间的艺术性也不容易实现,其本身创造的沉浸感反而打造了另一种时空效果。由此可见,VR作为一种新媒介技术已经处在电影的边缘,只能部分促进电影展演的逼真效果,但想创造一种新型的电影形式还有较大困难。
4.媒介的透明性和对媒介的迷恋
杰伊·大卫·波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在其专著《再造:了解新媒体》中指出:“直接性、超媒介性和再造就是现代媒介的三个重要特征。”*转引自党东耀的《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质探析》,《新闻大学》,2015年第4期,第100页。所谓再造是一种媒介补救另一媒介的呈现,不仅包含“整治、修复、补救和调和”等基本含义,还具有改革、重塑和重建的意义。再造具有直接性和超媒介性双重逻辑。直接性也被称为透明性,“决定了媒介本身应该消失而留下它所呈现的东西”*转引自党东耀的《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质探析》,《新闻大学》,2015年第4期,第101页。。而超媒介性则是提醒观众想起媒介,两者正好相反,正如作者认为的那样:直接性和超媒介性与人类的两种渴望有关系,直接性即“渴望透明的直接” ,超媒介性即“迷恋媒介或中介”。*转引自党东耀的《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质探析》,《新闻大学》,2015年第4期,第101页。按照此种逻辑,VR影视因其具有较强的沉浸感和临场感,观众根本感觉不到媒介的存在,或者说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透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电影立体感不强、反映现实能力薄弱的缺点。然而作为影视艺术,其创作与观看对媒介的依存度仍然很高,媒介为作者和观众划分了范围,也框定了集中点,否则,没有任何限制的艺术就变成了天马行空,其内核也被架空。当然,这本身是一个矛盾体,就像我们一方面谈论VR媒介技术,另一方面欣赏VR影视时却又找不到VR的存在,感受到的只有360度全景。到此为止,可以看出传统电影与VR影视中间有一道界线,前者追求超媒介,而后者则看重媒介的透明性,所以VR影视可以被看作一种新媒介艺术,还不能称为电影。
三、结语和讨论
关于电影媒介与电影边界问题的研究始终不会停止,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没有停止过,但不管其变化如何日新月异,电影必须得有一个内核,以此作为维持其自身之所以为电影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每一种艺术都有其活动范围,而不是无边无沿的,否则就成为无法触及的虚无。VR技术的发展势不可当,它与影视的结合的确为观众创造了震撼的体验,但要被归为电影至少现在还不合适,仍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艺术,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1]黄鸣奋.泛电影:21世纪初的媒体与艺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93.
[2] 张晶.艺术媒介论[J].文艺研究,2011(12):52.
[3] 孙略.VR、AR与电影[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3):14.
[4]《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VR电影不能称为电影[EB/OL].(2016-7-29)[2016-9-06]http://mt.sohu.com/20160729/n461693438.shtml.
[5] 孙莉.后“阿凡达”:电影艺术媒介特性的再思考[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4.
Film Media and Film Boundary—On the Non Film of VR Film and Television
ZHOU Zheng
Media are the intrinsic basis of art division, while the concept of film art also depends on its medi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ovie media,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films are both changed, but the VR (virtual reality), as a combin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forms the creation modes and viewing experience of films qualitatively, which has gone beyond the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movi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lms and VR film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lm media and film boundary.
film media; film boundary; VR media technology
2016-09-01
周正(1979— ),男,河南鹿邑人,讲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影视艺术研究。
本文系2015年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课题“新媒介语境下城市‘可参观性’文化的呈现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SK2015A253)的阶段性成果。
1674-3180(2016)04-0122-04
J9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