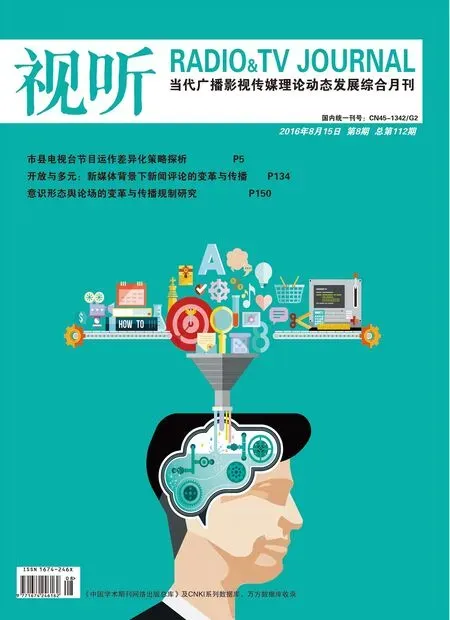浅谈纪录片叙事故事化的手法
——从《元帅诗人叶剑英》创作谈起
□ 仲 华
浅谈纪录片叙事故事化的手法
——从《元帅诗人叶剑英》创作谈起
□ 仲 华
纪录片就是通过拍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的事物,真实人物、真实空间、真实环境,并通过一系列的后期筛选和加工,来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并把观众完全带进这样一个全新的体验当中。在当前的电视纪录片创作中。故事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内容的故事化、叙述的情节化和悬念的设置,则是故事化叙事策略的主要手段。本文从《元帅诗人叶剑英》 创作谈起,分析纪录片叙事故事化的手法。
纪录片;叙事策略;悬念设置
纪录片中一般采用故事化叙述,但是纪录片的故事并不等同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的故事,它从本质上排斥虚构,更接近生活、历史的原生态,这是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内在约束与限度,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违背纪录片特有的真实性。
一、纪录片的故事化
故事化的纪录片具备许多影视剧的元素,能吸引观众,这种取长补短的做法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同时,纪录片的故事性更优于影视剧为观众所接受和认同,同样的题材内容,纪录片的故事性具有折服人心的效果,这种效果来源于纪录片的真实性。纪录片的选题又常因其时空上的大跨度,人物事件的独特性与显著性而形成故事情节。纪录片的故事化,其实就是指在纪录片的创作内容上和表达形式上,强调情节因素,不仅以讲故事的方式代替过去一味地对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刻板纪录。通过人的活动来见证重要事件,而且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偏向于人文世界的深度挖掘。
《元帅诗人叶剑英》虽是个命题作文,在已有的框架下,还是有创作空间的。按照以前的做法,将叶帅的诗词配画面加解说就成了,这样的做法省事易操作,但没有可视性、缺乏灵魂,我们就摈弃了这样的手法,我们通过挖掘诗词背后的故事,让人物变得饱满,让诗词灵动起来。叶剑英元帅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事实上,叶帅的每一首诗词创作都有时代背景,我们走访了许多曾经在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亲属,从他们的回忆中挖掘其后的故事。比如《羊城怀旧》——百战归来意气雄,廿年人事各西东, 关心最是公园路,十丈红棉依样红。其实,这是关于叶帅一段的爱情故事。在民国时期,叶帅在广东参加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爱上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护士,他们经常在公园散步、谈心,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到女孩的父母亲坚决反对,女方家庭是个富有绅士之家,他们觉得叶帅是行伍出身,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牺牲在战场,自己的女儿就成了寡妇,坚决反对他们结合。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哪知道事过20年后,国共合作统一抗战,叶帅成长为八路军的参谋长,回到广州宣传抗战。年轻的叶帅在广州的群众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会后一位少妇来找叶帅,叶帅一看她就是自己当年的恋人。然而,往事如烟,人事各非。叶帅心潮澎湃,感慨良多,随手写下那首怀旧诗。诗里有凄美的爱情。让我们、也让观众看到了叶帅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创作《元帅诗人叶剑英》时,我们选择的诗词尽量找寻故事,以故事化叙述来解读叶帅的诗词,让叶帅的形象更加饱满生动。
二、情节化叙事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纪录片故事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情节化的叙事。纪录片的“故事”不像故事片那样是虚构出来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选择和概括。生活本身是发展着的,生活本身就就具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当你把这些冲突和矛盾加以选择和概括时,就有可能形成既客观又完整的情节内容,这就是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过程。它依赖导演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来推动叙事。
纪录片的情节即生活的戏剧性,由于它特殊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法,与故事片的情节当然不同,故事片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而纪录片的情节则是生活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反映。因此,纪录片的情节常常是简单的、局部的、相对的具有某种冲突因素的生活内容。这种情节化的叙事,将为纪录片创作引入全新的时空观念,也将促使纪录片创造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认真地去对待生活。
再以《叶帅诗人叶剑英》为例,叶剑英元帅和陈毅元帅是两位肝胆相照的挚友,叶帅的诗词中有四首写给陈毅元帅的。在我们采访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时,他给我们展示了四封收藏了30多年的信件,那是叶帅写给因罹患癌症住院的陈毅元帅的慰问信和诗。看到这么珍贵的信件,我们也非常激动,它们是从未公开的珍贵资料。在片中我们让陈昊苏一封封地读出和展示出来,尤其读到这首诗:“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赣南危不屈,福建错能悛。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读着读着,陈昊苏的声音逐渐颤抖、感情有了起伏,甚至眼眶开始湿润,它表达了一种对老战友深切的勉励和怀念,观众也随着他的感情跌宕而变化。
又比如国际大奖的日本纪录片《小鸭子》中有一个情节,一只小鸭子因先天不足,身材矮小,几次都未从池塘里跳出来,只能眼看着妈妈带领着其他小鸭子远远而去。这只小鸭子能从池塘里跳出来吗?这一悬念似的情节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观众为小鸭子的命运担心。然而这只小鸭子没有灰心,一次一次的试着往上跳,又一次次地摔下来,不禁牵动观众的内心,默默地为它加油鼓劲。当这只不服输的小野鸭在第八次尝试成功地升空与它的同伴在空中会合时,此时观众的喜悦油然而生。生动真实的情节使观众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小鸭子的每一次失败,都倾注着观众的再一次期待,观众的在期待过程中获得了动态平衡,从而联想到人类自身,感受自己曾遭遇过的挫折和坎坷。
三、悬念的营造
除了强化冲突,深入情节、细节之外,学会讲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手法便是营造悬念。电视纪录片的表现方式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真实地还原事实,其二是使事实变得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在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中,要使事实充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悬念的营造是十分重要和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悬念是指受众对某事、某物、某人的未来发展、存在状况的一种期待、探究的心理,这种心理一旦被激发,就可以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因此,悬念的营造实质上就是激发受众的这种心理状态。
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的“向未知取材,与生活平行”的观念,正是对这种情节化叙事中悬念营造的另一种表达。向未知取材所营造出的悬念,不仅是节目展开的中心线索、各种矛盾和冲突聚焦的内容,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例如《我们的留学生活》有一集讲述一个年逾40的中国留学生携全家在日本拼搏奋斗的故事。全家人的命运就系于“他的博士论文能否通过答辩”这一悬念之上。围绕着这一悬念,从论文的开题准备、撰写的艰难、卷入经济事件、与妻子分居、生活的拮据直至最后结果的出人意料——未能通过答辩,悬念套悬念,一环扣一环,观众随着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正是这种悬念的营造,使得本片的情节化叙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参与及体验,使片子具有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我们在《元帅诗人叶剑英》第一集开头设置了这样的疑问:叶剑英元帅原来叫叶宜伟,以致于他在中学读书时在后山岩壁上题写的诗,“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因为署名“叶宜伟”无人识而被铲掉了,什么时候改成叶剑英呢?后来,叶帅到了云南讲武学堂学习,与同学合办了一个小册子《剑余诗集》,这个时期写的几首中都有“剑”字,如“把剑长歌气压轩”、“会将剑匣拼孤注”等等,说明叶帅很喜欢“剑”,到本片的结尾才揭晓,“剑”能代表他的远大抱负,才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还比如《叶剑英诗词集》中有一首诗这样写的:雨过斜阳照晚虹,高歌眉月正当空。烧将野草熏蚊子,开着车光舞“狗熊”。我们在《元帅诗人叶剑英》第五集中先提问:舞“狗熊”什么意思,难道是一种古时蒙古人的跳的一种舞蹈?后来,就由叶剑英办公室原主任王守江来揭谜底:原来叶剑英元帅在1961年到内蒙古考察时,晚上在大草原露营,夜晚开张车灯,有人跳舞的影子,因为穿得厚,跳起舞来就像狗熊,叶帅很形象地作了比喻,有了故事悬念的铺垫,枯燥的诗词就鲜活起来了。
总之,选择有故事情节的题材并予以故事情节化处理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毕业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纪录片对现实的诠释是简单的模式化的,仅仅只是停留在赚取眼泪煽情的层面,满足于观众本能的感观享受。在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中,创作者不能为了故事化而摆拍主人公,把原来真实的故事拍成假的,也不能为了情节跌宕起伏,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而人为干预主人公的生活等。如果这样只会舍本求末,也是缺乏职业精神的。所以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应该以非虚构为底线。
(作者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