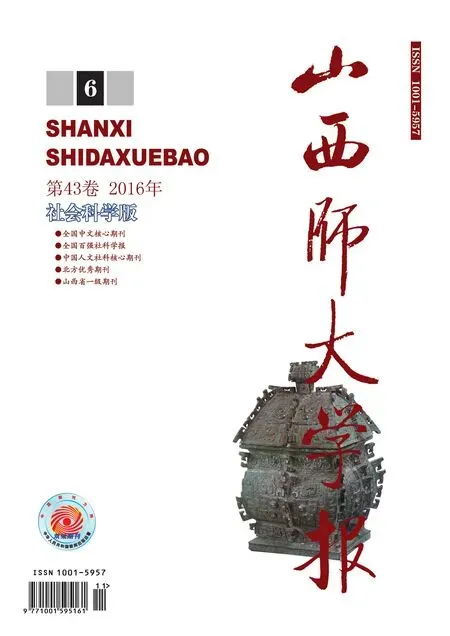文学研究的“对话”范式考察
----以钱钟书的文本互文性研究为例
陈 颖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当下的文学研究日益割裂了与传统文论的血脉因缘,缺失自己民族所特有的阐释理论话语,一味机械引进套用西方文论,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失语症”的学术困境。要突破这种困境,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不妨借鉴一种开放兼容的“对话”研究范式。这种“对话”,绝不是以某一方为主导的话语霸权,而是变单纯的以西释中为中西互释,在双向平等的互动中达成彼此的“视域融合”,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互补中实现新的理论创造。钱钟书先生的文学研究实践与这种“对话”范式不谋而合,他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同时,寻求中西理论话语的互补与互释,通过双方彼此之间话语的沟通、交锋、碰撞、吸收、汇合,使双方各有价值的部分充分显露出来,真正有所发现和创获,并最终获得理论逻辑的自洽。如对文本互文性的研究,就是他实践“对话”运思的成功范例,为我们应对当下文学研究的困境,提供了新鲜的思考与启示。
学界向来把“互文性”视为西方文论的理论创见,而事实上,我国学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相当深入的原创性研究,如在钱先生的批评著述中就散见着大量对文本之间孳生、暗合、创化等交互指涉关系的阐解与识见。这些理论言说表面看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颇为契合,事实上则是对中国崇尚“会通”之学的学术传统的承传与创化,它们不是拘于前人识见的“蹈迹承响”,而是在中外“同心之言”所构筑的整体文论语境中,富有独创性的“暗与其合”。
“互文性”的概念最初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娅5克莉思蒂娃提出,它强调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指涉与作用的关系,一部文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留存着异质之文的痕迹,留存着对其他文本不同程度的因袭与创化。因此,对文本的读解过程同时也是对其他相关文本的记忆重现过程。正如叶维廉所说:“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的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在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涌而绵密的音乐。”[1]65
中国传统文论中虽然没有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对应的概念或范畴,但也有许多涉及到文本之间交互关系的看法。如刘勰以《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来喻指不同文本的语词之间存在着“秘响旁通”的交互指涉性,它们共同交织出各种不同声音的潜在回响:“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2]251刘勰的这一说法颇具代表性,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文本往往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客体,而是浸润在与他文本共同交织而成的文本网络之中的。因此,中国传统阐释学重在探讨文本之间的映射关系,追寻字词的出处,在巨大的文本网络空间中搜求“故实”“本末”,一直是阐释的重心。“从两汉诸儒的‘讖纬’、两晋的‘格义’,到唐代《文选》诸注的引经据典、宋代杜诗诸注的释事释史,中国最正统的阐释著作所采用的方法,几乎使用的都是以其他文本来解释或印证‘本文’的方法。”[3]384这种阐释策略与西方的文本间性研究范式不谋而合,可谓“互文性阐释学”。
此外,中国古代的诗话也格外关注不同诗作之间的师承关系,对于字法、句法、诗法、用典等方面的承袭转化问题着力尤多。还有中国传统的类书也是对众多具有互文关系文本的梳理与汇总,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等类书,分门别类地将各种文献资料进行辑录或杂抄,构筑了一个个可堪会通的文本间性话语空间。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互文性理论在文本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潜在的对话可能性。
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中,钱先生将中西方有关文本互文性的言说“捉置一处”,在比勘与参映中提出自己对文本互文关系的三方面认识:一是缘于“意识腐蚀”之“蹈迹承响”,二是因于“心同理同”之“暗与其合”,三是克服“影响焦虑”之“用古入化”。
一、缘于“意识腐蚀”之“蹈迹承响”
从学生时代开始,钱钟书就对探究文本之间的关系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的《小说识小》《小说识小续》《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等文章,都是通过对具有指涉关系的不同文本的分析考察,揭示它们之间的渊源及影响关系。在他看来,爬梳整理文学互文现象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4]151探究文本之间的关系既可以细察作家如何运化他人作品,从中学习借鉴手法技巧,也可以探究作品之间的渊源及影响关系,进而更深入地品评文本。基于这种批评理念,钱钟书总是辩证地看待所谓“独创”,强调在文学的互文网络中考辨文本之间的“文字因缘”,细察它们在用句典故、手法技巧、情境意象等方面的承继与转化关系。
在对大量文学文本的通观圆览中,钱钟书发现一个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诗人在写景状物时,常常忽视主体自我的审美观感,一味求诸于现成的存语,“借古语自解”,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蹈袭前人。他称这种“以古障眼目”的现象为“意识腐蚀”,把其视为创作者的“膏盲之疾”。[5]588
“意识腐蚀”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哲人科林伍德提出,它强调后代文人的创作在前人话语的遮蔽之下会不自觉地消解自身的创造意识,疏离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钱钟书将科林伍德的这一概念借用过来运用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他认为“意识腐蚀”是造成文本互文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前人言说的遮蔽与腐蚀之下,创作主体或“明知故为”地因袭摹仿,或在习以为常的创作惯性驱动之下,“恬不为意”地袭蹈前人,进而造成了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例如,在《礼记5月令》中有“菊有黄花”之语,张翰《杂诗》中也有“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葱翠,黄花如散金”之句。唐代诗人崔善为在《答无功九日》中将这二语“捉置一处”:“秋来菊花气,深山客重寻,露叶疑涵玉,风花似散金。”而到了王安石《县舍西亭》中,则“径取张翰之喻春花者施之于秋花”:“主人将去菊初栽,落尽黄花去却回”。钱钟书指出,这种因袭显然“语有来历而事无根据”,是典型的造艺者“意识腐蚀”之例。[5]588
可以说,因“意识腐蚀”而导致的因袭摹仿是广泛存在着的文学事实,在文学史上俯拾皆是,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会常常“有犯”,“即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辈大家,亦每‘竞用新事’,‘且表学问’,不啻三年病疟,一鬼难驱”[5]1447。钱钟书以王安石为例,说他“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6]245。例如,他把王驾的诗作《晴景》“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蛺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改头换面为“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6]245在他的诗集中,此类因袭摹仿之作甚多,其采取的模仿手法也层出不穷:诸如“变相”“翻案”“摹本”“仿制”等。[6]245—246钱钟书指出,这种陈陈相因的创作倾向对于文学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都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7]19
那么,造成意识腐蚀的原因究竟何在?钱钟书认为,这既与既定语言系统的干扰与遮蔽有关,也缘于创作者自身主体性的失落。一方面,从语言的固有特点上看,任何语言符号都裹挟着前人言说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主体的表达。因此,作家在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亲近前人话语,落入公式化的“套板反应”之中。比如写赏月诗时,“(诗人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6]255—256
另一方面,从创作者的主体性上看,很多作者往往疏离现实人生,他们“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孽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7]14。躲进文学象牙塔之中的作家久与现实隔离,就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对事物感受的真切性与鲜活性:“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近,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只是‘他乡遇故知’。”[6]255—256于是,在创作中,他们“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词藻,虽然接触到事物,心目间并没有事物的印象”[7]14,自觉或不自觉地袭蹈着前人的好词佳句。可见,正是这种对前人话语的亲近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共同导致了文本的孳生与因袭。
二、因于“心同理同”之“暗与其合”
除了以上缘于“意识腐蚀”而导致的“蹈迹承响”之外,钱钟书还揭示了另一种文本互文性——因于“心同理同”之“暗与其合”。
钱钟书认为,文本之间如果在词句、命意或取象上思路同指,并不一定都是袭蹈或传承之文,而可能是基于“心同理同”的暗中契合之作。对此,谈艺者应注意加以区分,辨别文本是有意的模仿还是无心的暗合。如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名句,其中“绿”字是在经过十余次的推敲琢磨之后选定的。在对相关文本进行圆照周览之后,钱钟书确定“绿”字的此种用法在唐诗中屡屡出现,如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派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那么,“(王安石)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7]77
本着这种对文本互文性细致入微的质疑与求索精神,钱钟书在批评著述中着力发掘出大量具有暗合关系的文学现象,并将其与主观模仿的作品区别开来。他看到,“一家学术开宗明义以前,每有暗与其理合,隐导其说先者,特散钱未串,引弓不满,乏条贯统纪耳。群言歧出,彼此是非,各挟争心而执己见,然亦每有事理同,思路同,所见遂复不期而同者,又未必出于蹈迹承响也”。[5]440也就是说,具有指涉关系的文本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契合而非相受授者”,如老庄之于释氏;另一种是“扬言相攻而阴相师承者”,如王浮以后道家伪经之于佛典。[5]440那么,谈艺者如果一看到形貌相似的“归趣偶同”作品,就武断为“渊源所自”的骨肉之亲,就如同“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5]440背离了批评的科学精神。
那么,文本暗合现象是如何生成的呢?钱钟书认为,这主要基于事物的必然规律而产生的人类心理的相通性。他指出:“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斯宾诺莎论思想之伦次、系连与事物之伦次、系连相符,维果言思想之伦次当依随事物之伦次,皆言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4]50正如斯宾诺莎和维果所言,事物的必然属性决定了一切抽象思辨的内在规律的一致性,进而导致了人类心理的相通性。因此,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还是对宇宙规律的把握,抑或对诗眼文心的捕捉,都具有这种“心同理同”的相通性。在形形色色的言说背后,往往隐藏着它们“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呈现出其思想、心理、情感或意趣等方面“莫逆冥契”的一面。而这,也正是文本“暗与其合”的互文关系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区分了“蹈迹承响”与“暗与其合”这两种文本互文性的同时,钱钟书指出,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错综复杂,有时很难凭借其各自的语言痕迹来定夺,误判现象时有发生。他提醒批评者在考察文本时,既要从宏观处着眼,致力于在古今中西的“他者”文本交织而成的文本海洋中追寻意义;同时也要从微观处着眼,细致辨析文本之间微妙复杂的内在差异性:“上下古今,察其异而辨之,则现事必非往事,此日已异昨日,一不能再,拟失其伦,既无可牵引,并无从借鉴;观其同而通之,则理有常经,事每共势,古今犹旦暮,楚越或肝胆,变不离宗,奇而有法。”[5]1088这就要求批评者必须在确凿的事实依据基础上进行客观严密的分析,持正公允,而不能妄下断语,“非欲说盗袭为当然,俾穿窬得文过也”。[5]1025
三、克服“影响焦虑”之“用古入化”
钱钟书对于“蹈迹承响”与“暗与其合”文本交互关系的阐说揭示出了作家在进行审美观照时所处的尴尬处境: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文化的层累与积淀,他们原初新鲜活泼的天性和感觉,往往被前人言说所网罩和遮蔽,丧失了观照事物应有的天真状态,甚至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钱钟书感叹说:“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7]255—256这种缘于前人言说的遮蔽而带来的心理困境被当代美国文论家哈罗德5布鲁姆称为“影响的焦虑”。在布鲁姆看来,当作家创作时,难免会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无法摒弃来自前代文本话语的遮蔽。面对前人的言说,他们既崇敬又嫉妒,不得不通过吟诵、学习、模仿来消解内心的焦虑,或通过反讽、剥离、曲解甚至颠覆来有意修正前人作品,从而完成对前人作品的吸纳与超越。这就是后人不遗余力地改造前人作品的深层动因。
钱钟书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深入思索了宋代诗人面对唐代诗人的巨大身影而产生的“影响的焦虑”。他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和模仿及依赖的惰性。”[7]10在这里,钱钟书看到了“影响的焦虑”带来的两重性:借鉴与创新,师承与超越。他举例说,唐朝刘威有诗:“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王安石将其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苏子卿有咏梅诗:“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王安石将其改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钱钟书辨析说,这两种修改“迥乎不同”,应该“分别言之”,前者为“改他人句”,后者则是“袭人以为己作”;“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者也。”[6]244—245
也就是说,缘于“意识腐蚀”而导致的文本因袭现象显然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但不能绝对摒弃,如果文本能够点铁成金、“袭蹈”到“夺胎换骨”的地步,那就并非袭蹈,而是创化性的流变了。中国传统文论向来反对割裂挖补前人作品以缝合拼凑的“拘挛补纳”之作,而强调“用古入化”“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运化,主张在将前人的构思或话语重新熔铸运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的推陈出新之法。钱钟书认为,文本的推陈出新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述中,散见着大量有关“用古入化”、推陈出新的文本考察。如在谈及黄庭坚《演雅》中的“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两句诗时,钱钟书指出,黄庭坚的诗句“实本《诗·大东》:‘皖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一节,《金楼子·立言》篇九下全袭之,而更加铺比。”[6]6黄庭坚虽“承人机抒”,摹拟的是传统修辞的“有名无实之喻”,但能够“自成组织”,浑然朴质而毫无牵强,这就是对前人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脱胎换骨”。[6]6
对于文本诸如此类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造性新变,钱钟书非常推崇。他认为,对前人沿袭已久的语言范式进行颠覆或浑然天成地运化熔铸,可以挣脱文学惯例的束缚,以陌生化的审美手段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且所谓‘我’,亦正难与‘非我’判分。随园每将‘性灵’与‘学问’对举,至称‘学荒翻得性灵出’,即不免割裂之弊。吾侪不幸生古人之后,虽欲如‘某甲’之‘不识一字,堂堂作人’,而耳濡目染,终不免有所记闻。……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人已古新之界,盖超越而两忘之。”[6]206“我”的文本话语不可避免地镌刻着“非我”的前人话语的印记,只有把昔日学问“化而相忘”,熔铸运化前人话语,使之转化为自己的话语,才能跨越古新之界。
显然,对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钱先生有着相当深入而又辩证的思考。在他看来,文本的模仿与独创并不相互对立,模仿也是作家进行个性化写作的必经之路,没有模仿就没有独创,独创是模仿基础上的新变。他认为作家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或梅尧臣所说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创作方法,认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6]320事实上,这与梅尧臣所说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如出一辙,而且后者更“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6]320—321。在这里,钱钟书将中西文论对举,相互参映与互补,强调克服创作上的套板反应,一要在选材取境方面进行开拓,变庸俗为雅正,化陈旧为清新;二要在文辞用语方面进行转换,变华伪为诚朴,化俚俗为文雅。这些见解不啻为对作家突破“意识腐蚀”“影响的焦虑”规囿的启示性建议。
总之,钱钟书以独特的阐释策略对文本话语成分进行追踪蹑迹,通过对话语流动性联系的考察,多方发掘具有孳生、暗合及创化关系的文本,将它们捉置一处进行比勘、参映,在细微的语言裂隙中捕捉话语成分的承继与转换,在因袭与化用、模仿与改造中凸显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研究为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文本的生成以及文学阐释的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具有突破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钱先生在掘发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资源的同时,努力寻求中西文论之间的“对话”,在互释与互补中实现理论话语的激活与运化。这一研究范式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文化的尊严,其为当代学人深入思考如何有效激活传统文论话语资源,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都带来了新鲜的思路与启示。
[1] 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 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
[3]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钱钟书.钱钟书集[M].北京:生活5读书5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5读书5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