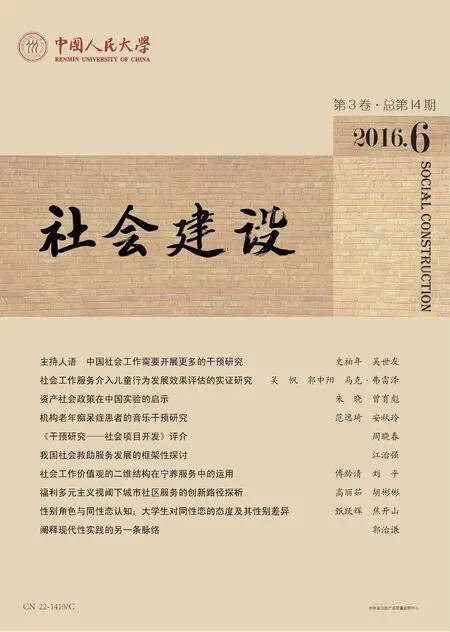阐释现代性实践的另一条脉络——读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郭治谦
□青年学者论坛
阐释现代性实践的另一条脉络——读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郭治谦
现代性是“脱域”于自然而形成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其实实践逻辑潜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脉搏当中,通过19世纪都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而获得呈现。大卫·哈维对巴黎城历史地理学的阐释恰好展现了现代性的实践逻辑:从“表述”到奥斯曼的“三角测量塔”、由空间言说到空间行动。在哈维的地理空间架构中,现代性不仅是描述性图景,更是可以自话的创造性破坏;现代性不仅具有决裂性,更具有延续性;现代性是资本与空间共谋的场域,也是其结果。所有这一切构筑了哈维现代性与巴黎二者的关联,也勾勒了现代性的实践纹理。
现代性;实践逻辑;空间;表述;“三角测量塔”
一、现代性——巴黎——1848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①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04)。主体性、科学性、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要义,而城市则是现代性实践的主要场域,这里集聚了理性思维、科学管理、制度设计,囊括了资本运作、土地变迁、商业积累以及社会阶层关系的粗暴浓缩,城市成为了阐释时空性和表现社会结构的最佳载体。
作为19世纪的欧洲大都市——巴黎——印刻了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足迹,城市空间变革与布局的调整反映和塑造着现代性的运作逻辑。哈维深谙此道,《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正是现代性与都市关联的一本书,是巴黎承载现代性,现代性在巴黎演绎的叙事。正如汪民安先生所说,“为什么选择巴黎作为研究对象?巴黎的改造正好承载了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它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征兆,是现代性的一个充分案例。巴黎,打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窗口。(欧洲的)现代性,它的种种面向,就是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身上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城市的剧变,是现代性的剧变;反过来,现代性的剧变也是城市的剧变。”②[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序二:XII。
哈维对现代性和巴黎的解读,主要围绕一个时间拐点和两个展开,一个时间拐点即1848年,两个①[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页。
是“表述”和“物质化”。在哈维的视野中,1848年是现代性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时刻。“1848年,戏剧性的事件席卷了全欧洲,尤其是巴黎。当时的巴黎在政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上表现出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态度……1848年以前的都市观点,顶多只能粗浅地处理中古时代都市基础建设的问题;而1848年之后则出现了奥斯曼(Haussmann),是他强迫巴黎走入现代……1848年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多半都是散布各处的手工业者;之后则绝大部分手工业者都被机械与现代工作所取代……1848年之前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顽固的管理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
1848年的巴黎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一年,法国爆发工商业危机,农业歉收,大量农民涌进巴黎,这里掺杂着流浪汉、妓女、不安分子……,社会混乱不堪。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英勇巷战,平民阶层、君主阶层、共和主义者、君主立宪派、工人阶级等都骤集或对峙或联合。改革派与革命癖者轮流粉墨登场,短暂的胜利,并没有让平民阶层和工人阶级享受悠长的喜悦,他们至多在杜伊勒里宫中奔跑追逐,并将王座拖往巴士底进行焚烧。革命的果实被马克思称之的“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三世窃取。正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奥斯曼破旧立新开启了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哈维认为,1830~1848年的巴黎是表述性的,是巴尔扎克式的现代性阐释,是言说胜过实践的表达。当然,期间也有革命主义者、梦想主义者想象的“现代性空间”,但笔者认为这已经脱离了“表述”的内里,更多是一种革命的政治上的纠错。1848年之后,在集独裁与民主于一身的拿破仑三世和其忠实拥趸奥斯曼的“铁腕”拆建下,巴黎彻底步入现代性之都。
二、现代性之“表述”:巴尔扎克的巴黎
1848年之前的巴黎现代性是如何“表述”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的第一部分《表述:巴黎1830-1848》主要通过巴尔扎克的视野得以展示。
巴尔扎克是一名小说家,善于以“闲逛者”或“游荡者”的眼睛观察和捕捉巴黎城中的每个人物、每条街道,甚至每个建筑。如波德莱尔、本雅明一般,巴尔扎克拥有极其敏感的神经和对现实的把捉,同时善于游走于虚构——隐喻之间。透过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窥见一幅幅由时间、空间、人物、语言所构成的现代性画卷。这里有地理空间、主体空间、资本空间、信仰空间,在哈维看来,恰恰是强烈的空间意识和空间架构自证了巴尔扎克表述性的现代性。
第一,地理空间:阶层区隔和道德距离。“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种生活方式,它揭示你是谁,你干什么,你来自哪里,你又在追求什么。故分隔不同阶级的物理距离,一样是展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道德距离。”②陆扬:《论哈维的三种巴黎空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你来自外省或农村,你表征的必然不是巴黎城的气质。圣日耳曼区的公寓管理员必然不同于昂坦道区的看门人。现有的位置和空间决定了你的社会存在。固有的空间屏障严格区分了圈子的界限,也定位了道德的秩序。“在历史的每个时期,上层阶级与贵族的巴黎都有着自己的中心,正如同无产阶级总有着自己的特定空间一样。”①[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7页。空间模式执行了道德秩序,通常空间中的所有人都各司其职、各安其事,但也有冲破空间、冲破道德秩序的行为发生。在《邦斯舅舅》中,邦斯舅舅就被女公寓管理员联合其他合谋者击倒,并盗走了他的艺术收藏品。空间出现了松动,阶层和道德模式被颠覆,表征现代性精神的“自由、平等”在此可以窥见一斑。
第二,主体空间:主体性凸显和时空废止。现代性主张个体性的彰显,特别是注重对主体心智能力的强调,意图通过心智提升、内部时空压缩来达成外部空间的改变。“巴尔扎克相信能将一切事物内化于自己的心智之中,然后再通过自己高超的心智能力将事物表现出来。”②同上,第56页。这种对个体心智的宣扬,既代表了现代性主体凸显的呼声,也隐喻着资本主义在地理扩张与加速资本流通上所隐含的革命性质——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倾向。19世纪30~40年代,铁路、运河、报纸等拉近了时空距离,改变了时空观念,相对时空与相关时空相继出现于现代性的舞台上。“不受时空限制的天启崇高时刻,让人既可掌握世界的整体性又能在世界中作出决定性的行动。这个崇高时刻明显联结着性激情以及对‘他者’的拥有(恋人、巴黎、自然、上帝)……资产阶级不断地想降低并去除时空藩篱……这里也透露出重要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神话。”③同上,第57~59页。如此,主体性的张扬便与资本主义的崇高抱负紧密联结起来,共同陈述着现代性的神话。
第三,资本空间:湍流的外空间与紧张的内空间。“在巴黎,‘社会各阶层,不管是低层、中层还是高层,都在需要(Necessity)这个无情女神的鞭子底下跑跳嬉戏:需要金钱、荣耀或娱乐’。资本的流通主导了一切……特别是由‘我们称之为投机的怪兽’来接管……而在更大层次上,对于房产与地租的投机也重塑了城市……新社会的权利指导线存在于信贷体系之中。”④同上,第39~41页。各阶层的需要通过资本的强力宰制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进而营造了湍流的万花筒般的巴黎。这里有齐美尔“麻木不仁”的人群,每件事都能被容忍,你的存在与否都不会对外在造成影响。这里有混乱不堪的商品市场,“街上群集了无数各式各样的商品——各式各样与混合的,发出恶臭与优雅的,鲱鱼与细洋布,丝绸与蜂蜜,奶油与薄纱——除此之后还有许多小店铺,巴黎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如同大多数的人不会感觉到他们的胰脏发生了什么事一样。”⑤同上,第39页。同时,外在世界总是意图刺透、居住并征服他人的室内空间,私人空间以及室内亲密关系在追求交换价值现实下不断受到无情威胁。在长期的内外张力之后,私人空间终于在奥斯曼大改造之后沦陷。
第四,信仰空间:拜物教横行与漫游者抵制。“拜物教是一种宏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存逻辑;而游荡者带着狡黠的眼光,是企图挖掘社会关系秘密的观察者,是试图超越和逃离拜物教的行动者。”⑥杨宇振:《巴黎的神话:作为当代中国城市镜像——读大卫·哈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国际城市规划》,2011(2)。哈维指出,商品拜物教借由生产与流通各项物品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建筑在商品流通之上,也在于巴尔扎克所经常主张的,每个人‘都在无情女神的鞭策……急需用钱之下’不断来回奔走、跳跃,并且被‘我们称之为投机的怪物’所吞噬……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无处不在,社会关系便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各项物品之中。任何物品的重新制造都将造就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在巴黎生活总是不断屈服于巴黎的拜物教力量。”①[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64~65页。商品拜物教俨然成为巴黎的另一种信仰,在这个空间里,个体不自觉沦陷其中,麻木、迷茫甚至神经质。当然,不同于马克思,巴尔扎克意图通过漫游来挖掘巴黎现代性社会关系的秘密并且穿透拜物教。也许,这正是现代性带给当时巴黎人的矛盾和内心冲突,也是现代性的自我悖论。
实际上,哈维借巴尔扎克之笔,间接将波德莱尔、本雅明的现代性体验与他自身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叙事相融合,达成了对现代性的完美表述。他将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地理空间的视角进行重释,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核(资本宰制一切、商品拜物教、区隔等)在1848年之前获得窥视。这种深究也为1848年之后奥斯曼的现代性“手术刀”提供了先在的潜意识的历史准备。
三、现代性之“实践”:奥斯曼的“三角测量塔”
对巴黎的表述不能替代其改造,巴尔卡克如此,社会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者也是如此。1830~1848年间巴黎出现了包括圣西门、傅里叶、普鲁东、勒鲁、孔西代朗等在内的各种路线论战,思想界动荡不安,各种视野与空想纷纷出笼,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也趋于成型。他们试图找出重建巴黎的恰当方法,并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巴黎,并且让巴黎成为自己的城市,“然而在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留给广大人民的只剩下失落与剥夺感。”②同上,第99页。
1848年,经历二月革命的抗议和六月革命的洗礼,最终在各方妥协下拿破仑三世登台并称帝建立第二帝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临。哈维认为,第二帝国试图建立一种混合独裁专制、尊重私有财产与市场以及民主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奇怪的政权组合形式,它粉碎了1830~1848年间关于身体政治的各种想象,拿破仑意图以男性与父权的形式召唤“皇帝双体”,确立环绕皇权来重构身体政治的概念以面对资本的累积力量。然而,现实终归是要面对的,问题不会因为谁占据了统治舞台而变得不同。拿破仑三世必须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可能的骚动。“例如改革与现代化、控制劳工运动及其诉求、搞活经济,以及让憔悴的法国从1848年到1851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病症中恢复元气……该实行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实践、制度架构和结构或社会投资……国家在私立和资本流通上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对于劳动市场、工业和商业活动、居住和社会福利供应等的干预程度。”③同上,第108~109页。而最难处理的是政治问题,既要让巴黎经济获得振兴,又要平衡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持政权的稳定。
因此,面对急速发展和索取无度的资本主义,新的帝国必须实行创造性的破坏,一方面可以创造出建国神话,另一方面有助于让人相信施行仁政的独裁帝国是唯一的选择。而这个重任唯有深谙皇帝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奥斯曼可以担当。
(一)奥斯曼的“三角测量塔”
“巴黎这座城市是以奥斯曼赋予它的形状进入这个世纪的。他用可以想象的最简陋的工具彻底改造了这个城市的面貌。”①[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161页。从1853年6月奥斯曼上台到1870年1月下台,巴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变。奥斯曼用专属于他的“三角测量塔”在大拆大建中实现了巴黎城的改头换面,难怪有人惊呼“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奥斯曼对巴黎城的空间改造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按照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弗朗索瓦兹·邵艾的总结归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②[法]弗朗索瓦兹·邵艾:《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Ⅰ》,邹欢译,《城市区域规划研究》,2010(3)。:
一是交通、供水与排水、呼吸:有机基础设施三大系统的改造。
第一,交通系统改造。道路网络是巴黎改造的核心,“奥斯曼很讲策略地分三步提出计划:第一步,先修造贯通城市南北和东西的‘十字轴’主干道;第二步,在十字轴的基础上修建其他主要干道;第三步是修建联通这些干道与新建市区的次要道路。”③张钦楠:《百年功罪推论说——评奥斯曼对巴黎的旧城改造》,《读书》,2009(7)。道路网将塞纳河两岸的主要地点和重要设施联系起来,东西和南北两条大轴线是网络的主干,斜向的道路和广场作为大轴线的补充,起到向次一级系统中心转化的作用。成果是惊人的,就铁路网来说,从1850年的1931公里扩展到1870年的17400公里,交通运量扩大为原来的两倍。与铁路系统相连的直线道路,交通流量也逐渐增加和改善。道路设施打通了巴黎内部空间、联络了巴黎与外省,也连接了国际市场。
第二,供水与排水系统的改造。当时的巴黎供排水存在很大问题,饮用水未经处理、下水道系统不健全等导致疾病如霍乱肆意侵扰,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令人堪忧。奥斯曼致力于打造一项现代化的庞大工程,首先在远处寻找足够水源(131公里外的杜伊河水引到巴黎城外的水库,获得瓦恩山区泉水的使用权),并能将其提升到足够高度,使其输送过程简单经济;其次,建设一个整体的供水网络。一方面把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开;另一方面通过拓宽已有城市排水管道,形成与供水网络相匹配的地下排水系统。
第三,呼吸系统改造。主要是“葱郁空间”,即“散步与植栽场所”的建立。弗朗索瓦兹·邵艾将奥斯曼的绿色空间工程分为三级,首先是城市周边森林公园,位于巴黎西部(布洛涅森林)和东部(凡桑森林)。次一级是位于城市内部的封闭公共空间,包括蒙梭公园、卢森堡公园、肖蒙高地公园、蒙苏里公园以及一些数量众多的公共小花园。第三级是一些开敞的、园林化的散步场所、绿化庭院、广场以及所有林荫大道。如香榭丽舍、女王庭院、王宫广场等等。绿色空间系统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加强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完美的结果。
二是独立设施与街区设施建设。
奥斯曼综合考虑历史、街区需要,修建了众多独立设施,如总屠宰场、歌剧院、商业法庭、国家图书馆、精神病院、老人院、大型公墓等等。同时,街区设施包括:学校、市政厅、信奉各种宗教的教堂。还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林荫大道两侧的“奥斯曼式”的公寓住宅,统一的门面和整齐划一的布局使整个巴黎看起来气派而典雅。
(二)“三角测量塔”背后的运行逻辑
从表面看,奥斯曼的巴黎大改造形塑了一个集私人住宅空间、公共娱乐空间、城市卫生空间以及便捷的出行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之都——巴黎,但透过连绵的工程,我们发现,“三角测量塔”是一个隐喻,其背后深藏的是现代性的运行逻辑,而这恰恰是哈维《巴黎城记》思考与写作的脉搏。
在哈维的视角里,“空间的生产”是第二帝国巴黎破解危机并得以存活的关键要素,而资本与国家的“合谋”或者说资本的“跋扈”则成就了奥斯曼,宰制了巴黎的现代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哈维提出他螺旋式的推演,“从空间关系开始,行径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①[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15页。
首先,空间的生产。哈维吸纳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空间的生产”的概念的分类及转变,并将其纳入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范畴之中。19世纪巴黎城的崛起,特别是奥斯曼主宰的大改造成为他空间研究的最佳案例。哈维认为,空间关系的重塑和空间规模的转变,就都市进程来说是主动而非被动的时刻。空间具有能动性、形塑性和扩张性,它不是被动的、收缩的和静止的。对于奥斯曼来讲,既要破除制约现代性发展的空间障碍,又要生产新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空间。空间的生产,对内主要是城市的扩张(伴随农村的去郊区化)和大规模的拆建工程,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等;对外主要是加强殖民侵略和大型运河类工程的兴建。通过内外空间的生产,一方面吸纳了大量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缓解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性巴黎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重要的实践之一就是空间的生产。
其次,资本的空间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动力是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控制,是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当代实践。”②董慧:《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哲学动态,2010(10)。面对第二帝国的各种问题,奥斯曼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这也是他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金融、信贷等体系下,巴黎过剩资本因空间的配置而获得自由流通。肇始于资本,运行于资本,最后控制于资本。表面上是皇帝、国家和奥斯曼控制了整个城市,但实际上“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资本便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也许还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到最后他只能成功地让巴黎成为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③[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23页。。
资本掌控着巴黎的新建,更主宰着现代性在巴黎的发展轨迹,新的城市风貌和熙熙攘攘的流动人群背后,掩饰不住的是资本的运筹帷幄。借助资本力量,巴黎实现了城市大改造,大换血,外在空间重构的同时带动了资本逻辑的空间生产。资本塑构了城市地理空间、历史空间、社会空间,更孕育了资本自身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的空间生产即资本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也透视着现代性运行逻辑。
最后,空间生产。空间的生产不仅生产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且生产社会关系、阶级分层、劳动分工、再生产结构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的生产必然造就空间生产,空间生产也形塑空间的生产,这或许是社会空间辩证法的逻辑。重点在于,奥斯曼对于巴黎的现代性空间配置与生产,不仅变更了巴黎的容颜,更让巴黎的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区隔。奥斯曼将工业区从市区迁往郊区,附带将工人阶级以及其他以出卖劳动为生活来源的阶级一并驱逐出去。市区高昂的租金让社会中下层阶级望而却步,左右岸的空间布局也将富人与穷人明显区分出来。“我来自哪个区”的信息几乎透露了个人所有的资料,包括出生、收入、社会地位、阶层、婚姻状况等。同时,大量的公共空间侵占了私人空间,因为居室家中是不能做饭的,大家聚集在咖啡馆、公园、酒吧等公共场所,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性的反叛提供了空间。空间改造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碎片化、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个体空间归属感丧失等问题。“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①孙荣、吴闪:《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城市改造——以巴黎改造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3(3)。
总之,在国家与资本的裹挟下,奥斯曼的“三角测量塔”发挥了“开膛手”的作用。他的空间改造,改造的不仅是砖瓦和管道,房屋和道路,城内与城外,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造”与奠构,是建筑材料与关系材料的有机整合,是城市与人的重新区隔与定位,是资本、市场与国家的裹挟与“合谋”。哈维将重点放在第二帝国巴黎改造时期,研究的不仅仅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奥斯曼改造项目,而是将改造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从发生学、实证主义和历史叙事视域阐释现代性的诞生。
四、现代性之实践脉络
从某种角度看,城市的发生学即是现代性的发生学。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讲,19世纪欧洲大都市空间的拓展与修复既表征着城市本体论意义上的进步,又同时演绎着现代性的实践逻辑。哈维关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的阐释与本雅明19世纪巴黎的现代性体验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都抓住了“现代性”这个关键词。而且,哈维在宏观解构的同时,也借助巴尔扎克、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获得了微观的体验。因此,透过《巴黎城记》,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实践逻辑。
(一)表述与行动
现代性既是表述性的,同时也是行动性的。表述包含着主体性的思维建构、客体的现实意象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当客体被表述的时候,主体已经完成了对客体的感性/理性分析,因此,表述既带有深深的客体再现,又带有强烈的主体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性最敏感的群体莫过于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因此,在哈维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画家杜米埃、摄影家马维尔等等,在他们或小说或诗歌或绘画或相片的呈现形式中,现代性的特性显露无疑。作为哈维表述现代性的“中间人”,巴尔扎克无疑是主角中的主角,他解开了现代性的神话,通过《人间喜剧》勾勒了巴黎现代性的地形图,并让现代性的性格以及与现实的矛盾抗争都获得表述,这种表述包含了巴黎文明进程的积淀,也析视着现代与传统之间“向前—向后”的拉力和推力。当然,巴尔扎克之后还有众多浪漫主义者和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如圣西门、傅里叶、布朗基等的思考与纠错,甚至还有第二帝国之前执政者的考量与准备。然而,表述毕竟仅仅是表述,它更多是建立在个体自我建构与解构的空间中,如巴尔扎克一般肆意穿透、期望,但始终停留在意想和故事的勾勒之中。现代性需要的是实践与行动,是想象叙事之后的付诸实际。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之下,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调集了资本、金钱、土地等展开了破旧立新的城市空间大改造,开始了现代性的践行之路,自此,巴黎才真正配得上“现代性之都”的称号。表述与行动的逻辑达到“和谐与共”,巴黎新城的崛起,印证了现代性不是停留在小说故事中的憧憬,而是架设在巴黎旧城废墟之上的“三角测量塔”,是行动的现代性。。
(二)决裂与延续
从奥斯曼的手笔来看,巴黎的现代性之路必然是与过去的决裂,必然是一个绝对的全新的开始。正如哈维在开篇导论中所说,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在于它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但是,真能做到完全的决裂吗?奥斯曼在潜意识中自我否认,因为对巴黎的很多改造在第二帝国之前就开始了。哈维将改造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其意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不是完全销毁旧的社会,而是在废墟中拔地而起,是过去历史的延续。因此,正如“希望是欲望的回忆”所表述的隐喻一般,决裂表征的是现代性“动作”的猛烈程度,而非绝对的断裂。恰恰相反,现代性是在秉着决裂的姿态延续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是法国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哈维的阐释告诉我们,从表述到行动的巴黎现代性是一个连续的发生学叙事,既是历史的必然轨迹,同时也是有别于历史的全新开始。决裂是在续承过往之上的决裂,连续是在决裂之中的延续,现代性是延续与决裂的有机统一。
(三)资本与空间
奥斯曼进行大刀阔斧的空间生产与修复,背后离不开资本的运作与流通。哈维认为,空间的生产必然是资本的生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运作必然是资本的空间与空间的资本相互勾连的结果。哈维援引马克思指出,“生产越是仰赖交换价值,乃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运输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于以时间来废除空间。”破除旧的空间障碍,新建新的空间区隔,通过时间的修复来达成资本的空间流通与时间流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在国家、资本与空间的“合力”下,历史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通道被快速打通,三者在现实空间中糅合、杂混,互相演绎“生产—再生产”的逻辑。“时空压缩”不仅出现在巴尔扎克表述性的现代性中,也出现在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中。巴黎城正是在时空压缩的节拍中逐渐走向世界,成为19世纪国家化的大都市,现代性之都的典范。
总之,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向我们诠释了建立在流动的资本、活动的空间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巴黎。从中可以窥见,现代性从表述到行动(“三角测量塔”是行动的隐喻)、兼具决裂与延续的运动轨迹,其间,资本与空间以及“时空压缩”是其内在机理。当然,空间和资本的深入解构在阐释现代性运作逻辑的同时也暗含后现代批判因子,只是哈维的这种批判带有极强马克思主义印记,因而对资本主义批判始终是其终极要义。
值得商榷的是,哈维凸显了现代性的“速度”和“大刀阔斧”改造的阵仗,却或多或少忽略了处于文明进程中的巴黎,特别是法国宫廷社会礼节、典仪、品味、服饰、习俗等对巴黎现代性的历史影响。关于这一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和《文明的进程》中有过深刻阐释。在他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经过,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作为“构型”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 ”长期的宫廷“构型”形塑着巴黎人,无论个体做何改变,“构型”却以较为稳定的力量延展着文明进程,除非内部力量失衡(法国大革命即是力量失衡的结果)。如果说现代性是文明进程的过程之一,那么19世纪巴黎现代性之都崛起的因子中必然有法国历史的影子,特别是宫廷礼仪形塑下的上层与下层社会之间的文明互构。哈维关于现代性的表述和行动勾连了“现代性之前”与“现代性之中”的巴黎,却唯独缺失了现代性之前的“之前”的历史性因子。因此,把哈维的现代性实践逻辑与埃利亚斯宫廷社会的文明实践相融合,将有助于更好诠释现代性之路。
An interpretation on Another Thread of Modernity’s Practice—Comments on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by David Harvey
GUO Zhi-qian
Modernity is an “artifi cial”rational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mode that formed by disembodying itself from nature, and in fact,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modernity is hidden in the puls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 is displayed through the urban space’s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19th century. David Harvey’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ris city show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Modernity, which lies from “statement” to Osman’s “triangular measuring tower”, and from the space action to the space language. In Harvey’s picture of geography space, the modernity is not only a kind of descriptive picture, but also a creative destruction by itself; the modernity not only has a feature of rupture, but also a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uity; the modernity is not only the fi eld of the conspiracy of capital and space, but also its outcome. All of this have construct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modernity of Harvey and Paris, and also have sketched the practical texture of modernity.
modernity; practical logic; space; statement; triangular tower
郭治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焦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