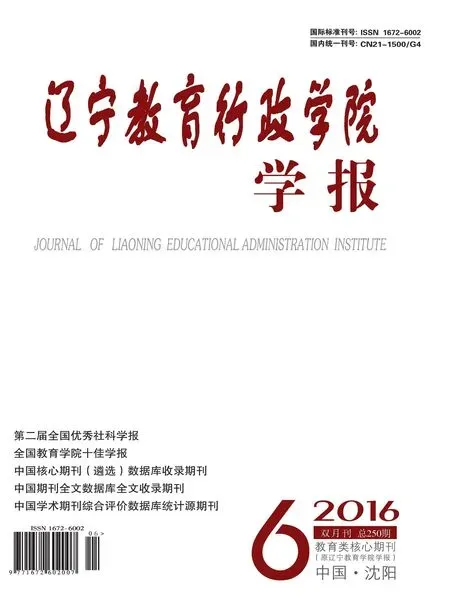芦焚文艺观分歧的原点
——由王任叔对芦焚的评价说起
程振慧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芦焚文艺观分歧的原点
——由王任叔对芦焚的评价说起
程振慧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芦焚与“京派”和“左翼”的关系涉及作家的文化身份归属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但要注重作家的外部活动,更要在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中,找出作家在文艺观上的表达。主要从时代情境中王任叔对芦焚文艺观理解的分歧点进行研究,认为正是王任叔在评论中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淆,主观上造成对芦焚作品风景和事物理解的二元分离,才形成了对芦焚京派和左翼文化身份的混淆。
芦焚;文艺观;文化身份;分歧
芦焚生于河南乡村,游走于北京和上海大都市,曾获过京派组织的《大公报·文艺》“文艺奖金”,也与左翼文人交往共同编辑《尖锐》杂志,艺术表现上同时兼具左翼和京派的特色,而所有这些矛盾把研究者的兴趣点最终都引向了芦焚的文化身份,是左翼还是京派?对于二者不同的归类,显示的是作家不同文艺观问题。早期的一些研究注重从文本分析把芦焚与沈从文作对比,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芦焚的“京派”归属也暗含了他“似京派”的性质。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芦焚表现一二·九运动的新史料、早期散轶文章被挖掘,他早年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体验也被重视起来,这样芦焚与左翼的关系似乎逐渐明朗,甚至有些学者推翻早期“京派”的言论,注重从报刊杂志的研究中重新发掘芦焚的左翼身份。①芦焚是京派还是左翼呢?最早对他的评论有京派李健吾的《读〈里门拾记〉》和左翼杨刚的《里门拾记》,两人都注意到了芦焚对人情世态和景物的描写“田园景色美好背后是人事的丑陋。”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其流派的归属,这样的观点似乎也说明着芦焚文艺观兼具“京派”和“左翼”不甚明确的特点,但两人并没有把这种含混性当作作者的独特性,反而是作为其文章技巧不成熟的缺点指出的。
那么把“诗意”和“人事”作为两种文艺观分离以证明其分别属于“京派”和“左翼”的归属源于何处呢?
一、“风景”概念置换中“老庄”哲学观的形成
芦焚1988年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两次去北平》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证据。
“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编写《中国小说史》,准备把我归入“京派”,并举李健吾、朱光潜两位的评论文章为例,认为我是“京派”后起的佼佼者。我的记忆力极坏,记不得他们文章中有此等话;犹孔记错,找出两位的文章重读,结果果然没有。只有王任叔同志讲过我‘背后伸出一只沈从文的手’。王任叔写别的文章,可能是位好作家,他对我的评论,我却不敢恭维。因为他只急于写文章,根本没有看懂。”[1]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芦焚对于自己的“京派”归属并不满意,在很多文章中他也表示了自己对流派划分的意见。第二,王任叔的看法成为了作家流派划分分歧的起源。第三,芦焚把王任叔的误读归结为其急于写文章。
我们暂且先搁置作家自己的态度,先看对于芦焚文艺观理解分歧的起源。王任叔1937年8月1日在《文学》第九卷第二期发表了《评<谷>及其他》,在其中他多次提到芦焚与沈从文的关联,但他所谓的“诗意”和“织绘”超出了刘西渭和杨刚文章中把编织作为作家在景色描写技巧上认识,而上升到了作家“一任自然的哲学观”在对《寻金者》和《落日光》人物的评论中,他把重点放在了人物感情的描写上,对芦焚描述人物的苦闷心态十分不满,而他的期待则是把个体的苦闷心态转化为社会性的活动。联系王任叔左翼的身份,很明显这是对普罗文学中战斗“号角”叙事的一种呼吁。此外,王任叔认为:
“作者过分的强调爱情的悲剧,即将家道的兴隆与衰败来个显明的对照。仿佛一切现象,不是人混合在这时代的潮流跑去,而是将时代一一变成化石,任他跌翻着过去,他与时代无关,时代更不能影响他,出去时是那么一颗感伤的心,回来时却还是那一颗感伤的心。……心理主义者的唯一手法,便是将社会的实相,涂上了幻想的烟云,以美丽代替了血腥。而我们沉醉于诗样的温馨里的批评家,却名之曰:善于织绘。”[2]
在这里王任叔把人物身上能力的薄弱、感伤情调的不变性,作为作家是受老庄思想中自然哲学观影响的根据,而他所谓的“织绘”也不仅限于景色的描绘,而成为作家对人物描写的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哲学态度。这样的理解从作品中人物对现实处理的消极结果上,似乎确有其合理性。但在论述中王任叔似乎有意把人物行动后的消极后果,置换成人物在现实中缺乏行动的能力。正如他把时代比作化石,把主人公出去和回来都保持不变的原因看作是其与时代分离下的不作为。显然,在王任叔看来芦焚自然哲学观便是一种与时代隔离的不作为、缺乏行动力的态度,一种自我情感的独语。这种方式俨然是对“京派”、“新月派”文艺观批判的一种翻版。
30年代抗战的背景不容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在迷恋于自我的情感之中,京派和新月派等自由主义者提出的闲适、幽默的文学主张被处于批评的地位。王任叔对芦焚的评价恰恰从侧面印证着芦焚“京派”的身份。其实在芦焚的很多小说中,时代的因素并没有减弱,也不乏与现实相关的行动者。《寻金者》中贫穷出身的朱珩在自卑心理下,企图寻找能够超过环姑的城里少爷表兄的财富来迎娶环姑;《落日光》中“有福的先生”确实如王任叔所理解的满怀着不知所以然的爱情流浪,又“高昂着心理的追怀情调”回来,但却并不像他所说的主人公与时代无关,时代已经让他从“吃闲饭”二爷变成了被小辈们害怕抢去遗产的“老流氓”。虽然他们行动后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但贫富转变的时代特征却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在《落日光》中,现实的悲剧并没有被作家生物学存在的感伤所掩埋,恰恰是通过其表现了出来。就连芦焚自己也曾在杂文《作戏文学》《幸亦不幸》中讽刺京派与新月派“超人”的态度。当然,王任叔也并没有完全忽略芦焚对现实的描写,他对芦焚的《谷》有着高度的评价“这里作者有他清新的朝气,有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但他对现实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乡村、家道衰败的外部景象上,而忽略了世态作为现实社会内部的一部分也在改变。这样,内外部的分裂作为了他解释芦焚笔下“乡村虽然衰败了,却没有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记”的有力言说,也成为了论证芦焚自然主义哲学观的有力证据。甚至于在时代特征明显的《牧歌》中,印迦拿起枪来反抗当权者和帝国主义剥削斗争的精神是鲜明的,老人、妇女全都投入抗争中有着强烈的阶级和斗争意识。而王任叔却又拿作家对风景编织的诗意,来说明“诗意将时代的风貌模糊了”显然,王任叔在这里又把“织绘”定义为作家对自然风景的描绘,这样在“织绘”定义的互换中,作家对风景的描绘就等于老庄不作为的自然主义哲学观。在对二者之间的必然关系论述中,他也就忽略了作家对故事叙述的核心内涵,夸大了风景编织的作用。
二、主观理念预设上文艺观的强说
在文艺学上,自然风景是以一种客观性、空间性存在的。正如日本学者所认为的“自然或环境作为用语给人以‘场所’的印象”[3],它不仅承载着空间的成分,也与自身的建构和社会现实相关。特别是当外在风景与现代性相结合,风景就不单单成为了一种外在视域上的表现,也超出了个体精神内化的形而上的意境指向,更成为了一种“把绘画和纯粹的‘形式视觉性’的作用去中心化,转向一种符号和阐释学的办法,把风景看成是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主体的一个寓言。”可见“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现代性和政治共同成为风景新的呈现方式。在只注意到风景呈现的表层,这样互换中的概念是不科学的,王任叔是否注意到这样的不科学性呢?
“芦焚先生也曾一度徘徊过人生的闹市,也看过若干时代的风貌,听过悲泣与哀号,碰过阴险与狡诈,在他浅灰色的衣衫上,也留下过小小的血迹。这里是《谷》,《金子》,《鸟》,《头》,《落雨篇》。”[2]显然,他也注意到了作品中风景编织下的世态内核,也曾不止一次提到作家对现实的正视和憎恶,但他却在自己早已预设作家是名士才情的前提下,把这些描写归结为是作家“‘织绘’的工作上不可少的‘风趣’”。这样,在王任叔主观的理论中,现实成为了风景的一种附庸,他把社会现实的客观成分舍弃,夸大风景作为人思想载体的作用,自然风景仅仅停留在了古典美学之上。彻底颠倒了刘西渭和杨刚所认为的风景作为描写现实技巧的运用,而把风景文艺审美性提高到了作品核心内涵的地位。韦勒克说“诗人的意象是他的自我的揭示”。[5]在芦焚的文章中大量风景的意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心境的外化,而更多却来自现实的映衬。芦焚生长于天灾人祸频发的河南农村,昔日繁盛的文化古都早已衰败,而他的老家化寨村更是千疮百孔废墟中的一角“那样的地方连一天也不能住。”附近通火车后,便如塞绝了来源的黄金小瀑布般日见萧条空阔的街道(《酒徒》);荒凉萧条的百顺街(《百顺街》);回荡着凄厉恐怖的毒咒的毕家废墟(《毒咒》)将这些故事的背景联系起来看,就是这样一幅现实的图景:灾荒匪乱,土棍恶绅,外来殖民的入侵,农村到处是空宅、弃园、荒地、废墟和瓦砾断墙。即使是柔和的风景下伴随着的依然是战争、失家的背景,正如大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反田园诗”的叙事。《过岭记》中小茨儿健美的人性却回应着战争的背景,《巨人》中抓离家的背后却是阶级差异下生存的困苦。《哑歌》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日夜盼望着义勇军的到来。为了废除“保甲”制度,他还把《无名氏》序言写成了带有强烈政论性质的文章。而来自王任叔主观形成的理论,把芦焚风景描绘中社会、政治的部分剔除只保留了文化审美的性质,在这样的批评范式中自然会出现矛盾性,正如他在评论《牧歌》时所说“作为一种寓言,作为一种情绪的鼓动,我们的作者是借这牧歌,做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我们却需要更有理性的反抗啊!”[2]而寓言是左翼的一种典型的描写手法,作为一种左翼理念的宣传,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承认了作品寓言和鼓动性似乎就承认了作品的现实性,在这里“牧歌”也被重新作为了现实描写的技巧和手段,而不是文艺观来理解,但为了重新回到自己前文的论述,他不得不忽视作品中真正的时代内涵,在结尾做出无力的呐喊“我们需要的是更有理性的反抗啊”,含糊其辞地把其认为作家远离时代的原因,直接归结为作家对社会机构想象的简单,对反抗想象的简单。
由此可见,自王任叔对芦焚的评价开始,风景与世态作为现实主义内外两部分开始被分裂,在研究者主观理论预设的“织绘”概念的转换中,风景编织的概念被夸大为了作品的核心,风景的描写也由技巧的运用,成为了作家“自然哲学”的文艺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的混淆,使“美好景致与人事丑陋的对峙”[7]也成为了以后研究者对作家“归属”问题划分,采取二元对立文艺观的原点。
注释:
①马俊江在早期的论文《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中把芦焚定位成“京派”。在《〈尖锐〉〈毁灭〉和〈铁流〉:1930年代文艺青年的转向、聚集和文学范本——从师陀的一篇轶文说起》中又从史料上把芦焚定位为左翼青年。
[1]刘增杰.师陀全集8[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9).
[2]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
[3](英)达比著.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4]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5]闻丽.师陀散文化小说文体论[D].山东大学,2011.
(责任编辑:武亮)
程振慧(1990-),女,河南濮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
2016-10-29
I20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