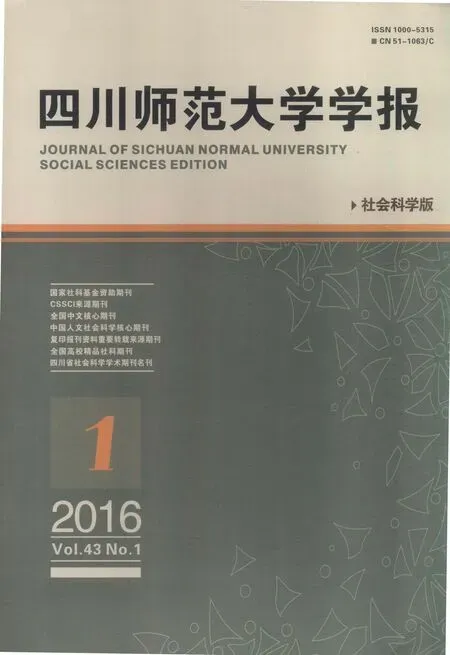教学视野中的师生关系——兼与刘艳侠博士商榷
周 序,李 芳
(1.厦门大学 a.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b.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综合研究室,北京 100816)
教学视野中的师生关系——兼与刘艳侠博士商榷
周序1a,b,李芳2
(1.厦门大学 a.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b.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综合研究室,北京 100816)
摘要:师生关系是否疏离,不在于教师是否传授客观知识,而在于传授知识的技术高低;对知识的自我建构,也不至于让学生盲从于师;追求“整全”的理想,由于抽离了客观知识,因而难以实现。教学不是割裂的,应该在客观知识的基础上追求“整全”。师生双方也不能是纯粹的“友伴”关系,而只能是“亦师亦友”。
关键词:教学视野;师生关系;“亦师亦友”

李芳(1983—),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
师生关系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师生双方之间的亲疏远近,往往影响到课堂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发表了刘艳侠博士的《不同知识类型学习中的师生关系》一文,文章指出:知识学习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师生关系。很多大学的课堂偏重于客观知识的教授,这会导致师生关系的疏离;也有老师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建构性的学习,但这种课堂面临着学生盲从教师的风险;只有当师生双方作为友伴,在对话中共同学习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良好的师生关系。文章观点鲜明、分析深入,令人印象深刻,但所表达出的一种忽视教师地位、轻视知识价值的思想,却难免令人存疑。该文对良好师生关系的展望也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局面。故笔者略抒浅见,向刘艳侠博士及广大教育工作者求教。
一疏离:客观知识之学的必然结果?
刘艳侠博士认为,在以客观知识为核心的教学当中,传授知识成为教学的目的,“学生往往作为容器而存在,把知识装进大脑即为教育的成功”[1],在这种情况下,师生双方的个性、特征、精神、品格,都湮没在对知识的无限崇拜中。
刘艳侠博士对知识传授的理解,受雅斯贝尔斯的影响颇大。她引用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的话说:客观知识的传递“对学生精神害处极大,最终会将学生引向对有用性世俗的追求”[2]5,因此她反对基于客观知识的教学,认为传授客观知识的教育是一种功利性的教育,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教师也仅仅是学生学习的工具而已。但是,如果刘艳侠博士肯耐心地将《什么是教育》这本书向后多翻几页,就会发现,雅斯贝尔斯继续写道:“大、中、小学教师都有责任维持秩序和形式,以使世界的精神财富流传下去。”[2]54所谓“精神财富的流传”,当然是指人们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客观知识的教学了。雅斯贝尔斯甚至还认为:“谁要是不知古希腊罗马,谁就仍停留在蒙昧、野蛮中。人们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整个的一生。”[2]56这样看来,客观知识在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理论中非但不是一无是处,反而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雅斯贝尔斯真正反对的,其实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不是客观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而是我们不能“以正确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2]149。
刘艳侠博士显然对客观知识的传授有一个误会,她认为,客观知识的学习就是记住一些现成的结论和答案。但事实上,客观知识的学习绝非停留于“记住现成结论”的层面,而是作为下一步学习的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新经验的产生只有在原有认识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经验作为一种观照,总是建立在已有的结构之上。对于一个完全无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就无法清楚地向他展示所认识的对象。”[2]88无论是学生思维的发展、能力的提升,抑或是获得刘艳侠博士所说的“成人品格”,都离不开扎实的知识基础。在号召大学要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今天,知识的大量积累更是成为大学生们进行研究和创新的前提,而创新也从来不是空洞的,也必须“依托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几乎不存在无知识的所谓创新”[3]。
那么,基于客观知识的教学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师生关系的疏离呢?刘艳侠博士认为,当教学以知识传授为己任的时候,教师与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知识而非关注彼此,因此师生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疏离的。她认为:“教师与学生同在一间教室共学一门课程,教师在教,学生在学,换任何一批学生和任何一位有专业知识的教师都不影响教学。”[1]然而,恰恰是这一举证存在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同样是教国学,于丹的讲授就会比很多老师的讲授更让学生觉得华美隽永,流连忘返;同样是读《三国》,易中天的品读就会比其他老师更加幽默,更能让学生开怀大笑;同样是在讲“教育学”的知识,钱志亮的课程就比其他很多老师开设的“教育学”课程更受欢迎。无论是于丹读《论语》,还是易中天品《三国》,抑或是钱志亮讲解“教育学”,都只是在向学生介绍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法或者一些已经得到验证的共识,但他们的课堂教学质量比别的老师高,他们本人也更受大学生的欢迎——于丹在2008年被评为北师大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一;而易中天早在他还任教于武汉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了;至于钱志亮,他的“教育学”课程频频让众多选课生和从其他高校慕名而来的旁听生挤破了头。很显然,这说明当大学课堂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时候,学生并不是只关心知识,更不是如刘艳侠博士所说的和教师之间“并未真正地发生关联”[1],实际的情况是,老师教得好,学生欣赏这位老师,就可能对知识产生兴趣,从而产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可见,在知识教学当中,学生和教师之间完全可能存在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当然,现实当中师生关系疏离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刘艳侠博士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并从知识教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是其研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她将关注点放在了“知识”上,认为只要是传授“知识”,就必然导致师生关系的疏离,却没有考虑到“教学”的水平有高低之分,教学水平的差距同样可能带来师生关系的亲疏有别。在当前大学讲坛,很多教师在进行知识传授的时候大都只是在读讲稿或念PPT,即便是一些名家泰斗,其教学水平也屡屡遭人诟病。孙绍振先生曾形容北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王力先生、王瑶先生和杨晦教授的教学是“茶壶煮饺子”,“余音袅袅,杳不可辩”,“口中含有热豆腐”,“草草停课”等[4]。这段评述还得到了邢红军等人的认可,被认为是“虽稍有不敬之嫌,但亦拿捏到位,分外传神,想来应当丝毫不会冤枉诸位”[5]。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或听之乏味,或不知所云,即便偶尔听得只言片语,也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说这些老师上课的时候没有关注学生,学生也不愿关注老师,并不过分。但这与其说是因为这些老师传授的是客观知识所以导致了问题,不如说是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存在问题。试想,当老师们的教学令人不敢恭维,甚至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的时候,师生之间何以建立良好的关系?相比之下,我们太缺乏诸如于丹、易中天、钱志亮等擅长教学,并因此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爱戴的老师。总之,师生关系是否疏离,并不取决于教学的内容是不是客观知识,而是取决于教师传授客观知识的水平如何。
二盲从:建构知识之学的潜在危机?
刘艳侠博士认为,大学生的学习,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所收获的客观知识,更在收获知识的过程之中。因而,与其从老师那里获得现成的客观知识,不如跟着老师学习做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收获知识。这种类型的学习被刘艳侠博士称为建构知识之学,在她看来,基于建构知识之学的教师之教要比基于客观知识之学的教师之教更加进步。但即便如此,这种教学却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危机,即学生在跟随老师做研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很有可能导致学生对教师观点或看法的盲从,“可能导向学生以师见为己见的后果,在对教师的尊重与爱戴中偏离了对整全知识本身的追求”[1]。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建构主义虽然派别林立,有学者甚至认为“有多少建构主义者就有多少建构主义”[6]261,但不论是何种建构主义,都强调不同学习者基于自己不同的经验背景建构出对外部世界的不同理解,都提倡学生的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因而,建构知识之学应该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因而也就与“盲从”无关。这种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建构知识之学,怎么会让刘艳侠博士觉得让学生面临着“盲从于师”的危机呢?
仔细分析刘艳侠博士所谓的“建构知识之学”,可以发现,原来,作者认为的“建构”,指的是“从游于师”。她引用梅贻琦的话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7]325也就是说,“从游”意味着身教重于言传,学生对教师长期的耳濡目染,就是让学生“从游”于师的有效途径。我们愿意相信,一个儒雅、向学的教师,很有可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并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作者所说的亲密关系。但亲密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学生得以主动“建构”知识的充分条件。常能听到大学生在评论某些知名教授的时候认为:某老师学问做得好,值得尊敬,但年纪尚轻却已华发初生,皱纹上额,因此“我只是崇拜这位老师,但并不羡慕这位老师,因为我不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亲密关系虽然建立,“从游”却并未发生。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自觉自愿地跟随老师一起探索真知呢?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应该使“越来越多的成人能够去感受知识和个人自学带来的乐趣……唤起对知识的好奇心”[8]76。苏霍姆林斯基也告诫教师说,应该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9]142。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发自内心地对知识感兴趣、产生探索的欲望,才能激发出他们自主建构知识的热情。如果学生只是看到教师如何在知识探索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废寝忘食,乃至疾病缠身,却感受不到知识的魅力,感受不到求知过程中的充实和幸福,自然就难以产生“成为像老师这样一个人”的意愿。
遗憾的是,刘艳侠博士并没有在如何挖掘出知识的魅力上进行探索,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教师的“行为”,她引用欧克肖特的话说:“并非野鸭的叫声,而是它的腾起,推动一群野鸭跟它一起飞行。”[10]63刘艳侠博士认为,当教师在求知的行为上做出表率之后,这种行为就“胜过任何语言的唤起与激励,它无声而坚定地说‘请跟我来’”[1],从而让学生自觉自愿地跟随教师学习。强调行为上对教师的跟随,抓住了建构主义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把学生当作“知识建构的主体”[11]。但仅有主体性,还谈不上是建构主义。不论何种派别的建构主义,在强调知识是学生主动建构的结果方面并无二致。所谓主动性,意味着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绝不像野鸭群随着领飞者腾飞一般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要有着自己的兴趣、意愿和动机以及自己的思考、判断和分析。由于每个学生个体在动机、兴趣、思维特点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在建构主义看来,每个学生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事物的某些方面,不同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侧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的理解,甚至“我们应当期盼并酝酿差异性”[6]385。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建构主义的教学当中,学生的收获是基于自身经验的建构过程,得到的是个性化的见解,自然也就无所谓盲从了。不然,我们何以理解与柏拉图亲如父子的亚里士多德怎么会说出“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这样的名言!?
建构主义是否适合在高校教学中普及,目前尚无定论。由学生建构知识是否真如刘艳侠博士所说要优于传授客观知识,也还见仁见智。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建构主义绝不应该只是耳濡目染,也不应该是“从游于师”,作者错会了“建构”之意,因此才会将“盲从于师”视作建构主义之学的潜在危机。如果我们清楚了解建构主义的特点,就会发现,这样的担心多少显得有些杞人忧天。
三共游:也许只是镜中花?
刘艳侠博士认为,理想的师生关系只能在“共游”当中产生。所谓“共游”,意味着教师不是以知识占有者的身份来传递客观知识,也不是以领路人的身份带动学生“从游于己”,而是要放下身价,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共同研讨、共同反思、共同进步。这样,“教师虽然仍是教师,但同时亦加入学生的行列;此时的教育成为动态‘成人’历程,在对真知的无限追求中,师生一起认识到自己作为未完成的存在,共游向整全之知”[1]。这样,师生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纯粹友伴般的关系,这种纯粹友伴关系中蕴含的平等教育理念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自然让人向往。
问题是,刘艳侠博士所谓的“共游”并非可以无条件实现的,而是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学生应该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意愿;二是学生要有得以与教师“共游”的能力,即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能够和教师搭档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这两个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呢?
对于第一个先决条件,刘艳侠博士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分析,仅仅是笼而统之地提了一句“大学中的师生往往有了一定的研究兴趣”[1],但这样的判断显然经不起实证数据的质疑。《中国教育报》曾报道说:“在高校,对专业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不在少数,有调查发现,近60%的大学生正在读着与自己兴趣不相符的专业”[12];一份针对数学学习兴趣的调查发现,仅有8.3%的大学生对高等数学课有着浓厚的兴趣,表示“一般”和“无兴趣”的比例分别高达46.6%和45.1%[13];而一则针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调查则发现,在大学生考过四级之后,对英语学习依然抱有兴趣者仅为33%[14]。当大多数大学生都对自己所学课程不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奢望他们可以与教师一起“共游”、携手钻研学问?布鲁贝克曾经告诫我们,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是“为了学术本身从事学术研究”[15]89。由于“学生是大学的来去匆匆的过路客……不是象教师那样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15]39,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所有大学生都视作自愿投身学术的群体,当然也就不能把他们都当成是有足够兴趣和教师一起“共游”于学术之海的未来学者。
对于第二个先决条件,刘艳侠博士也显得较为乐观。她认为,韩愈早就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所以师生双方没有地位高下之分,因而完全可能“成为彼此教化和共同成长的友伴”[1]。笔者认为,这是对韩愈这句话的一种误读。韩愈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可见韩愈认为得以为师者,不在于其生卒年月,而在于其“道”,所师者之“道”,显然应该是要高于自己的,如果老师的“道”并不“贤于弟子”,那又何来“师之”的必要。那么,韩愈为什么还要说“师不必贤于弟子”?联系前后文,我们可以发现,韩愈的本意其实是说,在某些“术业有专攻”的领域,师傅的造诣应该是要高于弟子的,因此孔子才会“师郯子”,即便从整体上看,“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因此,我们对韩愈的这句话不能作片面的理解,武断地推断说韩愈认为老师和学生在任何方面都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相反,韩愈恰恰是在强调师傅在师生双方共同关注、共同研究的领域内的水平造诣应该高于弟子。
也许刘艳侠博士会质疑说:还有布鲁贝克呢?布鲁贝克不是说过,“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在于其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其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15]13吗?这难道不能说明师生双方应该以平等合作的方式“联合起来”吗?遗憾的是,布鲁贝克想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布鲁贝克看来,“学生仅仅是初学者,他们还不是足够成熟的学者,因此不能充分享有学术自由。在他们的学习期间,他们应该被看作学徒或者是学术界的低级成员,正在发展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方法和习惯”[15]53。既然学生还“不够成熟”,甚至都不能享受充分的学术自由,说明他们无法和教师共同承担起研究高深学问的任务;即便有所承担,那也只能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的承担。从这个意义上看,布鲁贝克所谓的“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并不是说学生在学识和研究能力上已经和教师平等,而是指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既可以和老一辈人共同研究,也能从老一辈人身上汲取知识和养分的平台。
既然并非所有学生都有研究学术的热情和意愿,而有热情、愿意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也离不开教师的帮助,那么“共游”一说也就无从谈起。其实所谓“共游”,我们并不陌生,它本质上是一种绝对化的师生平等观念,即认为师生双方在人格、尊严乃至知识储备、研究能力、观点深度上都没有先后之分、优劣之别,都是“平等”的,享有同样的话语权。但如果教师和学生在思想层面都难以区分出深刻还是浅显、全面还是狭隘的时候,还需要教师吗?还有必要教学吗?有些激进的观点主张“不断用崭新的话语取代传统的、权威的话语”[16],而对“崭新话语”的合理性、合法性只字不提,或许就是误将“师生平等”理解为“知识、思想层面的平等”所致。教师之所以在知识储备、研究能力等方面应该拥有权威,就是因为他在所教授的科目方面投入了比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比学生更多的劳动,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普遍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在师生关系中,教师毫无疑问地应当在知识、能力、方法等方面扮演着权威角色,这也是师生关系区别于其他人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教师的权威角色并不排斥学生与教师一起交流、探讨和互动,但同时这种权威性赋予了学生向教师学习的权利,也赋予了教师指导学生的义务。否则,我们何以区分这到底是师生关系或者只是研究所里的同事关系?教师的权威不是不可以批判,但这一批判应该理性,应该建立在向教师虚心学习的基础之上。因而,理想的师生关系不应该是刘艳侠博士所说的一种纯粹的“友伴”关系,而应该是“亦师亦友”。当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陪伴、相互鼓励的时候,他们是友伴;而当学生在向教师求取知识基础、研究经验的时候,他们是师生。这样看来,刘艳侠博士所倡导的师生之间纯粹的“友伴”关系,便多少带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忘记了“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教师的历史使命。
四割裂的教学与整体的教学
刘艳侠博士对师生关系的研究之所以难以让人信服,是因为她略显僵化地将原本内涵丰富的教学活动划分成了客观知识之学、建构知识之学和整全知识之学这三种成分单一的形式,三种教学类型之间互无关联,甚至基于客观知识的教学还会妨碍学生整全知识的发展。如果这样一种类型划分是成立的,那么抛弃知识和建构,直接追求“整全”,便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但究竟何为“整全”,刘艳侠博士并未进行清晰地说明,仅仅提出要追求整全知识,就应该让学生“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活出自我”、“追寻生命高度”[1]。这样一些提法因缺乏实在的内容而显得有些不可捉摸,难以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有客观知识的传授,最好也不要有建构性知识之学,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整全之知”。如果说这样一种追求“整全”的课堂也给客观知识留下了一点空间的话,那么客观知识也不能通过教师的教授传递给学生,而是只能让学生在追求“整全”的过程当中通过与老师的共同探索获得。这样的教学,有诗一般的意蕴,也充满了人性的关照,但却显得不好把握,当然也不是那么便于操作。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教学,有实现的可能吗?
教学当中能不能脱离客观知识,直接追求“整全”?正如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大厦的宏伟和忽视了地基的价值,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可以为大学生的发展提供更高的起点和更宽阔的平台。客观知识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需要事事都去亲身经历。正因为如此,雅斯贝尔斯才会告诫我们:“如果有人想把传授知识的机构与教育机构分开来,就大错而特错了。”[2]149客观知识包含了前人长期研究获得的经验成果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研究方法和规则,这些东西不可能轻易地就被单个的、自发的探索打破,因此,客观知识自然是高高在上的,并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即便基于客观知识的教学可能出现作者所说的师生双方都只关注知识本身而不关注人的局面,但是如果想要创造新的知识结论,或者打破现有的研究规则,也必须先学习和了解这些知识和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教学,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不管是讲授为主的课堂还是探究为主的课堂,都只能是在客观知识的基础上追求“整全知识”,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获得人的发展。纽曼所说的“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17]59,也正是这个意思。保尔森等人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18]52,这已经非常接近刘艳侠博士所说的“整全之知”,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必须“通过不受限制地学习科学,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19]8才能实现。将知识学习和人的“整全”发展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割裂的思维方式。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场所,一直都是通过传授知识、研究知识来培养人,而非在“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当中二选一。因此,大学教学中根本就不存在单独的客观知识之学、建构知识之学,亦或是整全知识之学。传授学生一定的客观知识,是为了促进学生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发展;要发展学生的“整全之知”,也必须让他们拥有坚实的知识基础。脱离了客观知识的教学来追求整全知识的掌握,这样的教学至今还不曾出现过。
教学不能是割裂的,教学方法自然也不能是孤立的。刘艳侠博士非常推崇对话法,甚至认为“整全只有通过对话才可能出现”[1],表达出一种排斥其他教学方法的倾向。这或许是因为她将师生双方视作在研究过程中地位能力均无差别的个体有关,而对话法正好是作者心目中“师生平等”的体现。但作者虽然熟读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却没有留意到,布鲁贝克对启发式教学、友爱教学乃至讲授式教学都进行了肯定,布鲁贝克甚至说:“讲课仍然继续占统治地位:它为教授们提供了补充和解释教科书的机会。”[15]95而斯滕伯格和史渥林则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不赞成在教学里只运用一种策略。一方面,学生需要接触多种策略,这样才能形成多种技能……不管你用的是讨论还是照本宣科,只用一种策略会令学生感到厌倦。过分强调一种策略,把其他策略排除在外会削弱教学的效果,多种策略交替使用则要好得多。”[20]61正因为教学不是在空无一物的基础上直接追求“整全”,因而对于不同的知识,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教法,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培养他们进一步建构新知的热情,并最终实现学生在知识、思维、能力等各方面的提高。这样的教学,不只是客观知识之教,也不会只是建构知识之教,当然也不能仅仅是整全知识之教,而是兼而有之、兼容并包。这才是日常课堂当中可见的、可实现的、实实在在的教学,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教学。
当我们摒弃了割裂的思维,而采用一种整体的思维来看待教学活动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教学活动并不是只有知识灌输,也不是只有探究合作,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有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体验法、探究法等等,所谓“教无定法”,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教师也不只是在教授陈旧的知识,也不只是在和学生合作研究新知,而是在帮助学生积累知识基础的同时,带领他们一起从事学术研究;原来,知识也不只是一些现成的结论,而是含有无穷的魅力,将这些魅力展示在学生面前并藉此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研究热情,原本就是教学的题中之义。因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能依赖于将客观知识的传授从教学中剔除出去,也不能依靠降低教师的权威性以促进师生双方的“共游”,而是应该不断加强教学的科学性、艺术性,不断提升教学“通过知识来培养人”的效果,努力营造出一种“亦师亦友”的氛围,这样才能实现师生双方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艳侠.不同知识类型学习中的师生关系:大学师生关系三题[J].高等教育研究,2014,(8):82-86.
[2]〔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3]郑金洲.创新能力培养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2000,(1):13-16.
[4]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N/OL].[2012-09-15](2015-10-10).http://www.infzm.com/content/80797.
[5]邢红军,张园园,陈清梅.教学:大学教育的第一使命[J].大学教育科学,2013,(3):39-44.
[6]〔美〕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高文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1-12.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9]〔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第2版(修订版).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0]〔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人文学习之声[M].孙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1]郭建鹏.如何准确理解建构主义教学思想[J].教育学报,2005,(6):52-56.
[12]蔡年华.专业与兴趣撞车新生怎样走出困境[N].中国教育报,2008-09-03(7).
[13]曾翔.高等数学学习兴趣的调查与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8,(35):110-111.
[14]汤闻励.实时监控下的英语课堂兴趣调查分析[J].外语研究,2011,(2):67-72.
[15]〔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16]蒋关军.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后现代转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4):114-117.
[17]〔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8]PAULSEN F, et al. The Germ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Study[M].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ner’s Sons, 1906.
[19]〔德〕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0]〔美〕斯滕伯格,〔美〕史渥林.思维教学:培养聪明的学习者[M].赵海燕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罗银科]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Vision of Teaching
ZHOU Xu1a,b, LI Fang2
(1.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nstruction,
b.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2.Integrated Study Office,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16, China)
Abstract:Whether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universities is disengaged does not li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objective knowledge, but the skills in practicing it.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will not definitely cause students to follow their instructors blindly. The ideal of “wholeness” is hard to realize because it is isolated from objective knowledge. Only when teaching is based on wholeness can this ideal be possibly attained.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universities is not that of “friends and companions”, but only that of mentors and friends.
Key words:Vision of teachi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mentors and friends
作者简介:周序(1983—),男,四川泸州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教育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年)”的支持。
收稿日期:2015-10-10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1-00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