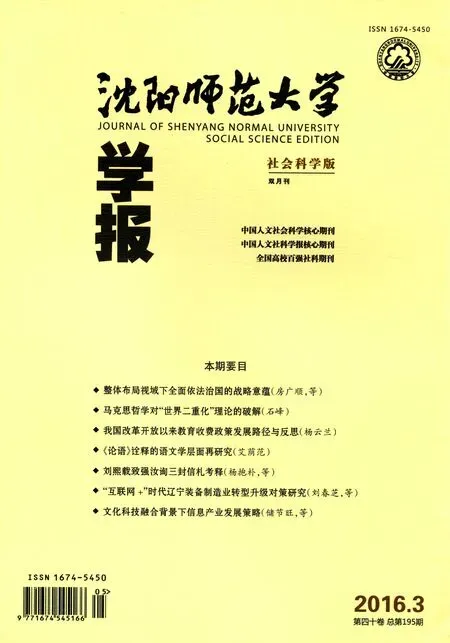战争视角下的中西文化——关于废名《阿赖耶识论》及“外编”的文化解读
于阿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战争视角下的中西文化——关于废名《阿赖耶识论》及“外编”的文化解读
于阿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废名写下自己唯一的哲学著作《阿赖耶识论》。1947年,他重返北平时就欲出版此书,然而真正的出版却一直等到2000年。抗日战争不仅构成了《阿赖耶识论》写作的外围环境,也深深决定和制约了作者的思考话题和言说立场。在此书中,废名深刻地论述了中西文化问题。这一点以往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大体而言,废名从战争的角度出发,重新体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的科技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化立场。
废名;《阿赖耶识论》;抗日战争;传统文化;西方科学
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废名于1937年冬至1946年秋,被迫居住在故乡黄梅。在那个敌寇频繁袭扰黄梅的战乱岁月,废名——这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京派”文学家,在阅读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却历时三年(1942—1945年)完成了此生唯一的哲学著作《阿赖耶识论》。
1947年返回北平后不久,废名就曾公布过此书要出版的消息①废名在文中这样写道:“《阿赖耶识论》稿上半年中国哲学会拿去了,并且给了我稿费,我本意是不要钱的,收稿费是表示一种契约的意思,希望把拙作早日印出来,同今世的科学家哲学家见面。”(参见废名:《“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见《废名集》(第四卷),王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3页。)。然而,在已经收到稿费的情况下,此书却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出版。20世纪末,止庵先生偶尔有幸读到了此书的手稿本。他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②止庵在文中写道:“废名不是可以埋没的人,这书也不是可以埋没的书”,并指出了此书对于废名的重要意义:“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写这《阿赖耶识论》是他最大的事业所在,所以说这是(也许仅仅是他自以为是)他的代表作也无不可。”(参见止庵:《樗下谈文》,《文艺评论》,1999年第3期,第76-78页。),并积极筹划此书的出版。最终,《阿赖耶识论》(止庵编订)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正式出版。2009年,此书收录于《废名集》(王风主编)的第四卷。《阿赖耶识论》出版之后,虽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总体上说,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且主要集中在佛学方面的解读③相关论文:陈建军:《世界:“心”“有”“理”——读废名〈阿赖耶识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5-9页。陈建军:《废名对进化论的反思质疑》,《孝感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75-80页。谢锡文:《废名佛学思想浅释》,《浙江学刊》,2008年第1期,第44-50页。谢锡文:《废名〈阿赖耶识论〉解读》,《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7-12页。谢锡文:《边缘视域人文问思——废名思想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陈振国:《废名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初探——〈阿赖耶识论〉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3-40页。。对于废名在该书中所论述的中西文化问题,尚未引起关注。因此,拙文将从中西文化问题角度切入分析。
有必要说明的是,废名在1947年重返北平后,还就《阿赖耶识论》中的某些话题展开过进一步阐述,大约写过四五篇相关文章,当时均已在刊物上发表。在止庵编订的版本中,以“附录”[1]的形式发表了四篇文章;而在王风主编的版本中,以“外编”[2]的形式发表了五篇文章④这五篇文章分别为:《说人欲与天理并说儒家道家治国之道》《孟子的性善和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和《体与用》。(其中四篇与止庵版本重合)。可以说,《阿赖耶识论》及“外编”五篇已经构成一个整体,本文论述主要就此展开。
一、“民无信不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废名身处其境,对此感触尤深。因此,他根据自己身处民间所亲眼所见的真实情景,放下了“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立场,转而重新评价和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考察这场战争何以会取胜的主要原因,废名认为,可能必须归功于儒家文化对“信”的推崇,也即对于“精神自信”的重视。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抵抗日本战争中,中国有一个“信”字,只有这一个“信”字可以抵抗强暴,现在也只有这一个“信”字是立国之道,因此我佩服孔子的话,去兵去食,而民不可以不信之,“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
废名对于这一“信”印象极为深刻。1947年重返北平后,他以自己抗战期间在黄梅避难的十年艰苦生活为蓝本,创作了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书中这样写中国农民对于战争的普遍看法:
关于胜利问题,莫须有先生在乡间常是探问一般老百姓的意见,一般老百姓的意见都是说日本老一定要败的。虽然头上都是日本老的飞机了,日本老不但进了国门,而且进家门了,一见了日本老都扶老携幼地逃,而他们说日本老一定要败的。是听了报纸的宣传吗?他们不看报。受了政府的指示吗?政府不指示他们,政府只叫他们逃。起先是叫他们逃,后来则是弃之。莫须有先生因了许多的经验使得他虚怀若谷,乡下人的话总有他们的理由罢,他对于世事不敢说是懂得了[4]。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信”也给当时来华的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奥登(W.H.Auden)与衣修伍德(Isherwood,C.)曾写作过《战地行纪》①此书的写作起因于英国一家出版社邀约“写一本有关东方的旅行读物”。恰好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们于是想写一本有关中国战事的游记。1938年1月,二人结伴从英国启程来到中国,居住6个月。这期间他们多次到达战争前线,亲眼目睹战争给中国士兵和中国农民,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沉重灾难。尽管他们在前言中指出:“我们不会说中文,对于远东事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因此,几乎没有必要去指出这个事实,即我们不能保证这本书里所作的许多陈述的精确性。”但是他们毕竟亲自见证了这一场战争,而且恰由于他们有着独特的身份,即英国人——游离于这场战争之外的旁观者,所以有时候通过他们冷静而客观的视角,反而能更真实地再现一些情况。一书。他们用惊叹的笔触记录下台儿庄战役期间,一群普通的士兵对战争的看法:
普通的中国士兵谈起中国有几多胜算时,虽稍微有些气馁,但最终仍是充满自信的,或者,至少是满怀了希望。“日本人用他们的坦克和飞机打仗。我们中国人靠我们的精神来作战。”他们中的一个说[5]。
这种坚定而朴素的民族自信意识,让奥登和衣修伍德——这两位不懂中文的英国作家惊讶了,也让废名——这位北平的读书人深深震惊了!震惊之下,废名开始陷入对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思考与认同。正是源于长久以来儒家文化对于“信”的推崇,这种自信才会渗入中华民族最底层民众的自我意识深处,才会在这场惨烈的抗日战争之中发挥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废名还进一步把之作为抗战胜利后的家国重建、未来发展的重要依仗。因此,废名一方面盛赞中国士兵与农民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不免呵斥读书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中国现在并没有到死地,因为本无死地在外面放着,而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对于民族之无自信,则真足以置中国于死地。”[3]1919
除了“信”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震撼了废名。在乡间百姓的平常生活中,废名也时常感受到民族精神的伟大。废名欣赏《大学》中的“平天下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为,这一点在孔子所称赞的大禹身上很好地表现出来,因为大禹治水时是“以四海为壑”,而不是“以邻国为壑”[3]1913。而中国乡间的模范农人大都如此。他们自己舍不得吃肉,却用酒肉祭祀祖先;他们房屋卑陋,田地工作却治理得很干净。在废名眼中,这体现出同大禹一样伟大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当然只能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潜移默化地熏染和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民族精神”不可思议的力量。由此,废名就开始思考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才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和圣贤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信仰孔子?他领悟到:
孔子的道理,不过替中国民族做一个说明而已……凡是属民族精神,都不是那个民族里面的少数圣贤教训出来的,是民族自己如此的,少数圣贤好比是高山,其整个民族便是平地。高山是以平地为基础,不是高山产生平地。确切地说,圣贤是民族产生出来。印度产生佛,希伯来产生耶稣,中国产生孔子,产生二帝三王,希腊则产生西洋文明吧[3]1914。
在这里,废名由自己的亲身体会重新思考和阐释了“民族精神”,以及圣贤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在废名看来,孔子等所宣扬的传统文化(即“民族精神”)与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精神信仰之间,不是由上而下的训诫关系或紧张关系,而是对百姓们的生活精华予以了适当地提炼。因此,他们二者之间其实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或者说一种注定的依存关系。这样一来,废名就转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民族根本精神的体认
在认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废名开始进一步思考,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于是,废名找到了孔子所称赞的“德”,认为这正体现着中国的民族精神。
我因此懂得中国圣人只是中国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是德不是力,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我们对于禹忘记了他的功劳,而佩服他的道德[3]1914。
在废名看来,“德”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高扬的一面大旗,无论对于圣人,还是对于普通百姓,这都是他们生活中最为看重的品性。
他紧跟着指出,以“德”为主的中国民族精神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中国民族决不会产生帝国主义”[3]1914。换句话说,也即中国不会主动发起战争去侵略别国。但现在的情形是,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谁来帮助人类摆脱战争?废名自然想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由于从战争中走来,废名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拯救自己,还将担负着拯救整个世界的重大责任:
我坚决地回答,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只有中国自己可以救中国。只有东方哲学可以救世界[3]1917。
中国真有救世界的责任,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正是现代潮流的旁观者。如何而自己卷入潮流呢?[3]1919
无独有偶,有关这方面还有另一则材料。根据奥登他们在《战地行纪》中的转述,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传教士——鲁茨主教(汉口的美国主教),说出了和废名几乎如出一辙的话,他也相信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你们得把眼光放远五百年……这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中将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的洪流,现如今已被犹大和专心一意的技术所改变,他将与另一个源于孔子的人本主义的潮流汇合,这股潮流曾受印度影响,并不痴迷于技术。这里会是新的世界文明的诞生地,中国人已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人类内心的一次革命,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如同牛津教团试图做到的那样——才能使世界免于毁灭。”[5]42
废名和鲁茨主教属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信仰和立场,但却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了厚望,相信它会对于世界的和平与文明做出重要贡献,这一点恐怕并非偶然。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废名与鲁茨主教都对于西方的科技文化充满了怀疑和批判,故而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废名写道:“现在的科学就是其鬼‘神',而中国人正是羡慕这个洋鬼‘神'得不得了,于是要全盘西化,哀哉。”[3]1918
也许废名已经意识到,他把自己置于了与“五四”文化不一样的立场。因为破除封建传统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这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重要口号。随着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文化的膜拜已经形成了那个时代强大的话语霸权。然而,目睹眼前的这些战争,让废名开始转向于重新体认“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这一可贵的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并由此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从战争的立场出发,废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做出了重要的调整与修正。
三、“致知在格物”——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揭示
废名在《阿赖耶识论》第五章、《说人欲与天理并说儒家治国之道》《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等多篇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致知在格物”这一主张,并由此具体阐述了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重要差异。
圣贤觉世的功课便只是这一句:“致知在格物。”我常想努力讲这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与科学的求知,恰是反对的方向,一是向内,一是向外[3]1910。
在废名看来,这无疑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缺陷。对此,废名予以了进一步阐释:
中国儒者合内外之道,孟子便已明白说了,“万物皆备于我”,只是中国学问是默而识之,不能将世界说得清清楚楚,虽然世界在其语默之中。欧西学问重在明辩,应该将世界说得清清楚楚,却是外物而内心,其结果乃至于俗不可医,因为明辨而妄语也[2]1868-1869。
欲辨石子的赤圆坚一,“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关物”,特嘉尔,赫胥黎,无论是谁,西方学者都不足以语此。因为他们是“无明”说话,便是执着。我所要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不守平日说物理的规矩[2]1872-1873。
废名认为,中国的儒者深深懂得“致知在格物”的道理,所以讲求“合内外之道”“万物皆备于我”,他们把自己与世界万物看作统一体,认为理解世界万物与理解自我是同一过程,在阅读世界万物的过程中他们也读懂了自我。西方的学者不懂“致知在格物”的道理,他们总是“外物而内心”“欲辩石子的赤圆坚一”。也就是说,他们把世界万物看成是自己内心之外的一个客观存在,并渴望明确地说清楚世界万物的特征。这种方法看似客观,其实“不守平日说物理的规矩”。因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言说物,而不是用“物的方式”去言说物,所以是“明辨而妄语”“‘无明'说话”。
在废名看来,西方文化这种“外物”的特性,必然地决定了其产生发达的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信奉“万物皆备于我”,决定了会较好地发展德与善这些方面,而不可能发达科学。废名写道:“提倡科学提倡了几十年而没有如故,这个事实不是唯物史观可以说明的。事实是,中国民族根本不会发达科学。”[3]1918这无疑是对“五四”时期科学主张的直接反思。与此同时,废名对于西方科学展开了严厉地批判,并衷心地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推崇。
西方学问的价值在科学,科学如能守科学的范围,既是“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则不至于妄语。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严格地说起来,“人之知识”正是业,业如何而知止呢?于是中国的学问尚矣。中国的学问“在止于至善”[3]1918。
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别在于,是“不知止”还是“止于至善”?换句话说,是“忠于物”还是“忠于心”?是仅仅寻求科学无限发达,还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内心?废名充满反思地写道:
我们生活之间都是外面有一个物,向外追求,耳逐声,目逐色,科学还要扩充耳的范围发明电话,扩充眼的范围用显微镜,我们说是进步,老子说是令人目盲令人耳聋令人心发狂。不要以为这话可笑,试看科学发达的今日谁还敢说“天理”二字?如果天理二字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现代人不是心发狂吗?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我今日真是觉得可哀[3]1911。
废名进一步指出:“求放心便是格物,你要能知道物不是物,同己一样,都是天理。你要用心。”[3]1911并且强调,平常的“耳目见闻”都不是“用心”,“忠于己”才是“用心”。
具体地讲,我们自己做事,要忠诚于自己内心;我们对待别人,乃至于外物的方式,也要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这基本上与前面废名所赞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相近的意思。
可以说,借助于“致知在格物”的启示,废名指出了中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差异。从方向上看,是向内与向外的差异;从形态上看,是道德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废名还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即“追求外物”的精神)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从而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即“止于至善”的精神)给予了高度地肯定。客观地讲,废名的这种认识也许自有其偏颇之处。但是,若放在“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备受批判的背景上看,废名的主张便具有了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同时,倘若放在当代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反思这一潮流上看,废名的主张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反思现代化潮流的先声。
四、“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批判
在上述谈论中,废名主要在哲学的层面,批评了西方的科技文化。接下来,废名进一步从战争的角度出发,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给予了更深刻地反省,从而表达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
废名谈到了眼前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我敢说,现在世界的灾难,就在一个‘为'字。西洋的‘为'或者有他的历史;中国的民族精神则本是‘无为',‘为'反而没有根据,为就是乱。”[3]1917废名进一步用佛教的“业”与“报应”,来解释这场战争的发生。在他看来,这正是由于“五四”以后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等文化思想的结果。
在一个战争的语境里来思考“科学”这一问题,这使得废名对于科学充满了反感。在废名眼里,这场战争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扩张。因而,废名对于科学的控诉,也就是对于战争的控诉:
现在世界的强国,德日是给科学烧死了,其他强国则正在拿着一颗炸弹不知道怎么好,想藏着将来拿去烧死人,又怕先把自己烧死了,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下神器不可为”。真的,同小孩子玩火一样,利害是不可测的[3]1918。
科学的发达带来了武器的先进,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本身必然也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或者应该说,如果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幸福的话,同时也带来了可怕的隐患和灾难。
废名曾经也是一名被“五四”所唤醒的年轻学生,所以他对于“科学”并不陌生,他当年很喜悦地阅读了吴稚晖先生的《机器促进大同说》,并且觉得“机器发达世界将真是大同了”;但是,他欢喜的梦想很快粉碎,因为他看到“事实是机器发达世界先来了两次世界大战。”[3]1918于是,这促使废名深深思考科学的本质,及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外国的灾难都是从科学来的,因为科学是一个权力的伸张,并不是理智的作用(纯粹数学或如康德哲学倒可以叫做理智作用,倘若有一种方法单独可以称之为科学方法,这便是科学方法。)换一句话说,科学正是印度佛教所说的“业”[3]1918-1919。
废名在这里一语道破科学的本质,科学里隐藏着战争的种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战争的语境里,废名会对于西方的科学展开不遗余力的批判。应当说,他矛头所向应当不仅仅是反思“五四”的科学口号,而是直接指向人类的战争本身。于是,废名借用老子和庄子的话,对于科学与进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我只是告诉大家,业不知止,“进化”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还有做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的义务,既是警告“进化”。《老子》一书,充分表现这个意思,他总是“畏”,劝人知止,“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3]1920-1921
我前说中国没有发达科学的可能,也不会产生机器,照庄子的神气他简直“羞而不为之”。我们何致于这样顽固,贵心知其意[3]1921。
在废名看来,按照中国传统道家文化来理解,关于科学发达的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能力和才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兴趣和道德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人们做不到,而是不应该去做。在这方面,道家为废名提供了知道“止”的典范。
废名认为,科学与进化都是不可取的,人类不能只是一味地追逐外物扩张,一味地只是向前看。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历史之中,回到圣贤身上,才能真正领悟到生活的重要启示。废名清醒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怀疑,从而明确地声称自己“信而好古”的文化态度。他要“温故而知新”,他要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要回到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中去。他认为,只有在回归的途中,才能够发现民族未来的道路。
综上所述,废名在《阿赖耶识论》及“外编”中流露出了对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倾心与推崇。由于身处抗战的特殊语境,废名从战争角度出发,重新体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的科技文化提出了严厉地批评。如果就中西文化整体而言,这其中也许不无偏颇之处,但若是仅从战争角度来看,废名的体悟自有其坚实的道理。尤其是考虑到“五四”以来批判中国传统和崇拜西方文化的整体背景,作为从“五四”走来的一代,废名思想所发生的这一转变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1]废名.阿赖耶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8-97.
[2]废名.阿赖耶识论[M]//王风.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08-1936.
[3]废名.说人欲与天理并说儒家治国之道[M]//王风.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19.
[4]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M]//王风.废名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25.
[5]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M].马鸣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8.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r——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Fei Ming's Alaya Theory and Its Appendices
Yu A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Fei Ming wrote his only philosophical works Alaya Theory. He said the book would be published when he
to Beijing in 1947,but the real publication had been waiting until 2000.The Anti-Japanese War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writing of Alaya Theory,but also deeply determines and restricts the author's thinking of the topic and the position of speech.In this book,Fei Ming thoroughly discusses the issu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which has not been mentioned in previous studies.In general,Fei Ming recogniz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severely criticized the wester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r,which shows a cultural posi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Fei Ming;Alaya Theory;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raditional culture;western sciences
I206.6
A
1674-5450(2016)03-0094-05
2016-03-20
于阿丽,女,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詹丽责任校对: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