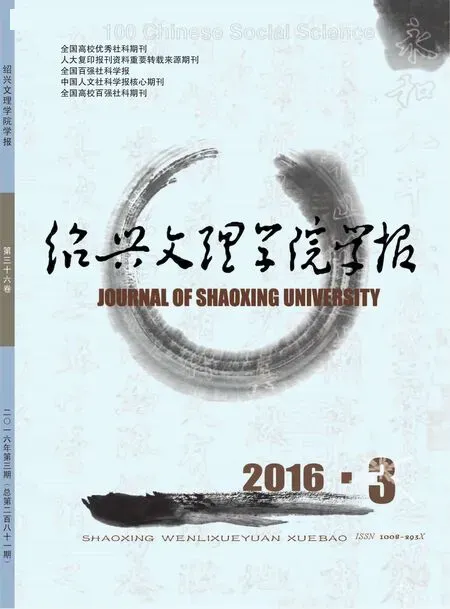从晚清“权利”话语的构建看翻译与权力的关系
马 嫣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从晚清“权利”话语的构建看翻译与权力的关系
马嫣
(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晚清时期的翻译较为特殊,多表现为对译文的操纵与改写。以《卢梭学案》为例,译者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卢梭的“权利”知识进行了改写,从“人权”“民权”“国权”这三方面引进并构建了中国式的“权利”话语,从而参与了权力结构的运作。
关键词:晚清;“权利”话语;构建;翻译与权力
一、引言
晚清时期掀起了一次翻译高潮,众多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皆为世人瞩目,且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译作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逐字翻译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如编译加按语、摘译加评论、翻译加创作等,而且,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操作,如增删、改写等。查阅近年文献发现,晚清这一翻译现象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兴趣,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以翻译的文化转向最受关注,特别是翻译与权力的关系,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论述制约和影响,较少从微观角度如针对具体某个文本来阐述,且大部分研究以探讨小说为主,研究其他体裁的较少。本文选择《清议报》第98、99、100期上刊登的《卢梭学案》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来看译者是如何对“权利”这一话语进行译介,并构建这一全新的知识,从而体现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的。
二、翻译与权力
自20世纪后半期西方译学界的文化转向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翻译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开始浮出水面。20世纪90年代,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共同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的序言中指出,“翻译学者需要探究某一社会之中那变幻莫测和变化无穷的权力运作,以及权力运作在文化产生过程中的意义,而翻译的产生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1],这揭开了翻译与权力研究的序幕。这一重大的文化转向与传统的语言范式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根本性冲突,原文不再是第一性的,译文也不再单纯派生于原文,翻译从此被置于更宏大的社会语境中,避免了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阐释学为译文的多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意义不是单义性的,而是多元性的。巴赫金提出了“杂语”概念,即文本隐含了声音的多元性,作者的意图通过他者的语言进行折射[2]。Jacques Derrida 等学者也提出,由于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策略的影响,意义既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作者的个人意图,也非原文静态的单一的再现[3]。一些翻译研究者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没有造成意义的终结,相反,由于受到社会大背景和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译者在不停地对原文进行着改写。这个改写的过程不再仅仅是对原文的再现,更多地是对其意义多样性的挖掘和对原文意义的偏离甚至是背叛[4]。Lambert和Robyns提出,翻译可以理解为一系列阐释行为的历史性产物,译文不应被看成是基于原文的最终而静止的产物,而是对应于原文的一个符号,其形式取决于与目标社会不同的准则和规范性模式之间的互动[5]。因此,意义并没有一个终点,而是在不停地被解读和被构建的过程中超越其原有的各种定义。对意义进行概念性的再述和历史性的重构使得翻译已不再是以往对原文的忠实再现,而是一种隐喻性的再构建。
在政治语境中进行这样的研究能更好地凸显翻译与权力的关系。根茨勒认为权力可以操纵翻译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和限制,翻译也可以引进“反动话语”(counterdiscourse),进行颠覆活动,自下而上对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而在这上下双向的互动中,译者往往充当了双重身份,他可能是权力结构中的一份子,也有可能是被权力结构边缘化了的译者,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通过对原文的操纵来达到对知识的操纵,从而达到对权力结构的操纵[6]。由此,翻译不再是一个简单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有意识的选择和制造的行为。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特定的政治概念就有可能会因为译者超越原有定义的再解读和再构建而发生变形。从这个角度看,译者就像政客一样,通过目标文化对翻译的操纵或利用,参与到了创建知识和打造社会这种权力行为中来了。本文将基于《卢梭学案》这一文本,来考察译者如何通过翻译,引进和构建有关“权利”这一知识和意识形态来实现对传统结构的颠覆,进而参与权力的建构。
三、《卢梭学案》和“权利”话语的构建
在晚清的翻译高潮中,除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等各种内容和体裁的作品,这些译介作品除了有一些单独出版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当时的报刊进行传播的。以《清议报》为例,它就曾发表过有关孟德斯鸠、霍布斯、伯伦知理、卢梭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的译介作品。其中,经梁启超编撰的《卢梭学案》是代表之一,译者通过摘译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经典语句来评论其思想,宣传其学说。在摘译加评论这种译介过程中,译者通过增改的方式对原文中“权利”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从“人权”“民权”“国权”这几个方面重新构建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权利”话语,这一全新的知识极大地开启了民众的自由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之心,从而参与到了当时的权力重构中。
(一)“人权”观的塑造
《清议报》在宣传卢梭的思想时把它总结为“天赋人权”,然而“天赋”这个词在原文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反复出现的只是一个字nature(naturel)表示“自然”,卢梭的本意是自然(nature)是绝对的,故人性(nature de l'homme)是绝对的,因此人的一切权利(droit)就是绝对的,故称为“自然权利”。译者在翻译时把“自然”的概念改换成了“天赋”,并突出“人”字,其用意非常明显。“天赋人权”是针对“神授王权”而言,历来王权论者都称君王为神之子,故有“奉天承运”“天子受命于天”之说,于是人权论者便提出人权受命于天来与之抗衡,这与当时有识之士对封建王朝专制的批判密不可分。
《卢梭学案》中提到“卢梭曰,凡人类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实由契于情好互相承认而成,是即契约之类也。既曰契约,则彼此之间,各有自由之义存矣。不独此也,即父母之于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抚育之固也,及其长也,犹相结而为尊卑之交,是实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7]。这一段出自《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论原始社会(Des Premières Sociétés)”开篇,“人类聚合”在原文中为“société”一词,表示“社会”之意,翻译成“人类聚合”突出了人,为译者强调“人权”作好铺垫。“家族”一词对应于原文中的“famille”,该词兼有家庭和家族之意。晚清时期我国仍延续以家长制为核心、以姓氏血缘为纽带的族宗制家族,这不仅表现为父权、族权为大,同时也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译者取“家族”之意,一方面更符合当时国情,另一方面也为了批判这种家族制。另外,此段译文中两次提到“父母”,而原文中仅有“父亲(père)”,并无“母亲”这一词,而“一夫一妻之相配,实由契于……不独此也”这句话也没有在原文中出现,这些都是译者刻意增添,为何要作此处理呢?原文中提到养育幼子,当时晚清社会男子在外谋生,女子则照顾家庭老少,在译文中增加“母亲”既符合实情,也对应“家族”概念。而增加“夫妻结合实为一种契约关系”的内容则是为了与“家族”概念一起更好地批判旧中国的“三纲”思想。封建统治者历来倡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清议报》以“天赋人权”为依据,多次对此进行了批判,称“臣有天赋之权,臣为天生之臣,即非君之所得而私有也;子有天赋之权,子为天生之子,即非父之所得而私有也;妇有天赋之权,妇为天生之妇,即非夫之所得而私有也”[8]。通过这样的翻译改写,中国人思想中没有的“人权”观念被译者塑造起来,成为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
(二)“民权”与“国权”观的塑造
在“人权”观的基础上,译者也打造了“民权”观,《卢梭学案》中摘录了《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四章“论奴隶制(De l'esclavage)”中的观点,“卢梭乃言曰,纵令人有捐弃本身自由权之权,断无为儿子豫约代捐彼自由权之权。何也,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9]。然而,原文中最后一句使用的是“nul”这个词,意为没有任何人,并没有单指父亲,译者缩小了原词的意义范围,突出了父亲这个身份,便于批判父权,从下文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若夫代子立约,举其身命而与诸人,使不得复有所改变,此背天地之公道,越为父之权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9]。原文中并无最后两句,“文明之世,所不容也”是译者刻意添加,批判父权意图更加明显。而后译者又对卢梭所言的不能代子捐弃自由权发表感想,他批判了当时的旧俗“父母得鬻其子女为人婢仆,又父母杀子”,认为这是“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权之所致也”[9]。晚清社会,宗族是封建体制的基础,《卢梭学案》中也引用卢梭的观点,称“家族为邦国之滥觞”[7],意为家族是国家的起源,因此父权在当时就是王权的缩影,批判中国旧俗和父权滥用,其意在批判王权,突出民权。梁启超曾表示“君主之权,因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10],即君王本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人民有了权利才使君主有了权利。
“民权”观的塑造也可以从《社会契约论》书名的翻译中看出,该书法文标题为“Du Contrat Social”,在《卢梭学案》中被译成“民约论”,意为“邦国之民约”。文中有一段卢梭的引言,“卢梭曰,众人相聚而谋曰,吾侪愿成一团聚,以众力而拥护各人之性命财产,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后,人人皆属从于他之众人,而实毫不损其固有之自由权,与未相聚之前无以异”[7]。这段话指出国家是由人民的契约而成,这才是国家最初成立的本义。将标题译成“民约论”可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君民的关系,即国家是为了人民而设立的,君主是人民推选的,有民才有君,这进一步剥去了君权神授的外衣,使广大民众开始意识到了“民权”的存在。而进一步考察上述引文,发现“勿使蒙他族之侵害”并没有在原文中出现,为何译者要增添这句话呢?当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正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时刻有亡国的危险,此处“他族”指的应是西方列强,译者加入此句正是为了说明兴民权可以救国,由此从“民权”观过渡到“国权”观,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清议报》曾在“民权”的基础上多次宣扬“国权”观念,麦孟华称“人权之于国权,二者实相比系。人权不强,国权必多阻屈”[11],梁启超也指出“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12]。这种“人权”观和“国权”观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引导更多的人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
四、结语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卢梭学案》中,译者通过特定的翻译策略实现了对原文中“权利”这一概念的改写,从人权、民权、国权层层递进地构建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式的“权利”知识,试图动摇晚清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译者自下而上的权利运作。从晚清“权利”话语的翻译和构建中可以看出,翻译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改变社会现实的手段,它们可以通过限定和引导社会主体的理解范围,打造意识形态,批判社会结构和关系,从而参与权利运作。翻译与知识、知识与权利之间的相互操纵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互动的、循环的链条。本文仅仅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探讨了翻译如何对权利机制产生影响,鉴于翻译与权利的关系复杂,研究者仍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出发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Bassnett,S.&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NewYork:Pinter,1990.
[2]Bakhtin,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3]Derrida,J. Des Tours des Babel [C]// In Graham, J. F.(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165-248.
[4]Bassnett,S.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C]//In Alvartez, R. & Carmen, M.(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10-24.
[5]Lambert, J. & ROBYNS, C. Translation [C]//In Posner, R. Robering, K & Sebeok, T. A. (eds.),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ion and Culture. Berlin: de Gruyter, 1997.
[6]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7]梁启超.卢梭学案[N].清议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第98期.
[8]泰力山.说奴隶[N].清议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第80期.
[9]梁启超.卢梭学案续[N].清议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第99期.
[10]梁启超.草茅危言——民权篇[N].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第27期.
[11]麦孟华.说权[N].清议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第44期.
[12]梁启超.爱国论三——论民权[N].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22期.
(责任编辑张玲玲)
On Translation and Power from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Ri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relatively special manifested as manipulation and rewriting of translated versions. In Jean Jacques Rousseau, the translator rewrote Rousseau’s knowledge of “Right” through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onstructed China’s discourse of “Righ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Human Rights”, “Civil Rights” and “Nation’s Rights”, thus participa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structure.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discourse of “Right”;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nd power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0-0067-04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0.013
收稿日期:2016-03-1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2015N057)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马嫣(1981-),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