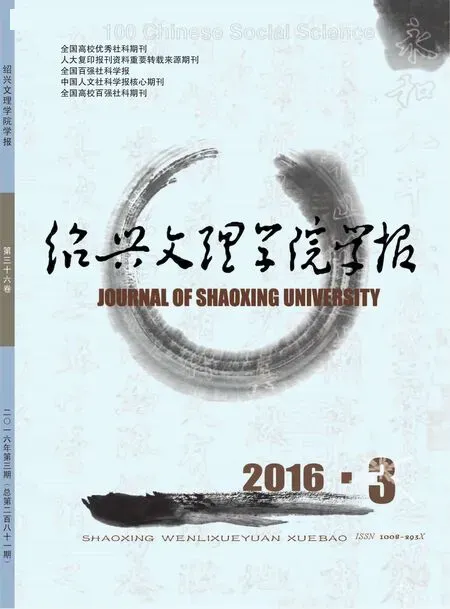董玘与徐阶因缘略论
钱汝平
(绍兴文理学院 越文化研究院,浙江 绍兴312000)
董玘与徐阶因缘略论
钱汝平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董玘是明代中期知名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阶则是大名鼎鼎的嘉靖、隆庆两朝首辅,明代杰出政治家。董玘与徐阶渊源很深,董是徐科举道路上的座师,又是文字之师、政治之师。而徐作为门生,也感恩师念,投桃报李,为保护座师子嗣免遭严党构陷、为座师死后的平反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一段师生相得的佳话。
关键词:董玘;徐阶;座师;文字之师;政治之师
董玘(1483-1546),字文玉,号中峰,浙江会稽渔渡人(现属绍兴市上虞区),明代中期知名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董玘自幼聪颖,素有神童之誉,19岁中举人,23岁会试第一,以榜眼及第。董玘长期供职于翰林院,是标准的文学侍从之臣,累官至吏部左侍郎。由于官场倾轧,年仅49岁、正当壮年且有宰辅之望的董玘被革职家居,复出无望,后以讲学而终。而徐阶则是大名鼎鼎的嘉靖、隆庆两朝首辅,明代杰出政治家,早已为人熟知,在此无需辞费。其实董、徐两人渊源很深,董是徐科举道路上的座师,又是政治生涯中的导师,两人交往密切,情谊甚笃。今就董、徐两人因缘略作梳理,以求教于当世之博雅君子。
一、科举的因缘
嘉靖元年(1522)八月,时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的董玘被任命为应天乡试主考官。当时年仅20岁的徐阶以生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乡试,不料在阅卷时,徐阶的试卷被同考官黜落。这件事情在明清载籍中有大量记载,自然要以徐阶亲笔所记最为可靠、全面。《世经堂集》卷十八《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明万历徐氏刻本)云:“嘉靖壬午主考南畿,阶时以诸生试,为同考所黜落,公阅而改品题焉,且将以为第一,属有沮者,乃以为第七,凡阶所以有今日,皆公赐也。”这段话涉及明代科举制度的背景。明代科举考试中,主考官一般不直接参与阅卷,阅卷主要由各房同考官担任,主考只负责接受同考官荐卷以及决定录取和名次之事,因此一个考生能否被取中,实际上同考官起到了决定作用。如果试卷被同考官淘汰,那么被取中的机会就十分渺茫了。但主考还有在落卷中“搜遗”的权力。所谓“搜遗”,就是为了防止阅卷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主考有权在落卷中再度检查评阅,从中录取自己认为优秀的考卷的行为。然而主考为避徇私舞弊之嫌,不敢对同考黜落的试卷过度搜求,而且他同时也得顾及作为同僚的同考官的面子。如果我们能从这个科举考试的背景出发来看待董玘破格录取徐阶并将其置于高等这件事,就会发现董玘的选择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他不但要顶住旁人对他徇私舞弊的讥评,还要承受破坏同僚之间感情的恶名,但董玘出于公心,为国选才,最终还是顶住了种种压力。事实证明董玘的选择是正确的。为此徐阶终生感激,发出了“凡阶所以有今日,皆公赐也”的感叹。我们知道,明清科举考试的录取比例是很低的。据潘承玉先生统计,明代童试录取率5%,科考录取率12%,乡试录取率3.33%,会试录取率10%,四者相乘,就是十万分之二。[1]可见一个成功的读书人背后,站着无数个不成功、不得志的读书人,很多才华横溢的读书人都以青衿终老,终生未得一第,如徐渭、冯梦龙、蒲松龄就是著例。徐阶20岁得中举人,次年会试中式,以探花及第,真可谓是少年高第,春风得意了,但在科举考试中,这样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徐阶17岁那年参加乡试落第,嘉靖元年第二次参加乡试,如果不是董玘的破格录才,徐阶必遭黜落。当然,我们可以说徐阶年轻,来日方长,但科举考试的偶然因素很多,并非是岁月的磨砺、知识的积累起决定作用,而往往是一步不着,步步不着,即使有可能在久困场屋之后侥幸获得一第,但岁月蹉跎,雄心壮志早已消磨殆尽,更有甚者,终生不得一第,抑郁潦倒而终。于此,笔者想起与徐阶同为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张居正幼年的一件事情。当时年仅13岁的张居正参加了湖广乡试,当考官打算录取张居正时,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指示考官黜落张居正,理由是:我们是为国抡才,13岁的孩子中举进入官场,官场上只会多一个吟风弄月的文人,这是国家的损失,不如趁其年轻,给他一个挫折,让他多磨砺磨砺。于是张居正是科落第,到下科才中举。当然13岁的孩子中举确实是早了一点,但久困场屋的磨砺对有治国临民之志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折磨。他们为博得一第,长年累月地把宝贵的青春年华消磨在无聊的八股文游戏当中,即使最后侥幸获得一第,进入仕途,但治国临民的本领近乎空白。试想一个四五十岁的读书人终日埋首八股程文当中,一旦获提拔担任了县令,毫无理政训练的他又该如何临民亲政呢?更何况古人年寿短促,这个年龄的官员又还能有几年可以为国效力?因此对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读书人来说,20来岁进士及第从而踏入仕途是最好的时机,至此他们可以抛开无聊的八股文游戏而真正进入学习治国临民的理政经验的阶段,经过几年的锻炼而迅速成长为治国理政的干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阶是幸运的,他能成为明代杰出政治家是有原因的。而这一切,董玘的破格“搜遗”给了徐阶以莫大的助力,所以徐阶“凡阶所以有今日,皆公赐也”的感叹,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并非虚情。
二、座主对门生的影响
徐阶自幼追随王阳明弟子聂豹研习“致良知”之学,是王氏心学坚定的追随者和虔诚的信奉者,而董玘受明初金华学派理学大儒章懋影响甚深,毕生恪守程朱理学,与王氏心学格格不入,因此董、徐两人的学术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师生情谊。董玘对徐阶的影响更多的是在人格的熏陶、文字的指授、政治的点拨上。
会稽董氏以立身刚直、清白廉洁传家。董玘父亲董复是成化十一年进士,初授黟县令,擢贵州道监察御史,累官至云南知府。伯父董豫是成化十四年进士,授奉政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兄弟二人官位都不低,但他们都因立身刚直、不避权贵而为当事者所忌,从而影响了仕途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不事请托,家无余资,董玘母亲娄氏竟以御史之女躬拾牛马粪秽以作燃料,清苦生活可想而知。这样的清苦生活并非虚构,徐阶与董玘过从颇密,往往得之于目验,《世经堂集》卷十五《封太淑人董母娄氏墓志铭》云:
嘉靖丙申六月十三日,封太淑人娄氏卒。太淑人其出为前御史屏梅公女,其归为故云南知府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颐斋公配,为吾师今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中峰先生母。其封于国之制为三品,然其生也,家无赀,卒也槖无遗财。……太淑人始归,董氏颐斋公方试春官不利,偕仲兄佥事公卒业太学。时乃无僮仆资斧,太淑人躬执炊爨,薪绝手拾秽遗暴而爇之,无怨言。某年颐斋公举进士,拜黟县令,太淑人在官所,朝夕惟为公设肉,身及子女皆茹淡。被服甚俭,一衣非十许年弗易。后公征入为御史,按畿内真定诸郡,太淑人留京邸,有干请者,绝不与通。继按闽,值岁大比,浙镇守中贵人为其侄求举,密遣人致重贿,太淑人时寄寓族子舍,贿者以治第为讽,言殊委曲,卒不顾。公自闽代还,多所纠劾,以忌出知云南。太淑人益仿公为清约,居九年,忌者竟罢公。公既素贫,四子一女至不能婚嫁,太淑人早作夜休,躬蚕缫,课树艺,次第卑事,公赖不烦。弘治乙丑先生试春官第一,进士及第,官翰林,严重端简,人无私交,太淑人闻之,喜曰:“吾乃幸有子。”数寄语先生,慎无易其初,故先生自为编修,至于少宰,以廉节闻天下。及先生被谗归,视其室萧然,太淑人出视,行李亦萧然,母子各大慰。先生日晨起撷疏煮粥,奉以进太淑人,太淑人食之尽,肤色加充泽。阶尝谒先生,先生赐之坐,屋仅十余间,坐处稍完洁,中可着七八人,余则已敝漏。有顷赐食,设大盂置菜数种,久乃有鱼肉,味皆淡薄,杯盘之属,小大黑白错。阶大骇异,以为此布衣之士所不堪。既而询诸其邻,曰:“先生平时饭客,尚不能办此也。”呜呼!颐斋公为知县,为御史,为知府,于人情可以富;先生在翰林二十年,为少宰又五年,于人情可以大富;以先生继颐斋公再世仕宦,于人情又可以富。然而无改于贫,太淑人既不挠其夫,尤其子,又臞身竭力以为之助,正言悦色以劝以勉,故先生父子所自树立,虽本大过于人,而太孺人左右先后之功岂少哉!呜呼!可谓贤矣……
又,同书卷十八《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亦云:
阶督学于浙,数谒公,公留语竟日,未尝以子弟亲旧为托,而诸藩臬之吏至不得一识公面,其廉介自重如此。
如果说娄氏以御史之女亲拾牛马粪秽以作燃料以及“被服甚俭,一衣非十许年弗易”等事还是得之于传闻的话,那么董家“屋仅十余间,坐处稍完洁,中可着七八人,余则已敝漏”的居住状况、招待贵客“设大盂置菜数种,久乃有鱼肉,味皆淡薄,杯盘之属,小大黑白错”的饮食情况,以及董玘“未尝以子弟亲旧为托,而诸藩臬之吏至不得一识公面,其廉介自重如此”的人品道德情况,总都是徐阶所目击,徐氏没必要撒谎。因此会稽董氏以再世仕宦的有利条件,本可富而不富,终以清白传家的描述并不是文人惯用的无病呻吟式的矫情,而确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座师董玘立身刚直、廉介自重、不事请托、言不及私的人格魅力对徐阶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在明代首辅中,徐阶以正直清廉出名。当然,我们不能按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比如说清廉,古人收受门生故吏的馈献并不算是受贿而有伤清誉,在当时这是正常的礼尚往来。作为首辅,徐阶为了推行贯彻自己的施政主张,不得不玩弄权谋,他向上得迎合皇帝的喜好,因为在高度专制的皇权时代,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无论多么高尚的政治理想都只不过是空中花、水中月而已;他向下还得与同僚言官们纠缠,要推行一种政治主张,势必会招来反对之声,如何消弭反对之声,减少施政的阻力,这是考验首辅能力的重要尺度。明代内阁按制度来说,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而已,并没有绝对权力,内阁首辅充其量只是皇帝的首席机要秘书。由于内阁掌握有票拟的权力,于是人们往往以前代的宰相之号称之。但按明代祖制来说,首辅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六部完全可以不听首辅的指挥。首辅的票拟也只能通过皇帝的批红才能贯彻实施,而由于皇帝的怠政,批红权往往转移至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手中,于是首辅又得与司礼监周旋。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要取得政治上的任何一点进展,都是很不容易的,都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因此,徐阶作为首辅,在施政过程中玩弄一些权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本质上是一个正人君子。在严嵩、严世蕃父子掌权的时代,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严氏父子明码标价地买官卖官,徐阶对此早已是深恶痛绝。他一上台,就一反严氏父子的所作所为,首先就杜绝苞苴,严禁买官鬻爵。经过徐阶的大力整顿,嘉靖末年政风、士风为之一变,王世贞说,徐阶在他事上多能量情罪而有所纵舍,“独驭贪酷吏严,所坐狱必竟不少贷,其杜干请,绝苞苴,即长安公卿邸中俱肃然亡敢以篚筐出入者”[2]。此外,他还保护过得罪严氏父子的“越中四谏”(沈炼、沈束、赵锦、徐学诗)、门生杨继盛、“戊午三子”(吴时来、董传策、张翀)。当然他还保护过因上《治安疏》而得罪嘉靖帝的海瑞。这些都是正人君子,徐阶为使这些正直官员免遭诬陷屠戮,做了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在徐阶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师董玘的影子。
徐阶于嘉靖二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旋得告归娶。次年八月,北上复官。行至山东清源地带,夜忽梦父帕首而呼名者再,心感不祥,乃反棹,抵彭城而闻父丧,遂号哭归。嘉靖六年服除,正式回京复翰林院编修职。从嘉靖六年至九年这三年期间,徐阶一直在翰林院供职,而此时其座师董玘已从詹事府詹事历官至吏部左侍郎了,但仍兼翰林院学士职。明代翰林院惯例,新进的庶吉士、检讨、编修、修撰等,均要对院中前辈执弟子礼。在这三年里,徐阶与座师董玘的交往应该比较密切,可谓是亲聆謦咳。董玘对徐阶的读书作文多有指授,《世经堂集》卷十八《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云:“公为文精于理而深于思,每命阶属草,涂窜损益,存者不能十二三。”董玘学问渊博,但不苟作,虽博极群书,而不轻言著述。他写的每一篇文字都经过精心的布局、多般的推敲,因此董玘的乡后辈沈束评其文章风格为“虽不务奇丽铿激之声,而雅饬浩荡委曲精致则一时文人少有出于其右者”[3],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而徐阶评价董玘“为文精于理而深于思”,且文字简炼,自然也是沈束评价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徐阶对董玘的为文风格是有真切的体会的。古人从政,要治国临民,首先得精通案牍之文,这些文章并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要针对性地书写,尤其需要在“理”和“思”上下功夫。如果为官者案牍之文写得既无条理,又无思致,且文字啰嗦繁琐,那么他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因此,这段时间的写作训练对徐阶以后的从政生涯有莫大的好处。比如在处置严世蕃图谋叛乱一事上,徐阶的奏折就表现了“精于理而深于思”的特点。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御史邹应龙弹劾严世蕃,奏入称旨,严世蕃谪戍雷州。然而严世蕃并未赴雷州戍所,而是取道南雄潜还原籍袁州,其党罗龙文亦逃入袁州。世蕃聚众至数千,营建室宇。袁州刑推郭谏臣使白诸监司散遣之。后世蕃闻闽、广群盗欲劫掠其家,复阴蓄家丁数千以备之。由是人心疑惧,啧啧不已。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巡江御史林润驰疏弹劾世蕃、罗龙文反怀怨望,蔑视国法,不赴戍所,召纳亡命,有负险不臣之志。并言道路皆言两人通倭。世宗诏委林润拿送世蕃、龙文至京。林润上《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再劾,并涉及严嵩容留曲庇逆子之罪,于是下法司拟罪。《明史》对此事有精彩的描述:
法司黄光升等以谳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佥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继盛)、沈(炼)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遂斩于市。[4]
老辣的徐阶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固然和他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老谋深算有关,但也不能说与他平时所受的精心布局、多般推敲、悉理深思、翦除榛莽、归于简练的写作训练毫无关系。而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拜座师董玘所赐。
董玘对徐阶的从政也有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徐阶的政治导师。嘉靖九年九月,董玘父亲董复去世,董玘遂离京奔丧,门生徐阶前往送别。汪应轸《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董公行略》:
门人徐阶祖道京门,泣谓之曰:“予归之后,分宜必当国用事,汝适当其时,勉为社稷臣,毋使缙绅受其荼毒。”故去分宜者,华亭也;豫授其方略者,公也。[3]
从这段记载来看,似乎董玘早在嘉靖九年就已经预见到严嵩以后要执掌权柄祸害缙绅之事了,因此在丁忧回乡前就向门生徐阶指授了应付严氏之策。汪氏《行略》还说除去严氏的是徐阶,而预授方略的是董氏。我们知道,古人撰写的墓志铭往往是在死者的亲戚好友所撰的行状基础上增删润饰而成的。徐阶所撰的《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其实就是以汪应轸所撰《明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董公行略》为蓝本的。但徐阶作墓志铭时,却删去了此节。徐阶删去此节,或是出于避嫌之需,或是汪氏之说有谀墓之嫌(汪是董的从外甥兼门生)。当然,汪氏之说似亦并非妄说,严氏当时已得帝宠,升迁很快,董氏被革吏部左侍郎后,补其职者即是严氏,严氏当国之势隐然已现。而徐阶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编修,但在座师董玘的眼中,徐阶是有宰辅之才的,是迟早要和严嵩正面交手的,因此他在离京前向其传授应付严嵩之策也不是没有可能。综观徐阶入阁后,甘居次辅十余年,为扳倒严嵩父子处心积虑,步步为营,扎实推进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徐阶确有乃师董玘的性格风范。因此说董玘是徐阶的政治导师,实不为过。
董玘与徐阶因科举考试而结成师生之缘,两人交往密切,情谊颇深,董玘不但在为人方面给了徐阶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为文、为政方面也给了他莫大的助力,因此可以说董玘是徐阶的人格之师、文字之师、政治之师。
三、门生对座师的回馈
在今本《世经堂集》中,涉及董玘的有三篇文章:《昭遇录序》(卷十一)、《封太淑人董母娄氏墓志铭》(卷十五)、《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卷十八)。当然,这只是古代文人、师生之间的酬酢之作,徐父死后,董玘亦作有《宁都县丞赠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徐君墓志铭》(《中峰集》卷八),但这也可说是双方关系密切、情谊深厚的体现。这是“虚文”的方面,我们不作讨论。
徐阶实质性的回报是在董玘身后。董玘有一子,名思近,字约山,以父荫得官,任宗人府经历。其时会稽人沈束因上疏弹劾严嵩而下狱,董思近出于义愤,上疏救之,为严嵩诬陷,几遭不测。时徐阶为内阁次辅,遂与严嵩周旋,思近才得以出知云南寻甸府。康熙《浙江通志》卷二十三《人物》(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云:“董思近,字约山,会稽人,以父玘荫官。适同邑沈束下狱,思近抗疏救之,几不测,华亭徐阶为玘所得士,慨然曰:‘吾师止一子,何忍坐视其死。’力为营解,得出知云南寻甸府,卒官。”为保护座师的子嗣免遭严党的构陷甚至屠戮,徐阶是出了力的。为严党构陷下狱的正直官员,徐阶总是尽量去保全。但这样的官员很多,徐阶无法也无力去悉数保全。他优先保护座师之子,使其远离政治中心、是非之地,免遭严党陷害,其用心良苦,我们可以想见。
徐阶为董玘平反也尽了全力。嘉靖九年九月,董玘父亲董复去世,由于疏请恤典及天气恶劣等原因,董玘回乡奔丧的日子被耽搁了几天。于是御史胡明善、汪鋐等出于官场倾轧,公报私仇,弹劾董玘恋栈官位,闻父丧而迟迟不行,当别有所图,而以前因请托被拒的同僚也乘机纷纷落井下石,以附和胡、汪的诬陷。在封建社会以忠孝治国的背景下,这样的诬陷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也就是说此人是大逆不道、无复人理了,这就等于宣判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再加上嘉靖帝极为重视儒家礼法,后人竟以明之理宗称之,于是处理就显得偏重,“上以玘忠孝大节已亏,法当论治,第念其日讲有年,姑与冠带闲住。都察院亦言其闻丧延缓事,俱有迹。上以玘已革职,姑免究,吏部更不许起用。”[5]虽然此后董玘连连上疏为自己辩诬,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董玘革职家居十五年,始终未能复出,后抑郁而终。
其实徐阶一直都想为座师董玘平反,但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时机。甚至在董玘去世的嘉靖二十五年,当董玘之子董思近拿着汪应轸所撰的行状来请他作董玘墓志铭时,他都没有答应。当时已是吏部左侍郎的徐阶之所以没有答应撰作董玘墓志铭,可能他觉得嘉靖帝当时是以“忠孝大节已亏”的名义处分董玘的,这是钦定的铁案,如果自己贸然答应撰作董玘墓志铭,为其辩诬,势必会得罪嘉靖帝,反而会弄巧成拙,因此素以行事稳健著称的徐阶是不会出此下策的。他在想一个万全之策,他在等待时机。时隔二十年后,当董玘之孙董祖庆向他再次请求撰作董玘墓志铭时,他终于答应了。《世经堂集》卷十八《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云:“嘉靖丙午六月二十六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卒于家,其子思近谓阶公门生也,奉学宪汪君状属铭公墓,而阶意有所待,迟之二十年,今年秋其孙祖庆复以请。阶因念昔之待者,既未可必副,而身已衰老,一旦溘先朝露,则公之行将遂不克彰显于世,其何以见公地下?乃叙而铭之。”当时的徐阶已是内阁首辅,而嘉靖帝也已病入膏肓,再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已死去二十年的革职官员了,这就使得徐阶少了不少掣肘,从而可以放开手脚、客观公正地为座师董玘辩诬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徐阶亦已年老,此时不写,更待何时?于是徐阶写下了这篇毫端倾注感情的《明故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中峰先生董公墓志铭》。徐阶在文中明确指出,董玘的落职完全是小人的倾轧诬陷所致:“初,公在吏部,拒绝请托,尤严于君子小人之辩。御史胡明善所为多不法,公疏出之,草已具而讣至,不果上。公又薄都御史汪鋐,鋐、明善胥怨公,公之请恤典也,值方郊,有司不敢覆请,及命下,则去闻丧已踰月。鋐、明善因诬公,谓有他觊,不肯行,而昔之以请托见拒者,咸相与构之,诏落公职。”徐阶以首辅之尊为其师董玘作墓志铭,实际上已拉开了隆庆元年董玘被赠礼部尚书并赐谥文简的序幕。
隆庆元年三月,经大学士徐阶上书陈请,董玘得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十二月《赠礼部尚书谥文简诰》下达。诰文如此评价董玘:“修史著直笔之誉,校文昭悬鉴之公。侍读经帏,能沃心而辅德;署篆铨部,克屏私而去邪。顾未陟于孤卿,乃卒困于群小。逮事久而论定,允位下而名高。”[3]对董氏一生的功绩作了客观评价,对其因遭小人诬陷而未能被重用,从而导致名高而位下一事深表可惜,算是迟到的平反。从这篇诰文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情感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出于徐阶手笔,或经徐阶润饰。
董玘与徐阶因科举而结缘。作为座师,董玘高洁的人品、精湛的写作技巧以及政治上的点拨都给了门生徐阶深刻的影响;作为门生,徐阶也没有辜负座师董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宦海沉浮、刻苦磨砺,徐阶终于成长为大明王朝的杰出首辅,由于出色的治绩而被目为一代名相。而徐阶又笃于师生之情,感念师恩,投桃报李,为保护座师子嗣免遭严党构陷、为座师死后的平反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一段师生相得的佳话。董玘地下有知,足可自慰。
参考文献:
[1]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风气[M]//中国越学: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47.
[2]王世贞.徐阶传[M]//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董中峰先生文集序[M]//中峰集:卷首.清光绪三十二年董金鉴刻本.
[4]奸臣·严嵩传[M]//明史:卷三百零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明]徐学聚.吏部[M]//国朝典汇:卷三十四.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
(责任编辑张玲玲)
The Karma between Dong Qi and Xu Jie
Qian Ruping
(Institute of Yue Culture Research,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Dong Qi was a renowned Neo-Confucianist, historian and writer in the mid Ming dynasty, whereas Xu Jie was a well-known first Grand Secretary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and Emperor Longqing,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in the Ming dynasty. Dong Qi and Xu Jie were closely tied; the former, a mentor of the latter on his way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structed both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o the latter. As a disciple, Xu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his mentor and did something in return by protecting Dong’s off-springs from false charges from the gang of Yan Song and by sparing no effort to redress Dong’s grievance after his death, hence an anecdote of the mentor and the disciple.
Key words:Dong Qi; Xu Jie; mentor; mentor of literature; mentor of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0-0050-06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0.010
收稿日期:2016-04-1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课题“《中峰集》整理”(2010YWHNO2)成果。
作者简介:钱汝平(1975-),男,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