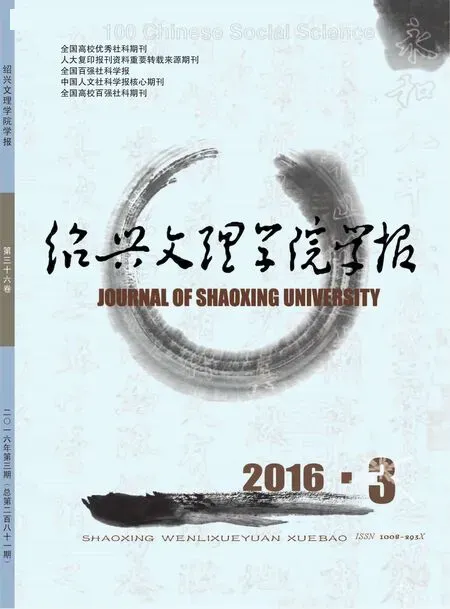开拓创新持续深化
——纪念陆游诞辰890周年国际研讨会学术总结
莫砺锋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开拓创新持续深化
——纪念陆游诞辰890周年国际研讨会学术总结
莫砺锋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各位代表:
受会议组委会委托,我对本次大会作学术总结。刚才三位小组汇报人都讲得很好,大家也基本了解了每个小组论文的内容、特点,连各组热烈讨论的现场气氛都很好地传达出来了。下面我对本次大会的学术论文进行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本次大会的论文大致上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或者是优点。
第一,在研究题材的开拓、研究角度的多样性方面胜过前人。许多主题以前好像不太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比如对陆游在后世的非学术性影响的研究,像郑永晓先生的《抗日战争时期陆游爱国诗词的影响与接受》,陆游对抗战时期的精神氛围的影响,这是我们以前很少提到,较少关注的。像陶喻之先生关注了苏雪林的《陆游评传》,这本书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些都是很新的题材内容的开拓。台湾学者廖一瑾先生的《陆游在闽时的海洋游历与台湾诗缘》对于陆游诗歌中写到台湾(当时称为琉球)的研究,都很开拓我们的视野。刚才小组汇报人也特别点出了张福勋先生的《陆游短论三篇》,张先生的论文就像他上一次会议提出来的《陆游有第四个女人吗》一样,富有启发性。这篇论文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提纲,但里面好多内容都能开拓我们的思路。另外,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也非常明显。比如说,对于陆游诗歌的研究,除了我们一向关注的爱国主题以外,这次就有学者谈到他的记梦诗、饮酒诗、戏作诗、入蜀诗乃至于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叫“呈示诗”等等。这个可以说是角度的新颖化,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当然,大部分的论文还是用我们本学科的传统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这也很好。我们的传统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论文,它们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比如说,我关注到有好多论文虽然题材不一样,但都注意到了“书写”这种观念。“书写”的观念恐怕是从现代西方文论中引进来的。这在很多论文中都做得很好,比如刘京臣先生的《陆放翁与大散关书写》就做得很好。但是在这方面,本人也有一点看法。由于方法创新,可能有的地方还是要引起注意。比如吕肖奂先生《“不得体”的陆游:交往困难症患者的人际关系诗歌》,虽然刚才小组汇报说这篇论文是独具慧眼,但我觉得,本文在前面用比较大的篇幅论述陆游不善交往,陆游与人交往的时候好像是“不得体”的。当然,这篇论文最后的主旨还是肯定陆游,说陆游因为在礼仪上的“不得体”,所以他的社交唱和诗就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显得有个性,而且真诚有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读了这篇论文以后,总有一点当年人们评价司马相如赋的那个味道,所谓“曲终奏雅”。司马相如作赋讥讽汉武帝好神仙,本来是要想讥讽他的,但汉武帝读了之后反而觉得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他前面的部分铺陈得太厉害了,反而把他的讥讽主题冲淡了,或者掩蔽了,我觉得吕肖奂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陆游是不是一个“交往困难症患者”?如果论文中的这些例证就能证明陆游是“交往困难症患者”,那么我们历史上的很多优秀诗人恐怕都是患有此病。比如说李白、杜甫,我们在李白、杜甫的诗中都能读到“前门长揖后门关”“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为云覆手雨”等等描写他们社交的诗句。他们对当时的交往,特别是一些庸俗的交往是非常地厌恶、批判的。李白在他的诗中还直接骂人说:“董龙更是何鸡狗!”陆游诗写得比他们温婉多了。所以我想,在古代的士大夫、文学家中间,真正有“交往困难症患者”的,恐怕只有三国时的祢衡才当得起此称,他确实是这样子的。祢衡到了许昌后公开声称京城的士大夫中只有两个人可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其他人都不值得交的。古代最早说到“名片”的可能就是这个祢衡吧,祢衡说“藏刺于怀,三年灭字”,他做了一张名片准备结交他人,结果放在口袋里三年都没投出去,上面的字迹都磨灭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交往困难症患者。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后面的主旨不错,但这个称呼是不是妥当,恐怕还可商榷。还有一篇写陆游交游的文章是杨挺和潘玥两位提交的《呈示诗:绍熙退居后陆游的社会交往与身份书写》。这篇文章的内容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方法上面确实是非常创新,这个方法创新就在于这篇论文多次引用西方现代理论家,不仅是文学理论家,还包括社会学理论家、文化学理论家的一些言论。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前后一共引用了24次。文章基本的书写方式就是引几首陆游诗,然后下面说“正如西方某某人说的……”,再下面也不见有其他分析,或新的探讨。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倾向,在我们提倡新方法的时候是否要引起一些警惕。我提供大家一个参考材料,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他有很多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学界反响也比较大。宇文所安教授曾经表示过这样的观点,这个观点见于1990年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因为我请宇文帮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宇文所安在那篇序里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将西方的理论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间,如果你的运用仅仅是用中国文学的文本来证实西方的理论是对的,那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位西方学者本人的感受,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不能说把我们古代的某个文本、某种文学现象比较合适地贴上一个西方的标签就万事大吉了,何况有的文章所贴上的标签本身也不合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不是批评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种风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总的来说,我们这次会议在方法上面是有所创新的。
第三,本次会议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学术信息,是我们以前关注得比较少的。比如关于陆游古文的研究。我们以前主要研究陆游的诗和词,对他的古文的研究是不够的。本次会议朱迎平教授提交的两篇论文告诉我们,他本人正在从事《渭南文集》的校注。尽管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已经举行了马亚中先生主持的《渭南文集校注》的首发式,但是,朱迎平教授的论文,特别是他的后面一篇文章,举例式地提出了11篇陆游古文的系年问题。我有一种预想,将来会出现一部在学术水平上可以和刚刚问世的《渭南文集校注》春兰秋菊毫不逊色的陆游文集的新校注。杜诗已经有“千家注杜”,尽管“千家注杜”有点夸张,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历代杜诗注本中起码有十种以上是各有其价值的,一个伟大作家的文集不妨有多种校注本。我们期望几年后能够看到朱迎平教授主持的新的《渭南文集》校注。这种新的学术信息对我们非常有用。
第四,新观点的提出。确实,本次论文中有很多的论文题目就使人耳目一新。比如说关于陆游与方志编写的关系、关于陆游古文创作中历史地理学的观点等等。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以前较少出现在学界的视野之内,本次都提出来了。当然,有一些并不一定是新的课题,前人已经提过了,但本次论文中有新的观点。比如说在大会上报告并得到点评的张剑先生的文章《陆游的醉态、醉思与饮酒诗》。大家都知道陆游的饮酒诗数量很多,张先生作了一个统计,说有3000多首,这个数量非常惊人。他的文章里除了写陆游饮酒诗的“醉态”以外,还提出一个新的名词叫作“醉思”,就是喝醉以后的一种思考,一种心理活动,这个观念非常新颖。尽管李贞慧教授已经有了很好的点评,但我还是想说一点想法。我觉得陆游虽然喜欢喝酒,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酒徒。像李白所说,一个纯粹的酒徒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天天喝得烂醉,这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问题是,作为酒徒的诗人喝醉以后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诗歌写作?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有没有不喝醉的时候?在这些方面,我觉得陆游做得很好。张剑先生的文章中没有征引陆游的那首《长歌行》,在陆游写酒的诗里,《长歌行》中的这几句恰恰是我最喜欢的:“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就是兴致来的时候,喝酒像钜野接受黄河的倾泻,但接下来就是:“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陆游平时要从事抗金复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不能喝得烂醉。最后又说:“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待到凯旋,就像岳飞说的“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这首饮酒诗写得非常理性。我想这就是张先生的文章对我们的一些启发。
第五,本次会议论文中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新观点的提出,而是对我们反复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之深化。学术研究是要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才能使我们的认识走向深入。
这次会议上引起我这方面感想的论文主要有两篇。
第一篇是小组汇报人、评点人都提到过的,蒋凡先生的那一篇份量非常厚重的文章《陆游晚节与韩侂胄开禧北伐评议》。蒋先生这篇文章研究了陆游生平研究和评价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陆游晚年写《南园记》以及他跟韩侂胄的关系。主持人说蒋先生的文章一出来就可以定论了,我想可能还不会定论。这个话题从南宋开始一直争论到现在,可能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蒋凡先生这篇文章无疑把我们的认识引向深化,请允许我稍微用一点时间说说我的感想。这篇文章有两大优点:一、蒋先生的考证做得非常细密、严谨,逻辑性和事实性两方面都不容置辩。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当时人们对陆游写《南园记》有很多负面的批评,有很多非议,其中有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虽然有史料,白纸黑字,但这些史料是不可靠的。蒋凡先生在这里引了一条很重要的材料,见于元人刘壎《隐居通议》,说陆游本来是不肯为韩侂胄写记的,但是有一天他的妾抱了一个未成年的幼儿,跑出来说:“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就是说,你的孩子还小,你不靠拢当权的宰相,就不为小孩子想想吗?于是陆游就动心了,就写了《南园记》。这个事情传闻得很广,但是蒋先生用非常明确的事实来证明这完全是虚构的。他的思路非常简捷,就是考察陆游的孩子的情况。陆游的幼子子遹在陆游写《南园记》的这一年早已成年了,已经23岁了。一个23岁的青年怎么还要他的生母抱着出来要求陆游写《南园记》?这说明这则材料完全是虚构的,甚至是恶意地编造出来的。我觉得像这种地方,用坚实的考订证伪某些史料,问题也就清楚了。当然,我还是有一点补充意见。我觉得蒋先生不妨再思考一下,陆游教诲儿孙的诗非常多,陆游写了那么多的诗歌教诲儿孙,都是鼓励他们要忠义,为人要正直,要从事农桑,世世做农民也很好,所以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小孩子将来的生活而卖身投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二、蒋先生的文章对文本的释读非常准确、合理。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朱熹死后陆游吊朱熹的诔文。他的文章提到,某些人攻击陆游,说陆游当年投靠韩侂胄,因为朱熹是所谓的“伪党”,所以陆游给朱熹写的诔文很短,只有24个字,这是敷衍了事,不真诚,以此证明陆游在政治上是投靠韩侂胄的。蒋先生对这篇诔文作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蒋先生的文章说,此文是“真诚恸哭,感动天地”。我个人的阅读感觉和蒋先生完全一致。吊祭文章,哪在于篇幅长短?陆游的这24个字,写得真是好,把他对朱熹的景仰、同情写得淋漓尽致。何况,古人本来就追求文字简练,当年孔子吊吴季札就是一句话:“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谁敢非议说孔子诔文写得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史实的考订跟文本的准确解读,就是蒋先生这篇文章最大的优点。
由于这篇文章涉及一个重大的话题,我本人还有一点相关的思考。我们现在研究古人、评价古人,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史书,或是史料。但是问题是,史书也好,史料也好,并不都是可靠的。关于史书的撰写,意大利的克罗齐说得很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都是当代史?就是史书的撰写一定含有撰写者本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一定是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宋史》就是元朝人的判断,而元朝人编《宋史》的时候,朱熹的理学已经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一定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如果他们觉得某人跟朱熹的理学宗派有一点不和,那么此人在《宋史》中一定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于陆游的记述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其实古代的史料中固然有许多真的材料,这是非常宝贵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也有许多虚假的乃至恶意伪造的假材料在里面。我联想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话,陈先生给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上课,他的教案后来被编为《史源学杂文》。陈垣先生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就引用《诗经·郑风·扬之水》中的两句话:“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你们不要轻信别人的话,别人是骗你的。就是白纸黑字的史料完全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恶意编造的。其实,陆游如此,朱熹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以同样的角度来回顾朱熹的话,见于白纸黑字的史料就有当时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大罪状。里面说朱熹把两位年轻貌美的尼姑占为己有,纳为妾;甚至说朱熹给老母亲吃糙米,自己却吃精米。这么荒唐的罪证都虚构出来了,所以白纸黑字不一定可靠。蒋凡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引用史料并不是有见即书,而是经过考核的。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第二点感想,即使没有虚假的材料,朱熹的门人、朱熹的后学、整个理学宗派,他们对于宋代历史人物的评判是有偏见的,门户之见比较严重。清人张佩纶曾经提到过,朱熹对苏东坡有比较多的批评,他认为,朱熹对苏东坡的评价没有心平气和,没有实事求是。他下面有一句感叹说:“虽大贤如晦翁犹不得其正。”朱熹是大贤,但他门户之见太深,太遵守二程的传统,所以对一些“异端”的人物就不能心平气和。蒋先生的文章里还引用了袁枚的一段话。袁枚虽然是才子,但是他作为学者有的思考还是非常好的,他说:“宋以后清流之祸,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就是这样一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愈演愈烈。这实际上就是指明末的东林党,东林党人跟南宋的理学宗派差不多,就是排斥异己非常苛严,缺乏宽容的精神。我们承认,宋代理学家是君子,明末清流东林党人也是君子,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绝对不宽容的态度造成了很多现实政治中的失误,也造成了人物评价上的失误。这就是蒋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我的一些启发。我觉得像这种重要的课题,学界还会不断地提出讨论,而我们的每一次讨论并不是说一下子就会得出一个定于一尊的定论,但是每一次讨论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这正是我们要办一届又一届的学术讨论会的宗旨。
还有一篇我感想较多的就是赵惠俊先生的《渭南文集所附乐府词的编次与陆游词的系年》。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很好的思路,以前我们讨论包括《钗头凤》在内的陆游词的系年的时候,一般是“就词论词”,但是他考察《渭南文集》,认为《渭南文集》篇目的前后次序是陆游手定的,前后次序是符合真的年月顺序,并认为《文集》中所附录的词集也是陆游手定,所以它的写作次序也是符合系年先后的。这样一来,他就认为《钗头凤》这首词介于陆游在四川时所写的四首词的中间,也应该是那个时候写的。也就是说《钗头凤》这首词不是在唐琬生前写的,是在唐琬身后写的,是陆游回忆当年的爱情悲剧,是一种追忆的书写。说实话,我初读这篇论文,一读到内容提要,就吃了一惊。我在前两次陆游研讨会上曾经点评过高利华教授研究《钗头凤》真伪的一篇文章,我曾经引用过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为什么引用这句话呢?我当年读到吴熊和先生否定《钗头凤》跟唐琬有关的文章的时候,也曾大吃一惊,而且心里很痛苦。所以我引用王国维的一句话,王国维年轻时读哲学,他说:“大抵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就是我们明明喜欢的结论,偏不可信;可信的结论呢,我们又实在不喜欢。所以我刚读到赵惠俊先生论文的内容提要时想:又来否定《钗头凤》与唐琬有关了,要把高利华教授好不容易才确立下来的、我认为已经定论了的一个观点又给推翻了,可爱者又不可信了。后来细看全文,原来不是这样,他认为《钗头凤》还是与唐琬有关。陆游四首词中的另外一首明确说到,回忆的是30年前的情事。就是陆游写的并不是他从南郑到成都这一段经历中的风流经历,不是现场书写,而是对往事的追忆。这个结论并不影响我们对《钗头凤》主题的解读,唯一要修正的是,它并没有题在沈园让唐琬读到。这篇文章又把关于《钗头凤》的讨论重新提出来,恐怕高利华教授还要继续写文章来申论你的观点。我当然是希望你能赢,证明它确实是题在沈园壁上的,但是学术就是学术,我们的感情取舍不能决定学术研究的结论。
这篇文章也使我有一些联想。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宋人笔记中有些记录是不可靠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例子就是朱熹迫害严蕊的事情。严蕊的《卜算子》被胡云翼先生选入《宋词选》,《宋词选》印数达100多万册,不胫而走,家喻户晓,有的读者根本不知道朱熹是谁,读了这首词后就骂朱熹迫害严蕊,他们把严蕊塑造成一个刚烈的女子,说这首词如何歌颂爱情。实际上学界早就已经证明这首词不是严蕊写的,严蕊也不是一个可敬可佩的奇女子,所谓朱熹迫害严蕊完全是一个冤案。这就涉及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的问题。像这个公案,我认为学界已经彻底搞清楚了。在束景南先生写《朱熹年谱长编》以后,已经把这个问题无可辩驳地说清楚了,《卜算子》不是严蕊所作。但是,读者不知道啊,我们的学术成果不为社会所知啊。2011年我在《文史知识》上写了一篇短文,我的文章的标题就是陆游的一句诗“死后是非谁管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一个人死后的事情就管不了了,人家说长说短也没办法反驳了。陆游当年感叹蔡中郎,想不到自己死后也是这样,朱熹死后、白居易死后都是这样。我这篇文章就是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严蕊的问题;第二个是所谓的白居易写诗讽刺关盼盼,以致关盼盼自尽的事情,其实也纯属子虚乌有,学界早就证明了的。但是民间不知道,社会上不知道。现在大家如果到网上看一看网友们的言论,有无数网友同情严蕊、同情关盼盼,把愤怒的口水吐在朱熹、白居易的脸上。我觉得我们学界应该要有点声音,我们的学者不能埋头在象牙塔里面,不能认为自己清楚就好了,问题是广大的民众都不知道你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那里说一些不准确的结论,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价值何在?我认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古典文学广为人知,让她的价值深入人心。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者,我们陆游研究界的同仁们,以后在写那些高深论文的同时也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大家也要向民众讲一讲陆游到底怎么回事,苏东坡到底怎么回事,让我们的研究成果广为人知,这是我们学术事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总的来说,我认为本次大会的会议论文的成就非常大。作为单个古代文学家的研究学会,一次会议能提交这么多篇论文,而且其中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可以作一些自我肯定。
我对本次大会的总结就到此为止。会议很短,天下本无不散之筵席,会议到中午就要结束了,代表们也要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我们的学会现在已经走入正规,下一次会议将在芜湖由安徽师范大学主办,希望在座的代表以及热心陆游研究的朋友们到芜湖去相会。陆游平生走过很多地方,他晚年寓居山阴时写过两句诗:“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在陆游足迹所及的地方中,我们已经在汉中举办过会议,下一次在芜湖,也是《入蜀记》里写到的地方。我预想,以后在江苏的镇江、四川的乐山、福建的福州、浙江的严州都可能举办陆游研讨会。当然,由于陆游一生中有半个世纪生活在绍兴,绍兴就是陆游研究最得地利、最接地气的地方,我们在若干年以后还会把会议再办回绍兴。我相信,到那个时候,陆游的三山故居已经修缮好了,沈园里的陆游纪念馆也建好了。所以,下一次在绍兴开会,我们既可以参观三山故居,又可以在沈园里设一个会场来讨论陆游的《钗头凤》。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张玲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0-0016-05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0.004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简介:莫砺锋(1949-),男,江苏无锡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晋唐笔法的传承
- 《兰亭序》文本的文化性意义
- 读《渭南文集》启文札记
- 简论鲁迅小说《示众》的电影化手法
- 董玘与徐阶因缘略论
- 夏承焘劝悔词研究